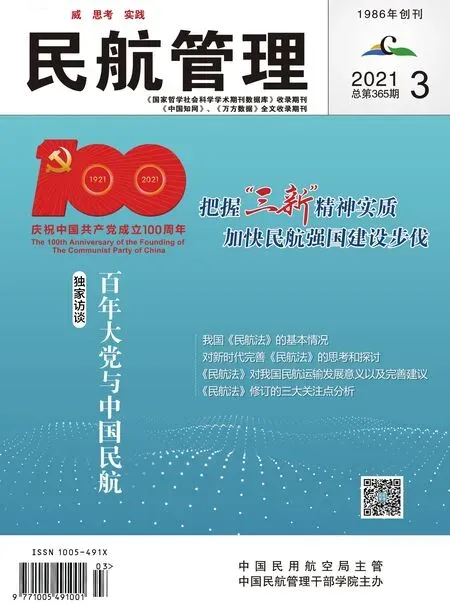我国《民航法》的基本情况
2021-12-07中国民航局吉大鹏
□ 中国民航局 吉大鹏/文
199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民航法》,建立了新中国民用航空领域的基本法律制度,构建了我国民航法律法规规章体系(以下简称“民航法规体系”)的框架,奠定了民航业依法治理的制度基础。《民航法》实施25年来,我国形成并持续完善民航法规体系。以《民航法》为龙头、若干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共同构成的民航法规体系,是改革开放以来民航业发展取得的最为重要的制度成果,有力保障并引领了中国民航的安全和发展。实践证明,现行《民航法》是接轨国际民航、符合我国民航发展实际的一部良法。
《民航法》的制定历程
旧中国民航领域立法已经有所实践。作为1919年首部国际航空公约——《空中航行管理公约》(1919年《巴黎国际航空公约》)的签字国,中国在航空事业初创阶段即将“拟定航空法规”作为重要议题。北洋政府航空署起草了《中国航空条例(草案)》186条,是迄今可见中国最早的航空法规草案。原拟1923年公布施行,因担心机场设备缺失难以应付各国飞机来华,被迫暂缓,终至流产。1941年5月,国民党政府公布了《航空法》八章67条,该法第五条规定“军用航空器、航空站、飞行场及航空人员不适用本法之规定”,可算是中国历史上首部、旧中国惟一一部民用航空法律。此法颁行时战事正酣,公布后并未施行。
新中国民航领域立法探索一直持续。1949年9月,《共同纲领》第四章第三十六条将“创办民用航空”明确规定为新中国关于交通领域的基本政策。1950年11月1日,毛泽东主席签发、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布了《飞行基本规则》,这是新中国首部航空法规。195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了《统一国际航空运输某些规则的公约》(1929年《华沙公约》)。1959年,曾启动包括《航空法》在内的航空法规起草工作。1974年,承认了《国际民用航空公约》(1944年《芝加哥公约》)。
改革开放以来民航立法取得历史性成就。颁布新中国首部《民航法》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1979年4月4日,中央政法领导小组委托外交部部署一批涉外法律的起草,其中起草《航空法》的任务由当时的民航总局承担,这是《民航法》立法工作的起点。民航总局成立专门的领导小组和起草工作组,在众多领导同志、民航专家、法学家以及工作人员长期的艰苦工作下,数易其稿,两次上报国务院。当时的国务院法制局开展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组织多名法学家开展论证,1995年将《航空法》草案改名为《民航法》草案并提交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1995年6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审议通过。6月23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次会议进行了第一次审议,时任民航总局局长陈光毅受国务院委托,就草案向常委会进行了说明。委员们对草案提出了不少重要修改意见,为常务会采纳(比如现行法第四条、第九十五条等)。10月23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进行了第二次审议,10月30日通过并公布。
《民航法》的主要内容
现行《民航法》共16章、215条,除总则和附则外,分章对民用航空器国籍、民用航空器权利、民用航空器适航管理、航空人员、民用机场、空中航行、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公共航空运输、通用航空、搜寻援救和事故调查、对地面第三人损害的赔偿责任、外国民用航空器的特别规定、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法律责任作规定。主要内容有三方面:
规定我国民航活动的基本制度。民航包括公共航空运输和通用航空“两翼”,第八章至第十章规定的“公共航空运输企业”“公共航空运输”以及“通用航空”,这是《民航法》其他各章节制度围绕的中心活动。公共航空运输制度主要包括: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制度(第九十二至九十四条)、“真情服务”的要求(第九十五条)、运输规则(第八章、第九章)、承运人责任(第九章第三节)等。通航制度主要包括:通航定义(第一百四十五条)、通航经营许可和非经营性通航登记制度(第一百四十六、一百四十七条)、第三人责任险(第一百五十条)。
规定民航安全管理的基本制度。 “两翼齐飞”并确保飞行安全,取决于“人机环”等诸多因素的共同配合,《民航法》根据我国长期实践经验,借鉴国际通行做法,从航空运输工具速度快、风险大和技术要求高的特点出发,将安全管理置于民航行政管理的首位,从安全有序组织航空活动所需基本保障条件入手,将包括行政许可等事前监管在内的各类安全管控措施,落实到民用航空器国籍登记和适航管理(第二、四章)、航空人员执照和机组管理(第五章)、民用机场建设和使用管理(第六章)、飞行保障与管理(第七章)等各运行环节,同时,对发生紧急情况后的搜寻援救和事故调查(第十一章)、第三人保护(第十二章)也有相关规定,较完整地构建起了中国特色民航系统安全管理法律制度。
规定民航涉外领域的法律制度。航空活动具有天然的国际性,《民航法》最大限度地与我国已经批准或者加入的民航公约规定相一致,吸收了我国尚未批准或者加入但内容合理的有关规定,体现了我国民用航空事业与国际接轨。第十三章专门对外国民用航空器相关活动做出特别规定,明确了外国人经营的外国民用航空器在我国从事活动的法律适用(第一百七十三条)、飞入飞出我国领空(第一百七十四条)、经营国际航班运输(第一百七十六、一百七十八条)以及安全管理(第一百八十一至一百八十三条)等制度;第十四章规定了涉外关系的法律适用。
此外,《民航法》较妥善的处理了民用与军用航空之间的关系。传统航空法调整内容主要是民航法律关系,各国皆然。由于空域是组织开展民航活动必须的前提条件,合理安排相关制度及飞行规则是立法过程无法回避的问题。从公开的草案说明看,国务院提交全国人大审议的草案文本有法律适用范围的条款,明确“本法适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民用航空活动”,但是现行法并无该条。对照第七章“空中航行”的具体条文可以了解到,不规定适用范围恰恰是符合法律文本和管理实际的选择。该章规定了涉及民军航关系的空域管理原则(第七十条、第七十一条)以及适用于所有航空器的飞行要求(第七十三条、七十六条),将空域具体办法、飞行规则和军民合用机场管理办法,明确规定由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另行制定(第七十二条、七十六条等);总则更是从国内法角度首次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领空”及“领空主权原则”(第二条)。《民航法》在主要规定民用航空法律制度的同时,也规定了需要各类航空活动遵守的法律规范,因此,将现行《民航法》称为新中国首部航空和民航领域的基本法律并不为过。
《民航法》的修订情况
法律制度要发挥权威性、确定性的作用,必须适度稳定,不宜频繁变动,更不能朝令夕改。然而,法律制度又绝非静止不变,稳定性是相对的,新陈代谢不可避免。法律制度要保持生命力,必须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与时俱进。根据发展变化,对法律适时进行“废、改、立”,既有现实必要,也是加强法制建设和增强治理能力的题中应有之义。
《民航法》颁布以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已经进行了五次修正。五次修正突出的特点有三个:一是每次仅对局部个别条款作出调整,二是改动的条文内容比较急需,三是通过国家“一揽子打包”修法方式进行。为区别于对《民航法》进行的全面修订,我们将这五次修正称为“局部修订”。
第一次修正(2009年)。根据2009年8月27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部分法律的决定》,修正涉及两个问题10处修改:一是解决与1997年修订后的《刑法》不衔接的问题。修改了民航法第十五章法律责任当中的9个条文,将适用刑法的表述统一修改为“依照刑法有关规定”。二是与2005年新制定的《治安管理处罚法》衔接,将1个条文中的《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修改为《治安管理处罚法》。
第二次修正(2015年)。根据2015年4月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等五部法律的决定》,修正涉及三个问题5处修改:一是依法开展国际运价审批改革。删除国际航空运输运价的审批规定。二是将公共航空运输企业经营许可与工商登记脱钩,由前置审批改为后置审批。修改了包括法律责任在内3个条文。三是落实价格改革的要求。将机场及其助航设施使用、服务收费标准的制定权交由民航主管部门单独实施。
第三次修正(2016年)。根据2016年11月7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十二部法律的决定》,修正涉及1处修改:贯彻依法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的要求,取消了领航员、飞行通信员资格认定。
第四次修正(2017年)。根据2017年11月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等十一部法律的决定》,修正涉及1处修改:落实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要求,将申办通用航空经营性许可证涉及的工商登记改为“先照后证”。
第五次修正(2018年)。根据2018年12月29日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修正涉及三个问题3处修改:一是落实机构改革涉及出入境检验检疫管理事项调整要求,删除了《民航法》中一处有关“检疫”的规定。二是根据国务院有关通用机场分类管理的要求,将非公众开放的民用机场的许可管理调整为备案管理。三是为无人驾驶航空器监管立法提供法律依据,在民航法作出授权性规定。
实践证明“局部修订”的方式优点明显。一是坚持问题导向,目标聚焦,便于达成共识。二是程序简便,工作高效,立法速度有保障。有人形象地称之为“小步快跑”。《 民航法》五次“局部修订”共涉及十个问题20处修改,条文总数由214条增至215条。面对国家立法资源稀缺的现状,此种方式,既有利于落实国家法制统一的要求,又为行业急需的立法事项提供了“快车道”。在推动《民航法》全面修订工作的同时,要高度重视此种方式,发扬“水滴石穿”的精神,积少成多,勿以“步小”而“不为”。目前,第六次“局部修订”正在研究中。
做好“局部修订”的同时,《民航法》“全面修订”从1999年起一直在持续开展。法律全面修改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涉及领域广、主体多、利益关系复杂,工作进程法定性、程序性很强,既区别于前述“局部修订”,也不同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的修改。持续推进《民航法》修订工作,要有“十年磨一剑”的恒心,要把握和处理好修法与推进改革、修法与新法制定、修法与法制统一等关系。
《民航法》全面修订是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工程。作为民航法治工作人员要进一步增加使命感和责任感,积极推动《民航法》全面修订早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