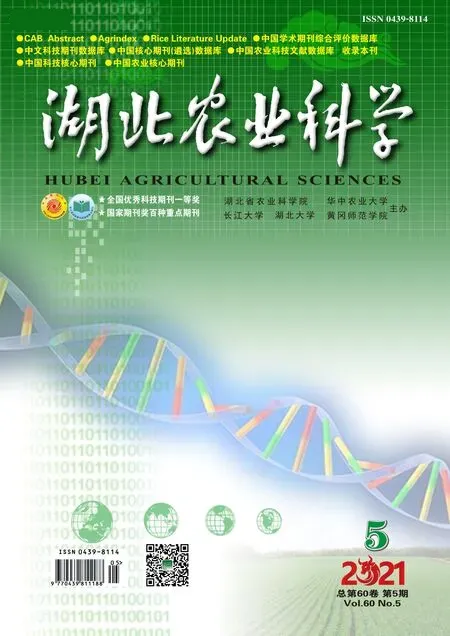经济发展中贫困人员身份识别的理性辨析与时代构建
2021-12-07叶世斌
叶世斌
(河池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广西 河池 546300)
2019 年底暴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疫情)引发全球性的公共卫生危机,导致全球范围内出现大规模停工、停产现象,并导致失业率上升,特别是暂时性失业的大规模出现。为了缓解危机中失业人员、低收入群体的生活压力,各国都实施了相应的纾困计划:一是直接针对全体居民发放现金;二是针对一些特殊群体的人员发放现金,如特定年龄段的居民、具体标准下的低收入群体、失业人员等;三是识别出已经或可能陷入困境之中的人员,实施有针对性的救助。针对处于困境中的人员展开的救助工作,也就是一般意义上的反贫困工作,贫困人员的身份识别要么是按照收入标准将贫困人员划分为极端贫困、相对贫困等,要么是按照衣食住行等基本生活条件是否得到了保障进行分类。据此,在反贫困中对不同群体的帮扶救助方式、程度也会相应的有所不同。
1 传统社会各国对贫困人员的身份识别
1.1 中国古代对贫困人员的身份识别
中国古代反贫困思想主要体现在慈善领域,《周礼》记载的古代慈善“保息六政”,具体内容包括“慈幼、养老、振穷、恤贫、宽疾、安富”六项,在分类上虽然存在部分重叠,但是这种分类方式就是一种对贫困人员的身份识别。这种分类思想几乎贯穿中国古代社会救济的始终。一是养老,对需要照顾老年人的家庭进行税收减免,降低家庭负担。西汉时期有规定“年龄超过80 岁的老人,免除两个儿子的人头税”[1]。二是慈幼,设立机构照料弃婴,并对无力养育婴儿的家庭予以补贴。如宋代设立居养院来养育婴儿,并设立举子仓,主要功能是对产子之家提供生活救助,减少弃婴事件的发生[1]。三是疾病救助,对有医疗需求但是经济困难的群体提供帮助。汉代王莽执政时期,“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1]。宋代更是设立了安乐坊、安济坊、施药局等机构来保障。四是丧葬救助,本族贫困家庭有丧事的,宗族成员要提供帮助,宋代更是设立漏泽园,专门负责掩埋代葬。这些政策既满足了贫困家庭的丧葬需求,也可以避免一些家庭因丧葬陷入更加贫困的境地。五是灾荒年的赈灾措施。赈济的种类主要包括赈谷、赈银、工赈三项[2],这三项政策与如今对贫困群体发放财物和安排工作或者提供政策支持扶持其自主就业是同样的思路。中国古代这种需求导向的分类救助就是一种早期的贫困人员身份识别,救助的范围为几乎属于没有援助就无法生存的“赤贫者”。中国古代这种对贫困人员的身份识别模式,也是为了便于有效地利用社会资源,有针对性地解决部分社会群体面临的困境。
1.2 西方国家对贫困人员的身份识别
14 世纪的英国贫困问题凸显,当时英国对穷人进行了分类识别,第一类是无劳动能力的穷人,第二类是遭遇不幸事件而变成穷人的,第三类是那些放荡成性、不可救药的穷人[3]。1601 年《伊丽莎白济贫法》颁布,对特定的贫困人员进行救助,同时对流浪行乞的人员进行严格约束,“游荡和行乞者一旦被宣布为流浪者,治安法官有权当众鞭笞他们”[3]。当时社会的观念是有劳动能力的都应当工作,穷人当中有很多无赖和恶棍等,所以需要对贫困人员进行身份识别。英国的济贫思想主要关注的是谁需要救济以及谁值得救济的问题。美国的济贫制度最早是沿袭英国《伊丽莎白济贫法》思想,体系上十分完备,具体的济贫项目都非常具有针对性,体现出对贫困群体的精准识别并实施相匹配的帮扶。如抚养未成年儿童家庭补助专门帮助单亲家庭、残疾人家庭或双亲处于失业状态并在积极寻找工作的双亲俱全家庭;补充保障收入主要面向老年人、失明人士和重残疾人士等,并且在申请者的资产方面有具体的规定;食品券计划一般要求家庭财产低于2 000 美元[4]。这些政策对受益者的身份都做了非常细致的识别,并非粗放型的直接发放补贴。17 世纪,法国开始建立贫民习艺所,老年人、病人、妇女和儿童被关在贫民习艺所,同时探索对贫民加以区分的办法,并对愿意就业者给予工作机会,设立公共救助的总机构,对未能获得工作的壮健贫困人员提供工作[5]。瑞典的早期社会救助主要针对低收入家庭、无失业保障的失业者、无健康保险的患病者、因带孩子而不能工作的群体等[4]。
2 传统社会贫困人员身份识别的缺陷及修正
2.1 传统社会贫困人员身份识别的缺陷
一是歧视受助者。英国《伊丽莎白济贫法》的出台背景就是把贫困的成因归咎于个人原因,对贫困人员进行身份识别,对个体的贫困状况、致贫原因进行全方位的审视,特别强调对贫困个体的道德评价问题,如懒惰、浪费等。他们认为,不少穷人是有劳动能力的,他们的贫穷是自身懒惰造成的,因为懒惰又造成自己的妻儿衣食无着,导致社会又不得不耗费资源去救助他们的妻儿。因此,17 世纪的英国依然有人反对给贫民提供救济,提出“饥饿是强迫人们干活的最好的办法”[3]。二是身份识别成本太高。身份识别意味着要调查清楚具体人员的贫困状况,开展此项调查本身需要耗费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此外,进行了身份识别,自然要对贫困人员不同的脱贫需求进行差异化的救助。为满足对应的需求、采购物资、运输、组织人力去发放都会产生成本,尤其在第一阶段的调查并没有真正摸清每个贫困人员的真实需求,情况会更糟糕,识别不准确可能会出现更加严重的资源浪费。三是身份识别不全面且具有滞后性。传统社会进行贫困人员身份识别主要关注那些比较明显的贫困现象。如中国关注老人、幼童的照料、疾病救济、丧葬救济等方面;英国关注流民问题;美国关注包括残疾人、退伍军人、老人小孩的救济或养育问题。在这些标准体系之外,可能还存在着因为其他原因致贫的群体。此外,旧的标准体系对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制造出新的事业失败者、新的穷人是无法识别的,只能在他们陷入贫困处境以后才能被发现。
2.2 建立全面保障体系替代贫困人员身份识别
传统社会把贫困认定为是个人因素导致,以此为前提进行的贫困人员身份识别和开展的救助没有能够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结构调整、资源配置体系变化等问题导致任何身份的人都有可能陷入贫困境地。随着技术进步带来的各行业、职业岗位的变化,不能及时跟上这种变化的将会被就业岗位暂时性淘汰,成为失业人口并有可能陷入贫困。既定的标准体系就不能总是全面识别并帮助真正的穷人,解决方案应当是建立一个全员的社会保障体系。这种思路在制度层面得到了体现,德国在1883 年出台了《疾病社会保险法》、1884 年颁布《工伤事故保险法》、1889 年颁布《老年和残疾社会保险法》、1911 年颁布《职员保险法》、1923 年颁布《帝国矿工保险法》、1927 年颁布《职业介绍和失业保险法》[5]。在这之后,法国、英国、瑞典等国家先后出台了类似的法案,这些法案主要包括工伤、养老、疾病和失业保险4 个方面。这个保障体系基本涵盖了所有人员的所有需求,任何可能导致特定人员陷入贫困境地的情况他们都设想到了,并且预先设定了保障的方案,这个体系几乎就是针对传统社会救助模式的种种缺陷来设定的。
2.3 全面保障体系的缺陷
全面保障作为体系完备的社会安全网络,的确起到破解贫困、保障所有人的养老、医疗、失业等诸多方面需求的作用,但是即便是在保障体系非常完备的发达国家,贫困问题依然存在。在美国,截至2016 年,950 万每年至少工作27 周的工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生活窘迫或极端接近贫困线[6],有劳动能力的人只会在失业的情况下才会陷入贫困,全面保障体系的制度安排就是避免这个群体失业或者在他们失业以后提供补贴、再就业培训等。但忽视了2 个问题:一是即便他们没失业,也有可能因为家庭成员或者自己某些方面的开支加大而陷入贫困;二是灵活就业人员,他们不在失业统计的范围之内。实施全面保障的英国、瑞典、德国、美国等国家都出现了福利开支过高,甚至导致国家财政危机的问题或者是劳动群体个人负担过重的问题。在智利,职工交费比率不断上升,有些部门已达到职工月收入的50%[5]。全面保障体系是一种模式化分配,它预先设定一个标准,只要符合标准就能领取相应的补贴,而现实当中总会有人灵活变通,尽量让自己符合标准,以便能从社会保障体系里面捞取好处。这会导致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不主动承担社会责任和家庭责任,不劳而获者反而过得挺好,这就是英国《伊丽莎白济贫法》制定者们所担忧的问题。
3 科学的贫困人员身份识别可以抵消现有保障模式的缺陷
3.1 尊重了国家财力的客观性
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背景下,对贫困人员进行身份识别需要经历实践的检验,跳出原有的思路,不断地予以修正。传统社会的救助模式保障范围太窄,没有能够覆盖尽可能多的贫困群体,在进行贫困人员身份识别时,对道德上有瑕疵的群体采取抛弃甚至惩罚的态度,并不能真正解决贫困这一社会问题。目前中国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但是人口老龄化、城乡结构发展变化、经济发展预期等因素都会对制度体系的进一步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美国目前在社会保险项目上花费约2.7 万亿美元,仅社会保障1 项就耗费1 万亿美元[6]。中国的现状决定了不可能按照这个方向去发展社会保障事业。全民基本收入显然可以省去扶贫的工作成本,直接解决穷人的生活问题,让他们有更多的选择,可以去做想做的和适合自己做的事情,但是更难解决的财政负担问题随之而来。而以贫困人员身份识别为前提的社会保障模式,可以很好地缓解国家财政入不敷出的问题。
3.2 准确识别了贫困人员的需求
脱贫需求的核心是生活得到改善,具体哪些方面需要优先改善、哪些方面是特定贫困群体最需要的,判断不准确就会出问题。在一些扶贫项目中,慈善机构的初衷确实很好,但他们的努力似乎没有成效,甚至产生浪费,几乎所有的实物捐赠,包括食品、服装、教科书、水罐和卫生用品等都存在这种问题[6]。因此,满足贫困人员脱贫需求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统一,也是多样性与一致性的统一。一些贫困群体的收入事实上已经能够满足基本生活,但他们的支出不合理,存在把有限的收入用于人情开支、赌博、购买烟酒等非必要消费,旁观者一般会对穷人的这种非理性消费持批评态度。事实上,紧迫的财务方面的担忧会对人分析问题的能力产生影响,越穷的人越难以做出理性的判断、合理制定消费计划。大量记录显示,发展中国家的穷人会花很多钱来置办婚礼、嫁妆、洗礼等,这很有可能是怕丢面子的结果[7],对他们而言,这些事情甚至比食物更重要。穷人因为生存压力过大,更喜欢赌博、玩游戏、抽烟喝酒、看电视,他们不像富人那样有更多的途径去缓解压力,事实上富人的生存压力比穷人小得多,这说明贫困人员在精神生活、社交生活上有较大的需求。特定的人员在特定时期究竟要通过何种途径才能脱贫,并没有可以照搬的方案,系统化的帮助并不见得符合其需求、让其成长。
3.3 兼顾效率与公平,杜绝资源错配
类似于全面保障体系的模式化分配制度,不仅有可能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以捞取好处,而且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的保障体系,本身还需要耗费较大的财政投入。劳动者努力工作为社会保障体系提供了资金,工作越努力的劳动者贡献越大,而保障的对象却包含所有社会成员,养懒汉式的社会保障模式肯定不符合提升社会生产效率的要求。僵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勤奋的劳动者而言是不公平的,会挫伤他们的劳动积极性,进而影响社会的生产效率,但忽略贫困群体的需求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其贫困往往是社会因素造成的。一个有劳动能力且愿意努力工作的人如果处于贫穷境地,大概有3 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先天的不平等,没有继承到足够的财产和机遇;二是后天的不平等,社会分工和竞争造成他的收入低;三是家庭负担;3 个因素都不是个人能够很容易解决的。罗尔斯提出,所有社会价值——自由和机会、收入和财富、自尊的社会基础都要平等地分配,除非对其中一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平等分配合乎每个人的利益[8],否则,不平等将会加剧贫困人员的恶劣处境。若对贫困现象视若无睹就是忽视公平,而全面保障会导致效率低下,只有以贫困和贫困人员身份的精准识别为前提采取的救助措施,才能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实现社会资源的合理配置。
4 贫困人员身份识别经验对危机应对的启示
4.1 社会危机冲击下中美的救助政策对比
新冠肺炎疫情波及全球,许多国家为防范疫情传播被迫停工停产,引发社会失业率上升。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20 年1 月和2 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5.3%和6.2%,环比分别上升0.1 和0.9个百分点[9]。受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蔓延影响,美国3 月失业率从上月的3.5%升至4.4%[10]。单看2个失业率的数据,很容易得出一个错误的结论:疫情对中国造成的影响要比美国更大。事实上2020 年1月份,中国失业率明显提高的原因,除了新冠肺炎疫情造成的影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1 月份恰逢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春节期间,许多外出务工人员返乡过年,很多与节庆活动相关度不高的工业、服务业、个体工商户等都会停业一段时间。因此,中国的失业率上涨并且超过美国,并不完全是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疫情引发的社会危机,导致一部分人陷入困境之中,中美两国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中国的救济政策主要以地方政府为主,各地区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包括发放消费券、举办购物节等模式,保障民生、刺激消费、提振经济。截至2020 年5 月8日,疫情发生以来,全国有28 个省份、170 多个地市统筹地方政府和社会资金,累计发放190 多亿元的消费券[11]。同时交通运输部印发通知,从2020 年2月17 日0 时起至疫情防控工作结束,全国收费公路免收车辆通行费,保障疫情防控和生产生活物资运输[12],这些措施切实降低了生产生活用品的运输成本,对消费品价格上涨起到抑制作用。美国的救济政策包括:为所有失业工人发放为期6 周、每周600美元(约合人民币3 888 元)的补助;为符合收入要求的群体发放刺激支票,其中符合全额补助条件的个人和已婚夫妇将分别获得1 200 美元(约合人民币7 777 元)和2 400 美元(约合人民币15 554 元)的现金补助。其中,个人和夫妇的收入标准低于75 000美元(约合人民币486 075 元)和150 000 美元(约合人民币972 150 元)。这些补贴是根据2019 年或2018 年的纳税申报单或者社会保障金领取情况确定受益人[13]。美国的救助政策可能出现的问题:一是降低失业人员再就业的积极性。失业人员每月可以领取2 400 美元(约合人民币15 554 元)补贴,而美国普通职员平均只有4 万美元(约合人民币259 240元)[14]的年收入,不工作显然也是一个很划算的选择。二是对特定收入水平以下的人员实施现金补贴,固定的收入标准体系必然会导致一部分需要保障的人员被忽略,而一部分不需要保障的人员又领取了补贴,造成资金浪费。
4.2 社会危机冲击下中美的救助政策效果
固定标准体系的无差别救助既不能保障所有困境中的人,也存在浪费国家财政开支的情况。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社会危机冲击之下,这种保障体系还必须发挥促进社会经济秩序恢复的作用。显然美国的模式对刺激消费、促进社会复工复产的正面作用并不明显。而中国奉行“国家统一决策与分级管理相结合”的社会保障模式,社会政策具有明显的地方化特征,应对疫情冲击的现金补助计划也大多由地方政府制定和实施[13],各地因地制宜,实施的促消费与稳就业相结合的模式对保障困难群体、恢复经济活动、稳定社会秩序的效果更佳。2020 年第二季度,中国各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分别为6.0%、5.9%、5.7%,逐步回落[15]。根据2020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可知,国内生产总值相较上年度增长了2.3%。美国劳工部公布的数据显示,7 月美国失业率为10.2%,虽然环比下降0.9 个百分点,但仍处于历史高位[16]。2020 年第二季度美国实际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萎缩32.9%,萎缩幅度远高于第一季度的5%,为1947 年有记录以来最大降幅[17]。社会经济生产活动恢复,失业率下降,大部分因疫情冲击而出现经济困难的人员即可通过就业迅速摆脱困境,减少了政府财政支出用于社会救济的开支。这就是中国的失业率与经济状况在本次社会危机冲击下能够迅速好转的原因。
5 结语
传统社会的差异化救济在价值理念、保障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存在问题,但不是彻底否定这一政策思路的理由。全面保障体系不仅没有彻底解决问题,反而导致国家财政负担过重、严重影响社会生产积极性。当下中国的精准扶贫,从价值理念上体现了对人的尊重、对效率与公平的兼顾、差异性与统一性的结合,在没有大幅度增加社会经济压力的前提下,准确识别贫困人员及其需求,为采取有针对性的救济措施提供了指导。在新冠肺炎疫情所引发的社会危机冲击之下,中国的精准扶贫所倡导的对困境人员进行身份识别的差异化救助模式经受住了检验。差异化救济要拓宽深度和广度,但绝不能走向包办一切的全面保障,更不能推向所谓的“全民基本收入”模式。政策的制定要更加关注实施的实际效果,考虑这种体系的投入与产出的问题而非宏观的社会效应或者是舆论反馈。在经济发展中,对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中心城市面临的相对贫困问题,以及西部省区的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山区面临的返贫风险问题,不能无差别地对所有人实施高标准的全面保障,也不能简单地只做基本生存保障。后扶贫时代的贫困治理,既要做好应对经济社会发展中共通性因素导致的长时期相对贫困与返贫风险问题,也要做好应对各种突发性、偶发性因素导致的个体、区域、甚至全域性短期贫困问题,继续坚持对特定人员的困难状况实施识别,是救助政策有效性的重要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