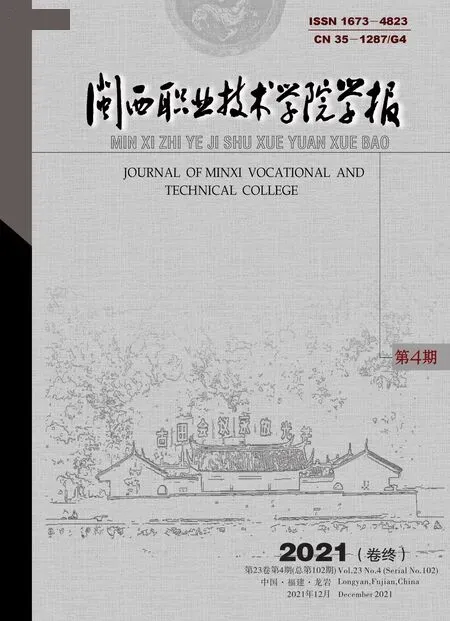苏童对女性悲剧生存境遇的反思
——兼谈《伤逝》《妻妾成群》的叙述差异
2021-12-07王亚琪
王亚琪
(天津大学 外国语言与文学学院, 天津 300350)
《妻妾成群》的情节并不复杂,有人认为它书写的不是“史实历史”,而是“概念历史”,围绕几个已成立的核心概念“男尊女卑”“一夫多妻”等来设定和虚构情节[1]。新历史主义观念下的苏童重写了一个民国故事, 虽然故事的结局没有脱离以往封建家庭的悲剧, 却借由想象看到了这一过程中的斑斓与光怪陆离,以此揭开传统历史对女性形象的遮蔽,还原现代早期日常生活中女性作为人的悲剧命运。
一、揭开历史对女性的遮蔽——欲望与自我
苏童虽是一名男作家,却擅长描写女性,在《妻妾成群》中他细腻刻画了颂莲、梅珊、雁儿、卓云和毓如这些独具魅力的女性。 小说用笔的着力点在于揭示女性的欲望和本能, 叙述女人们围绕性所发生的种种事件。苏童曾自述“在叙述性与性之间呈现这么一种非常‘粘’的勾结、纠缠,以这样的眼光、语气去叙述,一定很有意思”[2],在作品中他细致描写女性的感官、心理活动。
陈家人物之间的关系围绕性的依附、 顺从、竞争、吸引、替代等产生[1],小说的主要情节和矛盾冲突都围绕这些关系的变化与发展展开, 性的欲望力在平静的水面下暗潮涌动。 小说不以露骨的性欲描写为重点, 而以性欲驱动下人物表现的行为和心理活动为重点。 苏童通过场景的情感化渲染与人物活动心理描写的有机结合,传达出女性心底隐秘的欲望。心高气傲的颂莲不愿吃苦而自愿嫁入旧家庭成为一名小妾, 这一决定的出发点是为了物质生活上的满足,但真正嫁入陈家后,她发现自己感受到性的愉悦和阴雨天气的生理需求。 苏童以近似“零度”的叙述笔调描写颂莲的心理活动,十分擅长从视觉、听觉、嗅觉等角度的感官感受对屋内和屋外环境的暧昧与阴暗进行铺设,如“秋天里有很多这样的时候,窗外天色阴晦,细雨绵延不绝地落在花园里,从紫荆、石榴树的枝叶上溅起碎玉般的声音。 这样的时候颂莲枯坐窗边, 睬视外面晾衣绳上一块被雨淋湿的丝绢,她的心绪烦躁复杂,有的念头甚至是秘不可示的”[3]。密闭环境对心灵的压抑与束缚, 无所事事的无聊与寂寞, 迫使颂莲将时间消磨在观察周围的物件和环境中。 除却自身的生理需要,颂莲也懂得利用“在床上的热情和机敏”来迎合满足男主人陈佐千,颂莲很实际,她“有意识地”以争取陈佐千的宠爱来获得依附在男性身上的权力和脆弱的主体地位。
此外, 生育渴望和焦虑也伴随纯粹生理需求而来,它关系着女性的自我生存。女人们千方百计地生孩子生儿子, 因为她们清醒地认识到没有子女会对自己在大家庭中造成生存威胁。 她们对生育的渴望并非所谓的母性自然, 而更多地出于在封建家庭生存的考虑。 女性这种通过利用自然赋予的生育能力来谋求自身生存的行为, 是被压抑束缚的一种女性自我感知和自我保护的行为。 从梅珊和颂莲的对话以及颂莲的内心活动, 可以窥见女性生育的真相与其中包含的残酷。经历桌上风波后,颂莲再次看见自己月经这一正常生理现象后, 她开始对自己能否为陈家生孩子产生特别的焦虑与不安。 这种焦虑与颂莲感受到陈佐千的一次次冷落相伴随, 在遭受冷落的孤独中, 她越发强烈地感受到自己在陈家的一无所有,焦虑与恐惧变得日益严重。而透过三姨太梅珊之口, 她看到为了自我生存, 同为女性却要相互倾轧、谋害。 颂莲“疯女人”的种种表现,反映女性对伴侣唯一性的更深层次占有欲望, 揭示封建一夫多妻制对女性心理的扭曲。
围绕女性的身体欲望、生育欲望和身份竞争,苏童用女性的叙述视角和细腻、富有感官色彩的笔触,通过意识流心理语言描写, 揭示了女性首先作为人所具有的关于性的欲望, 展示女性残酷争斗和挣扎的生存图景——她们之间的相互倾轧, 是女性为实现自我要求的一种畸形表达。
二、女性走向崩溃的精神世界——恐惧与反抗
对《妻妾成群》,苏童曾表示不希望接受者把这篇小说解读成“旧时代女性的故事”或“一夫多妻的故事”,而应将其理解为“一个关于‘痛苦和恐惧’的故事”[4]。他从发生学角度,述说自己创作《妻妾成群》《红粉》是缘于“对旧时代一种古怪的激情”[2]。 在《妻妾成群》中,他将“痛苦和恐惧”凝结在颂莲深层的心理结构之中,让她在与虚无的纠缠反抗中,最终陷入“疯女人”精神崩溃的泥淖。
颂莲发疯的过程是精神崩溃在精神病学病理上的复原,一个在时间上存在积累变异,从精神领域最终到物质性身体都发生彻底混乱的过程。 围绕井这一意象,父亲自杀、后花园墙角井的诱惑、卓云被投井这三件事催化颂莲的发疯。 陈家花园里的井有一种魔力,颂莲住到后花园不久,便注意到墙角那块紫藤花架下的废井。当她一次次走近废井,从最开始的“凉意”、奇怪的感觉到出现幻觉和幻听,中间还穿插陈家发生的其他事件,以致颂莲对这口废井的恐惧日甚一日, 最终随着梅珊那一声沉闷的声响彻底失去理性的控制。
苏童承认自己“对图像的迷恋”,他竭力想通过语言实现表达的“野心”。 他说:“如果我自己要拍电影,我自己也会对我的小说感兴趣,说到底,可能就是因为我对图像的迷恋, 将其带入到了我的小说当中”。[2]苏童用充满感觉的语言表现颂莲精神状况细微、渐进的变化。 借颂莲的叙述视角,苏童调动起各种感官体验来描述她眼里的那口废井, 将敏感细微的感官体验与幻想相结合展现“神经质”特征的人物世界。随着病症不断加深,颂莲逐渐将现实情景与压力下的幻觉混为一体。 陈佐千生日之前颂莲就已经开始出现幻觉和幻听。 一天她到井边,“突然被一个可怕的想象攫住,一只手,有一只手托住紫藤叶遮盖了她的眼睛, 这样想着她似乎就真切地看见一只苍白的湿漉漉的手,从深不可测的井底升起来,遮盖她的眼睛。 颂莲惊恐地喊出了声音——手,手。 她想返身逃走,但整个身体好像被牢牢地吸附在井台上,欲罢不能,颂莲觉得她像一株被风折断的花,无力地俯下身子,凝视井中。在又一阵的晕眩中她看见井水倏然翻腾喧响, 一个模糊的声音自遥远的地方切入耳膜:颂莲,你下来;颂莲,你下来”[3]。 这段叙述十分密集, 充满紧张感, 将颂莲脆弱的神经铺展得一览无余。 回到房间后,颂莲精神世界的动摇仍余波阵阵,客观存在的井已成为负载压抑与黑暗的恐怖意象,并进一步引发颂莲对自身存在主体的本质性思考——“她颂莲又是什么? ”而这一思考又成为加速颂莲走向精神崩溃的助推力和催化剂。
之后集中描写颂莲对井的幻觉主要有两处。 一处是颂莲听梅珊在井边唱戏,“她听见井水在很深的地层翻腾,送上来一些亡灵的语言……‘我怕。’颂莲这样喊了一声转身就跑”[3]。 另一处是颂莲得知雁儿死去的消息后,因为内心充满自责与内疚,颂莲再一次想到废井和井中的手。 颂莲经常向周围的人探询这口井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她了解这口井的用途,但她一直拒绝相信,不断进行自我认知的否定。废井的传说在另一个维度上加深颂莲的恐惧。卓云、陈佐千、 梅珊和宋妈等人对废井的传说都表达得含糊不清, 这种暧昧的态度在陈家后花园这个封闭狭小的空间里,加剧人物的恐惧心理。颂莲幻象与幻听中废井对她的诱惑, 其实是内心对自身命运的预测与恐惧。苏童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一直引而不发,耐心地勾勒颂莲微妙纠结的精神世界, 直到颂莲喊出一声声“杀人”,反复重复“不跳井”的语言和行为,最后才揭开颂莲埋藏已久的对自身命运和结局的恐惧。 颂莲低估了封建制度和封建家庭,高估了自己的适应性,作为个体的她无法负载历史的重担然后调转方向,依旧只能裹挟在历史的洪流中。
有人指出《妻妾成群》中经常显露出“女人=东西≠人”这个女人也承认的不等定律逻辑[1]。 而女性自身对这一男权话语体系的认同则引人深思: 究竟出于何种原因和目的, 女性要选择如此贬低同性甚至自身?将女性降格甚至物化,其根源是封建环境下男权立场的话语体系, 因此男主人陈佐千在颂莲不能满足自己的性欲时会骂道“没见过你这种女人,做了婊子还立什么贞节牌坊! ” 他甚至将她等同于妓女。在呼吁新文化的时代背景下,以男性为中心的权力话语体系在陈家依旧毫不动摇, 甚至渗透到女性话语当中。由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等级序列关系,女性通过模仿男性来释放被压抑的情感和自我, 颂莲不如意时骂下人雁儿,“连个小丫环也知道靠那一把壮自己的胆,女人就是这种东西”。 而当她在饭桌上显露不悦时,又会被封建家庭的正妻、男性的代言人毓如训骂道,“你也不拿个镜子照照, 你颂莲在陈家算什么东西?”封建等级序列的牢固为矮化和物化女性提供了通道和途径,即使同为女性,也因为所处地位等级的差异而相互之间处于对立甚至对抗的境地。[3]
颂莲毕竟曾经是女学生, 她偶尔也会对自己作为女性的处境进行超越集体无意识的思考, 但无法找到出路的她只会愈来愈感到无可奈何, 于是颂莲回答毓如“说对了,我算个什么东西。 颂莲轻轻地像在自言自语,她微笑着转身离开,再回头时已经泪光盈盈,她说,天知道你们又算个什么东西! ”“女性是什么”问题和废井问题一直困扰着颂莲,在一次与梅珊的对话中,颂莲发出了“我就是不明白女人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女人到底算个什么东西,就像狗、像猫、像金鱼、像老鼠,什么都像,就是不像人”的论述,以一种极端化的表述反映颂莲对女性非人处境的窥视,同时也预示她朝精神崩溃的方向越走越近。颂莲并非没有反抗, 但她的反抗不是将自身推向更加无望失宠的深渊, 就是只能对着四周黑暗的 “无物之阵”发出绝望的呐喊。 颂莲被男主人陈佐千骂婊子后,只能独自在房间“对着黑暗的房间喊,谁是婊子,你们才是婊子”,或者借着酒精骂骂咧咧。 即使最后疯了,颂莲“不跳井”的“宣言”也显得如此苍白与无力,她彻底失去自主的能力,只能做虚无的挣扎。[3]
三、叙述差异中的殊途同归——死亡与疯癫
鲁迅的《伤逝》与苏童的《妻妾成群》,都对20 世纪初新女性的婚姻选择与命运走向、 悲剧性的生存境遇进行反思。 子君与颂莲的选择看似在新与旧上大相径庭, 但背后都存在同样根深蒂固的男性权力话语, 压抑并造成女性对自我主体认识与确立的模糊。 子君和颂莲在所谓“新男性”与“旧男性”的压制下都逐渐对自我产生怀疑、迷茫,以致从“觉醒的女性”再次陷入“传统规定的角色”的认知当中。《伤逝》与《妻妾成群》跨越半个世纪的时空对话展示出一个残酷却异常现实的场景——20 世纪初的恋爱自由、婚姻自由、妇女解放运动等,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两篇小说中的紫藤花只能攀附而生, 意象具有极强的隐喻色彩,投射女性脆弱的命运,正如当时女性依附男性而活的现实困境,子君和颂莲都是如此。《伤逝》中子君和涓生租住的窗外有一株老紫藤和紫藤棚架,在涓生的回忆中子君的到来伴随着紫藤花,“她又带了窗外的半枯的槐树的新叶来, 使我看见,还有挂在铁似的老干上的一房一房的紫白的藤花”“穆然,她的鞋声近来了,一步响于一步,迎出去时,却已经走过紫藤棚下,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5],这种叙述安排将子君的形象与紫藤意象交叠成一体。《妻妾成群》中对紫藤的描写较多,陈家的紫藤在废井的周围,将紫藤和废井在空间设置上联系起来。颂莲第一次近距离走到井边时, 作者进行了细致的描写,“有一阵风吹过来, 把颂莲的裙子吹得如同飞鸟,颂莲这时感到一种坚硬的凉意, 像石头一样慢慢敲她的身体,颂莲开始往回走,往回走的速度很快,回到南厢房的廊下, 她吐出一口气, 回头又看那个紫藤架,架上倏地落下两三串花,很突然地落下来,颂莲觉得这也很奇怪”[3]。紫藤架上毫无预兆、无法把握而跌落的紫藤具有很强的隐喻意义, 象征那些不知名的女眷、“屈死鬼”、梅珊、雁儿、颂莲等女人。
紫藤花意象是两篇小说文本最直接的呼应,而叙述的两极差异——指向男性与指向女性, 则是二者最具对话张力的维度。 《伤逝》的副标题是涓生的日记,小说套用日记的形式,以男主人公涓生为叙述视角, 以男权话语体系为文本指向。 在涓生的叙述中,子君的形象不仅单薄,而且背负着导致两人婚姻走向失败的指责。 《伤逝》对从传统延续至现代的男性本位叙事提出质疑, 对男性启蒙者的优越姿态进行讽刺。而在《妻妾成群》中,苏童选取女主人公颂莲为叙述视角,表现女性基于自身感受的体验。男主人陈佐千出现频率低,描写少。从《妻妾成群》改编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中,陈佐千的出现始终是背影或侧面,不仅没有特写,而且连正面的镜头都没有,与小说的叙述策略相一致[6]。
《伤逝》与《妻妾成群》叙述主体差异是子君与颂莲拥有对自我身体言说权利不同程度的差异。诚然,两人都不具有彻底的自我言说能力, 但子君是彻底失去,而颂莲还有些自我表达。在走向式微的封建家长陈佐千面前的颂莲,与在新文化代言人、启蒙者涓生面前的子君相比, 知识赋予颂莲的优越感与权利无形中影响她刚直的性格, 影响她对自我欲望的表达与抗争。
现代初期妇女解放的浪潮滚滚, 但女性无论选择走哪一条道路,其实所面对的都是充满艰辛的路,生存空间一样的逼仄与狭小。《伤逝》展示了20 世纪初出走的女性“娜拉们”大多数的结果——回归原生家庭,却无法像从前一样平静生活,最终甚至走向死亡。《妻妾成群》是半个世纪后的重谈,再次反思曾高声呐喊的女性解放的不彻底性。 颂莲接受过新式教育, 不可能走毓如的道路, 没有卓云那样的心狠手辣,又缺少梅珊“放浪女人”的胆量,最终只能在夹缝中被逼成“疯女人”。 子君“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 ”的呐喊[5],与颂莲“女人是什么东西”的厉声咒骂都充满深刻的绝望。
苏童曾说,《妻妾成群》是“写一个十八岁的女孩子, 闯入一个她无法应对的世界……况且主要的问题在于,我不是要写三十年代的女人,而是要写女人在三十年代,这是最大的问题”[2]。 《伤逝》与《妻妾成群》 的差异, 还体现在前者有一个约束与限定的时间,而后者则努力突破前者的时间标签,体现新历史主义创作观的内涵:“以当代人对历史的认知来建构或重塑过去, 它是理解历史的结果而非历史本身的结果。”[1]苏童曾说:“在写作时,我试图摆脱一种写作惯性,小心地把‘人’的面貌从时代和社会标签的覆盖下剥离出来。我更多的是讲人的故事。”[7]不仅仅是苏童, 与他同时期的20 世纪80 年代许多作家都体现这种创作风格。苏童在《妻妾成群》中所展现的,是一名男性作家对历史和女性世界富有人性色彩的想象和还原。
从1986 年发表《一九三四年的逃亡》开始,苏童便表现出回溯过去的写作惯性,也表现了其“回忆的诗学”的创作特点。 20 世纪70—80 年代,文学领域从“人道主义”到“人的主体性”,“人学”话语被广泛地讨论。 苏童在《妻妾成群》的创作中对人或女人的强调,都离不开当时文学界、思想界的环境影响。 虽然苏童强调自己欣赏并选择“零度写作”的态度,但丰富的细节描写还是透露出他对历史中女性命运悲剧的反思倾向[8]。
四、结语
《妻妾成群》的意义与价值在于苏童在想象与突围中发现了个体的秘密与历史的遮蔽之间复杂的关系, 进而在发现的基础上推进了作为一位具有女性意识的男性作家所能触及的基于女性身体体验的叙述深度。《妻妾成群》与《伤逝》这两篇小说,在隐秘的对话关系中交相呼应着一个一直未完成的命题——对人与女人内涵和处境的思考。正是这种回望与凝眸的姿态与细腻的女性身体悲剧色彩书写,使《妻妾成群》这篇看似话题古旧的小说,能够在当时各种新作的竞相喷涌中,依旧获得独特而广泛的关注与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