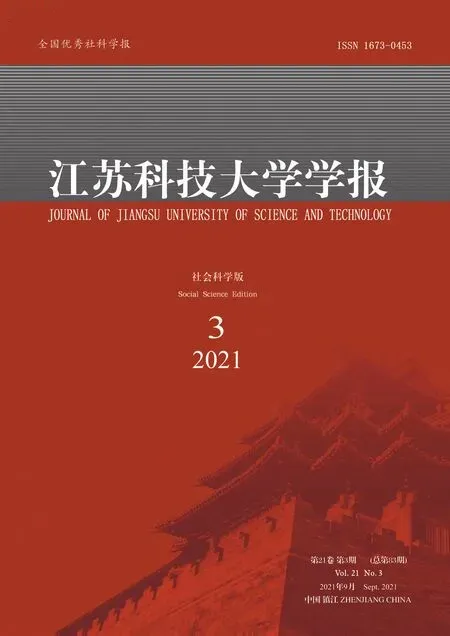安倍政府时期日本媒体右转的原因、实现路径及其影响
2021-12-06邓天奇
邓天奇, 周 亭
(1.中国传媒大学 传播研究院,北京 100024;2.中国传媒大学 政府与公共事务学院, 北京 100024)
二战后,虽然日本在政治体制上采取西式政党政治,但其政党政治存在先天不足,最突出的特点便是政局上的混乱。战后日本的绝大多数首相如同“走马灯”一般,磨合期尚未完成便黯然离场。张宏艳指出,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不同,日本政党政治的孕育和发展与其政治、经济发展并无直接关系,从本质上来看依旧是日本封建传统政治的再延续(1)参见张宏艳《独具特色的日本政党政治》,《攀登》2008年第5期,第123-126页。。既然日本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均有别于西方,那么由政府、媒体、社会三者构建的政治传播生态自然也有别于西方,因此不能简单地将研究西方国家政媒关系的相关范式直接用于对日本政府媒介政策的研究。进入21世纪以来,自民党等日本政党通过媒体进行了大规模的政治动员,日本政治与社会组织、大众传播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极大改变。安倍晋三(Abe Shinnzou)的前代首相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首创了以大众传媒为舞台进行政治表演的“剧场政治”模式,该模式对于稳定日本政治格局起到了巨大作用,也影响了安倍晋三的政治思想。对此,今西光男(Imanishi Mitsuo)指出,安倍晋三虽然基本继承了小泉纯一郎的政治传播思想,但在具体传播策略上却与其存在明显区别(2)参见今西光男《安倍晋三政権とメディアの関係-首相会見が「記者クラブ主導」から「官邸主導」に》,http://gendainoriron.jp/vol.08/feature/f05.php。。安倍尝试发挥媒体对政治的巨大影响力,寄希望于凝聚日本社会情绪化的民意和舆论,借助民族主义以巩固自身相位。鉴于此,必须结合日本特有的政治传播生态与安倍之后剧场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来重新审视安倍政府时期日本媒体右转的原因、实现路径及其影响。
一、安倍政府时期日本媒体右转的原因
所谓的“媒体右转”是指媒体丧失批判精神和监督政府的职能,受到国家与政府的控制,是一种媒体与政府语调保持一致的状态。21世纪以来,剧场化的政治选举深刻影响着日本政局。在安倍两届任期内,日本媒体呈现出不断右转的趋势。
(一) “剧场政治”解构原有的政治传播生态
日本国家政治体制的短周期性决定了日本政治的戏剧性特点。在议会内阁制这一权力架构下,日本政权的稳定性与延续性差,首相居于弱势地位。日本的国家领导人在当选后,其政治得失便会迅速成为公众舆论的热点,许多日本首相均因媒体形象塑造不当而黯然退场。因此,日本的政治选举形成了起擂、对打、离场这一周而复始的循环。
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原有的政治传播生态开始崩溃,原本作为政治传播主要媒介的报纸被强调娱乐化的电视所取代,媒体化的政治开始形成一种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格局。部分政治家从此获得启示,尝试使用诉诸于情绪的直观刺激手法,借助非好即坏、非黑即白的对立逻辑,在电视节目中占据了优势地位,从而成为“明星政治家”。剧场型的政治节目在情绪刺激下获得了日本大众的关注,为电视媒体带来了巨大的广告收益[1]275。
自安倍第二任期后,互联网凭借其开放性、多元性、海量性等特征逐步成为各类信息传播的主要场地,也成为日本剧场政治的全新表演场地,诉诸于情绪刺激的手法得到进一步运用与发展。网络技术与智能技术的不断发展使得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相互嵌套和重叠,为日本社会中的民粹主义思潮及其情绪化言行提供了技术基础。越来越多的日本政治家开始尝试选取“二者择一”的图式,在网络平台上采取“政治简单化”“政策口号化”的方式,以期在日本大众面前树立改革派的形象。这使得日本社会进入了“全员加速”的状态。
(二) 民族主义致使社会思潮走向右倾
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经历泡沫经济后,社会的高度闭塞和大众意识的内向化成为催生新民族主义的温床,整个社会思潮右倾化,以美化日本侵略史、修宪、亲美排华为主要表征的民族主义思潮迅速蔓延[2]。
首先,这一思潮表现在歪曲日本对外侵略史上。1996年桥本龙太郎(Hashimoto Ryutaro)政府执政以来,日本社会开始出现一股否认侵略历史的思潮。在各种民族主义势力的强力推动下,日本政府不顾各方反对,通过篡改历史教科书等方式美化日本的对外侵略行为。其次,日本政府积极谋求改变战后发展路线,试图修改“和平宪法”这一战后日本政治的压舱石。此举加速了日本民族主义思潮的兴盛与蔓延。再次,在对外关系上,日本政府不断加强日美同盟关系,妄图依靠美国实现日本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安倍政府执政后,日本在全球治理和区域合作上不断加强与美国的合作,紧抓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机遇,寄希望于与美国共同牵制复兴中的中国。最后,在对华关系上,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些右翼人士出于转移国内矛盾的需要,大肆宣扬“中国威胁论”与“中国崩溃论”,企图煽动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
安倍政府时期,日本社会各界在“国家利益至上”思潮的“感召”下,倾向于追求“政治正确”,表现出保守化的趋势。特别是在国际竞合与国家利益相关的议题上,社会各界纷纷追随日本政府和自民党,日本媒体也时刻紧跟日本政府的脚步,在涉及政治立场的报道中注重迎合执政党的主流意识形态。
(三) 政府谋求执政长期化以实现国家战略
21世纪以来,日本前首相小泉纯一郎首次打破了日本首相频繁轮替的局面,以政治表演实现了执政的长期化。在小泉纯一郎长期执政过程中,日本的政治家与政党开始注重利用传播工具塑造自身媒体形象。亦即,若想在政治上取得成功,便需要进一步深化并把握政治、媒体、公众三者的关系,充分发挥媒体在政治方面的工具效用。作为小泉纯一郎忠实继任者的安倍自上台伊始便对传播政策进行再检讨,力求强化日本政府在政媒关系中的主导地位,以实现其执政的长期化。
安倍在第一任期内继续沿用了“剧场政治”的常用手法,即通过人为造势来制造影响力[1]350。在该时期内,日本政府希望促使政府议程与媒介议程、公众议程实现同步化,以弥合政府政策与民意之间的沟壑,意欲通过隐蔽的公关团队以专业化手段提升自民党的政治传播能力,进而实现“美丽国家”这一国家战略[3]。在安倍第二任期内,日本的大国之路更多地面临来自外部的战略考量以及中国崛起的挑战。在该任期内,安倍政府将更多的注意力投向了日本的大国化发展这一外向的、民族主义化的议题。为了实现这一政治抱负,安倍政府必须动用行政力量,拉拢更多的媒体服务于政府议程,以建立更加完备的政治传播体系。
(四)日本媒体依附于政治权力的保守传统
回顾日本的大众传播史可以发现,日本媒体对于政治权力的依附早已有之。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作为新生事物的近代报刊就已将自身定位为政府的“翼赞”力量[4]。此外,日本早期报刊的创办者也多为政治家或政党团体。《时事新报》(《产经新闻》前身)是日本新闻史上第一份独立报纸,其创办人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是日本著名的军国主义理论家和政治思想家。该报虽为民办报纸,但政治性极强,其在20世纪前期日本对外扩张过程中扮演了摇旗呐喊的角色。创刊于1872年的《东京日日新闻》(《每日新闻》前身)的创始人福地源一郎(Fukuchi Genichiro)也是一位著名的政治家,与时任日本首相的伊藤博文(Hirobumi Ito)关系密切。此外,《东京朝日新闻》(《朝日新闻》前身)的创刊人村山龙平(Ryohei Murayama)也有深厚的政治背景,他曾被敕选为贵族院议员,获得二等勋章。由此可见,日本几大主流媒体的前身在创刊伊始便与政治紧密勾连,形成了依附于政治的媒体基因。
二战后,日本实施了大规模的民主化改革,对包括大众传播在内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改造。然而此次改革仅仅是在制度架构上将大众传媒列为第四种权力,仍未能完全理顺国家与媒体的关系,媒体依附于政治权力的保守传统并未获得实质性改变。此外,在本次改革后不久,日本右翼势力的代表人物正力松太郎(Matsutaro Shoriki)便重回传媒领域。旧势力不断抬头,再加之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浪潮不断勃兴,引发了日本媒体的再保守化[5]。
安倍政府时期,自民党业已实现强势回归,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再度兴起。由于惧怕中国的区域影响力日渐扩大并担忧日本经济的未来,在日本社会中一些歧视和仇恨等长期被压制的观念再次喷涌而出。在自民党总体保守化、日本政党总体自民党化这一大背景下,日本媒体再次强化了对政府的依附,其保守化趋势更为明显。
二、 安倍政府时期日本媒体右转的实现路径
在当今媒介化的社会中,建构完备、有效的政治传播体系已成为政府和政党的刚性需求。安倍政府顺应了这一时代潮流,确立了一套舆论引导力极强的政治传播机制,通过强化记者俱乐部制度掌握了国内议程设置的主导权,通过运用一系列行政手段笼络媒体以影响公众议程,并打压左翼媒体,甚至试图在立法层面上直接干预新闻自由。
(一) 强化记者俱乐部对新闻发布的垄断
日本的新闻媒体对掌握政治权力的日本政府、执政党、政治团体等新闻源具有极高的依赖性。安倍政府通过强化对记者俱乐部的控制,使其与主流媒体形成 “合流”,保护了右翼团体与个人的既得利益。
虽然日本的记者俱乐部经常强调自身只是一个新闻工作者相互交流的场域,且在名义上倡导“绝不干涉新闻报道”,但其在本质上仍然是政府对媒体施压的手段之一。日本的记者俱乐部制度规定,参加日本政府主导的新闻发布会的前提是必须加入记者俱乐部。这一规定体现了记者俱乐部的封闭性、垄断性与特权性。一直以来,首相官邸的所有采访活动均需永田町俱乐部(内阁记者会)与官邸方面(官房副长官、官邸报道室)进行协调,具体商定首相见面会、官房长官会、政策发表会的日程及规则等细节[6]。永田町俱乐部是日本政治新闻的中枢,由《朝日新闻》《读卖新闻》《每日新闻》以及共同社、时事通讯社这五大传媒集团和日本广播协会的领军记者组成。这些领军记者多拥有10年以上的政治新闻报道经验,且大多与安倍出自于同一派阀,并同期入驻首相官邸。特权政治记者的存在无形中加深了日本政府与主流媒体的互动和联系,成为不同党派与官僚、机构之间协调的桥梁,安倍政府藉此可以牢固地垄断信息发布渠道。
记者俱乐部不仅具有极强的排外性,而且在报道倾向上也力求一致。针对具体的议题,各大媒体的记者需要召开集体会议讨论关于报道的共同方针,所有媒体成员必须在后续报道中贯彻这一方针[7]。如果某一媒体与政府口径相左,记者俱乐部便会对该媒体和记者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为了确保本机构记者拥有通畅的采访渠道,俱乐部成员必须进行自我规制,减少与政府的冲突。
(二) 利用行政手段强化媒体人事控制
在安倍第二任期内,日本政府一直在积极推动旨在强化首相在行政系统中绝对地位的行政制度改革。受政治体制改革的影响,日本出现了“强政府、弱媒体”的局面,行政机关不断加强对媒体人事工作的控制。
在政治传播上的重大失败曾致使安倍于2007年辞去首相大位,因此安倍自2012年再度执政后,更加重视对媒体的控制,主要途径之一便是利用行政手段干涉主流媒体的人事安排。2013年11月,日本参议院表决通过了包括日本广播协会在内的12个机构的政府人事安排方案,其中百田尚树(Hyakuta Naoki)、长谷川三千子(Hasegawa Michiko)、本田胜彦(Honda Katsuhiko)和中岛尚正(Nakashima Syousei)4人担任日本广播协会经营委员会委员。日本广播协会是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公共媒体,而新任的4位委员皆与安倍有密切关系,具有明显的党派色彩。百田尚树是日本著名的右翼作家,曾与著名的保守派评论家长谷川三千子在自民党总裁选举中共同给予安倍晋三以鼎力支持。本田胜彦则担任过安倍学生时代的家庭教师,曾担任海阳学园、海洋中等教育学校校长的中岛尚正与安倍也极其亲密[8]。为了在日本最具影响力的公共媒体中获得绝对优势地位,安倍政府还将极右势力的代表人物籾井胜人(Momii Katsuto)置于日本广播协会会长的高位。此外,安倍还注重通过人脉关系加强与《读卖新闻》等右翼媒体的联系。在等级森严的日本社会,安倍放下首相身段、营造亲媒形象的举动实属罕见。
除通过特殊手段安插自己的亲信在媒体管理层担任要职外,安倍还通过诸如言论人恳谈会、日本文化人会议、日本自由主义会议等软性手段来笼络媒体,试图从源头上控制日本的国内舆论,迫使舆论引导者自觉服务于政治,心甘情愿地担当御用文人。
(三) 打压以《朝日新闻》为代表的左翼媒体
在西方国家,媒体批评、监督政府是极为正常的现象,而国家元首指名道姓地明确抨击作为“第四权力”的主流媒体的情形却较为少见[9]。安倍执政期间曾经在参议院中直接点名批评部分左翼媒体,指摘其言论有损于日本的言论生态、破坏了日本的新闻伦理。
在安倍第一任期内,左翼媒体曾经猛烈抨击安倍政府,因此安倍在第二任期内更加注重压制反对媒体,特别是对《朝日新闻》进行了言论控制。《朝日新闻》是日本第三大报,其秉持不偏不倚的报道立场,长期以来被视为日本左翼媒体的代表,其在历史认知、修改“和平宪法”、扩军等问题上一贯与安倍政府的右翼保守思潮相左[10]。2014年,安倍政府凭借其在国会占席过半的巨大优势,强行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案》。针对这一情况,《朝日新闻》明确表示反对,并刊发了一系列强烈批判安倍政府不顾民意强行通过该法案的报道,引起了安倍本人的极大不满[11]。2016年,分别隶属于朝日电视台、日本广播协会、东京放送的古馆伊知郎(Furutachi Ishiro)、国谷裕子(Kuniya Hiroko)、岸井成格(Kishii Shigetada)三位记者被迫辞职,因为三人曾于此前强烈反对安倍政府关于重启核电等一系列破坏战后和平秩序的政府计划。对此,时任日本总务大臣的高市早苗(Takaichi Sanae)在国会中公开宣称,日本政府拥有让存在政治偏见的电视台停播的合法权力[12]。此举直接体现了安倍政府中的保守势力对左翼进步媒体的打压与污名化。
在安倍第二次执政之前,日本政府为了保证媒体获取政府信息的权利均等,防止首相打压异见媒体,要求首相参加电视台节目需由内阁记者会与首相共同协商决定。但安倍在第二任期开始后不久便修改了关于首相参加电视节目的相关规定,并在所参与的电视节目上表露出明显的倾向性[13]。2015年,安倍先后出现在日本电视网、富士电视网以及日本广播协会等媒体机构,但并未参加朝日电视网、东京电视台以及TBS等左翼媒体的任何节目。由此可以看出安倍政府“党同伐异”新闻政策的具体内涵,即对符合自身利益、立场的右翼媒体进行大力扶持,对思想有悖于政府施政风格的左翼媒体则予以强力钳制。
(四) 强化立法以限制新闻言论自由
战后,日本针对传媒领域先后制定了《电波法》《广播法》《电波监管委员会法》等,以期对日本的大众传播产业进行规制,但这种规制主要表现在体制框架的建构上,并不涉及对内容生产的限制和管理。
自安倍第二次执政以来,自民党先后在众议院、参议院取得了绝对控制权,凭借这种雄厚的政治资本和强大的民意基础,安倍通过新闻立法加强了对媒体的管制。2014年12月10日,安倍政府在日本国会正式通过了《特定秘密保护法案》。该法案旨在加大对泄密公务员、议员、警察等国家机关人员的惩处力度,强化内阁对军事、外交等国家机密的管控,将安保、外交、间谍、恐怖活动四大领域内的涉密情报规定为特定秘密,且日本政府的一切行政机关均有权规定特定秘密的范畴[14]。
安倍政府出台的《特定秘密保护法案》规定了类目庞杂的特定秘密,但对于究竟是何种行为构成了隐匿行为等诸如此类的细节问题,安倍政府并未在法案中进行明确界定[15]。该法案虽未直接限制日本新闻媒体的权利,但在具体执行上却极大触及了《电波三法》所从未涉及的内容规制。新闻工作者因此普遍受到来自政府的压力,政府各大部门的公务员也因担心泄漏机密而拒绝在媒体上抛头露面,其直接影响便是媒体的自我审查日益加剧。
三、安倍政府时期日本媒体右转的影响
在政治传播体系上,安倍政府驾驭了媒体,实现了自身长期执政的政治企图。但由于政府对媒体规制过严及自民党明显的右倾化取向,日本的媒体生态陷入混乱局面,媒体影响力逐渐下降。同时,媒体言论的失序又反作用于日本政治,进而加剧了日本政治现实的右倾化程度。
(一) 媒体社会责任缺失导致集体失语
安倍第二个任期是日本媒体生态走向保守化的重要阶段,受高度封闭的记者俱乐部制度的影响,作为独立个体的新闻记者难以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日本媒体内部对政府意图进行自我忖度的传统使得部分新闻记者丧失了新闻敏感度,媒体报道的失真现象时有发生。特别是在涉及日本“国家正常化”等重大政治议题上,当新闻专业主义的理想与现实的利益、诱惑和压力发生冲突时,日本的大多数媒体均倾向于放弃自身的舆论监督职能而选择政治和经济利益。在日本媒体责任高度缺失、媒介发展被高度垄断的情况下,新闻专业主义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乌托邦。
一方面,在恳谈会、记者俱乐部等软硬措施的双重施压下,日本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和新闻纪律观念也逐渐弱化,在行使采访权与报道权时易受到多方的利益胁迫和诱惑,时常暴露出制造虚假新闻、新闻侵权等职业道德失范问题,甚至出现了利用新闻做交易的“有偿新闻”这一现象。这种不正之风破坏了日本的新闻媒体生态,损害了新闻工作的声誉。另一方面,日本的新闻立法还不够健全,《特定秘密保护法案》等界定媒体红线的法规仍然存在缺陷,其结果便是对日本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缺乏强制性的约束机制,导致新闻自由难以在实践中被真正贯彻。
一直以来,虽然日本媒体在设备和人员配备等传播硬实力上占据极大优势,但其保守的媒体运作机制和牺牲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功能的倾向决定了日本媒体在涉及当代世界的核心议题上难以发出自己的声音,更无法形成传播软实力强大且具备全球影响力的旗舰级主流媒体。
(二) 言论同质化打破媒体立场平衡
战后,日本媒体界形成了左、中、右三足鼎立且基本稳定的传播格局。安倍政府采取行政、立法等综合性手段限制了日本的媒体自由,使得日本的新闻媒体在进行议题设置时往往自觉追随政府的政策议程,试图扮演“传声筒”的角色,为受众“想什么”“怎么想”提供主流的、统一的保守意见。在当今日本人的思维中,序列主义仍然根深蒂固,大众仍然坚信主流媒体提供的特定的意识形态和标准化的价值观。这种日式的集体主义思维使得日本大众习惯于将自身观点不断与主流媒体引领的舆论风向进行对标。在安倍政府议程与媒体议程的配合下,大量右倾化言论迅速占领日本的主流传播场域,此前基本平衡、相互牵制的日本媒体格局开始走向极化和失衡。
当前,随着日本媒介市场竞争的白热化,商业利益、政治利益与媒体责任之间的冲突日益尖锐,部分日本媒体和记者不再关注自身的新闻业务,对于新闻言论创新与观点开拓的欲望急剧下降。他们出于现实考量更多地将精力用于维护与日本各大政治团体的关系上。虽然此前日本的新闻传播界曾一度高举现实主义批判旗帜,但在日本社会总体保守化的趋势下,除极个别心怀新闻理想的左翼进步媒体外,大部分日本媒体的言论在风格定位、目标受众上更加趋于一致,形成了“众报一面”的格局。日本媒体独立性和独特性的弱化,是导致日本媒体在传播思想、传播理念、传播方式、传播效果等方面均呈现同质化的重要原因[16]。
(三) 媒体报道右转加速政治现实右转
大众传媒以现实世界为基础展开的传播活动并非是对现实的客观再现,而是具有选择性、倾向性与立场性,其所形成的信息环境是具有高度象征性的“拟态环境”。安倍政府积极谋求打破战后体制,这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观已经影响到日本媒体的新闻生产。在过去的20年间,日本的舆论界完成了对日本国家发展战略等重大议题的全社会的“舆论共识动员”[17]。在谈及历史认识、修改教科书、修宪、领土争端等重大战略问题时,日本的网络媒体与传统媒体相互配合,呈现出并肩为安倍政府摇旗呐喊之势。当安倍政府意欲推行某一政策时,传统媒体会当即开始议程设置并进行深度报道,而网络媒体会迅速跟进传统媒体的报道,将传统媒体设置的媒介议程转换为公众议程[18]。
一方面,在日本民族主义不断发酵的背景下,日本的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中出现了越来越多颠倒黑白的言论。受安倍政府议程的影响,日本媒体有意制造了大量诸如使日本走向“正常国家”的言论,使得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愈发紧张。另一方面,日本媒体频繁地让鼓吹日本优越意识的各类鹰派人物登台发表混淆视听的政治谎言,这种极端民族主义言论助长了日本“国家利益至上”的排外倾向[19]。在由安倍政府宣传机器塑造的“拟态环境”中,许多日本国民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最终在大众传媒所散播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走向了群氓的狂欢,而这也进一步诱发了日本政治现实右转。
四、结语
原本在日本政权更迭上拥有主要话语权的派阀集团被削弱后,媒体人气和公众形象成为影响日本首相选举的首要因素。政治经验丰富的安倍晋三深谙只要政府、媒体、舆论三者实现集体合谋,政治领袖便可以借助媒体舆论对政治现实施加重大影响[20]。安倍政府以鲜明的右翼立场引起日本媒体舆论的持续关注,以超强的声望操纵媒体人事,弥合了媒体议程与政府议程之间的裂痕,形成了持续向前的政治统治合力。单从这一点来看,安倍政府建构的政治传播体系在维护自民党统治、保持自身政治优势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
然而当“政治正确”成为日本媒体的唯一追求时,媒体本身的自我约束和观点的理性权衡便不复存在,随之而来的便是对“专业主义”的漠视与践踏。在同质化的极右言论引导下,日本民众仿佛再次回到了关于“政治大国”“修宪国家正常化”等充斥着民族主义思想的“拟态环境”中,而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也因此受到严重威胁。近代以来,日本媒体一度在建设民主国家、代表公众监督权力和批评政府等方面扮演了重要角色,但其在运作机制上始终未将政党和政府排除出去,也未能摆脱民族主义与排他主义的束缚。新闻专业主义强调媒体是社会公器,应该服务于公众利益。当今,日本媒体迫切需要打破政治和利益的双重屏障,与政府保持距离,扛起维护多元社会的大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