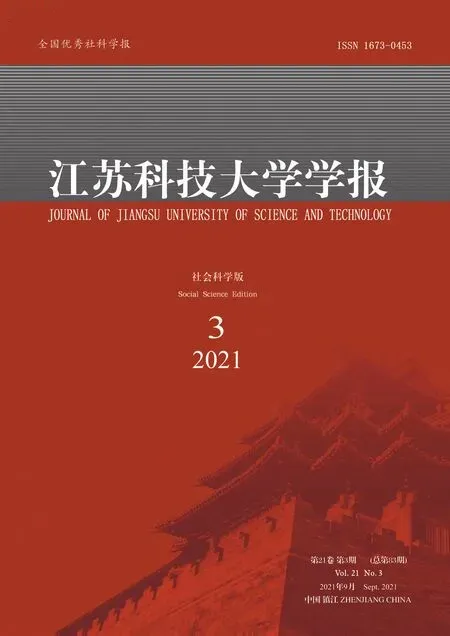论韦努蒂对德里达翻译观的“延异”
2021-12-06赵静
赵 静
(1.江苏大学 京江学院,江苏 镇江212000; 2.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00)
德里达(Jacgues Derrida)以前的西方哲学认为,世界存在某种绝对的参照物,并且事物都能与参照物之间发生确切的关联。在这种哲学逻辑思维下,翻译也被看做是纯粹的二元对立,即译文是原文的对立项,译者是作者的对立项。而德里达提出的解构主义打破了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的结构主义,以差异作为本源,将翻译解读为对意义的多重阐释。在德里达解构主义翻译观的启迪下,各种翻译理论应运而生。韦努蒂 (Lawrence Venuti) 深受德里达的影响,在吸收解构主义思想的同时,又提出了自己的文化翻译观。韦努蒂的翻译理论时而被归于解构主义学派,时而又被归于文化研究学派,这说明韦努蒂和德里达的翻译思想既有相通之处,又有所区别。笔者认同蒋骁华和张景华在《重新解读韦努蒂的异化翻译理论——兼与郭建中教授商榷》一文中的观点:韦努蒂的翻译理论与解构主义有本质的区别,其思想属于文化学派[1]。除此之外,笔者认为韦努蒂翻译思想是德里达翻译思想在文化领域的“延异”。
笔者从两者的思想基础、可译性、忠实性等共同之处展开讨论,进而探讨韦努蒂在主体间性、“他者伦理”、文化构建、翻译目的及标准、翻译方法五个方面对德里达思想的“延异”,以便进一步厘清二者之间的内在联系和相互差别,思考解构主义翻译观在政治、文化领域带来的深刻变革。
一、 德里达与韦努蒂的翻译观
德里达《语音与现象》《论文字学》《文字与差异》这三部著作的出版标志着解构主义的诞生。德里达的解构主义主要集中在哲学和文学领域,但是他对翻译也发表了很多看法。
首先,德里达将翻译定义为“一种阅读活动”,并通过解构式的阅读策略提出“去中心化”的解构思想,从而提出了解构主义翻译观。
其次,德里达提出“延异”的概念,是德里达解构主义思想的核心。在他看来,文本的意义不再是恒定不变的,而是处于不断流动、不断改变的状态,一切事物都具有差异性。在“延异”的基础之上,德里达又提出了“存异”的翻译主张,即“所有译文都是另一个早先存在的翻译,因为历史文化的含义,译文中的词语被不同人的解读,我们习以为常的原文可能是一种历史上的互文,或者说更早被翻译过的文本,翻译实际上是回归或者连接一系列意义的链条,是不断修改或推迟意义的过程”[2]299。
再次,他提出了“印迹”“播撒”和“可重复性”的概念。在德里达看来,“所指”只是一个符号,应当与意义相分离,意义要通过语境得以确立。而“印迹”则是“所指”或意义在不同语境中所代表的流动的存在物,因此“印迹”的概念说明文本意义具有不确定性。因为“延异”的缘故,意义被“播撒”到了四面八方,文本意义的流动性被无限扩大,于是语境成为文本翻译的关键,意义需要上下文语境,换言之,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能确定意义。然而德里达并不是一味强调意义的无限流散,相反他承认结构具有稳定性。文本结构的稳定是文本得以理解的前提,文本的“印迹”是语符的重复。值得注意的是,德里达所说的稳定是相对的。“差异”和“延异”是德里达理论的基础,文本是建立在历史性的“差异”和不断“延异”之上的,在不同的语境中并不总是稳定不变的。
最后,德里达提出“relevant translation”(相关翻译)的概念,并且提出翻译的“债务说”。在德里达看来,原文自身的结构就具有翻译的需求,原文在产生的那一刻开始就需要翻译,甚至请求被翻译,因此翻译是一个偿还债务的过程。好的翻译就是人们所期待的翻译,是完美传达信息且无语法问题的翻译,这也是一种绝对理想的状态。
韦努蒂将翻译放在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宏观语境中进行研究,其代表作有《译者的隐身》和《翻译之耻》。首先,在《译者的隐身》这部著作中,韦努蒂批判了主导西方翻译史的归化翻译法,指出这种追求流畅的翻译策略体现了西方霸权主义的价值观。在韦努蒂看来,归化和异化不仅仅是语言的选择问题,从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角度看,两种翻译策略的选择还体现了翻译的伦理道德和文化身份认同等深层次问题。他提出了“异化翻译”和“抵抗式翻译”的概念,即在翻译中保留原文中有异国情调的东西,有意抵制目的语的文化价值。“异化翻译”将文本的异质性重新纳入考虑范围,并且对目的语语言和文化始终采取批判立场。其次,韦努蒂认为翻译不仅可以塑造文化身份,产生文化认同,而且对社会变革有深远影响。异域文本和“他者”价值可以通过翻译进入本土的主流文化,进行渗透、破坏或者建构,以此来改变本土的文化认同。不仅如此,韦努蒂还指出,翻译无法摆脱其根本的归化性质,因此会产生文化身份塑造以及塑造背后的权利问题。再次,韦努蒂提出了翻译伦理的概念,他将归化翻译的伦理定义为“化同伦理”,将异化翻译的伦理定义为“存异伦理”,然后他又解构了这一对二元对立的概念,提出了“因地制宜”的伦理。该伦理是韦努蒂从全球化角度出发思考翻译对文化变革所起作用时所提出的概念。
二、 韦努蒂对德里达翻译思想的“延异”
(一) 韦努蒂对德里达翻译思想“延异”的基础
对于翻译的本质,德里达在《写作与差异》中提到:“differance一词中的字母a表明主动状态和被动状态的不确定,而且这种不确定也不再受二元对立的控制和构组。”[3]也就是说,“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不再是确定的,而是有差异的和不确定的。除此之外,德里达提出了“意义链”概念,他认为“意义是一条无止境的能指链上关系和差异的效果——多义的,互文的,受制于无穷的联系”[4]。因此在德里达看来,“差异”是翻译的本源,意义永远是有差异和被延迟的,永远都不可能是原文。韦努蒂继承了这种观点,他认为翻译的目的就是要凸显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差异性,并且他还指出,“翻译是在译者理解的前提下,用译语的能指链条来替代源语文本中的所指链的过程”[5]。他的异化翻译策略就是要尽力保留原文的语言和文化特色。这正好印证了德里达的“差异”思想。
德里达对“忠实观”进行了解构,认为意义是流动的、开放的和不确定的[2]296。而韦努蒂借用了刘易斯(Philip Lewis)的“滥译的忠实”概念,同样认为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是随意、不确定的[2]478。而韦努蒂的异化翻译在某种程度上正是对原文不确定意义的一种呈现。值得注意的是,“滥译”一词最早也是源于德里达。德里达认为,“好的翻译一定会滥用文字,而且翻译是引发对原文进行解释的一种形式”[2]478。
对于可译性,德里达在《巴别塔之旅》中提出了翻译的悖论,“上帝把翻译工作强加于人类,同时又禁止人类翻译”[6], 即翻译是必要的,但绝对意义上的翻译是不存在的。换言之,要在语言的共性基础上存在差异性,因此绝对翻译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德里达在提出“债务说”时认为,原文对于译文而言,处在永不停歇的负债状态中[7]。因此对于可译性,德里达认为只能无限地接近绝对可译,但永远都够不到[8]。反观韦努蒂,通过他对“忠实观”的解读可以看出,他始终认为译文永远不可能忠于原文,永远有缺陷,需要补足。因此,从韦努蒂的角度来看,绝对翻译也是同样不可能的,而只能是无限地接近原文。
对“差异”、传统“忠实观”的解构,以及对“可译性”不能“同真”只能“近真”的认知,是韦努蒂对德里达思想“延异”的基础。德里达“延异”思想的本质就是衍生,而韦努蒂的翻译理论正是对德里达翻译思想在政治、文化领域的衍生。
(二) 韦努蒂对德里达思想的“延异”
1. 对主体间性认识的“延异”
在翻译研究中,原文一直以来都被放在第一位,译文是从原文中派生而来,译文是依附于原文而生存。在这样的观念下,译作作为原作的衍生物是不具备与原作相同地位和独立性的,而译者只能“隐身”以便给人一种假象:译作是作者用目的语写成的作品。现代西方哲学解构了这种主客的二元对立,将目光转向了“主体间性”,即“表征自我和他者的关系,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主体能够达到或建立的客观性”[9]。许钧在《翻译学概论》中将“主体间性”分成了四个层面:译者与原作者、原文与译文、译者与文本、译者与读者[10]。据此,笔者从这四个层面分析德里达与韦努蒂翻译观对“主体间性”认识的不同之处。
对于译者与原作者之间的关系,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学派认为“解构主义强调的是互文性,而不是作者,宣布上帝已经死亡,力图从根本上颠覆作者只作为意义来源的理念。因而解构主义翻译理论否定了作者的原创性”[1]。德里达将差异作为翻译的本源,就是直接忽视了原作者,让译者直接与文本进行对话。而韦努蒂认为“作者、译者与学者其实是在做类似的事情,创作、翻译与研究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原创并不是自生的,而是作者利用久已存在的文化素材,经过重新整理,按照某种价值观重新写就的”[11]43。由此可见,韦努蒂和德里达一样否认了作者的原创性,然而韦努蒂对德里达观点的“延异”之处在于,他并没有否认原作者的存在。尤其是当他提出译者的“隐身”观点时,他所针对的是原作者高高在上而译者自我被抹杀的传统认知,“隐身”的前提就是原作者的存在。
对于原文和译文之间的关系,德里达认为,译文是原文的“重生”,不是译文依赖于原文,而是原文依赖于译文,并且译者所追寻的文本意义隐藏在译文中,而不是在原文中[2]298。德里达认为,如果原文需要补充,那是因为它在原出处就有缺点,不完整,译者对原文并不是完全认同[12]。因此,在德里达看来,原文和译文除了“重生”关系之外,还有互补的关系,原作从一开始就不是高高在上的,并且原文和译文是平等和独立的关系。也正是从这种关系出发,德里达取消了原文的独创地位,因为原文和译文在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原文只不过是以前译本的译作,而译文完全可以被当作原文的再次翻译[8]。韦努蒂同样打破了原文和译文的传统关系,认为译文中有自由发挥的成分,对原文并不是百分之百的“忠实”。韦努蒂借用“滥译的忠实”概念,即排斥主导当代翻译实践的流畅策略,支持与其相反的策略[2]478。换言之,韦努蒂否定了传统的原文和译文关系,否定了译作对原作忠实的观点。笔者认为,韦努蒂与德里达一样,对传统原文和译文关系进行了解构,并在此基础上,韦努蒂又进一步作出“延异”。与德里达认为原文和译文互补的观点不同,他将原文看作是译文所参考的蓝图,译文只能是对原文的一种诠释和不透明的表述,但是译文产生的源头仍旧是原文。
对于译者与文本之间的关系,德里达认为,“原文是一种被需要的状态,即本身处于匮乏或者流放的状态。翻译对于原文来说处于一种先在。原文的延续处于一种需要,一种被翻译的需要,有些类似于巴别塔的需要:翻译我吧”[13]。因此,每一次翻译都给原文带来了新的意义创造,甚至要求译文比原文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德里达的“债务说”同样也说明:译者不再受制于原作,而是创造性地再现原作。在德里达看来,译者不再是原文意义的模仿者,而是原文生命力的创造者和守护者,原文成为提供意义创造的场所。德里达还指出,“如果译者既不补偿也不复制原作的话,那是因为原作可以继续存活并在改变自身。翻译就将真正地处在原作的发展时刻,因为原作在扩大自身的同时也在实现自我完成”[14]。不难看出,德里达虽然认为译者具有创造性,但译者还是应当本着再现原作特点的目的去再创造。笔者认为,韦努蒂提出的“抵抗式翻译”是对德里达将译者看作创造者观点的继承, 因为他一方面抵制流畅的翻译,另一方面抵制原文,提倡对原文进行大胆的删减以便让原文特征更加明显。例如,韦努蒂在翻译意大利诗人安吉利斯的诗歌时,同时背离了源语与目的语的语言规范,使得译本比原文还要晦涩、陌生。其译文无论对于英美读者而言,还是对于意大利读者来说,都是陌生的[2]478。由此可见,德里达和韦努蒂都将译者看作创造者,将文本看作译者进行再创作的参照,但韦努蒂的“延异”之处在于,他不认为文本对译者有一定的约束作用,而是赞同译者的“自由发挥”并不受源语文本的制约。
对于译者和读者之间的关系,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学派认为,原作者和读者之间不再有关系存在,读者可以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自行获得文本的意义[2]298。因此,文本的意义是开放的,“能指”也具有多样性,意义的变化取决于读者。同一作品出现不同的译本也是以此为依据的。而韦努蒂虽然接受了施莱尔马赫(Schleiermacher)的观点,“译者要么尽量不打扰原文作者,让读者靠近作者,要么尽量不打扰读者,让作者靠近读者”[15],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之所以提出“异化翻译”的概念,前提就是他认为文本的意义是多元的、开放的,允许对文本做出独特的解读。韦努蒂心目中的译者和读者都是“文化精英”,因为“大众的审美意趣是追求文学中所表现的现实主义错觉,抹杀艺术和生活的区别,他们喜欢的译文明白易懂,看上去不像是翻译”[11]19。由此可见,韦努蒂同样继承了德里达关于文本具有开放性、多元性的观点,他的“延异”之处就在于选取了特定的读者群和译者群,是在一个特定的框架内研究翻译。
2. 对“他者伦理”的“延异”
在德里达的“延异”和韦努蒂的“存异伦理”概念中,“他者”概念都是两者理论的核心观点。
首先,德里达的“延异”理论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符号本身转移到与符号构成差异关系的“他者”身上,并以此无限推延,使得以往被压抑、遮蔽和边缘化的“他者”得以凸显。韦努蒂提出,异化翻译法可被看作是抵抗种族中心、文化自恋,以及反抗帝国主义行径的方法[16]。由此可见,韦努蒂赞同德里达凸显“他者”的观点,认为那些处于边缘、弱势的文本更值得翻译。
其次,德里达不认同利维纳斯(Levinas)的观点,后者认为“他者”是一个纯粹被隔离起来的旁观者。德里达认为,“自我”与“他者”存在辩证的关系,“他者”包含自我性,“他者”与“自我”之间可以相互对话、理解和命令。也就是说,差异存在的前提就是“自我”与“异相自我”的辩证存在。因此,在存异伦理和化同伦理问题上,德里达并不赞同两者的绝对对立,他认为所有的翻译都发生在一个“自成一统的介域”,在“绝对和最大限度的不相关,亦即彻底的异常和晦隔状态之间获得定位”[4]。而韦努蒂则认为“存异伦理”虽然“改造了在本土文化中占支配地位的那些文化身份”,可是这一改造往往“随后发展为另外一种支配状态和另外一种民族中心主义”[11]82。韦努蒂继承了德里达关于“他者伦理”的辩证思想,否认了二者的纯粹对立,将伦理看作一个矛盾的动态演变过程。此后,韦努蒂进一步提出了“因地制宜”理论,将翻译放在复杂、动态的全球语境中考虑,无论是归化还是异化,凡是能因地制宜促进文化更新和发展的就是好翻译[17]。
因此,韦努蒂和德里达都持有翻译要凸显“他者”、“他者伦理”具有动态演变性的观点,而韦努蒂进一步“延异”,将“存异”和“求同”作为“自我”和“他者”的辩证存在,根植于“因地制宜”的伦理。
3. 对文化建构的“延异”
解构主义是一种是非理性的怀疑主义思潮,虽然它有助于对结构内部非理性因素的认识,但它本身缺乏统一的框架和纲领,并且在内容方面也鲜有实质性内容。解构主义将翻译放在语言的虚构世界中,与外部世界切断联系,让翻译活动成为一种语言的互相解释以及意义任意生成的游戏,从而导致翻译研究的混乱以及无政府状态[18]。但解构主义在解构原文之后,却没有重新建构的模式或者方法。对于原文本所包含的文化因素,解构主义对其进行了解构,却没有提供具体的原则来进行拆解之后的重建。而韦努蒂指出,“翻译有助于塑造本土对待异域国度的态度,对特定族裔、种族和国家或尊重或蔑视,能够孕育出对文化差异的尊重或者基于我族中心主义、种族歧视或者爱国主义之上的尊重或者仇恨。从长远来看,通过建立外交的文化基础,翻译将在地缘政治关系中强化国家间的同盟,抵抗霸权”[19]。因此,对于韦努蒂而言,翻译更是一个政治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去文本和重构文本语境的历史性过程。韦努蒂基于解构主义思想提出了在社会、文化的宏观背景下研究翻译的主张,他提出的异化翻译与抵抗式翻译构建了一个凸显异族文化、抵制西方主流价值观、促进本土文化认同的翻译形象。韦努蒂主张以巨大的构建能力再现外来文化,他认为翻译不仅能塑造文化身份,产生文化认同,还对社会变革有深远影响。
对于文化建构,韦努蒂继承了德里达对原文本语境消解的观点,但德里达并没有对消解之后的文化建构路径提出进一步的建议。韦努蒂却在消解语境的基础上提出了文化建构的新思路,将翻译研究推向了社会、文化、政治等更为广阔的层面。这正是他的“延异”之处。
4. 对翻译目的及标准的“延异”
翻译任务是针对翻译目的而定的。对于德里达而言,翻译是一种语言和文本对另一种语言和文本“有调节的转换”,一篇译文的价值在于其对语言差异的反映程度及对差异的强调程度,因此翻译的目的是体现语言意义的差异。德里达提出了翻译标准“relevant translation”。这个词首先在德里达的论文《什么是相关的翻译》中被提及,“relevant translation 是尽了职责,偿还了债务的,可能的最好的翻译”; 同时他又说道,“无法确定一种源语,能将‘relevante’ 和‘releve’相对应……我们甚至不知道它是否是一个单义词,或者是包含多词的同音异义词或者同音异形词”[20]425。由此可知,这个词实际上只是一种文字游戏,意义并不能被确定。他借助这个词语对自己提出的翻译标准进行自我解构,其用意就是解构了寻求忠实、对等的传统翻译观,解构了自封的对意义的把握、提炼和传递[7]。随后德里达再次提出,“一切皆不可译,一切又皆可译”[20]427。为了达到体现差异的目的,他解构了传统的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提出原作的不可再现以及译作的未完成性,并且将可译性和不可译性放在同一水平线上,认为这两者辩证存在于任何一个文本中,这无疑消解了具体的翻译标准。反观韦努蒂,他的翻译目的同样是为了表现差异。他认为翻译的目的是抵制英美霸权,让译者“显形”,而好的翻译是具有陌生化倾向的翻译,它能表现出语篇的异质性,让弱势语言和规则得以显形。由此可见,韦努蒂和德里达一样,都认为翻译目的是为了表现差异,但韦努蒂认为翻译的目的不仅要表现语言差异,更重要的是要表现文化差异。对于翻译标准,两者都消解了传统的译文对原文亦步亦趋的标准,但是德里达在消解了翻译标准之后无意提供一个“结论”或“解决方法”[7]。换言之,德里达并没有提供一个有实际意义的翻译标准,而韦努蒂却按照德里达的“延异”思想进一步提出了“少数化”翻译,之后又提出“因地制宜”的翻译标准。
5. 对翻译方法的“延异”
德里达在《什么是相关的翻译》中提出了“经济法则”。该法则要求译者要在“质”和“量”的原则中寻求平衡,即译者要用恰当的语言和方式将原文中所包含的内涵和外延意义尽量呈现出来,但是译者不能添加原文中没有的东西,字数上也不能与原文的字数相差太多[21]。这个法则和德里达对于可译性的认识相呼应,消解了具体的方法,转而寻求中间路线。反观韦努蒂,他所倡导的异化翻译策略不仅在词语上要逐字对译,而且要在译文中保留外来词汇,突出原文的异质性,哪怕这种翻译有可能在译文中造成陌生的表达方式。正如韦努蒂在翻译德里达论稿时说到的:“尽可能地接近他的法语,尽量模仿他的句子结构、用词风格和排印特点,努力创造出相似的效果。”[14]韦努蒂与德里达在翻译方法方面持有同样的观点,即要将原文的意义尽可能呈现出来,然而德里达的“经济法则”消解了具体方法,而韦努蒂意欲突出对异质意义的传递,提出了陌生化的翻译方法。
三、 结语
通过比较德里达和韦努蒂的翻译观发现,虽然两者的翻译观有相通之处,即德里达与韦努蒂都关注“翻译之用”——翻译理论,但韦努蒂毕竟是翻译理论家也是翻译实践者,所以读者可以从韦努蒂的翻译理论中找到“翻译之器”。他们的翻译观是有本质区别的。德里达的翻译观提供的是一种翻译的思维方式,而韦努蒂的翻译观却是将翻译置于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中,将其看作是一种文化干预的手段。德里达的翻译观意味着,旧的思想中心需要不断被打破,同时新的、不稳定的中心需要被建立,而韦努蒂的“少数化”翻译和“因地制宜”的翻译标准为构建意义链提供了可操作性手段。因此,韦努蒂的翻译观是对德里达翻译思想的继承和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延异”,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关于翻译中政治和文化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