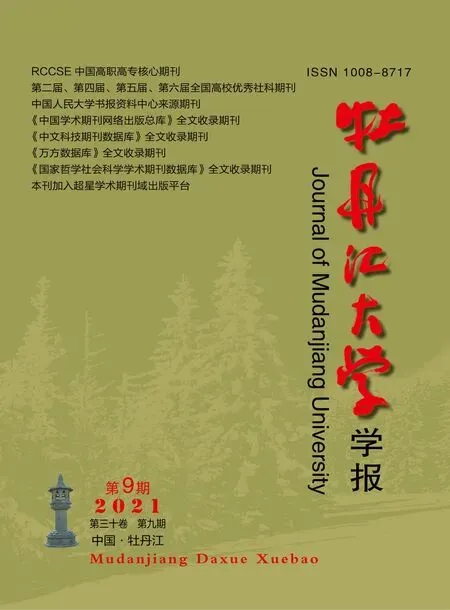让不可靠叙述“可靠化”
——《A&P》之叙述艺术
2021-12-06阙钰聪刘明录
阙钰聪 刘明录
(广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6)
美国著名作家约翰·厄普代克曾两次获普利策奖、两次获国家图书奖以及欧·亨利奖。前人对其作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他的代表作《兔子四部曲》,而对短篇小说《A&P》的关注度不高。《A&P》讲的是小镇超市青年收银员萨米看见三位女孩穿着泳衣进店后,被她们大胆的自由前卫深深吸引,鲜明对比之下,引发了自己内心深处由来已久的对单调重复工作的厌倦、对顺民般的超市顾客充满贬义的评头论足,最终为三位女孩出头与刻板经理对峙而主动辞职的故事。前人对《A&P》的研究并不多,比较突出的是杨秀萍探讨了美国当代青少年的成长主题,[1]方文开研究了《A&P》中隐含的文化政治修辞,[2]郭定芹则关注到其中的隐喻符码和性意向。[3]在叙事研究方面,杨晓霖注意到人物的个性化视角,但更多集中在小说措辞与篇章的表现和叙事意义。[4]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聚焦叙事人称,研究第一、二人称叙述交织碰撞的表达效果,以及探讨不可靠叙述带来的文学张力。
一、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脱离伦理规范
不可靠叙述是由韦恩·布思在《小说修辞学中》首次提出的,“布思衡量不可靠叙述的标准是作品的规范(norms)。所谓‘规范’,即作品中事件、人物、文体、语气、技巧等各种成分体现出来的作品的伦理、信念、情感、艺术等各方面的标准”①。随后,美国叙事理论界权威代表詹姆斯·费伦将不可靠叙述发展完善,形成不可靠叙述的系统性框架:事实/事件轴上的“错误报道”和“不充分报道”;价值/判断轴上的“错误判断”和“不充分判断”;知识/感知轴上的“错误解读”和“不充分解读”②。
短篇小说A&P中出现了大量的不可靠叙述,因为主人公萨米以第一人称“我”叙述故事时,内心对三个女孩大肆幻想,对顾客和同事毫无敬意,并不是一个正派人物形象,“倘若‘我’作为人物有性格缺陷和思想偏见,那批评家就倾向于认为‘我’的叙述不可靠”[5]135。
当“我”看到同事麦克马洪为三个姑娘指路时露出的觊觎窥视的丑态——“轻轻地抚弄自己的嘴巴,目光追随着她们,打量着姑娘的关节”[7]148时,感到恶心厌恶,内心想“可怜的孩子,我开始为她们感到惋惜了”[7]148。但是“我”却全然忘记自己内心也对这些女生大肆展开性幻想——“臀部肥大,显得柔软可爱”[7]145;“她的眼睛不停地扫视着排排货架,然后站住,非常缓慢地转过身来,这种姿态惹得我心痒难挠”[7]146;“刹那间我顺着她的话音,仿佛偷偷溜进她的起居室”[7]149。“我”对麦克马洪的厌恶是知识/感知轴上的不充分解读,即只感受到他人的龌龊,却宽恕甚至放任自己的觊觎,是一种脱离伦理规范的体现。
另一方面,安斯加·纽宁聚焦于读者的阐释框架,断言“不可靠性与其说是叙述者的性格特征,不如说是读者的阐释策略”③,因此读者的认知同样是判断不可靠叙述的标准。如果从读者认知的角度看,萨米把顾客比 作“sheep”“pig”“house slaves”,这 些词充满了鄙视性和人格侮辱,同时拥有顾客身份的大众读者显然会认为萨米与自己的道德认知、审美期待相违背,于是读者有理由认为萨米是一个不可靠叙述者。
第一人称叙述者由于观察视野和知觉感受只能集中在“我”自己身上,因而有其限制性而产生不可靠叙述。文中的“我”内心对自己的顾客充满鄙夷,对同事的丑态加以轻蔑,对自己的性幻想大肆放任,而第一人称叙述却成功地把“我”的真实想法隐藏在“我”的内心,对他人毫不尊重却不必暴露于大众视野,但是读者很容易看出这个人物的性格与伦理规范相左。那么小说是如何通过一个负面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表达自己的主题呢?它需要让第一人称叙述者与读者同谋或者利用这种“不可靠性”。
二、与读者同谋——穿插第二人称叙述
第二人称叙述其中一个定义是“故事的主人公由代词你指涉”[8]。在这里引用“第二人称叙述”这个概念并不是只为了强调“你”可以是故事中的人物,还意在借用第二人称叙述的某些特质:一是叙述话语具有强烈的对话感[9]21,二是代词“你”存在与受述者重合的情况,三是可以正当、公然进入“你”内心、挖掘“你”想法的特权。第二人称叙述由于“你”代词的出现,很容易调动读者参与文本创作,因此读者就有可能对文章内容产生认同感,“我”从而达到与读者同谋的目的。文章插入的第二人称叙述经过分析,可以大致分成以下三类,分别产生了三种不同的认同方式。
(一)召唤式认同
叙事读者是“叙述者谓之写作的想象的读者”,受述者是“叙述者说话的对象”[10],詹姆斯·费伦认为,“受述者越是受到完整的描写, 受述者与叙事读者之间的距离就越大; 同样, 受述者受到的描写越少, 二者之间的重合就越大”[11]。在《A&P》中,受述者“你”表现为不具体的人物形象描写时,“你”的指代性非常强,可以是任何读者,偶尔穿插在“我”为主导人物的故事中,因此受到“你”代词召唤的叙事读者很容易扮演受述者的角色,产生强烈对话感,将自己作为“我”旁边倾听的那个人物“你”,这是认同感产生的第一步。第二步,当“我”用一种对话常用的“you know”结构时,可以引起有共同特定经验的群体的共鸣,“you know, it is one thing to have a girl in a bathing suit down on the beach…and another thing in the cool of the A&P”[6]58,像是“你”和“我”朋友间的默契共识——海滩上穿泳衣确实不瞩目,但是在超市的日光灯下穿泳衣是多么耀眼,这样的“you know”共识引起了彼此的共鸣,拉近了“你”和“我”的心理距离;或者用口语体中引起对话的反问句式召唤读者加入交流:“Do you really think it’s a mind in there or just a buzz like a bee in a glass jar ?”[6]57,“你”在情窦初开的年纪真的能知道女孩心里在想什么吗?大多数青春期的男孩确实不懂女生的心思,读者读到这里都会会心一笑,萨米一个青春期大男孩的形象——带着这个年纪特有的懵懂和幻想,进入了读者视野中。
(二)代入式认同
第二人称叙述中的接受者与叙述者在人称上产生了重合,这不可避免地导致读者在阅读小说时,会在不同程度上把自己等同于这个“你”[9]37-38。“你”进入了故事本身,成为了故事当时情节发展的参与者,会产生代入式认同。比如在萨米第一次将顾客比作“sheep”的时候,他为之做出了解释,邀请读者亲眼看看当时的场面,“you could see them, when Queenie’s white shoulders dawned on them, kind of jerk, or hop, or hiccup, but their eyes snapped back to their own baskets and on they pushed”[6]58,此时“你”有一种亲临现场的代入感:“你”看到了顾客们因为看到昆尼她们穿着泳衣出现而受到惊吓的那副滑稽样,他们还慌乱地掩盖自己的过度反应——他们就像羊一样温顺,丝毫不敢对穿泳衣逛超市这种冒险张扬的做法有任何认同,甚至不敢看。同时作为观察者和读者的“你”就可能明白“我”所说的“sheep”并不是一个夸张词而是多么贴切了。在萨米的叙述中,这个小镇离海边不过五公里,但是却有人二十年来都没见过大海,对穿着泳衣来超市的人更是口瞪目呆,于是小镇人思想僵化、停滞不流、墨守成规的形象跃然纸上。
当第二人称叙述出现在萨米的工作日常 时,“It’s more complicated than you think, and after you do it often enough,it begins to make a little song, that you hear words to…flying out”[6]61,在这里小说有意模糊了“我”和“你”之间的界限,使“你”完全进入“我”、成为“我”:“你”开始经历“我”日复一日的机械工作,这些重复的工作带给“你”的唯一乐趣就是听工作时柜台抽屉和结账机器发出的叮当声,将这些声音串成乐符。于是“你”便不难理解,一个正值壮年、精力充沛的小伙子在每条重复着单调工作时的压抑心情了,所以“你”就能想象“我”看见三个穿泳衣的青春女孩进店的那种视觉冲击、新奇与兴奋。
(三)霸权式认同
不同于第一人称叙述只能活跃在“我”的视野和内心,第二人称叙述有一种正当的可以公然进入“你”内心窥探、挖掘“你”想法的特权,因为“叙述接受者这个角色在第三和第一人称叙事中观看别人而不被人观看的特权现在被完全剥夺,他不再处于个人隐私受保护、受尊重、不被议论的优越地位,这是第二人称叙述的关键所在”[12],此外“第二人称叙述就是一种霸权式的,‘不礼貌’的话语形式”[9]42。
那么,总书记为何提出“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这当然不是说以往我们对权力的运行没有制约和监督,而是指这种制约和监督还“不强”,或“不太强”,还没有真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因此,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琢磨的问题应当是:权力为什么需要“关进制度的笼子”?约束权力之“制度之笼”由谁来编织以及怎样编织才真正有效和管用?等等。
当“我”直言不讳地说出 “you never know for sure how girls’ minds work”[6]57时,正在围观“我”内心世界的读者突然发现自己成了聚焦点,作为受述者的许多男性读者内心真实的想法被当场揭露、无处隐藏,因此他们无法不对主人公“我”产生认同——女孩总是这样难以捉摸,令人遐想。
“我”如此肯定在超市点火带来的顾客骚动不会比三个女孩带来的骚动大,用的句子 是“I bet you could set off dynamite in an A&P and the people would by and large keep reaching and checking oatmeal off their lists”[6]58,而 不 是“I could set off…”,读者更容易被前者说服,是因为同为故事人物和受述者的“你”只能听任叙述者安排你的所作所为却无从插嘴。
促使读者对文本中的“你”产生认同,进而参与文本的创作,是第二人称叙述独有的美学力量和诗性品格。[9]38第一人称叙述的不可靠性会在间接穿插第二人称叙述的情况下,通过读者的召唤交流、代入认同与霸权认同,让读者参与文本创作,产生了认同感,因而消解了部分不可靠性。
三、有意为之——利用不可靠性产生张力
韦恩·布思认为:在读者发现叙述者的事件叙述或价值判断不可靠时,往往产生反讽的效果,[5]134嘲讽的对象是叙述者,也就是说“作者和读者会在叙述者背后进行隐秘交流,达成共谋,商定标准,据此发现叙述者话语中的缺陷”[5]134。出于策略考虑的隐含作者为了让读者领会其言外之意,会建立一个不可靠叙述者。
如果作者想表达新生代的反抗精神,为什么不用有大胆、富有创新意识的昆尼而是用对工作厌倦、百无聊赖的愣头青收银员萨米作第一人称?因为昆尼们并不缺乏反叛精神,她们不需要受到召唤和启迪,需要被召唤的是萨米们。其次,作者想利用萨米作为小镇市中心超市的收银员的视角,因为他能接触到的众生百态更多,“超市是一个城市最大众化的公共场合,最能反映一个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和道德规范取向”[6]62。文章创作的1960年是美国一个特殊的年代,二战后美国加快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步伐,经济发展带来的非理性自由放纵冲击着传统的清教徒节俭、严肃、禁欲的思想;“人们在工作过程中被物化,个性逐渐消失”[13],对个性的解放需求与工业化带来的机械支配产生冲突。此外,民权运动、女权运动、性革命运动、青年的“反文化运动”都发生在这个时期,萨米作为这个思想观念尖锐撞击年代的见证者,他眼中的世界非常有代表性。因此,萨米的“不可靠叙述”可以被刻意利用以产生张力。
文学范畴的张力,是一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制衡、相互吸引,最终收缩为一个整体的存在状态,它既克服了对作品的意义的单一性的提取,也尊重了文本构成的多样性,既其内在的非同一状态,其内在的对立与差异”[14]。在小说《A&P》中,无论是审美倾向、人物刻画,还是第一人称叙述者“我”都充满了这种内在的对立与差异。
(一)审美张力
萨米眼中的女性魅力全部都集中在了三个女孩身上,而所有对女性的贬义歧视都集中在顾客身上:第一个出场的五十岁妇女是“挑我错误为乐”的“witch”,是斤斤计较的“cash-register-watchers”之一,第二次的女性角色深有意味“house slaves”,由于超市的大多数顾客都是女性,因此“sheep”也多指女性顾客,第三次女性出场是“women with six children and varicose viens mapping their legs”[6]59,最后萨米辞职离开商店时街上依然有“some young married screaming with her children”[6]62,这些女性的形象永远符合当时审美主流的家中天使:对柴米油盐的支出精挑细算、温顺臣服不会大胆冒进、总是围着孩子转。三个女孩们则完全与之相反:鲜艳亮丽的泳衣、令人遐想的身材、前卫又自由的个性。萨米对女顾客主观的偏见和贬义与他对三个女孩的赞赏和钦慕形成了一种审美张力。
(二)人物张力
第一人称叙述由于其对他者主观地丑化和美化,极方便表达确切的情感倾向。在“我”的叙述中大致出现了四类人,一种是“我”这种被机械操控、消解自我个性的底层工作者,表现为“我”对这份工作的厌倦;一种是经理这种严肃禁欲、认真工作的清教徒,他对女孩们投放主日学校校长般的眼光(Sunday-school-superintendent stare[6]60);一种是昆尼这种崇尚放纵式自由的中产阶级的子女,身着泳衣却迈着女王般从容优雅的步伐,不由让“我”幻想她家的家庭聚会也许会喝考究的史立滋牌啤酒;第四种则是僵化守旧的顺民顾客。小说因“我”的爱憎分明深化了这些不同人物的矛盾冲突,产生了强烈的人物张力,也表达了“我”对个性创新的“爱”与对严肃守旧的“憎”。如果换成常用的第三人称叙述,会因为笔墨没有更多集中在“我”的视野和认知范围内的描写,缺乏“我”的主观色彩带来的人物张力,从而消解“我”作为无个性底层的声音。
(三)自我张力
“赵毅衡先生提出了‘二我差’概念,‘二我差’, 即叙述自我 (现在进行叙述的‘我’)与经验自我 (当年正在经历故事的‘我’) 的在信息获取、社会认知、思维判断、表达能力和年龄等等方面差距”[15],萨米的叙述自我与经验自我态度的差异形成了一种“自我”张力。
萨米在当时离开商店后的“经验自我”说的是“I felt how hard the world was going to be to me hereafter”[6]62,反抗后尽显失落和迷惘。如果说那是一种怒发冲冠为红颜的莽撞,事后总会有些懊悔得罪了父母的老朋友、丢掉了工作,但是“叙述自我”却表达出了一种并不后悔的坚定感:“Now here comes the sad part of the story,at least my parents says it’s sad but I don’t think it’s sad myself”[6]59,这个句子用了现在时的时态,而且以一种预言式叙述的方式先出现在萨米与经理吵架离职之前,是一个理性的总结,表明现在的“我”并不认为当时反抗的做法不可取。现在的叙述自我之理智顿悟与当时的经历自我之失落迷惘与形成了张力,也突出了小说的主题之一:反抗会带来短暂的迷茫与痛苦,但是不会带来信仰缺失。
四、总结
小说A&P的叙述视角是有代表性的小人物其第一人称不可靠叙述,并且读者显而易见地发现了叙述中的伦理推卸。这种不可靠性通过两个方法消解:第一,顺应文章的召唤进入机械化无个性的小人物的真实世界——通过穿插的第二人称叙述产成认同,认同僵化温顺、机械无我的不可取,认同解放自我、追求个性的美好;第二,破解不可靠性被利用的原因——通过审美、人物、自我张力的二元对立,看到当时主流的一面和真正要表达的、被主流掩盖的另一面:主流崇尚当无我顺民,而非主流号召自我觉醒。
注释:
①转引:申丹.何为“不可靠余述”?[J].外国文学评论,2006(04):134.
②转引:申丹.何为“不可靠余述”?[J].外国文学评论,2006(04):134-135.
③转引:申丹.何为“不可靠余述”?[J].外国文学评论,2006(04):1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