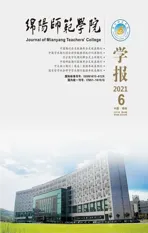《第一次的离别》的乡愁抒写
2021-12-06路美莎
蔡 颂,路美莎
(湖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湖南长沙 410081)
作为新冠疫情后影院复工上映的第一部影片,《第一次的离别》以实际行动支持着电影行业重振旗鼓,与重映中节奏紧张、视效华丽的大多数商业影片不同,本片以大篇幅的悠长远景镜头深情凝视金色故土——新疆沙雅,通过孩子们“三次离别”的经历解构了成长过程中的家园情结,利用维吾尔语和普通话并行的语言设计揭示了城乡迁移大潮中的文化失落与寻根省思。全片弥漫的淡淡乡愁不仅缓和了当下后疫情时代的焦虑情绪,也为观众打开了通往精神故乡的大门。
一、金色故土:影像空间中的深情凝视
故乡不仅赋予一个人最初的生命体验,也在漫长的岁月中伴随一个人成长,成为一个人精神与心灵上的避风港湾,作者对故乡丰沛充盈的情感成为了创作的原动力。透过作品,故乡对作者的塑造一览无余,而注视故乡,则可解码作品的情感内蕴与记忆烙印,如荣格所言:“个人原因与艺术作品的关系, 不多不少恰好相当于土壤与从中长出的植物的关系, 通过了解植物的产地, 我们当然可以知道并理解某些植物的特性。”[1]影片导演王丽娜曾说,故乡沙雅于她而言是“世界的尽头”,金色的南疆盆地神秘美丽、历史悠远,沙漠、戈壁、胡杨林勾勒出辽阔旷野,牛羊遍地,瓜果飘香的景象。沙漠、胡杨林、棉花地作为新疆地域风景中最别致的代表,在影片中传递着诗意、柔情与思念,既建构了一个幽深美丽、风情迷人的影像空间,也成全了导演对故土的深情凝视。
影片中多次出现沙漠的远景或全景镜头,一望无际的沙漠有时与夜幕融为一体,如大海一般沉静;有时在正午的阳光下散发着耀眼的金光,璀璨夺目。三位小主人公常常穿梭于沙漠中,凯丽抱着小羊回家的傍晚,三个孩子在沙丘上追逐嬉戏着,暮色下的他们成了一幅跃动的剪影;凯丽和弟弟陪着艾萨寻找妈妈,三个孩子横穿无垠的沙漠,红黄绿三个小点由近至远,在沙漠中渐渐远去,如同遥远而闪耀的星火。在纯净、广阔、平静的沙漠衬托下,孩子们的童心与真诚显露无遗,沙漠对他们来说并不是神秘莫测、危险丛生的凶险之地,而是他们玩耍的乐园、回家的必经之旅。伯格曼曾说“拍电影就是跃入自己童年的深渊”,导演王丽娜小时候曾有整夜在沙漠观看星空月夜的经历,沙漠的深邃和美丽让她着迷,她将童年的记忆与个人的体验倾注于沙漠这个独特的景象中。
作为新疆最古老的珍奇树种之一,胡杨在维吾尔语中的意思是“最美丽的树”,素有“活着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倒,倒了千年不朽”的美誉,余秋雨曾在《西域喀什》中将其形容为“灿如火阵”,因为一到深秋,形态各异的胡杨一片金色,绚美壮观,是塔里木河岸上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影片中三位小主人公的常去之地就有胡杨林,他们总是爬上一棵貌似枯死但尤为粗壮的胡杨,在树上眺望远处的天际,或是说着学校、家常的悄悄话,或是畅想着未来,胡杨林则静悄悄地听着他们的话语,唯有风过吹动叶子的簌簌声响。鲍尔吉·原野在散文集《流水似的走马》中称赞胡杨“姿态如人”,像仰天太息的壮士,像为自己包扎伤口的士兵[2]。同样,影片中的胡杨也体现出人的姿态和精神,它就如同一位历经风霜的老者,经过历史的洗练仍然驻扎在这片土地上,大漠风沙带来的苦痛和磨难都未曾使其衰落或倾倒。胡杨与少年,厚重的历史图腾与懵懂的生命记忆相互交汇碰撞,胡杨驻守着亘古不变的神秘南疆,少年们试探着充满引诱和规训的外部世界,两种意象背道而驰却又奇迹般地偶合,从而与本片的精神内核相呼应。影片以胡杨对大漠的坚守召唤出乡愁,使其存在犹如灯塔,让缥缈的思乡之情得以附体,落地生根。
塔里木棉花声名远扬,而沙雅是塔里木盆地的棉花生产大县。棉花作为最主要的经济作物之一,成为沙雅人民赖以生存的经济来源。凯丽父母出现的镜头多数都是在棉花地里采摘棉花,可见棉花对一家人生活的重要性,但棉花地在此处绝不仅仅意味着物质层面的保障,而是被映射为凯丽一家人的情感交流场域。比如几个发生在棉花地里的段落:凯丽在棉花地旁教弟弟读诗,父母采着棉花讨论姐弟俩的教育问题,一起细数未来的打算,二人微红的面庞上露出对未来幸福的憧憬;凯丽帮父母一起干农活,爸爸给妈妈唱起离婚时为挽留她写的情歌,凯丽妈妈如少女一般羞红面颊,温暖的情意在棉花地里缓缓流淌;冬季来临时收割棉杆,凯丽父母体贴彼此,总是为对方多做一些农活,二人结束劳作驾着马车迎着暮色回家,构成了一幅令人向往的田园牧歌图……在棉花地里,一家人的情感和意愿总是能得到充分的交流,饱满洁白的棉花有了精神层面的象征意义,不仅寓意着一家人的团圆美满和相互支持,也寓意着凯丽一家人对乡土的依赖和留恋。
以景传情,情在景中,沙漠、胡杨林、棉花地不仅是展现沙雅特色和南疆风土人情的自然景观,也负载着导演对故土的浓浓思恋和感恩之情,沉静的镜头和远大的景别一如导演的视线,深情凝望这些景观的同时传递出最真切的思乡之情。
二、三次离别:成长视角下的家园情结
林清玄在散文集《人生幸好有别离》中曾提到:“爱别离虽然无常,却也使我们体会到自然之心,知道无常有它的美丽。”[3]人生在世,离别虽然无常,但也是常有的事,一个人回顾自己的成长历程,不难发现人生的每个阶段都会经历离别。《背影》中的朱自清在离别的站台体会父亲的年迈与困窘,《再别康桥》道出了徐志摩离别康桥时的缱绻情思,《藤野先生》中的鲁迅倾诉了与老师分别之后的感激之情与真挚怀念……“离别”是文艺作品中常见的情境体验和人生遭遇,作为该片的叙事主题,“离别”在主要人物的经历中被反复提起,三次离别不仅勾连起了小主人公们的亲情、友情和乡情,也在成长的语境中倾诉着无法言说的家园情结。
第一次离别在影片伊始。先于电影画面出现的是一段自然的声响——牛羊家畜的呜鸣、乡民的呼赶吆喝、鞭子的飒飒抽打声,当这些声音先从黑暗中传来,声画错位的手法便让观众的身心融入了乡野的氛围里,在脑海中先验地构建了一幅人与自然、田园牧歌的乡村图景。在随之而来第一个画面里,羊群在尘土飞扬的小道上伴着铃响边吃边走,艾萨和父亲在羊群后面挥舞着鞭子,鲜活的羊群被赶进羊圈里。对艾萨一家来说,牛羊不仅是这个不富裕的农村家庭收入里的一部分,还是艾萨和哥哥不可缺少的童年玩伴。艾萨的母亲由于患病而失去了说话的能力,整日卧床不起,神志也不清醒,艾萨独自在家照顾母亲,小羊羔就成了他可以说话的对象和某种程度上的情感投射,但是凯丽和弟弟却急切地将小羊接走,艾萨无法挽留,与小羊羔迎来了第一次分别。羊羔对艾萨不仅意味着玩伴,更具有某种亲情上的羁绊,艾萨在照顾小羊的过程中获得了开心与快乐,这是沉重的家庭生活无法给予的,小羊对他来说具有了与家人同等的情感,而他与小羊的相处也满足了人类想象中的家庭氛围——艾萨担心羊羔拉肚子尚未痊愈,主动提出照顾它;追上抱着小羊离开的凯丽,为小羊搭建小窝,艾萨对羊羔负有责任感与关爱,这也是一种感情流露,他把羊羔当成了可以交流感情、付出情感、相互陪伴的家人。
第二次离别是艾萨与母亲分开。哥哥离家上学,艾萨也要完成学业,父亲的身体大不如以前,农活应付不暇,家中生病的母亲无人照顾,父亲不得已把母亲送进了养老院。母子情深,血浓于水,人类从出生起就对母亲怀有深深的依恋,羊羔跪乳,乌鸦反哺,子女孝顺父母天经地义,这不仅是情理上的呼应与回馈,也是家庭情感的基石。但母亲的离开打碎了这个家庭的完整,艾萨与母亲的亲情关系受到不可抗力的影响,造成了某种形式上的断裂,这也对艾萨的家园情结形成了威胁。心理学中认为,从幼儿在体验到与母亲分离的苦楚的一瞬间,就开始另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那便是在心里描画母亲的意象(Image)。通过想象,他感觉到母亲的依稀存在,借此缓和对母亲的渴念[4]。因此在艾萨的家园守望中,他梦想成为干部或是医生,母亲的病可以被治好,生活能得到改善,但这却在母亲后来的缺席中消泯了。文艺作品中, “母亲”往往是大地、故乡的象征,电影中“母亲”形象的缺席, 正是对故乡消失、乡土失落的沉痛隐喻[5]。在电影的最后一幕中,艾萨在暮色里的山坡上独自一人赶着羊群,与电影开头父子俩赶羊的画面形成鲜明对比,年老体弱的父亲退出了家庭的权力中心,父权发生让渡,意味着子女不得不接受成长,对家庭的守护和责任的继承构筑了艾萨新生的家园情结。
第三次离别则是女孩离开家乡。凯丽的父母决定带着一家人去库车生活,因为那里可以给凯丽和弟弟提供更好的教育环境和资源,凯丽对家乡的一切万般不舍,在母亲的提议下,她把一幅画带走作为纪念,画上她和弟弟、艾萨手牵着手一起追着火车。作为工业文明的产物,火车将现代话语引入了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打破了自然经济的状态,在都市与乡村之间架起一座互通有无的桥梁,影片中艾萨的哥哥也是通过乘坐火车离开了家乡到外地上学,于是火车在凯丽的心中负有离别的寓意。在这一情景段落中,导演使用了交叉蒙太奇,将凯丽乘车与艾萨寻羊的镜头交叉剪辑,小羊离开羊群,凯丽离开家乡,从互相照拂的族群集体转向远离乡邻的个体小家,稚嫩的他们都脱离了族群的保护,凯丽在车上望着逐渐远去的老家,神情虽然忧伤,却已不再落泪,心智上的成长在此刻已经悄然完成。家作为空间形象, 相对于陌生、广漠的世界, 它狭小却亲切, 昏暗却温暖, 平庸却安全。它荫庇童年的生长, 维系血缘的亲情, 繁衍延续生命, 传递历史的记忆与讲述[6]。艾萨和凯丽通过一次次的离别逐渐认知到家园概念,唤醒了他们对家园的守护意识,而这也从侧面抒发了导演对家乡难以割舍的情感,传递出根深蒂固的家园情结。
三、双语并行:城乡迁移背后的寻根省思
方言是一个地区的文化历史结晶,也是一种特定的环境再现,贾樟柯、管虎等第六代导演十分青睐“方言表达”,方言成为他们电影中构建小人物叙事的有效手段;毕赣、顾晓刚等新人导演也热衷于方言叙事,以此营造故事发生地与外界疏离隔阂的朦胧意境。在本片的人物语言中,方言占据了绝大篇幅,老一辈人的沟通交流使用维吾尔语,只有在小主人公们上课、读书时,普通话才成为首要选择。双语并行的设计成为这部影片的鲜明特征,一方面影片通过维吾尔语展现了新疆沙雅的原生风貌与风土人情;另一方面也从侧面暗示了少数民族向城市迁移背后的乡土文化失落和身份认同焦虑。
方言叙事不仅只是原生态地域文化的展示,更多的还将城乡身份差异带来的身份认同焦虑通过方言展现给观众[7]。这种身份认同焦虑主要体现在小主人公们的语言表达上——是否会说普通话和能否说好普通话。从影片中不难得知,普通话是新疆地区小学里一门极受重视的课程,普通话的考试与整体成绩挂钩,如果普通话成绩不合格,那么就意味着整体成绩不达标。影片通过几个段落揭示了普通话教育在维吾尔族同胞生活中的重要程度,比如父母多次谈到凯丽有待提高的普通话成绩时都忧心忡忡,凯丽在干农活、吃早饭的间隙也要教弟弟说普通话……影片结尾,凯丽妈妈为了让凯丽和弟弟拥有更好的学习普通话的环境,一家人从乡村搬至库车。从维吾尔语到普通话,从小乡村到城市,对方言的剥离和城乡迁移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身份归属焦虑。注意影片中的细节就不难发现,出走与留守是影片中人物谈话的主要内容:艾萨在葡萄架下遇到了父子三人在争论是否去城里打工,艾萨的哥哥在收拾秸秆时告知父亲要出去上学遭到父亲挽留,凯丽妈妈不止一次提议去库车继续生活但爸爸多次反对……乡村的保守落后与农活的枯燥无味使乡民厌倦,城市的先进便捷与优渥资源让乡民向往,无法避免的城乡迁移大潮此起彼伏。城市与乡村形成的二元对立看似无法取舍,但当遮天蔽日的水泥高楼取代了风吹簌簌的胡杨树林,工业废气影响了奔腾的牧马群羊,迁移必然会造成出走者的身份定位模糊和心理感知失重,而由其供养的民族文化生活和记忆也将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壤。
本片以关切的姿态审视不可避免的城乡迁移潮流,体现了导演王丽娜对乡土文化流失的关注和反思。小学生们懵懂地背着唐朝古诗,转头却欢快地唱起维吾尔语歌谣;哥哥寄来的信里介绍通往外面的火车多么新奇,凯丽爸爸妈妈却驾着马车、驮着柴垛、迎着夕阳回家;凯丽坐上轿车依依不舍地离开村子,艾萨在风雪中骑着马儿呼唤丢失的小羊……从这几组对比蒙太奇中能察觉出导演对民族文化的追寻与惋惜,对乡村牧歌的怀念和向往,对精神故乡的呼唤和重建。
四、结语
近年来,少数民族题材电影以愈发觉醒的姿态进入大众视线,其中的“乡愁表达”不在少数,张扬的《冈仁波齐》展现了前往“精神之乡”朝圣的藏民群像,李睿珺的《家在水草丰茂的地方》通过“爷爷”的去世反思了工业文明所造成的蒙古草原上生态家园的消逝,鹏飞的《米花之味》诉说从大城市返乡的傣族母亲在乡土守候与城市诱惑中诞生的矛盾心理,万玛才旦的《塔洛》解构了中年牧民走出藏地后的自我认同危机和精神失落乡愁……这些影像作品的表达风格万千,或诗意或写实,或清新或魔幻,但都不约而同地扎根于民族文化记忆的沃土。
《第一次的离别》没有刻意通过成年人的身份进行沉重批评或言说思乡苦闷,既不是从“他者”的视角关注少数民族生存现状,也不是以“归来人”的身份聚焦现代化进程下个体的孤独与迷茫,而是另辟蹊径从少年人的角度来完成对故土守望的乡愁书写。因为比成人更天真,更接近天然,更接近天道、天命,更少受到文化的感染与习染[8],所以他们的“看见”更接近本真,更能触碰乡愁的内核,影片通过朴实真挚的少年人视角表达了对乡土文化失落与精神家园失根的追问与反思,利用去戏剧化表达和散文化的手法营造清新质朴的诗意,在少年成长的语境下描画孩童守护遗落家园的情结,从儿童的角度审视了在现代生活方式影响下乡民们内心渐渐消失的文化归属感和日益渐增的身份认同焦虑,以充满诗意的口吻构筑起儿童视角的乡愁表达,为少数民族电影的乡愁视野再添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