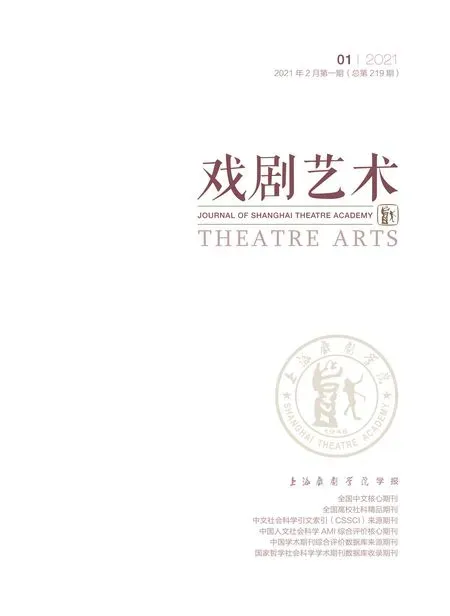从“剧本中心”到“导演中心”
——论新时期以来话剧导演与剧本关系的转型
2021-12-06杨光
杨 光
新时期以来,中国话剧发生的变化是颠覆性的。文化地震学把文学、艺术、思想史上经常发生的情感变化和转移划分为三个级度,其中最强烈的一种就是“那些剧烈的脱节,那些文化上灾变性的大动乱……这些震动似乎颠覆了我们最坚实、最重要的信念和设想……使整个文明或文化受到怀疑,同时也激励人们进行疯狂的重建工作”。(1)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詹姆斯·麦克法兰:《现代主义的名称和性质》,马尔科姆·布雷德伯里、詹姆斯·麦克法兰:《现代主义》,胡家峦等译,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2年,第3页。新时期以来,话剧艺术所发生的变化正处于这一级度。而在新时期话剧艺术所发生的诸种变化中,导演和剧本关系的转型可以说是其中最重要、最特殊、最值得玩味的一个现象。
中国当代戏剧处在一个导演主宰的时代,正如吴戈所说:
导演意识的强悍与导演群体的崛起,带领中国戏剧艺术进入了一个“导演主宰时代”。导演意识的强悍,的确是新时期戏剧舞台一个不算短的时期非常抢眼的艺术现象。因为,这个时候,导演艺术家们怀揣思想解放与观念更新后的各种奇思妙想,的的确确站在了剧目创演、艺术创造的指挥者的位置上。(2)吴戈:《中国内地新时期话剧导演研究》,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6-17页。
“导演时代”是对当代戏剧总体特征和整体趋势的概括,我们不必要去考究它是从哪一年、哪件事或者哪出戏开始的。它也并不是否定剧作家在具体剧目中的地位和功能,而是强调导演在整体上充当了当代戏剧的指挥者和引领者。无法想象,如果剧坛缺少了徐晓钟、胡伟民、王晓鹰、査明哲,当代戏剧将会何等的单调和乏味,如果没有了林兆华、孟京辉、田沁鑫、王延松,戏剧界又将少了多少话题。可以说,导演和剧本关系变化是当代戏剧研究中最值得关注的课题之一,中国当代戏剧面临的其他种种现象只有置于导演和剧本关系变化这个大的背景下才能说得清、说得透。
一、“剧作家时代”导演与剧本的关系
在论述“导演时代”下导演和剧本的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对“剧作家时代”的导演和剧本的关系做简要的梳理。
焦菊隐、洪深、朱端钧、夏淳、舒强等都是“剧作家时代”颇具影响力的导演,其中焦菊隐最具代表性。从他们对剧本的态度和操作中,我们可以窥见“剧作家时代”导演和剧本关系的几个特点。
第一,在剧目生产中,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严格分离,二者的边界很清楚,没有哪个导演会介入剧作家的构思和创作。剧本如需修改,导演也应尽可能尊重剧作家:“剧本必须进行重大修改时,导演应把意见提供作家,由作家自己动手。得到作家的正式授权,导演才可以删改”,“作家如坚持原议,无论导演情愿不情愿,最后都应当按原稿演出。”(3)焦菊隐:《焦菊隐论导演艺术》(上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第345页。
第二,在美学选择上,“再现美学”是这批导演的整体取向。“再现美学”除了主张逼真地再现生活,再现现实外,还讲究生活逻辑、艺术逻辑、剧本逻辑的协调统一。焦菊隐为人称道的一些经典的舞台处理大多“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如《茶馆》中第一幕马五爷的舞台调度。从剧本设定来看,马五爷信洋教,其社会地位高于茶馆中的其他角色。因而在开幕时,焦菊隐给他特别安排了一个在空间上略“高”于其他茶客的位置。他的下场处理更为精到:首先他戴上帽子,直面观众朝幕线方向走,继而走向舞台上的中心位置,王掌柜来请安,此时,教堂钟声响起,马五爷用手拦王掌柜,示意不要打扰自己,然后摘下帽子,右手随钟声划“十”字。这寥寥数笔粗看起来就是对生活的“复制”(生活逻辑),但它既遵循着剧本的题旨(剧本逻辑),也把焦菊隐对马五爷的态度——认为他靠着洋教耍威风——揭示了出来(艺术逻辑)。朱端钧在为上海戏剧学院1957届表演系排演的《上海屋檐下》中也有一个相似的精彩处理。林志成回家,按照习惯在家门口脱皮鞋、换拖鞋。妻子彩玉也像往常一样为他收拾鞋子,但刚转身就意识到拖鞋已经给突然登门的前夫匡复穿了,遂一时僵住,拎着皮鞋呆站着不知如何是好。林志成脱鞋后一直没等到彩玉取来的拖鞋,就自己找。最后目光聚焦在了匡复脚上。于是,他便急忙从彩玉手中取回皮鞋穿上。匡复起先不知林志成找什么,懂了之后便要换鞋。林志成更加窘迫、尴尬,让匡复不要换,两人不自然地再三推让……进门脱换鞋本是生活中很常见的家庭习惯(生活逻辑),但朱端钧却将其巧妙地搬用到舞台上。通过这个细节的处理,三个人的关系更为具体、形象地展示在了舞台上(艺术逻辑)。进一步来说,《上海屋檐下》的剧本整体风格朴素含蓄、深沉洗练,在处理这个内蕴十足的场面时宜“静”不宜“闹”,宜克制、内敛,不宜挥洒、张扬。因而,虽然舞台提示中并没有脱换鞋的调度提示,但朱端钧的这个处理算不上“僭越”,它仍然遵循着剧本的内在逻辑。
第三,在戏剧身份上,导演的定位是“作家的化身”。“作家的化身”包含两层意思:首先,导演自己在日常生活中要具备作家的能力和修养,或者说要有“作家性”。焦菊隐本人就是由文学进入导演这个行当的:“我的导演工作道路的开始是独特的:不是因为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才约略懂得了契诃夫,而是因为契诃夫才约略懂得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4)焦菊隐:《焦菊隐论导演艺术》(上册),第57-58页。因而,他特别提倡导演要多读包括剧本在内的各类经典文学作品。其次,“作家的化身”要求导演在创作中必须“体验”剧作家。这是焦菊隐呼吁导演培养“作家性”的目的。焦菊隐认为,导演不能脱离剧本在舞台上信马由缰地创作。在他看来,导演要充分把握剧作家的创作心态,理解剧本的精神要旨和整体风格,“用‘灵魂的眼睛’去看清文学作家的意图,看清文学作家笔下的生活和人物”。(5)焦菊隐:《焦菊隐论导演艺术》(上册),第109页。即使是技术成分最多、独立性最强的舞台美术部门,焦菊隐也要求他们必须“体现作者的意图,并且要突出作者的风格”。(6)焦菊隐:《焦菊隐论导演艺术》(下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5年,第673页。
整体而言,“剧作家时代”导演和剧本的关系就像书法中的“临摹”:导演要深刻把握字体的间架结构,“再现”出“原帖”的“神”。如果临摹者(导演)的文化造诣高于原帖(剧作家),完全可能超越“原帖”(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导演“抬”戏)。但即使如此,临帖也不至于彻底改头换面。
二、新时期以来导演与剧本关系的新变
导演主体意识的觉醒是新时期戏剧革新的动力之一,中国话剧在革新浪潮中逐步进入“导演时代”。
1980年上海工人文化宫剧团演出的《屋外有热流》是戏剧探索的早期成果。《屋外有热流》的诞生源于导演的魄力。导演苏乐慈鼓励剧作家大胆写,舞台上怎么体现由她来负责,贾鸿源后来说:“有了这句话才有了《屋外有热流》。”这里,导演和剧本的关系已经悄然发生了变化。
在创作《屋外有热流》时,剧作家有意识地借鉴传统戏曲和现代派的手法,探求剧作的新形式。然而,不管是写意结构还是各式各样的现代派手法都意味着导演在二度创作中不可能再恪守“再现美学”。苏乐慈鼓励剧作家“大胆写”看似解放的是剧作家,但实际上也解放了导演。因为,剧作家“大胆写”在客观上决定了导演不可能再“附庸”于剧本。为了内容和形式的审美自洽,导演必须打破传统的以剧本为中心的工作方法,寻求舞台表现的新形式。
随着戏剧探索的深入,剧作家主导的创演格局开始发生变化,导演开始以更为强悍的态势登上戏剧舞台。
80年代初,导演胡伟民追问“我是谁”:
古希腊戏剧演出中的合唱教师?中世纪欧洲宗教演出中的圣职执事?文艺复兴时期的莎士比亚、莫里哀、洛佩·德·维加、哥尔多尼?18世纪魏玛剧院院长歌德?19世纪的奥地利天才里夏·瓦格纳?20世纪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戈登·克雷、梅耶荷德、布莱希特、彼得·布鲁克、格洛托夫斯基?中国的汤显祖、冯梦龙?……
他们是“我”,又不是“我”。
我们共同担负一个职务——导演。然而,昔日的光荣属于他们,今天的追求属于“我”——当代导演。(7)胡伟民:《导演的自我超越》,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44页。
胡伟民这里特别强调的“我”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导演不只是一项“职务”、一个“工作”,更是一门独立的艺术。因为,作为“职务”“工作”,任何具备职业技能的人皆可胜任,并不需要“我”的在场。只有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我”才有价值,才不可替代。第二,导演的创作可以相当自由,“无法无天”(胡伟民语)。作为“当代导演”,“我”可以,也应该在戏剧中有自己的追求、探索和思考。
胡伟民的态度充分彰显了导演主体意识的觉醒,标志着中国话剧开始向“导演时代”挺进。胡伟民虽然没有明确表示“当代导演”与剧本应该以何种关系相处,但是,“当代导演”一旦觉醒,便不可能满足于继续充当“作家的化身”了。随着导演主体意识的觉醒,导演与剧本的关系在几个重要维度上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第一,阐释立场的变化。过去,导演的阐释要求以剧作家为中心,焦菊隐甚至鼓励导演“研究作家的其他著作”,以便“更能体会他的艺术风格”。新时期以来,导演对剧本的阐释开始“以我为主”:剧本本身讲什么不重要,导演从剧本中联想到什么、生发出什么成了舞台呈现的重点。例如王晓鹰导演的《伏生》就偏离了剧作家的预设规定而显示出极强的导演色彩。从王晓鹰过去的作品来看,他喜欢将角色“逼”到极端情境中,深入地描摹、刻画人物的内在冲突。从早期执导《雷雨》时删除鲁大海,到后来选择外国经典作品《简·爱》《萨勒姆的女巫》《哥本哈根》等来“拷问灵魂”无不体现了他的这种偏好。《伏生》亦是这一审美取向的延续。对比《伏生》的剧本和演出,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差异。《伏生》的原剧本是一出以喜写悲的现代悲喜剧:伏生不惜生命保护《尚书》以求文化多元,最后却阴差阳错地导致了“独尊儒术”的文化悲剧,其中不乏荒诞和讽刺。但在王晓鹰的舞台阐释中,伏生在极端情境下的抉择成了重心,严肃的悲剧性成了演出的基调,原剧本中弥漫的喜剧色彩被王晓鹰大大削弱了。《伏生》不是个例。在当代话剧舞台上,导演创造的实际的演出形象与剧本所“提示”的演出形象之间的张力正日益扩大。
第二,剧本操作方式的变化。过去,一度创作和二度创作泾渭分明,几乎没有导演介入剧作家的工作。新时期以来,导演开始不同程度地参与到剧本的修订中。王培公在动笔写作《周郎拜帅》之前已经和导演王贵达成了“编、导协议”,《桑树坪纪事》的导演徐晓钟也是从一开始就和小说作者和戏剧改编者共同讨论,参与剧本写作和改编。查明哲只要接手原创剧目,就会和剧作家频繁交流。总之,他们的“导演构思”直接影响了剧作体例和样式的选择。90年代后“出道”的田沁鑫为了充分实现其构思,直接亲自操刀写作剧本。她在剧坛的部分影响力也正源自其“编导合一”的工作方法。随着导演群体的日益强势,这种情况逐渐发展到极端。不少年轻导演拿到剧本匆匆阅读后,就开始向编剧提出各种意见,并以“退出剧组”为由,要挟编剧根据自己的要求修改剧本。还有的已经成名的导演索性在排练场自己即兴修改剧本。甚至还有一些“大导”直接“雇佣”编剧根据自己的呈现需求而写作。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当代话剧编剧正在群体性地沦为“写手”。这一变化是导演和剧本关系转型中最明显、最受人瞩目也最有争议性的现象。
第三,剧本观的变化。“剧本观”指的是导演者在剧目生产中对剧本功能、地位的总体认识和基本态度,其大体上可划分为中心主义剧本观和材料主义剧本观。前者重视剧本,肯定剧本的地位,主张剧本是“一剧之本”,后者把剧本视为导演创作的素材。过去的导演普遍视剧本为中心,强调“一度创作”的基础性地位。当代导演的剧本观开始由中心主义向材料主义倾斜,林兆华排《哈姆雷特》声称自己不替莎士比亚说话而是为自己说话,这是对中心主义剧本观的公然挑战。在他看来“导演排戏,我颠覆这个剧本都可以”。(8)张弛:《中国当代戏剧名家访谈录》,北京:团结出版社,2017年,第95页。孟京辉对此也有一个形象的比喻,他认为导演类似于“主厨”,剧本只是他烹饪的素材。
总之,当代导演不甘于“死在演员身上”,不甘心“藏”在剧本背后,他们要成为“演出的作者”,要“活在舞台上”。
根据导演对剧本创作介入的程度,导演和剧作家的关系大体上可分为合作型和主导型。在前种关系模式下,导演根据自己需要,同时结合剧作家的个性风格、剧本的思想立意,对剧本进行删减、修改、调整、修正。它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一度创作的独立性,最终呈现在舞台上的成果还能多多少少地看到剧作家的影子。后一种关系模式中,导演成了绝对的主导者,导演根据自己的整体构思来组织、操作、编排剧本。在这种关系中剧作家沦为附庸、“写手”,剧本降格为材料。
每个导演在不同创作阶段、面对不同剧本,会选择不同的处理方式,比如任鸣早期做过一些经典解构的尝试,后来还是回归到了现实主义的美学轨道上。査明哲对于当代剧作家的剧本一般介入程度较深,会花费大量时间和剧作家共同打磨剧本,但对于经典外国剧本就不会做太大的改动。但是,这些阶段性的、局部的差异并不影响对一个导演整体倾向的把握。
如果对当代导演做一个粗糙的划分,“合作型”的导演包括徐晓钟、胡伟民、査明哲、王晓鹰、任鸣、王延松等。“主导型”的导演以林兆华、孟京辉、田沁鑫、李六乙、牟森以及不少受“后戏剧”美学影响的青年戏剧导演为代表。就美学上而言,前一派导演虽然广泛糅合了象征、表现等手法,但大体上仍保留了现实主义的美学框架,风格上呈现出开放的现实主义的态势。后一派导演则彻底颠覆了现实主义的美学传统,另起炉灶,探索全新的戏剧美学支点。他们共同形塑了中国当代戏剧的美学格局。
三、导演与剧本关系转型的世界性和本土性
导演和剧作家、剧本之间关系的转型是戏剧发展的世界性潮流。
20世纪以来,剧作家和剧本受到排挤,“导演中心”逐步确立。20世纪初,戈登·克雷就断言:“诗人不是属于剧场的,他从来也不是出身于剧场,将来也不可能是属于剧场的。”(9)戈登·克雷:《论剧场艺术》,李醒译,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6年,第4页。之后,一批强势型导演陆续登上戏剧舞台。俄国有梅耶荷德、塔伊罗夫,德国有皮斯卡托、布莱希特,法国有阿尔托、普朗雄、姆努什金,他们都主张以导演为中心展开戏剧创作。梅耶荷德强调导演是“独创性的艺术,而不是从属性的艺术”,导演“应该在想象中建造起‘剧本的第二层楼’。无论如何,剧本对于戏剧不过是材料”。(10)A·格拉特柯夫:《梅耶荷德谈话录》,童道明译编,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6年,第44页。布莱希特没有明确为导演张目,但其叙述体戏剧理论客观上与“导演中心”形成了呼应。在叙述体戏剧中,舞台各元素都具有了独立意义:“美术家和音乐家重新获得他们的独立性,能够用各自的艺术手段去表达主题。整个艺术作品作为可以分离开来的各种成分展现在观众眼前。”(11)布莱希特:《布莱希特论戏剧》,丁扬忠等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0年,第64页。当舞台元素开始获得独立意义,导演——作为建立演出统一性的角色——就必然承担更为重要的职能。上述导演中影响最大的是阿尔托。阿尔托把导演视为戏剧“唯一一位创造者”:“戏剧的典型语言是围绕导演而形成的,导演不再是剧本在舞台上的简单折射度,而是一切戏剧创造的起点。”(12)安托南·阿尔托:《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桂裕芳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93年,第90页。在他看来,以剧本为中心设计演出是戏剧的沉沦:“当戏剧使演出和导演,即它所特有的戏剧性部分服从于剧本时,这个戏剧就是傻瓜、疯子……反诗人和实证主义者的戏剧”。(13)安托南·阿尔托:《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第36页。他所推崇的巴厘岛的戏剧正是“排除了剧作者,而强调西方戏剧术语中的导演”。(14)安托南·阿尔托:《残酷戏剧——戏剧及其重影》,第54页。阿尔托的观念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英国导演彼得·布鲁克,他说:“如果我们听到一个导演在大谈什么为作者服务,大谈什么让剧本自己来说明自己,那我心中就会疑云四起,因为这是最困难的事。如果你只让剧本说话,那就可能连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15)彼得·布鲁克:《空的空间》,刑历译,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第37页。
随着“导演中心”的确立,戏剧舞台上开始出现经典剧作的多元化演出形象,这些演出形象都凸显出较强的“导演性”。例如,在1954年马雅可夫斯基剧院演出的《哈姆雷特》中,导演奥赫洛普柯夫用监狱式的大铁门代替台口大幕,同时在铁门划分的格子中嵌以皇族图案和锋利的铁刺。这样的处理显然不同于读者阅读剧本时对《哈姆雷特》的一般想象,它带有鲜明的导演色彩。1926年梅耶荷德导演的《钦差大臣》的影响力在导演史上更大,以导演来命名这次演出在西方已成惯例。梅耶荷德在排演中凸显了自己的理解,剧本只是触发他剧场灵感的素材。在梅耶荷德眼中,《钦差大臣》展示的是一架“贿赂机器”,这是他由剧本生发出的演出主题。梅耶荷德在该剧中所做的探索都是沿着他所理解的这个演出主题来操作的。比如,在公众盛情款待完“钦差”赫列斯达可夫后,赫列斯达可夫醉醺醺地回到自己住处,栽倒在一张椅子上。此时,十五个官员为了邀宠专门来向赫列斯达可夫行贿。导演没有让他们轮流依次出场,而是创造十五个人“集体行贿”的效果:舞台上的十五扇红色木门同时打开,十五个官员以机械式的步伐、体态迈入室内,唱出他们的“台词”。而赫列斯达可夫以同样机械的节奏和动作“收礼”。借助这种形式,梅耶荷德在舞台上打造出了这台脱离了果戈里而专属于导演的“贿赂机器”。
多元化的演出形象是导演崛起的必然产物。如今,以导演为中心的“舞台写作”已经成了一种创作趋势,法国导演普朗雄的这番话可以说是当代导演的共同信条:“一场演出既是剧本的写作又是舞台的写作;而这种舞台写作……的重要性是与剧本写作同等的……舞台写作得负起所有的责任,正如写作(我指的是小说或剧本的写作)本身一样。”(16)转引自宫宝荣:《“主仆”-陌路-伙伴——20世纪法国剧作家与导演关系的演变》,《戏剧》,2011年第2期。
随着改革开放,戏剧的导演化思潮逐步影响到中国,中国当代导演与剧本关系的转型成为这股世界性浪潮中的一朵浪花,中国的话剧导演以其特有的创造力丰富着世界戏剧舞台。但是,应当注意的是,当代话剧导演与剧本关系的转型发生于特定的背景下,故而呈现出鲜明的本土特征。
第一,从戏剧体制的角度看,中国当代导演和剧本关系的转型发生于国家化戏剧高度挤压民间戏剧的背景下。西方导演崛起时,欧洲的商业戏剧已经获得了充分的发展。当时,以导演为中心的各种“先锋派”某种意义上是一种“反商业”的探索。反观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没有动摇国家化的戏剧体制。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大量剧作家为了生存只能根据政府的命题、订制而写作。在这类写作中,“政治保险”是重中之重,因而对剧本的审查也异常严格。剧作家在这种生产体制下只能畏手畏脚地先图“审查通过”,其独立性相当有限。剧作家李宝群直言说:“由于各级领导对戏剧剧目审查把关相对其他艺术门类还是比较严格,你写得过于尖锐、直接,或对复杂的社会生活把握得不准确,就会出麻烦。”(17)李宝群:《对辽艺戏剧的再思考》,李宝群:《从梦想到现实:李宝群戏剧随想集》,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6年,第123页。这样一来,要想保证剧场演出的魅力,只能寄希望于导演的二度创作。这是中国导演与剧本关系转型的“先天不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话剧导演的崛起是话剧艺术在现有生产体制之下所展开的一次自我拯救:它试图通过二度创作的转型来填补剧本审查造成的审美塌陷。
第二,从戏剧本体建设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导演和剧本关系的转型发生于戏剧的文学性未获得充分发展,戏剧精神充斥着虚假、平庸、反智、自恋的背景下。20世纪,西方导演崛起时,戏剧文学早已取得了卓越的成就。之后,导演固然风头十足,剧作家却也从未落于下风。易卜生、斯特林堡、契诃夫、奥尼尔、阿瑟·米勒、田纳西·威廉斯……如果20世纪缺少这些剧作家,仅仅靠导演之力,那也只是一个残缺的“导演的世纪”。反观中国,“剧作家荒”“剧本荒”一直都很严峻。以国家话剧院为例,自2000到2013年,国话本院编剧可为剧院提供原创剧本的仅有3位,其中还包括已经去世的李龙云和已经退休的过士行。青年编剧的从业状况也不景气,培养职业编剧的戏剧文学系的毕业生大量转行。(18)详可参阅陆军:《青年编剧成长机制缺失刍议》,《戏剧》,2015年第6期。少数坚持从事剧本写作的,也主要以影视剧为主。
除了“量”的贫乏,“质”的问题更令人堪忧。90年代以来,中国话剧始终存在一股“文学焦虑”,学者们不厌其烦地呼吁着“戏剧的文学性”。这种“文学焦虑”源于当代剧本原创力的疲软,想象力的缺失,戏剧主体意识的匮乏:一方面,大量的对畅销小说的跟进式的改编盛行剧坛,原创作品少;另一方面,戏剧家在思想文化的开掘和创造上几乎没有提出什么新的东西,甚至一些作品连文学叙事的基本功都不过关,就像剧作家何冀平所说:“一些剧或电影,从头到尾不知要说什么……没有立意,让观众去想,美名曰‘非现实主义’。”(19)张弛:《中国当代戏剧名家访谈录》,第74页。剧本质量的低下导致导演不得不“出手介入”。因此,当代话剧导演之所以显得“强势”,与剧作家群自身的退化不无关系。如果剧作家在人性的开掘、情节逻辑的梳理、舞台手段的化用等方面都能做到让导演改无可改,导演和剧本、剧作家之间自然会达成新的平衡。
第三,从戏剧文化的角度来看,中国当代导演和剧本关系的转型发生于启蒙的现代性尚未实现,“人”的地位和价值尚未获得充分尊重的背景下。西方现代导演的出现是同“导演-剧本”转型同步的,它们都发生于理性出现危机的历史时刻。过去,社会有相对统一的观念,舞台上的统一性不必依靠导演就能形成:“协调存在于剧院创作之前。和谐产生于一个由各种不可分割的因素而组成的社会,其共同的思想感情存在于一个‘戏剧的观念’中。”(20)杜定宇编译:《西方名导演论导演与表演》,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10年,第469页。20世纪初,古希腊奠定的、到启蒙时期发展至顶峰的理性文化开始遭到质疑:“从根本上说,存在着这样一种事实——或者,我该说我的论据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一直以特殊‘理性’方式组织了空间和时间知觉的那种统一宇宙论已被粉碎。”(21)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134页。人们开始经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的现代性体验。于是,剧场内需要有人专门负责建立演出的统一性,现代导演应运而生:“现代导演者的基本职责应该是运用综合与体现的统一原则,为一个分裂了的社会提供这些现在已经失去的道德标准。”(22)杜定宇编译:《西方名导演论导演与表演》,第470页。因此,某种意义上而言,西方导演的集体崛起是质疑理性的产物,是文化地震后吁求重建的产物。这个文化背景是中国所不具备的:20世纪以来,戏剧文化在革命的牵制和政治的干扰下始终与启蒙疏离,实现启蒙现代性、确立“人”的价值和主体性地位对中国而言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中国的发展状况还远未达到“反思理性”的程度。这既是中西导演和剧本关系转型最深层的差异,也是我们今天审视、评价导演和剧本关系转型的重要标准。
结 语
过去,剧作家主导着剧目创演,剧作家的高度就是戏剧的高度。北京人艺的“三驾马车”(曹禺、老舍、郭沫若)无一例外都是剧作家出身。观众看一出戏首先关注的也是“编剧”,看戏主要看的是剧情。在这个剧作家“当家”的时代,导演的创作被严格限制在剧本提供的总体情境下,即使像焦菊隐这样颇负盛名的导演也必须严格恪守“二度创作”的边界。如今,导演取代了剧作家成了话剧艺术的主宰者,观众也早已习惯以导演来命名一台演出,甚至一些导演还形成了一批忠实拥趸。这究竟是最美好的时代还是最糟糕的时代,是中国话剧希望的春天抑或失望的冬天?
剧作家刘锦云说:“当今的戏剧舞台看上去局面繁荣,但在很大程度上是靠导演撑着。我不是逞别人志气,灭编剧的威风,是事实如此”,“中国当今戏剧的智慧集中到导演身上来了。”(23)整理自刘锦云在上海戏剧学院“青年导演研修班”上的发言。另一位剧作家赵耀民则对“二度创作”非常不满:“对于我所有的剧作,人们只要读剧本就够了,看不看演出都没关系,不看更好。”(24)赵耀民:《三十年戏剧创作自述》,《南大戏剧论丛》,第十三卷(2)。两位剧作家的不同态度彰显了导演与剧本关系转型的复杂性。导演和剧本错综复杂的关系让戏剧的前行变得挣扎且茫然。我们享受着导演在剧场里创造的果实却时常怀念着“剧作家”这个旧情人,我们目睹着导演以一己之力支撑着戏剧这艘巨轮挣扎着前行却仍然期待着导演和剧本的“复婚”。导演和剧本究竟该如何“相处”,各自有什么样的“权利”“义务”,二者在何种层面上应同心协作,又在何等层面上可能产生冲突、如何化解等等都是戏剧界亟待回应的问题。
目前,学界普遍关注到了“导演-剧本”关系变化这一现象,但系统性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对其评价也常失之于片面:或认为“导演时代”顺应了世界戏剧发展的潮流,导演和剧本关系的转型即是中国戏剧现代化的表征,应给予充分的肯定;或批评其放逐文学,呼吁退回到“剧作家时代”。本文是对这一现象的宏观勾勒,以期引起学界对这一现象展开更为深入的学理性探讨。考虑到问题的复杂性,有关这一现象的不少问题都还未论及。比如目前不少戏曲剧本会特邀话剧导演来执导。在这类作品中,话剧导演与剧本的关系已经远远超出“剧本中心”还是“导演中心”这个话题,它还与现代戏曲、话剧与戏曲的关系等重要的学术问题扭结在一起,绝非只言片语能讲得清。从这个角度而言,本文所提供的也只是关于这个话题的“剧本”,它具有独立的生命,但更期待有不同的“导演”来丰富、阐释甚至解构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