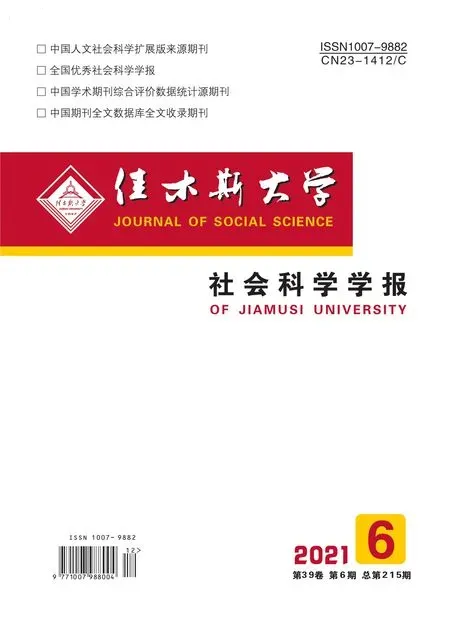感悟诗学:梁宗岱象征主义诗论的东方神韵*
2021-12-06李韦佳
李韦佳
(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感悟是一种借助印度佛教内传,同时又融合了老庄之道、儒学心性论、禅宗及其理学而不断中国化的诗性哲学。感悟由哲学、宗教而生活化、审美化,不断展开自己复杂的层次与结构,并最终渗透于中国诗歌的各个层面,成为中国诗学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1]。有别于分析式、逻辑式的西方诗学,中国的感悟诗学具有整体性、直觉性的特点,诗人凭借真诚、聪慧的心灵体悟万物本真的神秘,体认万物返本求源的方式,以此作为切入生命与文化、人生与宇宙的结合点,并在此基础上追求物我合一、心与物冥的审美境界。这种感悟思维对于鉴赏文本、诠释经典、解读理论具有独到的作用,不仅能很好地与西方分析式的思维互释互补,而且还能为人类诗学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然而,在中西文化激烈碰撞的二、三十年代,中国传统的一切权威性的观念都在“打倒孔家店”中瓦解,老子“善者不辩,辩者不善”的主张自然也被西方的思辨、分析、归纳、演绎所取代,各大理论主张、“主义”涌入诗歌领域,模仿外国诗进行文艺创造几乎成为通识,传统的感悟诗学也由此陷入了沉寂与反思。
沐浴着“五四”风潮长大、又赴欧游学六余年的梁宗岱,在“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的呼声中,并没有陷入全盘西化的泥淖,而是理性思考中西传统诗学的利弊得失,既注意对西方的象征主义思想做本土化的选择、处理,又尝试以中国古代的诗学主张来阐释西方思想,做到了中西互释、融会贯通。在诗歌形式方面,他并未一味鼓吹新体诗、贬斥旧体诗,既看到新诗的工具“极富新鲜和活力”,也看到新诗的“贫乏和粗糙之不宜于表达精微委婉的诗思却不亚于后者(指旧体诗,笔者按)底腐烂和空洞”[2]157。由此,中国传统诗学的精髓及其独有的感悟式思维方式也得以顺利融入梁宗岱自身的诗学建构中,为其诗论增添了一丝东方神韵。
具体而言,本文将从感悟对梁宗岱诗学文体的影响和感悟对其诗学观念的浸染两个方面分析梁宗岱诗学中的感悟特性。
一、生成与建构:感悟对诗学文体的影响
感悟性思维首先影响了梁宗岱诗学文体的生成和存在形态——其诗学的产生方式是感悟式的,存在形态是零碎、松散的。中国古代诗歌、诗论注重直观体验,诗歌往往是随意记录逸闻趣事和瞬间感悟所得,诗歌鉴赏也多以直觉的、情感的、浑然感悟的方式进入作品,因此中国诗话的呈现面貌多是松散、杂乱、零碎的而非体系性建设的。即便《文心雕龙》这样“体大思精”的文论专著也是刘勰在学习佛教经学后有意识模仿、建构的结果,千百年来也只是偶有所得,并不成大气候。梁宗岱的诗论文章多是触景生情、遇境感兴之作,或是针对某个具体问题阐发的个人意见所作——如《论诗》是与徐志摩书信往来时,念及前信“‘《诗刊》作者心灵生活太不丰富’一语还太拢统”所做的“申说”[2]26;《论崇高》是与朱光潜关于“sublime”一词的翻译争议引申而来——这显然是传统感悟思维引发的诗人自身审美领悟与创造激情的结晶。这种浑然感悟和直觉印象式的切入方式使其不受西方先在的象征主义框架和现成的理论束缚,而是注意把握批评文本的内在感受力和自我审美体验,思想为灵感所鼓舞,艺术体验随心灵而倾泻,自然也就形成了其诗论单篇文章整体、浑融,而诗论总体却以零碎、松散的形态存在。
审美体验与智性思考相融合的诗歌批评方式是感悟性思维影响其诗学文体建构的第二个表现。直觉、感性、整体的思维方式并不意味着传统诗论家排斥“理”的存在,相反,这种浑融整体的态度还使论者具备了更强的知识吸纳性与包容性——这使其在鉴赏诗歌时不以裁决判断自居,而是以发现和阐发为己任,呈现出一种审美体验与智性思考相融合的“直觉的情感的理”。梁宗岱学识广博,他不仅在诗学方面对传统诗歌和西方象征主义诗歌有深切、透彻的把握,而且在音乐、绘画、雕塑等方面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在其文论集《诗与真》《诗与真二集》中,既有《谈诗》《论诗》等论诗的篇目,还有《论画》《黄君璧的画》等专谈绘画的文章。即使是一些文论篇目,他也能在感兴之时广征博引,援引相应的音乐、造型艺术来为自己的观点做支撑。如《论崇高》一文,从其产生方式来看,是梁宗岱与朱光潜就“sublime”的翻译问题激烈辩论后提笔所作,显然具有感悟思维的特征。然而其中也不乏智性:梁宗岱从自己的审美感悟出发,不仅对朱光潜理论的来源克罗齐的“直觉与表现”说以及康德的《判断力批判》进行了分析评判,而且细致分析了画作《摩西像》《蒙娜丽莎》,交响乐《第三交响乐》《月光曲》和小说《罪与罚》的片段来为自己的观点支撑。从审美体验出发,论点直击要害,论据广征博引,论述条理清晰,不仅具有相当的说服力,且其关于“艺术最高的力”的阐发又颇具启发性,令人叹服!
智性与感悟性思维相融的特点使梁宗岱的诗论书写方式具有独特性:智性使其文章涉理,而感悟则使其文章含情。彭燕郊曾将之概括为:“既文情并茂,又逻辑严明”,李振声则称其是“以诗的笔触探涉理论问题”,都是相当准确的。当然,梁宗岱天性的浪漫情思、诗人的敏感心性也都是其笔端含情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梁宗岱的诗论文章中,繁复却又不失灵动的意象、新奇却又不失精妙的比喻可谓俯拾皆是,如《论诗》中梁宗岱分别以纸花、瓶花、生花比喻艺术的三种境界;《年轻的命运女神》中他以“群蜂”隐喻诗人思想的活跃;在《论画》中为表现“力的实现”的境界,连用六个比喻,一气呵成、气势磅礴。还有《保罗·梵乐希先生》那美妙的开篇:
当象征主义——瑰艳的,神秘的象征主义在法兰西诗园里仿佛继了浮夸的浪漫派,客观的班拿斯(Parnasse)派而枯萎了三十年后,忽然在保罗梵乐希身上发了一枝迟暮的奇葩:它的颜色是妩媚的,它的姿态是招展的,它的温馨却是低微而清澈的钟声,带来深沉永久的意义。[2]7
梁宗岱将象征主义比作法兰西“诗园”中一朵“瑰艳”的花,形象地展现了法国文学流派纷呈的繁荣景象以及象征主义诗歌在其中的地位和扮演的角色;“枯萎了三十年”表明象征主义所遭遇的困境,以及它有待发展的前景;绽放的“奇葩”,展现了梵乐希对象征主义的继承和发展;“迟暮的”与“妩媚的颜色、招展的姿态”巧妙组合,暗示象征主义呈现出不同于以往青春艳丽的、沉静又舒展的魅力;“温馨”“低微”又“清澈”的钟声既轻颤人的心房,又好似象征主义经过蜕变时那一句“哦”的低声轻叹,“深沉永久的意义”也就在这一声轻叹中自然而然地表达出来了。繁复而新奇的意象,视觉、听觉在一个套一个的比喻中巧妙联结,整段话都是一种诗意的表达。李振声先生所述“整个论述过程,意象纷披,元气淋漓,甚至颜色妩媚,姿态招展,显得既华美又铺张”[3],大概也是由此而来了。
二、渗透与选择:感悟对诗学观念的浸染
感悟式的思维方式不仅影响了梁宗岱诗论的外在形态,还影响了梁宗岱对诗歌从创作缘起到酝酿、物化最终至批评鉴赏的全过程的认知与理解,使其在构筑自己的诗学大厦时,有意无意地去选择、发展与感悟思想相契合的诗学观念。本文即从诗歌创作的缘起、酝酿、物化及鉴赏的全过程来条分缕析感悟思维在梁宗岱诗学中的具体体现。
(一)创作缘起:诗人之悟
这里的“悟”即指灵感、感悟。梁宗岱看来,作品形成的第一阶段即是接受灵感。而灵感的来源可谓多种多样:
“山风与海涛,夜气与晨光,星座与读物,良友的低谈,路人的咳笑,以及一切至大与至微的动静和声息,无不冥冥中启发那凝神握管的诗人的沉思,指引和催促他的情绪和意境开到那美满圆润的微妙的刹那……”[2]320
这给艺术创造带来无限希望的同时,也为其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基于此,西方象征主义者形成了一种带有神秘色彩的艺术观念,如马拉美把诗人的唯一使命归为“对大地做出神秘教理般的解释”,瓦雷里则认为诗歌真正的美属于彼岸世界。但在梁宗岱看来却并非如此,他一方面否定了文艺的神秘性,指出文艺创造“并非神出鬼没的崭新发明,而是一种不断的努力与无限的忍耐换得来的自然的合理的发展”[2]320;另一方面也表明灵感最大的来源是生活,诗人要创造文艺,就应当“热热烈烈地生活,到民间去,到自然去,到爱人底怀里去,到你自己底灵魂里去……”[2]29
无论诗人是在长久时间内获得的人格感化,还是一时一地的创造冲动,这种明显具有“触景生情”与“遇境感兴”色彩的感悟实际上都只是一种纷乱、紧张的情绪,是一般人都能拥有的、浅层次的感悟。梁宗岱认为,艺术家应具备一种超乎常人的宇宙意识。凭借这种宇宙意识,诗人能“从破碎中看出完整,从缺憾中看出完满,从矛盾中看出和谐”“纷纭万物于他们只是一体,‘一切消逝的’只是永恒的象征”[2]105。对此,梁宗岱专门对李白和歌德进行了分析,认为李白能打破人生“狭的笼”、以豪放飘逸的胸怀体认造化之神工,歌德能以热烈而又不失理智的情感察宇宙万物之幽微,与他们宇宙意识的丰盈大有干系。实际上,梁宗岱提倡的这种宇宙意识正是中国传统“天人合一”观念的现代化阐述:古人把世界万物看作一个彼此交融、不可分割、相互影响的有机整体,在这个整体中,万物皆有灵性。而梁宗岱叙述的“我们只是大自然的交响乐里的一个音波”“我们眼前无量数的重大或幽微的事物与现象”乃至“空气的最轻微的动荡”都会影响我们的生活”[2]74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含义。在这“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整体观念下,诗人们于是不得不以宏观整体的视角思考人与自然、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并从中参悟宇宙人生的奥义、获得艺术的灵感了。
(二)作品酝酿:陶醉与澈悟
梁宗岱认为,诗歌创作需要作家进入一种陶醉的心理境界。在这种境界里,诗人放弃了自我的动作与认识,主客体之间的分辨变得模糊,其心灵也逐渐宁静并且慢慢沉入一种恍惚的形神两忘的非意识状态——“近于空虚的境界”。在这难得的 “真寂空间”,没有什么能够阻碍诗人对世界的感悟与沟通了:
“我们内在的真与外界的真调协了,混合了。我们消失,但是与万化冥合了。我们在宇宙里,宇宙也在我们里:宇宙和我们只合成一体,反映着同一的荫影和反应着同一的回声”[2]89。
值得注意的是,梁宗岱在阐述象征主义这个观点时运用的“空虚的境界”“真寂”“万化冥合”等都是与道家的“虚静”“物化”思想相通的。梁宗岱以这样独特的悟性发现中西共通之处,并适时用带有明显的中国传统特征的语言阐释西方象征主义的观点,既便于理解,又能引发读者在学习西方理论时对中国传统诗学的联想,打通了传统文论与西方象征主义理论之间的壁垒。而这种中西互释的阐述方式显然是梁宗岱有意为之:其在阐释时还专门提及并翻译了波德莱尔在《人工的乐园》中对这一观点的一段具体论述,以此进行更直观的中西比较、互释,充分展现梁宗岱促进中西方文学观念融会贯通的良苦用心。梁宗岱正是以这样一种独特的悟性和匠心为象征主义诗学观的阐释增添了一丝东方神韵。
当然,梁宗岱也意识到要使艺术的表现成为可能,则诗人进入陶醉、形神两忘的境界后,对事物的领悟应是一种“澈悟”,是“更大的清明而不是迷惘”。这种“清明”当有两重性:它不仅是指诗人沉静于自身、对自我内心的精微省察,还应该是指诗人对“外”认识的透彻深刻。由此,梁宗岱认为诗人“在某种意义上是两重观察者:“他的视线一方面要内倾,一方面又要外向。”对内的省察使他探涉灵魂的奥妙,对外的探索让他参悟宇宙的玄机,二者相生相成,互相激荡。正如其在《谈诗》中所言:“我们对心灵的认识透彻,愈能穷物理之变,探造化之微;对于事物与现象的认识愈真切,愈深入,心灵也愈开朗,愈活跃,愈丰富,愈自由”[2]84。
(三)走向文本:感悟物化
然而,任何绝妙的感悟“无论在心灵里如何玲珑浮凸,如何肢完体固,必定要写在纸上,画在布上,或刻在石上才能够获得确定的形体,才能够决定它是否达到最高或最完美的程度。”[2]323文字作为诗歌的物化工具,从某一意义上来说,“不独是传达情意的工具,同时也是作品底本质”。由此,诗人必要利用文字去暗示灵感的全部。这种作品本质观及其对文本语言和形式的高度重视正是梁宗岱对重视诗歌语言本身的象征主义产生兴趣的原因之一。
针对感悟语言化、文本化的物化问题,西方象征主义反对浪漫主义的直抒胸臆,提出了寻找“客观对应物”的非个人化情感表达。主张诗人用一系列的事物、场景、事件来表现诗人某种特定的情感。这样借助客观对应物来表达诗人情感主张与中国传统的“即景生情、因情生景”很相似,梁宗岱也不反对将象征理解为“情景的配合”。但他强调,情景的配合应有“程度分量的差别”。结合王国维的“境界说”,梁宗岱将情景关系分为“景中有情,情中有景”和“景即是情,情即是景”两个层次。认为将情感、生命与景物的一一对应只是把抽象情感附着在外物上的简单比附,即“景中有情,情中有景”,此时物与我之间依然各存其本来面目,是诗歌境界中的较低一层,也是对象征的肤浅理解。真正的情感移植,或曰真正深入的情景关系,应当是“依微拟义”。诗人将自己的心情“印上那片风景”,物我浑融合一,诗人已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由此,梁宗岱对朱光潜视象征为比附的说法提出了批评,认为把象征作为意象浑融的“兴”,能够应用于作品的整体,“而拟人或托物可以做达到象征境界的方法”,但若如朱光潜所言象征即是比附,则象征的含义就肤浅化在了“修辞学底局部事体”中去了。由此,梁宗岱进一步明确象征应具有的特征:(一)融洽或无间;(二)含蓄或无限。这里所谓融洽,便是指“一首诗底情与景,意与象底惝恍迷离,融成一片。”[2]66
其次,感悟物化形成的文本本身也应具有可感性和启发性,这就需借助诗歌语言的暗示性与音乐性。暗示是指诗歌文本中以某种隐蔽性的表述来代替直接陈述、促进读者去猜测的方式,其本身就极具启发性为象征主义者们进行过多方面的阐述,如瓦雷里曾表示诗歌语言具有“文字的空白”,诗歌“含混朦胧的产生正是阅读者深沉的标志”。梁宗岱也认为诗歌语言应当有暗示性,诗人在创作时应注意使语言的经营与意象的排列,使其“暗示给我们意义和兴味底丰富和隽永”。这样,诗歌才能够“藉有形寓无形,藉有限表无限,藉刹那抓住永恒,使我们只在梦中或神底瞬间瞥见的遥遥宇宙变成仅在咫尺的现实世界。”[2]67这里的音乐性是指内在于诗歌的通过声调、节奏、格律表现出来的能与音乐艺术构成类比关系的音乐性[4]。象征主义诗人们赋予音乐性以极高的地位:诗歌应该是“被强烈地节奏化了的”(瓦雷里),诗人是“节奏的仆人”(马拉美)。梁宗岱更是把节奏视为艺术的生命,把音乐视为最纯最高的艺术境界。梁宗岱认为,“把诗提高到音乐的纯粹境界”“一切象征是人殊途中共同的倾向”[2]20。不仅如此,梁宗岱指出,诗歌不能离开芳馥的外形,因为其深沉的意义正是“随着声、色、歌、舞而俱来”。这种富有音乐性的文字不仅能够“引导我们深入宇宙的隐秘”,而且能“令我们重新创造那首诗”。
(四)读者鉴赏:密契妙悟
诗人遇境感兴、即景生情,在其无意识的宇宙观念作用下,思考人与宇宙、个体与社会的有机关联,看出矛盾中的和谐、破碎中的完整,并由此进入心凝形释、万化冥合的陶醉境界,最终经过长期的打磨与萃取,将抽象的思想物化为具体的存在——作品。读者既可以从中“认识作者的人格、态度和信仰”,还可以“解析出作者的人生观、宇宙观、艺术观”,甚至“重新组织其灵魂活动的过程和背景。”因此,梁宗岱认为,文艺的欣赏与批评应把作品当作“评判一切艺术家的主要的,或许唯一的标准”。这种做法似乎忽视了文艺的外部研究,“容易流于孤陋”“流于偏颇”,对此问题,梁宗岱作出了解释:
我以为一个作家之所以为作家,不在他底生平和事迹,而完全在他底作品。概括地说,一个诗人底生活和一般人并没有很大的差异;或者,假如他有惊天动地的事迹而没有作品,他也只是英雄豪杰而不是诗人。而在另一方面呢,一件成功的文艺品第一个条件是能够自立和自足,就是说,能够离开一切外来的考虑如作者底时代身世和环境等在适当的读者心里引起相当的感应。它应该是作者底心灵和个性那么完全的写照,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那么忠实的反映,以致一个敏饶的读者不独可以从那里面认识作者底人格,态度,和信仰,并且可以重织他底灵魂活动底过程和背景[2]209。
因此,即便是梁宗岱将文艺欣赏划分为了两条道路,(即“走外线”——对作家的批评鉴赏不从作品着眼而专注于他的种族、时代、环境,和“走内线”——直叩作品之门,以期达到它的堂奥。)但是其文学批评实际是以作品为鉴赏中心的。而且他不仅自身以作品为中心鉴赏文本,还呼吁读者也以作品为中心去获得感悟。梁宗岱这种将作家人生经历、感悟与作品、时代连接为一个有机艺术生命整体的做法,既是传统文学中宇宙生命意识与整体思维的展现,又与西方的作品中心论相区别,不仅抓住了感悟式批评的根本,还具有鲜明的独特性。
在作品中心的基础上,梁宗岱指出文艺欣赏应是“读者与作者间精神的交流与密契;读者的灵魂自鉴于作者灵魂的镜里。”[2]88这其实是相当有难度的:因为一首伟大的诗是作者最高且最深微的精神活动,对其鉴赏批评自然也需要鉴赏者有相当的悟性,并且付出“意识的更大努力与集中”,才有可能完成在作品里“分辨、提取和阐发”伟大诗歌中所蕴含的启示的任务。这并非所有人都能做到,梁宗岱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故在文中对一些评论家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他们虽然自称为批评家,但实际上是心盲、意盲、识盲的,他们在看不懂或领会不到时,“只下一个简单严厉的判词:‘捣鬼!’‘弄玄虚!’”[2]89。
那应当如何达到“精神的交流与密契”境界呢?除了上文所述“意识的更大努力与集中”,梁宗岱还提出了两个办法:其一,增强自我的阅历与经验。如梁宗岱谈到自己能对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和歌德《一切的顶峰》有所感悟,正是其登高经历的贡献。其二,妙悟。梁宗岱在文中引用严羽《沧浪诗话》中“大抵禅道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表明不仅作诗需要妙悟,读诗也需要。梁宗岱认为:
“一切最伟大的诗都是直接诉诸我们底整体,灵与肉,心灵与官能的。它不独要使我们得到美感的悦乐,并且要指引我们去参悟宇宙和人生底奥义。而所谓参悟,又不独间接解释给我们底理智而已,并且要直接诉诸我们底感觉和想象,使我们全人格都受它感化与陶熔。”[2]99
参悟不仅是间接解释给理智,更是直接诉诸感觉和想象。梁宗岱这一说法明显与西方象征主义主张用理智分析诗歌的做法区分开来,他更强调读者自身的感觉和想象,主张读者“全人格”都受作品的“感化与陶熔”。
综上,感悟思维成为理解梁宗岱诗学理论的外在形态与内在观念的一条重要线索:它不仅造就了梁宗岱独特的诗论文体形式,还影响了梁宗岱对诗歌从缘起、酝酿、物化最终至批评鉴赏的全过程的认知与理解,使其构筑了自己独特的诗学大厦。梁宗岱在感悟思维的影响下,一面有选择地吸纳、改造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理论,使其具有中国本土化的特色,促进了象征主义诗学在中国的传播;一面积极寻找传统诗学与西方象征主义的共通点,既以传统诗学阐释象征主义观念又以象征主义观念解读中国古代诗作,赋予了传统诗学现代性意义,促进了传统文学的现代化转换。梁宗岱的这种尝试与努力不仅契合当时的时代环境,为“新诗发展的分歧路口”指引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方向,而且对中国当代诗歌如何自立于世界,如何在保有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吸收外来文化等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