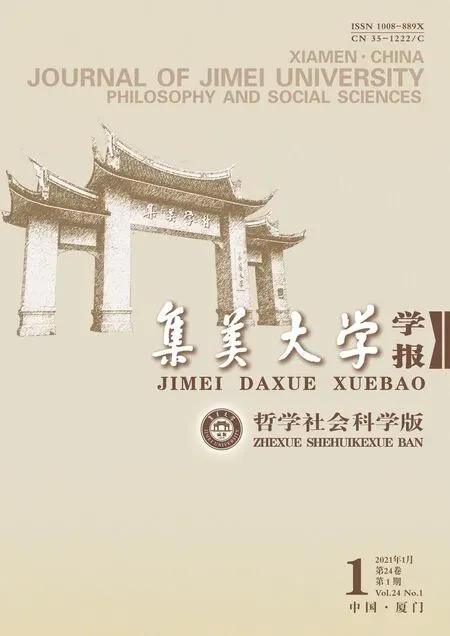抒情场景的重构与抒情角色的重塑
——论陆机《拟古诗》对“古诗”的改造
2021-12-06庄筱玲
庄筱玲
(集美大学 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魏晋时期,随着文人诗传统的形成,诗歌中的拟作现象开始出现,并形成“拟古诗”这一文类。陆机逐篇模拟汉代“古诗”的《拟古诗》十四首(1)陆机的《拟古诗》,《文选》只收录了十二首。有学者指出,另外两首应是陆机集中的《驾言出北阙行》(拟《驱车上东门》)和《遨游出西城》(拟《回车驾言迈》)。见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本,1983年,页22。本文依其说。便是其中最早的一组著名作品。不过,这组作品给人留下一种矛盾印象:它亦步亦趋地追随原作,甚至“用严格的对仗呼应原句”[1],“如今人摹古帖是也”[2],但是,它又总给人“不似”的感觉,如贺贻孙《诗筏》所说:“陆士衡拟古,将古人机轴语意,自起至迄,句句蹈袭,然去古人神思远矣。”[3]143-144这种“不似”到底是模仿的失败,还是陆机有意为之呢?当代大多数研究者倾向于认为这是有意的偏离,有学者指出陆机拟作是有意地以典雅化、繁缛化的修辞来“提倡某种新风气”[4],更有论者指出这正是陆机本人“呈才诗学”的体现。[5]这些观点突破了视“拟诗”为“二手”之作的偏见,也有利于我们认识这组诗在六朝时为何评价颇高。不过,仅从修辞效果或呈才动机来评判这组作品,似乎还未能真正揭示其在诗歌史上的意义。黄金明先生认为,这组拟作反映了西晋时期由“为情造文”到“从诗做诗”的创作观念的变化,[6]是颇有见地的见解。“从诗作诗”不仅体现出对于“诗艺”的有意追求,更蕴含着自觉的文本对话意识——拟作并非消极的模仿或被动地接受“影响”,作为对诗歌传统的一种体认,它以主动的姿态“具体反映了对于时间上属于‘过去’的作家作品的辨认与想象”。[7]从这个意义上说,陆机的《拟古诗》仿佛“通过一面有分析能力的镜子去观察原物”[8],并透过这样的诠释拓展出新的表达可能。陆机的《拟古诗》对“古诗”的改写,并不仅仅是修辞上的踵事增华,而是有改造“古诗”之“抒情表现”的深刻用心。
一、场景构设与叙写的客观化
读过《古诗十九首》的人大概都会对诗中一个个鲜明生动的场景印象深刻:楼上思妇,叹息青春寂寞;出游的士子,难消失意与无常的悲哀;宴会陈唱,放言无忌;月下徘徊,忧心悄悄;折芳寄远,衷情难诉……葛晓音先生曾将汉魏诗歌的叙写特点归纳为“场景片段的单一性和叙述的连贯性”,“许多汉魏诗歌的叙述和抒情往往只是通过一个时间地点相同的场景片段的描写来完成的。”《古诗十九首》“也是只取一个场景,在场景的书写中层层抒发感情”。[9]在这样的叙写中,景物元素与人物活动、情感反应自然交织在一起,诗歌场景是抒情角色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并透过抒情角色的所见所闻所感,随着抒情角色心理流转的历程“自然”地呈现。也因此,在这样的诗歌中,并没有形成明晰的、定型化的叙写结构,而是触情而起、随事而发,无拘无束。
陆机的拟诗保留了“场景的单一性”,可谓得“古诗”之“体”,但我们也发现,在陆机的多首拟诗中,“古诗”那种写景叙情浑沦一体、不待安排的呈现方式被打破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古诗《明月何皎皎》与陆机的拟作:
明月何皎皎,照我罗床帏。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客行虽云乐,不如早旋归。出户独彷徨,愁思当告谁?引领还入房,泪下沾裳衣。(古诗)
安寝北堂上,明月入我牖。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凉风绕曲房,寒蝉鸣高柳。踟蹰感节物,我行永已久。游宦会无成,离思难常守。(陆机拟诗)
原诗从主人公在明亮的月光中失眠写起,由失眠起而徘徊,然后便接以人物的独白。月亮只是偶然的抒情由头,诗在触物起兴的入题之后,迅速转入“情感反应”。而陆机拟诗,则围绕“月”的意象进行精心描摹:以主人公原本的安寝与明月的直“入”表现月光的惊扰,又以月光的“照之有余辉,揽之不盈手”暗示可望不可即的惆怅,再以“凉风绕曲房,寒蝉鸣高柳”写出月下室外环境的冷冽与寂静,之后才是游宦无成的叹息。在这样的叙写中,“景”被独立出来,成为浓墨重彩的部分,“景物铺写”与“情感反应”平分秋色,诗歌结构形成明晰的三段式:入题—铺写—反应,而原诗中或“居”或“游”的暧昧不明的场景,也被提炼、重构为“月照—思归”这一经典情境。
一方面是“景”被设计得充满情感暗示意味而得以凸显,另一方面是“景”的呈现与“情”的抒发均被纳入极有步骤的程式化结构中,这使得陆机拟诗中的场景仿佛是个精心构设的抒情舞台,我们的目光首先被有序的舞台布景占据,然后才看到人物登场独白。我们不再是由角色引领着去感受都市的繁华、季节的变迁、郊野的荒凉、宴会的热闹、春天的活力,而是一开始就置身于对象化的景物之中。比如《拟西北有高楼》,原诗开头四句对“楼”的描写,关注点并不是“楼”本身,而是以楼的高不可攀和封闭性,写出了楼上歌者在楼下听曲者心中难以接近的印象。陆机拟诗则将笔力贯注在对楼的“瑰伟”的描摹,用“峻而安”写其堂皇与庄严,用“出尘冥”“蹑云端”营造其脱离尘俗的姿态,为下文出场的佳人之孤高无偶起到暗示作用。又如古诗《青青陵上柏》,写都市景观并没有精心组织的描写顺序,只是顺着主人公边走边看即目所见记录下来:“洛中何郁郁,冠带自相索。长衢罗夹巷,王侯多第宅。两宫遥相望,双阙百馀尺”,在凌乱随意中恰恰写出一个初到大都市的卑微士人惊讶、新奇的心态以及目不暇接的感觉。陆机拟诗则围绕都城的“气派”与“热闹”两个方面进行着意刻画,描写顺序显然经过精心安排,由远及近,由大及小,由建筑到人物:“名都一何绮,城阙郁盘桓。飞阁缨虹带,层台冒云冠。高门罗北阙,甲第椒与兰。侠客控绝景,都人骖玉轩”。
此外,“古诗”中非常突出的季节流转的景物意象,也往往是通过诗中角色的视角来呈现,囿于当下即时的感受。如《明月皎夜光》写秋夜之景,季节的变易是在夜深不眠者的谛视与聆听中被“自然而然”感觉到的。陆机拟诗则致力于营造整体性的季节变化场景:“岁暮凉风发,昊天肃明明。招摇西北指,天汉东南倾。朗月照闲房,蟋蟀吟户庭。翻翻归雁集,嘒嘒寒蝉鸣”,由宏观的天象到细小的生物,由天地间的整体变化到具体个别的感应,秩序井然,仿佛是对“天地运转”这一观念的有步骤的图解。
除了对景物的有序刻画之外,与“古诗”相比,陆机拟诗还更多地以人物动作姿态的描摹来代替直诉其情的表达。与“古诗”或借物起情或借事发端之后便转入抒情独白不同,陆机拟诗往往把情感反应分解为“人物愁苦姿态的描摹+抒情独白”,使得人物的动作姿态也成为被流连把玩、悉心刻画的对象,从而凸显于抒情场景之中。比如,古诗《行行重行行》开头六句以辽远的空间来展现别离的情境,此后的相思、哀怨、自解都是围绕这一“阻隔”的情势而作倾吐,对思念“姿态”的直接描述则只有“衣带日已缓”“思君令人老”“努力加餐饭”三句。而陆机拟诗只在开头一句“悠悠行迈远”交代了离别的事实后,即转入对思念“姿态”的多方描摹,如“戚戚忧思深”“思君徽与音”“伫立想万里,沉忧萃我心。揽衣有余带,循形不盈衿。去去遗情累,安处抚清琴”,对思妇忧思郁结、伫立远望、揽衣自怜、抚琴纾闷的情态和动作一一描画,仿佛透过一双第三者的眼睛从旁窥探。再如《拟迢迢牵牛星》,原诗虽也有“纤纤擢素手,札扎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的描摹,但终归是为了通过无心纺织来强调织女的哀伤孤苦。陆机拟诗则把人物的姿态作为描写重点,以“粲粲光天步”写人物盛装华服地行走于灿烂天河之上,以“牵牛西北迴,织女东南顾”写两人深情回望,而“华容一何冶,挥手如振素”已全无日复一日独自织作的寂寞,反而流露出对女性妩媚姿态的从容把玩。拟诗最后四句更用连续性的动作刻画人物踮足企盼、举首落泪的痴怨情态。其他如《拟涉江采芙蓉》将原诗中“采之欲遗谁”的怅然发问改写为“采采不盈掬,悠悠怀所欢”,将“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化为“沉思钟万里,踟蹰独吟叹”;《拟兰若生春阳》结尾以“引领望天末,譬彼向阳翘”替换原诗的“谁谓我无忧,积念发狂痴”,都是将情思借由深具画面感的动作表出,在人物的主观视角之外加入客观性视角。
如果说,景物犹如舞台布景,人物的动作姿态犹如戏剧表演,那么,陆机的拟诗便是通过对“景物”与“姿态”的强调,将抒情场景客观化、距离化,从而将“古诗”笼罩于抒情角色主观视角、主观情思之下的“对面倾诉”式的抒情变为仿佛通过“第三者”观察、转述的步骤分明的展示。如古诗《庭中有奇树》,由主人公见到庭中那棵奇树“绿叶发华滋”蓦然兴感写起,展现其折芳欲寄、路远莫致、“但感别经时”的层层涌现的心理活动,全诗都是抒情主人公对着不在场的对方深情诉说。陆机拟诗则先以“欢友兰时往,迢迢匿音徽。虞渊引绝景,四节逝若飞。芳草久已茂,佳人竟不归”六句交代背景,然后才是主人公的出场:“踯躅遵林渚,惠风入我怀。感物恋所欢,采此欲贻谁”。“感”的部分被压缩到只剩两句,全诗好像是通过一个第三者的介绍“写出了一个有头有尾的故事”。[10]38古诗《行行重行行》全是以思妇的口吻追溯当年的离别,忧伤当下的阻隔,猜测对方不归之因,感喟年华的流逝。陆机拟诗则“话分两头”,先写思妇的忧思之深,再转到游子的角度写其思乡之情、归乡之难,最后又回到思妇,仿佛是两个人物隔空对话的客观展示。
因此,在陆机的拟诗中,“古诗”中那种极具情感冲击力的直言诉说通过有意构设的抒情场景,被拉远了距离,成为一个个可供把玩的“戏剧情境”,人物仿佛躲入了重重帷幕之中,“减却许多率真之素质,与磅礴之力量”。[11]146拟诗比起原诗给人以“含蓄”或“隔膜”的感觉或许就源于此。
二、抒情角色的重塑与托喻化的解读
陆机拟诗从抒情表现上对“古诗”的另一个改造,是对游子、思妇角色的重塑:通过改造人物的精神内涵,拟诗一方面呈现出贵族文人的“身份感”,另一方面在单纯的相思、失意之情中引入托喻指向。
面对离别、失意、人生无常,“古诗”中人物的“反应”基本上是质朴直接、“情感直觉式”的:或陷入无可奈何的伤怨,或沉溺于及时行乐的颓放,浸透了怆痛的激情。相应地,诗中的抒情角色也具有真率无隐、爽朗鲜明的性格。陆机拟诗中,抒情角色变得典雅矜重起来,多了一份情感的克制和伦理的自觉。古诗《行行重行行》中的思妇对良人抛下自己、“相去万余里”有着深深不解与埋怨,在长久的等待中,有“浮云蔽白日,游子不顾返”的猜疑和年华老去的惊慌,最后劝慰自己“努力加餐饭”,表达出对现实无可奈何的感受。陆机拟诗则一味强调思妇的执着与深情,她不但未曾质疑游子为何不归,而且始终不悔,结尾的“去去遗情累,安处抚清琴”更带上玄思色彩,这显然已不是现实困境中焦虑重重的思妇,而是抒情情境中忠贞自守的理想化人物。至于《拟青青河畔草》,更是把原诗中抒情角色“昔为倡家女”的尴尬身份改换成良家少妇,将原诗中难耐寂寞、有“挑逗”嫌疑的独白变为“空房来悲风,中夜起叹息”的守情不渝的等待。
台湾学者梅家玲曾指出:“从曹植开始,诗人为思妇代言,往往是为了排解一己的‘失志’之憾,因而成为自我欲望、焦虑的转化投射。即使有些作品未必有比兴寄托之意,其所认同、图现的‘思妇’,也是‘应然’成分多于‘实然’成分的理想中人物。”[12]陆机拟诗中的思妇,正可作如是观。
陆机《拟古诗》中的“佳人”也或多或少带着作者的自我投射。“古诗”《东城高且长》和《西北有高楼》均刻画了一位善于弹琴理音的女性,抒情主人公在听曲之际,为悲伤的音乐打动,进而产生对歌者的倾慕,不过,歌者的形象虽然突出,诗中叙写的重点却均在于音乐的悲哀和听者的感动。而在陆机的两首拟诗中,叙写的重点被转移到歌者技艺的高超或者容貌的美好。《拟东城一何高》以“长歌赴促节,哀响逐高徽。一唱万夫叹,再唱梁尘飞”渲染歌者的技巧变化及惊心动魄的演出效果,强调歌者才气的超凡。《拟西北有高楼》与“古诗”“重在写其哀”相比,则“重在写其美。”[13]不管是出神入化的技艺还是倾国倾城的美貌,其实都是“美质”的象征,高楼上的寂寞佳人也因此有了“贤才不见用”的自矜意味。拟诗中芳草美人之意最为显明的莫过于《拟兰若生朝阳》,“古诗”中“兰若生春阳,涉冬犹盛滋”只是托物起兴,拟诗则以“嘉树生朝阳,凝霜封其条。执心守时信,岁寒终不凋。”表达托物明志的明确意涵。
这种“身份意识”和托喻色彩也体现在陆机拟诗对“游子”形象的重塑上。如《拟青青陵上柏》,“古诗”的主人公是“斗酒相娱乐,聊厚不为薄。驱车策驽马,游戏宛与洛”的卑微人物,繁华气派的都市并不属于他,他到这里来只是凑热闹与看热闹。陆机拟诗中,主人公则是“方驾振飞辔,远游入长安”,除了“多一层贵游子弟的豪华气派”[11]137外,还有一份意欲有为的自我期许。又如《拟今日良宴会》,贺贻孙《诗筏》说:“古诗从欢娱后,忽尔感慨,似真似谐,无非愤懑。”[3]144拟诗则把这种带着愤懑意味的宣泄变为郑重其事的自我激励。正如马茂元先生所分析:“……说得这样的冠冕堂皇,大有左思《咏史诗》‘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的气概”。[10]98再如,拟《回车驾言迈》的《遨游出西城》、拟《驱车上东门》的《驾言出北阙行》,或将建功立业、修身立名的志向明白道出,或感喟深沉、慷慨勃郁,一改“古诗”玩世不恭的怀疑主义态度。
经过这样的改造,“古诗”质朴单纯的游子、思妇之辞被拓出“比兴寄托”的解读空间,后世对《古诗十九首》的解读即多有沿着这个路向的,如张庚《古诗十九首解》论《青青河畔草》说:“凡士人不能安贫而自炫自媒者,直为之写照矣”,刘履《古诗十九首旨意》亦云:“言青青之草,郁郁之柳……以兴世俗轻进之人,自炫以求售……且不斥言之,而婉其词以倡女为比,其深得诗人之托讽之义欤。”[14]最为典型的是清代王闿运的《拟古十二首》,这组诗乃是仿照陆机《拟古诗十二首》而作。十二首前各有一小序,评析古诗意旨与陆机拟作与原意之异同。王闿运将《西北有高楼》至《明月何皎皎》的九首古诗归为枚乘所作,认为其中指涉着枚乘“择主之思”“去京游梁”“追念故恩”“刺浮薄大臣”“念国”等等意涵,而余下三首也都是不得志的贤人君子之诗,他认为陆机拟作除了少数篇章与原作之意旨相合,其他的则或“反其义也”,或“但为伤别”,或“辄改其意”。[15]姑且不论王闿运的解读是否牵强,他虽然质疑陆机,但实际上是却是沿着陆机的方向把《古诗十九首》的托喻意义进一步放大。
三、“文本对话”与抒情范式的转化
陆机《拟古诗》是文学史上对“古诗”的第一次大规模拟作。陆机拟作“古诗”的具体动机是什么并没有留下明确的记载,是否与其入洛后的心境经历相关也是颇有争议。陆云《与兄平原书》曾载:“一日见正叔与兄读古五言诗,此生叹息欲得之。”[16]正叔指的是西晋诗人潘尼,这里的“古五言诗”或当指汉代无名氏古诗。潘尼的“叹息欲得之”,说明了这些“古五言诗”的魅力,但也透露出这些诗在当时流行的程度并不高。后来被视为中国诗歌史上无可逾越的抒情经典的“古诗”,此时或许还较少进入文士们的视野,所以才让潘尼一见之下有惊艳之感。我们不妨推测,强调“诗缘情而绮靡”的陆机敏锐地觉察到这些古诗的抒情价值,因此意欲摹拟而改进之。
陆机认同“古诗”淳挚深厚的情感表达——从潘尼与陆机共读“古诗”时的叹息,我们不难想见二人对于“古诗”叹赏服膺的态度,作为一个“悲情的感物者”[17],他对于“古诗”人生无常的悲感无疑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和强烈的共鸣。(2)陆机《文赋》中以“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最早归纳出“感物叹逝”的抒情模式,“叹逝”主题贯穿于陆机的绝大部分作品中,他的《思亲赋》《叹逝赋》《大暮赋》《感丘赋》以及诸多的乐府诗都是对这一主题的直接表达。但是,作为一位具有深厚学养和理性精神的作家,陆机并不满足于诗歌创作天然自发的状态,他的《文赋》深入剖析了文学创作的运思,试图将其解析为一个可以清晰把握的过程。陆机拟诗并非机械地步趋原诗或仅凭感觉的跟随,而是探入原诗的场景,提炼、重构具有特征性的情境,这与他在《文赋》中提出的从“物”到“意”再到“文”的创造转化过程是一致的。陆机意识到写作并不是一个把人的思维活动对象(即“物”)直接呈现为文字的过程,这其中还要经过一个“意”的中介,所以,诗并不仅仅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而是要经历从“物”到“意”,从“意”再到“文”的自觉营构:从“感物而动”的经验世界到赋予这种混茫的经验以某种界限和形式,进而以文字的媒介体现此“意”。因此,陆机的《拟古诗》一方面摹写、诠释了“古诗”所展现的“情感原型”,另一方面则通过对景物和人物动作姿态的有意强调和有步骤的铺写,对“古诗”固有的抒情场景重新构设,将抒情拉开距离。“古诗”的抒情是直接进入游子、思妇的角色,通过单一视角对外
在景物、事态进行观察、描述,将内心的波澜起伏加以倾吐,陆机的拟诗则将主观视角与客观视角相结合,更细腻和多角度地观察、叙写人物的情感经验,并对这种经验做出反思,将抒情冲动与理性观照相融合。陆机拟诗对景物的铺写脱离了人物感知的束缚而趋于独立和统整化,也让诗歌场景兼具写实与象征的意味,使得“场景”有了向“情境”转化的可能。如果说,“古诗”的抒情是以“人物感知”为中心,陆机拟诗的抒情则以“情境营造”为中心。也正因为脱离了单一的“移情感知”,拟诗对抒情角色的塑造有了更多的想象空间与自由,尘世男女的悲欢离合,转变为文人存在处境的隐喻。魏晋时代,乐府、古诗中的游子、思妇角色已经积淀为高度常规化的角色,从曹植开始,诗人借由改造这些类型化的角色来塑造抒情自我,陆机拟诗也将“古诗”类型化的人物转化为文人自我呈现的媒介,寄托一份“怅焉有怀”的隐约心曲。
文学创作不仅是激情的迸发,也是激情的节制和运思的结果。从汉末古诗到“魏制”“晋造”,五言诗日渐从直觉式的素朴抒情走向意匠经营的书写,越来越深地烙上诗人的个性印记,抒情场景的距离化与抒情角色的个性化,正反映出这个时期诗歌创作的自觉追求。虽然因为过分囿于与“古诗”章句上的对应,陆机对“古诗”的转化或许不算非常成功,拟诗的情境营造难以浑融,人物形象也失之呆板,不过,通过与“古诗”的“文本对话”,陆机《拟古诗》不仅“把古诗潜藏的无迹可求的表达方式呈现出来”[6],对于“古诗”的经典化起到了重要作用,(3)以陆机的拟作为开端,汉末古诗成了六朝时期被摹拟得最多的作品,正是这组拟诗推动了“古诗”的经典化过程——钟嵘的《诗品》评论“古诗”正以“陆机所拟十四首”为“一字千金”之作,对十四首之外的“古诗”的评价则是“颇为总杂”,萧统《文选》所选的《古诗十九首》,与陆机所拟重合的也有十三首之多,现存南朝作家对古诗的拟作,所拟篇目亦基本不出陆机拟作的范围。也对我们认识魏晋时期五言诗抒情范式如何向着文人化、个性化转化有着深刻的启示。
四、结 语
陆机《拟古诗》在南北朝时期评价颇高,在后世却毁誉参半。作为“从一首诗产生另一首诗”的创作,在素来强调“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将诗歌视为诗人真实经验的记录与呈现的诗学传统中,拟古诗无疑容易招致“为文造情”的批评,然而,如果我们将文学创作视为通过文字营构和情感想象来创造个人经验与生活世界之外的一个自成意义的世界,“为文造情”其实是文学自觉的必然。陆机《拟古诗》不仅改造了原作的语言风格与修辞风格,更重要的是,它一方面依照既有文本而作,对“古诗”的抒情特质进行凸显,另一方面则通过“重写”将抒情场景加以距离化、抒情角色加以个性化,从而寓涵了魏晋时代五言诗抒情范式转化的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