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 灵
2021-12-05冷火
黄昏就这样不知不觉地爬上了墙壁,趴在那,懒洋洋地散发着热量。苏趣出汗了,近一个小时里他和对面的女子仅仅聊了些无关痛痒的话题。室内开着冷气,黄昏的热与光线有关,此外还有心情。苏趣坐在向阳的地方,阳光照在他身上。女子名叫柳遥草,遥草是真名,相亲网站要求会员必须实名认证。她自报家门时苏趣微微愣神,思忖是哪三个字。柳遥草倒是非常直接,“柳树的柳,遥远的遥,草原的草。”她这样解释。“别叫我小草,我不喜欢别人叫我小草。”她这样补充。
相亲是自我推销。如果觉得对方不错,那么接下来要尽量展现出自己最好的一面。苏趣很会表现,他彬彬有礼、谦和内敛、微笑、坐得笔直、手机调到静音模式、递纸巾时细心地折叠两下。柳遥草平静地看他,脸上没有太多表情。苏趣觉得柳遥草与众不同,他知道只有对一个人心生好感时才会有这种感觉。柳遥草是有个性的姑娘,冷静、干脆、坦率、不敷衍,她的这些特点令相亲频繁冷场。说白了,就是苏趣跟不上遥草的节奏,他总是慢半拍,硬要将自己分成两截车皮,一截真实,一截完美。他忙于不停转换,脑子里乱哄哄的,有列绿皮火车一直在开。
为加深了解,苏趣谈到了星座。他对自己的星座向来有某种自信。巨蟹座。苏趣认为这是个顾家而又温暖的星座。通过星座,他想传递一种讯息:我是个充满安全感的暖男。出于礼貌,遥草点头:“我是天蝎座,大家都说这是个变态的星座,我对星座没有研究过,对变态这个概念也不感兴趣。”遥草的一番话让苏趣颇为尴尬,他放低视线,在桌面上看了会儿橡木的纹路。他还看到了树枝的影子,风吹动树枝,他的思绪也跟着摇晃了几下。咖啡厅设有读书区,书架上有黑胶唱盘出售,苏趣觉得文艺或许可以拉近两人的距离。他将话题引向了音乐和阅读。苏趣自认为读书不少,对流行音乐也有自己的见解。他有信心把这个话题进行下去。他说:“咱们聊聊音乐和读书吧!说说你喜欢的。”
“我有文身。”遥草用纸巾沾了沾唇角。
“文身,很好啊……”
“是喜欢摇滚乐,所以才文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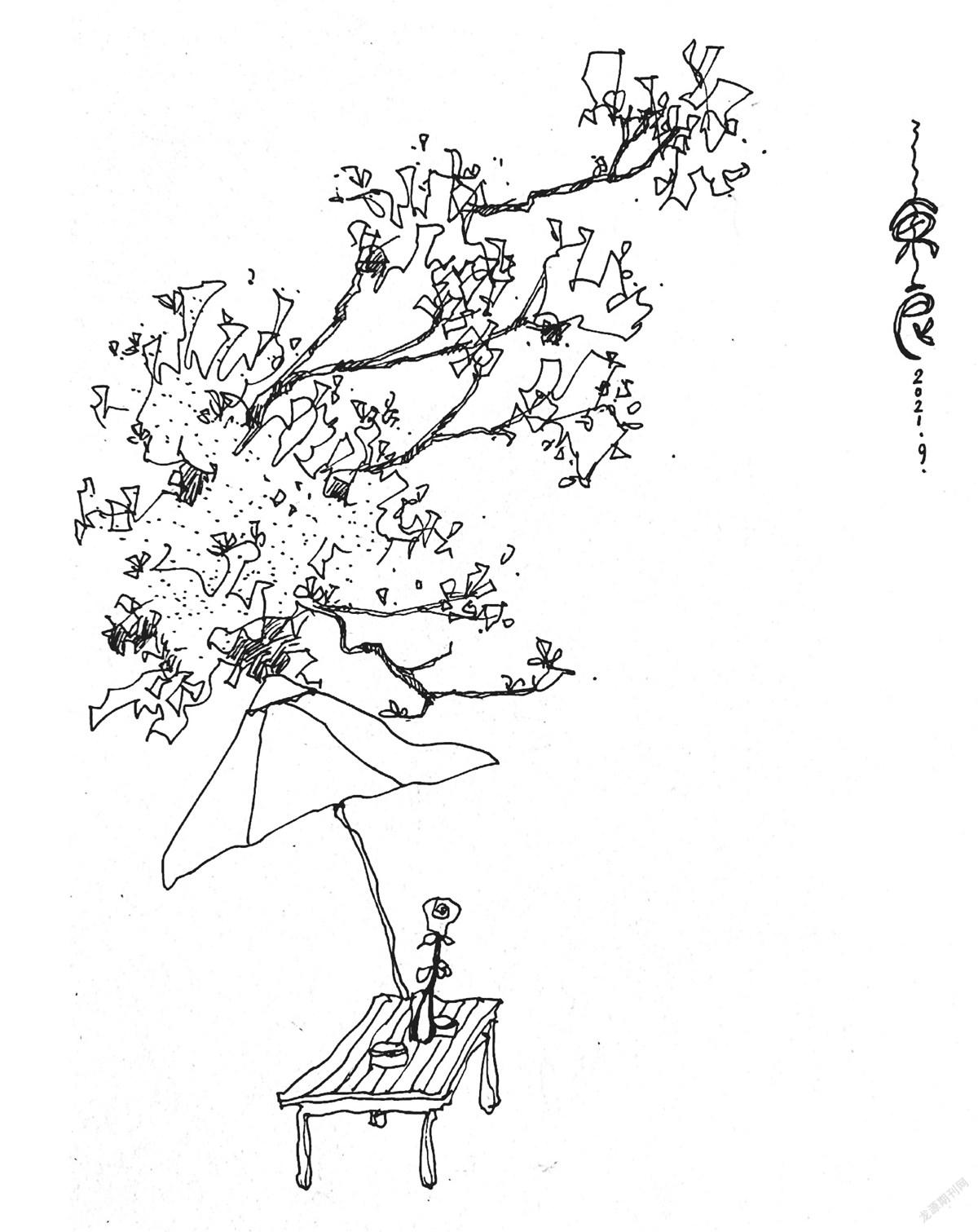
“哦。”苏趣想她或许与摇滚乐手有过感情。
“前男友是贝斯手。”
“真酷……”苏趣搞不清贝斯手是干吗的,他心里酸溜溜的,表情也发生了变化。
“都是以前的事了。今天不该提起过去的混蛋。”也许是因为苏趣的表情,遥草第一次有了真正的笑意。刚见面时她也笑过,但那是程式化的微笑。
“你问我什么?喜欢的音乐。”遥草喝了口余温尚在的咖啡,“我最讨厌流行乐,腻歪!喜欢英伦,嗯,朋克也还说得过去,总之就是那种轻快明朗的感觉,节奏一出来,心就会产生层次感,很愉悦。金属也还好吧,太重的不喜欢,有些乐手总爱急于表现。”
“英伦……是不错。邦乔维……”
“那是烂大街的,再说,他也不英伦。”
“哦,英伦……”
“ ‘山羊皮或者‘绿日什么的。”
“……”苏趣的嗓子变哑了,“改天我好好听听。”
“至于书。”遥草咬着嘴唇,眼睛专注地盯在某一点上。她思考时的表情令苏趣怦然心动。
“很难说最爱看谁写的,一个作家打动人的作品也就那么几部。看过《幻影书》?”
“没有。”
“奥斯特的,里面有句话让人印象深刻——‘她从没见过一个男人能把某样东西同时说得那么脏又那么美。”说完柳遥草笑了,又问:“帕拉尼克呢?他有本书也不错。”
“……”
“《斯通纳》呢?约翰·威廉斯。”
“也不太了解……”
“斯坦贝克喜欢吗?写过《罐头厂街》。”
“罐头……”
“就是写《愤怒的葡萄》的那个。”
“我知道这本书……”苏趣的咖啡杯被频繁地拿起再放下。他本想聊聊国内作家或者某部世界古典名著,但就遥草的反应来看,似乎已经没有继续这个话题的必要了。
黄昏爬上墙壁用了一个小时,从开爬那会儿苏趣就为它掐好了时间。苏趣有些泄气,他觉得自己像个傻瓜,此前准备的话题以及想要展现的风度在这段时间里全都变成了咖啡杯上残余的痕迹,除了冲洗时搓几下外没有任何意义。他看了看遥草,对即将到来的沉默感到沮丧。
柳遥草没有沉默:“抱歉,和我聊天是不是很无趣啊?”
“怎么会呢?我一直覺得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你是与众不同的姑娘。”柳遥草的直接让苏趣措手不及。
“你做什么工作?”遥草向后靠上椅背。“可有一直追逐的目标,或者说梦想?”
“我在报社上班,每天与新闻打交道。至于梦想……”苏趣停顿了一下,“除了想结婚,目前也没别的。哎?小时候的算吗?”
“算。”
“开一家电影院。我从小爱看电影,曾幻想开家自己的影院,放什么完全随自己喜欢。”
“看来你小时候看场电影并不那么容易。我喜欢公路电影,在汽车电影院里看一场公路电影多棒!”
“我没有去过汽车影院。小时候,父母工作忙,他们给的零花钱也很少。你呢?你在哪上班呢?”至此,谈话才真正转入相亲的轨道上。
“我?我没什么工作。写歌唱歌。就这样。”遥草舔了舔嘴角。
“唔,很酷的工作。”
“也算不上什么工作啦。随心所欲而已。”
“会出唱片?”
“说不准。就眼下来看,结婚的话,八成会成为家庭主妇。”
“嗯……”苏趣交叠着手臂。
“你在想你妈能否接受我这样的女孩儿?”
“没,没想。”
“得了吧,我看人可是很准的!”遥草又笑了。
苏趣附和着笑。柳遥草的话不假,他确实想到了父母这环,双亲一直希望他找个工作稳定、温柔贤淑的媳妇。不过,即便如此,苏趣也决意和遥草走下去。她独特的气质吸引着他。苏趣琢磨这种感觉,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从未见过大海的人,突然间站在了海边,眼前却是黑夜,是完全的海天一色,海浪声声又看不到大海的真容。她带给他无尽的想象。
“喂,你走神了。”柳遥草单手托腮,她正目不转睛地盯着苏趣。
“抱歉,我在想,在想一种感觉。”
“你坐过跳楼机吗?”遥草并不在意苏趣关于感觉的思考,当苏趣站在海边时,她想的是游乐场。
“没坐过。我怕心脏受不了。”
“你心脏不好?”
“不,挺好的啊!”
“那干吗不坐?害怕?”
“说实话吧,是有点不敢坐。”
“我也不敢坐。”
“我还以为你坐过。”
“没,一想到从那么高的地方直直下来,我就心跳加速。有机会的话,一起去坐跳楼机可好?”
“什么?”
“那就这样说定了!”
一下午的相亲时光最终变为了跳楼机之约。
约定的日子很快到来了。站在耸入云霄的跳楼机前,苏趣一个劲地直吞口水。这是个阳光充沛的周二上午,为了避开人流高峰,苏趣特意请了事假。他仰望着跳楼机顶端,细碎的光芒频频向他眨眼。
“听说这是附近几个省里最高的跳楼机。”遥草站在一旁,同样仰望高处。
“我也听说了,想不到在我们这样的城市居然有一部这么了不起的跳楼机。”
“上吧。”遥草用手肘碰了碰苏趣。
由于是工作日,游客非常稀疏,跳楼机前只有五六个犹豫的人。苏趣把心一横,坐上了圆形座椅。工作人员逐一为游客系好安全带,将安全压杠底端的插片引入卡槽。苏趣呆坐着,头脑一片空白,等他回过神来却发现遥草并没坐在身边,她回到了刚才的位置上,正笑眯眯地冲他挥手。她还为他尖叫了几声。
“喂,我说,你怎么不上来啊!不是说好一起的吗?”苏趣摇晃身子,大声喊叫。
“你先来一次试试。”柳遥草一脸坏笑地抱着肩膀。
“哎。”
几声提示音后座椅缓缓上行。刹那间,强烈的恐惧感袭遍苏趣全身。随着地面逐渐远离,城市开阔而又壮丽的景象投映到视网膜上,四周错落有致的建筑张开怀抱,呼啸的风令苏趣冷汗直流。他不得不将视线缩小在一片很小的区域内,旋转木马的圆顶、几棵松树、树下卖烤肠的手推车,他寻找柳遥草,仿佛她是他的救命恩人。她冲他挥手。苏趣喊了几声:“我还没准备好,先让我下去!”他用力挥舞双手。一切都是徒劳的。他越升越高,心脏犹如一位顶级拳手,在他太阳穴上频频挥拳。他闭上眼,因为恐惧接着又睁开了。
在最高点,他光秃秃地坐着,如同坐在光秃秃的电线杆上。这种光秃秃的感觉,可以归纳为无助,他知道接下来只能听天由命,如果机器出现安全故障,他将像蒲公英种子那样被风带入更高更远的地方,然后是坚硬的地面和尘土味。
他哭笑不得,甚至有点恨她。他看到她在笑。在她笑的同时,世界急速地下降了,是世界要把世界砸出一个大坑那样的下降。有生以来,苏趣第一次感到生命是片柔弱的草叶。
“喂,你还好吧?”柳遥草拍打着苏趣的后背,“快说说什么感觉,一会儿我还要坐呢。”
“简直就是死过一次的感觉!”
“呵,现在的你才像个正常人,我喜欢,继续说啊,我喜欢这种真实的感觉。”
“太刺激了!”苏趣失控地比画着,“这么说吧,那种,那种突然坠下来的感觉,就像有只手攥着你的心脏,从裤裆里用力往下拽出来一样!你知道吗?那种身体往下被掏空的感觉……我觉得死也就这样了,关键是,太快太快……脑子还留在上面,心就被拽到了下面,呼,太恐怖了,我不会再坐第二次了,我发誓!”
十分钟后,苏趣再次坐上先前的椅子。这一次柳遥草在他旁边。她闭着眼睛,手心里满是凉丝丝的细汗。两人的手握一起,他为她打气,看她脸上欢乐和惊恐的表情。跳楼机上行时柳遥草大声尖叫,她还问苏趣为什么不叫?苏趣说耳膜都要破了,叫不出来。他突然变得异常冷静。自打这次后,苏趣爱上了跳楼机。此后十年间,他在十个游乐场里总共坐过二十三次。他让恐惧俯首称臣,那只曾将他掏空的手再也没能从他两腿之间伸进去过。
十年后。在苏趣四十岁生日的第五天,他的老搭档、老朋友,趣味超级电影院的合伙人刘卫曾经问他为什么爱坐跳楼机,他回答:急速下降可以形成一个回忆与思考的特殊区间,在这个区间里能够屏蔽很多东西,绝对的孤独,绝对的漫长和短暂。
十年前的那天,也就是两人相亲后的第四天,苏趣和柳遙草不仅坐了跳楼机,还体验了一次空中小飞盘。“小飞盘”单从名字上看不免让人觉得有些孩子气,它孤零零地立在那里,瘦弱地挺着光杆,犹如一根营养不良的火柴。在它四周,几个简陋的套椅呆头呆脑地晃动着,风坐在上面,百无聊赖。
“咱们还玩这个吗?”
柳遥草和苏趣牵着手,两人的手随着脚步前后摆动。
“这个小意思啦。”苏趣满不在乎地说。
“这个看上去确实很小儿科。”柳遥草的牙齿连续叩打几下,像一只猛兽对猎物发出了挑衅。
“虽然不刺激,不过,”苏趣学着遥草也叩打牙齿,“不过,坐上去一转会不会晕?我对旋转项目可不怎么擅长。”一上午的光景,苏趣发现两人已经对尖叫项目产生了免疫。
“转得很慢,刚才我注意过了。”
“那好吧,上!”
乘坐空中小飞盘的游客只有四个人,除了苏趣和柳遥草还有对中年夫妇。大家相互点头,好像在说:小孩子的游戏,玩玩吧。反正又不刺激,转两圈放松放松。
睡醒后的小飞盘慢慢伸了个懒腰,风推着套椅缓缓升入空中。随着距离不断拉大,地面张开了笑脸。苏趣和柳遥草有些后悔,后悔不该把一切想得过于简单。小飞盘非常彪悍,用低调欺骗了游客,它太过简陋,置身其中才会发现它其实是个恶作剧高手。
漂浮的套椅如同一个个独立的小秋千,乘客坐在里面双脚悬空。众人在恐惧中尖叫起来,他们紧抓两旁的铁链,手心里冷汗直冒。秋千起伏,秋千升高。直到此时所有人才惊讶地发现原来这个立着的光杆是如此之高,坐在秋千上旋转如同在天空里晃晃悠悠地裸飞。小飞盘太坏了,它不像跳楼机那么实在,在瞬间带来强烈的刺激,它将恐惧的毒药缓缓涂抹到每个人的心上,从心尖开始,一点一点,乐此不疲。更要命的是除了恐惧,旋转和缓速还会令人不由自主地笑。
坐在前方的中年女子说:
“啊,受不了啦,要吓死了!呵呵,哈哈。”
她的丈夫说:
“哈哈,哈哈,太高了,什么时候停啊,怎么这么久啊!”
他的妻子说:
“哈哈哈,这东西怎么转得让人忍不住要笑?”
她的丈夫说:
“就是啊,呵呵,我想吐,我想使劲地笑,但又没法大声笑出来。”
他的妻子说:
“呵呵呵呵,根本就没法大笑,心里太痒痒了。”
她的丈夫说:
“我快不行了,不行,闭上眼还是一样害怕,一样忍不住要笑。”
柳遥草和苏趣也是相同的状态。
苏趣说:
“我们上当了,呵呵,呵呵,我都淌泪了!”
柳遥草说:
“啊……我根本叫不出来啊!呵呵呵,还得坚持多久啊,我再也不坐这个了!”
小飞盘在空中足足转了六分钟,在高空里将欢笑与恐惧完美地拼接在一起,所有人都是哭着笑的。
一天将尽,苏趣和柳遥草坐在游乐场中心的长椅上看夕阳。两人不约而同地感到这是一个谈论婚嫁的绝佳时机,就像电影在落幕前总要对观众有所交代。
“他大爷的,那个小飞盘太能搞了。”遥草掏出烟,用目光询问男伴是否也要。
“是啊,他大爷的,安乐死也就这样了。”苏趣没有吸烟的习惯,但还是点了一支。
“我说,”遥草将烟和呼吸送入晚风:“和我在一起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变坏了?”
“哦?有点吧。开始动不动地说脏话了。”
“什么嘛,其实这就是你本来的样子嘛。”
“我以前并不将脏话挂在嘴边。”
“那又怎样呢,人总要宣泄情绪吧,我一直喜欢让自己更真实一些。”
“我是不是比以前真实了呢?你觉得。”
“哼哼,比在咖啡店里故意寻找话题时真实多了。那时你可是位‘无趣先生。”
“现在呢?”
“马马虎虎吧。”
“我还没有你的联系方式,也没听过你唱歌。”苏趣的手悄悄爬上了遥草的指尖。
“别那么土气好不好?嗯……你相信,相信一种冥冥之中的,唉!说缘分也很土气。”遥草皱皱眉头:“怎么说呢,就是那种心灵感应吧!你相信吗?”
两人沉默片刻。
“灵。”遥草弹落烟灰。
“风。”苏趣脱口而出。
“风灵!”遥草兴奋地叫出声来,“对对!就是这种感觉!两个人想要对彼此说的话会随风传到各自心上,风的灵魂就是如此。完美!”遥草攥住了苏趣的指尖。
夕阳将光照涂上遥草的脸颊,一丝风在她发线里隐没。苏趣看着她,觉得她是他人生中最美的一幅画。
“其实……”
“其实什么?”柳遥草歪歪脑袋。
“其实你也可以偶尔试试流行乐。”
“我明白你的意思。没有必要太自我,对吧?”
“嗯。偶尔大众一下也不错啊!”
“谢谢啦,我会认真考虑的。”柳遥草莞尔一笑。
夕阳的光逐渐深沉起来。
“我说,我们,你看……”苏趣注视着遥草的侧脸,夕阳在他眼睛里跳动着。
“一周后给你答复。或者就此别过,或者给你生儿育女。”
“这怎么还是两个极?”
遥草侧转身子,意味深长地看着苏趣:“因为我还有夢,需要做个了断。”
“梦?”
“梦想啊。我说过的,如果结婚我就做一个家庭主妇,那样的话也就不能与乐队继续追逐理想了,毕竟大家是一个整体嘛。不是说告别就告别的。”她停顿了一下又说,“喜欢一个人会不自觉地变得像他一样,需要改变很多自我,要做出抉择。我是个认真生活的人。”
“改变……但是,结婚后也可以继续你的音乐梦想啊。”
“你觉得现实吗?这可不是嘴上说说的。”
“现实……我不知道……”苏趣低头看着夕阳中的影子。
“那就一周后见,还在这里。傍晚。见不到的话也就不要怀念了。”
游乐场是在三年前关闭的,如今在旧址上建起了一座规模庞大的露天影院。每到一年中的这天,苏趣总要到影院里转转,这是他瞒着妻子的秘密,他心中唯一的秘密。他和妻子是在坐过山车时认识的。十年前,他和柳遥草分别。一周后,柳遥草没有出现在游乐场的夕阳里。
“今天怎么变得深沉了?”刘卫摇晃着廉价威士忌。
创业之初,刘卫和苏趣一直坚持着穷也要有品位的观点,多年来他俩总爱边喝廉价威士忌边相互打气。几经沉浮,两人开办的趣味超级影院大获成功,辐射了多座城市,其中最大的特色是开发了露天模式。今天是创业十周年纪念日,十年前的今天苏趣没有等到遥草。他失望地走出大门,在光秃秃的大路上遇到了正在跑步的老同学。苏趣问为什么在这里跑步。刘卫说被女朋友半路赶下了车,心里不爽,跑跑步减压。他和刘卫跑了几步,问对方想不想开电影院。
“今天电影演什么?”苏趣没有回答刘卫。
“一部爱情片,适合小情侣的。好像叫《爱与梦想》,韩国人演的,很无聊的那种。”刘卫对着酒瓶喝酒。
“看看吧。”苏趣拿过酒瓶。
露天影院里陆续坐满了前来观影的客人,空气里满是爆米花的甜腻味。苏趣很想开发几种可以替代爆米花的电影零食,他向来抵触高热量的食物。去年他让前台增加了不带壳的干果和风味炒豆,可顾客们依旧只对爆米花情有独钟。他喝了口酒,脑海里又冒出了汽车电影院的想法,他曾对刘卫提到过几次,刘卫的观点是:一场大堵车的盛会将面临各种问题,纯属瞎折腾。苏趣说:坐在发动机盖子上肩并肩地看场电影多棒,这是品牌特色而非利益至上,别忘了我们的趣味性。刘卫说:它只适合地广人稀的地方,在我们这交警会恨死你的。苏趣继续喝酒,打算过几年到西部地区开一家汽车影城,他觉得独自坐在车顶上看公路电影是件趣事。
星河下,巨大的幕布上不断转换着男女主角俊美的面容。一个半小时后影片放映结束,观众们没有退场。
“有意思,今天观众的素质怎么这么高?往常都是一结束就立马起身的。”苏趣看了看刘卫。
“是有点奇怪。”刘卫的呼吸里有淡淡的酒气。
“都在听歌啊!”前排一个女孩忍不住转过身子。
“听歌,什么歌?”刘卫盯着女孩的紫色发卡。他喜欢戴发卡的姑娘。离婚后他决意不再结婚。
“主题歌啊,电影的主题歌最近火了,这歌是当红乐队幸运草的力作。听说是乐队主唱写给昔日恋人的老歌。”
“是金属幸运草乐队,你每次都忘!”女孩的同伴,另一个扎着马尾的女孩加入进来。
“当红乐队?”苏趣下意识地重复着,他对乐队怀有一种特殊情结。
“大叔,你太OUT了,连金属幸运草都不知道。”马尾女孩露出了鄙夷的神情,“他们刚出道时曾是地下乐队,没什么名气,后来去了国外,再回来就火了!”
“而且只有这首歌带流行色彩,其他的歌曲都很金属,所以这首歌成了……”
“这不就是出口转内销嘛!”刘卫脱口说道,他对姑娘的兴趣要远大于电影及歌曲本身。刘卫的前妻是职业经理人,与刘卫离婚后同总经理移民到法国,刘卫去法国旅游时前妻一家人接待了他。刘卫与总经理喝波尔多红酒。两人曾在国内见过几面,前两次是公司年会,最后一次是在刘卫家的客厅。
“大叔总结得比较到位。”发卡女孩的语调里透着钦佩,她是个娃娃脸,大眼睛上涂着勃艮第红色眼影。
“看样子你们刚进入职场不久吧?怎么没带男朋友来?”“大叔,您有点八卦了。”“不要随便叫别人大叔,我才三十出头。”“您经常这样搭讪?”“静彤,我看大叔别有用心。”“别把人都想得那么复杂好不好,看完电影打算怎么回去?需要我开车送吗?”“我们有车。”“那一起吃个消夜如何?”“这个……”“附近有家很高档的西餐厅,里面有我的股份。店里的法国菜不错,食材全都来自法国。”“莉莉,现在回去还早吧……”“我无所谓了。”
众人的交谈是梦的空壳。苏趣站在空壳外面。夜空冷静深沉。巨大的沉默中,歌声自夜空緩缓降落。夜空是秋水,是一个女子闭起的眼睛。苏趣深深地呼吸。他感受风的灵魂。
无趣先生
他/一个暖男/相亲时选了咖啡店/总在寻找话题/总是/没有意思/坐在他的对面/又感觉时间太快光阴短暂/虽然他很无趣/可我有一点喜欢
他/一个暖男/陪我坐空中的秋千/天空那么孤单/还好/有流云作伴/我们笑着旋转/眼泪会不会成为雨点/虽然他很无趣/可我有一点喜欢
再见/无趣先生/亲爱的暖男/那一天的夕阳留在了身边/再见吧/无趣先生/亲爱的暖男/虽然也想给你完美的答案
再见/无趣先生/梦想还很遥远
再见/无趣先生/风的灵魂总在想念里/轻轻吹动琴弦
刘卫的注意力一直都在姑娘们身上,他没有留意苏趣离开的时间,等他路过办公室门前时发现老搭档正在里面站着。刘卫没有推门,离开走廊去了专属车位。
伫立良久,苏趣猛然拉开窗子,他想对深邃的夜空喊些什么,扑面而来的夜风冲进来,令他欲说无言。
作者简介
冷火,张炜工作室学员,山东省青年作家高研班第二十期学员,泰安市签约作家。在各期刊累计刊发小说五十余万字;出版诗歌小说集《简笔素描》。曾获齐鲁金盾艺术奖一等奖等奖励。
责任编辑 菡 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