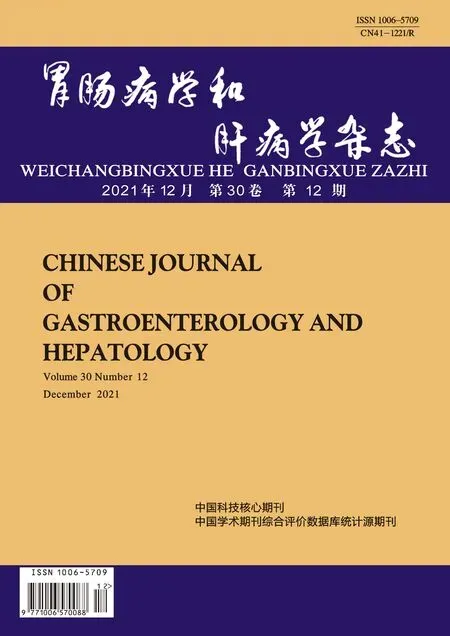全反式维甲酸与肝纤维化关系研究进展
2021-12-05加军霞武希润
加军霞, 武希润
山西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消化内科,山西 太原 030001
肝纤维化是一个严重的健康问题,具有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全世界每年约有150万人死于由其进展所致的肝硬化和原发性肝癌[1],其发展是以细胞外基质(ECM)的累积为特征,随后通过持续性的损伤和(或)炎症破坏正常的肝脏结构,导致肝细胞功能障碍,如果不及时治疗,纤维化会发展为肝硬化,最终导致肝功能衰竭甚至死亡[2]。肝星状细胞(HSCs)在肝纤维化发生发展过程中起着核心作用,是肝脏中产生ECM的主要细胞类型,当肝脏受到致病因子刺激后,它们从静止状态转为形成纤维瘢痕组织的活化状态,向α-平滑肌肌动蛋白(α-SMA)阳性表型转化,分化为ECM分泌细胞,使ECM的合成及降解失衡,增加Ⅰ型和Ⅲ型胶原、细胞骨架蛋白α-SMA的沉积,导致肝纤维化的形成[3-4]。全反式维甲酸(all-trans retinoic acid,ATRA)又称视黄酸、维生素甲酸、维甲酸等,是动物体内维生素A的代谢中间产物,近些年发现其与肝纤维化发展关系密切。本文就ATRA与肝纤维化的最新研究进展作一概述。
1 ATRA概况
ATRA又称视黄酸、维甲酸、维A酸等,分子式为C20H28O2,是动物体内维生素A的中间代谢产物,具有广泛的生理学和药理学活性,是维持生长发育不可或缺的物质。
维生素A在哺乳动物体内不能合成,来源于饮食,主要是来自动物中的视黄醇酯(retinol ester,RE)和植物中的类胡萝卜素。RE可能被胰脂肪酶和肠磷脂酶B水解为视黄醇和游离脂肪酸(FFA),然后被肠上皮细胞吸收。类胡萝卜素主要存在于蔬菜中,约50%的类胡萝卜素被黏膜细胞完整地吸收,其余50%被氧化成视黄醛,然后还原为视黄醇。视黄醇不溶于水,在肠上皮细胞中,视黄醇与细胞视黄醇结合蛋白Ⅱ(cellular retinol binding protein Ⅱ,CRBPⅡ)结合形成CRBP-ROH复合体。在肠上皮细胞中,被吸收的视黄醇一部分在卵磷脂视黄醇酰基转移酶(lecithin retinol acyl transferase,LRAT)作用下重新酯化成视黄醇酯并参与形成乳糜微粒(CM),然后分泌并通过淋巴循环输送到身体的其他部位,其余的直接通过门脉循环运输[5-7]。进入血液循环后,乳糜微粒甘油三酯被脂蛋白脂肪酶(lipoprotein lipase,LPL)水解和添加载脂蛋白E后,形成含有视黄醇酯的CM残粒,肝细胞通过受体介导的内吞作用吸收残粒,视黄醇酯被水解。当机体需要时,HSCs中视黄醇酯水解成视黄醇后被运输回肝细胞,与视黄醇结合蛋白(retinol binding protein,RBP)结合形成RBP-ROH复合体,并与一种也在肝脏合成的更大的蛋白质—甲状腺素运载蛋白结合形成三元复合物进入血液循环,RBP-ROH与甲状腺素运载蛋白的结合阻止肾清除RBP-ROH。肝脏是维生素A的主要储存库,而肝内80%以上的维生素A以RE的形式储存于HSCs中,少量RE和类胡萝卜素也由乳糜微粒和残粒携带到肝外组织中供使用和储存[6,8]。
当机体需要时,视黄醇在脱氢酶、同分异构酶等的作用下生成维甲酸,维甲酸类有多种同分异构体,如13-顺式维甲酸、9-顺式维甲酸(9-cis RA)和全反式维甲酸等,其中ATRA被认为是维生素A的主要生物活性衍生物,是目前临床应用较广泛的药物。ATRA通过激活两个核受体家族来调节基因表达,即视黄酸受体(RARs)和视黄酸X受体(RXRs)。二者均有α、β、γ三种亚型, 各亚型又有多种异构体。体外研究表明,RARs可被ATRA和9-cis RA激活,而RXRs仅被9-cis RA激活[6,9]。研究证实,维甲酸以弥散的方式进入细胞,并与细胞内的结合蛋白CRABP-Ⅱ结合,部分蛋白会携带维甲酸进入细胞核内与RAR/RXR异源二聚体中的RAR结合,然后激活靶基因启动子区域的维甲酸反应元件(RAREs),在维甲酸存在的情况下控制维甲酸反应基因的表达,进而激活下游基因的表达发挥作用。RAREs是由DR1、DR2或DR5碱基对分隔的两个六聚体基序PuG(G/T)TCA的直接重复组成[10]。
过氧化物酶体增殖物激活受体(PPARs)是另一组与RXR形成异二聚体的核激素受体,包括三个亚型:PPARα、PPAR β/δ、PPARγ。最近的研究[6,8]表明,ATRA不仅可以结合RARs,而且可以作为配体与PPAR β/δ结合,脂肪酸结合蛋白(FABP5)可以将ATRA转运至细胞核,PPAR β/δ激活并与PPAR反应元件(PPRE)结合调控基因表达。除了RARs、RXRs和PPARs之外,ATRA还可以与维甲酸相关孤儿受体(ROR)β和γ结合,与RARs和PPARs不同,RORs与RXR不会形成异二聚体,其作为单体通过与DNA中特定的ROR反应元件(ROREs)结合来调控基因转录。
2 ATRA与肝纤维化相关研究
近年许多研究发现,肝损伤发生发展与维生素A水平关系密切。Freund等[11]发现慢性胆汁淤积病患者维生素A处于低水平状态,且在不同的慢性淤胆症鼠模型中,维甲酸已被证明可以减弱甚至预防肝纤维化,调节肝脏对淤胆损伤的免疫反应。Liu等[12]通过临床试验发现,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患者的血清维甲酸浓度较低,维甲酸水平与肝甘油三酯含量、肝脂肪变性严重程度和肝损伤程度呈负相关。Chaves等[13]发现,血清维生素A水平随着慢性肝病严重程度的增加而逐渐减少。越来越多的研究证明ATRA可抑制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Yu等[14]在大鼠胆管结扎模型中发现ATRA可以减少胆汁酸生成和胆管增殖,并减少促炎细胞因子抑制肝纤维化,对胆汁淤积性肝病患者有重大意义。Assis等[15]通过研究发现,ATRA单独或联合中等剂量熊去氧胆酸能抑制原发性硬化性胆管炎患者体内胆汁酸的合成,减少肝纤维化和炎症标志物的产生。Cortes等[16]证实,ATRA通过依赖RARβ转录下调肌球蛋白轻链2(MLC-2)的表达来促进人HSCs失活,MLC-2在细胞骨架张力、机械传感和ECM沉积中起重要作用。Li等[17]发现,ATRA在体内和体外对鼠HSCs和LX-2细胞均可抑制TGFβ1表达及下游促纤维基因(CTGF、TIMP-1)的表达,减弱基质金属蛋白酶抑制剂(TIMP-1)对基质金属蛋白酶2(MMP2)的抑制,促进MMP2的活性,降解基质蛋白从而抑制肝纤维化。此外,还有证据[18]显示,ATRA可显著降低人肝星状细胞株(LX-2)的α-SMA和胶原α1链蛋白基因(COL1α1)的mRNA水平,且呈剂量依赖性。
3 ATRA抑制肝纤维化的机制
3.1 TGF-β-smad信号通路
3.1.1 抑制胶原生成:转化生长因子β(TGF-β)是一种强效促纤维化细胞因子,在肝和其他器官(包括肺和肾)纤维化的发展中发挥关键作用[19]。它是一个由35个以上细胞因子组成的超蛋白家族,在胚胎发育、细胞增殖、炎症、组织修复和免疫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TGF-β亚型存在于不同的生物体中,在哺乳动物中描述了三种形式的TGF-β(β1、β2和β3),在鸟类和两栖动物中已经鉴定出亚型4和亚型5。在非活性状态(TGF-β休眠状态),它与休眠相关肽(LAP)结合。分泌后,TGF-β通过TGF-β相关潜伏蛋白(LTBP)的蛋白水解而被激活,此时TGF-β即与受体结合并传递相应的信号。还有一种特殊的激活机制,由LAP-TGF-β复合物与血小板反应蛋白1(TSP-1)结合启动,有人认为TSP-1与LAP-TGF-β复合物结合,改变其构象,使TGF-β与受体结合。其受体分为三种类型,受体复合物是异源四聚体,由两个结合配体的“Ⅱ型”受体和两个信号传导的“Ⅰ型”受体组成[20]。RⅢ型固定在细胞膜上,称为β-甘聚糖受体,主要功能是稳定RⅠ和RⅡ形成的异源四聚体。TGF-β家族的受体位于细胞表面,与其他生长因子和细胞因子不同的是它们对丝氨酸或苏氨酸磷酸化的高特异性,其发挥作用由跨膜丝氨酸-苏氨酸激酶受体转导的信号介导。
smad蛋白已被确认为TGF-β信号的主要转导因子,介导细胞表面受体信号到细胞核中。脊椎动物中有8种smad蛋白(smad1~smad8),根据功能不同分为三类:受体激活的R-Smad(smad1、smad2、smad3、smad5和smad8),联合调解员C-Smad(smad4),抑制剂I-Smad(smad6和smad7)。R-Smad根据其Ⅰ型受体激活的方式分为两大类,一类包括smad2和smad3,它们是通过TGF-βⅠ型受体或称激活素受体样激酶(ALK)对其C端进行磷酸化而激活的;另一类包括smad1、smad5和smad8,被骨形态发生蛋白(BMP)激活[21-22]。smads具有同源的N-端和C-端结构域(分别称MH1和MH2),并由高度分散的富含脯氨酸的连接区域连接。R-Smad的羧基端区域有磷酸化基序(SSXS),可以被Ⅰ型受体磷酸化。smad4缺乏磷酸化基序,但具有独特的smad激活域(SAD)。I-Smad缺乏可识别的MH1域和磷酸化基序,但具有MH2域,在调节TGF-β信号转导过程中起重要作用[23-24]。
所有正常细胞和大多数肿瘤细胞的表面均有TGF-β1受体,TGF-β1被认为是最具促纤维化作用的细胞因子。TGF-β1-smad信号通路是经典的促肝纤维化通路。TGF-β信号转导过程:在细胞表面,配体与丝氨酸/苏氨酸残基(TβⅠR和TβⅡR)中激酶活性的跨膜受体复合物结合,诱导Ⅰ型受体的富含丝氨酸/苏氨酸区域(GS区域)被Ⅱ型受体磷酸化。磷酸化Ⅰ型受体招募smad受体(smad2和smad3),smad受体被激活并与smad4结合形成复合物,转移到细胞核内并与SBE序列(smad结合元素)结合,从而完成其生物功能。I-Smad通过MH2域能与活化的TβⅠR结合,但由于缺乏关键的磷酸化基序,干扰smad2或smad3的磷酸化,从而调节其活动[22,25]。转录控制不仅通过与靶DNA元件直接相互作用,还通过与其他转录因子(AP-1)或与辅激活因子(如CREB结合蛋白)或辅抑制因子相互作用来实现。
有研究[26]表明,ATRA通过下调激活蛋白-1(AP-1)和c-Jun氨基末端激酶(c-Jun N-terminal kinase,JNK)的表达抑制下游基因TGF-β的转录,减少HSCs中胶原的产生。AP-1研究最多的是由Fos(c-Fos、FosB、Fra-1、Fra-2)和Jun(c-Jun、JunB、JunD)组成的同源/异源二聚体复合物,其与特定的DNA序列结合,使下游基因的转录被激活或抑制。在人类细胞中,c-Fos诱导是非常短暂的,其mRNA被快速降解,TPA(12-氧-十四酰-13-乙酸酯)介导的c-Jun mRNA的诱导,虽然也是短暂的,但持续时间比c-Fos要长得多。因此,AP-1依赖的胶原酶基因的表达遵循c-Jun蛋白表达的动力学,JNK抑制被认为是ATRA抑制AP-1的关键步骤,多项研究证实TGF-β1可激活成纤维细胞JNK信号通路,促进ECM沉积和纤维化。ATRA抑制AP-1的产生可能是由:(1)抑制AP-1的上游信号JNK的活性,Li等[27]报道,ATRA通过其受体作用抑制JNK和p38MAPK激活改善大鼠早期实验性脑缺血再灌注损伤;(2)在AP-1上竞争相同的结合位点;(3)通过抑制TGF-β1的表达来减弱TGF-β1诱导的JNK活性[28]。TGF-β1与JNK信号通路相互促进、相互作用,形成正反馈。
AP-1的结合位点也被认为是TPA应答元件。曾有实验[29]证明,ATRA能有效抑制TPA诱导的AP-1活性是由于RARα和RARβ的参与,主要的生物活性作用在于RARα,RARα抗AP-1活性是ATRA依赖性的,而RARβ是直接抑制剂,加入ATRA可进一步增强这种抑制作用。值得注意的是,ATRA与RARs结合后还可抑制AP-1复合物与AP-1位点的结合。
综上所述,ATRA与RAR结合后通过抑制AP-1和JNK来抑制TGF-β1mRNA表达,从而抑制其下游促纤维化基因(CTGF、MMP-2、TIMP-1、TIMP-2和PAI-1)的mRNA表达,诱导纤溶基因的mRNA表达,抑制HSCs的增殖和胶原生成。
3.1.2 促进胶原降解:ECM蛋白的过度沉积是导致肝纤维化的主要原因,基质蛋白的降解主要是通过基质金属蛋白酶(MMPs)发挥作用,MMPs专门降解胶原和非胶原基质。肝脏基质的降解主要是通过四种酶的作用进行的:MMP-1、MMP-2、MMP-3和MMP-9。在纤溶系统中,MMPs一方面在尿激酶纤溶酶原激活剂的作用下通过蛋白裂解被激活,该过程主要的调节剂是纤溶酶原激活物抑制剂PAI-1,PAI-1可阻断纤溶酶原向纤溶酶的转化,导致MMPs不能被激活。另一方面通过与其抑制剂TIMP结合来抑制蛋白水解的活性,在肝纤维化过程中,ATRA通过抑制TGF-β1,下调其下游促纤维基因(TIMPs、PAI-1)的mRNA表达,诱导MMPs的产生,进而降解生成的胶原[30]。
3.2 调节Th17/Treg比例失衡许多研究[31-33]显示,肝纤维化与Th17/Treg比值失衡关系密切。Th17和Treg细胞是具有独特免疫调节功能的T淋巴细胞亚群,均是由初始CD4+T细胞前体分化而来。TGF-β是两种细胞分化的中心细胞因子,可同时诱导Foxp3和RORγt的表达。低浓度的TGF-β与IL-6协同促进RORγt的表达,从而促进Th17细胞的分化。RORγt还上调IL-23R的表达,IL-23与IL-23R的结合进一步诱导RORγt并增强和稳定Th17细胞的发育和功能。然而,在无促炎细胞因子的情况下,高浓度的TGF-β可抑制RORγt的表达,有利于Treg细胞的生成[31]。Th17细胞在许多慢性炎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中发挥着强大的促炎作用,主要分泌促炎细胞因子IL-17,然后通过诱导其他促炎介质和招募白细胞(主要是中性粒细胞)到炎症部位来促进组织炎症,IL-17A是IL-17家族中最具代表性的一员,而Treg细胞通过分泌IL-10和TGF-β1有效地调节其他免疫细胞的功能和免疫应答,CD4+CD25+Foxp3+细胞是最具特征的Treg细胞。Th17细胞促进组织炎症,而Treg细胞抑制炎症,共同维持免疫平衡[32]。
维甲酸在调节免疫细胞分化,特别是调节Th17/Treg失衡中的作用已经得到证实。Li等[33]发现Th17/Treg比值失衡与肝硬化密切相关,两者呈正相关,Th17/Treg比率可以作为HBV感染患者肝硬化一个指标和发生肝癌的一个风险因素。有研究[34]表明,ATRA通过增强TGF-β诱导的smad3的表达及其磷酸化促使靶基因Foxp3表达增加来促进Treg转化,并通过抑制IL-6R和IL-23R的表达抑制Th17的发展[35]。ATRA增强smad3磷酸化和Foxp3表达依赖于TGF-β,在无TGF-β的情况下,维甲酸仅增加smad3的表达,而对smad3磷酸化无明显影响。据报道,ATRA还会增加smad3结合位点区域的组蛋白乙酰化,由于组蛋白乙酰化与基因激活和表达增加相关,使磷酸化smad3结合增加,有助于维甲酸作用的TGF-β诱导的Foxp3转录[36]。除了促进Treg转化,ATRA还抑制IL-6/IL-23介导的Th17分化,似乎是通过多种机制实现的:(1)增强TGF-β诱导的Foxp3表达对抗Th17分化;(2)抑制IL-6受体的上调降低Th17的分化且减弱了IL-6对Foxp3诱导的抑制作用[37];(3)维甲酸抑制IL-23R的表达,从而抑制Th17表型的稳定和进一步成熟。虽然维甲酸在体外对Treg细胞的转化有很强的促进作用,但在体内持续的炎症刺激下维甲酸治疗并不能显著增加Treg细胞的数量。相反,在无强烈炎症的情况下,维甲酸可能增加体内的Treg细胞。总之,在肝纤维化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可能是Th17/Treg平衡,而不是Th17或Treg细胞数量的改变。最近一项新的研究表明,除了smad3信号外,MAPKs中的ERK和p38构成了ATRA调节Th17/Treg平衡的主要的非smad信号通路,并对其起辅助作用,此实验还证明ERK通路不仅可以促进Treg的诱导,还可抑制Th17的分化,而p38通路只参与促进Treg的诱导[38]。
3.3 抑制HSCs活化HSCs的活化是肝纤维化发生的重要因素,抑制肝脏中的氧化应激是防止疾病进展的关键途径。ATRA可通过抑制硫氧还蛋白互相作用蛋白(TXNIP)的表达抑制氧化应激,从而减弱HSCs的激活来抑制肝纤维化的发生发展。为了检测氧化应激是否参与HSCs的活化,Kanki等[39]用抗氧化剂N-乙酰半胱氨酸(NAC)处理过度表达TXNIP的LX-2细胞,通过测定总谷胱甘肽量、α-SMA和COL1A1的mRNA水平,结果发现NAC通过激活GSH系统降低活性氧簇(ROS)从而抑制TXNIP过表达时HSCs的激活,表明氧化应激诱发HSCs活化。基于维甲酸应答元件(RAREs)的电子分析,使用HCC细胞系进行全基因组筛选,鉴定出26个维甲酸应答基因,其中包括TXNIP。ATRA抑制TXNIP的具体调控机制尚不完全清楚,据报道TXNIP在其启动子上游区域包含DR5 RARE,核受体异二聚体可能招募转录抑制因子如组蛋白去乙酰化酶至RAREs时,靶基因TXNIP表达被抑制[40]。硫氧还蛋白(TRX)通过将二硫化物还原成巯基来抑制细胞ROS,TXNIP与TRX结合抑制TRX的抗氧化活性上调ROS。ATRA治疗后TXNIP表达被抑制,其对TRX抑制作用减弱,使ROS下调。ATRA通过对TXNIP作用使ROS下调,抑制了氧化应激,从而抑制了HSCs活化[18]。
4 展望
肝纤维化是一个世界性的健康挑战,患病率逐年上升,但缺乏有效的治疗策略,通过上述研究发展的介绍发现,ATRA可通过TGF-β-smad信号通路抑制胶原产生、调节Th17/Treg比例诱导Treg细胞分化并通过抑制TXNIP来抑制HSCs活化,从而抑制肝纤维化的进展达到保护肝脏的目的。ATRA有望成为预防和治疗肝纤维化新的方向,为临床上肝纤维化防治研究提供了新思路。但由于ATRA在体内各种调节机制复杂,对其抗纤维化作用和临床应用还需要进一步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