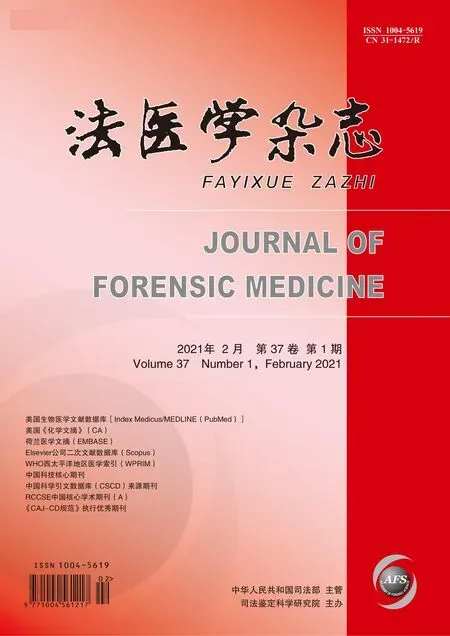面部血管瘤术后耳郭缺失、面瘫医疗损害1例
2021-12-05张利娟鲍身涛李慧文
张利娟,鲍身涛,李慧文
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皮肤科,北京100029
1 案 例
1.1 简要案情
某年11 月18 日,李某因患“右侧面部血管瘤”入住某省儿童医院,经行导管动脉硬化栓塞术后遗留右耳郭大部分缺失、右侧面瘫等表现。患方对医院的诊疗行为提出异议并诉至法院,要求对医院诊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进行法医学鉴定。
1.2 病史摘要
李某,女婴,2 个月20 d。11 月18 日因“发现右面部包块1 月余”入住某省儿童医院。查体:神志清楚,精神可,反应可。面色正常,营养良好,发育正常。右面部可触及大小约2 cm×2 cm×2 cm 包块,质韧,边界欠清,包块皮肤无破溃,无压痛,包块局部皮温不高,无波动感。初步诊断:右面部血管瘤。11 月20 日采取静吸复合麻醉法,取右股动脉入路,用Seldinger 法穿刺成功后,置入4F 小儿鞘,常规肝素化。用Cobra2导管选择性插入右颈外动脉,造影示肿物染色明显,由颈外动脉分支供血。微导管超选择性插入供血动脉,向内注入平阳霉素3.5 mg、碘化油1 mL、地塞米松1 mL,用聚乙烯醇颗粒栓塞剂栓塞供血动脉,造影示肿物染色基本消失。术中患儿无明显不适,出血约2mL。术后次日,李某右面部包块较前质硬,右面部肌肉活动受限。术后5 日,李某右面部肌肉活动受限无明显缓解,并相继出现嘴角歪斜、右耳后皮肤呈片状暗黑色瘀斑。临床先后予行活血化瘀、促进微循环等治疗。术后20 d,李某因“右眼睑闭合不全,右耳郭外下约1/3、乳突区延续至下颌角处皮肤渐呈暗黑色焦痂样变”再次入住某省儿童医院,诊断为“右耳郭皮肤坏死,右侧面神经损伤”等,医方考虑为药物外渗所致,剪除右耳郭坏死组织。现遗留右耳郭大部分缺失、右侧面神经损伤致面瘫等表现。
次年3 月19 日,某省儿童医院肌电图检查结果:右侧面神经颞支、颧支及颊支见纤颤电位,动作电位波幅减低,动作电位潜伏期延长,提示右侧面神经颞支、颧支及颊支存在生理传导阻滞现象,符合右侧面神经部分损害后改变。
1.3 法医学检验
1.3.1 体格检查
李某被抱入检查室,神清,营养状况尚好,检查尚合作。家属诉李某右耳听力无明显下降。右耳郭大部分缺失,仅残留外耳轮上半少许组织,余外耳道结构完整。双侧睑裂稍不等宽,右侧稍变窄,双眼睑可闭合,双眼球各方向运动无明显受限。静息状态时口角无明显歪斜,微笑时口角左偏,无流涎表现,伸舌居中。
1.3.2 阅片所见
手术当年11 月17 日某省儿童医院颌面部增强计算机体层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CT)、图像重组和计算机体层血管成像(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CTA)示:右侧面颊部皮下见大小约2.1 cm×3.8 cm 软组织团块影,形态不规则,密度不均匀,动脉期扫描有明显强化,静脉期扫描可见延迟强化,团块内见多发迂曲扩张血管。CTA 可见右侧颈外动脉分支进入团块中央,符合右侧面颊部皮下血管瘤表现。
手术当年11 月24 日某省儿童医院头颅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MRI)示:右侧面颊部皮下血管瘤介入治疗后,范围较前片缩小,见团块状长横向弛豫时间(T2)信号、T2加权像(weighted imaging,WI)脂肪抑制稍高信号,右侧腮腺区皮下脂肪、颈深部软组织及右耳后软组织肿胀,均呈长T2信号,右侧乳突内见长T2信号。
术后第2 年6 月14 日某市儿童医学中心头颅增强CT 示:右侧面颊部皮下血管瘤介入治疗后,右侧腮腺区见小片状稍高密度影,未见明显增粗引流静脉及供血动脉,右侧耳后皮肤增厚。
1.3.3 鉴定意见
某省儿童医院在对李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对本病严重程度认识不足、对该术式可能带来的损害后果估计不足以及手术操作不当等医疗过错,该过错与其目前遗留的右耳郭大部分缺失、右侧面神经损伤致面瘫等损害后果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系主要原因,过错参与程度拟为60%~80%)。
2 讨 论
血管瘤是一种临床常见的以血管内皮细胞增生和细胞密度增高为特征的先天性良性肿瘤或血管畸形,来源于血管或淋巴管,多见于出生时或出生后不久,是婴幼儿期最常见的良性肿瘤,身体任何部位皮肤与软组织内均可生长,40%~60%发生于头颈部[1]。其具体发病机制目前尚不完全明确。婴幼儿血管瘤在临床上主要表现为增生期和消退期2 个阶段。增生期约为5个月,多数患儿在出生后不久出现并快速增生,在1岁左右时血管瘤进入漫长的消退期,消退期时常可为期数年,部分患儿的血管瘤完全消退可发生在5岁以内,80%患者在7~12 岁基本或完全消退。资料[2]表明,在6岁之后消退的患儿更易导致瘢痕、多余皮肤及毛细血管扩张等多种情况发生,导致患儿一定的美容损害和心理障碍。面部血管瘤一般会自然消退,但部分可能呈继续生长趋势,不仅对患儿外形美观造成严重影响,还可能引起出血、感染、功能障碍等多种并发症,所以家长通常迫切要求早期治疗。
目前治疗颌面部血管瘤的手段包括保守观察、药物治疗、介入治疗、激光治疗、手术切除等。对于该病的治疗时机和方法的选择,主要取决于血管瘤的大小、部位及进展程度,相关医务人员的临床经验及医疗单位的设施。虽采用手术治疗效果肯定,但存在术中出血、手术不彻底及易复发等不足。颈外动脉造影和栓塞术对诊治颌面部血管畸形有重要作用[3],不仅能明确病变性质和部位,而且能选择性阻断供血动脉及其瘤床的自身血运,防止侧支循环形成,控制肿瘤增长,故其能作为术前预防性出血措施,也能作为一种根治性手段用于手术难以奏效的颌面部血管畸形治疗。对于以下4 种情况不宜行动脉栓塞:(1)瘤体位于颈内外动脉分叉处,栓塞剂有可能反流入颈内动脉者;(2)颈内外动脉有异常交通者;(3)供血动脉不明确的海绵状血管瘤,动脉造影瘤腔不显影者;(4)特敏患者。硬化疗法属于药物治疗方法,其机理主要是化学刺激引起的炎性反应,从而形成血栓并机化,使瘤体消退,也可能引起溃疡坏死等并发症。平阳霉素作为硬化剂用于恶性胸腔积液及淋巴管瘤的治疗,疗效显著,近几年用于治疗血管瘤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平阳霉素是一种抗肿瘤抗生素,没有骨髓抑制及免疫作用。平阳霉素瘤内注射可在局部聚集高浓度药物,导致窦腔内的内皮细胞萎缩及破坏,造成血小板黏着,进而形成血栓,瘤体纤维化,达到抑制血管瘤发展的作用,有效减小瘤体,提高治疗效果。研究结果[4]表明,平阳霉素联合地塞米松瘤内注射治疗婴幼儿口腔颌面部血管瘤具有创伤小且效果好等优点,而采用低质量浓度的灌注液不仅可以取得良好效果,还可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并发症的发生。陈平有等[5]采用经腔直接注射明胶海绵微粒、平阳霉素的混合物行灌注栓塞治疗颌面部血管瘤,取得明显疗效,认为此方法集血管硬化治疗和栓塞治疗为一体,作用时效长,疗效优于单纯栓塞或栓塞加局部注射平阳霉素。本例中,某省儿童医院根据被鉴定人李某入院时临床症状、体征,作出“右面部血管瘤”的临床诊断成立。考虑到李某面部包块逐渐增大、边界欠清、质韧等病例特点,医方选择平阳霉素3.5 mg、碘化油1 mL、地塞米松1 mL经导管动脉硬化栓塞术的手术时机及手术方案不违反临床一般诊疗原则。术后次日李某右面部包块变硬,右面部肌肉活动受限,并相继出现右耳郭皮肤坏死及右侧面神经损伤等表现,医方先后给予药物治疗并剪除右耳郭坏死组织等处理亦符合当时实际情况。
一般说来,面部血管瘤经行栓塞术造成耳郭缺损、面瘫的发病机制主要包括:(1)在将异常血管栓塞的同时,误将旁边正常血管一并栓塞;(2)异常血管与正常血管之间有“交通”,术前未能仔细检查,行栓塞术时,经过交通支误栓正常血管;(3)药物外渗的毒性作用;(4)被栓塞的血管形成硬化结节,甚至“异物肉芽肿”压迫周围神经、血管等解剖结构。
根据分析,患儿出现右耳郭大部分缺失、右侧面神经损伤致面瘫的原因如下:
(1)颈外动脉造影和栓塞术严重并发症有广泛动脉痉挛、面瘫、失明、脑栓塞、肺栓塞等的发生率为0.9%~1.96%[6]。主要原因是栓塞剂反流入颈内动脉或通过颅内外动脉间的交通支进入脑动脉,造成栓塞。头面部血供丰富,许多疾病常因术中出血被迫终止手术或得不到根治。传统采用颈外动脉结扎术以达到治疗或减少术中出血的目的,但效果并不理想。介入性颈外动脉栓塞术前先行超选择性动脉造影,可充分了解病变的供血来源、确切部位、范围以及与周围血管的关系,这样更有利于栓塞剂注入病变部位,从而达到治疗效果。
本例中,经导管动脉硬化栓塞术容易引起组织缺血、坏死、破溃及感染等损害后果。因此,术前应结合临床辅助检查(如血管造影等)仔细诊断、明确瘤体的病变类型、是否表浅、皮肤组织是否侵犯,准确评价术后皮肤组织坏死等风险。同时,未见医方在术前对该患儿血管瘤的具体情况进行必要的检查,没有根据病变形态进行分类,亦没有明确该瘤体与周围组织的关系,说明医方对本病例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对该术式可能带来的损害后果估计不足。病情危险者需专人监护,栓塞前必须行造影检查了解病变大小、确切部位、血供情况及有无与颈内动脉异常吻合,以作为栓塞剂用量及导管位置的参考。造影后导管应尽可能接近靶血管,以防液体栓塞剂反流(逆流)。在释放栓塞材料时应在透视下连续观察栓子流向,以免栓塞剂流向非靶血管,一旦出现造影剂滞留或反流应立即停止。
(2)平阳霉素注射治疗效果佳,偶尔引起患儿发热、胃肠道反应、口腔炎、过敏性休克与血管瘤局部坏死等并发症。硬化剂治疗的并发症包括过敏反应、中毒反应、皮肤黏膜坏死以及感觉神经或运动神经功能障碍。皮肤或黏膜坏死的发生率约10%,可能是由于用药量大或药液渗入皮下、黏膜下组织[7]。灌注栓塞剂时,导管头位置须适当,切勿过度阻碍血流,应采用间歇团注方式释放栓塞剂,既能有效地使栓塞剂均匀分布于瘤体,又可防止因注射过快、过猛使栓塞剂外渗引起组织缺血坏死或伤及面部神经。本例中,医方的手术记录略显简单,未见在栓塞过程中导管头位置、注射方式及注射速度的记录。且就现有送鉴材料分析,术前李某并不存在“右耳郭缺血坏死、右侧面神经损伤致面瘫”等表现,上述损害后果发生于本次栓塞术后,该损害后果的发生在时间上与手术操作之间存在延续性、在解剖部位上与栓塞范围之间亦存在吻合性。此外,医方也考虑到上述损害后果的发生与药物外渗有关。据此推定,本例栓塞术后出现的右耳郭缺血坏死与医方误栓正常血管有关,右侧面神经损伤致面瘫等损害后果与被栓塞的血管形成硬化结节,压迫周围神经、血管等解剖结构有关。
当然,本例患儿面部血管瘤生长迅速,面部包块质韧、边界欠清,出生不足3 个月的婴儿面部血管十分纤细,这一复杂的解剖特点增加了手术操作难度及术后损害后果的(如组织缺血、坏死等)发生率。据此认为,被鉴定人李某自身疾病因素与其目前的损害后果之间亦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
综上所述,某省儿童医院在对李某的诊疗过程中存在对本病例的严重程度认识不足、对该术式可能带来的损害后果估计不足以及手术操作不当等医疗过错,该过错与其目前遗留的右耳郭缺血坏死、右侧面神经损伤致面瘫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医疗过错系主要原因,参与程度拟为60%~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