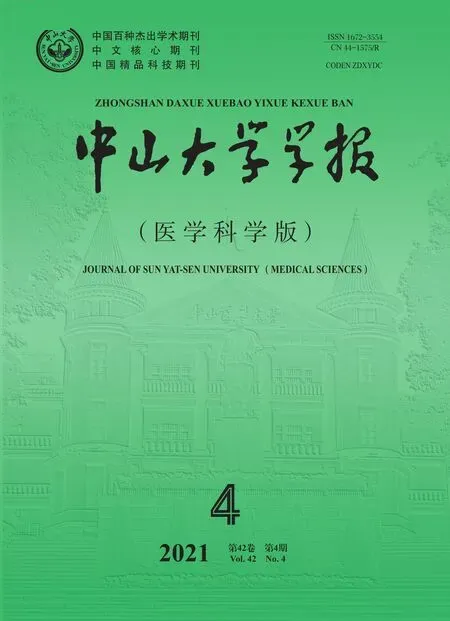神经调控在昏迷患者促醒中的研究进展
2021-12-05马超
马 超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康复医学科,广东广州 510120)
意识障碍(disorders of consciousness,DoC)是指各种严重的神经系统损伤导致意识状态的改变,包括昏迷、植物状态和微意识状态。昏迷患者可遗留各种功能障碍,包括意识、认知、情绪、吞咽、言语、大小便、运动功能等障碍,严重影响患者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随着临床救治水平的提高,昏迷患者病死率逐渐下降,但意识障碍的发生率明显上升,严重影响患者生存质量,增加患者家庭和社会负担[1]。临床上针对昏迷患者的早期救治包括手术治疗,对症支持治疗,抗感染和脑保护治疗等。目前常见的康复治疗技术包括针灸、高压氧及神经调控技术。神经调控技术分为中枢神经调控和外周神经调控,其中中枢神经系统调控技术包括经颅磁和经颅电刺激、脑深部电刺激、脊髓电刺激[2];外周神经调控技术包括正中神经电刺激、迷走神经刺激、三叉神经电刺激等[3-6]。本文综述了各种中枢和外周神经调控技术在昏迷促醒中的临床应用以及治疗机制,并比较了不同的调控技术的临床疗效。
1 中枢神经调控技术在昏迷促醒中的应用
1.1 深部脑刺激
深部脑刺激(deep brain stimulation,DBS)是一种有创性的神经外科手术,它通过立体定位技术在皮质下区域植入电极,并通过电极将电脉冲传递到脑内特定区域,从而达到治疗目的。DBS 精确度高,可达毫米,并且可以靶向刺激脑深部核团以及白质束,现已成熟应用于帕金森病、原发性震颤和癫痫等疾病的治疗[7]。DBS 的作用靶点在不同疾病中是不同的,包括额叶、穹隆、伏隔核、内囊、丘脑、部分脑干核等,其中丘脑核团以及相连的白质束和核团是参与唤醒所必须的核团[8],因而DBS 对意识障碍的治疗也在逐步开展。
DBS 治疗意识障碍的临床案例可追溯到1969年,Hassler[9]等在1 名创伤性脑损伤后持续性植物状态患者的丘脑左腹前核和右侧苍白球植入电极,刺激的频率分别为50 和8 Hz,结果表明刺激后患者自发肢体运动和眼球运动增加,觉醒时间延长,并且脑电图显示刺激后患者左侧颞叶皮质慢波减少,双侧皮质、丘脑和苍白球快脉冲增加。Tsubokawa[10]等对8 例因脑损伤所致持续性植物状态的患者进行6 个月以上的DBS 治疗,刺激靶点为中脑网状结构以及非特异性丘脑核团,结果显示,其中4 名患者脱离植物状态,可执行指令和表达需求。Lemaire[11]等进行一项持续11个月的前瞻性研究,对5 名意识障碍患者进行双侧30 Hz 低频电刺激,刺激靶点为丘脑苍白球,结果显示2名患者在修订后的昏迷恢复量表(the coma recovery scale re‐vised,CRS-R)的听觉、视觉和口部运动∕言语功能这几个方面的评分均较基线有显著改善。此外,利用PET评估患者治疗前后脑代谢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2 名患者的内侧皮质代谢相较基线状态明显增加。
综上所述,DBS 主要通过刺激上行网状激活系统和丘脑区域治疗意识障碍。中脑的网状结构可通过胆碱能和谷氨酰胺能连接驱动丘脑核,经过丘脑中继核,再通过丘脑皮层纤维进一步驱动大脑皮层第Ⅳ层细胞,促进觉醒。Moruzzi[12]等通过动物实验证明了DBS 对猫网状结构的高频(300 Hz)刺激可以导致脑电图去同步化,而脑电图去同步化是动物和人类大脑皮层激活和觉醒的标志。另外,研究[13]也表明高频(100 Hz)刺激啮齿动物的中央丘脑可引起觉醒水平的提高。尽管DBS 在意识障碍患者中的应用已经持续50 余年,但是目前的证据仍然基于少数患者,仍需开展针对DBS治疗不同程度的意识障碍患者的高质量、随机对照的临床研究。
1.2 脊髓电刺激
脊髓电刺激(spinal cord stimulation,SCS)是一种公认的治疗意识障碍的方法,它相较于DBS创伤性更小,更加简便,可灵活调节不同的刺激参数(频率、振幅等)以及不同的脊髓节段以实现兴奋或者抑制脊髓神经元的活动,从而达到不同的治疗目的[2]。SCS 通过在C2~C4 硬膜外间隙植入电极,发出电脉冲刺激网状上行激动系统,进而调节神经回路。
Kanno[14]等进行一项持续20 年的前瞻性非随机对照观察性研究,对214 例持续植物状态患者的C2~C4 水平植入脊髓刺激器,每日进行刺激,结果显示54%的患者意识水平和神经功能具有明显改善。Bai[15]等比较了不同频率的SCS刺激11名微意识状态患者前后脑电图的变化,结果显示70 Hz SCS 刺激后δ 带显著减少,5 和100 Hz SCS 刺激后δ和γ 带同时减少,这提示SCS 可以调节微意识状态患者的脑功能。Si[16]等对10 名DoC 患者采用不同频率的SCS 刺激,利用近红外光谱成像技术观察患者脑血流情况,结果显示70 和100 Hz SCS 刺激可显著增加前额叶区域的脑血流量。此外,70 Hz SCS 刺激可以增加前额区和枕叶区域的功能连接,这提示SCS 可以促进脑血流的增加以及脑内的信息传递。
SCS 促进意识恢复的机制还不是十分清楚,目前研究认为其机制可能与网状结构的激活[17]、丘脑中继核团的激活以及脑血流量的增加[18]相关。
1.3 经颅磁刺激
经颅磁刺激(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TMS)是Barker[19]等于1985 年首先创立的一种无创的、操作简便、安全可靠的对大脑神经细胞进行刺激的电生理技术。重复经颅磁刺激(repetitive tran‐scranial magnetic stimulation,rTMS)是将一定频率和强度的磁脉冲以成串刺激的方式按一定间隔连续发放,可以对局部大脑皮质和功能相关远隔区的兴奋性、脑血流、脑代谢和神经递质等产生不同的诱导作用,对患者的运动、认知、言语及情绪等产生调节作用[20]。高频(>1 Hz)rTMS 主要产生兴奋的作用,低频(≤1 Hz)rTMS 主要产生抑制的作用[20-21]。针对不同患者大脑功能状况,需要采用不同的强度、频率、刺激部位、线圈方向来调整治疗方案,取得最佳的治疗效果[20-22]。针对DoC 患者的治疗,rTMS 常采用5、10 和20 Hz 的频率[21-22];刺激强度一般选择患者静息运动阈值(resting motor threshold,RMT)的90%~120%;刺激部位主要选择左、右侧前额叶背外侧区(dorsal lateral prefrontal cortex,DLPFC)以及左、右侧运动主皮质区(primary motor cortex,M1),通过刺激DLPFC 或M1,对与之存在广泛连接的皮质和皮质下组织尤其是丘脑产生间接刺激,最终产生调控作用[21-22]。
已有研究[22]表明,DoC 患者的意识水平的恢复与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DMN)和额顶网络(frontoparietal network,FPN)的功能连接相关,因而DMN 网络及FPN 网络的相关皮质区节点被视为意识恢复的观察指标。一项基于静息状态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resting-state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rs-fMRI)的功能连接(functional connections,FC)研究[22]发现,与健康受试者相比,DoC 患者DMN 网络及FPN 网络数个脑区FC 发生显著改变。此外,采用TMS 技术联合脑电图记录的TMS-EEG 技术能够检测TMS 在全脑皮层诱发脑电波动的时空变化模式,并以特定参数量化评估TMS 的远隔效应[23-24],基于此,研究者不但能在治疗前预测rTMS 效应,也能采用TMS-EEG评估开发新的个体化治疗靶点。
总之,目前rTMS 治疗DoC 患者的研究数目仍较少,多为小样本量研究,各研究的结论缺乏一致性,rTMS 治疗意识障碍的有效性证据仍有待进一步研究。
1.4 经颅电刺激
经颅电刺激(transcranial electrical stimulation,tES)亦是一种无创的大脑刺激技术,可通过电流刺激大脑皮层而改变脑功能状态[21]。tES包括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tDCS)、经颅交流电刺激、经颅随机噪声刺激等。作为当前应用最广泛的tES 技术,tDCS 可通过低强度直流电(0.5~2.0 mA)来调节大脑皮质兴奋性,阳极可以增加其兴奋性,阴极则能降低其兴奋性。tDCS不产生动作电位,主要通过改变神经元的跨膜电位来实现神经兴奋性调控[21]。
多项研究[21,25-26]分别以2 mA 直流电刺激左侧DLPFC 或双侧M1,连续刺激5~20 次不等,研究结果显示:tDCS 可提高部分DoC 患者意识状态,对微意识状态患者作用效果尤为显著。虽然tDCS 对微意识状态患者的疗效存在整体水平上的显著性,个体水平上仍有大量受试者对tDCS 治疗缺乏良好反应[27]。一项正电子发射断层扫描技术研究[25]显示,微意识状态患者中对治疗反应更好的群体可能在额顶颞叶、左侧DLPFC、扣带回、海马及丘脑等区域拥有更高的灰质体积和代谢活性,即与意识相关的皮质区,尤其是注意和工作记忆网络相关皮质代谢活性可能是tDCS显效与否的重要影响因素。
TMS-EEG 技术同样能够检测和评估tDCS 对全脑皮层脑电波的影响,明确其作用机制。一项关于tDCS 前后的TMS-EEG 检测显示:单次前额叶背外侧区tDCS 刺激可减少大脑的慢波活动,包括慢波出现率和慢波斜率,而慢波活动强度与高频波抑制呈正相关,慢波活动的减弱是昏迷患者功能恢复特别是意识恢复的前提[28]。
tDCS 治疗参数和刺激靶点也可能影响疗效。目前关于DoC 治疗几乎均选择2 mA 的刺激强度[21],但刺激强度相同的电流作用于不同个体时,在神经组织中产生的实际电流强度亦有差异。因此,个体化的治疗参数值得进一步研究。刺激部位选择方面,左侧DLPFC 是目前最多的刺激靶点[21,25-26],这主要是因为前额叶皮层是皮质-皮质下网络的重要节点,特别是其与丘脑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初级感觉、运动皮质作为非侵入性神经调控另一常用靶点也被用作tDCS的刺激位点[21]。
tDCS 的主要风险同样是诱发癫痫,但在已发表的DoC治疗研究中,除部分患者出现刺激部位皮肤短暂发红、刺痛外未见其他不良反应[21]。由于开展时间较短,相关研究数目较少,受试样本量低,关于tDCS用于DoC治疗的研究仍处于初步阶段。
2 外周神经调控技术在昏迷促醒中的应用
2.1 正中神经电刺激
正中神经电刺激(median nerve stimulation,MNS)通过刺激正中神经将神经冲动传导至脑干、丘脑及大脑皮层,达到改善脑血流、提高皮层兴奋性等作用。该方法作为一种经济、便携、无创、安全的治疗手段已被应用20余年。
多项临床研究发现正中神经电刺激对昏迷患者促醒的疗效明确。Cooper[29]等通过双盲随机对照试验发现,昏迷患者经过2 周的右侧正中神经电刺激治疗后比对照组苏醒的人数明显增多,格拉斯哥昏迷评分及格拉斯哥昏迷预后评分显著改善。Peri[30]等研究发现采用正中神经电刺激的昏迷患者苏醒时间比对照组相对缩短,对于已经恢复意识的患者,正中神经电刺激组的功能独立性评分更高。但是这些研究的样本量偏小,关于MNS 用于DoC的治疗效果仍需进一步研究。
正中神经电刺激可能通过以下机制产生促醒作用:①促进相关神经递质的释放,正中神经电刺激活上行网状激活系统,经过丘脑中继,刺激蓝斑释放去甲肾上腺素、前脑基底核释放乙酰胆碱、中脑及下丘脑释放多巴胺、下丘脑外侧区释放食欲素-A 蛋白以达到唤醒作用[30-32];②增加脑血流量,正中神经电刺激可刺激对侧丘脑及脊髓背核,增加额顶叶皮层的脑血流量[33];③增加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神经营养因子是神经可塑性的关键因子,可将不活跃突触转化为活跃突触,改善突触功能,增强意识水平。
正中神经电刺激对于昏迷促醒的治疗部位多选取利手侧,治疗参数如下:电流强度10~20 mA,频率40 Hz 刺激脉冲300 ms,持续时间20~30 s∕min,每天持续治疗时间在3~8 h之间,治疗周期为2 周一个疗程[3,30]。目前临床研究尚未报道正中神经电刺激治疗的不良事件,该治疗方法相对安全、可靠。
综上所述,正中神经电刺激治疗在昏迷促醒、改善意识障碍上有一定的效果,在昏迷促醒的治疗上具有广阔的前景,早期进行该治疗有望缩短昏迷时间,改善意识,提高生活质量,促进患者康复。
2.2 迷走神经刺激
迷走神经刺激(vagus nerve stimulation,VNS)作为一种周围神经电刺激技术,通过电刺激迷走神经调节脑功能,它已被广泛应用于癫痫、抑郁以及认知障碍的治疗。迷走神经电刺激包括植入式和经皮电刺激,其中经皮VNS 是将电极片置于耳廓处,刺激迷走神经在耳廓的传入支,这种方法也称为经皮耳廓迷走神经刺激(transcutaneous auricular vagus nerve stimulation,taVNS)。taVNS 目前也逐步应用于意识障碍的治疗[5]。
Corazzol[34]等于2017年通过迷走神经刺激使一位脑外伤后持续植物状态15 年患者意识改善,治疗过程采用植入式电极,刺激强度逐渐增加到1.5 mA,治疗6 个月后评估其效果,结果显示CRS-R 评分由5 分上升到10 分,18F-FDG PET 结果显示在刺激后3 个月枕顶叶、额叶和基底节区域的活动广泛增加,丘脑的代谢信号增强。2017 年Yu 等[35]报告了一例taVNS 治疗心肺复苏后植物状态的病例,该患者在发病50 d后接受taVNS治疗,每天2次,每次30 min,连续4 周,刺激强度为4~6 mA。治疗4 周后,患者CRS-R 评分由6分升至13分,fMRI结果显示taVNS激活了后扣带回∕楔前叶和丘脑,并且增加了后扣带回∕楔前叶与下丘脑、丘脑、前额叶腹内侧皮层、颞上回之间的功能连接,减少了后扣带回∕楔前叶和小脑的功能连接。除了以上的病例报告外,一项前瞻性的临床研究招募了14 例持续6 个月以上的意识障碍患者进行taVNS治疗,治疗4周,每周5 d,每天2 次,每次30 min,刺激强度1.5 mA,结果显示治疗1月后患者CRS-R 评分显著改善,其中诊断为微意识状态患者评分改善更明显[36]。以上临床研究初步证明了迷走神经刺激对慢性意识障碍患者意识水平的改善作用,但是尚缺乏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支持。
目前关于taVNS 治疗意识障碍患者的机制研究偏少,主要通过神经影像学技术研究taVNS 对不同脑区的作用,Briand 等[37]结合意识的神经连接基础、迷走神经的解剖与功能以及taVNS 的fMRI 结果,提出了以下关于taVNS 作用于意识障碍患者的机制:①激活上行网状激活系统;②激活丘脑;③重建皮质-纹状体-丘脑-皮质环路;④通过激活显著网络以促进外部网络和默认模式网络的负性连接;⑤通过去甲肾上腺素途径激活并增强外部网络的连接;⑥通过5-羟色胺途径增强默认模式网络连接。
2.3 三叉神经电刺激
三叉神经电刺激(trigeminal nerve electrical stimulation,TNS)作为一种周围神经电刺激的治疗方法,在治疗癫痫、注意力缺陷、小儿多动症、创伤后应激障碍等中枢神经系统(central nervous sys‐tem,CNS)疾病方面具有巨大的潜力[38-40]。
TNS 治疗CNS 疾病中常用的外周电刺激参数和刺激周期均具有良好的安全性,不良反应发生率低,未有CNS 严重不良反应(如诱发癫痫等)报道。我们开展重症康复已近10 年,首次提出“TNS 昏迷促醒治疗”这一新理念,并在临床上应用,使意识障碍患者神志明显改善,逐步转为清醒。我们曾报道一例因“垂体瘤术后昏迷”的患者[6],治疗前GCS 评分7 分(E2V1M4),诊断为“持续植物状态”。既往促醒治疗包括常规药物治疗,高压氧、正中神经电刺激等,但意识未见明显改善。在获得患者家属知情同意后,我们对患者进行TNS 治疗,采用低频电刺激,将两对电极连接到双眼眶上裂和眶下孔,以刺激眼神经(V1)和上颌神经(V2),并在TNS 治疗前后进行功能性MRI检查,以评估患者多个脑功能区的度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DC)。患者在TNS治疗后4 周出现了自发睁眼和单字发音,GCS 评分为11分(E4V3M4),在此基础上我们继续治疗2周,患者进一步觉醒,其GCS 评分为15(E4V5M6)。并且,通过fMRI 发现患者治疗前后大脑多个区域的度中心度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其中小脑和颞下回的DC 升高,而三角部额下回、中央后回、中央前回和辅助运动区的DC 降低[6],而这些大脑区域与语言、注意力、工作记忆、运动相关信息处理和躯体感觉功能等密切相关[41-42]。尽管这些区域的DC 改变的确切机制尚不清楚,但我们推测该患者在TNS后脑内脑血流量和代谢受到一定程度的调节。此外,我们对昏迷患者促醒的一项回顾性分析发现TNS 治疗组意识状态较常规治疗组明显改善,这提示TNS可以改善昏迷患者的意识水平[43]。
基础研究表明,TNS 在脑损伤意识障碍大鼠中应用可产生神经保护作用[44],表现为炎症因子(TNF-α、IL-6)水平下降、脑血流量增加,但是TNS在昏迷患者中是否有类似神经保护作用仍需探索。近期我们团队通过观察脑损伤昏迷大鼠的脑电图特征,并根据大鼠昏迷量表进行意识水平的评估[45],初步证明了三叉神经电刺激能明显改善大鼠的意识状态,有效促醒昏迷大鼠。同时发现三叉神经电刺激能显著激活三叉神经脊束核和下丘脑外侧区,进而引起觉醒肽(hypocretin,Hcrt)在脑脊液中的含量增多。相关研究表明,觉醒肽的含量变化和昏迷促醒的效果密切相关[46],提示三叉神经电刺激可能通过激活特定脑区引起相关神经肽的表达和释放的增多,进而起到昏迷促醒的作用,为后续改进昏迷促醒治疗策略提供新的思路和方向。上述研究为三叉神经电刺激对脑损伤的恢复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为今后的临床应用奠定了基础。
3 小结与展望
综上所述,本文重点介绍了中枢和外周神经调控技术的种类、临床应用及其作用机制。尽管昏迷促醒技术多种多样,但是每种技术的临床疗效不一,其治疗的机理也不十分明确。虽然我们在临床治疗过程中观察到三叉神经电刺激在昏迷促醒治疗中的有效性,但仍需要大样本量和多中心的临床研究证实。在基础研究方面,我们初步证实了三叉神经电刺激能够使昏迷大鼠的脑电活动和行为学有所改善,通过三叉神经电刺激可以增加大脑皮层的血流量,减轻脑水肿,修复血脑屏障。我们进一步的研究发现,通过三叉神经电刺激,脑干和丘脑核团之间也存有着内在的联系。但鉴于中枢神经系统结构的复杂性,该疗法的机制尚需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