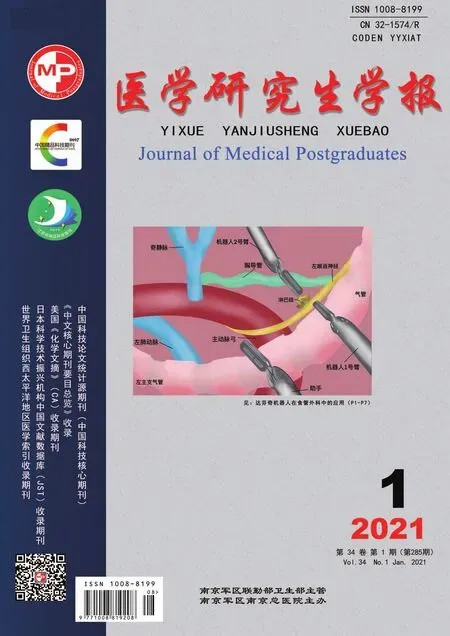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与免疫相关性肠道疾病的研究进展
2021-12-04穆燕菊静综述缪应雷审校
穆燕菊,吴 静综述,缪应雷审校
0 引 言
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myelodysplastic syndromes,MDS)是一组高度异质性克隆性疾病,高风险向急性髓系白血病(acute myeloid leukemia,AML)转化。近年来发现免疫异常在MDS发病中起重要作用并引起重视,约15%~25%的MDS与炎症性或自身免疫性疾病相关[1]。其中合并的肠道疾病以白塞病、炎症性肠病及乳糜泻较多见,且具有难治性,缺乏系统有效的治疗手段。临床通常用“一元论”对疾病进行解释,常忽略多种疾病共同发病的情况,时常延误病情诊治,故对于同时或相继出现血液学、胃肠道等多个系统的症状体征时,需考虑“多元论”进行诊疗。本文就MDS合并白塞病、IBD及乳糜泻的流行病学、临床表现、诊断、治疗及预后等研究现状作一综述,以期提高临床医师的警惕,做到早识别、早诊断、早治疗,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1 MDS
1.1 流行病学与发病机制MDS为老年男性最常见的血液病之一,流行病学报道存在一定差异。MDS在美国、亚太地区、希腊、荷兰、澳大利亚的总体发病率分别约4/10万、3.2/10万、4.8/10万、2.8/10万、4.8/10万[2-5]。成人MDS中位发病年龄约76岁[6],发病率随年龄增长而增加,且白种人(4.8/10万)较普通人(4.6/10万)高发[2]。最新的SEER数据表明80岁及以上男性、女性发病率分别约85/10万、39.9/10万,但MDS伴孤立del(5q)男女比例约1∶1.5[2]。儿童MDS发病率较低,中位发病年龄6.8岁,无明显性别差异,发病率约(1.8~4) /10万[7]。我国尚无大规模的MDS流行病学资料,多为老年发病,随着人口持续老龄化,将给社会经济发展和个人生活质量带来极大影响,需引起各界的高度重视。
MDS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清楚,目前普遍认为是多因素、多阶段、连续动态的病理过程。原发性MDS主要危险因素为年龄、男性、白种人、肥胖、吸烟等,继发性MDS主要与放/化疗史、有机毒物接触史等有关。MDS可能发病机制:遗传畸变诱发复发性体细胞突变和细胞遗传异常,约50%的MDS患者存在染色体异常(多为染色体的增添或缺失,以+8、-5/5q-、-7/7q-、20q-等常见,而染色体平衡易位较少见),继发性MDS超过80%的患者出现单基因或多基因突变,此外与免疫紊乱、表观遗传修饰(如TET2、DNMT3A、EZH2、ASXL1等)、剪切因子异常、抑制性细胞因子、铁过载等存在密切相关[8-9]。成人MDS主要为年龄积累相关的获得性体细胞突变,儿童及青少年MDS则更常与遗传易感性有关,约20%~25%儿童MDS继发于范可尼贫血、家族性MDS等先天性骨髓衰竭综合征。
1.2临床表现与诊断MDS主要表现为血细胞减少相关的症状和体征:贫血、发热、感染、出血、脾大等,但儿童MDS以单纯性贫血少见,约50%儿童病例伴有全血细胞持续性减低。MDS的诊断为排除性诊断,需排除自身免疫性溶血性贫血等自身免疫性血细胞减少症、肿瘤或风湿免疫性疾病等慢性病性贫血以及肝硬化脾功能亢进等继发性疾病等,以血象和骨髓象为基础进行综合诊断[8]。
1.3治疗与预后目前MDS的治疗方案主要包括促造血、免疫调节、甲基化、袪铁、造血干细胞移植等治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已批准阿扎胞苷、地西他滨和来那度胺3种药物治疗MDS。MDS的预后取决于是哪种亚型,约30%患者转化为AML。Aref等[6]报道MDS中位生存周期10.4~33.8个月,难治性贫血伴环形铁粒幼细胞增多最长,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原始细胞增多型最短。
2 MDS合并白塞病
白塞病是一种全身血管炎性疾病,以复发性口腔溃疡、外生殖器溃疡、眼炎为典型表现,约3%~25%可累及消化系统[10]。近年来,白塞病伴发血液病的风险明显增加。Ahn等[11]报道1.8% 的白塞病患者伴发恶性肿瘤,其中恶性血液病以MDS最为常见。李国华等[12]报道41例伴发恶性肿瘤的白塞病患者,MDS占伴发血液病的70%。此外,MDS伴发累及消化系统的自身免疫性疾病时,以白塞病最为常见[1- 2]。MDS合并白塞病有两大突出特点:一是易出现8号染色体三体异常,二是多数患者肠道病变。
2.1流行病学与发病机制白塞病自1937年首次报道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散发,以东亚延伸至中东的“丝绸之路”一带高发。有研究报道白塞病的全球总体患病率约10.3/10万,土耳其、中东、亚洲、南欧、北欧及北美的患病率分别约119.8/10万、31.8/10万、4.5/10万、5.3/10万、2.1/10万、3.8/10万[13]。我国白塞病患病率约14/10万。白塞病的发病率约0.05/10万~3.97/10万[14]。MDS合并白塞病的患病率约0.4%~3.1%[10],主要集中在亚洲国家,尤其以日本、韩国高发。我国Shen等[10]报道MDS合并白塞病的患病率约2%(16/805),以老年女性为主。白塞病诊断的平均年龄(49.9±12.4)岁,MDS为(47.5±12.2)岁,MDS合并白塞病好发于40~69岁的中老年人[15]。
MDS与白塞病虽是两组性质不同的疾病,但两者的发病机制存在一定关联,综合国内外相关研究大致归纳为三方面:①遗传畸变:目前少数个案报道MDS合并白塞病患者在接受造血干细胞移植(Hematopoietic stem cell transplantation,HSCT)后明显缓解,可见染色体及基因异常在MDS合并白塞病中有重要作用,尤其以8号染色体三体异常最为突出。Fujimura等[16]报道MDS患者中约6.5%~16.3%存在8号染色体三体异常,当MDS合并白塞病时该比例约73.3%。而一项上海的研究报道当MDS合并白塞病时该比例则高达81.3%[10]。Chen等[17]发现存在8号染色体三体异常的CD34+造血祖细胞中炎症因子基因表达明显上调。此外,淋巴细胞参与了白塞病和MDS的发病,TNF相关凋亡诱导配体 (TNF-related apoptosis-inducing ligand,TRAIL) 及其受体 (TNF-related apoptosis-inducing ligand Receptor,TRAIL-R) 对调节淋巴细胞稳态起重要作用,但值得注意的是Testa等[18]发现编码TRAIL-R的基因刚好位于8号染色体短臂21-22位点 (8p21-22)。动物实验表明由8号染色体长臂12-13位点 (8q12-13) 上的基因编码的IL-7过度表达可使小鼠产生慢性结肠炎[16]。活性氧可造成白塞病的组织损伤,存在8号染色体三体异常的MDS合并白塞病时活性氧含量则增加。尚有研究报道MDS合并白塞病的患者中存在7号染色体缺失,该异常核型可致MDS在短期内进展为AML,但确切关系尚不明[19]。②免疫异常:MDS合并白塞病存在明显的免疫调节异常、炎性因子过度产生及中性粒细胞功能障碍。白塞病的病理本质为多系统性血管炎,且免疫异常可能损伤造血干细胞,诱导MDS发生。Pineton等[20]报道淋巴细胞稳态失调参与了白塞病发病,当白塞病合并白血病时一方面白血病细胞及相关抗体直接损伤血管,另一方面通过形成免疫复合物间接损害血管。白塞病患者的IL-1β、IL-6、IL-8、IL-17、TNF -α、IFN-γ等炎症因子表达异常,而这些炎症因子也参与了MDS的发生。此外,糖皮质激素和免疫抑制剂对MDS和白塞病均有一定疗效。③药物因素:目前研究者普遍接受治疗白塞病所应用的秋水仙碱、环磷酰胺等细胞毒药物可促进MDS进展的观点。药物一方面直接引起染色体异常,另一方面间接作用于细胞调节过程,诱发MDS等肿瘤发生。鲁索利替尼对骨髓增生性肿瘤有一定疗效,但有学者报道一例8号染色体三体异常的骨髓纤维化患者在接受鲁索利替尼治疗后出现回肠多发溃疡及肠穿孔[21]。
2.2临床表现及诊断MDS合并白塞病从临床表现来看,仍以口腔溃疡、生殖器溃疡及皮肤表现等皮肤黏膜损害为突出表现,但肠道病变、发热、血细胞减少、C反应蛋白及血沉升高等表现具有一定特异性,尤其是与8号染色体三体异常相关的肠道病变。邵勤等[15]报道白塞病伴发MDS时消化道病变发生率约50%,远高于单纯白塞病的比例(21.5%~60%),且约有46.7%患者出现发热症状。有研究报道单纯白塞病患者回盲部溃疡约48.9%,而白塞病并发MDS时该比例高达90.0%[10]。对于MDS与 白塞病两种疾病发病的先后顺序目前争议较大。
MDS合并白塞病的诊断尚无金标准,以两者各自诊断成立为基础。白塞病主要依据白塞病国际标准评分系统进行诊断,敏感度93.9%、特异度92.1%[22]。有学者报道针刺反应在单纯白塞病中阳性率约60%~70%,但白塞病并发MDS时阳性率明显降低,仅为13.3%。MDS合并白塞病时,MDS分型主要以难治性贫血及难治性血细胞减少伴多系发育异常等低危组最常见[15]。这就要求在临床治疗过程中,当遇到MDS出现皮肤黏膜损害等白塞病症状或白塞病患者出现血液系统表现时,均需提高两个系统疾病重叠的警惕。
2.3治疗与预后MDS合并白塞病被认为是一类难治性疾病,预后差。尚无特效药,目前仍以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为主要治疗手段,部分患者予以化疗,极少数患者因肠道病变需手术治疗。目前有少数研究报道新兴生物制剂、HSCT等具有较好疗效[1,23]。Asano等[23]分析了10例存在8号染色体三体异常的骨髓衰竭合并白塞病患者(平均年龄29.1岁)在接受HSCT治疗后明显缓解,其中90%患者为MDS合并白塞病。也有研究者不断报道阿扎胞苷、氮杂胞苷等对MDS合并白塞病患者有效[1]。对于儿童及青少年HSCT可能是目前唯一有效的治疗方法。
3 MDS合并炎症性肠病
炎症性肠病(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IBD)是一种非特异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溃疡性结肠炎(ulcerative colitis,UC)、克罗恩病(Crohn's disease,CD)及未定型IBD。6%~47%可累及包括血液系统在内的多个肠外系统,特别是CD(35%)[24]。IBD可引起贫血、外周血细胞减少,常使临床医生忽略了IBD合并血液病的情况。IBD在MDS常合并的自身免疫性疾病中所占比例约11%~18%。自1992年Eng等[25]首次报道4例MDS合并CD患者以来,不断有研究报道MDS合并IBD的案例,可见MDS与IBD之前一定存在着某种联系。
3.1流行病学与发病机制IBD主要高发于西方国家,但近年来我国患病率也在不断攀升,据报道美国IBD患病率预计2025年达0.6%[26],中国IBD总病例预计10年内将达150万例。IBD主要好发于年轻人群,仅约16%为老年人。有研究报道IBD中MDS发病率约170/10万~550/10万[27-28],远高于普通人群,诊断中位年龄约71岁,晚于IBD的高发年龄而比较接近MDS的好发年龄。有学者表明MDS合并IBD时以CD最常见,MDS合并CD、UC及未定型IBD的患病率分别约为72.9%、25%及2.1%,且男性(62.5%)受累较女性(37.5%)多见。但目前仍缺乏大规模的临床试验来进一步证实MDS合并IBD的风险是否增加。
MDS合并IBD的机制不明,尚不能确定是共同的致病机制导致两种疾病的发生还是一种疾病继发于另一种疾病,但目前推测主要是以下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遗传畸变:涉及基因易感性、染色体异常和基因突变等多个方面。近年来研究已证实NOD2基因是CD的易感基因,同时,NOD2基因所编码的NOD2蛋白是NF-κB激活的重要调节因子,可通过调控NF-κB影响造血祖细胞发育,从而诱发包括MDS在内的血液系统肿瘤。同时,MDS是由染色体异常或基因突变所引起的克隆性疾病,这些遗传畸变可导致骨髓细胞所衍生的抗原提呈红细胞的功能障碍,从而引起IBD等免疫介导的疾病[30]。彭涛等[29]报道9例MDS合并IBD的患者中,有2例进行了染色体检测,且1例出现8号染色体三体异常(47XX+8),同时对外文文献分析发现进行染色体检测的MDS合并IBD患者约43.9%(18/41)存在染色体异常,且两种疾病的发病间隔短于染色体正常患者。Kono等[31]报道一位63岁MDS合并IBD男性患者存在8号染色体三体异常。Eng等[25]也曾报道有3例患者出现了20号染色体异常。但目前在东方人群中检测出NOD2基因突变率极低,可见遗传畸变并不能完全解释MDS合并IBD的机制。免疫异常:一方面MDS表现为T/B淋巴细胞、NK细胞、CTL细胞等细胞数目减少,Th1/Th2比值增加;另一方面MDS克隆性过度表达或产生新的抗原可能触发细胞毒性T细胞克隆增生并活化,分泌过量的TNF-α、IL-1、IL-6等炎症因子,而这些炎症因子同时也参与了IBD的发生发展。同时,CD及UC患者中CD4+Th1、CD8+Th2细胞分别占主导地位,Th1、Th2及Th17细胞大量激活,炎症因子/抗炎因子失衡,IBD患者过度表达的白细胞介素及TNF-α等可能也增加了患MDS的风险[32]。有学者报道MDS中异常骨髓细胞导致抗原提呈细胞功能异常,可产生大量TNF-α、IL-12等炎症因子诱发MDS相关的IBD[30]。亦有文献报道一位老年男性MDS合并IBD患者经乌斯他单抗(IL-12/23p40单克隆抗体)治疗后,IL-6、IL-17表达明显减低且临床症状明显缓解,可见Th17细胞可能在MDS相关的IBD中充当了重要角色[31]。其他:药物治疗、射线暴露及感染等因素亦可能参与了MDS伴发IBD的过程。已有报道免疫抑制剂和生物制剂等药物可增加MDS等血液病风险。早期关于1500例IBD患者的队列研究发现25例患者伴发MDS,且其中2例患者有硫唑嘌呤及类似物使用史[27]。近期文献报道接受硫唑嘌呤治疗的患者MDS风险明显升高,标准发生率约3.7~8.4。射线暴露为继发性MDS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IBD患者行影像学检查时射线暴露的机会也随之增加,可能增加伴发MDS的风险。此外,MDS患者的中性粒细胞吞噬及杀伤能力受损,易发生感染,尤其是胃肠道感染,致使肠道菌群紊乱,进一步促进IBD的发生发展。
3.2临床表现及诊断MDS合并IBD时缺乏特异性的临床表现,为两类疾病各自临床表现的合集。UC主要临床表现为腹痛、腹泻及黏液脓血便,CD则以腹痛、腹泻、体重下降伴发热、肛周脓肿/瘘管及肠外表现等为主。据报道一位IBD伴发MDS患者出现了腹痛、腹泻、发热、回肠末端溃疡、C反应蛋白及红细胞沉降率明显升高等IBD表现,以及外周血细胞三系减少、贫血等MDS表现[31]。另一项研究也报道了类似表现[30]。MDS合并IBD时,以IBD首先发病多见,其中CD、UC及未定型IBD首发所占比例分别约58.3%、22.9%及2.1%。MDS合并IBD肠道受累以结肠病变最常见(52.1%),回肠受累27.1%,回、结肠均受累12.5%,左半结肠受累6.2%,仅直肠受累2.1%[29]。
MDS合并IBD诊断同样取决于各自诊断是否成立。IBD的诊断主要依据症状体征、内镜、实验室、影像学及病理组织检查。MDS诊断同前述。在临床实践中,若IBD出现外周血细胞若干系减少及一般治疗难以纠正的贫血时需注意是否合并MDS等血液病;同样,MDS出现腹痛、腹泻、黏液脓血便等时需警惕是否合并IBD,尽早完善骨髓穿刺、内镜及活检等针对性检查。
3.3治疗与预后MDS合并IBD目前以激素联合免疫抑制剂治疗为主,但疗效欠佳,且MDS免疫力低,使用免疫抑制剂可能诱发致命性的感染。一些研究报道抗TNF-α抗体、新型生物制剂及HSCT对MDS合并IBD具有一定疗效,但也有文献报道对这些治疗存在抵抗。TNF-α均参与了IBD及MDS的发病,目前英夫利昔单抗(抗TNF-α抗体)主要运用与IBD特别是CD的治疗,但也有用于治疗MDS有效的报道[33]。有学者报道一位MDS相关的IBD患者在接受阿扎胞苷(DNA甲基转移酶抑制剂)治疗后肠道溃疡消失[30],临床症状缓解。而另外一篇文献则报道一名63岁MDS合并IBD患者对抗TNF-α抗体及阿扎胞苷抵抗,而经乌斯他单抗治疗后好转[31]。HSCT是根治MDS等血液病最有效的方法,且近来HSCT开始应用于重症IBD治疗,HSCT或为MDS合并IBD的潜在治疗方法。Hu等[34]报道1例CD合并MDS患者在接受HSCT治疗9个月后停止免疫抑制剂,14个月后症状完全缓解。
但总的来说,MDS合并IBD预后不佳,有证据显示19例MDS合并IBD患者,17例无缓解,且最终4例在1年内死亡。这可能因为:①发病机制有异于单纯的两种疾病;②MDS及IBD相互干扰两种疾病对常规药物的反应;③MDS合并IBD好发于老年人,受基础疾病影响且接受HSCT等治疗机会小;④可能伴发致命性的感染。
4 MDS合并乳糜泻
乳糜泻又称麦胶性肠病,是遗传易感人群因摄入麸质蛋白而诱发的一种自身免疫性慢性胃肠疾病。贫血为非经典型乳糜泻最常见的肠外表现之一。据报道缺铁性贫血患者中乳糜泻患病率约3%~9%,而存在消化道症状时该比例达10%~15%,可见乳糜泻与血液病关系密切[35]。MDS合并乳糜泻报道较罕见,但两者可能存在某种关系。
4.1流行病学与发病机制乳糜泻发病具有地域差异性,主要集中于北美、欧洲及澳大利亚,患病率约0.3%~5.6%,美国的诊断平均年龄38岁,仅20%患者年龄大于60岁,且以女性受累多见[36]。MDS合并乳糜泻较罕见,尚无明确的流行病学资料。Bindi等[37]曾报道了3例MDS伴发乳糜泻患者,中文文献尚无相关报道。
MDS合并乳糜泻的机制尚不明确,基因易感性及免疫异常可能参与了发病。基因突变及染色体异常是导致MDS的主要原因,而30%~40%的人群存在乳糜泻遗传易感性[38]。已确定HLA-DQ2和HLA-DQ8为乳糜泻的潜在致病基因,麸质蛋白肽刺激HLA-DQ2和HLA-DQ8限制性T细胞时可进一步诱发固有免疫及适应性免疫应答,从而表达大量的IL-15、IFN-γ等细胞因子,而MDS的细胞因子也表达异常[39]。
4.2临床表现及诊断治疗MDS合并乳糜泻时两种疾病的临床表现均存在,无特异性表现。经典型乳糜泻患者通常表现为腹痛、腹胀、慢性腹泻、脂肪泻等胃肠道症状,但仅可解释约30%的确诊病例[36]。非经典型乳糜泻则以缺铁性贫血、代谢性骨病、转氨酶升高等肠外表现为主,易误诊误治,致使约75%~90%的乳糜泻患者未被确诊[40]。MDS合并乳糜泻需两种疾病均确诊。小肠组织活检是诊断乳糜泻的金标准,结合临床表现、特异性血清血标志物(如抗组织转谷氨酰胺酶IgA抗体)及有无麸质蛋白饮食综合诊断。当存在与铁、叶酸或维生素B12等吸收不良无关的贫血,特别是大细胞性时需考虑是否叠加MDS。对于MDS合并乳糜泻尚无特效的治疗方法,一方面严格无麸质饮食,另一方面控制MDS的进展。
5 结 语
MDS与白塞病、炎症性肠病等多种免疫相关性肠道疾病关系密切,但目前资料主要来源于个案报道,缺乏大规模的大样本多中心随机试验结果作为支撑。临床诊疗过程中应尽早完善骨髓穿刺、内镜、活检等相关检查尽早确诊,并不断寻找及开发具有较好疗效的治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