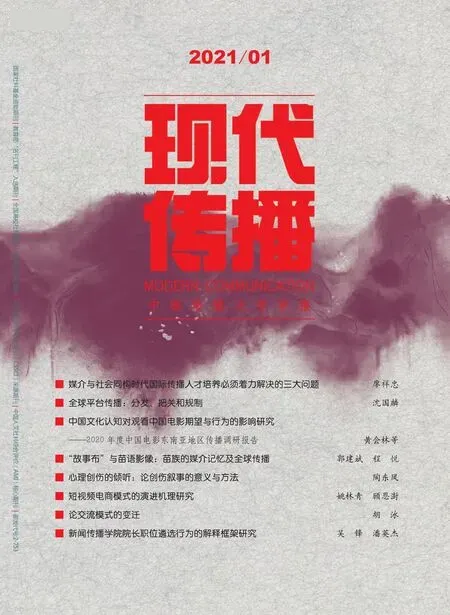心理创伤的倾听:论创伤叙事的意义与方法
2021-12-04陶东风
■ 陶东风
20世纪后期,随着战争创伤神经症在越战老兵身上不断出现,一大批来自不同领域的学者开始把目光投向创伤研究并不断取得进展。①在众多创伤研究成果中,如何通过受害者的讲述进行创伤的治疗和修复,是一个重要方面。比如,临床心理医生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的《创伤与复原》(Trauma and Recovery,1992)一书主张:个体的创伤可以通过向别人讲述的方式得到复原。②这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思考和治疗创伤的方式,该著作一度成为心理创伤治疗领域的畅销书。
但是,讲述不是独白,不是讲述者(创伤受害者)能够单独完成的独角戏,而是讲述者与倾听者(包括但不限于心理医生)之间的对话(即使听者常常只是若隐若现地低调在场,这在场也至关重要)。创伤受害者是否愿意讲述,讲述什么和如何讲述,都与倾听者的在场及其倾听方式密切相关。大屠杀幸存者、意大利著名见证文学作家普里莫·莱维在其第一部杰出的见证作品《这是不是一个人》的“作者前言”中这样解释大屠杀幸存者的创伤讲述动机:“写本书的意想和念头在死亡营的那些日子里就已经产生了。出于把事实讲述给‘其他人’听的需要,出于想让‘其他人’参与的需要,在从死亡营里出来获得自由的前后,这种需要存在于我们中间,像有一股强烈而又直接的冲动,它并不亚于人活着的其它基本需要。”③
大屠杀的幸存者,也是20世纪最大的创伤受害者群体,其讲述/见证的需要与被倾听的需要是相互依存的。讲述离不开听众,见证本身需要被见证。希望被倾听是讲述的基本动力。莱维还写道:在战后作为一家化工厂的化学家在来往于都灵(莱维的家乡)与米兰(莱维工作的地方)的日子里,他无法控制地、“随心所欲地”和火车上那些不认识的人交谈,向他们讲集中营的故事。据莱维的访谈者马可·贝波里蒂记载,莱维不止一次把一本书比作“一部能够运作的电话”④。“电话”是一个交流而非独白的工具,说话人知道在电话的那头有人正在倾听。
在回答安东尼·鲁道夫的采访时,莱维进一步把这种指向倾听的讲述和书写大屠杀记忆视作一种治疗/康复:“写作《这是不是一个人》是一种治疗,当我回到家中时,我丝毫不平静。我感到彻底的不安。我对所有人,甚至不认识的人,讲述这些故事。”这是因为,“通过写作,我有了被治愈的感觉。我被治愈了”⑤。
一、创伤叙述者的困境
很多大屠杀幸存者都不愿意甚至断然拒绝讲述自己不堪回首的往事。耶鲁大学心理学教授多丽·劳布用“对回归的畏惧”(the dread of return)表达幸存者的这种心理,并提出了“二次伤害”的概念。⑥劳布指出,回忆过去、讲述创伤很可能会成为对受害者的“二次伤害”:“对于命运重演的畏惧成为创伤记忆的关键,也成为不能言说的关键。一旦内在的沉默被打破,一直被回避的大屠杀可能会复生并被重新经历。然而这一次创伤受害者再也没有了忍受煎熬的能力。”好不容易九死一生活下来的幸存者,谁又愿意“再死一次”?“如果打破沉默的代价是再度经验创伤,叙述行为就可能增加伤害。不是解脱,而是二度创伤。”⑦挺身而出见证大屠杀的作家、诗人,比如策兰、莱维,最后都选择了自杀,不能不让人感慨系之。
为什么讲述创伤会成为“二次伤害”而不是解脱或新生?在这里,有没有倾听者以及听的方式至关重要。“如果讲述创伤的人未能被认真聆听,讲述行为就会被经验为创伤的复归——重新经历创伤事件本身。”⑧可见,未被认真倾听是造成“二次伤害”的根本原因。这里涉及的情况非常复杂,值得分层次认真深入地予以分析。
首先,大屠杀幸存者在面对自己创伤性的过去时,常常陷于尴尬、分裂、矛盾、纠结的处境。对此,美国著名创伤研究专家、哈佛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系临床教授朱迪思·赫尔曼曾有如下描述:
对暴行的一般反应是将它排除于意识之外。某些反社会常态的事,会恐怖到让人无法清楚表达的程度,而只能用难以启齿(unspeakable)这个词形容了。
一方面想要否定恐怖暴行的存在,另一方面又希望将它公之于世,这种矛盾正是心理创伤的主要对立冲突之处。暴行的幸存者通常会用高度情绪化、自相矛盾和零碎片段的方式述说他们的惨痛遭遇,但这种方式严重损及他们的可信度,因而导致出现到底是说出真相,还是保持缄默的两难困境。
受创者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症状是:既想让人注意到那难以启齿的创伤秘密,又想极力掩盖它的存在。⑨
很多幸存者不愿意讲述、见证大屠杀的暴行,是因为它实在过于残酷血腥,太不堪回首、难以讲述。幸存者不愿意再次揭开伤疤完全合乎情理。这里面既有加害者令人发指的罪与恶,更有受害者人性沦丧的耻与悔。集中营是一个让人失去人性、蜕化为动物的地方(比如像动物一样与其他囚犯争食,趴在地上吸食别人的呕吐物,为了自保而对自己的狱友甚至亲人极度冷漠,等等)。正因为这样,莱维认为奥斯维辛是让人沦为畜生的大机器。用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姆·贝托汉的话说:“我们希望遗忘它……希望忘记德国灭绝营的故事。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希望它压根就不曾发生。我们最能接近于相信这个故事的办法,就是不要再去想它,这样我们就没有必要去勉力接受其噩梦般的场面。”⑩集中营挑战了我们对人的自信和乐观,对上帝的期待和信仰,将人性的脆弱和幽暗暴露无遗。这样,创伤受害者常常宁愿选择沉默以便保护自己。
但是,这恰恰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大屠杀创伤见证的必要性。见证大屠杀的意义有很多,但笔者认为最重要的是丰富、深化对人性——尤其是人性之阴暗面的理解。用芝加哥大学教授布鲁姆·贝托汉的话说,集中营“让我们多了一个认识人类的维度,一个我们都想要忘却的那个方面”。“想要忘却”的方面正是人不愿意面对的人性之脆弱、阴暗:不仅是刽子手的极恶,也包括受难者在极权环境下的软弱、苟活、奴性、自私、堕落。“灭绝营的独特之处,并不在于德国人在这里灭绝了上千万的人口……真正新颖、独特、吓人的,是数量如此之众的人,他们就跟挪威旅鼠一样,是自觉排队走向了死亡;这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这是我们必须慢慢弄明白的事情。”在一般的情况下,这些阴暗面常常被掩埋在无意识深处,只有在集中营这样的极端环境下才暴露无遗。它才是更需要见证的心灵创伤。
二、通过倾听参与创伤
遗憾的是,尽管有些幸存者选择勇敢地站出来作见证,但他们却常常遭遇不被倾听或不被相信的尴尬、失望乃至绝望的境遇。莱维本人就不止一次写道:他的见证、他关于奥斯维辛的讲述无法引起听众的兴趣。在《这是不是一个人》中,他记载了听者对自己的讲述“无动于衷”“毫不在乎”,他们“谈论着其他的事情,仿佛我不在场”。莱维对此感到心痛:“一种绝望的悲伤生自我心”,“为什么每日的痛苦如此不停息地转化进我们的噩梦中,永远重复着同样的遭遇——没有人倾听我们的故事?”这就是说,这种不被倾听的悲伤和绝望甚至变成了一种反复纠缠幸存者的噩梦,变成了另一种新的创伤。“我们经常觉得,自己是令人厌烦的讲述者。有时甚至眼前出现了一种象征性的梦,好奇怪,那是在我们被囚禁期间夜里经常做的梦:对话者不再听我们在说什么,他听不懂,心不在焉,然后就走掉了,留下我们孤零零的。”
这里的“听不懂”不能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幸存者证词的文字并不艰涩),它实际上是指由幸存者讲述的故事与听者的常识(惯常化的知识和经验)之间的鸿沟导致的难以置信。大屠杀实在太黑暗、太骇人听闻、太令人匪夷所思,以至于超出了人类的理解能力和认识范畴,让人无法相信。埃利·维赛尔在其《夜》的“作者序”中写道:“凭心而论,那时的目击者都认为,至今仍然认为,别人不会相信他们的见证,因为那样的事件发生在人类最黑暗的地带。只有到过奥斯维辛的人,身临其境的人,才知道事情的本来面目,别人则永远不会知道。”法国著名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里亚克在《夜》的“前言”中也指出:“谁能想到世界上竟然有这种事情!把羔羊从母亲怀中夺走,这种暴行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莫里亚克将之称为“诡异的邪恶”,认为它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相当多的研究成果证明:“心理创伤的研究不断带领我们进入不可思议的领域,并让我们的一些基本信念濒临崩溃。”
除了知识上的断裂之外,拒绝倾听创伤的更深层原因恐怕来自情感上的抗拒和抵制。如上所述,集中营的故事骇人听闻,暴露了大量存在的难题,蕴含了人性中最幽深、最深藏不露、羞于公开的奥秘。倾听这样的故事,固然是一个难得的深入了解人性、认识他人、认识自己的机会,但也是对听众心理承受力的挑战。讲述和倾听这样的创伤故事,不但对于讲述者,而且对倾听者而言都是一件极其痛苦、难堪甚至是难以忍受的事情,是一场充满陷阱的冒险之旅(甚至自己遭遇创伤化)。正因为这样,劳布指出,必须控制好倾听者在听的过程中可能会产生的种种抵制(心理防御),包括担心被讲述的暴行所淹没,陷于灭顶、瘫痪的感觉,强烈的退出(不想再听下去)欲望,等等。
这样,倾听创伤的人必须勇于在听的过程中变成创伤的参与者与共享者,在自己身上部分地经验创伤及其带来的痛苦。也就是说,在听的过程中,受害者与创伤事件的关系,会转移到听者那里。倾听者如果想要发挥听者的功能,如果想要让创伤呈现出来,就必须分担所有消极情绪,与受害者/讲述者一起与过去的创伤记忆“搏斗”,与遗留的消极情绪“搏斗”。听者必须从内心深处感受受害者的失败与沉默。而这,正是见证得以形成的前提。
当然,倾听者在参与创伤的同时却无需也不应该完全变成受难者。倾听也是见证,是对受难者的见证行为及证词的见证。但他仍然是一个独立个体,保持着自己独立的位置和视野。“听者在发挥创伤证人之证人的功能(function of a witness to the trauma witness)的同时,依然是一个独立的人,体会到他自己的为难与挣扎。虽然与受害者的经验部分交叠,他依然没有变成受害者——他保持了自己独立的位置、立场、视角。”倾听者是分裂的,各种力量在他身上搏斗、撕裂,如果他要适当地执行其任务,就必须尊重自己的这种冲突和分裂身份。
由于倾听者参与了创伤见证的发生,因此,倾听者既是“创伤证人的见证者”(witness to the trauma witness),见证了证人的诞生(大屠杀的受害者并不都是见证者,他们中的大部分选择了拒绝回忆、拒绝作证);同时也是自己的证人,见证了自己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倾听者。通过同时意识到既存在于创伤见证者、也存在于他自己的内在的、持续的冒险,他的倾听使得他成为使见证成为可能的人:启动见证,同时成为见证过程和见证动力的维护者。
三、讲述、倾听与治疗
创伤经验的根本特点之一是:它总是像一个难以驱散的噩梦不断返回来纠缠受难者。现代创伤理论的创始人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1917)中强调:创伤是一种突发的、人在意识层面无法适应的震惊经验,且这种经验具有持久性、顽固性和反复性。他给“创伤”下了这样的定义:“一种经验如果在一个很短暂的时期内,使心灵受到一种最高度的刺激,以致不能用正常的方法谋求适应,从而使心灵的有效能力的分配受到永久的扰乱,我们便称这种经验为创伤的。”在1920年出版的《超越快乐原则》中,弗洛伊德把创伤与“梦”联系起来,指出:创伤对于意识而言是一段缺失的无法言说的经验,人们常常在不知不觉间无法自控地重复伤害自己或他人,这种“重复强制”的行为,即我们所说的创伤;而其无法把握、难以言说的陌生性,被劳布称为创伤的“他者性”(a quality of otherness)。
创伤事件虽然真实,但是却在“正常现实”的范围外发生,超越了寻常的因果、顺序及时空,这使它处于相互联系的经验范围之外,也缺乏界定它的现成知识范畴,难以理解、无法叙述(参见上文)。如果不能得到有效治疗,创伤受难者就将带着一个永远没有终结、也无法终结的噩梦活着。这一点在创伤文学的创作上也有反映。欧文·豪指出:经历过奥斯维辛和古拉格的作家,“他们必须带着给他们留下永恒伤疤的经验而活下去。他们反复地、时常强迫性地回到这个主题”。有很多集中营的幸存者一方面拒绝回忆,拒绝谈论(集中营的)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拒绝交往并陷于幽闭麻木;另一方面又无法忘记,长期被噩梦所折磨。依据朱迪思·赫尔曼的命名,前者为“禁闭畏缩”,后者为“记忆侵扰”,这两个“相互矛盾的反应,会形成一种摆荡于两端的律动”,它是“创伤后症候群”的最大特征。
精神分析理论在这方面开出的药方是:为了摆脱这不可知、不可说而又无休止纠缠幸存者的创伤经验,必须启动一个治疗过程,通过精神分析师的倾听和引导,让幸存者通过讲述使创伤事件再外在化(re-externalizing the event);而再外在化的过程必须有医生——可以理解为一种特殊的倾听者——的配合:“这个事件的再外在化只有在一个人可以表达并传递(transmit)故事给外在的他人并再次收回于内的情况下,才能发生并生效。”
同样,耶鲁大学大屠杀音像资料中心收集的那些关于创伤的自传性叙述,既是对创伤的见证,也是与心理分析类似的治疗过程。与叙述的双重功能(见证与治疗)相对应,资料中心的研究者如费尔曼、劳布,也具有双重角色:既是治疗者,也是访谈者(倾听者)。创伤讲述、历史见证与心理治疗是同时展开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心理医生与创伤受害者之间的相互信任至关重要。医生要和“病人”一起通过相互之间的“安全测试”:相互证明对方的持重、理性、沉稳、值得信任和尊重。只有这样,幸存者才会把自己“托付”给医生/访谈者。这意味着医生/聆听者与“病人”/讲述者在通过“安全测试”后建立了“信任合约”:“其中一方持续地叙述创伤、展现其生命记录,而另一方则暗示地对见证者说:在整个见证的过程中,我将尽我所能始终陪伴你。你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我将全程保护你。在旅途在终点,我将离开你。”一方面,这个倾听者需要保持“低调在场”(unobtrusively present)的姿态,不能粗暴、轻易地介入见证过程,不能自我张扬、自以为是、喧宾夺主;另一方面,他又要敏锐感受并记录证人言说中的蛛丝马迹,在受害者犹豫、退缩时扶持、鼓励他/她继续讲述下去。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著名神经生理学家、心理学与人类学家教授里弗斯,与他的病人西格弗里德·萨松之间就建立了这样一种“信任合约”。萨松原为一名骁勇善战的军官,但后来转变立场成为著名的反战诗人和献身人类和平事业的公共知识分子。他因此而遭到极大的压力甚至可能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同为诗人的军官同僚格雷夫斯安排萨松去里弗斯那里接受治疗。里弗斯尝试用人道主义的方法来治疗萨松、并以此证明其比惩罚性的传统方法高明。他以有尊严的、尊重的态度对待萨松,鼓励萨松自由地说出战争的恐怖。对此萨松充满感激:“他(里弗斯)让我立刻有了安全感,他似乎了解我的一切。……我愿意用尽我收藏的留声唱片去换取一点我和里弗斯的谈话录音。”
这再一次表明:见证不能由创伤受害者一个人在孤独中进行,必须有可信赖的、合格的、乐于倾听的“他者”,“见证创伤的过程是包含听者的过程,为了让见证过程发生,需要一个他者的、连接性的、亲密的、完全的在场并处于倾听的位置”。“证人是在和某些人说话,和某些他等待已久的人说话。”很多人就是因为缺少这样的倾听者、陪伴者而失去了见证的动力和勇气。
从伦理角度看,创伤讲述的最终目标是修复创伤者与他人及世界的信任和爱的关系。赫尔曼认为:在创伤事件发生之后,患者变得更加容易受到伤害,他们或过度警觉,对世界失去信任;或深受记忆侵扰,创伤经验以强迫重复的方式不断返回;或紧闭畏缩,对一切麻木无感。特别是,创伤事件粉碎了人与社群之间的连接感,受害者对社群产生普遍的不信任感,认为这是一个“虚伪”的世界。“它(创伤事件)撕裂了家庭、朋友、情人、社群的依附关系,它粉碎了借由建立和维系与他人关系所架起来的自我,它破坏了将人类经验赋予意义的信念体系,违背了受害者对大自然规律和上帝意志的信仰,并将受害者丢入充满生存危机的深渊中。”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方法就是重建与他人、与社群、与世界的连接关系,使得“个人与广大的社群有更多的接触与互动”。如此,创伤的讲述才必须指向听者,它本质上必须是双向的交流,只有交流才具有修复人际关系、修复创伤者与世界之关系的功能,才能恢复生命的“外部关联性”。这一切通过独白是无法实现的。但如果创伤者的讲述不被倾听、不被理解,就必然使得他长期缺乏“人类一家的感觉”(the sense of human relatedness),缺乏被爱的感觉,甚至出现错觉,觉得自己爱别人不够,认为自己才是要对灾难负责的人。未被讲出的事件在他/她的无意识中变得如此扭曲,以至于使得他/她相信是自己而不是加害者,要对其所亲历的暴行负责。这样的受害者变得完全丧失了见证的能力,劳布称之为“见证的崩溃”(collapse of witnessing)。
四、善于倾听沉默,尊重知识局限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在倾听创伤见证的过程中,听者不应该过分纠缠于细节的准确性,尤其不应该对真实性持有机械的、僵化的理解,而应尊重受害者在特定条件下的知识局限。如前所述,创伤受害者并不拥有对于创伤事件的完整知识,更不能透彻理解它。以大屠杀为例,幸存者对于大屠杀的记忆很可能在细节上不准确(尤其是从科学真理的标准看)。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是:耶鲁大学大屠杀见证录像资料中心的一个访谈者、奥斯维辛集中营一个年近七旬的女性幸存者,在回忆奥斯维辛集中营暴动时出现了细节错误。她说暴动那天晚上“四个烟囱窜出火焰,火光冲天”。之后不久,有一个历史学家在一个研讨会上就此指出:该妇人所说“四个烟囱”不符合历史事实。事实上当时冒火的烟囱只有一个而不是四个。他由此断言这个证人的记忆不准确,其见证不可信。在他看来,细节真实具有绝对甚至唯一的重要性,否则就会被历史修正主义者抓住把柄加以利用。
劳布本人也参加了这个会议。她不同意这位历史学家的观点。她的理由是:“这位妇人见证的不是爆炸烟囱的数量,而是某种更根本、更关键的事实。一个不可想象的事件的发生。”在奥斯维辛,一个烟囱的爆炸和四个烟囱的爆炸一样不可思议。数量的多少不如发生的事实及其给犯人带来的震撼重要,更不如它所代表的纳粹无往不胜的神话的破灭重要。这个难以置信的事实的发生打破了关于奥斯维辛不可抗拒的主导认知框架,依据这个框架,犯人在奥斯维辛进行武装抵抗这样的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而这位妇人见证的就是这个框架的破灭。这是一个比细节更为重要的真理。
劳布的观点让我想起苏联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观点。在《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又译为《战争让女人走开》《战争中没有女性》等)末尾附加的创作谈《写战争,更是写人》中,她自称“灵魂的史学家”,反复强调战争书写中人性维度和情感维度的重要性,甚至说“我不是在写战争,而是在写战争中的人。我不是写战争的历史,而是写情感的历史”。与“战争的真实”相比,“人性更重要”。阿列克谢耶维奇将自己的上述见解提升为自己的记忆理论:“回忆”不是对已逝去的经历作冷漠的复述或记录。“当时间倒退回来时,往事已经获得了新生。”因此,回忆也是一种创作、至少是一种重构。省略、补充、改写是无法避免的。在其《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史》的“结束语”中,阿列克谢耶维奇写道:“我常常想,相对于简单而机械的事实而言,人脑海中的那些模糊的情感、传言、印象其实更接近事实真相。……令我着迷,念念不忘的也恰恰正是这些情感的演变历程,以及人们再谈及这些情感时无意之中表露出来的某些事实。我尝试着去寻找这些情感,然后把它们收集起来,加以保护。”显然,那位集中营幸存妇女心目的“四个烟囱窜出火焰”应该就是她“心中念念不忘”的“脑海中的印象”。
无论是历史学家、精神分析学家还是作家,都应该尊重幸存证人的知识局限,不能以此为由其剥夺其讲述的权利。比如,劳布得知这个妇人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属于“加拿大突击队”成员。这个突击队是纳粹从囚犯中选出的一些人组建的,其工作是挑捡被瓦斯毒死的犹太人的遗物,纳粹要将它们没收并运回德国。她在访谈中自豪地回忆起自己如何把一些比较好的衣服偷偷私藏并送给自己的囚犯同伴。但她根本不知道自己所属的突击队,也不知道这些遗物来自哪里。这就是所谓的“受害者的知识极限”。这个时候,劳布知道自己不能再问下去,应该尊重这个极限。劳布就此阐释道:“作为一个访谈者与倾听者,我所尝试的恰恰就是尊重——不要扰乱、逾越——妇人之所知与其所不知、所不能知之间微妙平衡。只有以这种尊重——对局限和沉默的边界的尊重——为代价,妇人所确知的东西——也是我们一无所知的东西,她下决心加以见证的东西——才能发生并得到倾听。”如果像历史学家那样抓住妇人的知识局限不放,并全盘否定其证词的见证价值,这就必然导致只有她能传达给我们的信息、只有她能讲述的故事,也一起遭到清除。
倾听者/访谈者不但不能以自己的知识(比如这次起义被无情镇压,起义囚犯被全部处决,而且在起义一开始就遭到了波兰抵抗组织的背叛,等等)和预先见解干扰、妨碍见证人讲述,或者质疑其讲述的全部真实性,而且还要明白倾听者的历史知识、其既定的理解模式,反倒可能会干扰其倾听,而且其自身也带有很大的局限性。劳布对此始终保持了高度的自省和反思:“我可能会有证实自己所知的冲动,而提出使见证翻车(derailed the testimony)的问题。……不论我事先设定的议程是历史的,还是精神分析的,都可能不自觉地干扰见证的过程。在这方面,有时候不知道太多反而有用。”
这绝非为无知辩护或提倡无知。为了能够听见、能够觉察暗示,倾听者必须有足够的知识。但是这些知识不应该以既定结论或预先的拒绝来干扰或阻碍倾听的过程,不应该遮蔽不可预见的、崭新的、充满分歧的信息。重要的是在见证展开的过程中发现新的知识。见证中的知识不是对现成的“既成事实”的复制,而是一个新的、有自己独立存在理由的事件。受难者见证的是他/她的心中、他/她眼中的历史,而且是只有她才能见证的历史真理中的本质部分。比如这个妇人看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烟囱在爆炸,也就是不可想象的事情正在发生,她所见证的就是她亲眼所见之事的不可思议性,是对暴行的抗拒,是对生还的执着,是关于反抗行为的活生生记忆。这种记忆是历史学家不具备的,尽管历史学家所掌握关于烟囱的数量、暴动的失败、反抗者的惨死等知识,是这个妇人所不具备的,但这并不影响其见证的独特价值。这种“不可思议性”打破了奥斯维辛的神话,导致了既定的“奥斯维辛框架的突然破裂”(bursting open of very frame of Auschwitz);而历史学家证实的事实(如只有一根烟囱爆炸,波兰地下组织的背叛),并没有打破这个框架。
莱维在其小说《扳手》中写道:“正如讲故事是一门艺术一样——将故事千回百转地严丝合缝地组织起来——倾听也是一门艺术。它同样古老,同样精妙。”的确,倾听也是艺术,而且倾听的水平直接影响到讲述的水平。交谈是必须的,但交谈也是艰难的。俄国著名诗人曼德尔斯坦姆有言:“一次谈话的平台是以登山运动员般的努力为代价创建起来的。”这句话被当作普里莫·莱维、乔瓦尼·泰西奥的对话录《与你们交谈的我——莱维、泰西奥谈话录》开篇的卷首语,值得我们深长思之。
注释:
① 至20世纪90年代,创伤研究达到了其黄金时期。在此过程中,先后涌现出一大批历史学家、人类学家、精神分析学家和文学—文化批评家,如劳伦斯·兰格(Lawrence Langer)、阿尔文·罗森菲尔德(Alvin Rosenfeld)、杰弗里·哈特曼(Geoffrey Hartman)、朱迪斯·赫尔曼(Judith Herman)、多丽·劳布(Dori Laub)、凯西·卡鲁斯(Cathy Caruth)、卡莉·塔尔(Kalí Tal)、多米尼克·拉卡普拉(Dominick Lacapra)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79年,针对“二战”中犹太人被屠杀的历史,心理医生、大屠杀幸存者多丽·劳布与大名鼎鼎的文学理论家哈特曼等,启动了著名的“大屠杀证词福图诺夫录像档案”(Fortunoff Video Archive for Holocaust Testimonies)研究项目,所有档案均存放于耶鲁大学的斯特林纪念图书馆。这一工程大大激发和促进了之后的创伤研究,也使得耶鲁大学成为创伤研究的重镇。
② [美]朱迪思·赫尔曼:《创伤与复原》,施宏达等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9年版。
④ [意]马可·贝波里蒂:《我是一头半人马》,载[美]普里莫·莱维:《记忆之声:莱维访谈录,1961-1987》,索马里译,中信出版集团2019年版,前言第17页。
⑥ 在研究如何倾听创伤诉说的学者中,耶鲁大学心理医生多丽·劳布(Dori Laub)值得重视。在其与文学研究者肖珊娜·费尔曼(Shoshana Felman)合作撰写的《证词:文学、心理分析与历史中的见证危机》(Testimony: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Psychoanalysis,and History,1992)一书中,两位作者从精神分析和文学批评的视角对大屠杀见证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特别是劳布执笔的第二章“见证或听的变迁”(Bear Witness or the Vicissitudes of Listening)与第三章“无见证的事件:真理、见证与幸存”(The Event without A witness:Truth,Testimony and Survival),就创伤见证与倾听之间的关系、访谈者(作为特殊的倾听者)与受访者(诉说者)的关系等问题,提出了极具启发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