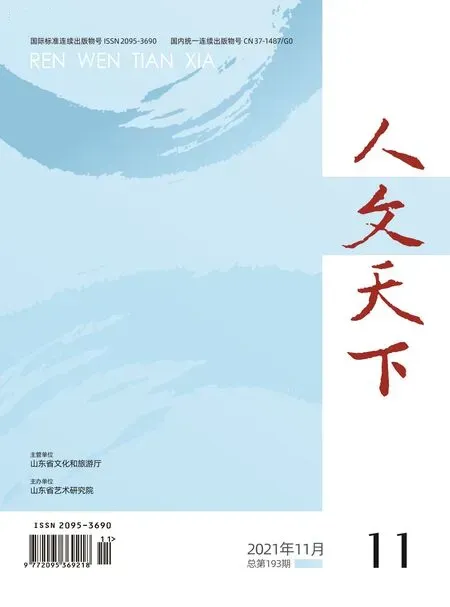符号、镜像、生活:女性话语下的革命叙事
——评莱芜梆子《新娘》
2021-12-04■莫非
■莫 非
革命历史题材是中国戏曲现代戏的类型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百年文艺的重要内容,革命历史主题为戏曲提供了“时代主体性的思想内容”和“独具时代性的叙事形态”。莱芜梆子现代戏《新娘》是山东省地方戏振兴保护剧本扶持项目、山东省舞台艺术重点创作项目及济南市舞台艺术创作重点扶持项目,该剧以抗日战争为背景,取材于有“带枪的老乡剧团”之称的莱芜响水湾剧团的历史事迹。新娘青青在新婚之日,遭遇指腹为婚的丈夫林大钟离家参加革命并拒绝婚约,由于婆婆的隐瞒,不知情的青青一边等待丈夫归来,一边在响水湾剧团参与抗日宣传和战斗,并遇到了同样寻找在前线爱人林汉卿的女八路军战士红梅。红梅为保护百姓而牺牲。青青在战场上见到了红梅的爱人林汉卿,并在战斗结束后,发现林汉卿竟与自己一直等待的丈夫林大钟是同一人。面对真相与现实,战争与人生,亲情、爱情与革命情,青青做出了自己的选择。
一、作为符号的爱情:革命与成长叙事的象征
婚姻和爱情是《新娘》叙事的一条线索,剧情从新娘杨青青的婚变而起,因青青与红梅对爱人的等待和寻找延续,以青青的爱情选择结束。同时,剧中还有另一条叙事线索,即革命战争背景下个人的命运历程与成长。爱情、革命、成长三个要素构成了这两条交织线索的核心叙事结构。其中,爱情作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于人物形象的塑造与全剧主题意蕴的营造中呈现出其象征意义。
爱情对于青青来说,首先是一个心结,同时也是其追求。因为丈夫在新婚之夜离家,青青作为在封建婚姻习俗和传统思想束缚下的女性,第一反应便以为自己被嫌弃、被抛弃了,随后因相信婆婆“只要你在,他会回来”的承诺而决定等待。看似自愿选择的背后,既有战乱的危险、父母双亡的家境及乡村社会的礼俗规则等外在因素造成的不得已,也有青春少女对爱情的憧憬,还有一份个性独立的不甘。即使几年过去,走进了剧团的一方新天地,青青仍然“还有一个心愿藏心间,只要能找到他见上一面,我甘愿随剧团走遍山川”,因为她认为林大钟“识文解字该懂理”,不理解他“不辞而别为哪般”。所以,青青坚持保持新房陈设,就为了要等对方“亲口道由缘”,给自己一个交待。然而在等待的过程中,青青及其爱情逐渐发生了变化。青青与林大钟从未谋面,在舞台呈现上,林大钟这个角色也一直未出场,仅以幻象的形式出现在青青的思念和想象中。作为一个缺席的“在场”,催化着两个女性角色之间的情感交叠与关系的发展。只存在于青青想象中的这个丈夫形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模糊,又随着他人的描述而在幻想中被青青不断地再塑造,从婆婆口中的“忠厚,模样好,识文解字”,变化成红梅“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方方的脸膛、高高的鼻梁”的爱人林汉卿的样子。在战乱的苦难和等待的未知中,对丈夫的想象带给青青情感上的慰藉和心理上的支撑,但青青原本真实、具体的爱情对象林大钟也在这种想象中逐渐消隐,被理想化、典型化为一个丈夫的符号和爱情的象征。
随着外部环境的变迁,青青爱情的变化与其成长历程构成了同频共振的关系。在敌人围困的危急情况下,她毅然决定烧掉代表其婚姻存在证明的新房;面对敌人威逼利诱,她坚守不屈力图保护红梅;被红梅的牺牲所震撼和感染,她决心要像红梅一样投身革命;得知当年被退婚的真相和林大钟的身份后,她将长期的等待当作对红梅和林汉卿对自己恩情的报答,放弃了对爱情和婚约的执着。由此,从对婚约的坚持和守护,到对爱情的憧憬和期待,再到投身革命舍弃儿女私情,最后重新认识自己的内心情感,青青从一个封建家庭体系下的妻子、儿媳,一步步蜕变为自由独立的女性、战士,爱情在其心中的地位变迁,正是这种女性自我意识觉醒与发展的昭示。
二、镜与像:女性主体身份确立的历程
《新娘》的爱情与成长两条叙事线索的展开,建立在青青与红梅两个女性角色的人物关系的发展基础之上。剧中设置的这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相似又不同的女性角色,在彼此交融的情感与经历中,建构起相互映衬的女性身份镜像。
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人的自我身份建构可以分为两个过程:在最初的镜像阶段,即大约在婴儿时期,婴儿首次从镜面中看到自己的影像,并把镜中的“他”当成了“我”,从而开始依靠这个外在的他者首次形成自我意识;在之后的镜像阶段,经由无数个“他者”的作用,自我得以被不断确认、充实和完善,镜像与自我合为一体,个体与他者实现统一,最终完成主体自我身份的确立。镜像理论作为女性主体性建构研究的理论依据之一,在此理论视角下的女性,同样经历了对镜中自身的想象和凝视、在镜像和他者的影响下蜕变的各个镜像阶段,其自身的女性意识得以被唤醒,从而产生独立的主体意识。
剧中的青青,初出场时是一个订下指腹为婚婚约的普通乡村姑娘,虽与未婚夫从未谋面,但在心中始终暗暗描绘着一个知书达礼的好郎君形象,憧憬着婚姻生活带来的安稳与幸福。随着婚变后为排解心情和寻找丈夫而加入剧团,青青第一次见到在舞台上演出一曲送郎参军《汶水谣》的红梅,她被“扮了妆的女人好似那仙女下凡,开了嗓的女人好像那百灵婉转”深深吸引。舞台上光彩照人的女演员,正是此时因婚变而产生自我否定的青青望向镜中的渴望:如果自己也能那样美,唱得那样好听,丈夫是否就不会离开?在跟红梅熟识、学戏并随团四处演出后,青青也成为受欢迎的女演员,有了“小彩虹”的艺名。但这时她已不再满足于唱得好听、被观众喜欢,而是“跟你学跟你唱,也要做你这样的人”,想和红梅一样成为一名战士。
“拉康认为,自我的建构离不开自身,也离不开自我的对应物,即来自于镜中自我的影像,自我通过与这个影像的认同而实现。”①刘文:《拉康的镜像理论与自我的建构》,《学术交流》2006 年第7 期。如果说在凝视镜中之像的过程中,青青开始产生了蜕变的渴望,那么在“自我与他者”的关系构建中,这种蜕变则得到了实现。红梅的身份被敌人发现而使其所在的青青家遭到包围,青青为救红梅做出了艰难的抉择,“你为百姓能舍命,我为啥不能舍上房”,烧掉了为等候丈夫而一直保留的新婚洞房,制造突围机会,并只身引开敌人掩护众人。在遥不可及的虚幻爱情的物质象征与生死存亡的现实和大义之间,青青选择了后者。大火不只是烧掉了曾经作为其精神支柱的幻想中的爱情,也使她将自我的认识和价值付诸行动,实现了凤凰涅槃般的蜕变。随着红梅的牺牲,二人的镜像关系被重构。青青化悲愤为力量,继承了红梅的遗志:“要学你临危不惧义凛然,投躯报国染就霜枫一片丹。”青青投身战斗,并与林汉卿在战场相遇,又在战斗后相认。
对再次面对爱情心结的青青来说,红梅与林汉卿的关系仍然是镜中可望而不可及的完美镜像,而林汉卿也因母亲的私自作为伤害了青青而心存愧疚。剧中以红梅幻象的出现,引发人类共通情感与普世价值的传达,弥合了二人以及母亲之间的情感错位与裂隙。在不断地确认、充实和完善过程中,个体一直在试图努力走向镜中的理想镜像。而剧情至此,镜像则走出了镜子,走向一直凝视着它的自我,二者在现实中合二为一,个体与他者实现了统一。于是,青青最终发出了主体自我身份确立的呐喊:“我是青青,我是小彩虹,我还是红梅!”
三、革命叙事内涵探索:生活信仰与人民战争的呈现
革命历史主题的传统呈现以英雄事迹和宏大叙事为主,随着创作的不断深入开掘,越来越多剧作将视线投向多样的人物群体,以多维视角解读英雄主义,赋予革命叙事更生动的表达和别样情怀,《新娘》也在此意义上做出了自己的尝试。
剧作的内容聚焦于抗日战争时期后方普通却不平凡的群众,他们既是农民,又是会演戏的剧团演员,也是能上战场的战士,剧中通过情节设置和细节安排对这一群体的特点进行了充分表现。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商量一起报名进剧团当演员,家人赶来阻止,因为在传统观念里,“家规祖训不可犯,女人哪能进戏班”,而“抛头露面太危险”也是普通百姓在战乱年代信奉的生存规则,但最终还是拗不过女子们“我们要当花木兰”的决心;与孙子相依为命的手艺人锢漏子大爷,知道剧团“干的是大事”,主动为剧团放风瞭哨,有情况就喊起“锯盆锯锅锯大缸——”;剧团排演激励了群众报名参军的节目《锢漏子参军》,则是历史上曾真实演出过的民间鼓词抗日宣传作品。没有激烈的战争场面,而是戏中有戏的展示;不是通过宏大的战场,而是通过普通群众的生活日常展开革命历史主题的叙事。
剧作经由对战争背景下村民生活不同层面的表现,折射出了百姓的淳朴善良,自发参与战斗的气节,以及生动的人物个性。剧中的人物塑造,用富有民间色彩的手法刻画出抗日斗争中的百姓群像。群戏中重点勾勒出的洒脱姑娘菊子和阴柔男旦双喜的欢喜冤家组合,二人夸张的性格反差通过报名参加剧团、伪军盘查等场景制造出诙谐的效果,而在帮红梅脱围的危急时刻,利用二人与平时大相径庭的性格表现反衬出两人感情的深厚和不惧牺牲的豪情。一手导致了青青悲剧的婆婆,对青青隐瞒真相有其惧怕无依无靠的私心,也备受欺骗带来的良心煎熬,既有在面对战乱危险时的软弱和恐惧,也有在危急时刻“救命要紧”的觉悟和挺身掩护家人的勇气。延续香火的传统守旧思想与朴素道德观的善良知理等不同人性侧面,在婆婆这个人物塑造中得到了对立统一的融合呈现。
如此,莱芜梆子《新娘》通过对乡村广大民众的共性与具体角色个性的刻画,使平凡个体闪耀出群体英雄的光芒,彰显出为革命奉献牺牲的普罗大众朴实却崇高的革命信仰。经过生活戏剧化、斗争生活化的叙事方式,对抗日战争特定时代背景下“带枪的老乡剧团”这一特殊群体及其事迹予以呈现,凸显出人民战争的革命历史主题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