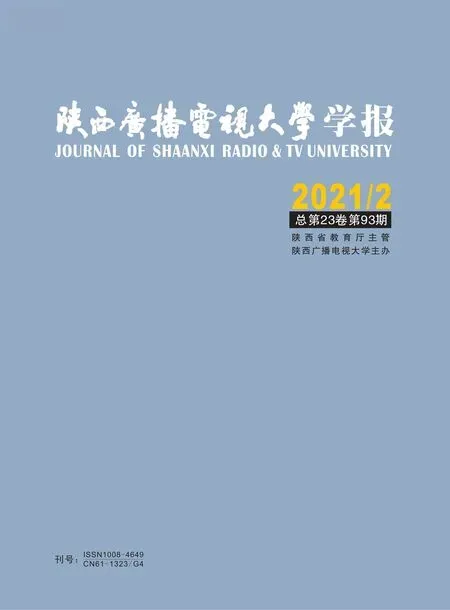论“隐括”在传统戏曲创作中的作用及其文化价值
2021-12-04高晓玲
唐 瑛,高晓玲
(1.西安石油大学 人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065;2.安康市汉滨区教育局,陕西 安康 725000)
“隐括”是传统戏曲创作常用的重要方法,其产生时间由来已久,最早可追至先秦,在中国传统诗词曲赋及小说领域被广泛使用。深入研究“隐括”在戏曲创作中的作用,不仅对研究保护中国传统戏曲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当代戏曲乃至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发展也有重要启示和理论价值。
一、“隐括”在不同文体领域的广泛使用
“隐括”一词最早见于《荀子·大略篇》:“乘舆之轮,太山之木,示诸隐括。”《大戴礼记·卫将军文子》说:“外宽而内直,自设于隐括之中,直己而不直于人,以善存。”从中可见“隐括”的原义指矫揉弯曲竹木,使之平直或成形的工具。在文学批评上,最早使用“隐括”一词的是刘勰,《文心雕龙·熔裁》篇说:“蹊要所司,职在熔裁;隐括情理,矫揉文采也。”这里的“隐括情理”是指矫正情理方面的不当,这是对“隐括”矫正曲木工具原义的引申。在诗歌史上,最早使用“隐括”的是唐代同谷子的《五子之歌》,此作完全是根据《尚书·五子之歌》一篇作品改编而成的,借改编古人诗歌,来寄托自己的悲愤,并以之讽刺当时的政治,已与今天所说的“隐括”意义接近了。词史上有隐括词,确立隐括词体风格的是苏轼,皆因宋代有以诗入词度曲的风气。宋人创作隐括词的直接动机,首先是出于对作品的极端欣赏之情而产生隐括的兴趣。隐括的过程,也就是特殊方式的欣赏过程。隐括词作者通过对名作临摹改编获得与原创者思想感情的共鸣,或者因为前人创作先获我心,故用隐括形式借他们酒杯,浇自己块垒,以之寄托自己的思想情感。[1]中国古代小说史中,史传小说、历史演义小说等也广泛使用隐括手法,四大名著都包含有隐括手法。
戏曲以曲词为蓝本,词为“诗余”,曲为“词余”,戏曲为通俗文艺,又兼小说叙事演义的特色,“隐括”自然成为戏曲的核心创作方法之一了。综观中国戏曲史,在戏曲学中首先用“隐括”这个说法的是元代文学家钟嗣成,其《录鬼簿》评论同时代戏曲家萧德祥“凡古文俱隐括为南曲,街市盛行”,意指改造经典材料入曲,而使之焕发新貌的创作方式。《续编》论庾吉甫,亦有“寻章摘句,腾今换古”之语,评赵公辅有“寻新句,摘旧章”之语,也含有隐括旧篇之意。[1]许多传统戏曲作品的创作更离不开隐括。魏晋时期歌舞戏《踏摇娘》流传到隋唐时期,思想主旨由原本抒发士子悲愤的写怀之作变为具有喜剧性质的民间风情小戏[3],即是“隐括”手法。元人白朴“敷衍”唐人白居易《井底引银瓶》作《裴少俊墙头马上》,改其主旨“止淫奔”为“赞淫奔”,也是“隐括”。汤显祖《牡丹亭》传奇,一般认为取材自明代话本小说《杜丽娘慕色还魂》[4],茅元仪《批点牡丹亭记序》道:“……中有《牡丹亭记》,乃合李仲文、冯孝将儿女、睢阳王、谈生事,而附会之者也……”,也就是说《牡丹亭》传奇的情节构思方式在《搜神记》的故事中便可窥见端倪,而《杜丽娘慕色还魂》则是直接的剧情蓝本,可见《牡丹亭》传奇亦是 “隐括”前人文本而来。除此之外,近代传统戏曲创作,亦不乏“隐括”前人文本而成的传世佳作,如梅兰芳《霸王别姬》(齐如山作)取自昆曲《千金记》,程砚秋《春闺梦》(吴菊痴作)取自唐人王昌龄七绝《闺怨》、陈陶七绝《陇西行》,张君秋《诗文会》(沈凤西作)取自明杂剧《绿牡丹》等等。
二、“隐括”在传统戏曲创作中的重要作用
1.满足作者主体心理与价值取向
隐括者,修改润色,考虑斟酌。[5]在传统戏曲创作中,“隐括”之所以成为重要核心创作手段,在于可以用隐括“寓意于言之所乐”,“取其言之足以寄吾意者,而为之歌,知所以自乐耳”(刘学箕《松江哨遍序》)。当创作未能或者难以出色地表达作者自己的感情时,借重他人作品,抒发自己感情,甚至把隐括作为一种精神寄托,可以达到与古人合一的精神境界,从中得到乐趣,这种乐趣是自己创作所不能代替的。因此可以说,满足作者主体心理与价真取向,是戏曲创作隐括法得以广泛使用的原因及作用。
以汤显祖的戏曲“处女作”《紫箫记》为例,故事取材于唐代蒋防的传奇小说《霍小玉传》,但在主要情节和次要人物上做了较大的改动。根据《紫箫记·开宗》中【凤凰台上忆吹箫】[6]所述的情节,剧本大致还有“李益娶妾”、“尚子毗救友”、“唐公主和亲”等主要情节未完成,但是依然可以根据已完成的半部作品以及《开宗》一出中所交代的故事脉络领会李益的整体形象。汤显祖笔下的李益洗去了《霍小玉传》中轻薄纨绔的特质,从一个负心浪子转为痴情才子,不仅深情,更有胸怀家国的士人君子之志。《紫钗记》传奇系直接根据《紫箫记》传奇改作,此次改作充分显示出汤显祖创作技巧和艺术思想的成熟。相比于《紫箫记》,《紫钗记》传奇则更多地继承了《霍小玉传》的核心情节再加以改编,而此时李益的形象也更加丰富饱满。如果说《紫箫记》传奇中的李益是一个理想化的士人君子,那么《紫钗记》传奇中的李益并不完美,但却更接近于现实:风流而不下流,灵动而不失憨厚,有坚定钟情的一面也有摇摆犹豫的一面。如《堕钗灯影》一出中,李益拾得霍小玉紫玉钗,归还时,向侍女浣纱说道:“请问小玉姐侍者,咱李十郎孤身二十年余,未曾婚聘,自分平生不见此香奁物矣。何幸遇仙月下,拾翠花前?梅者,媒也;燕者,于飞也。便当宝此飞琼,用为媒妁,尊见何如?”[7]一个风流而不失风趣的书生形象顿时跃然纸上。《得鲍成言》一出中,他向鲍四娘阐明“不为淫邪,非贪赀箧,要安顿的定迭”[8],彻底与《霍小玉传》中贪慕姿色和荣华富贵的李益划清了界限。《移参孟门》一出中,卢太尉以李益“不上望京楼”的诗句对他进行要挟,威逼利诱他停妻再娶,而李益便以“已有盟言,不忍相负”[9]八个字说尽了心中的无限柔情,也展示出对爱情的坚定专贞。通过对比可以看出,《霍小玉传》中的李益更接近于“浪子”,而“才子”的光芒也因此被掩盖;而《紫箫记》、《紫钗记》中的李益,则能切实地让人体会并相信“才子”的风度——无论是初见霍小玉时的“雅痞”式调笑,还是后面高中皇榜的事实,以及镇守玉门关时解决边患的非凡谋略和胆识,都足以让读者心向往之。汤显祖作《紫箫记》传奇时,正值青春年少却遭科举失利之际。从《紫箫记》中不难看出一个青年士子的理想与抱负,因此整部作品带有浓厚的文人气质——文本雕琢华美,精于铺陈叙写,情节顺畅平和而少矛盾起伏,李益更像是理想中贤君子的化身。后改作《紫钗记》传奇时,汤显祖已然经历过一段仕途的坎坷,对现实与理想有了更为深切的体悟,因此在新作中少了些许瑰丽动人的文人理想,转而增添了曲折矛盾,李益的形象也走向丰满复杂。如果说《霍小玉传》是讽喻现实之作,《紫箫》、《紫钗》二记则是汤显祖用隐括法借他人酒杯,寄托自己文人理想的写怀之作。
2.文本善于化腐朽为神奇
隐括的创作效果在善于“化用”,其与“袭旧”的本质区别亦在于此。王实甫《西厢记》对董解元《西厢》的“隐括”,不是被动袭用的,而是用自己的风神融透原作之语句,使之统一进自己的风格中。徐复祚亦在具体的曲辞批评中,高度评价了王实甫的“隐括”手段。如论《西厢记·乘夜逾墙》中《驻马听》曲云:“其前四句,与贺方回词不妨并传。而‘不近喧哗’与‘自然幽雅’八字,尤为贺词衬起,妙不可言。”此指《驻马听》“不近喧哗,嫩绿池塘藏睡鸭。自然幽雅,淡黄杨柳带栖鸦”句,隐括贺词《浣溪沙》“淡黄杨柳暗栖鸦”语。王氏将贺词名句嵌入曲辞中,改“暗”为“带”,以自创语与之构成妙对,化中景为近景;而“不近喧哗”、“自然幽雅”的衬入,虚实结合,强化了境界的幽深感。这种化用,使成句变成了自己创化境界的有机组成部分,用其意象而深化其境界,是真正的换骨手。相反,如果只是据实引用,不作改造和熔铸,则被视为缺陷。[10]
3.实现传统戏曲“娱乐”与“教化”的文化价值
戏曲的繁荣离不开商品经济的发展与市民阶层的兴起,作为生长于市井闾里的通俗艺术,最重要的一点便是顺乎人情世道,不避浅易通俗。但是,中国文化的本质是“士君子”的文化,是极其重视身份与格调的“雅文化”,而中国文学的最高宗旨却是修养自持、关怀寄托,这直接影响到戏曲文学的发展,使得有元一代投身戏曲创作的文人不自觉地将这种“雅文化”的理念和取向倾注其中,于是有了寄托感慨、讽喻现实的写怀之作,甚至由元杂剧沾溉明清两朝戏文传奇。戏曲至明清两代,有传奇风行于世。明清传奇以篇幅宏大、风采瑰丽著称,亦多有文人书写感怀、梦幻之作,在漂浮的时代中勾勒了一片理想的境界,为世人提供了一份心灵的慰藉,假南曲诸腔(主要是崑腔)之力兴盛数百年。
传统戏曲创作以“隐括”为主要手段,以宣扬普世的人伦道德与价值观念为核心取向。汤显祖以《霍小玉传》为蓝本,改作《紫箫》、《紫钗》二记,固然倾注了个人理想与艺术追求,两部传奇虽有对情节和人物形象的大量改动、丰富,却并非对于传统价值观念的反动和颠覆,而是创造性继承。京剧大师荀慧生先生曾经谈到改编传统文学作品的基本原则:“创制者。因剧本新成,声必重谱,凡古典名著优美作品,为保存文学之完整,求与音律之适合,如《钗头凤》词、《还珠吟》古乐府,按宫协商,浅歌低咏,往往废寝忘食,俾画作夜研究,必有所得而后已。继续演作,屡谱新声者十余年不稍辍。”[11]这是一代艺术大师的卓越见识。
三、对当代戏曲文化的启示
俞平伯先生曾对昆曲的研究与保存问题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今日而欲言保存研究,如何而可乎?曰无他,先存伶工之传耳。欲言复古,则古不可复也,亦不必全复;欲昌明之于来世,则吾未见来世有可以昌明之道也。但卑而勿高,但述而不作,曰存今而已。就今日之可存者存之而已。今既存,则以之规往可也,以之开来亦无不可,提倡即在保存之中,非保存之外别有所谓提倡也。”[12]俞先生此论,启示我们对传统文化应该坚持的正确态度是:继承先于创造,拟古亦是创新。
前辈的陈墨香、李释戡、齐如山等杰出的剧作家何以成功,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一辈大师均是古典文学底蕴深厚的卓越学人,他们所有的创作均是本乎传统而后合于当世。所谓“继承先于创造”,道理有三:其一,“君子务本,本立道生”[13]。继承必要恪守本分,心怀诚敬地继承前人所创并留传于当世的佳作,能够百年传承始终颠扑不破的作品自然是真正的瑰宝,从这些佳作中不难求得前人精妙高深的见识与手段。无论是创作者还是演员,忠实继承都是对基本功的训练和巩固。其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古人的教育是浸润式的培养,是人生与文化、艺术交融合一的化育。继承艺术传统的同时继承文化传统,这是对于人格心性的修炼,在古雅庄重的文化艺术的化育中领会其要旨与真谛所在,便不致为浮光掠影的俗浅文化所惑。其三,如俞平伯先生所说“今既存,则以之规往可也,以之开来亦无不可”,在如今这个大雅衰落、斯文不作的时代,为后人和历史保留下些许古雅元音是当世人对文化的责任。盲目“创新”与“颠覆”无异于饮鸩止渴,存其精华、留其三昧是涵养体贴之道,唯有如此才能令戏曲文化在飞速发展的经济社会中存留一线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