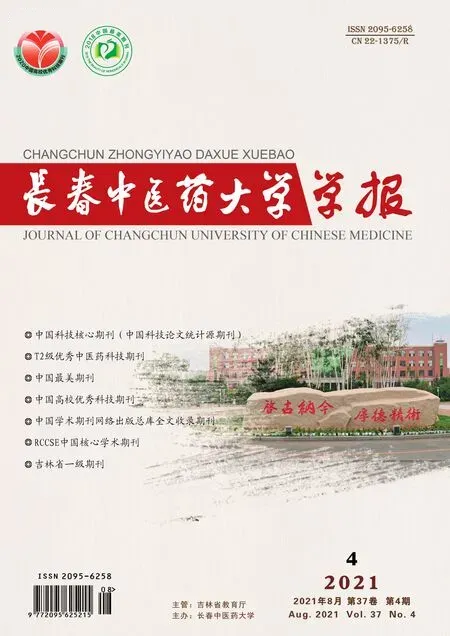《景岳全书》论治痢疾
2021-12-04周天羽张文星
张 威,周天羽*,张文星
(1.辽宁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肛肠科,沈阳 110032;2.辽宁中医药大学研究生学院,沈阳 110847)
痢疾,即《黄帝内经》中之肠澼,因其闭滞不利,又被称为滞下,临床表现以腹痛、里急后重、脓血便为主。与溃疡性结肠炎(UC)表现相似,故溃疡性结肠炎可以从痢疾的角度论治。目前,西医学认为UC的发病机制不明确,故治疗效果不佳,并被列入世界难治疾病[1],但中医药对于UC的治疗有着独特的优势,有很大的发展前景[2-3]。《景岳全书》是明代医家张介宾(公元1563—1640年)所著,承《黄帝内经》之精要,集各家学说之精华,兼及毕生之经验[4]。该著作中设有痢疾专篇,分别从病因病机、辨证以及治疗等多个方面对痢疾这一疾病进行了详尽阐述,在中医治疗痢疾方面有较深造诣与研究,为后世医家所推崇。现对《景岳全书》痢疾篇的学术观点与方药特点进行探析,整理出该著作对于痢疾的认识。
1 《景岳全书》对痢疾病因病机的认识
1.1 痢因人事食寒,并非天时暑热
《素问·太阴阳明论》云“食饮不节,起居不时者,阴受之,阴受之则入五脏,入五脏则(月真)满闭塞,下为飧泄,久为肠澼。”指出了痢疾发生与饮食生活习惯有着密切关系。“痢疾之病,多病于夏秋之交,古法相传……此其病在寒邪,不在暑热,病在人事,不在天时,从可知矣”[5],开篇张介宾就借当时医家普遍观点引出自己观点,即当时医家普遍认为夏秋相交之季,暑热之邪盛行,炎热酷暑之毒邪蓄久而发为痢疾。张介宾则认为不然,天气炎热而过食生冷,从而导致本病的发生。虽经盛夏不犯寒凉之品者,则很难患及痢疾,由此可见,本病的发生并非单独暑热之邪所致。因此,张介宾提出,痢疾发生并非天时暑热之邪为患,而是人事贪食寒凉之物所生。
1.2 邪气盛为标,正虚为本,阳盛则成湿热
“但胃气强实者,虽日用水果之类,而阳气能胜,故不致疾……则随犯随病,不必伏寒,亦不必待时,尤为易见”[5],书中提到正邪与痢疾发生的关系。若胃气强实,用寒凉之品而阳气能胜,则不发病;若正气稍弱,阴邪内伏,伺虚而动,而七至八月间为阳消阴长之时,寒湿之邪易伤及脾胃;若平素脾胃虚弱,则食寒即发,邪不必伏即发病。痢疾为本虚标实之证,标为寒邪而非暑热,本为脾胃虚弱,又根据正邪的关系划分为感邪即发(正不胜邪)、伏发(正邪相峙)与不发(正能抗邪)。张介宾分别从邪气与正气两个角度分别论述了痢疾的病因病机,批判性地指出,当时医家只见夏令暑热之邪,而不见病人之脏寒,强调“口不受寒,痢何以得”。另外,也指出,有少部分人脾胃功能强盛,正气充足,可使寒湿之邪转化为湿热,故用寒凉或通利之法,使得全篇论述准确而全面。
2 重视辨证与辨症相结合
痢疾辨证的根本在于辨清寒热虚实,又根据其具体表现不同,采用不同的治法。本病的病位在脾胃,与肾关系密切,总属本虚标实之证,以脾肾阳虚为本,以火热、寒湿之邪为标。
2.1 辨脓——审正气足与不足
“凡腹中积聚之辨,乃以饮食之滞……而尚敢云攻之逐之,或用苦寒以滑之利之者否”[5]。景岳认为,痢疾便下的脓垢为脏腑的膏脂,其本质是精血,无论胖瘦均有,胖人多而瘦人少。患痢疾之后,脾胃受损,膏脂不固,随大便而下,若正气充足,则随去随生;若脏气衰败,膏脂丢失殆尽而无以生,或久泄久痢,下痢血而无脓,均为危急之象,而非邪去正安之征象。
2.2 辨腹痛——断实热与虚寒
“凡泻痢腹痛,有实热者,有虚寒者……则痛当自止,此不必治其痛我也”[5]。腹痛的病机多为实热或虚寒。实热者多责之于食积与火热所致。食积者,见腹胀满而坚硬,痛而拒按,治则轻者宜行气导滞,重者宜通利导泻;火邪所致者,见内热之象,治宜清热泻火。并且作者提出“邪实于中者,必多气逆”,因此,在治疗上都应以佐以行气之法。虚寒证在本病中更为常见,多责之于外感寒邪与过食生冷两种外因,伤及中阳或元气不足,证见喜温喜按,但胀满而不坚,无热象等表现,治宜速用温补脾肾之法,使脾肾暖,则痛自安,因此不必治其痛。作者还提出,若痛甚者,温阳药中应少佐木香以行气,当归以和血,待痛减后去木香,予当归以防耗气、滑肠;若寒在下焦肾,应加吴茱萸以暖肾止痛。
2.3 辨里急后重——辨气之寒热虚陷
“凡里急后重者,病在广肠最下之处……故凡欲治此者,但当以治痢为主”[5]。里急后重即虽欲出而无所出,无所出而又似欲出,因此其并非食积等有形实邪所致,而是无形之气使然。热邪、寒邪与脾肾气虚均会导致本症的发生,故治疗上应分清寒热,并重视“气”在本症中的重要性。刘完素云“调气则后重自除”,故本症应用调气之法治之:气寒者应以温调,气热者应以凉调,气虚者应用补调,气陷者应以举陷而调,使气得以和,本症得以愈。而不可用行血散气之法,如木香、槟榔、大黄一类,以防耗伤中焦之气。
2.4 辨口渴——审阴液伤与未伤
“凡痢疾之证,必多口渴……使能不治其渴而治其所以渴,又何渴之有”[5]。口渴者可分为真渴与似渴,真渴乃为火热之邪伤及阴液所致,治宜清热;干渴则是阴不足不能荣于口所致,故治宜滋阴。根据寒热的强弱关系又可具体分为:渴而欲冷饮,为火热之邪伤及中焦脾胃,耗伤阴液所致,治宜用清热之法;口热渴欲饮水而不多饮,为阴液亏虚,不能上盛于口所致,而并非火热之邪,因此治宜滋阴生津;口干渴喜凉而饮后不喜凉,为中焦有寒,上焦有热,属寒热错杂之证,故治疗上宜温养脾胃少佐以清利上焦之法。此外,作者还强调了补脾益气在此症中的重要作用。一者,气能生津,气虚则水无以生;二者,土能制水,脾土虚则不能制水,导致水液不固。因此,口渴者不能仅用清热与滋阴之法,应当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即“不治其渴而治其所以渴”。
2.5 辨小便——查热与非热
“凡泻痢之证,小水必多不利……余则不知其何谓。可恨,可恨”[5]。本症分为真热与非热两方面原因所致。若是真热所致者,则见上下皆有热象,小便热赤,或淋漓涩痛,或尿血,治宜清热泻火。非热所致又可分为四个方面:1)中寒逼阳于下,则见上寒下热之象;2)泻痢亡阴津亏,则见阴液不足,甚者亡阴之象;3)肾阳不足不能运化尿液,则见肾阳虚衰之象;4)妄用渗利之品伤及血分,则见阴亏至极伴有血虚之象。因此,非热所致者总属亡阴之证,应补以真阴。
3 病程不同治疗方法不同
3.1 痢疾前期
张氏认为本病前期多由于饮食伤于脾胃所致,根据正气强弱,治疗方法及预后也不相同。“生冷初伤,饮食失调……略祛寒滞,愈之极易”[5]。若过食生冷,初感寒湿之邪,正气充足而未衰,即正盛邪实,症见腹痛腹胀、暴泻暴痢,治宜祛寒除湿,若寒邪盛者,应用热法,方用抑扶煎或五德丸。若湿邪盛者,应用和法,方用平胃散、五苓散或胃苓汤。“脾胃虚弱之辈,但犯生冷……或五德丸、四神丸之类,俱可间用”[5]。平素脾胃虚弱,又过食生冷,即正虚邪实,若无实热之象,治宜温补脾气,应用热法,方用佐关煎。“痢疾初作,气禀尚强……多致不可解救,最当慎也”[5]。饮食积滞引起痢疾发生,症见腹坚满而胀痛,形体与脉象俱实者,治宜泻下导滞,通因通用,方用大承气汤、神佑丸、百顺丸。张氏在治疗本病前期多用茯苓、厚朴、陈皮、肉桂、干姜等中药温中行气健脾。现代研究认为,厚朴主要成分为厚朴酚、和厚朴酚,均具有抗溃疡、抗氧化、抗炎等作用,对实验性UC大鼠具有免疫调节作用[6]。代谢组学研究发现,陈皮通过调节腹泻大鼠体内的酮体及丁酸代谢,从而改善腹泻引起的能量物质的代谢[7]。肉桂的主要活性成分肉桂醛,具有消炎抗菌作用,研究表明其能够抑制dectin-1/TLRs/NF-κB的免疫炎症信号通路,减轻结肠黏膜损伤,从而对UC产生治疗作用。通过统计学研究古今医家治疗UC的用药规律,分析结果发现干姜为最常用药物之一[8]。因此,应用张氏理论治疗本病前期能够取得良好疗效。
3.2 痢疾期
痢疾期张氏针对呕吐、便血、发热等不同症状辨症施治。“痢疾呕恶,兀兀欲吐……宜大分清饮、益元散之类主之”[5]。若胃气虚寒而致痢疾伴恶心呕吐者,治宜温补安胃,方用五君子煎、六味异功煎、温胃饮或圣术散,若呕吐严重,阳气欲脱者,治以六味回阳饮。若肾阳不足,气不归原而致呕吐者,治以胃关煎或理阴煎。若胃火上逆而致呕吐,伴烦热胀满等症者,治宜清热泻火,降逆止呕,方用大分清饮或益元散。“湿热邪盛,而烦热喜冷……若数剂不效,便当思顾脾肾矣”[5]。痢疾湿热邪盛,症见便鲜血,烦热喜冷,腹胀满而脉实者,治宜清利湿热,湿盛者,方用清流饮、黄芩芍药汤、香连丸或河间芍药汤;热盛者,方用大分清饮或茵陈饮。“痢有发热者,似乎属火……必宜胃关煎及右归丸之属主之”[5]。发热者本为热证,但其本质为虚热,痢疾过下而伤及精血,阴虚血亏,则见发热而躁动。若阴虚兼有实火,脉尚且有力者,治以加减一阴煎、保阴煎。若仅为阴虚火旺,脉虚而无力者,治宜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方用三阴煎、六味丸或八味丸。若阴盛格阳,四肢发热而躯干发凉者,治宜热因热用,方用胃关煎或右归丸。
在治疗痢疾便血时,张氏多用黄芩、黄连、木香、芍药等清热之品,其治疗的作用机制可能与抑制IL-17、PI3K/AKT信号通路等有关[9]。现代药理学发现,黄芩-木香通过降低血清中促炎因子的表达,增加机体抗氧化作用,恢复肠道黏膜功能,从而治疗本病[10]。黄连中的黄连总生物碱能够激活PPARγ、抑制p38MAPK与NF-κB信号通路,从而缓解结肠组织炎症损伤,促进结肠黏膜修复[11]。张氏认为,痢疾发热多为阴血亏虚所致,故常用生地黄、熟地黄、芍药、当归等滋阴养血之品治疗。现代研究发现,地黄有止血、促进造血细胞、增加细胞免疫功能、促进网状内皮系统的吞噬功能等作用[12],白芍能够收缩结肠平滑肌,促进结肠运动,具有止泻、抗溃疡、抗炎等药理作用[13]。当归具有抗炎、镇痛、改善血液循环等作用[14],其配伍白芍可能作用于HIF-1、TNF、NF-κB等信号通路治疗溃疡性结肠炎[15]。
3.3 痢疾后期
“病痢,凡脾肾俱虚而危剧可畏者……或兼用四维散、九炁丹、复阳丹,庶可保全也”[5]。痢疾后期,脾肾两虚。若以脾虚为主者,治宜先用胃关煎,再用温胃饮。若以肾虚为主者,用四维散、九炁丹或复阳丹。“久痢阳虚,或因攻击、寒凉太过……庶或有可望生者”[5]。痢疾日久或误用寒凉之法太过,导致脾肾阳衰,大便滑脱不固,则虚而不受补,宜回阳救急,灸百会、气海、天枢、神阙等穴位。
现代医家认为多用人参、附子、干姜、甘草等回阳救逆之品治疗本病后期及本病的重症。现代研究发现,人参中所含的人参皂苷Rg3能够通过下调TNF-α、IL-6,上调IL-10水平,调节Th1/Th2平衡,抑制NF-κB活化,调节肠道免疫,促进肠道粘膜的修复[16]。附子中的乌头碱成分具有免疫调节、抗炎、镇痛等作用[17],从而在溃疡性结肠炎中发挥作用[18]。干姜中的姜酚类化合物有明显镇痛、抗炎、抗溃疡等作用[19],甘草中的复方甘草酸苷能够阻断Toll样受体介导的核因子-κB信号通路中的TLR与NF-κB p65的表达,从而治疗本病[20]。此外,研究表明灸法通过经络使中药从腧穴直达病所,能够缓解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临床症状及大肠黏膜病变,改善细胞因子水平[21]。
4 小结
《景岳全书》是明代时期中医学的一大理论成果,详细阐述了痢疾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治疗方法。作者在文中多次借用丹溪等他人的观点,批判性地指出本病的发生并非都是热证,反而以虚寒证更为多见,通过论述正气与邪气的关系,清晰地阐明了本病的发生机制,认为本病是本虚标实之证的观点一直沿用至今,并强调了在本病的的辨证过程中尤其重视分清虚实与寒热。治疗上按照疾病的发生发展阶段分为痢疾早期、痢疾期与痢疾后期进行论治。《景岳全书》是中医学发展史上新的里程碑,为中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为后世医家进行研究治疗本病提供了一定价值的参考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