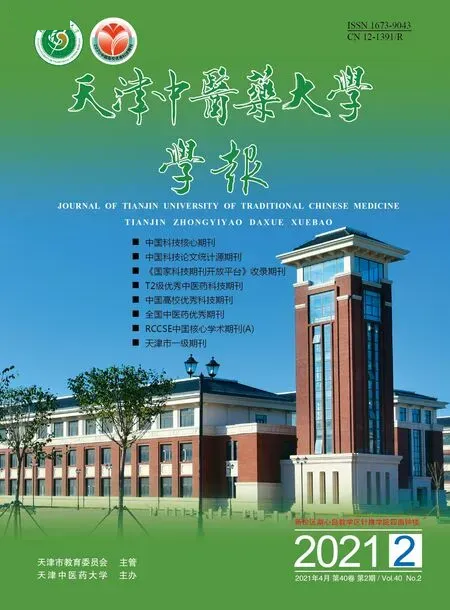王树槐教授辨治荨麻疹临证思路*
2021-12-04何禹哲朱虹陈帅
何禹哲,朱虹,陈帅
(1.扬州大学医学院,扬州 225009;2.扬州市中医院,扬州 225009;3.江苏省苏北人民医院中医内科,扬州 225001)
荨麻疹是由于皮肤、黏膜小血管扩张及渗透性增加而出现的一种局限性水肿反应[1],以鲜红或苍白色大小不等、发作部位不固定的风团,疹起与疹退均迅速,疹退后皮肤不遗留痕迹为主要特点[2],影响患者生活、工作。现代医学一般将其分为急性荨麻疹、慢性荨麻疹。其属中医“瘾疹”“风疹块”等疾病范畴。
王树槐主任中医师,曾任扬州大学医学院院长、江苏省中医药学会常务理事、扬州市中医学会秘书长等职,业医五十载,医术精湛,学验俱丰,尤其擅长治疗各类皮肤疾病。王教授强调,临证当注重病机分析,辨证论治,崇徐灵胎“药有个性之专长,方有合群之妙用”之说,不拘泥于一方一药,圆机活法,巧妙论治。笔者有幸侍诊于前,获益良多,现将其辨治荨麻疹临证思路介绍如下。
1 急性荨麻疹
急性荨麻疹以起病急骤、全身泛发的红斑或风团、持续数分钟至数小时、一般24 h内可自然消退、退后不留痕迹为临床特点[3],通常其病程少于6周。临床多单以风邪或兼夹寒、热、湿、搔抓为外因。究其内因,发生急性荨麻疹者多属过敏体质,中医体质学说中称之为特禀质,是先天禀赋不足和禀赋遗传等因素导致的一种特殊体质,临床上因过敏体质而发病的患者表现为个体生理功能与机体自我调节的能力低下,反应性增强[4]。王教授认为,因肾藏先天之精,对于此类先天禀赋不足之特禀质,可从鼓舞肾气、通行肾阳的角度用药治疗。根据中医理论,若先天之精不足,元气匮乏,无以化生充足之正气以充斥形体官窍而易病,客邪喜犯虚体。风邪袭表,或兼夹寒、热、湿邪与卫气相搏、阻塞玄府;或搔抓刺激,腠理闭塞,肤表肌腠不得畅达而生皮疹,故有以受风过盛而发者,有以受寒受热而发者,有以反复搔抓而发者,有以药物食物过敏而发者,究其根本为肾阳郁内,正气不通,肤表肌腠失调。
王教授综合本病的发生机制认为风邪是致病的首要因素,选用陈实功《外科正宗·卷四》之消风散为基础方加减。该方主要用于治疗疥疮、瘾疹等,广为皮肤科临床所用[5]。中药组成包括荆芥、防风、牛蒡子、石膏、当归、生地、蝉蜕、知母、苦参、苍术、胡麻各一钱,木通、甘草各五分[6]。王教授首创“三通消疹法”治疗急性荨麻疹,该法包括疏散风邪,通畅肤表;祛邪解肌,通达腠理;温经活络,通行肾阳。临证用药,取原方中荆芥、防风辛温走散之意,祛风透疹以通表。外邪多与风兼夹而闭塞腠理,夹寒者加麻黄、桂枝、细辛以助辛温解肌散寒,并取细辛芳香透达之性通达腠理,亦有现代药理研究表明细辛所含成分具有抗变态反应的作用[7];夹热者加用有“疮家圣药”之称的连翘,疏散风热,消肿散结;夹湿者配用土茯苓、白鲜皮、地肤子祛风除湿,燥湿止痒。临证亦常加用淡附片温肾助阳,配合桂枝取《金匮要略》肾气丸“少火生气”之意,鼓舞肾气以通行肾阳,兼以温通经脉,经脉通则经络活,肾阳畅则正气通达,邪不可干。诸药相伍,治疗急性荨麻疹效捷。
2 慢性荨麻疹
皮疹反复发作经久难愈,病程长达6周以上者为慢性荨麻疹。症见红色或苍白色大小不等的风团,时多时少,或见片状病灶、皮肤水肿,持续时间不超过24 h[8]。
2.1 以调和营卫为基本大法,予调营实卫法缓消皮疹 皮肤为经络散布之处,以气血为媒介,内传脏腑,外输肌肤毛窍,故与气血、五脏六腑皆有关联。王教授认为慢性荨麻疹发病的基本机制是因营卫不和而致。营主血脉、卫主肌表,营属阴、卫属阳,在生理功能上有着互相协同的作用,营在内卫之守也,卫在外营之使也。慢性荨麻疹多为机体营血不调,卫外不固,若加以外邪侵袭,营卫相互搏结,则皮疹反复发作,加之患者卫表亏虚,无以御邪,风、寒、热、湿等邪气皆可趁虚而入,故以调和营卫为基本大法,攘外必先安内,调营血以助卫表和,实卫气以助卫表更实。
王教授临证每从调和营卫为基本治法入手,辅以固表实卫之法,能有效缓解慢性荨麻疹发作频次。桂枝麻黄各半汤由桂枝汤和麻黄汤组成,王教授认为此方取桂枝汤之调和营卫配合麻黄汤之发汗解表,一内一外,相辅相成。《本草求真》记载:“桂枝以调其营,营调则卫气自和。”该方原用于太阳病迁延日久,患者未能发汗排出病邪,病邪郁遏于肌表,欲出不能,欲入未可,宣泄无力,由于太阳表邪不解,阳气拂郁不伸,遂导致皮肤病的发生[9],故以该方微助发汗,汗后疹除。《素问·五藏生成》记载:“肺之合皮也,其荣毛也。”卫气行于脉外,故取麻黄宣肺之效,助卫气通行腠理至肤表之间以卫外。《本草新编》记载:“桂枝乃发汗之药也,有汗宜止,无汗宜发,此必然之理也。”可见桂枝一可温通经脉以助气津血液输布有序,二可防麻黄发汗太过以伤其营。王教授据《素问·痹论》“卫者,水谷之悍气也”得出“治过敏者,勿忘实脾,因水谷之精来源于脾之运化,故脾气充则卫气实”。故常加用玉屏风散以益气健脾实卫气。方中黄芪性甘温,为补益脾气之要药也,白术亦健脾益气,防风祛风解表,因其性辛散走表,故可袪肤表之风团。诸药合用,缓消皮疹,明显改善慢性荨麻疹患者的症状,降低复发率。
2.2 皮疹缠绵多因肝脾失调,以缓肝健脾法使肌肤调柔 王教授认为,荨麻疹反复发作,日久不愈,多为肝脾失调,内湿为患,如《素问·至真要大论》记载:“诸湿肿满,皆属于脾。”脾虚生湿,水湿停滞皮肤则生水肿样皮疹。《金匮要略》记载:“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反之亦然,见脾之病,多因肝犯,怒伤肝、思伤脾,临床多见因心烦易怒、忧思多虑而致肝脾不调证。脾受肝火灼伤,失去荣养则运化乏力酿生湿邪;肝郁则气机不利,气滞则湿聚,湿阻肌肤腠理而不得发,萌生皮疹。肝藏血、脾统血,若肝脾失调,则血不安于脉内,浸润肌肤,亦可出现淤青色色素沉着。
若患者皮疹缠绵不愈伴见心烦易怒、舌质红、脉弦数等症,王教授认为其多与患者平素情志不畅、精神压力大而致肝火炽盛证、肝火犯脾证,肝火内扰,气机郁而不行,肝犯脾,脾转运失责则生湿,故见皮肤风团肿块。王教授临证常取明·薛己《内科摘要》中的丹栀逍遥散之意以调肝理脾。王教授指出:“肝火清、肝气顺则缓,缓肝勿忘健脾。”故又自拟丹栀逍遥散之变方,加夏枯草去柴胡以加强清泻肝火之力,伍以香附疏肝气;加用太子参,合原方中白术、茯苓、甘草为四君子汤以健脾益气;同时加辛苦寒之赤芍,合原方中酸苦寒之白芍,辛酸同用以达凉血不耗血,活血不动血之意。王教授临证善加药对,据《本草纲目》对紫花地丁的记载:“治一切痈疽发背,疔疮瘰疬,无名肿毒恶疮。”对于疹色鲜红的患者,王教授认为其病机为热毒郁结,血脉不利,血停湿聚,发为皮疹,故以紫花地丁与“疮家圣药”之连翘为药对,共助清热解毒、消肿散结。诸药相伍,有效缓解荨麻疹患者病程缠绵之苦。
2.3 内通则外解,浊祛则肤泽 《素问·皮部论》云:“百病之始生也,必先于皮毛,邪中之则腠理开,开则入客于络脉,留而不去,传入于经,留而不去,传入于腑,廪于肠胃。”阐述了病邪由皮毛至肠胃的过程。王教授认为,若患者肠胃积滞、尿液潴留,机体产生的秽浊不能正常地排出体外,浊气必会反蒸于皮毛。故临证王教授较多关注患者二便情况,若患者二便不调,秽浊可由肠胃、膀胱循经传至周身血脉、肌表,浊气可阻滞血脉并蒸腾于外,与卫气相搏发为皮疹。
王教授提出:“气血不通则浊难行。”临证之中,王教授以“通”字为立法,巧妙运用通便、利尿、祛湿、活血行气之诸通疗法,取《丹溪心法》卷三之越鞠丸为基础方,随证加减。若见腹胀、排便困难者,其乃肠胃气滞,水谷糟粕难排,加用《儒门事亲》卷十二之木香槟榔丸中君药木香、槟榔行气消积导滞,因其皆归胃、大肠经,有“调气则后重自除”之意,通行肠胃之气以行气消痞,缓泻通便,腹胀自除;若见舌苔厚腻、湿邪困重、或小便不利者,方加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之五苓散,驱除体内秽浊。王教授认为,对于慢性荨麻疹患者,多为外湿内湿合而为病。《伤寒论·辨太阳病脉证并治中》记载:“治太阳病发汗后,大汗出,胃中干,烦躁不得眠,渴欲饮水,少少与之,令胃气和则愈。若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五苓散主之。”患者脉浮提示表证仍在,伴见小便不利、消渴,表明里证并存,故选五苓散以表里双解[10]。若不见表证者,王教授则将原方中桂枝改用肉桂,以振奋脾阳,加强祛湿之力,宗“治湿不利小便,非其治也”,配入清热利尿通淋之车前子以祛湿邪于小便之中。诸药合用,共奏浊祛则肤泽之功。
2.4 阳气内闭束邪不出,升阳温阳合法畅达肌表 临证见某些慢性荨麻疹迁延多年不愈的患者,其人形体健壮或适中,常自觉肘膝关节以下冰凉,舌质红苔薄白,脉弦数。王教授认为,此类患者乃阳气闭塞,顽邪郁固其内。卫气贯通皮肤肌腠,阳气升发则卫气得以输布,卫气得阳气之温煦,便可奋起抗邪,邪气受阳气之升发便可被驱逐于外,邪祛则皮肤肌腠得以通畅,故可使皮疹平复。
王教授临证总结出“若要卫气充,需加阳气以助之”的经验要诀,以具升阳、温阳功效的中药,如黄芪、葛根、升麻、附子,组成“升阳温阳合剂”。其中葛根、升麻有透疹之效,黄芪有托毒之功,故三者皆有使病邪向肤外通透之意,相得益彰。附子归心脾肾经,其性大热,温上、中、下三焦之阳以助卫气贯通全身。因葛根、升麻、附子药性属辛,能散能行,卫气得以布散,气血得以通行,皮疹即可消散。
3 典型病案
患者女性,32岁。2018年4月5日初诊。患者因“皮肤反复发热出疹5年,加重1个月余”就诊。患者自述初起可见皮肤发热后泛发风团,半月一发,发无定处,瘙痒不甚,数小时内即可消退,近期症状加重,3~5 d周身皮肤发热后出现风团一次,瘙痒难忍,持续1 d,疹退处见紫色色素沉着,服用抗过敏药效果不佳。皮肤检查:可见风团有鲜红色或暗红色,大小不一,瘙痒,无压痛,疹退处见暗斑。刻下:前臂、颈部泛发风团,瘙痒不适,烦躁,胸闷,纳差,来月经前乳房有胀感,经量少,睡眠尚可,便溏,每日2次,舌质红,苔白腻,脉弦。中医诊断:瘾疹。辨证:肝火犯脾。治法:缓肝健脾祛湿,行气调血和营。处方:牡丹皮10 g,栀子10 g,夏枯草10 g,当归10 g,赤芍 10 g,白芍 10 g,太子参 15 g,白术 10 g,茯苓 10 g,川芎 10 g,香附 10 g,麻黄 6 g,桂枝 10 g,连翘 10 g,紫草 15 g,地肤子 15 g,苦参 10 g,甘草6 g,每日1剂,早晚水煎服,连服7剂。
拟方分析:患者病程长达5年之久,因湿性缠绵,考虑湿邪作祟。问平时生活状态得知患者性情急躁、易发火,得出肝气郁而化火,肝火内扰,肝气乘脾,脾失运化,症见纳差、便溏;肝脾不调,气血不畅,营卫不和则见疹出鲜红,肝火灼伤血络可见色素沉着。故以王教授自拟的缓肝健脾祛湿,行气调血和营之丹栀逍遥散变方治疗,方中牡丹皮、栀子、夏枯草肝血同清;取香附疏肝之效合夏枯草清肝之功共奏疏肝气、清肝火,肝得缓;太子参、白术、茯苓、甘草合为四君子汤,补气健脾祛湿;牡丹皮、栀子、赤芍清热凉血,配合川芎、当归活血之效,血热得降,血行得畅,血自调;前药皆为调和营血、卫气做铺垫;另取辛温行卫表之麻黄宣提卫气,配合通脉、养血之桂枝、白芍调和营血,营血、卫气一走肤内,一行肤表,相互羁绊,营血调则卫气和;方中亦加入连翘、紫草、地肤子、苦参以清热解毒消肿、凉血消斑、祛湿止痒共治其标。
2诊:患者自觉瘙痒较前好转,风团1 d内可消退,半月一发,皮肤检查示风团淡红,较前减小,胸闷较前好转,无便溏,舌质红苔薄腻,脉弦。前方去夏枯草、川芎、香附、连翘、紫草、地肤子,加防风、柴胡,继续予以7剂。
拟方分析:患者自述胸闷较前好转,因肝经循行胸部经脉,乃知肝经郁火得以消减,又因患者诉无便溏,得知肝气犯脾得以改善,脾健运袪湿则无便溏,遂袪夏枯草、川芎、香附,加柴胡专以疏肝解郁;因患者风团减小,色泽淡红,可知原方清热消肿,凉血消斑之药奏效,故去连翘、赤芍、紫草;因患者诉瘙痒较前好转,又见舌苔薄腻,可知其体内湿邪已消其大半,故以原方中地肤子易防风,减轻祛湿止痒之力,增强祛风止痒之功。
3诊:患者诉效果明显,两月一发,发时少许痒感,月经正常,睡眠可,二便调,皮肤检查正常,舌质淡红,苔薄白,脉弦。2诊方去赤芍、苦参,加黄芪。7剂巩固治疗,后随访患者,半年未起风团。
拟方分析:因患者皮肤正常,又见其舌质淡红、薄白苔,可知血热已消、湿邪已袪,故袪方中赤芍、苦参以停用清热凉血燥湿之药;因患者诉瘙痒进一步减轻,故加入黄芪,与前方中之防风合为“玉屏风散”,补气固表以实卫气,卫气实则邪不可干,痒症可除。
4 结语
荨麻疹病因繁多,病机复杂,症状不尽相同,现代医学治疗主要采用抗组胺、皮质类固醇激素等药物治疗,虽可缓解症状,但复发率高,降低患者免疫功能。王老师从整体出发,辨证论治,注重病机分析,彰显中医药个性化治疗的特色,根据患者病情变化,灵活运用中药药对,其理法方药独出心裁,给予我辈后学以启迪。同时,王老师尤重对患者摄生指导,药物治疗与非药物治疗相辅相成,每获良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