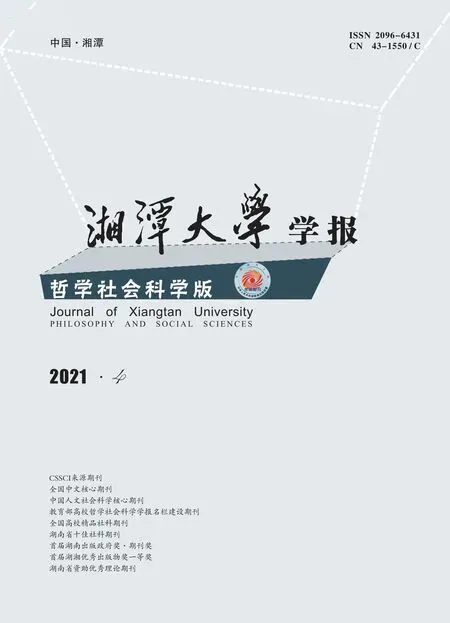自然之债的起源与价值*
——以罗马法文本片段分析为中心
2021-12-03睢苏婕
睢苏婕
(湘潭大学 法学院,湖南 湘潭 411105)
我国《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第26条规定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未超过年利率24%,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约定的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借贷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年利率36%,超过部分的利息约定无效。借款人请求出借人返还已支付的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31条又规定没有约定利息但借款人自愿支付,或者超过约定的利率自愿支付利息或违约金,且没有损害国家、集体和第三人利益,借款人又以不当得利为由要求出借人返还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借款人要求返还超过年利率36%部分的利息除外。利息计算包含“两线三区”,即,利率 0%-24%(法律保护区)、36%以上(无效利率区),而利率介于24%-36%则在学理上被称为自然之债,该部分利率一旦支付不得要求返还[1]45。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针对上述内容修改为出借人请求借款人按照合同约定利率支付利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但是双方约定的利率超过合同成立时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四倍的除外。这一重大修改不再按照“两线三区”的划分来对待民间借贷利率,而是通过4倍LPR利率的界限将民间借贷利率直接分割为0%-4倍LPR利率(法律保护区)与4倍LPR利率以上(无效利率区),此种改变直接导致民间借贷自然之债在我国司法实践的消失。此种变化,到底是司法裁判标准紧跟社会市场变化的体现,还是司法解释对私法自治领域的肆意扩张,这不禁再次引发对自然之债的概念及其功能的讨论,本文拟从罗马法文本入手,对自然之债的起源及其本质展开讨论。
一、自然之债的起源争议
研究自然之债首先需要正本清源。古罗马法学家盖尤斯曾说:起源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这句话既展现法的延续性又被称为法的体系性发展的思想宣言。只有明确了自然之债是什么,从哪里来,才能更好地比较自然之债及其相关概念的联系,更好地理解自然之债在我国实证法中的具体体现。
关于自然之债起源有两种主要观点(或者说最激烈的两种学术争端),即,自然之债是起源于自然法还是起源于奴隶缔结的债务。这个争议伴随着债法学术发展史的全过程,也是私法领域的一个核心问题。在20世纪初,德国法学家格拉滕维茨(O.Gradenwitz)之前,关于自然之债的研究几乎完全是出于自然法学派的视角,该学派认为自然之债是产生于自然法上的债。而格拉滕维茨是“添加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分析不同罗马法文本的基础上首次提出自然之债并非起源于自然法,而是起源于奴隶债务。当时,他的研究并未获得广泛接受,但却刺激了学界对自然之债罗马法起源的进一步研究。在其后,不断有学者对格拉滕维茨提出的观点进行评析,但主流观点仍旧坚持罗马古典法中的自然之债起源于自然法。直到20世纪中叶,意大利学者布尔德斯(A.Burdese)的研究对自然之债的自然法起源说进行了有力的抨击,才逐渐使学界中自然法起源说与奴隶债务起源说进入相持不下的局面。
我国学者大多赞同现代法上的自然之债起源于自然法[2]80,认为自然之债生命躯体的血与肉,在罗马法上都已经基本成形了。罗马法上自然之债的贡献,是使我们从源头处反思和完善现有债法体系以及在克服绝对形式理性上获得一些支撑。我国学界将罗马法起源中自然之债简单划分为两种类型:其一,他权人缔结的债,其二则是社会道德义务。他们认为自然之债的两个分类均与罗马法上的自然法相关,而罗马法中社会道德义务类自然之债才真正与现代意义上的自然之债制度相关,也是影响现代自然之债制度的关键。
二、自然法起源说的反思
(一)罗马古典法中自然法与万民法的关系
自然法源说在表达自然之债起源于自然法时往往表述为自然之债起源于万民法之债,在论述中或多或少将万民法(ius gentium)、自然原因(naturalis ratio)、自然法(ius naturale)这些术语相等同,因此我们首先需要厘清罗马古典法时期自然法与万民法的关系。
盖尤斯在其《法学阶梯》的开头写到,所有受法律和习俗调整的民众共同体都一方面使用自己的法,一方面使用一切人所共有的法。每个共同体为自己制定的法是它们自己的法,并且称为市民法,即市民自己的法;根据自然原理(naturalis ratio)在一切人当中制定的法为所有的民众共同体共同遵守,并且称为万民法(ius gentium),就像是一切民族所使用的法。因而罗马人民一方面使用它自己的法,一方面使用一切人所共有的法。在这个文献片段中,盖尤斯并未提及自然法,但他在后续章节中指出西塞罗把自然法当做万民法的同义语。[3]2优士丁尼的《学说汇纂》中还收录了与盖尤斯同时期的法学家乌尔比安对自然法的另一个定义:自然法是大自然传给一切动物的法则,也就是说,这个法不是人类所特有的,而是生活在陆地和海洋的动物包括飞禽所共有的。由此而产生我们称之为“婚姻”的男女结合及其子女的生育与繁衍。我们可以见到其他动物和野兽也都精通这门法。[4]40尽管乌尔比安提到并界定了自然法的概念,但是其中存在太多矛盾和不一致,因而罗马法学界一般认为这是优士丁尼在收录其文本时进行了修改的结果。[5]246
与盖尤斯《法学阶梯》不同,优士丁尼汇编的目的在于筛选和保存古典法时期作品的精华,并在其编纂完成后禁止使用原始文献,但这一编纂行为导致原始经典文献几乎全部失传。加之优士丁尼为了使编纂后的法典能够适应当时的统治环境,需要对古典时期法学家的作品进行修改。因此《学说汇纂》的内容并不一定真实地反映了古典法法学家们的原意。就现有的文献资料,比较主流的观点认为,在古典法时期自然法(ius naturale)与万民法(ius gentium)的概念存在重合,如果非要作出区分,那么可能体现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在使用“自然法”这个词时注重的是这种法起源于自然原理(naturalis ratio),而使用“万民法”一词时强调的是它的普遍适用。[6]50如此我们便可以理解,为什么自然法起源说的核心观点是自然之债起源于自然法(万民法)。
(二)自然之债起源于自然法之证否
自然之债起源于自然法,也即起源于万民法的观点可追溯于德国法学家希博(H.Siber)的学说[7]68,希博认为在罗马古典法时代,由市民法调整的债即为法定之债,而基于万民法调整的债则为自然之债,这两种债都具备各自的诉讼形式予以保护;而在优士丁尼时期,原本的“市民法-万民法”二分法被“市民法-万民法-自然法”三分法取代,而自然法不再被认为是实证法,基于自然之债的人不再具有诉权。他们认为对于此时的罗马人来说自然之债不再是具有“法锁”意义的债,而仅仅是一种道德义务。[8]485换言之,在罗马古典法中的自然之债是具有强制性的,其具备万民法上的诉讼保护,而在优士丁尼法中,自然之债可以从总体上被认为是以自然法为基础的道德之债,只具有裁判官法意义上的诉讼保护,在市民法层面仅具备有限的法律效力。
自然法起源说的主要文本依据是优士丁尼《学说汇纂》当中的一个文本片段:
《学说汇纂》D.50.17.84.1保罗:《论问题》第3编 债务人负有万民法上的义务,基于善意之诉承担责任才合乎自然。(D.50.17.84.1(Paulus 3 quaest.)Is natura debet, quem iure gentium dare oportet, cuius fidem secuti sumus.)
该片段本身语义并不完整,有学者指出它缺少拉丁语语法的构成元素,最后一句“cuiusfidemsecutisumus”就缺少指示代词。该《学说汇纂》文本片段显然是经过优士丁尼时期编纂者的修改,故而该片段并不“纯正”,说其是描述罗马古典法时期的法律规定有些牵强。该片段的含义大致谈到了根据万民法返还借款的义务。因此有些学者将这个片段翻译为:“自然之债的债务人,依据万民法为给付,基于善意之诉承担责任。”[9]80但很多学者提出反对观点,认为该本文片段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本,无法通过同时期其它文本片段来相互印证,因而只通过该单一的文本来确定自然之债起源于自然法不太严谨。法学家迪钦次欧(L.Di Cintio)也认为《学说汇纂》片段D.50.17.84片段中的文义并未论及自然之债这一术语,片段中 “naturadebet”一词的原意仅指“自然秩序”,也即一切事物运行均需符合的规律。此外,《学说汇纂》收录的另外两位同时期法学家的文本片段(保罗D.19.2.1以及乌尔比安D.4.5.2.2 ulp.)中提及的“natura”同样也并非指代自然之债。[10]9再者,针对上述同一片段(D.50.17.84)本身的含义,学者间的理解也不尽相同。意大利法学家彭梵得(P.Bonfante)在解读该片段时认为即使当事人一方不是罗马人,双方一旦缔结契约,就得到了市民法的认可,从广义上而言属于市民法之债,因而受到市民法的调整,不再属于万民法之债。[11]48当然,为了回应这些反对自然法源说学者们的观点,法学家科尼奥利(P.Cornioley)对希博提出的观点进行了限缩。他认为,不是所有万民法之债都可以称之为自然之债,只有万民法中的非要式契约之债才属于自然之债,并且这些契约的缔结具有“自发性”以及“与自然相符”的特点,比如,契约的缔结是基于所有人普遍认可的诚信(fides)理念之上,而这些诚信(fides)理念的确立早于任何具化的法律规则[12]16。但科尼奥利的回应也很快就遭到了质疑,反对者们认为在该片段语义相对不确定的情况下,科尼奥利又引入了一个更为宽泛且抽象的诚信(fides)概念来论证自然之债的起源,显然不具备合理性。[13]12
目前,罗马法学界大部分学者均认可自然之债的起源与自然法无关。以万民法的学理基础来推断自然之债的起源,不具备合理性。支持自然法源说的学者引用的片段中的“naturadebet”没有特定的法律特点,没有具体的法律效力,它指代的不是一种法学问题,而只能看作是一种普遍的法学现象(fenomenico)。这种所谓的“自然债务(naturadebet)”是“自然(natura)”一词的泛指使用,没有实际意义,只是在强调法理中的自然秩序[10]15。
三、自然之债起源于奴隶之债
(一)奴隶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相分离
在罗马法中,因其政治结构的需要,所有生物意义上的人被“人格”这样一顶具有公法意义的桂冠区分为法律上的“人”和“非人”[14]85,自然之债的概念也始终与“人与非人”的区分相联系。
在现代民法中,自然人的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相辅相成,权利能力是行为能力的前提和基础,行为能力则为权利能力实现的条件。而在罗马法中,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相分离,一个权利能力受到限制或者根本不具有权利能力的人可以具有行为能力,最典型的就是奴隶的行为。那些在法律上被视为“物”、不享有基本人格的奴隶不仅作为底层劳动力,而且也充当着贸易和工业领域中精明的管理人员。[15]101在这些“非人”之间不存在法律上的权利义务关系,但是现实中这些无法律主体资格的奴隶之间也需要进行交易,也不可能时刻有他人(具备法律主体资格的市民)替他们的交易订立契约。正因为奴隶之间的交易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如果他们顺利履行交易则相安无事,如果因一方或双方的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发生纠纷,这时这些人之间的债就是“自然之债”,这也是一些罗马法学者提到的“纯自然之债”[11]150。
另外,除了上述非法律主体之间发生的所谓“债”属于学者们定义的“纯自然之债”,还有一种有着近似自然之债外观的债:在罗马法中,奴隶和家子均属于广义的他权人范畴,不具备法律上的主体资格。但是由于生产经营的需要,他们被允许代表家父或主人与他人缔结债务。此时奴隶或家子的活动完全是依据主人或者家父的命令、指派或者委托进行,这时第三人可以通过“依令行为诉讼”(actio quod iussu)、“船东诉讼”(actio exercitoria)、“经管人之诉”(actio institoria)和“准经管人之诉”(actio quasi institoria)要求家父履行契约,此时承担责任的主体是家父而不是他权人,这些债则显然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自然之债。
(二)奴隶自然之债的第一个文本片段
记载奴隶缔结自然之债的最早的文本出自雅沃伦(Giavoleno)的作品,他在《论拉贝奥遗作》中收录了一个案例并进行了评述[16]55:
“某家主遗赠给他的奴隶,让我的继承人支付经我遗嘱命令获得自由的奴隶我帐上欠他的5个金币。”塞尔维(Servius)认为,给奴隶的遗赠是无效的,因为一个家主不能对奴隶负债。我(雅沃伦)认为,按照立遗嘱人的意思,这个债更应该看成是自然之债而不是市民法债,这就是目前的实践做法。”
在罗马继承法遗嘱解释中历来存在“误言无损真意原则(Falsa demonstratio non nocet)”[17]53,即,部分遗嘱内容因书写或陈述等错误无效时不影响遗嘱当中其他内容的效力。按照市民法,因为奴隶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所以即使家主在遗嘱中承认其欠奴隶5个金币,这一“债权债务关系”在市民法上也是无效的。但是,通过遗嘱解放奴隶之后,奴隶会变成具备民事主体资格的自权人,家子再按照家父的遗嘱对奴隶进行遗赠的行为是被市民法认可的。也就是说,在这一片段中家主和奴隶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无效不会导致遗嘱中指示家子解放奴隶并对其遗赠的行为无效。而雅沃伦却创造性地提出一个自然之债的概念,来确认之前的“债权债务”也具备一定的效力。
当然,雅沃伦为了弱化这一概念提出的争议,在其片段中刻意强调了“根据遗嘱人(主人)的意志(menstestantis)”这一前提,毕竟,根据罗马市民法,奴隶不能成为债权人也不能成为债务人,而是作为权利客体的“物”来对待,而这个片段中认定奴隶享有的自然之债有效是为了符合家主的真实意愿。
通过这个片段我们也可以窥见在自然之债产生之初法学家们所起的作用:自然之债是法学家在当时奴隶大量参与市场经营管理活动的背景下,在不直接违反市民法规定的前提下,通过法学家解释为已经大量出现的社会实践问题所作出的变通。
(三)奴隶自然之债最重要的两个文本
上述片段仅提出了自然之债的概念,但并未详细记载奴隶缔结自然之债的特征。后面这两个最为经典的文本则可以看到自然之债的基本逻辑及其特征:
D.46.1.16.3 e 4(Iul.53dig.):“… 3.对于民事债和自然债随时都可以提供保证;4.自然之债应该受到重视不仅是因为奴隶可以缔结自然债,而是因为自然之债一旦清偿就不得请求返还。事实上,虽然在狭义上不认为自然之债债务人就是债务人,但是在广义上他们却仍然是债务人。因此,从自然之债债务人那里获得清偿之人,亦视为获得了自己债务的清偿。”
该片段来自法学家尤里安所著《学说汇纂》的53篇,这个片段提到了自然之债最核心的效力——“清偿留置”,也即债务人对自然之债一旦清偿就不得要求返还。清偿留置效力贯穿自然之债制度发展的始终。也正是由于该片段具有的典范意义,因而被优士丁尼皇帝选入其《学说汇纂》中。
关于自然之债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也即自然之债是否具有强制性,或者说是否可以通过诉讼得到保护,法学家们意见不一。这主要是因为上述片段D.46.1.16.3 e 4中代词“eorum”缺乏指示对象。关于其所指如何,理论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法学家希博认为,“eorum”一词是优士丁尼编纂人员的书写错误,将阴性a误写为阳性o,本来 “earum” 应该是指代的是“诉讼”,也即自然之债可以得到诉讼保护,具有强制性。按照他的观点,这个片段可以理解为自然之债应该受到重视不仅是因为有专门为自然债务设立的诉讼,而是因为自然之债一旦清偿就不得请求返还。[7]70而法学家格拉滕维茨则认为“eorum”是阳性,指代的是奴隶债,他认为这个片段表明奴隶可以缔结自然之债,自然之债一旦清偿就不得请求返还。格拉滕维茨查阅了很多优士丁尼编纂文本中出现的“eorum”一词的用法,“eorum nomine”在所有文本中都是作为惯用词组出现,提及的都是奴隶与其主人之间的债,因此,“eorum”其实是“eorum servile”的简写,也就是“奴隶缔结的债务”。正因为在市民法严格规范下,奴隶既不能作为债权人也不能作为债务人,在解读本片段时,只有将“eorum”理解为“奴隶缔结的自然之债”才与下文的语义协调一致。两者相较,学界更认可后者的观点,而前者提出的“优士丁尼编纂者书写错误”“自然债具有强制性”等观点无法证成。
尤里安师承谢沃伦,在其师研究的基础上继续发展,构建了自然之债的核心概念:自然之债是不具备强制性的债务,债务人一旦履行不得要求返还。随着奴隶自然之债的概念不断拓展,该概念框架被适用于其他他权人缔结的债的领域,尤里安的片段也被用作他权人缔结的自然债的范本,在优士丁尼时期也成为解释其他自然之债种类的“一般条款”[18]53。另外,虽然后期自然之债的本质属性发生了变化,但是“不具备强制性”“一旦支付不得要求返还”等特点一直延续到现代法当中。
优士丁尼《学说汇纂》本身则或多或少由编纂者根据当时的社会现实对以往法学家家的作品进行调整与改编。而盖尤斯是罗马古典法时期著名的法学家,其《法学阶梯》是后期被现代学者发现的,其对罗马古典时期的法律解释更为真实可信,而关于奴隶自然之债另外一个重要的文本正是出自盖尤斯的《法学阶梯》,也正因为这一片段的出现,使自然之债起源于奴隶债有了无可反驳的证据。
Gai.3119a:“担保人则可以参与缔结所有的债,无论这些债是通过实物或者话语缔结的,还是通过文字或者合意缔结的;他所参加的债是市民法之债还是自然之债,这无关紧要,甚至他可以为奴隶负债,无论从该奴隶那里接受担保人的是异邦人,还是应当接受给付的主人自己。”
在这一片段中,这位著名的法学家用了三次转折层层递进地解开自然之债在古典法中的典型形态。虽然片段中并未将自然之债和奴隶缔结的债等同,但是通过直接的文义解释便可得出奴隶缔结的债属于自然之债这一结论。这一片段也与尤里安片段中的观点相契合。
从上述两个片段可以看出,正是古典时期法学家们感受到了社会的需求,因而在法律层面承认奴隶自然之债的存在, 并赋予了奴隶自然之债有限的效力。此时的自然之债可以看做是一种“抽象的”市民法,除了缔结自然之债的主体不具备市民法主体资格之外,其他效果几乎与市民法之债等同。[16]67
随着中世纪自然法主义的兴起,自然之债的范畴曾一度非常宽泛,因为自然法学家们以自然法为基础构建的自然之债的范畴囊括了与法定之债展现出不同特征的所有种类。但是这些分类方法在罗马法渊源中找不到对应。因此这种用自然法统一构建自然之债范畴的努力有时难免陷入极端。通过上述对自然之债制度罗马法起源的考察,我们发现自然之债并非起源于自然法。法学家格拉滕维茨从奴隶缔结的债这一领域重新定义自然之债制度的起源,引领自然之债的研究转向新方向发展。这再次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罗马法学者对自然之债起源的高度重视,并掀起对自然之债的研究分历史时期探讨的热潮。在优士丁尼的文本渊源中无法用一个统一的分类来涵盖所有自然之债的文本片段,但是我们回溯本源的过程中,能在古典法中找到相对统一的自然之债的概念内涵。这一概念内涵是随着古罗马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奴隶在商贸习惯中取得不可替代作用的背景下才产生的,用以指代奴隶缔结的债,虽然由于主体不具备能力因而不能通过诉讼获得保护,但是债务人一旦支付就不能要求索回,除此之外对自然之债还可以进行担保,因而其在抽象意义上除了主体因素外,其他效力几乎与市民法之债效力等同。然而,自然之债不是个一蹴而就的法学概念,我们能看到的罗马法学家们对自然之债所作出的解释都是一个个相对独立的文本片段,他们感受到经济社会的变化,进而结合自己的法理知识,利用法学解释的手段对严苛的市民法作出变通。通过多个法学家们的法律解释,自然之债从其概念起源到形成具体模式不断地发展,慢慢拓展了自然之债概念的外延。
四、自然之债的价值与法律解释的重要性
我国最新颁布的《民法典》并未用专门条款规定自然之债制度,但并非如某些学者所言的自然之债制度在当今社会已不复存在,是一种落后的、边际制度。虽然自然之债从未以法条方式固定于我国制定法渊源之中,但在具体实践和司法案例中却从未缺席。最高法的《决定》在一定程度上为企业融资难以及“套路贷”“虚假贷”频发等问题提供了司法保护路径,通过明确民间借贷利率保护上限排除了民间借贷类自然之债发生的可能,但在超诉讼时效债务、小额赌债、非婚同居、限定继承等领域引发的纠纷中均有自然之债的身影。这一方面源于民法的裁判规则属性,即,法官不得以法无明文为由拒绝民事裁判,但更重要的是,自然之债以法定之债为原色,以不具备强制性和一旦支付不得请求返还为支点,仍在法律与道德之间体现其缓和实证法僵硬性的当代价值。
正如古罗马法继受者之一的意大利,其最新的《民法典》吸收1804年《法国民法典》和1900年《德国民法典》之长,是后法典编纂时代的又一丰碑。在其法典编纂中他们重新纳入了“遗失许久的”自然之债这一古老罗马法概念,用以调适复杂的社会环境变化与严苛的实证法之间的矛盾。我们目前的实证法当中虽然没有直接规定自然之债制度,但从自然之债的起源中我们已经看到它本就是一种“超法律义务”,与法定之债结构相似,具有必要的财产性内容。自然之债一直普遍存在于实践与规范之间,而这种“中间地带”正是法律解释能发挥最大作用的空间。正如自然之债在古代社会中的发轫一般,法律工作者特别是民法领域的工作者应当充分利用民法的法律解释方法,让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之债在内的一些法学理念在不同个案中依然体现其实践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