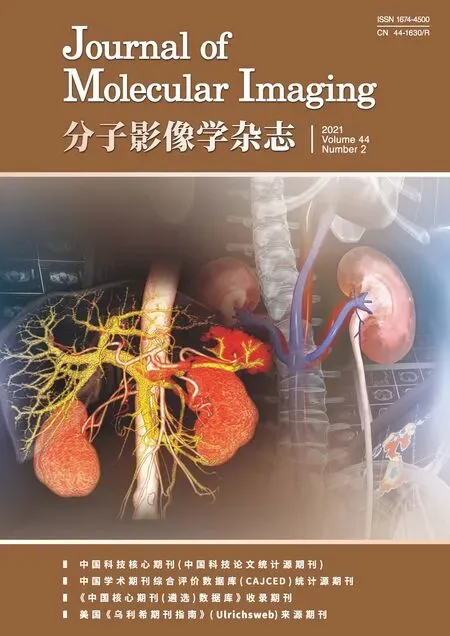功能磁共振成像技术在针刺治疗中风偏瘫脑机制研究的现状及前景
2021-12-02胡赫其鲁海韩李莎胡佳慧张春红
胡赫其,鲁海,韩李莎,胡佳慧,张春红
1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针灸临床部,天津 300193;2天津中医药大学研究生院,天津 301617;3宝安纯中医治疗医院针灸推拿康复科,广东深圳 518000;4浙江省人民医院康复科,浙江杭州 310014;5国家中医针灸临床医学研究中心,天津300381
中风是最常见的急性脑血管病,其较高的发病率、病死率、致残率已严重威胁到人们的生活。针刺作为中医重要的外治手段,在镇痛、脑血管病、心身疾病等领域疗效可观,尤其在中风病的康复治疗中发挥日益显著的作用,在世界范围内已广泛应用于临床。目前,对针刺效应的机制研究也在拓宽加深,逐渐深入到现在的分子、基因等微观水平;而近年来多模态成像技术的介入将该领域引入可视化方向,为探究针刺的中枢效应机制提供了新思路、新方法。这其中,功能磁共振成像(fMRI)是集功能、影像、解剖为一体的活体定位脑功能活动区的技术,它根据神经周围毛细血管的血氧水平变化间接反映神经活动,并以此为基础进行数据分析得到人脑不同区域的激活情况以及各个脑区之间的关系,因其兼有较高的时空分辨率且安全无创的优点,是目前脑功能成像应用最广泛的技术之一[1-2],并逐渐产生了针刺神经影像学这门新兴的交叉学科[3]。本文就目前基于fMRI技术研究针刺治疗中风偏瘫脑机制的现状予以多角度、多层次的论述,分析目前可能存在的问题并展望其应用前景。
1 fMRI应用于针刺治疗中风病的研究现状
fMRI根据扫描过程中是否执行任务分为了任务态(task-fMRI)和静息态(rs-fMRI)。经典的fMRI研究主要指任务态研究,task-fMRI通过执行特定任务如主动或被动运动,来诱发大脑皮层出现相应的神经活动,分析BOLD信号变化,观察特定任务下的神经元响应,针刺任务常包括接电针或手动捻针[4]。研究发现人体处于安静时的大脑活动也非常活跃,尤其是有些脑网络,如默认网络在静息状态下活动要强于任务状态,因此学者们认为rs-fMRI能反映人脑自发活动情况,rs-fMRI要求被试者处于安静放松状态下获取信号,之后根据目的对数据处理分析,观察针刺后局部脑区活动以及不同功能脑区之间的连接情况及对运动/感觉等脑网络的调制影响。随着fMRI研究愈发成熟,派生出了许多分析方法,目前常见的任务态分析方法为基于GLM一般线性模型分析脑激活区,此外包括通过动态因果分析和格兰杰因果分析的有效连接(EC)及表征相似性分析等也逐渐受到关注,静息态分析方法有局部一致性(ReHo)、功能连接(FC)/EC、低频振幅(ALFF)/比率低频振幅(fALFF)、脑网络分析方法等[5-6]。
1.1 task-fMRI研究
针刺治疗中风偏瘫的task-fMRI研究,多数采用组块设计、事件相关设计,将任务状态与静息状态对比,分析针刺刺激时中风患者健-患侧脑区的激活与负激活效应,主要观察针刺的即刻效应。有研究在任务态下发现,与假针刺相比真针刺阳陵泉能正激活患侧颞叶和舌状回、小脑,而健侧的运动皮质和患侧的下肢运动皮质激活效应较低,认为针刺可增强运动-认知相关脑区的联系,并降低未受损运动皮质的代偿,从而减轻患侧肢体的联合运动,缓解痉挛状态[7]。有研究发现相较于执行运动任务时激活的脑区,针刺阳陵泉穴除了同侧运动前区有部分激活外,双侧基底核等椎体外系有明显激活,分析针刺可能通过皮质-基底核-丘脑-皮质的反馈回路来调节兴奋性谷氨酸和抑制性氨基丁酸两种神经递质的释放来降低肌肉肌张力[8]。也有研究采用任务态设计,对16名缺血性卒中患者研究后发现,相较于假针刺,针刺外关穴能明显负激活健侧的顶叶前梨状皮质区,该区域与病灶的位置接近,认为是针刺引起病灶周围血流量增加导致该区相对抑制,是机体自我代偿的体现[9]。有研究对中风患者针刺曲池穴和足三里穴,观察不同取穴对脑激活区域的影响,发现针刺曲池穴主要激活患侧次级体感皮层,而足三里穴激活了双侧次级体感皮层及健侧下半月小叶[10]。以上研究说明针刺不同穴位可激发特定的脑通路,从而引起相应脑区的激活。Li等[11]发现针刺在得气和非得气状态下激活的脑区不同,针刺外关穴得气后对小脑右前叶、边缘叶有特异性激活,可见得气也是针刺起效的关键因素。有文献对缺血性中风患者的fMRI研究采用组块设计,比较外关穴针刺刺入与针刺捻转之间的脑部激活区域差异,结果示针刺激活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健侧半球的初级感觉、运动皮层,且针刺捻转较针刺刺入能激活更多的脑部区域,说明针刺操作手法可能会对最终的疗效产生重要影响[12]。
1.2 rs-fMRI研究
1.2.1 ReHo分析 ReHo是一种局部功能活动特性分析方法,通过计算某一体素与相邻若干体素时间序列之间的肯德尔相关系数,然后将相关系数向每一体素赋值,其代表着某一脑区局部的功能强度[13]。ReHo值增高表明脑局部的神经元活动在时间上趋向同步,因此该分析法主要研究局部神经的同步性活动情况[14]。有学者在静息态下观察针刺阳陵泉前后对中风患者脑部ReHo值的影响,研究发现与针刺前相比,针刺后患者的健侧额中回、中央前回、中央后回、顶下小叶及双侧尾状核的ReHo值增强,从神经自发活动层面说明了针刺通过对健侧局部区域的功能重组,实现对患侧脑损伤的代偿[15]。Chen等[16]对10例缺血性中风患者进行健侧肢体针刺,发现针刺后患侧中央前回和额上回ReHo值升高,患侧顶叶上叶、健侧梭状回和辅助运动区ReHo值降低,认为针刺能刺激双侧大脑活动,尤其是位于中央前回的初级运动皮质和前运动皮质,也是运动启动和运动控制的最重要脑区,与肢体功能的恢复有关,但两侧激活程度及部位不一致,因此针刺时需斟酌考虑选择健或患侧肢体。谢西梅等[17]则比较了不同针刺方式对缺血性中风患者ReHo信号的影响,发现电针较常规针刺激活的脑区更多,且信号改变更明显。
1.2.2 ALFF/fALFF分析 ALFF/fALFF也属于局部功能活动特性分析方法,该方法将每个体素的时间序列提取出来,通过滤波得到频率为0.01~0.08 Hz的低频信号,然后经傅里叶变换得到频率域,进而得到对应的能量谱,通过计算得到ALFF值,可反映脑局部的自发活动[18]。而fALFF是由ALFF值除以整个频段ALFF值得到,fALFF可有效抑制脑池部位的非特异性信号,减少生理噪音干扰,提高检测脑自发活动的敏感度和特异度[19]。有学者采用ALFF来分析针刺痉挛侧拮抗肌对静息状态下大脑功能活动有何影响,结果发现与针刺前相比,枕中回、丘脑、额上回、楔前叶等脑区的ALFF值增强,分析可能是通过直接或间接调节椎体外系的功能活动水平,从而降低痉挛部位肌张力水平[20]。欧芳元等[21]将脑梗死患者和健康人比较,观察针刺前后静息状态下全脑fALFF的特点及变化,结果示脑梗死组治疗4周后患侧颞下回、小脑、枕上回、中央前回及健侧楔叶等脑区fALFF值显著升高,双侧后扣带回等脑区显著下降,其中中央前回和中央旁小叶比值与针刺治疗后Brunnstrom运动功能分级呈正相关,说明脑梗死患者在针刺后脑区的fALFF值发生变化,可能与针刺改善梗死后运动障碍及重塑功能网络相关。
1.2.3 FC/EC分析 FC反映的是不同脑区之间神经活动的相互关系,对所得数据进行皮尔逊相关分析,得到不同脑区关系强弱结果,根据是否在时间尺度上估算时变可分为静态功能连接和动态功能连接[22]。而EC则是采取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多变量自回归模型或者格兰杰因果分析和动态因果分析,既度量了大脑不同区域之间连接关系的强弱,又能记录神经元之间的时间关系,使连接具有方向性,可以阐明了大脑活动的神经交互机制[23]。Zhang等[24]发现在静息状态下,中风患者在针刺后后扣带回与右侧顶下小叶、额中回、颞下回以及双侧额上回等的功能连接减弱,而与双侧中央前回、中央后回、顶下小叶、颞上回、岛叶及右额下回的功能连接增强,认为针刺的起效机制可能是通过对默认脑网络的调节。Fu等[25]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探讨针刺对脑梗死内在静息网络之间有效连接的影响,发现在针刺前,左额顶网络的输入大部分来自其他网络,而默认脑网络向其他网络的输出最多,针刺后可逆转该现象,说明针刺可能可调节多个脑网络,尤其是通过作为中继站的默认脑网络在左额顶网络与感觉运动网络之间传递信息,从而重新整合脑内的有效连接,发挥神经功能重组作用。
1.2.4 脑网络分析 近年来,基于图论的脑网络分析法成为一个研究热点,该方法假设大脑由节点(脑区)和连边(节点间的连接)组成,使得各个脑区之间形成各种连接,构建大脑功能连接图,并通过各类指标(包括聚类性、最短路径长度、模块化、局部效率和整体效率等)比较针刺前后的功能连接差异[26]。Han等[27]在静息状态下通过图论分析研究针刺对中风患者小世界属性的影响,发现中风后全脑网络的平均局部效率等小世界属性均有所降低,而针刺能显著提高中风个体的聚类系数和平均局部效率,进一步证实了针刺对中风后功能性全脑网络的调节作用。有学者观察针刺对3例不同部位卒中后失语患者脑网络的影响,发现针刺后3例患者皮层语言网络、皮层下网络的内、外连接总体均上升,说明皮层语言网络、皮层下网络内、外连接的增强与针刺后的语言功能恢复具有相关性,同时3例患者皮层语言网络的内连接均有增强,提示可以此作为语言功能的监测指标[28]。
1.3 双态结合研究
目前,也出现了将task-fMRI与rs-fMRI联合应用的研究,根据研究目的选用分析方法来观察中风患者有无执行/被执行任务时对应指标的差异。有学者将任务态和静息态相结合,对健康人和中风偏瘫恢复期患者在针刺前、中、后分别进行rs-fMRI与task-fMRI扫描,结果显示患者在被动运动任务期间皮质和皮质下的有效连接明显降低,针刺阳陵泉可以增强小脑和初级感觉运动皮质间有效连接从而代偿[29]。Ning等[30]也采取相同的试验设计,发现针刺阳陵泉可使中风偏瘫患者原本降低的双侧初级运动皮层之间的功能连接增强,而健康组前后无明显差异。
1.4 小结
综上,通过task-fMRI、rs-fMRI的研究发现针刺时/后,大脑皮质运动区、感觉区以及小脑、基底节等部位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激活,脑局部活动明显增强,同时针刺也可改变某些区域之间的功能连接/有效连接,对运动、感觉、语言等脑功能网络发挥调节作用,被认为是潜在的针刺中枢效应机制。此外,中风后全脑网络趋向于效率低下的随机网络[31],而针刺能够调节中风后全脑网络的中断模式,改善全脑功能网络小世界拓扑属性,使得神经功能得以重组。腧穴与脑区之间也存在特殊相关性,针刺不同的穴位能引起中风患者不同脑区激活状态的改变,比如针刺外关时运动、听觉、语言、情绪有关等相关脑区出现激活[32],而针刺阳陵泉主要集中在小脑、中脑、大脑皮质等运动区[7-8],也在中枢层面解释了经穴作用靶点的特异性。
2 讨论与展望
人脑是由上千个神经元细胞构成一个结构与功能高度集合的整体,但其中功能结构的关联性仍待研究。自从发现大脑结构网络具有“小世界”属性和模块化结构等拓扑属性后[33-35],随着多模态成像技术逐步成熟,人脑连接组的研究逐步从大脑结构网络扩展到了大脑功能网络,这为进一步探索针刺的脑效应机制提供了技术支持,同时为临床工作者治疗中风偏瘫提供了有证可循的可视化依据,并加深对针刺如何改变大脑功能从而治疗中风的理解。fMRI技术从20世纪90年代逐步兴起,现已趋于成熟,而在这之前脑电图、脑磁图等无创脑功能检测技术早已深入大脑病生理研究领域。相较于能直接反映神经电生理、电磁活动的脑电图及脑磁图,fMRI只能通过神经周围小血管血氧水平变化来间接地说明脑活动情况,但其超高的时空分辨率是其它检测技术所无法比拟的,因此fMRI应与其他检测技术互相弥补,全方位、多维度观察脑活动。但不可否认的是,在技术和研究层面,其操作性、科学性有诸多问题仍值得深度探讨。
首先是任务态、静息态如何选择。目前针刺对中风患者脑机制fMRI研究任务态和静息态均有涉及,其试验设计、分析方法、观察目标均不同:(1)task-fMRI:任务态反映的是被试者在执行/被执行任务时大脑的活动情况,体现针刺的即刻效应[36]。目前以单一针刺任务组块设计和非重复事件相关设计最为多见,此外还有研究者采用针刺配合被动运动任务,但因为试验本身较为复杂,且为了排除两次任务组块间的干扰总体扫描时间较长,对患者及施术者要求较高。值得注意的是,针刺具有持续性效应,作为基线的静息态可能存在波动,干扰试验结果,故更建议采用非重复事件相关设计[37],扫描过程中仅予针刺刺激1次,之后继续留针扫描;(2)rsfMRI:既往研究表明人脑在静息状态下也存在自主神经活动[38],静息状态下的信号在脑功能网络内的不同脑区之间呈高度的同步性,能反映人脑自发的神经活动,能够通过不同的数据处理方法得到针刺前、中、后的脑功能特点或变化情况[39]。试验设计较任务态研究简单,对患者要求低,更适用于中风患者[40]。但操作时为了保证患者处于安静平稳状态,笔者认为针刺的刺激强度不宜过重,而在临床治疗时,尤其是对中风急性期患者,为寻求最佳疗效,刺激往往较强,试验和临床仍有较大差异。所以在实际应用中,应根据研究目的的不同选择合适的方案,必要时可采用双态联合研究的范式。
其次,目前fMRI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第一,因目前技术水平的限制,网络节点的选择以体素或者脑区为主,仅仅局限在大脑不同区域之间的联系,而无法揭示深层神经元或神经元集群的连接关系,使得针刺中枢机制研究仍停留在较大尺度水平上,难以解释针刺在更细微的神经元之间是如何进行效应传递[33]。第二,不同脑图谱以及节点的选择会造成结果的差异。Wang等[41]以两种脑图谱为基础构建脑功能网络,发现两者的拓扑参数有明显差异,而且选择以脑区或体素为节点也对网络拓扑性质产生明显影响。中风状态下无论是患者之间还是与正常人相比大脑结构绝不相同,结构是功能的基础,基于正常人脑图谱的fMRI研究对疾病状态下的意义尚待探讨,因此未来研究应当制作出适合中风病研究的脑图谱并选取合理的节点。第三,中风的病程和治疗周期较长,fMRI仅能反映较短时间内动态变化,尤其是任务态设计,难以做到对脑活动长期的动态观察。某些研究分别在治疗周期前后扫描并对结果进行比较,两次扫描间隔较长,外界对受试者的干扰难以把控,期间进行多次扫描也不太现实,因此采取该试验设计,其结果可能缺乏准确性。
对于目前针刺治疗中风病的fMRI研究,仍存在很多不足。对于类似研究所得出的不同结果,未能对原因及中枢机制作更深入的阐释,而且对健患侧脑活动影响的差异性缺乏进一步分析,而这可能与受试者的年龄、病程、病灶部位以及施术者针法水平等因素有关[42],要归纳出其中的普遍性和特异性并找出其中的关键脑区还需要大量针对性的试验研究,并对试验设计要有统一的标准。此外,很多试验结果表明针刺后虽然某些脑区间的功能连接较高,但它们在结构上不直接相连,这其中的原因以目前已有的分析方法难以做进一步研究。且现有的研究分析方法较单一,以观察局部脑区激活情况为多数,功能连接和有效连接能够反映两个节点无向的统计依赖关系和有向的因果效应[43-44],但该类研究相对较少。建议未来研究重点应转向通过有效连接构建一个有向的功能脑网络来刻画针刺效应在不同脑区传递的方向性,而不能只停留在单一脑区层面。
总之,fMRI针刺相关研究方兴未艾,在试验设计、分析方法、结果讨论等方面仍需探索,与临床实际也难以完美契合,但目前仍是脑机制研究的重要技术手段。当下对脑的研究如同冰山一角,针刺对脑的调节作用机制也亟待进一步证明,未来倡导多学科并举,传统理论与现代技术交叉融合,将以fMRI为代表的多模态影像技术融合应用于针刺研究并构建出针刺治疗中风的特异性脑效应网络,这对中国特色脑研究计划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