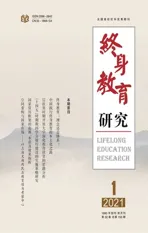空间重构与国家在场
——以上海文庙改民众教育馆为考察中心
2021-12-02周慧梅汤浩泽
□ 周慧梅,汤浩泽
民众教育馆作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社会教育的综合机关,在政府行政力的强力铺设下,数量、规模不断扩增,文庙、贡院、关帝庙、钟鼓楼旧址等地方公产成为其空间布局的主要凭借物。对于公共空间在民族与国家建构中的作用,学界已有广泛认同①,对于民众教育馆借助传统公共祠庙产生的社会功能,笔者亦进行了些许尝试②,从社会文化史角度揭示传统公共空间现代转型中的教育意蕴、社会秩序与政府职责之间的博弈,探索集体仪式与国家认同的互动。张国鹏以上海文庙为中心考察了政权与信仰变革下的民国文庙的空间演变③。从学界成果看,甚少涉及文庙旧有管理者以及社会各界与政府、政府不同机构之间的博弈。有鉴于此,笔者以上海文庙改设民众教育馆为考察中心,梳理政府对文庙空间重构与意识形态的渗透输送、民众对传统空间新象征意义的接受和认同的过程,分析上海市教育局与工务局如何联手通过一整套符号与集体仪式的空间重组及仪式操演,使得传统公共空间得以“旧貌换新颜”,分析文庙改建过程中各方权势博弈以及空间布局的价值取向,通过文庙这一公共祠庙的现代赋形看空间重构与国家在场之间的互动。
一、社会舆论与传统空间转向
上海文庙始建于元代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明清两代屡有增建修,几经迁移,清咸丰五年(1855年)重建于海防道署遗址,建成后占地28亩,作为“庙学合一”场所,上海文庙承担了官方祭典和府学教化的双重功能,春丁祭孔典仪式最为社会瞩目,官府要员及佾舞诸生“莫不整肃衣冠,恪恭将事。于五鼓时恭诣西门外大成殿,随班行礼,次及两庑先贤前,陈太牢之供,举释采之典。时则鼎彝悉备,管合龠具陈。舞则按部就班,乐则和声依咏。(旁观者甚形拥挤)莫不叹为观止”。[1]除去隆重庄严的春秋丁祭,还有新进生员“入泮”,地方长官、学宪的文庙拈香和先哲入祀等系列仪式,彰显文庙在地方社会中的作用。民国肇基,随着社会舆论变化,文庙作为儒学象征的传统空间开始转向。
1912年7月,上海文庙成为国民公会上海部的办公地点,定期举行讲演会,向民众宣传共和理念,洒扫局董陆蔚臣还提出孔子诞辰日允许普通民众进入文庙观礼的建议[2],以便文庙适应共和政体的新政治语境,表明文庙管理者开始思考文庙在新政体的空间转向。次年9月孔子诞辰日“在沪各团体暨各学校教习及男女学生”三千余人的规模集聚文庙,[3]礼节亦新旧杂陈。1914年丁祭日“由观察使杨君主祭,洪知事张汪两厅长暨崔朱贾三君为陪祭,均行三鞠躬礼,孔教会会员仍行三跪九叩礼,各学堂及绅商等次第行三鞠躬礼”[4]。民主共和理念被嵌入“以正人心,以立民极”的儒家道德教化传统中。
1915年8月26日,江苏省教育行政第二次会议开幕,江苏巡按使提出各县文庙内附设通俗教育馆提案,内文称在其内陈列普通书籍、图报、理科卫生之模型以及圣贤遗迹、遗像等,并附设通俗讲演会,“裨众展览,而坚信仰”,职员则由县教育行政人员兼任,该提案获得一致通过。[5]次年1月,江苏巡按使公署与沪海道尹公署联衙饬令属地知事,对在文庙内设立通俗教育馆做进一步的阐明,“窃维崇圣德而风后世,文庙之设,由来尚已。晚近以还,弦歌不作,遗泽浸衰。入夫子之门,举凡文物章服礼器之属,荡然无存,即当年礼乐之堂、宫墙之地,非倾圯亦荒芜矣”,提议按大总统颁布教育纲要中社会教育专条规定, “修而葺之,量地为用,凡所陈列之品物图书等,悉以供公共阅览为目的,启智慧于群黎,即所以垂德化于无穷”[6],将文庙辟为社会教育场所,面对普通民众开放。次日,上海县知事将附设办法登载于《申报》,声称将在该馆附设通俗讲演会。[7]惜经费无着,直至省署所定筹备期限届满无果而疾[8],但文庙改建、面向公众开放的社会舆论已悄然埋下。
1924年5月,上海市文庙洒扫局董事王慕结提议将文庙改建成公园,对公众开放,使儒家文化传诸民间。此提议得到多名局董赞同,列名发起将文庙改建为“上海文庙园”议案,并移交县议会办理。[9]其时上海舆论正处于租界公园“华人与狗不能入内”的漩涡之中,此议一经公布,赢得众多响应,“上海的租界亦有数处公园,但是他们的门首往往悬着‘华人与狗不能入内’的示牌,咳,这不是最耻辱的事,呜然,而亦是华人‘自取其咎’,一则中国人没有道德心,二则自己没有公园,供人们的游息,所以西人才有这种的举动”,而“文庙是尊孔子而设的,每年除了祭祀的日子,一年两度的开放,就终年封闭,非但失了尊孔的真谛,反而作了鸟巢兽窟,很大的房屋,就此颓敝不堪”,认为改建成公园后,“大可供人瞻仰,引起他崇拜孔子的思想”。[10]该年12月,《申报》上登载《文庙宜开放》,简便经济被作为宣传要点,“孔子固圣之时者,也当亦顾而乐之,许为移风易俗之良法矣。各地之办理教育经管公产者,曷起图之?慎勿以文庙为神圣之地而任令其颓废至失观瞻也”。[11]当然,舆论提倡与实际运行是两码事,文庙洒扫局局董们改建公园的议案石沉大海,县议会却先后通过改建四祠、规复文庙旧制的决议,1925、1926年的上海文庙在孔子诞辰日举行祀礼,增加乡贤入祀忠义孝悌祠、节孝祠,以示褒扬孝悌节烈。可见,文庙的传统空间价值仍备受重视,传统士绅仍把持着文庙改制的话语权。随着新政权确立,文庙改建才得以落到实处。
1927年3月,国民革命军攻克上海,6月4日,江苏省政府饬令各县撤销文庙奉祀官[12],文庙洒扫局随即改做上海市教育协会会址,7月13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第四团团长俞济时将新兵招募处迁至文庙办公。1928年2月21日,大学院训令废止春秋祀孔大典,从制度上规定政府不得再参与孔子祭祀。2月29日时值孔子春丁祭日,上海绅学两界同人公推社会活动家姚文楠为主祭,自发前往文庙举行祀礼,因大学院训令限制,舍弃牛羊三牲,无学舞鼓乐,仅供设鱼肉笾豆菜酒等物,春丁祭场面凄清。[13]4月20日,江苏大学区县教育局联合会上,兴化县教育局呈请江苏大学区通令各县文庙一律改设通俗教育机关,以免任其荒废,会议以决议形式通过。[14]上海市教育局摩拳擦掌,为将文庙改设通俗教育馆而积极运作。
9月18日,以改良风俗、开展社会教育为己任的上海少年宣讲团发起人汪龙超致函市长张定璠,以推动社会教育发展为由,提议将孔庙改建为公园,并附设通俗教育馆,“窃念公园为社教之一种设施,查沪南人口稠密,市肆繁盛,独公园之设尚无”,“应就原有公共建筑而改造之,事半功倍,易于功成。查文庙地处沪南中部,占地广阔,建筑坚固,有泮水之池,魁星之阁,明伦堂可作公共讲演之用,改废物为利用,又可表孔子之圣贤。群众得以游览,不若只闭之无益。并得加以建设,如通俗讲演所、通俗教育馆、阅览书报所、改良茶馆等”。21日,上海特别市政府将呈文下发至新成立的工务局,令其“核议具覆”。接到市政府饬令后,该局局长、留德工程学博士沈怡亲赴文庙实地勘察,23日回复张市长,认为文庙的位置、交通和内部布置都适合改建公园④,支持汪龙超的改建提议。
为了扩大舆论,汪龙超将其提议刊登于《民国日报》,社会人士纷纷响应。市民尹勇等11人具名呈文市政府,表明他们赞同将文庙改建为公园,“沪南文庙,地处中心,建筑坚固,内有魁星阁、泮水池、明伦堂,可作讲演之所,藉此宣传三民主义,既可将党义灌输民众,又可表示尊孔,供人游览,即社会教育亦可发展,将此废物,化为有用”,“且沪南民众,渴望有年,因前军阀铁蹄所压,虽提议者不乏其人,而未得效果,今既处于为民众谋幸福之青天白日旗下,可解决一切,故有公园之建议于前,同人等响应于后,用特具呈请求钧府鉴核,赐予允准,则社会幸甚,党国幸甚”。尹勇等人直接以宣传三民主义、党义灌输等政治目标,并借民众对新政府期望心情,给市长巧妙施压。[15]文庙向普通民众开放,已与将尊孔“传诸民间”无关,而是国民政府权力下潜的政治需求。
在多方合力下,市长张定璠很快做出决定,10月2日,训令工务局会同教育局核复尹勇等人呈请,拟定文庙改建公园的计划。工务局第二科科长许贯三负责草拟计划,提出大成殿“为全庙大小各殿堂内神像收容所”,作为尊孔之遗迹,崇圣祠则改作图书馆,大成殿旁的“走廊厢房暂改作国货售卖所、标本陈列所、国货陈列所或民众茶点室”,而旧有的长约七十丈的高围墙“均应拆去”。⑤
这个计划遭到上海市教育局的反对。教育局遵从内政部给苏省政府饬令[16],10月15日,上海市教育局接管文庙[17],积极筹划将文庙改建为民众教育馆。教育局之所以公开与工务局抗衡,从《申报》披露的信息看,皆因在接收前已与市政府就文庙改建达成共识:“上海特别市教育局,前以设施民众教育馆及图书馆,无适当地点,而事实上又极为需要,势难再缓,后以文庙地方宽泛,足供设施,曾奉到市政府训令接收在案,兹悉教育局方面,已与县政府接洽就绪,定于下周一前往接收,想将来本市社会教育方面定有一番新设施矣。”[18]教育局接收后,马上筹备民众教育馆,并计划在其中附设儿童乐园、博物馆、公共讲演厅、简易体育场等。[19]很有意思的是,同日《申报》第25版刊登市政府给予工务局的饬令,称“现文庙业已收归市有,已着工务局计划一切,对于园内各项布置以及花草树木,将参照各大都市公园情形,并根据科学原理,以期尽美尽善云。又本市以市政进行,贵有开明之市民,否则市政进行,定有阻碍,是以开办民众学校及采取种种宣传方法,阐扬市政真谛外,并亟谋图书馆之设立,以增进市民之智识,现以南北两市之公园地址既经觅定,拟即在该两园内附设图书馆各一所,并责成教育局筹备一切”。[20]显而易见,上海市政府将文庙的改造,实际上交由工务局、教育局共同负责。
教育局接收文庙后,局长韦悫(留美博士、大学院院长蔡元培亲荐)深谙中央政府社教政策,11月14日,在未与工务局沟通前提下,呈文市政府,“上海县之文庙,自经本市教育局接收后,即拟利用其地设立民众教育馆一所,该局以此为推广民众教育之第一步,亦即民众教育中之重要工作,经积极计划,务使之成为事实,昨该局将该馆计划及概算书呈请张市长审查”,提出将文庙全部改建为民众教育馆的诉求。[21]面对教育局单独行动,工务局局长沈怡致函张定璠市长,重申文庙改建公园计划及市政府批文,请市长裁夺。2月4日,张定璠训令维持前次批文,否决教育局擅自将文庙改设民众教育馆的提议,饬令教育局重新递交计划及预算书。⑥教育局采取“迟迟不递交计划及预算书”等消极应对策略,加上经费难以落实,⑦这份市长训令成为一纸具文。5月初,韦悫调任中央大学教育学院院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执行委员、宣传部部长陈德征接任教育局局长。工务局利用新旧局长交接之际,于5月15日致函教育局,要求其按照前议尽快制定民众教育馆的详细计划;同日在国民党上海执委会常会上以一区党部名义,呈请咨询市府文庙改建公园议案;与此同时,工务局再次呈文市政府申明文庙改公园的必要性,请求市政府尽快饬令财政局拨还垫款,饬令教育局从速拟定民众教育馆计划。⑧一个月后,教育局递交了如工务局所愿的详细计划。
工务局通过各种努力得到了如愿结果,却因市长更迭化为泡影。张群作为政学界的核心人物,于4月1日接替张定藩出任上海市市长。他就任后,面对工务局与教育局之间改建文庙的纠纷,根据教育部、内政部、财政部会衔公布孔庙保管办法⑨,决定将文庙全部改为民众教育馆:“本府一百二十七次市政府会议决议,将孔庙改设民众教育馆,其中古迹名胜务加保留,并使之公园化。”⑩市政府的决议,使得前任教育局局长韦悫的主张“原地复活”,同时兼顾了工务局改建文庙为公园的计划,传统空间的现代赋形正式拉开帷幕。
二、传统空间重构与布局变化
根据市政府决议,教育局与工务局联手推动文庙空间改造。两局首先统一文庙修葺方案:分步改建文庙。11月20日,工务局局长沈怡会同教育局局长徐佩璜(1930年接任陈德征)同至文庙详为勘察,就文庙修葺达成共识。12月13日,工务局、教育局联衔会呈市政府,以“保存原有古迹名胜暨发展民众教育为原则,并于设备上务使之公园化”为整体思路,“凡古迹名胜,俱照旧保存,并利用余地,增建屋舍为办理民众教育之用。庙内原有建筑物,如门首、牌坊、桥拱、大成门、大成殿、崇圣祠、明伦堂、魁星阁,或以先圣关系,或以古建筑之美丽,悉家保存,并重行修葺。惟旧有大成二门及东西两庑房屋,因无修理价值,俱拟拆除,使各部分联成一贯,形势上也可顿见宏伟,并改筑沿文庙路之墙垣,以壮观瞻。复于庙内依照公园布置方法,加驻步行路线,栽植花草树木,并将魁星阁前之池水设法澄清,俾市民于瞻仰庙貌、阅览书报之余,并获身心游息之所”,并于四周空地上建筑图书馆、音乐厅、博物馆、动物园等,建筑形制力求与庙内原有建筑物收相得益彰之美。这份呈文,强调保存文庙原有建筑,以便文庙空间象征成为社会教育发展助力,究其原因,既与外界批评舆论有关,更与国民政府的“致敬传统”的社会教育发展路径有内在联系。1931年1月16日,张(群)市长批准此项计划,市政府指拨改造经费。[22]
经费到位后,两局分二期工程,将文庙改建落到实处。一期工程主要是整理文庙景观,文庙南面围墙完全拆除,用砖墩、冬青树来做装饰,每墩相间五六尺距离,中植冬青树,路人得见园内景色;文庙中的两座牌坊因年久风蚀全部卸下,将石柱抛洁后重新砌造;文庙内四座石桥一律拆除重建。第二期主要修理建筑,如大成殿、崇圣祠、明伦堂等,修补竹篱、浚池叠石、种植花草树木,大成殿“加大髹漆,金碧辉煌,至为壮观”,10月初全部竣工。从空间布局上看,保留了文庙的大部分建筑及景观。10月12日,上海市民众教育筹备处迁入文庙崇圣祠办公。教育局职员李大超兼任馆长,负责民众教育馆的筹办工作。1932年4月1日,专任馆长杨佩文到任,鉴于“本市人口稠密,适合高尚娱乐之场所,公园惟租界有之;南市一带,近年来人口激增,地无闲隙,民众业余,无可游览,佩文接任以后,第一步即着手规划园景”[23], 6月1日,民众教育馆允许民众入内参观; 10月10日全馆全面开放。
教育局主导下的文庙空间塑造发生了大的变革。大成门被改造成民众教育馆的时事展览室、儿童阅览室及娱乐室,崇圣祠为该馆的“一·二八”战绩展览室、生计展览室,明伦堂为演讲厅、民众学校及阅报处,藏经阁成为市立图书馆所在地,魁星阁被改造为民众教育馆的会客室,儒学署成为公民教育展览室、东北战迹展览室、健康教育展览室;而政府令保留的大成殿,变成了“祀孔彝器陈列所”。从这种空间塑造看,培养时代公民、激发民族精神、倡导科学健康等西方理念是民众教育馆的主体活动,文庙固有的儒家文化象征仅保留了一个“祀孔彝器陈列所”,文庙建筑作为历史陈迹被展览。很有意思的是,上海市民众教育馆将景观与展览的开放时间做了分别规定,可窥教育局对文庙原有空间旧有文化象征及固有功能并未沿袭之意,仅仅是借助建筑空间,“旧瓶装新酒”,这种态度在1934年后祀孔仪式中得到更淋漓尽致的体现。[1]
工务局对民众教育馆的如此空间布局,实际上并不十分认同,背后是文庙改造利用理念不同的现实投射。教育局在于寻求最大限度推行社会教育的场所,如正式开馆月余,民众教育馆因馆舍不敷使用,专门呈文教育局,称“查该馆馆舍狭窄,确感不敷应用,经派员实地查勘,认为大成门两旁空屋,稍加修改,尚能切合使用,并与中央规定利用文庙办理社会教育之旨亦相符合,且大成门之名称照院令规定,应在废除之列,修葺利用,更无妨碍之处”。教育局转请工务局施工改造,拟将大成门南向木栅及中间横壁拆除,并于两壁队旗墙壁、装置门墙改建为房屋,以便辟为民众问字处、民众代笔处、民众诊疗室及时事展览室之用。此改造动议,遭到工务局强烈反对而搁浅, “工务局力持保存原有之大成门样式之主张,不允改造,是以所谓大成门者,仍只有屋顶而无墙壁门窗之过路门埭耳,本馆为举办事业计,自未便因噎废食,所有时事展览,遂不得不因陋就简,布置在不蔽风雨之大成门内,致使展览品难于管理,诚莫大之憾事也”。[23]事隔半年,民众教育馆馆长杨佩文提及此事,依然意难平。
民众教育馆的空间塑造主要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通过实现所设定的目标来表达举办宗旨,办理者(馆长、馆员)通过空间布置、事业开展对宗旨进行生动展示。从该馆概况记述可知,该馆主要活动可分为塑造国家与革命精神,实施普遍社会教育如健康展览、巡回文库、改良说书等。就展览室效果记录看,民众教育馆几乎均统计了展览开放以来的参观人数,如“一·二八”战迹展览室半年参观人数为635 342人,健康教育展览室、公民教育展览室开放3个月参观人数分别为388 439、286 249人,而大成殿设的孔庙祭祀礼服陈列所,仅有“开放后,参观者纷至沓来,均欲一睹为快,幸大成殿地位宽大,未见拥轧”的笼统说法,并无详细统计数据。[23]结合民众教育馆对文庙旧有建筑的布局安排,可见其空间塑造 “以教育改造达社会改造”的社会教育功能,以期形成一个共同而明确的精神气质,“大成殿仍是大成殿,魁星阁仍是魁星阁,池沼依旧,树木无恙,而风景却大不相同”。[24]文庙的旧有建筑经此塑造有了“学者”气质:“在文庙公园,不仅使你感到空气的新鲜,他还会告诉你,这是什么花或什么树,属于那一类那一科的,并且,在一·二八纪念室里,你可以见到六百磅的重量炸弹,你可以见到忠勇健儿用铁血换来的种种战利品,你可以见到那些畏死的兽类的护身符,在这里,你会听到卫国健儿悲壮底呼号,在你耳畔重复的喊叫。其他,他会告诉你祀礼的用具和一些普通的卫生常识。”[25]开放的、免费的“文庙公园”变成了上海市民众教育馆的代名词。
三、仪式操演与国家在场
国民党政府建立后,面临着严重的道德重建任务,遂采用“固有的民族道德”来挽救这种“隐世厌世、浪漫颓废”[26],祭祀孔子成为以传统儒家道德来建立新的道德规范、恢复民族自信心的最直接、最有效的仪式。
1934年开始,国民政府重新开始举行孔子诞辰纪念,设在文庙旧址的民众教育馆责无旁贷,自然承担了这个仪式操演,孙中山遗像、党国旗等国民党政党符号,与原本孔庙的儒家传统无缝对接起来,传统空间的现代赋形得到进一步加强,体现出强烈的国家在场。
1934年8月27日,上海市党政机关在民众教育馆大成殿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举行前《申报》曾进行连篇累牍的报道,比如市府将在民教馆举行孔子诞辰纪念、用什么音乐等[27],纪念大会当天更是隆重,“纪念大会会场,设在市立民教馆内大成殿,头门上交悬党旗国旗,上有白布横匾,上书‘本市各界举行先师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字样,殿之正中神龛上,悬挂总理遗像及党国旗,市府特绘之孔子遗像,则供于前面桌上,两旁分列钟鼓琴瑟庙堂之乐,四周壁柱上,满贴标语,殿外搭有临时凉棚,为各界代表席,布置颇为庄严肃穆,原有祀孔彝器,已迁至该馆讲演厅陈列,任人参观,以资观摩”。纪念会议程如下:(1)全体肃立;(2)大同乐会奏中和韶乐;(3)唱党歌;(4)向党国旗、总理遗像及孔子遗像行三鞠躬礼;(5)主席恭读总理遗嘱;(6)主席吴铁城报告纪念孔子意义;(7)童行白、潘公展演说;(8)公安局奏乐;(9)礼成。[28]本次纪念大会计到各界代表1 000余人,市党部童行白、市长吴铁城为会议主席,全市各机关团体、学校及工厂各休假一天。
无论市长吴铁城、市党部代表童行白,还是市教育局局长潘公展,他们在孔子诞辰纪念大会上的发言基调均着力阐述三民主义与孔子道义的内在切合性。吴铁城认为,“国民党奉行三民主义,三民主义是总理革命思想的结晶,总理的革命思想,固然很多激发于现代的科学,然蕴育于中国固有文化者也很多……我们可以说孔子是集古代的大成,而总理是集古今中外的大成,因此我们要完成中国国民革命,我们必须实行三民主义,而要实行三民主义,必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必要尊崇孔子。今日之尊崇孔子,并非复古,也不是崇拜偶像,今日之尊孔,乃是谋民族之复兴”,宣传孔子学说的时代精神。潘公展将孔子的民族精神与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对接,“纪念孔子诞辰,必须要纪念孔子那种民族的精神……孔子的精神,是‘攘夷狄’,攘夷狄就是孔子学说的结晶,也就是总理的民族主义,攘夷狄又可做复仇的解释,顾今日纪念孔子,应有复仇的精神”。[28]以孔子学说来攀附复仇,激发民众应对强敌的信心和勇气。在仪式中,突出世俗党国的价值取向,文庙“圣域”传统被刻意消解。
借助纪念孔子诞辰的仪式,新生活运动亦攀附进来而被大力宣传。“蒋委员长提倡新生活运动,亦是根据旧礼教,出发点是礼义廉耻,现在国家的毛病很多,就是大家思想没有标准,没有重心,没有中心信仰。孔子可以说是表率人物,要按他的言行去做,拿他的言行统一意志,形成全国的思想中心。”[29]很明显,纪念活动中,孙中山被作为当时中国政治文化的符号象征,彰显国民政府的统治合法性,借纪念孔子来宣传国民党的政治主张,宣传新生活运动,集体仪式背后隐含着国民党政治权力的渗透与运作,体现的是意识形态如何被创造、被传播,在宏大的集体仪式中,不仅完成了“对历史文化的认同”,还达到了“政治上的认同”。延亘千年的孔子诞辰祭祀,悄然换上了国民政府倡导的新道德的“芯”。
文庙作为上海市标识性很强的建筑,市党政机关充分利用了大成殿的独特空间,头门上交悬党旗国旗,神龛上悬挂总理遗像、党国旗等空间符号,与神桌上放置的孔子遗像一起,一段隐喻之旅引导着孔子诞辰集体仪式的整个过程。其中政府明确将党国意志、革命话语附加在文庙场域,从纪念对象上看,由原来孔子及先贤先儒变成了党旗国旗、总理遗像和孔子遗像,作为纪念主角的孔子被排在了第三位;而整个典礼议程完全套用“现代礼仪”:用唱党歌、向党国旗总理遗像及孔子遗像行三鞠躬礼、恭读总理遗嘱和主席报告、演讲等现代集会的程序,代替了“迎神、初献、亚献、终献、撤馔、送神”等传统祭孔仪式,大力宣扬孙中山符号,孙中山已超越孔子而居于祭孔仪式空间的中心位置。从典礼到仪式、内容都被纳入国民党党化的轨道,孙中山作为政党符号和三民主义的政党意识,贯穿在整个孔子诞辰活动中,祭祀先师孔子的文庙仪典的回归不过是“旧瓶装新酒”,并非儒家信仰在社会层面的复活与地方传统士绅的话语权回归,文庙曾有的相对独立的“道统”更多演变成了象征意义。国家权力利用仪式呈现和发扬“固有之道德”的社会政治形象,充满韵律和生动象征的党歌替代了一咏三叹的孔子赞歌,有效地营造了一个富含时代感、满含民族自豪感的国家团结情感和氛围。
政府通过恢复孔子诞辰纪念来重新诠释儒家文化,并将之镶嵌到民族国家、三民主义、新生活运动等时髦话语中。对于文庙空间秩序的部分回归,在赢得遗老遗少情感的同时,也引起社会人士的担忧:“该馆并为推广民众的见识将原来珍藏在洒扫局的祀孔器服在孔子庙开放‘祀孔彝器陈列所’,现在,这些祭器、祭服、乐器、舞器,不再仅仅乎展览,而要真的用得着了。那民众教育馆,也许就在不久将来仍旧变回神圣的文庙吧。”[30]各式精英之所以支持民众教育馆的象征性重建,为民众呈现一个祭祀先师孔子诞辰的盛大场面,是出于回应儒学衰微、国内各界对移植来的“新式教育”指责增多以及为国民政府提供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形象的需要。换言之,他们理解并深深相信纪念孔子诞辰集体仪式的力量,它有助于为国民政府的社会结构提供情感支持,既安抚了那些对儒学留恋的“遗老遗少”,同时,通过把这些仪式和想象中的儒家文化主导、曾经强盛的中华帝国历史联系在一起,试图唤起了民众的国家认同。
福柯认为“空间是权力运作的基础”[31],空间布局作为政治权力付诸实践的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空间如何定位,相应会氤氲不同的政治氛围。文庙作为一种有广泛民间基础的固态文化存在,作为一种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威权空间,国民政府非常重视,假址于此的民众教育馆更是通过用党国旗、总理遗像等进行内部布局以及相应的集体仪式操演等来实现其空间的现代重构。
上海市教育局之所以能在新任市长张群支持下取得压倒性胜利,在于国民政府将文庙园林化以便民众娱乐的同时,更期望将之塑造成社会教育的平台,成为“唤起民众”“改造社会”的凭借,将文庙全面改建为民众教育馆便是最佳方案。
任何一个空间的命名都是一种观念、意识对空间进行控制的体现,孔庙、贡院、关帝庙、钟鼓楼等具有政治和文化象征含义的建筑群被改设为民众教育馆,其本身就是对原有空间意义的重构,反映出政府对空间新生意义的强调。在文盲率高达80%的民国时期,普通民众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了解孙中山,理解国民政府政策规定,很大程度上与设在传统或新式的公共空间的民众教育馆有很大关系,民众在潜移默化的状态下形成关于孙中山、三民主义及国民党的集体记忆。民众教育馆作为社会教育的综合机关,作为党治主义象征、话语宣传与实践的空间展示场域,改变了原有的物理性空间状态,成为承载意识霸权的异质空间,在塑造现代新型国民中扮演了重要作用。国民政府利用这些传统公共空间改设社会教育机关,不仅是一种经济选择,更是政府意志在空间重构中的体现。国民党通过传统公共空间更名和改建,将党旗国旗、总理遗像等政党符码镶嵌其中,增添各种时髦游艺项目,设立各式展览室,通过开展种类多样的活动,将社会教育机关打造成一个大众化、免费的公共空间,实现国家权力渗透方式的转变。
当然,在文庙公园、民众教育馆等社会教育机关的定位上,精英与民众之间一直存在着明显差异,政府和知识精英期望这些由传统空间重组的社会教育机关成为教化民众、塑造国民的场所,寓教育于娱乐,而实际上民众对此并不能完全认同。一方面,他们会受到党旗国旗、总理遗像所营造的政党符号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这个免费的“文庙公园”有“学者”气息;但另一方面又不会全然接受,他们依然以自己的方式在民众教育馆、公园活动。鉴于政府对文庙建筑的保护和传统士绅的坚持,由文庙改设的民众教育馆内部空间与布置发生变化,但依然庙宇高耸,大成殿里依然陈列了雕刻精美的孔子像及其从祀弟子、历代先贤,棂星门、魁星阁等依然巍峨,“我们一行六个人,先瞻仰孔圣暨诸贤神座,无不肃然起敬意”。[32]特别是1934年国民政府恢复祭祀先师孔子诞辰后,在一般民众心目中,文庙俨然再次恢复到原来儒学圣殿地位,“进门先见魁星阁,大门口三架石牌坊。小假山,小池塘,小凉亭,小桥梁,小小景致小地方,钟鼓高架多威显,大成殿阁居中央。先师神位高高供,名贤排列在两旁”。[33]只不过由原来的“闲人免进”变成了免费游览、“白衣人也可游泮水”的”“公园文庙”而已。无论社会教育机关如何努力对传统空间来进行空间重构,但在普通民众观念中,传统空间的象征意义仍没有多少改变,棂星门、魁星阁、大成殿等传统建筑依然是昔日祭祀先师孔子的符号,对假址于此的民众教育馆举行的教育活动没有多少情感认同。政府的制度设计与民众情感接受之间存在着缝隙和张力。这一方面的问题,在传统空间改组的社会教育机关中普遍存在,值得进一步关注。
注 释:
① 法国记忆社会学家Pierro Nora(皮埃尔·诺拉)、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南京大学教授陈蕴茜等研究成果尤具代表性。诺拉对法国“记忆的场所”进行了大量研究,特别探讨了纪念性空间具有回溯性、前瞻性双重功能,前者主要是唤起民众对该类教育空间的固有记忆,后者则通过纪念空间的布置营造,将民众旧有的记忆与未来设想相互勾连,从而让民众通过参观、参与纪念空间而获得理解认同,从而适应未来的发展趋势,特别强调公共性纪念场所作为“记忆的界质”对社会记忆的影响;安德森认为,近代国家之所以能形成“想象的共同体”,就是因为人们拥有共同的记忆,而提供这些记忆资源的载体之一就是纪念空间,这些纪念空间以不同的形式讲述或呈现相同的故事逐渐演变成民众的集体记忆,为民族和国家提供认同的资源;陈蕴茜教授考察了中山公园、中山陵等空间建构,揭示了总理遗像等作为国民党政府符号的广泛应用。具体详见:Hue-Tam Ho Tai,Pierre Nora and France National Memory,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Vol.106.No.3.Jun.2001,pp.906-922;[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睿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3页;陈蕴茜:《空间重组与孙中山崇拜——以民国时期中山公园为中心的考察》,《史林》2006年第1期;《国家权力与近代中国城市空间重构》,《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② 详见周慧梅:《民众教育馆馆舍的教育意蕴》,《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9年第2期;《社会秩序与政府职责:以北平市第二民众教育馆附设影院风波为中心》,《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6年第6期;《集体仪式与国家认同:以山西省立民众教育馆为考察中心》,《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
③ 张国鹏:《政权与信仰变革下的民国文庙——以上海文庙为考察中心》(1911—1934),南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中国近现代史方向,2016;张国鹏:《民国时期的上海文庙改制》,《中国文化研究》,2020年夏之卷。
④ 详见:《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Q215-1-8090,藏于上海市档案馆。
⑤ 详见:《呈为响应沪南公园建议将文庙开辟公园请求核准事》,《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Q215-1-8090,藏于上海市档案馆。
⑥ 详见:《文庙改建公园抑改为民众教育馆清核示呈悉仰查照原案办理由》,《上海市工务局有关民众教育馆文书》,Q215-1-8251,藏于上海市档案馆。
⑦ 详见:《为陈明文庙公园经费业已制定的款拟仍照原案办理由》,《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Q215-1-8090,藏于上海市档案馆。
⑧ 详见:《为函请迅将拟建文庙公园内民众教育馆设备计划拟送过局俾便进行由》,《上海市工务局有关民众教育馆文书》,Q215-1-8251,藏于上海市档案馆;《为陈明文庙公园经费业已制定的款拟仍照原案办理由》,《上海市工务局关于文庙整理文书》,Q215-1-8090,藏于上海市档案馆。
⑨ 鉴于各地孔庙财产处理颇多争执,三部会衔发布孔庙保管办法,其中第二条提到“孔庙财产,均应拨充各地方办理教育文化事业之经费,不得移作他用”;第四条规定“孔庙房屋,应有各该保管孔庙之教育行政机关及时修缮,其原有之大成殿,仍应供奉孔子遗像,于孔子诞辰开会纪念”;第五条“孔庙地址应充分利用,以办理学校,或图书馆民众学校等”。这一政策出台,为教育局利用文庙办理社会教育提供了政策依据。详见:《教财内三部公布孔庙保管法》,《申报》,1929-03-07,第10版。
⑩ 详见:《上海特别市市政府训令第1310号》,《上海工务局有关民众教育馆文书》,Q215-1-8251,藏于上海市档案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