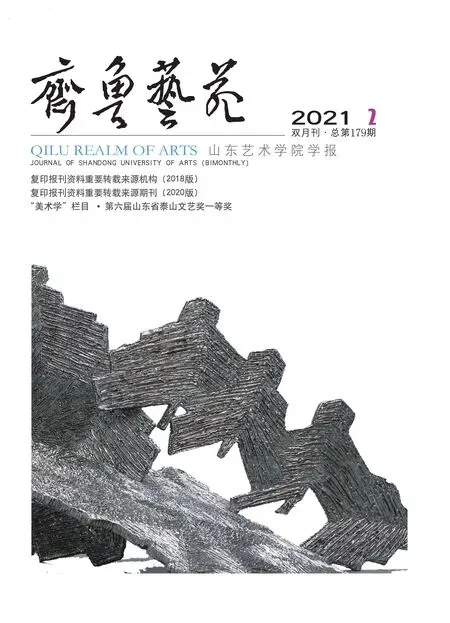吕温《乐出虚赋》中乐“象”问题的美学思考
2021-12-02张高宁
张高宁
(上海音乐学院音乐学系,上海 200031)
吕温是中唐时期的文学家、政治家、思想家,其家学深厚,自小饱受儒家文化熏陶,文化素养极高,其文章被刘禹锡所称赞:“文苑振金声,循良冠百城,不知今史氏,何处列君名”。《乐出虚赋》是其众多文章之中的一篇赋,载于《文苑英华》。从文学角度来说,此赋的成就并不算高,然而从中国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角度而言,其对音乐之“象”特征的讨论,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时至今日,其中所涉及的对于音乐之“象”的论述也值得深入探讨。
本文试从《乐出虚赋》中所涉及到的关于音乐之“象”的论述进行分析,通过对音乐之“象”的思考,探索《乐出虚赋》中音乐之“象”的美学内涵及其审美体验。
一、解读乐赋
《乐出虚赋》篇幅不长,按照其行文逻辑,可大致划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吕温道出了音乐之“象”的基本状态及其基本的音乐本体观念。
《乐出虚赋》开篇曰“和而出者乐之情,虚而应者物之声”,吕氏认为和谐地表现出来的是音乐之中的情感,而从虚空之中做出反应的是乐器的声音,只有“去默归喧”“从无入有”,才能奏得理想的音乐。音乐“因妙有而来,向无间而至”,吕氏反复提出了一个观点,即认为音乐产生于虚空之中,是“无中生有”,从寂静中发迹,不知为何,不知如何,所谓“虚”“妙有”“寂寂”“玄关”“方寸”,都很好的表现出其神秘的性质。而这正是吕氏的音乐本体观:他认为音乐是神秘不可知,来源于无形虚空之中,奥妙只在“方寸”之中。随后他又提出“于是淡以无倪,留而不滞。有非象之象,生无际之际”,这是对来自虚空之音乐的评价,吕氏认为这音乐静而不止,恬淡和气,有并非实像之像,在那看不到边际的边际……。对音乐源起及其玄妙的论述,正是他音乐本体观的最好体现,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老子》第一章)[1](P1),吕氏正是用这种递进否定的方式阐释了音乐之“象”的基本特征。需要注意的是,吕氏在阐述了音乐“空虚无滞”的寂静本质后,进一步为我们理解这种音乐观念进行了解释。“故圣人取象于物,观民以风。辟嗜欲之由塞,决形神之未通”,通过“取象于物”“观民以风”,使得欲望满足、形神相同,在此,“象”与“物”、“形”与“神”都成为两个层级的概念,当由“物”至“象”、“形神”想通后,便出现了“与吹万而皆唱”的“可听”的音乐。这种认识观念涉及中国传统文人的审美趣味及思考方式,他们不只注意到现实生活的世界,更注意到精神的世界。他们抱有一种超越的心态,不满足于对物象的表面阐释,而是寻求上升到精神层面的“神”,追求得意之“象”,正如我们古人对于技与道的追求,我们不满足于形而下的技,只有超乎技,入乎道,才能算是真正的得道者。而此时,“虚空无滞”“妙有而来”的不可言说的音乐,也正是寻求一种如此的阐释方式。
第二部分则是对之前所呈现问题的一种思考与升华,既然音乐“从无入有”“妙有而来”“根乎寂寂”“有非象之象,生无际之际”,自虚空中来,无所不至,又不知何以至,因而讨论音乐如何于虚空之中产生并如何与作为欣赏者的人建立联系尤为重要,故而此部分提出“是故实其想而道升,窒其空而声蔽”,充分表明了从虚空之中所产生的音乐,需要充分发挥想象,通过想象,音乐之“象”才能作为一种审美经验深入人心。之后则是对音乐经由想象获得实际功能性特征的论述:“波腾悦豫,风行于有道之年;派别宫商,雷动于无为之世,杳杳徐徐,周流六虚”。而如此音乐则“如是则薰然泄泄,将生于象罔”,表明了他对于音乐本质的认识。
可见,《乐出虚赋》中关于音乐之“象”的美学观念,一方面包含着对于音乐本体与音乐本质的认识,另一方面其认识方式和认识观又体现出他对于音乐的审美经验和美学理想。吕温的根本观点就在于认为音乐之“象”来源于“虚”,涉及的是音乐本体观的虚实之论,而他提出的音乐经验要依靠审美想象,则涉及到了音乐的审美经验问题与接受问题,最终将音乐与“象罔”联系起来,道出了其对于音乐本质的根本认识,因此,吕氏《乐出虚赋》中音乐之“象”的美学内涵,无外乎包含在“象”“虚”“音乐想象”“象罔”这几个核心概念的内涵延伸及其相互关系之中。
二、音乐之“象”
从字义上看,关于“象”,《周易·系辞》有言“象也者像也”“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2](P543)《韩非子·解老篇》有明确的解释:“人希见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图以想其生也,故诸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今‘道’虽不可得闻见,圣人执其功以处见其形,故曰‘无状之状,无物之象’”。[3](P52)前者“象”为动词,有模仿、摹拟之意,而后者则是以借大象稀少罕见,只能得其象骨,并通过“想”来重现“象”的故事来喻“道”,以至于“以意想者皆谓之‘象’也”。当人的思维进入到构建“大象”的逻辑之中,此“象”便具有了形象、形式等意思。可见,“象”是中国古老的一种认识方式、审美范畴,根据它的不同词性,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进行音乐之“象”的分析:
首先,“象”作为模仿、摹拟之意时,其“比类”之意在中国音乐美学思想中体现出来,人们通过物形、动作和一定实践进程的再现来认识音乐,可以说是一种最早的对音乐进行的“比类”。如在孔子之前,就有史伯对音乐与天、人、社会万物之间“同构”关系的认识;《吕氏春秋》中时空统一、包罗万象的宇宙系统图式,则是将五音十二律与五时十二月,与五方、五色、五味及其相应的自然及人事的变化、活动相联系,这也是比类的一种具体体现;儒家音乐美学思想则是更多的将音乐与政治、道德相互比附,其“礼乐”思想正是以乐“比德”“象德”的具体体现。汉代诸家之间相互结合,形成兼采法、道的新道家、统摄法、道的新儒家,皆带有浓厚的阴阳五行色彩,以致发展为谶纬神学。在这种文化趋势下,音乐与天、道德之间的联系更为密切,以音乐类比阴阳、五行、十二支干,形成了复杂、牵强、神秘的音乐观,《新语》《新书》《淮南子》《乐记》《汉书》等等皆是如此。马融的《长笛赋》中,在其听笛声悠悠之后写到“尔乃听声类型,状似流水,又象飞鸿”[4](P437),将长笛之乐声“类”为流水淌淌,飞鸿渐渐,其意在比类,但却营造出了立体的音乐境象,其描述过程是比类,其形成结果却是第二种角度的音乐之“形象”。所以说当类比、模仿之“象”经由审美想象,脱离了原始的道德比附,而是试图构建出音乐的形“象”时,其具备的审美意味显然更浓。
从第二种角度看,“乐象”这一概念早期在《荀子·乐论》中被提及,“声乐之象;鼓大丽,钟统实……故鼓似天,钟似地”[5](P180)。蔡仲德先生指出“其‘象’并非艺术加工的产物,而指钟鼓等乐器所发音响的状态、相貌,所以还不是艺术之‘像’”[6](P627)。但很明确的是,这里的钟鼓乐之“象”,是指形象。钟与鼓作为天地之象征物,当钟鼓齐鸣时所显现出的原始磅礴气象,便是乐的“形象”。蔡仲德先生虽说此处之“象”并非艺术加工的产物,但是经由天地钟鼓而鸣发的乐象,本身就具备了鬼斧神工的艺术造诣,是非艺术加工,却具备艺术张力。同时,音乐之“象”作为艺术之“象”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艺术自觉的过程,也是审美意识自觉的过程;《老子·十四章》说“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恍惚”[7](P30),《二十一章》又说“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8](P44),则是将“象”与“道”联系起来,以“象”喻道,这里的“象”,其本该具备的形象是无法言喻的,只能作为对“道”的一种描绘,这种解释方式,对我们理解《乐出虚赋》中所谓“有非象之象,生无际之际”的音乐之“象”含义有着重要意义,并可以看出后者深受前者的影响;而集儒家音乐美学思想之大成的《乐记》中提到的“声者,乐之象也”[9](P285),实际上是探讨了音乐表现手段的特征,认为声音是音乐的表现手段,这里的“象”,显然也具备“形象化”的特征,作为声音这一基本素材只有通过“文采节奏”之饰才能成为“乐”,才能成为有“意”之“象”,成为艺术之“象”。
通过两个角度的分析比较,我们可以看出,《乐出虚赋》中“有非象之象,生无际之际”的音乐之“象”,应属于第二个角度。是对音乐“形象”的描绘,这种描绘同老子对于道之描述“惟恍惟惚”“恍兮惚兮”[10](P44)有异曲同工之妙。他没有直接告诉人们“道”是什么、音乐之“象”是什么,而是用形而上学的“负”的方法,告诉大家其不是什么,然后让人们自行领悟,这也是中国美学中极富特色之处。《乐出虚赋》指出音乐之“象”,是“取像于物”而来,但是不占空间,不在目前,存在于“无际之际”,并非实在之形象,所以称为“非象之象”,是“象”外之“象”。而这种看似虚无飘渺的描绘,对于只能闻其声,却看不见、摸不着的音乐艺术来说,在当时无疑是相当合理的一种认识,体现了古人对于音乐现象的一种朴素又富有意味的思考。
三、乐从“虚”来
《乐出虚赋》中反复强调音乐来自虚空,“虚而应者物之声”“因妙有而来”“根乎寂寂”等意思皆是如此,故而“虚”在这里对于理解音乐之“象”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顷,音声相和,前后相随”[11](P4)这些相辅相成的范畴一样,虚与实也是长久以来被相对而论的一对审美范畴,在此我们主要对“虚”的内涵进行探讨。顾名思义,“虚”作为一种审美范畴,应是一种玄之又玄且不可说、冥冥之中的非客观存在,是一种抽象的、需要感性思维来体会的“意味”。从词源考析来看,《说文解字》将“虚”字列入丘部,“虚,大丘也。昆仑谓之昆仑虚。古者九夫为井,四井为邑,四邑为丘。丘谓之虚。”[12](P242),《康熙字典》中除“丘”义之外,另有“虚”“孤”“水”之义。可见,“虚”字含有中国传统美学的“阴性”特征,“更加倾向于道家哲学”[13]。而对于“虚”这一范畴的探究,我们除了在一向主张“致虚极,守静笃”的老庄思想中找到契合点之外,更可以追溯到魏晋玄学的发展。玄学是魏晋时期开始流行的一种崇尚老庄的思潮。玄学在早期道家思想的基础上更加广泛地吸取了时代的精神特征,形成了道家文化的新发展,其基本特征是略具体而深究抽象,也可以说是道家之学的一种新的表现方式,故又有新道家之称。“在其理论上表现为‘有无’‘本末’之论,目的是在于论证名教与自然的统一”[14](P256),文人士大夫对于现实的不满,企图性归山野,却又为凡世杂务所束缚,既不得全性逍遥,又不愿安居庙堂,在这种矛盾下,人们企图寻求两者之中的平衡统一,而玄学所谈“重虚”“重远”“重求之不得”,满足了脱离生产实践的上层阶级的精神追求,形成了终日谈玄的社会风气,越是神秘不可得,越是百思不得解,越是“惚兮恍兮”越能刺激到他们那已不再对世俗事物敏感的审美神经。故而玄学的形成和盛行如同一针兴奋剂,虽然不利于唯物元气说的进一步发展,但无疑以其玄而又玄、离奇深奥、妙不可言的表现方式,形成了中国传统美学中极为瑰丽的独特审美韵味,对音乐、绘画等各类艺术的理论发展也形成了深刻的影响,形成了对“象外之象”“味外之味”的追求、探讨。《乐出虚赋》完成于中唐,魏晋的哲理思辨精神早已融入到新的时代风潮中。佛教的兴盛,形成了儒、释、道三足鼎立、互相制约又互相发展的局面,而佛理中“不可说”的要义,“谐无声之乐,以自得为和”(《全晋文》)[15](P593)的主张,另如《金刚经》中大量极具辩证性的句偈“如来说:世界,非世界,是名世界”;“如来说:三十二相,即是非相,是名三十二相”[16](P77),对于《乐出虚赋》的“虚空”音乐观,从其重“空”“虚”的精神内涵来看,很难说不受到影响。另外,从宏观的审美意识的发展角度来讲,正如人们常谈的意境产生的三个阶段:“庄孕其胎,玄促其生,禅助其成”[17],唐朝佛教文化繁荣,吕温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而这也正是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时期,在这一特定的时期,国家内忧外患,佛教的出世观点一定程度上对当时的文人阶层产生了影响。现实世界的不稳定使人们转向语言所不能及的思维深处,不可见、不可说、却可听的音乐成为了玄理延伸的对象。通过这种思考,我们可以对“虚”有如此理解,即前面所说从审美角度而言,魏晋以来,有重“虚”不重“实”的审美倾向,重“虚”则有“得意忘言”之趣味,虽未说出音乐到底来自何处,却能使人意会到音乐的“玄妙”体验,更加使人倾慕于音乐的神秘而向往之,符合当时的审美趣味,使人们能够接受。
可见,音乐来源于“虚”与用形而上学的“负”的方法谈论音乐之形象实际是相辅相成的,前者是在通过“不可知”追求“玄而又玄”的审美体验,后者同样是以“象外之象”“物外之物”“际外之际”去尝试描绘无影无形的音乐之“象”,两者共同形成了《乐出虚赋》的音乐本体审美观。
四、“象”由“想”出
上文解释了音乐之“象”本身的基本逻辑内涵及其来源于“虚”的本体观念,这是《乐出虚赋》前部分所呈现出来的基本内容,而在《乐出虚赋》后半部分中,他提出“是故实其想而道升,窒其空而声蔽”,则是将玄妙不可得的音乐玄学逐渐转为具有实际功能性趣味的音乐思考。
吕温认为音乐之“象”的产生酝酿,必须要通过自由的想象,也只有通过想象才能使来自虚空的音乐不至于流于虚空。吕氏认识到音乐的“空虚”本质,所以强调经人的主体能动作用,充分发挥人作为审美主体的想象力,在欣赏此“根乎寂寂”的音乐时能够将自己的主观情感、想象付之于音乐之上,从而使音乐具有了人文“意义”,达到其所谓的“道升”。在此,音乐从虚空无尽之中通过人的想象,与社会、国家产生了联系,音乐的实用性趣味开始出现:
“波腾悦豫,风行于有道之年;派别商宫,雷动于无为之世。杳杳徐徐,周流六虚。信阗尔于始寂,乃哗然而戒初。铿锵于百姓之心,于斯已矣;鼓舞于一人之德,知彼何如。是则垂其仁,有其实,乐因之祖述;究其形,实其质,声因之洞出。”[18](P574)
当音乐从虚空之中进入到人间,经由想象获得“人文意义”,就能在百姓之中广为流传,增强他们的信心,宣扬彼此间的美德。从这里也可以看出,《乐出虚赋》在音乐本体观念上深受佛道影响,但是在音乐的功能性认识上还是以儒家的“入世”思想为根基,强调音乐的社会功能,彰显出“以文化乐”的中国音乐传统。
同时,此处针对于音乐之“象”的想象,涉及到了音乐审美的心理特征,在《庄子·大宗师》中,“游心乎天地之一气”所表达的就是——审美离不开“想象”,“游心”即指自由想象,也涉及到了艺术审美的心理特征,表明无论是庄子还是吕温,都深刻的认识到了艺术的特殊性,而音乐艺术其所具备的非实体性、时空流动性,以及表现手段的不确定性,也使音乐审美成为一种超功利而自由,“是感觉、知觉、感情、理智、想象诸因素的交融,是以渗透理性的感情与想象达到主客一体,物我同一,‘无言而心说’的境界”[19](P174)。如此,“有非象之象,生无际之际”的音乐之象,于想象之中散发,才能“波腾悦豫,风行于有道之年;派别商宫,雷动于无为之世。杳杳徐徐,周流六虚。”,成为乐之典范。
五、归于“象罔”
《乐出虚赋》最后所述“如是则熏然泄泄,将生于象罔”,是整篇乐赋的总结,其关键在于“象罔”二字。“象罔”取自《庄子·天地》“黄帝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望,还归,遗其玄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离朱索之而不得,使吃诟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20](P197)这个故事以“玄珠”喻“道”,以“知”“离朱”“吃诟”“象罔”四个虚拟形象比喻四种不同的求“道”方式。前三者分别代表明善于思虑者、察秋毫者、聪而善辨者,他们三人求“珠”(道)却不得,而“象罔”却求得,那么“象罔”为何物?关于“象罔”的含义,郭庆藩注:“象罔者,若有形,若无形,故曰眸而得之。即形求之不得,去形求之不得也”[21](P5),吕惠卿注:“象则非无,罔则非有,不皎不昧,玄珠之所以得也”[22](P113),王先谦集解引宣云曰:“似有象而实无,盖无心之谓。”[23](P116)。通过历代大家的注释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象罔”是一种不可言说、没有确定形式、若有若无、似象非象的范畴,其本身就是一个独立的矛盾体,正如前文所述“有非象之象,生无际之际”一样,是对音乐本质特征的描绘。
但是,我们还要注意到,“象罔”与前面所论述的音乐来源于“虚”的认识有一定的不同,“象罔”作为一个矛盾统一体,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种阴阳和合、无所不包的概念。吕氏最后将音乐归于“象罔”,极可能是音乐在本体特性及其功能特性上恰好包括了两个上下维度的视野,在其本体性质上,音乐体现出“象罔”中的“无”之意,而在其功能性特征上,音乐则体现出“有”的内涵,依此理解,吕氏将音乐的本质归于“象罔”是一种较为客观、理性的认识。
六、结语——乐“象”之美
对于《乐出虚赋》中所论述的玄而又玄的“音乐之象”本体观念的审美体验到底是以什么样的方式进行的呢?《中国美学思想史》中指出:“玄则有味生。淡味,指的是审美感受的一种多层次的深厚境界”[24](P257),这种“味”从最早的饮食感官等直接的审美味感不断地锐化、深化,逐渐向内心体味转移,这是以“玄理的抽象化掉具体的五行,将五色五声从五味的黏连中剥离出来,而且也将‘道’的体味与具体的养生气化分解开来,从而使味成了对本体的体验玩味,成为离具象的理性穷尽,并进一步移入理性的审美”[25](P257)。可见,在魏晋玄学、佛教禅理的影响下,“有非象之象,生无际之际”的音乐之“象”,有了合理的思想基础.。而我们所进行的审美体验,正是在此思想基础上进行的,这种审美体验方式正如千百年来文人雅士对象外、言外、笔外、音外之情、理、含蓄之美的不懈追求、不断玩味一样,形成了独特的中国意味的审美特点。而这种方式正是在继承中国传统审美方式的基础上,对传统审美范畴在当时时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下进行“切实际”的“感同身受”体验,就如同“玄则有味生”,以这种方式去体验那种玄之又玄、无法言明的独特审美韵味。
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注意到,吕氏对于音乐之“象”的论述,在具体的逻辑上是十分清晰的,其音乐本体观有着较为合理的思想内涵,并非局限于不可言说的审美范式。吕氏在澄清其具有玄学意味的音乐本体观后,毫不犹豫地肯定了音乐经由人的想象而与现实社会产生的关联,所以,音乐之“象”,正在于其“象罔”之本体特性上,一方面具有乐之起源于“虚”的形而上气质,另一方面也是指其与现实社会交融后所具备的形而下之社会、道德属性。儒道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互相吸收融合的特点,在《乐出虚赋》对于音乐之“象”的论述中深刻的体现出来。
中国音乐美学作为中国美学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进行研究的方法论上应该大胆借鉴后者,特别是中国传统音乐美学因其自身所具有的特殊性——保存音响少之匮乏,以至对其音乐思想的美学剖析缺少可靠的音响资料,而恰恰在中国美学学科语言中,形态化的审美范畴能够对传统音乐美学思想的文字表述进行有效互补,从而通过一种文学性的、哲学性、感性的方式,并结合当时时代的风潮与传承的特点,对音乐美学问题进行综合性的探析。
本文通过对《乐出虚赋》中“虚”“象罔”等重要范畴的审美分析,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述音乐之“象”的音乐美学内涵,同时,也对如何进行这种审美体验做出了一定的思考。通过分析,我们可以看出,《乐出虚赋》中对于音乐之“象”的论述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它是在多种思想文化背景共同作用下形成的独特的音乐“观”,是中国古代为数不多的从正面论述音乐之“象”的文章,其中的许多范畴都值得用审美的眼光来对待。同时,我们要积极认识到《乐出虚赋》的当代价值,如《乐出虚赋》对于音乐本质来源于“虚”的认识,十分符合音乐本身的特点,音乐美学家苏珊·朗格曾认为,音乐存在于时间的幻象之中,这似乎与吕氏“妙有而来,向无间而至”的音乐观点有着某种相似性。可见,《乐出虚赋》中对于“乐象”的论述不仅对于探讨中国历史文化语境中的音乐本质、音乐本源问题十分的重要,而且也对当代音乐哲学观念中对音乐本质的思考有所启发,同时,《乐出虚赋》中进一步延伸出来的要求发挥音乐想象力、音乐功能性的特征对进一步拓宽中国音乐创作中的思想性、文化性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值得进行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