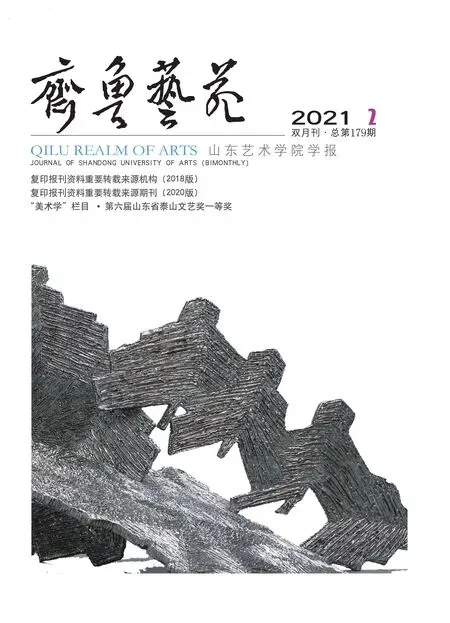“献礼片”形态的承续与超越
——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
2021-12-02宋法刚
宋法刚
(山东艺术学院传媒学院,山东 济南 250300)
作为2019年国庆档的现象级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不仅创下了主旋律电影的诸多票房纪录,更以自身对历史情境的还原与书写,直接荡起了观众内心的时光记忆、民族自豪与家国情怀,也使其引发的话题传播热议事件,成为一次具有共振意味的集体狂欢。该片由7位各具创作风格且富有市场经验的导演分别制作,以开国大典、原子弹爆炸成功、女排奥运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开幕、神州载人飞船返航以及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等7个历史高光时刻为线索,全景式地呈现出一幅“新中国”发展历程的壮美画卷。值得一提的是,影片脱去了宏大叙事的窠臼,转而以小人物的视角进行情节构设,使得个体在总体历史面前的动然一瞬,悉数跃然于银幕之上,使观众之“我”与影片人物之“我”形成指涉、互为观照。奋战一线的工程师、默默无闻的研究者、活泼可爱的小男孩、一丝不苟的护旗手、幽默风趣的出租车司机、无私奉献的扶贫办主任以及英姿飒爽的替补飞行员等平民英雄,使原本触不可及的历史,瞬间幻化成一种可供触碰的共有记忆。最终,影片以31.14亿的超高票房挺进国产电影票房榜单,成为当之无愧的“主旋律”电影星空图谱中的灿烂“北斗”,而“七星”方阵的制作方式,也为电影工业体系化构建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一条更为明晰的路径。
一、“命题性”与“能动性”:工业体系下的规划与协调
正如电影理论家约翰·霍华德·劳逊所言:“一部影片是由一系列的章节组成的,这些章节是有明确的界限的”[1](P379)。在电影工业体系中,策划作为整个环节的起始键和核心源,是整部电影章节中的绪论。尽管策划的重要性无需赘述,但“主旋律”电影的策划难度却值得一提。通观此类电影的创作之路不难发现,一部分影片汇入传记式人物书写的洪流之内;一部分影片则沉入历史节点的宏大叙事之中。在此创作语境下,大量的相似创意与叙事雷同使得观众观之乏善可陈。另外,作为夹杂典型意识形态特征的影片,主旋律电影企图“在特定历史社会语境中塑造自我和他人”[2](P76),具有鲜明的说教性与导向性,而这些特性在多元文化泛滥的当下时代,就显得古板而生硬。正是如此,策划一档别出心裁的“主旋律”影片,便显得尤为必要,但在必要之下却尽是难以抽离的桎梏与枷锁。作为一部集锦式的作品,《我和我的祖国》无法脱离策划这一核心存在而各自独立完成的创作,但它并未陷入窠臼之内,而是接下了“主旋律”电影的接力棒,成为工业美学下极具规划与协调的一曲奏鸣。
黄建新导演作为《我和我的祖国》的总制片人,实际上握有了影片的指挥棒。作为《我和我的祖国》的总制片人,黄建新曾经提到,7个导演拍摄7个历史瞬间的念头“是他和总导演陈凯歌在2018年10月接到相关主管部门的通知后,反复思考讨论,才商议出来最适合这部影片的呈现方式”。作为“作品等身”的导演,黄建新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与资源,因此在协调影片的过程中显得措置裕如。另外,随着《建国大业》《建党伟业》《建军大业》等献礼“主旋律”电影的相继问世,黄建新也摸索出了涉及“主旋律”电影的创作观念,即通过演员资源的整合,扩大影片影响力,以实现生产与消费的对接。在此种观念之上,黄建新也考虑通过导演资源整合的方式,实现“主旋律”电影的进一步突围。尽管这种方法史无前例,但却得以更为有效地调动起了不同导演的创作能力与激情,更能借导演票房号召力的东风,实现宣发效应的最大化。另外,这样的呈现方式,实际上与“新中国”70周年大庆的节点休戚相关,黄建新直言:“70年,7个导演拍,7和70,挺有意思的,这个想法就出来了。”
与演员的整合有所出入,导演的主观能动性更强,自身的风格特征亦是难以抹杀。因此,黄建新等人在筹备之初,便“用了两个月的时间选择题材”,寻找了策划团队来进行选材,选出了二三十个具有“历史瞬间、全民记忆、迎头相撞”[3](P69-76)的创作理念”的选题,其中包括了航空母舰、汶川地震、南方洪水等重大事件。在众多事件中,黄建新等人认为事件之间应该存在时间存续的关系,确立一个明确的时间线,并以此串成一段中国70年的心灵史。黄建新指出:“7和70这个概念,得统一,差不多10年一个,有的稍微跨度长一点,(这样能)代表不同的时期”。在具体规划和特殊设置的拉动下,不同风格的导演,通过内部规范与斟酌讨论,建立起一条与核心相符却各自成节的创作链条。
二、“小人物”与“大历史”:产业经验与文化价值的完美对接
电影工业美学的体系既强调电影的工业属性,又主张电影的美学价值。因此,电影工业美学否认大规模的批量生产,但并不否认经验复制所带来的创作动能与美学价值。换言之,电影工业美学也如同“工艺美术运动”一般,是一种强调“大量的、经济的制造物品,而又无损于创造性和美质的手段”[4](P187)。《我和我的祖国》的创作,实际上也与电影工业美学所强调的经验复制休戚相关。具体而言,7位导演所惯常使用的叙事策略,实际上与该片中“小人物”与“大历史”的笔调相统一。
总制片人黄建新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代表人物,创作出一系列反映时代小人物的影片,如《黑炮事件》《站直啰别趴下》《背靠背脸对脸》等。实际上,黄建新的早期创作,吻合了“第五代”导演整体的创作观念与改革开放初期的文化新风。在特殊的时代语境之下,从历史拉入个体、将个体指代历史,成为常有人走的路。另外,黄建新监制的“主旋律”影片《投名状》作为蝉联金像、金马的双料最佳,同样是以“小人物”与“大历史”相勾连的方式,进行叙事的。除了总制片人黄建新以外,《我和我的祖国》的总导演陈凯歌,同样出身于“第五代”导演,经典之作《霸王别姬》,同样是将“小人物”与“大历史”进行关联,使人物命运与时代进程环环相扣。除“第五代”导演以外,张一白、徐峥、管虎、薛晓路、宁浩、文牧野等几位导演,皆擅长拍摄具有“小人物”色彩的影片,对于相关人物描摹与刻画的把握了如指掌。因此,以“小人物”与“大历史”相结合的《我和我的祖国》,可以说是工业美学流程下经验复制的产物。
尽管如此,影片实际上更是一次历史的必然选择。可以说,“小人物”与“大历史”相结合的方式,既是当下市场的需要,也是时代文化的主流。文化这种“贯穿了所有的社会实践,是它们相互之间关系的总括”[5](P53)因子,无时无刻不流动在创作者周围,使之成为创作内容的缩影与模板。放眼于当今社会,被放大的“超级英雄”已经不再是观众趋之若鹜的对象,而与观众互为观照的小人物,反而更能撩拨到彼此的心弦。值得一提的是,电影创作中所展现出来的工业美学价值,实际上建立在创作者对于市场与文化的把握与洞察之上。换言之,作为工业而言的艺术“商品”,更加不能弃时代语境而独自逆旅。
《我和我的祖国》中的“小人物”,涵盖了工程师、科研工作者、学乒乓球的小孩、护旗手、出租车司机、退休的扶贫办主任、飞行员等。他们在特殊的历史节点上挥毫一转,成为“大历史”的牺牲/奉献者:工程师牺牲了家庭,完成了开国大典中电动升旗的使命;科研工作者牺牲了爱情,实现了第一次原子弹爆炸的成功;乒乓少年牺牲了懵懂的初恋,完成了为邻里播放女排夺冠节目的任务;护旗手战胜了自我,实现了分毫不差的使命;出租车司机放弃了看开幕式的机会,转而为少年圆梦;扶贫办主任拿自己救命的钱,换来了两位少年的成长;飞行员放弃了亲自参加阅兵仪式的机会,为队友保驾护航。他们作为角色被观众凝视,又作为普通的个体让观众投射,成为观众“建立起二次认同的他者”[6](P43)。在建立起认同之后,观众也随角色进行转变,成为勇于战胜自己的工程师、放下面子收获力量的出租车司机以及收获乒乓球梦的少年。剧中角色的成长,不仅使得观众“从这种与悦人的一致性和完满性的幻觉中获得快感”[7](P92),更使得他们直接成为成长中的个体。
毫无疑问,“作为一种创意文化产业,电影一方面能创造票房即经济价值,另一方面则还能创造符号价值或象征价值,即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8](P7-15)。《我和我的祖国》正是借产业经验完成了内容生产,又实现了文化产业属性和文化社会属性的完美对接。黄建新强调:“每10年都会为重要节日拍一些电影”。 实际上,这种献礼式的作品不仅迎合了“我和我的祖国”的个体情绪、民族情绪,更成为党员教育“不忘初心”活动的优质内容。
三、“老导演”与“新导演”:资源合力下的百花齐鸣
美学离不开风格的研究,工业美学亦不丢失对于风格的考量。风格即是作品因于内而浮于外的整体面貌,它是艺术创作者成熟的天然标志。这部由7位年龄各异、特色各迥的导演共同完成的影片,凝聚着第五代导演、第六代导演及新一代导演们对于历史的不同侧写方式和独成一脉的创作风格特征。尽管整部影片都围绕着大历史中的小人物,但创作者所选择的表达方式却不尽相同。可以说,7位导演以独特的亮相方式,完成了影片的集锦式创作。因此,7位导演风格上的碰撞,也成为该片值得书写的关键之所在。
首先,第五代、第六代导演的作品,在《我和我的祖国》中直接“对垒”。《白昼流星》的导演陈凯歌,作为第五代导演的佼佼者,创作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佳作。《白昼流星》同样能看出导演身上鲜明的风格气质,即历史与个体命运融合的叙事特征以及环境大于个体的叙事结构。换言之,《白昼流星》中的人,不再是孤立的个体,而直接成为群体的特殊指代。与第五代导演的寓言性言说不同,第六代导演则表现出了浓郁的个体化意志。《前夜》的导演管虎,堪称第六代导演中的怪才,其作品兼具个性化的叙事特征以及商业化的创作思维。在《前夜》中,这种风格特征继续延续,使得工程师的昨昔与今日、各岗位工作人员的妥协与互助、迫在眉睫的“快”与危难之时的“慢”相互碰撞。另外,极具商业洞察力的管虎,在作品的处理上幽默风趣、犀利生动,因此,《前夜》也在人文关怀精神的基础上,带有鲜明的戏剧张力。
其次,擅长拍摄商业类型片,尤其是爱情片的两位导演“狭路”相逢。《相遇》的导演张一白擅长描摹城市男女的鲜活爱情,同样的,《相遇》亦是两个城市青年,从邂逅相恋到因故分离,再到公车相遇的故事。当男青年再度遇到久违的爱人,喋喋不休与只字不提、追忆的渴望与眼神的扑朔、奔放的追逐与怯懦的回避,集中在一个景深长镜头之下,显得激情有力。与激情流露的张一白不同,薛晓路在《回归》中显得温情十足。以爱情片《北京遇上西雅图》成名的导演薛晓路,擅长描摹人物内心情感,其导演的《回归》,便在这一点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当具有不同身份特征的个体,保证回归“一秒不差”之时,个体内心的情感追溯,也彻底建立完成。
最后,因共同制作一部影片而结缘的三位导演,也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各显“神通”。2018年上映的《我不是药神》,彻底让新人导演文牧野家喻户晓,而其背后的两位监制——宁浩、徐峥,也同样成为被人称道的前辈典范。《我和我的祖国》也让原本一盘棋上的三人,各自独立、尽显神通。《北京你好》的导演宁浩,擅长描摹草根人物的形象,其作品带有鲜明的黑色幽默气质以及荒诞的生命体验意味。在《北京你好》中,这些典型的风格特征,借出租车司机这一形象,生动地诠释出来。《夺冠》的导演徐峥,属于演而优则导,但其作品以小人物为着力点,通过诙谐幽默的内容推动叙事。在影片《夺冠》中,冬冬的可爱与懵懂、上海弄堂的市井气与烟火味、冬冬的情愫与夺冠的激情,都成为牵动观众心弦的所在。文牧野导演的《护航》,则展现出了其在“类型化”制作上的天分,女飞行员过去与现在的坚守、爱情与事业的取舍、个人与集体的抉择,十分震颤人心。
面对当下电影危机以及影视产业寒冬,中国导演放弃了风格之争等诸多争议,转而进行合作抱团。这种合作像是一种朋友间的握手言和,但更是创作者对中国电影市场的高度认知,对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深度认同下做出的选择。
四、“短视频”与“大制作”:“快时代”下的影像潮流
电影工业美学强调契合时代、应时而作。这是工业体系中作品创造于人、服务于人、回馈于人的回环锁链中,所形成的天然场域。尽管在这条工业体系中,创造者创造的是一系列非实体的“文化经济的商品”,但这些“商品”也成为“意义和快感的促发者”[9](P31)。因此,创作者便不可忽视受众群体的整体期待和现实渴望。在互联网时代,“短”便是这种整体期待和现实渴望的集中显现。随着“电脑和手机的功能逐渐趋同”[10](P726),视频的碎片化倾向已经成为大势所趋,人们更希冀利用碎片时间观看碎片视频,从而更为高效地满足自身的收视需要。在此情景下,短片的制作,便更加贴近了受众的观看需求、顺应了时代的影像潮流。《我和我的祖国》尽管是一个整体一致、单珠成串的集锦,但仍旧可以分割为7部各自成篇的沧海独珠。这与早年具有段落结构特征的《爱情麻辣烫》《万有引力》等影片不同,它不再是“形散神不散”的文字游戏,也不是通过结构性处理后的情节拼凑,而是几个故事各自独立成篇的精彩合集。这样的短片合集,通过大银幕的方式呈现出来,不仅对于故事的讲述时间,加以重新的界定,更对电影的时间长度,进行了大胆的尝试与突破。值得一提的是,时间的改变,必定带来一系列电影元素的改变。
实际上,每一个故事以短片的形式出现,观众可以直观的感受到创作者对于这一选题的情节压缩。如《相遇》实际上大大压缩了方敏这一角色的前史,而将方敏与高远的爱情凝聚在公交车上的长镜头之中;《白昼流星》压缩了少年成长的转合,以至于使得米利埃主教式的救赎与观看飞船返航的心灵重建稍显断层。压缩是创作过程中一次迫不得已的时间重组,但随着剧情的压缩,高潮跌宕的情节也演变为短片美学的一大倾向:在短片《前夜》中,一晃而过的个体、今夕前夕的对照、家庭与事业的取舍,都紧凑而连贯的一笔带过,成为“国”之背后的点点繁星;在短片《回归》中,升旗手朱涛、女港警莲姐、外交官安文斌、修表匠华哥,也指代了一个又一个身份各异的群体,成为你我虽各异,心愿却相联的“回家”礼赞;在短片《北京你好》中,一张奥运会开幕式门票,链接了两段父子的情感,成为情感救赎路上的通行证。这些情节性的压缩与强化,实际上极大程度地服务于短片美学的创作之路,成为银幕新形式的一次集体展望。
另外,短片的形式,实际上也为工业内容的产业化之路,提供了一条路径。毕竟,合则一团火、分则满天星的集锦方式,直接便于影片进行二度传播,即通过网络形式,实现整合传播的同时,也实现了各自的碎片化传播。影片《我和我的祖国》一经撤档,便于爱奇艺、腾讯、优酷等诸多网络门户上架,在超高票房的天顶之下,迎来了网播热度的又一春。值得一提的是,分段化播放、抑或取舍式观看,成为该片的一大观影选择,这也极大地迎合了网络播放空间的个性化设置。
尽管影片以短片集锦的形式呈现给观众,但却并不同于以往的短片产业格局,表现出了“大制作”的一面。《我和我的祖国》由华夏电影主控投资,华谊兄弟、文投控股、万达电影、金逸影视、华策影视等公司联合出品。尽管华谊兄弟一直不便于告知该片的具体投资金额,但高配置的制作团队、逼真的历史场面、高能的摄制安排以及精准的服、化、道设置,都体现出该片精益求精的追求,宣告了本片的“大制作”格局。在“主旋律”献礼大片的旗帜下,诸多具有顶级流量的明星倾情加入,选择“零片酬”参演。这样一来,在整个工业流程中,原本占投资比例极高的支出内容转变为零,使其他内容增加成本并以此提高产品质量。换言之,这一举措使得各投资公司的投资金额大幅度侧重于影片制作,电影质量也获得了显著提升。值得一提的是,7部影片中制作难度最大的《前夜》,更是直接表现出规模足、场面大的创作格局,整部短片不仅外景全部采用特效,更是组织了大量的演员参与、游走在画面之中,以制造开国前夜的兴奋状态。其他6部影片,虽然在难度上不比《前夜》,但也倾尽了创作者的全力。在这样的大制作模式下,《我和我的祖国》在国庆档一路高歌猛进,上映首日便累计票房2.44亿元,36小时更是突破5亿元的票房大关,最终收获了31.14亿元的票房佳绩。
五、“分工化”与“合流化”:产业形态下的探索与优配
“进入新世纪后,‘文化产业’成为中国的国家文化发展战略,电影又与‘文化创意产业’连在了一起。”[11](P7-15)实际上,产业的完善,离不开电影从生产到营销的各个环节,它意味着无论最初的创意、策划阶段,还是最后的宣传、营销阶段,都是电影工业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合环节。电影工业美学的实现,离不开创作者的分工与合作,甚至可以说,脱离了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共赢约定与互助原则,便不足以称之为“工业美学”。换言之,合作是建立工业系统的基础,共赢是实现工业流程的公约。在《我和我的祖国》中,分工的细化更是远大于一般,它不仅要求各链条的具体分工得当,更囊括了7组风格鲜明而具有不同经验的组合。
在具体的导演主创选择上,作为总导演的陈凯歌率先被选中,成为整部电影的领头羊。作为总制片人的黄建新,原本有执导一部影片的可能,但他考虑到自己作为总制片人,需要完成具体的制片工作,因此便把这一位置空了出来。黄建新与陈凯歌等人一同,在一份长长的导演备选名单中,筛选出其余6位导演。黄建新指出:“有的导演在戏上不能过来,有的还有某些别的事情,最终就落在了这7位导演身上。这7位导演都挺高兴,欣然接受。”通过最初策划的内容,7位导演选择了自己乐于且擅长的故事,并分头同总制片人黄建新以及总导演陈凯歌细谈自己对于这一题材的构想、故事的安排以及人物的设置。7位导演再根据具体的构想,寻找合适的编剧,配合自己完成故事的创造。正是由于这种分段、分层的工业化创作方法,使得7个电影剧本皆于春节期间顺利提交。
在具体的故事创作完成后,接下来的影片拍摄制作环节便显得尤为重要。尽管7部影片仅是时长在20分钟到30分钟区间内的短片,但使用一个剧组线性、连续的拍摄,却显得耗时耗力。因此,黄建新并未考虑一个组“连拍”或者两个组“分拍”的传统创作模式,而是采用更具工业化形态的分头制片方式加以创作。实际上,分头制片的策略,不仅减少剧组与导演之间的磨合期,直接地缩短拍摄时间,更能有效地调动7位导演,选择适合自身且相对高效的拍摄队伍。对于总制片黄建新而言,7个剧组分头制作对于导演而言是释放,对于自己而言更是松绑。在这样的调整与设置下,7个剧组分别设置了相应的制片人,且这些制片人皆是导演惯常的合作伙伴,譬如《前夜》的制片人朱文玖是管虎的老搭档,同管虎合作过《斗牛》《杀生》《老炮儿》等作品;《夺冠》的制片人刘瑞芳、陶虹亦是徐峥的合作伙伴,同徐峥合作过《港囧》《我不是药神》等作。在这样的具体分配之下,黄建新只需要对各组的制片人进行管理,完成统筹制片。正是由于流水线式的分工方式,使得《我和我的祖国》的制片于管理而言更具协调,于制作而言更具效率。
尽管该片显现出“分工化”的工业倾向,但也表现出“合流化”的工业流程。实际上,两者之间并非是非此即彼的,而是互为协同的表里。首先,该片的“合”体现在风格上。在以往的电影中,工业美学的合作流程往往是通过导演、编剧、摄影、后期等各部门的协调加以实现的。与之不同的是,集合了7位导演创作的《我和我的祖国》,在合作的流程上便显得更具复杂性。换言之,创作者为了“和”而采取了折中、“平均”的处理方式,这也正与电影工业美学所强调的“大众化,‘平均的’,不那么鼓励和凸显个人风格的美学”[12](P32-43)相一致。
在《我和我的祖国》中,整部影片都在“追求塑造的就是伟大历史瞬间中发挥价值的普通人”[13](P69-76),这也是影片一致性的起点。另外,在宏大叙事和个人叙事之间寻找契合之处,也是创作中不可规避的难题。影片选择了几个相对典型的范式,使7部影片得以在形式上具有相似性。其中,最为典型的是《我和我的祖国》通篇都借助历史素材,打开了真实与虚构间的一扇窗。在《前夜》中,影片的首尾段落,通过相关的历史纪录片和新闻素材,使得观众从虚构的剧情中,建立起真实的观念。值得一提的是,在开国大典上,林治远走向人群、伫立于毛主席身后的素材,是通过修复旧素材并再度着色、抠图成像所形成。我们也随着演员黄渤的走进而真正身临到那段激动人心的历史高光时刻之中。在影片《相遇》中,导演同样借助真实素材建立具有真实感的历史语境,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画面出现在方敏与高远之间,个体的情感与国家的荣辱瞬间建立起了直接的关系,高远的牺牲变得愈加伟大。在影片《夺冠》中,女排比赛的素材,作为第二叙事时空,直接牵连着冬冬的悲喜,它也同紧张、刺激的冬冬“战场”,形成了超越空间的共振。《回归》中香港回归现场的真实素材、《北京你好》中的奥运会开幕式素材、《白昼流星》中的宇航员真实参与素材以及《护航》中的阅兵式素材无不如是。
其次,《我和我的祖国》还表现出了资源上的“合”。早在《建国大业》《建军大业》《建党伟业》等献礼片上映之际,观众便大呼“数星星”。所谓“数星星”,即一语双关地交代了影片中出现的明星庞大,多如繁星。作为总制片人的黄建新,在此次影片中更是纠集了一众演员、明星进行参演,明星数量高达50余人。其中,黄渤、张译、吴京、杜江、葛优、刘昊然、陈飞宇、宋佳、王千源、任素汐、马伊琍、朱一龙、佟丽娅等一众演员,更是极具票房号召力的一时之选。可以说,这样的集合,极大程度上利用了明星的人气,通过明星效应与粉丝经济的完美搭桥,加大电影的宣传力度。总制片人更是集合了最具影响力的7位导演,集合创造力的优势,使得整部影片呈现出群星荟萃的观感,并引之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这也是“主旋律”电影,特别是“献礼片”的价值之所在。更值得一提的是,随着7位导演的介入,颇具经验的制作团队,也纷纷加入其中。可以说,影片在整合导演资源的时候,同时整合了导演的粉丝和人脉,整合了宣发资源。
最后,影片同样在营销与宣发环节,表现出集体发力、共振的事势。影片由统一的发行团队进行统筹发行,其中包括华夏电影发行有限责任公司、联瑞(上海)影业有限公司、上海猫眼影业有限公司、新丽电影发行团队、五洲电影发行有限公司以及北京光线影业有限公司、上海淘票票影视文化有限公司等经验丰富的发行团队。在营销上同样如是,该片由北京果然影视文化有限公司、霍尔果斯青春光线影业有限公司、EPK制作、斐然传播集团等团队联合营销,共创未播先火的氛围。各营销公司在网络平台上不仅抢占了话题,更是凭借精心制作的预告片,让中国影迷热血沸腾。与此同时,凭借《我和我的祖国》熟悉的旋律,以王菲特有嗓音演唱的同名主题曲MV,更是成为宣传中的焦点。除此之外,“表白祖国”的线下活动,作为产业链条中的一部分,同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功效。
结语:全案整合评估及对中国“主旋律”电影未来发展的思考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华诞,2019年度的国产“主旋律”电影既不缺乏数量,又实现了质量的飞跃。在娱乐大片横行的时代下,国产“主旋律”电影不遗余力地发挥着自身的宣传与教育使命,实现了传递文化自信、发扬文化自觉的总体目标。值得一提的是,该年度的国产“主旋律”电影表现出整体高票房的走向,而《我和我的祖国》更是以31.14亿的总票房成绩脱颖而出,伴随着国庆70周年的激情时刻,显得余味绵长。《我和我的祖国》可以说是一次“主旋律”电影的突围,透过这次突围,我们也不难发现,“主旋律”电影的创作之路并非独木一条。《我和我的祖国》既是“命题性”与“能动性”协调下的结果,又以“小人物”与“大历史”的形式,完成了产业经验与文化价值的完美对接,它还通过“老导演”与“新导演”的同台演绎的方式,展现出资源合力下的百花齐鸣,它是“短时代”的产物,又是“大制作”的体现。最为重要的是,它通过“分工化”与“合流化”的搭建,彰显了产业形态下的探索与优配。总而言之,《我和我的祖国》契合了电影工业美学的发展之路,用聚合之火点燃了满天繁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