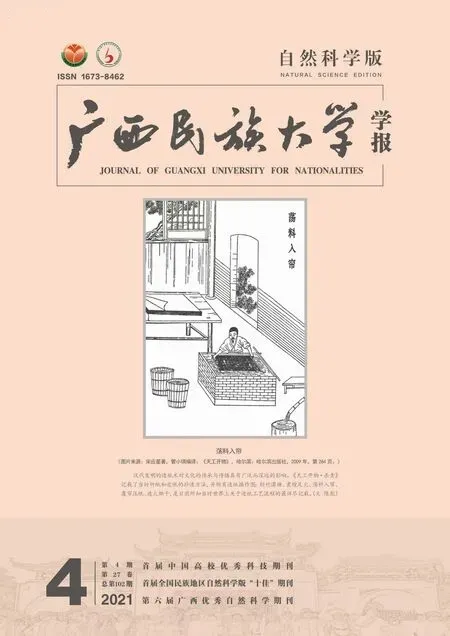《淮南子》“气”的宇宙生成论与浑天说*
2021-12-01张怡哲孙小淳
张怡哲,孙小淳
(中国科学院大学 人文学院,北京 100049)
0 引言
中国古代的宇宙论思想以浑天说、盖天说和宣夜说等理论为核心,其中关于浑天说与盖天说之间的争论历来为学界所关注。在研究浑天说及盖天说的形成过程中,《淮南子》是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它成书于公元前140 年左右,是由淮南王刘安组织编写的一部总结先秦及汉初思想文化的综合性著作。其中有关宇宙论的学说,既有与盖天说相关的记录,又有与浑天说相近的思想,学界对此有很多争论。持盖天说的学者认为,《淮南子·天文训》中通过圭表测影计算天地的大小,且以“千里差一寸”为基本假设,所反映的天地结构与《周髀算经》一致。①贺圣迪和石云里认为《淮南子》是《周髀算经》盖天说体系的直接先导。因为《淮南子·天文训》中用圭表测量天高方法表明了两点,一是天地是两个相互平行的平面;二是天地间的距离以及太阳的运动的范围都是有限的,皆可通过科学的方法加以测量和研究。而这两点恰恰也是《周髀算经》的立足点。[1]陈广忠也持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淮南子》是用盖天说的理论来解释日月五星和二十八宿的分布与运动的。[2]与此相反,金祖孟、吕子方等学者则认为《淮南子》中有体现浑天说的思想。金祖孟认为浑天说是一种天圆地平说,《淮南子》所描述的地面是一个圆形的平面,其上还有“旸谷”和“虞渊”供太阳出入,这些特点都符合浑天说的特征。[3]吕子方提出《淮南子》中已建立了一套初步的、但是比较完整且系统的浑天说理论。落下闳在此基础上,做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以实物的形式将天的形状、日月运行等天象展现出来,从而奠定了浑天说理论的基础。[4]席泽宗认为《淮南子》关于二十八宿宿度的记录暗含着浑仪在战国时期或已出现。[5]前人的研究已较全面地呈现了《淮南子》与浑天说、盖天说之间的诸多关联,但是大多仅关注与天文计算相关的宇宙结构论,忽视了《淮南子》宇宙生成论思想中所展现的天地结构。
东汉张衡在《浑天仪注》中对浑天说的天地结构给出了经典的表达:“浑天如鸡子,天体圆如弹丸,地如鸡子中黄,孤居于内。天大而地小,天之包地,犹壳之裹黄。”[6]3对于张衡此说中的大地究竟是球体还是平面,人们历来存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天为球体,包裹着大地,天大而地小是浑天说的核心特征。盖天说有平天说、《周髀算经》盖天说和周髀家盖天说等流派,[7]他们关于《淮南子》的讨论多集中在与《周髀算经》盖天说的关系。《周髀算经》成书于西汉末年或东汉初年。[8]《周髀算经》认为“天如盖笠,地法覆盘”,即天像一顶笠帽,地像一只倒扣的盘子。“北极之下高人所居六万里,旁沱四溃而下。天之中央亦高四旁六万里”。[9]17说明在盖天说理论中,天地是两个分离的平面,天始终在上,地始终在下。由此可见,浑天说与盖天说的主要分歧在于天是否包裹着大地,或者说“日月星辰的周日旋转是否出入地下,也即分歧在于解释天相旋转的方式不同”[10]60。文章以浑天说和盖天说之间的根本分歧出发,考察宇宙生成论和宇宙结构论,审视《淮南子》中“气”演化天地万物的生成论过程,以及在九州八极的具体天地结构中,是否已经展现出圆形天包裹大地、天在外地在内的浑天说的特征。
1 “气”与天地万物的生成
《淮南子》中的宇宙生成论思想主要体现在《天文训》和《原道训》中,其中《天文训》描述了宇宙、天地、万物的具体生成过程。
“天地未形,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故曰太昭。道始于虚廓,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天地之袭精为阴阳,阴阳之专精为四时,四时之散精为万物。积阳之热气生火,火气之精者为日;积阴之寒气为水,水气之精者为月。日月之淫为精者为星辰,天受日月星辰,地受水潦尘埃。”[11]165-167
以此来看,天地万物的生成过程依次为:虚廓—宇宙—气—天地—阴阳分判—四时—万物,这个过程以天地的形成为节点。就天地形成之前的状态而言,整个宇宙都处于无形的“太昭”状态,即天地未形,道之本体还未开显自身的状态,其特点是“冯冯翼翼,洞洞灟灟”,指其幽而能明,浊而能清的特征,这说明道并非虚无,而是一种无形无相的东西。[12]这种无形的道开始在虚廓中开演自身,充满宇宙。宇宙中气的产生,并非产生了一种新的“气”,而是指原本无形无相的气在宇宙中逐渐变得有形有相,即气有清浊。这体现了一种气本原的哲学观,即道由最初的无形之气逐渐形成有形之气。
天地的生成,因气之清浊差异而成为可能。“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在此描述中,天地的形成纯粹是一个物理过程,气的清浊差异促使气向不同方向运动,清阳者先弥散开来而成天,随后重浊者凝滞而为地。由此可演绎出天地的结构,即在天地形成之前唯有气独存,气因清浊差异,以至于运动速度不同,越是清阳之气扩散速度则越快,先层层弥散而形成天,最后重浊之气不容易散开,只能凝聚在一起形成地。“凝滞”一词概括所有,“故天先成而地后定”,此过程自然生成的是天包裹着地、天在外地在内的浑天结构,而不是盖天说主张的“天如盖笠”。有种反对意见认为,地形成后体积重,必然下陷,最终形成天在上、地在下的盖天结构。①笔者在2020 年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学术年会(天文学史分会场)宣读本文后,有学者提出此质疑。这种质疑其实针对的是另一个问题,即天地形成之后,地为何不下坠。《淮南子》中并没有对此做出直接的说明,后文有关“九州八极”天地结构的论述似乎可以间接地回答,所谓八殥、八纮、八极是指不同密度的云气,对于生成过程而言,从最外层的八极到最里层的八殥,气的密度越来越大,层层弥散包裹大地,那么云气则能给予大地浮力而使其不下坠。更直接的解释是在张衡的《浑天仪注》中:“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6]3正是“气”与“水”的浮力使得天地不坠不陷。以此可以发现,从《淮南子》到《浑天仪注》,天在外、地在内的浑天理论在不断完善。
2 《淮南子》与《灵宪》生成论思想比较
《淮南子》以“气”为本原的宇宙生成论和张衡在《灵宪》中的宇宙生成论非常相似。
“太素之前,幽清玄静,寂漠冥默,不可为象,厥中惟虚,厥外惟无。如是者永久焉,斯谓溟涬,盖乃道之根也。道根既建,自无生有。太素始萌,萌而未兆,并气同色,浑沌不分。故《道志》之言云:‘有物浑成,先天地生’其气体固未可得而形,其迟速固未可得而纪也。如是者又永久焉,斯谓庬鸿,盖乃道之干也。道干既育,有物成体。于是元气剖判,刚柔始分,清浊异位。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动以行施,静以合化,堙郁构精,时育庶类,斯谓太元,盖乃道之实也。”[13]3215
《灵宪》将宇宙的生成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为“溟涬”,即道还未显现自身的阶段,此时的道“幽清玄静,寂漠冥默,不可为象,厥中惟虚,厥外惟无”,恰似《天文训》中“冯冯翼翼,洞洞灟灟”的“太昭”,此时天地、阴阳、万物都尚未形成。第二个阶段为“庬鸿”,元气开始萌动,但尚未开始分判。正如《道德经》中所说的“有物浑成,先天地生”。[13]3215在天地还未形成之前,宇宙中就已充满了元气,这与《天文训》中虚廓生宇宙、宇宙生气的阶段一致。第三个阶段为“太原”,也是天地成形的阶段。元气剖判,气因其清浊差异开展不同的运动,天成于外,地定于内。此阶段与《天文训》中“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清妙之合专易,重浊之凝竭难,故天先成而地后定”[11]166相同,二者都认为天地形成以气之清浊为动力机制,只是《灵宪》中则更直接地指出了“天成于外,地定于内”的天地结构。不仅如此,《灵宪》更直接地指出了清阳之气的运动轨迹就是“圆以动”,而浊阴之气“平以静”,其侧重点并非大地是平的,而是与《淮南子》中的“重浊者凝滞而为地”一样,重在突出重浊之气相对于清阳之气而言运动速度极慢,最终凝聚成地。显然,《淮南子》与《灵宪》有密切的关系,只是与《灵宪》相比,《淮南子》的生成论思想更原始一些。[14]8
《淮南子》和《灵宪》中的宇宙生成论也与战国时期楚竹书《恒先》中的“先天地”部分的论述相同。[14]11《恒先》①竹简中“恒先”写为“亘先”,根据李零的注释,“亘”同“恒”,故“亘先”读“恒先”指作为终极的“先”。是道家著作,“恒先”为“道”的别名。《恒先》中的宇宙生成论分为两部分,先是气从无为到有为的过程,见第1 号简:“恒先无有,质、静、虚。质,大质;静,大静; 虚,大虚。自厌不自忍,或作。有或,焉有气;有气,焉有有;有有,焉有始;有始,焉有往者。”[15]288作为本源的“恒先”经历了由寂静到萌动的过程:无有—有或—有气—有有。具体而言,“恒先无有”是指道体本身的特点,即大质、大静、大虚,相当于《天文训》中的“太昭”与《灵宪》中的“溟涬”。“有或”是指有形的气形成之前的状态,相当于《淮南子》中的“虚廓”和《灵宪》中的“庬鸿”,此时元气开始萌动,但尚未开始分判,没有质量上的差异。直到有形之气产生之后,才有“有”,即有万物和时间的开端。《恒先》第4号简则叙述了气因清浊差异而生天地的过程:“浊气生地,清气生天。气信神哉! 芸芸相生,伸盈天地。”[15]291气因清浊差异而生天地的观念正是《淮南子》与《灵宪》生成论思想的核心。由此可以发现,这种生成论思想在古代有很大的影响力,从《恒先》到《淮南子》,再到《灵宪》,“气”生成天地的这一思想在不断地丰富,故而宇宙生成论为浑天说的形成与不断完善奠定了理论基础。
3 气与昼夜、阴阳的关系
“气”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天地生成过程中,而且在解释冬至、夏至日与“阴阳”之间的关系时,《淮南子》仍然突出了“气”的重要性,这使其与《周髀算经》中的盖天说理论存在较大的差异,而与浑天说思想的关联更为紧密。
《周髀算经》是以太阳所在日道的差异来解释冬至、夏至日与阴阳变化的:“故春秋分之日夜分之时,日光所照适至极,阴阳之分等也。冬至、夏至者,日道发敛之所至,昼夜长短之所极。春秋分者,阴阳之修,昼夜之象。昼者阳,夜者阴。”[9]28春秋分日时,日在中衡,昼夜等长;冬至日,日在外衡,昼短夜长。显然,《周髀算经》直接将昼等于阳,夜等于阴,所以一年四季中阴阳变化也就等于昼夜长短变化。阴阳只与太阳运动有关,并无“气”的含义。
《淮南子》在讲述冬至、夏至日与阴阳之气变化的关系时,指出在冬至日时,阴气向北到北极,向下到黄泉。
“日冬至则斗北中绳,阴气极,阳气萌。故曰冬至为德。日夏至则斗南中绳,阳气极,阴气萌,故曰夏至为刑。阴气极则北至北极,下至黄泉,故不可以凿地穿井。万物闭藏,蛰虫首穴,故曰德在室。阳气极,则南至南极,上至朱天,故不可以夷丘上屋。万物蕃息,五谷兆长,故曰德在野。”[11]208-209
黄泉被认为是地下极深之处,也是极阴之地。冬至日是阳气萌发的阶段,古代认为冬至日阳气萌发始于黄泉。如《白虎通·礼乐》云:“《乐记》曰:‘埙,坎音也。管,艮音也。鼓,震音也。弦,离音也。钟,兑音也。柷,乾音也。’埙在十一月,埙之为言熏也,阳气于黄泉之下熏蒸而萌;匏之为言施也,牙也。在十二月,万物始施而牙。”[16]121-122《史记·律书》曰:“十一月也,律中黄钟。黄钟者,阳气踵黄泉而出也。”[17]1085显然,《淮南子》对冬至、夏至与阴阳关系的解释不以太阳运动为标准,而是强调阴阳与“气”的关系,阴阳二气有其特定的生成机制,阳气萌发于黄泉,黄泉为极阴之地,那阳气得以萌发的动力何在?结合上文对《淮南子》生成论思想的阐释,天地的生成就是因为“气有涯垠,清阳者薄靡而为天,重浊者凝滞而为地”。《灵宪》也说:“天成于外,地定于内。天体于阳,故圆以动;地体于阴,故平以静”,换言之,天地本身具有阴阳二气的特性,阳在外,阴在内,这便使阳气从黄泉萌发有了理论基础。显然,《淮南子》对阴阳的认识与其“气”本原的生成论思想一致,如此一来,以天地之间阴阳二气的交感作用来解释节气的变化也就很容易理解。
4 “九州八极”的天地结构
《淮南子》对天地结构的具体描述主要集中在《地形训》中,《地形训》开篇即陈述大地承载的范围。
“墬形之所载,六合之间,四极之内,照之以日月,经之以星辰,纪之以四时,要之以太岁。天地之间,九州八极,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泽有九薮,风有八等,水有六品。”[11]311-312
六合即指四方上下,四方为东西南北,上下则指天地。这是以地平面为观测点所呈现的天地范围,这一范围可用“九州八极”来概括。那么明晰九州与八极具体所指则尤为重要,因为天地大小及结构关系就隐含其中。《地形训》中“九州”延续了邹衍“大九州”的说法,中央翼州即邹衍所说的“赤县神州”:“以为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17]1840《地形训》与此相同,认为大九州之外则为水域,[18]由近到远依次为“八殥”“八泽”“八纮”“八极”,与中央之“九州”共同构成九州八极。
“九州之大,纯方千里。九州之外,乃有八殥,亦方千里……凡八殥八泽之云,是雨九州。八殥之外,而有八纮,亦方千里……凡八纮之气,是出寒暑,以合八正,必以风雨。八纮之外,乃有八极……凡八极之云,是雨天下,八门之风,是节寒暑;八纮、八殥、八泽之云,以雨九州而和中土。”[11]330-336
《地形训》给人们呈现了一个以九州为核心,向外依次为八殥、八纮、八极的环形结构。但是,此环形结构已不是一个平面结构,而是一个立体结构,以九州大地为中心逐渐向天际蔓延。因为从八殥、八纮、八极的云气凝结成雨降于九州大地可知,八殥、八纮、八极并非指大地,而是弥漫在九州大地之外,且层层包裹着大地的云气。若非如此,八极之云又如何雨九州?地居中央,云气将其包裹,就此来看已经是半圆形的天地结构了,若云气可以深入地下,自然就是圆形的天包裹大地的浑天结构了。
事实上,《淮南子》也直接描述了地下的状况,主要通过日月五星的运动来体现。《天文训》云:“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谷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亿万七千三百九里。禹以为朝、昼、昏、夜。”[11]236-237这是对太阳周日视运动的描述,日从旸谷出,最终入于虞渊,日出前,日落后,太阳都是在地平面以下,且可以在水中运行。《地形训》也有类似的表述:“东方川谷之所注,日月之所出。”[11]352这说明在地平面以下有供日月出入的通道。对此,汉代杨雄在其“难盖天八事”中已做了强有力的论证,表明浑天说的理论与实际观测更相符。杨雄在第六难指出:“天至高也,地至卑也,日托天而旋,可谓至高矣。纵人目可夺,水与景不可夺也。今从高山之上,设水平以望日,则日出水平下,影上行,何也?若天体常高,地体常卑,日无出下之理。於是盖天无以对也。”[19]507当我们站在高处观察日出,太阳的位置是在水平面以下,显然盖天说的理论与实际观察相违背。
这种描述符合“气”演化生天地的生成论思想,八极之云气包裹着大地,给予大地以浮力,类似张衡《浑天仪注》中的思想:“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浮。”[6]3自张衡之后,关于“日月如何出入水中”也是历代浑天说理论改进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五代时期的邱光庭对这一问题做了较理想的解答,他认为“日月星辰,并入于水”这个道理是说不通的,所以将其改造为“气之外有天,天周于气,气周于水,水周于地,无天相将,形如鸡卵”。[7]148
由此来看,《淮南子》与《周髀算经》的差异极为明显,《淮南子》以太阳升落解释昼夜变化:“日出于旸谷,入于虞渊”,而地球同时昼夜恰为浑天说的特征。[20]《周髀算经》认为太阳的照射半径与人目所及范围相等,都为167 000里,日出是因太阳运动进入人目所及167 000里的范围内,日落则因太阳移动到人目所及范围之外。对于整个大地的昼夜情况而言,总有一半处于白昼,另一半处于黑夜:“故日运行处极北,北方日中,南方夜半。日在极东,东方日中,西方夜半。日在极南,南方日中,北方夜半。”[9]42正如刘智所描述的盖天说与浑天说的区别:“盖天象笠,极在其中,日月远近,以为晦明;浑仪以天裹地,地载于气,天以回转,而日月出入以为晦明。”[6]12《淮南子》中,地平以下还有供日月出入的通道,日月可以绕到地平之下;而在《周髀算经》中,太阳始终在地面以上,即使太阳运行到最低点,仍要比地面高20 000里,[20]天地始终是分离的,太阳绝不会绕到地下。
5 结语
笔者从宇宙结构论和宇宙生成论两个维度阐释了《淮南子》中的浑天说思想要素。在宇宙生成论上,《淮南子》以“气”的清浊性质差异来解释天地的生成过程,即形成了圆形的天包裹大地,地居其中,天大地小的浑天结构。通过解析《恒先》《灵宪》中的相关内容,可以看出浑天说在宇宙生成论思想方面在不断拓展与完善。就宇宙结构论而言,《淮南子》关于天地之间“九州八极”的叙述展现了层层云气包裹大地的天地结构,结合对地平面以下日月出入水的描述,表明《淮南子》的确已显示出圆形的天包裹大地的浑天结构。对比《淮南子》与《周髀算经》中对昼夜长短的变化与阴阳二气关系的认识,发现二者持有截然不同的解释原则。《周髀算经》中昼夜与阴阳直接对应,太阳运动轨道的变化是其唯一依据。而在《淮南子》中,阴阳有“气”的特性,太阳运动并不是阴阳二气变化的根本原因。
就这两方面内容的关系而言,《淮南子》对天地大小、形态的宇宙结构论解释,是以“气”本原的生成论解释为基础的,结构论是生成论的具体展现,而生成论则是结构论有效的理论基础和活力源泉,二者相互关联展现了《淮南子》中所具有的浑天说雏形,张衡的浑天说思想也包含了这两部分内容。从此也可以窥见中国古代科学更丰富、更复杂的一面,即对自然的观察、预测与解释必然包含了古人关于自然如何生成的形而上的思考。这便启发人们在面对中国古代科学时应持有更开阔的视野,不仅应关注古代科学与当代科学相近的部分,也应阐释其思想背后特有的视角和理论关怀,如此才能揭示中国古代科学的丰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