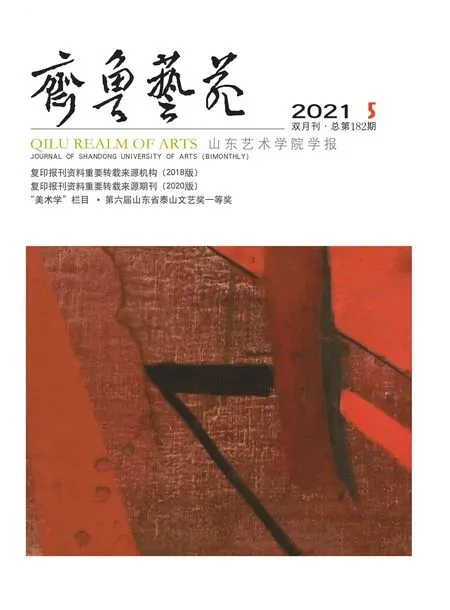从边缘到中心:1930年代左翼电影批评的公共领域分析
——以《申报·电影专刊》的左转与两场笔战为中心
2021-12-01何莹莹
何莹莹
(南京大学文学院,江苏 南京 210046)
《申报》(1872.4-1949.5)作为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且具有广泛社会影响的民办报纸,被称为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百科全书”。《申报》的电影副刊《电影专刊》(1932.11-1935.4)是左翼最重要的赤色电影文化阵地之一,在中国电影发展史上同样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在对《申报》副刊的研究中,学者李欧梵曾借用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理论,通过《申报·自由谈》(以下简称《自由谈》)审视近代中国报纸副刊的“批评空间”。“公共领域”是法兰克福学派学者哈贝马斯在其《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提出的概念。所谓“公共领域”是17、18世纪随市民社会的发展,而逐渐兴起的一种文化场域。人们借助报纸杂志等纸媒,通过沙龙、咖啡馆来传递消息、互相沟通,最终形成一种社会公共舆论,从而形塑民族风格。[1](P2)该理论是基于欧洲18世纪以来英、法、德等国的政治史实,衍演而生的一种理想模式,是有关“现代性”的理论陈述。李欧梵指出,将这一概念硬套到中国社会是不妥当的,他对哈贝马斯学说进行故意“误读”是想借“批评空间”这一概念,探讨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文化问题——自晚清以降,知识分子是如何开创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的?[2](P137-154)基于对《自由谈》“游戏文章”的举例阐释,李欧梵认为当时的报纸副刊继承了梁启超等人所期望的文章的公共性,已“不再是朝廷的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逐渐演变成官场以外的‘社会’声音”[3](P137-154),由此建构了中国近代具有公共领域性质的“批评空间”。在这一思路下,“批评空间”特指一种“文化场域”,表现为知识分子发表言论的平台、尺度与话语空间,打开了反思近代报刊等公共领域的新思路。
李欧梵的讨论始于《自由谈》的创刊(1911.8.24),止于国民党对言论空间的控制。到了1930年代,在内忧外患、审查严格的情况下,报纸副刊要生存已属艰难,要拓展表达空间和话语尺度更是为难。在当时复杂形势中,《申报·电影专刊》(以下简称《电影专刊》)等电影副刊创办了起来,且曾获市场热销,其短暂的蓬勃发展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此外,《电影专刊》作为左翼影评人发表文章的阵地,曾引发多次笔战,衍生出广受讨论的舆论话题,这也是重梳中国电影史的重要问题。本文沿着分析报纸副刊的公共领域的思路,从影评史料出发,重梳《电影专刊》“向左转”的原因,以“凤鹤之争”与“软硬之争”两场舆论争议为抓手,对20世纪30年代左翼影评力量崛起的命题进行再思考。
一、《电影专刊》的转向与左翼话语权的扩大
中国电影批评史上的“报刊影评”的崛起,肇始于左翼电影运动的开展。早期电影批评集中在专门的电影丛刊中进行,国民党掌握着主要话语权。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力求更大程度地掌握文化话语权。电影作为大众文化的产物,有着广泛的受众和影响力,被当时的左翼文艺工作者视作是展开国民教育的重要依托,电影批评也就成了必争之地。为此,“左翼剧联”在1932年7月成立了以共产党人为主的“影评人小组”,主要成员有夏衍、王尘无、石凌鹤、鲁思、舒湮等。中共当时没有自己的公开报刊,左翼文艺工作者的处境极为困难,即使偶尔筹措经费创办了一份电影杂志,仅推出一期就有被当局查禁的风险。与此同时,随着上海电影业的发展,《申报》《晨报》各大报刊都创办了电影副刊。左翼影评人在“电影副刊热”的背景下,很快改变了开展电影运动的策略,积极借助民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的报纸,建立进步电影批评的阵地[4](P72-93)。
(一)话语权争夺:赤色文化阵地的形成
当时《申报》是面向全国发行的最重要的民办报刊之一,在1920-1930年代的销量位居全国首位,受众范围广,主要以商业获利为目的。而且,据鲁思叙述:“申报在当时是一张影响较大的报刊,它的《自由谈》、《本埠增刊》、《星期增刊》和《读书指导》等副刊,是极受广大知识青年们欢迎的。如果从‘文化革命深入’这个角度来看,《电影专刊》的确是值得我们争取的一个文化阵地。”[5](P7)在这些因素的推动下,左翼电影小组开始将力量“渗透”到《电影专刊》中。
《电影专刊》上的栏目包括新片介绍、圈内八卦、影片宣传、电影小说等等,有较强的娱乐属性,以商业利润为目的。从创刊词《百里锣》可以窥见《电影专刊》起初的发文定位,“第一种用意是告诉人家,影戏快要开映了,请大家安静些。第二种用意是借此可以提起观众的精神,并且使他们很愉快的去领略剧情。”[6]初期以宣传影片和解析剧情为主要内容的《电影专刊》没有政治倾向,还曾因日常刊登肉感照片及与电影无关的广告,被评价为一份“矛盾的电影刊物”[7]。但是娱乐内容未能让该刊获得好销量。从边缘地位转变为被读者要求增刊的副刊,真正给《电影专刊》带来蓬勃生机的,恰是1933年集中涌入的左翼供稿群体。作为《电影专刊》的特约撰稿人,凌鹤在回忆文章中自述:“该刊编辑钱某丝毫不干预,这就使我们左翼剧联有了发表言论的园地,自然是大好事情……只要‘电影专刊’在读者中扩大影响,从而使中外影片商人争在他报上刊登大幅广告,大量增加收入,他当然是笑逐颜开了。”[8](P59-61,50)当时的主编钱伯涵并非专门的电影艺术家,报馆资本家以扩大收入为目的,这给了左翼影人占领话语权的机会和宽松的发文环境。凌鹤不但自己刻苦撰文(署顽石、亚夫、丹枫等化名的都是凌鹤的文章),也引荐了许多左翼电影人的稿件,如夏衍用黄子布等笔名发表理论文章,郑伯奇以席耐芳、郑君平等名字发文[9](P59-61,50)。左翼群体通过积极供稿在读者群中树立了威信,迅速将该刊占领为言论阵地。与此同时,《电影专刊》文章更新快,质量较创刊初期有了提升,销量逐渐走好,甚至出现读者要求补报的情况,逐渐改变电影副刊一开始的弱势话语权。得益于影评文章和报纸产业之间紧密的互生性,《电影专刊》焕发生机的同时,左翼电影运动的影响力在社会渗透,左翼的电影批评也越来越成熟。
(二)影响力扩大:左翼影评模式的建构
重梳《电影专刊》会发现,左翼电影批评虽作者众多,但整体文章风格相似、语言浅显易懂。影评文章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翻译介绍苏联、日本等国外电影理论;二是批判国民党的反动电影及其理论以及帝国主义的辱华电影;三是开展“进步影评活动”,扩大左翼电影的影响。其中“进步影评活动”引发的舆论关注较多。对30年代的《歌女红牡丹》《新女性》等进步电影,左翼影评家积极撰稿,高度赞扬其中反映革命立场、民族情感,关怀农民悲惨生活的剧情,进而指引国民思想。在对软性电影、好莱坞电影等“非左翼”电影的评价上,左翼影评人往往从意识形态、技巧层面分别谈论。例如,上海30年代曾有一系列好莱坞“兽片”(以动物作为主题的电影)盛极一时。左翼影评人的一系列文章大都认可“兽片”奇崛的趣味和审美体验,称赞其“形式和技巧的确优秀”,同时猛力批评“兽片”等娱乐片是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文化侵略武器,应当警惕资本主义社会对中国人民斗志的消磨[10]。这种意识形态影评模式占据了当时左翼电影批评的相当一部分版面。随着进步影评运动的发展壮大,左翼影评人阵营越来越壮大,他们常利用友人聚餐、包影院等形式,一起对影片进行口头评论,集思广益形成一致见解,再由几个人执笔成文、集中发表。这是影评力量的整合,能形成更加强烈的社会舆论,往往能够吸引读者关注相关话题,扩大了当时各大电影副刊的影响力,有效开拓了电影批评的文化场域。左翼影评以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思想与革命倾向,在很短的时间内通过报刊影评赢得了广大的读者群体,在电影批评领域夺得相当的话语权。在1933年电影的“软硬之争”出现之前,左翼阵营几乎占据了所有的电影评论舆论阵地,以自己的传播策略占据压倒性的舆论优势。
二、“凤鹤之争”及其未完成的影评“清洗运动”
凌鹤作为特约撰稿人并不属于《申报》的工作人员,这让《电影专刊》免担政治的干系,发文尺度更加灵活。针对副刊的“尺度”问题,《晨报·每日电影》(以下简称《每日电影》)主编姚苏凤与凌鹤之间发生龃龉,引发了“凤鹤之争”。
(一)笔战争端:左翼因阵地制宜的策略
1934年9月15日,姚苏凤编剧的影片《路柳墙花》上映。该片讲述在农村生活不下去的阿毛娘等人到上海讨生活,但没能过上期待的生活,又返回农村的故事。该片上映后不久,凌鹤就在《电影专刊》上发表《评〈路柳墙花〉》,从影片的商业价值、演员表演、导演技巧等方面肯定了该片的成就,文章末尾则从意识形态角度对编剧提出批评,认为编剧没有暴露出社会的黑暗,反而指出了一条错误的、回到农村的路[11]。单就这篇影评来看,凌鹤的评价较为公允。引起笔战的是该文与凌鹤化名“吟秋”发表在《大晚报·星期电影》上的影评《〈路柳墙花〉小言》的对比。《〈路柳墙花〉小言》的基本观点与《评〈路柳墙花〉》无异,肯定艺术技巧而批评回到农村的结尾,批判该片缺乏社会教育意义。不同之处在文章末尾,“吟秋”之文将矛头直指编剧姚苏凤的意识形态问题。“《路柳墙花》的姚苏凤先生聪明得很,他明知农村是无家可归的,可是他却要教她们回到农村去,理由是‘原来上海是这样不清不白的地方’。”[12]姚苏凤被两篇不同态度的影评惹怒。针对“回到农村”这个结尾,姚苏凤已在试片之后吃点心的时候和凌鹤当面解释过,这是电检会命令修改的。凌鹤明明知道实情,却对此加以攻击,这使姚苏凤大为光火。苏凤还在回应中质问凌鹤:其一,凌鹤为何用化名发表不同的影评,两篇影评的标准不一,《申报》上实名写的有讨好制片者之嫌,而“吟秋”之作对剧作者暗放冷箭。其二,凌鹤指出的诸多问题在卜万苍导演的《黄金时代》中也都存在,他却态度悬殊。除了对凌鹤两篇态度不一的影评的不满,该文末尾,姚苏凤总结凌鹤影评的“荒谬”通病:“在凌鹤先生的影评里,所习见的毛病是(一)武断和曲解(二)矛盾(三)避重就轻(四)徇私(五)缺乏常识(六)机械的意识论等等成分的集合。”[13]这一总结看似批判凌鹤的影评,实则点明了当时左翼电影批评的通病。面对苏凤的诘问与批判,凌鹤在《电影专刊》上回应:化名不是问题,姚苏凤先生自己也有许多化名。苏凤虽曾“当面解释”回到乡下去的字幕之故,但观众并不知情,影评当以观众的观感来发表。至于对卜万苍《黄金时代》的批评,凌鹤摘出自己《评〈黄金时代〉》的原文,表明自己同样也进行了较严正的批评。[14]但这些解释未获姚苏凤的信服,双方的矛盾还因几个来回的笔战而加剧了。
至于苏凤的第一个问题,凌鹤为什么要在不同刊物上用不同的批评态度撰写影评?这一点凌鹤没有在笔战中直接回答。从鲁思《影评忆旧》的资料来看:由于《申报》在当时影响较大,《电影专刊》是上海赤色电影文化运动之主要地盘之一,因此凌鹤“因地(阵地)制宜”,为了避免引战而在《电影专刊》上发表较温和的影评,维护该刊的正常运行,而在其他报刊有选择地发表更具有战斗性的批评[15](P7)。这种“因阵地制宜”的策略充分说明了左翼影评人对《电影专刊》的重视,也从侧面反映了左翼电影批评的目的倾向。他们将电影批评作为在公共领域参与现代民族话语建构的武器,为“文化革命的深入”而在不同的平台有组织、有策略地发表文章,彰显了左翼影评群体民族启蒙的意识。
(二)战火蔓延:从泛化讨论到互揭私德
“凤鹤之争”关联的话语场域线索错综,除了二人直接交锋之外,许多影评人与剧作人加入论战,纷至助澜。《影迷周报》1934年第1卷第2期直接以“影评和剧作”为专号出刊,收录相关评论文章。鲁思、舒湮等人从影评人身份参与讨论,从意识形态指责《路柳墙花》对于当时社会情势模糊不清的认识,有“毒害”大众的可能性。随着左翼影评文章的集中发表,对《路柳墙花》的批判形成舆论优势。“剧作人”的相关声援文章较单薄,有被“围剿”之势的姚苏凤在后来的文章中直接揭私德,攻击凌鹤为“小丑式的政客”,指出他妄图控制影评界的野心,号召对影评进行“清洁运动”。[16]
“战火”蔓延后,《影迷周报》专号的第3、4期出现了一些“中间”或“第三方”的观点。梅熹反对调解苏凤与凌鹤之纷争,认为“只有这样热烈的争战才能归纳些东西出来,推动影坛接近真理的东西。”[17]作为姚苏凤在《每日电影》的同事,舒湮在10月4日以《每日电影》编者的名义刊出《结束苏凤、凌鹤间的笔战》,要求双方就此停战,影评清洁运动应“从长计议”[18]。在《影评与剧作之战结论》一文中,佚名作者作了四点总结,第一:凌鹤苏凤此次论争的最重要的真义应该是对电影检查制度的批评;第二,论争双方的激愤态度要不得;第三,影评清洁运动是对的;第四,凌鹤与苏凤都存在公私不分的过错。[19]这一总结直指要害,指出笔战双方的情绪化问题,更重要的对检查制度与电影批评“清洁运动”的反思及对当时文化评论氛围与立场的理性建构却未能完成。
通观“凤鹤之啄”始末,凌鹤所代表的左翼影评人通过集中力量笔战的方式,占领了舆论优势。但是,左翼影评人对苏凤所指出的模式化通病未能加以重视,意识形态式的电影批评,仍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左翼影评主流,这是较大的遗憾。此外,双方在论战白热化的时候,詈骂之声盈篇累犊,“小丑式政客”“软性的淫妇”等揭私德行为和污蔑多见于报端,将争论探讨引向了不良发展的轨道。
(三)争论余绪:《每日电影》的新抉择
原本姚苏凤主编的《每日电影》也是刊登左翼影评的重要电影副刊。从1932年7月创刊以来,洪深等左翼影评人固守《每日电影》这一阵地发表影评。但与凌鹤笔战之后,《每日电影》不得不进行新的选择。日本大阪市立大学的白石(张)新民梳理:“笔战结束不久,围绕苏联电影《循环》的评价问题,姚苏凤又重新向凌鹤开火……之后,左翼人士脱离《每日电影》转入《影谭》。为加强《影谭》的电影舆论界的地位和影响力,《影谭》创刊不久,尘无就以‘离离’的笔名在《影谭》上发表了《上海电影刊物的检讨》,开始贬低《每日电影》。苏凤凌鹤间的笔战使《每日电影》陷入了一种孤立的困境。在孤立无援的处境中,姚苏凤开始重新选择。穆时英的《电影批评底基础问题》一文打破了《每日电影》自《青春线》之后两个多月的沉寂,开始向《影谭》发起进攻。以此为标志,《每日电影》开始倒向‘软性电影’论者一方,成为‘软性电影’论者进攻左翼的主要阵地。”[20](P43-51)经历笔战后,原本在《每日电影》发文活跃的左翼影评人销声匿迹,转向了《影谭》,而处境尴尬的《每日电影》重新抉择,加入与左翼对峙的阵营,加剧了当时“软硬”两大电影批评阵营的冲突。
三、重识“软硬”阵营的冲突与权力话语博弈
“凤鹤之争”是将左翼人士与论敌的影评斗争发展到白热化的标杆性事件,直接导致的《每日电影》的转向,加剧了左翼电影工作者和论敌文化上的交锋。“凤鹤”两大阵营的力量角逐是左翼电影批评话语权逐渐走向上风的标志性公案,若放诸于1930年代电影批评的整体环境中会发现,这既是一个独立事件,也是电影“软硬之争”的阶段性表现,背后是多阶段、多面向的文化场域。
(一)“凤鹤之争”背后多面向的文化场域
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从业人员是“两头小,中间大”的状态。起初,进步的左翼电影居于最少数,30年代大部分电影从业人员还处于中间状态,特别是一些小影视公司。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影坛,多方势力开始不断争夺电影话语权。在30年代,很多“中间”的电影从业人员因资金与阵容薄弱,难以生存和发展,就逐渐向进步力量靠拢。左翼影评的势力逐渐扩大,获得了更多的话语权,逐渐就有了与论敌公开叫板的实力。在“凤鹤之争”登场之前,电影界的“软硬之争”进行得正酣。“凤鹤之争”可以看作是“软硬”电影理论不断碰撞之后表现在具体影片批评实践方面的必然结果。
“软性电影”与“硬性电影”的论争,以1933年3月《现代电影》杂志的创刊为起始标志,以1937年软性电影论者在艺华的制片活动终止为止,前后持续超过三年。“软性电影”概念由黄嘉谟首次提出,强调电影的艺术特性和商业属性,反对左翼影人将政治意识强加于电影而导致其“硬化”的做法。他的观点得到了刘呐鸥、穆时英等新感觉派作家的支持。对应的“硬性电影”论者是以夏衍为代表的左翼电影人士,主张电影应该为表现劳苦大众的生活、表现工人阶级的现实生活服务,应对大众具有教育意义。
客观来看,“软性电影论者”与左翼影评者的争论,实质上是围绕电影的传统“载道”功能与现代“休闲娱乐”功能所展开的创作观念的冲突。强调电影娱乐功能的“软性电影论者”表现了与当时作为国际大都市的上海相适应的现代大众文化精神,而左翼电影批评家坚守着启蒙的立场,认为电影应有教育意义,应如实地反映当下社会的现状,揭示出社会问题并推动社会的进步。这场论争从现阶段中国电影的讨论开始,很快就转移其他话题上,包括作为艺术形式的电影的功用和影评人的任务等。就论争结果而言,从相当数量的报章文章,可以窥见其中出离意识形态博弈的文化场域的冲突,包括对进步电影、娱乐电影等多种电影观念的解读,对电影技巧的认知等等。
(二)左翼阵营的舆论建构与争论的意义
对于电影的表现主体,左翼影评人认为电影是大众化的,其“大众”的含义是广大的无产阶级,尤其喜好写“劳苦大众”“天明”“奋斗”等题材的电影。软性电影论者认为左翼影片存在着公式化、概念化倾向,指出这种只重内容而轻形式与技术的表现,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形式主义。
对于电影的功能,左翼电影批评家主张把教育大众与反映现实结合起来,影片应如实反应社会现实并教育大众革命思想,号召群众投身到救亡图存的斗争中去。软性电影论者认为电影应以娱乐为重,电影应“充实着戏剧给予人生的原有素质,是值得欣赏的艺术影片,是会使大众快乐的高尚影片”[21];是“给眼睛吃的冰淇淋,给心灵坐的沙发椅”[22]这种趣味主义、娱乐至上的电影观;是对电影教化功能的反对。
对于电影的技巧性,左翼电影工作者践行的是内容与形式相结合的电影批评,运用内容与形式的相结合的一元观点,分析帝国主义电影、软性电影理论以至中国新生电影,达到揭露帝国主义电影实质的目的。而软性电影论者重点指出当时的左翼电影缺乏完整的形式和内容,对技巧有一定的要求。左翼电影批评家认为软性电影论者思想不合时宜,不符合民众高涨的反帝爱国情绪。
从以上三方面内容展开,左翼影评工作者和论敌围绕着电影的本质、功能目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以及电影批评的标准等问题展开了论辩,形成二元对垒的舆论态势。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影响,当前难以对两场论战的“输赢”下一个清晰的结论。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一些软性电影的影评人似乎在当时占了上风,进入了明星、联华公司,取代了一些左翼电影人的位置。但左翼影评人被更广大的知识分子基础所支持,在很长一段时间有较强的号召力,是真正夺得话语权的一方。
在“软硬之争”“凤鹤之争”两次笔战交锋之后,左翼阵营的舆论优势趋于显著。“笔战”形式是左翼影评人争夺话语权、形成舆论力量的重要形式,也在客观上推动当时人们对近代电影业有了更宏观的认知,把对电影的讨论推向更加广阔的文化场域。在当前看来,1932-1934年以笔战形式开拓的话语空间是特殊政治文化背景下的“批评空间”,二元对垒的文人对立阵营也是时代的产物。在近代电影的起步阶段,对国外先进理论的学习刚开始,对国产电影的实践处于探索阶段,“笔战”的方式很难激发出优秀的思想结晶,反而可能加剧文人对垒的矛盾。在泛政治化的语境下,语言被文人当作政治宣传或个人攻击的武器。报刊影评上时常出现文人互相谩骂和攻讦现象,可见“笔战”的极端形式不利于构建理性的电影批评的舆论环境。
从公共领域角度看,“软硬之争”实质是左翼电影批评力量对话语权一次强有力的争夺,显露出了左翼阵营占上风的优势,其结局更是将这文化场域上的对垒,泛化到政治意识形态博弈的层面。穆时英、刘呐鸥等软性电影论者,在“软硬之争”落幕之后,真正成了国民党的御用文人,穆、刘二人还在抗日战争中做了汉奸。这样的情况和结果,很容易让人将“软性电影论者”们划到“反动派”的阵营里去。但在权力话语博弈之外,我们不应忽略“软硬之争”“凤鹤之争”等的争论,在文化场域上形成的反思总结,实际上对电影制作产业是有促进作用的,对当时电影业的发展产生过不容忽视的影响。20世纪30年代,多位左翼影评人与软性电影论者,为更有力地说明自己的电影观念而亲身做编剧、导演,积极推动当时电影制作、生产与批评活动的开展,留下了娱乐电影《化身姑娘》、进步电影《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代表作,促进了近代电影产业的发展。
结语
整体而言,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副刊,不仅是娱乐的载体,更是权力话语角力的场域。《申报·电影专刊》是左翼电影工作者积极争取电影批评话语权的重要阵地。从夏衍、黄嘉谟等人的电影“软硬之争”,到凌鹤与姚苏凤的“凤鹤之争”,都表现出左翼影评人在30年代对电影话语权的积极争取之态度,亦是通过持续的、集体式的批评文章,而逐渐占领上风的力量博弈。但是,在左翼逐渐占领舆论优势之后,左翼影评人与论敌展开的观点的笔战,既是出于对电影的不同认识,也受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政治话语的扩大化,导致艺术争论常常上升为意识形态层面的龃龉,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影文艺创作与批评工作的开展。此外,主编与供稿群体的立场转变,很大程度地影响了相关舆论阵地的转移,这种“艺术场”中的个体话语权力迁转与畸变,也是20世纪30年代电影批评公共领域实践所产生诸多问题之一,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