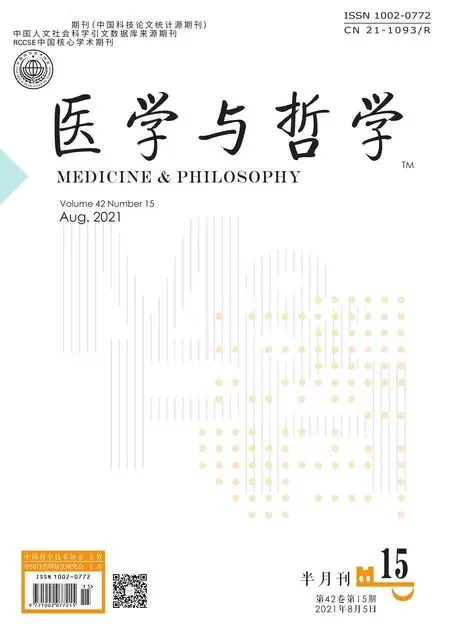死后人工生殖的伦理思考
2021-12-01沈燕如
李 磊 沈燕如
叔本华曾说“死亡和生殖的交替好像种族的脉搏”,死亡意味着个体生命的终结,生殖意味着个体生命的诞生,两者很难在同一时间状态内发生,但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ART)的迅猛发展,随着“人造子宫”体外培育技术的不断研发,死亡与生殖不再绝对地对立,死后人工生殖由不可能变为技术可行,在此背景下,近年临床实践中出现死者家属要求医疗机构为死者提取生殖细胞以用于人类辅助生殖的案例,且今后社会必会面临上述新兴科技引起的现实诉求所造成的伦理问题、法律问题。死后人工生殖一般指将死者生前冻存的生殖细胞通过ART与死者有特定关系的人进行生育结合的医疗技术,也可扩大定义包括提取死者生殖细胞以用于与死者有特定关系的人进行生育结合[1]。根据死者性别划分,可分为女性死后人工生殖、男性死后人工生殖。对于前者,因孕育生命的器官子宫仅女性拥有,则死者丈夫若行死后人工生殖,或通过“人造子宫”这一体外培育技术,或通过代孕等,鉴于体外培育技术的不成熟性及代孕的违法性,在此不讨论女性死后人工生殖具体问题;对于后者,又可分为:(1)ART者。男性死者生前与妻子已开始接受ART治疗,或存有冻精(精子与妻子卵细胞尚未人工授精),或存有冻胚(精子与妻子卵细胞已经人工授精,形成胚胎并冷冻保存)但女方未移植胚胎等,其妻拟继续接受ART治疗生育子代。(2)非ART者。男性死者生前出于生育力保护等因素而存有冻精,或其生前明确表示同意死后取精,或其家人要求对死者取精,同时其女友/妻子要求进行ART治疗生育子代。笔者在文中仅就男性死后人工生殖的现状与伦理思考作以简单交流。
1 男性死后人工生殖的相关临床案例
1.1 国内临床案例
1.1.1 广东
2004年,一位正在接受ART治疗的已婚男性因车祸意外死亡,其妻拟使用于广东省妇幼保健院生殖中心冻存的13枚胚胎继续治疗,以期产子,但医院依据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关于禁止为单身女性实施ART的规定,拒绝其妻继续治疗要求,后经其妻3月余的申诉,最终由原卫生部发文广东省卫生厅,同意其妻可以继续接受ART治疗[2]。这是我国首例在丈夫死亡后其妻利用既有冻存胚胎进行ART治疗的临床案例。
1.1.2 台湾
2005年,台湾一位军人在移防中意外殉职,其家人与女友要求医疗机构为死者精子冻存,为死者生育后代,最初卫生主管部门以《人工协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中的相关规定,认为不可以开展死后取精,从而拒绝死者家人要求,但后来受到社会舆论等压力,允许为死者先行精子冻存,后续精子的处理使用问题再行研议[3]。然而,死后生殖所涉及的法律、伦理等问题显然不是短时间内能够厘清并解决的,最终这一临床案例以死者家人决定销毁死者精液而宣告结束。
同年,一位已婚未育的男性保险员于上班途中猝死,但死者生前立有遗嘱以声明死后可以对其精子冻存并用于妻子生育后代[4]。此临床案例中,家人同样取得了死者精液,但也同样因死后生殖的违法问题等致其妻最终未能进行ART治疗。
1.1.3 四川
2006年,四川一位已婚未育男性驾驶员因车祸去世,其妻子接受悲痛现实后,决定为亡夫生子,遂请成都市锦江区妇幼保健院的医生为其亡夫进行了死者精子冻存手术,家人计划后续通过ART治疗完成怀孕[5],但取精后未进行辅助生殖。
1.1.4 山东
2014年,山东一位已婚未育男性溺水身亡,其家人计划由医疗机构为死者精子冻存,但医疗机构出于死者无法做到知情同意,且取精后精子的处理可能会导致纠纷的考量,拒绝了死者家人取精冻存的要求[6]。
1.1.5 广西
2018年,一位妻子在其丈夫死亡后,拟继续在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生殖中心进行辅助生殖治疗以再次为亡夫生育子代,治疗诉求被医疗单位拒绝,当地法院认为该夫妻已经通过ART治疗而育有1女,故未认可女方在其丈夫死亡后进行死后人工生殖的诉求[7]。
1.2 国外临床案例
1.2.1 法国
1981年,法国一位癌症患者开始治疗前进行了生育力保护,将精子冻存。1983年,其婚后二天死亡,其妻试图获得亡夫精子进行辅助生殖,精子保管中心拒绝此请求。后经法院审理,以“优先考虑死者生前对精子处置指示”的角度,在死者父母与其妻作证死者有死后生殖意愿后,判定精子保管中心归还死者家人精子[8]。
1.2.2 美国
1991年,美国一位男性在自杀前将精子寄存于加利福尼亚州一家精子银行,并通过书面文件及遗嘱明确表达其死后,该精子处置权交由其女友。当其女友主张对精子使用权利时,遭到死者的成年子女反对。最终死者女友通过法院诉讼获得精子使用权而进行辅助生殖[9]。
美国第一个对男性死者进行死后取精并进行死后人工生殖的临床案例亦发生在加利福尼亚州,一位女性在其丈夫死亡30小时后进行了精子提取,并通过ART技术怀孕且顺利生育1女。但后续在此子女与死者关系确定上出现了问题,行政单位依据州法不认可死者为此子女父亲,不认可此子女继承血缘亡父的社会利益[10]。
1.2.3 英国
世界首例死后取精并通过ART完成生育后代的临床案例发生于英国。1995年,英国一位脑膜炎患者突然死亡,其妻在医疗机构帮助下对死者进行了精子冻存,并拟行死后生殖,但鉴于英国《人类授精与胚胎法案》禁止在缺乏男性在先书面同意的情况下对其遗体进行精子提取并辅助生殖,其妻遂转至比利时进行人工授精,最后分别于1998年和2002年各顺利生育1子[11]。
1.2.4 日本
1999年,日本一位慢性骨髓性白血病患者在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前进行了精子冻存,术后向家人表示后续治疗若出现不测,希望其妻利用冻存精子产下后代。当年10月,患者死亡,其妻按照患者遗愿实施ART治疗,并于2001年成功生育后代[12]。
此临床案例虽然完成男性死后人工生殖,但子代身份却历时6年申请仍未被认定婚生子女及与血缘亡父的父子关系。
1.2.5 德国
2008年,一对进行ART治疗的新布兰登堡的夫妻,在精卵人工授精后进行了冻存,后男方因车祸不幸死亡,其妻拟继续进行治疗以期受孕产子,但医疗机构依据德国《胚胎保护法》禁止死后人工生殖行为等相关规定拒绝为其妻继续治疗,其妻遂欲转至波兰进行后续ART治疗,但德国医疗机构亦拒付生殖细胞以避免成为死后人工生殖施行的“协助犯”[4]。此临床案例后续经历2起诉讼,至二审裁定医疗机构将受精冻存的胚胎进行返还结束。
2 死后生殖的伦理问题思考
上述临床案例的具体情境虽然不同,但涉及和触碰的问题却大体相同,均涉及男性死后人工生殖的伦理和法理问题等,问题本就难以厘清,更何况加入了不同国家的不同风俗。世界范围内以法律条文明令禁止死后人工生殖的国家有德国、法国、瑞典等,美国生殖医疗协会对死后人工生殖的建议是医疗机构在死者生前未明确同意或可推断同意死后人工生殖时,其生存亲友不能利用死者配子或胚胎进行死后人工生殖,相较国外,我国尚无相关法律制度,唯一涉及到医学人工生殖领域的法律文书是1991年由最高人民法院作出的《关于夫妻离婚后人工授精所生子女的法律地位如何确定的复函》,复函提出的“在夫妻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明确同意进行人工授精,所生子女就视为夫妻双方的婚生子女,父母子女的权利义务关系适用于婚姻法的相关规定”也并不适用死后人工生殖,与此同时,国内现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办法》主要是从行政管理角度对开展ART的医疗单位及医疗技术人员进行的规制[1,13-15]。
在无ART之前,除非死者生前进行的性行为可导致其女友/妻子受孕,死后绝不会再产生自然血亲的子女后代,死亡与生育没有交集,但随着ART这一医学科学技术的出现,死亡与生育开始有了交集,ART可以让死者享有生育权,与此同时,情、理、法在这一技术的迅猛发展之下,开始显现冲突,出现不匹配的滞后与尴尬。面对男性亲友的离世,在世亲友必然十分悲痛,尤其是面对未育男性的去世,更会加剧此悲痛情感,此时逝者父母或女友/妻子希望通过ART生育逝者的子女后代,此诉求可以理解,但面临诸多伦理困境。
2.1 拟行死后人工生殖的成人层面伦理问题
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包括尊重(自主)原则、不伤害原则、有利原则、公正原则。若对男性死者死后取精进行ART,这种具备伤害遗体的有创性操作是否侵犯了死者尊严?同时,由于死后人工生殖相关的特殊性、敏感性,导致几乎每一起所涉临床案例都会引起新闻媒体等的报导,更有甚者,有的报导直列当事人姓名等隐私、罗列相关操作细节等,违背了医疗操作的保密原则,这是否也是对死者的不尊重?死者尸体或人体组织不属于一般的物,不属于法律上的物,不能作为继承标的,结合现行法律,死者亲友只能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进行遗体的捐献、丧葬等事宜,所以男性死者生殖细胞的法律属性导致其亲友没有对其精子的支配权,死者的亲友不能像继承死者一般财产一样继承生殖细胞并通过ART而自由应用于死后人工生殖中[16]。若死者生前未明确同意死后人工生殖,又会侵犯死者的知情同意权,同样有悖尊重原则,此时如果死者生前本就反对死后人工生殖,更有悖死者意愿、有悖有利于当事人的原则,即便死者生前存在冷冻精子的医疗行为,但也不足以证明、推定其同意死后人工生殖;若死者在临逝前的较短时间内,突然自发或受亲友情绪感染而临时决定“留后”而同意死后人工生殖,这种在时间有着急迫限制的环境下,其作出的决定无法保证是理性的、深思熟虑的、不会改变的,很难体现理性下的自主原则;若死者生前深思并通过文书或影音资料明确表示同意死后人工生殖,同时亲友亦自愿进行,这满足对死者尊严、知情同意权、自我决定权等不存在侵犯,但这种满足死者“留后”遗愿、满足生者情感慰藉的最终结果是出生子女出生即缺失生父关爱、出生即在单亲家庭,虽不能断定这些客观事实一定会导致孩子心理、精神层面出现不可逆伤害,但在单亲生活环境等各种现实问题面前,他们必然会比拥有双亲生活环境的同龄人存在更多的心理、精神健康成长隐患,这种结果对出生子女不公平,亦不负责任。
2.1.1 血脉传承观念根深蒂固
一个生命的诞生可以因受“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传统血脉传承文化的影响,若死者为已婚、未育、独子男性,其亲友对死后人工生殖的诉求可能最为强烈。我国社会重视血脉传承,特殊的传统文化与风土人情使得传宗接代这一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当事人或也存有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认为有子代则可以在老后给予生活照料。在这些背景下死后人工生殖相关医疗操作比较符合社会伦理,但一方面,随着时代变迁,我国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善,人们不再仅能、必须通过子代来保障老有所养、老有所依;另一方面,在医学领域内,医学伦理与社会伦理虽存有交集,但医学伦理的指导意义应该高于社会伦理,因为医学伦理本身的要求更加严格,医学的特殊性与医学伦理的严谨性相契合,医疗技术必须在合理、合规、合法的前提下施行,必须保持治疗疾病的初衷不随意改变,不能因ART可以治疗不孕不育而推导出“死者无后=可施行死后人工生殖”“死后人工生殖技术可行=现实可行”等。
2.1.2 忽视生育权相匹配的责任
一个生命的诞生可以因成人享有生育权,生育权归属夫妻二人,即夫妻作为共同体,生育权由夫妻双方共同支配,其实际内容体现为夫妻须统一决定是否生育子代、何时生育子代等,所以当丈夫死亡后,妻子单方不具有独立决定生育的权利。但在死后人工生殖情况下,生育权这一夫妻共有权利变为单方权利,丈夫死亡后其妻可自行决定是否生育,对现行法律提出了巨大挑战。与此同时,随着男方死亡,婚姻关系即而解除,夫妻关系不再存续,若坚持离开婚姻关系的单方生育权就属空谈了,女方若以亡者之妻的遗孀身份即可进行死后人工生殖,更加剧此挑战,所以即便死者生前同意死后人工生殖,因夫妻关系的解除也未必能够顺利实施。生育权虽有自由属性,但因其结果为创造生命,涉及子代的家庭成长环境是否完整等,成人享有此权利的同时,也应受到相关义务、责任、法律的限制。
2.1.3 无法正面失亲之痛
一个生命的诞生可以因夫妻间的深厚感情、可以因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父母之痛等,父母、妻子寄希望于通过死后人工生殖为男性死者产子留后,子代被赋予了更多的精神寄托、感情慰藉,质朴挚情的出发点非常可以理解。生命因亲情、爱情而炫丽丰满,生命也会因意外变故而留有遗憾,林林总总的元素构成了一个生命的全程,就算死者本人生前看淡生死,对生死处之淡然,对生命中的某些遗憾可接受,但他的至亲又如何忍心在“现实技术可行,现实未明令禁止”背景下无动于衷地承受丧偶无后、丧子无后。此外,若死者妻子拟利用死者生前本就冻存的精子、胚胎,或对死者进行死后取精等进行死后人工生殖,在悲痛情绪缓解后或出于保障子代完整家庭的权利,或出于单亲抚育子代的巨大社会压力等因素,不再选择为亡夫生育后代,其是否会受到他人的情感质疑甚至指责,而死者父母是否会着力于境内的非法代孕、境外的代孕机构,这些情况无疑会造成更多的家庭矛盾及伦理冲突;若死者妻子决意进行死后人工生殖,并成功生育子代,其后续生活所面临的养育压力必然很大,即便抛开子代权利保障不谈,其在子代抚养、工作打拼等诸多现实社会压力之下依靠爱情信仰而辛苦前行,可能离世的爱人也不希望看到。无论亲情、爱情,都出发于爱,爱的形式有很多种,但其中肯定包含放手,感怀于与死者曾经拥有过。
对于死亡,正如郑晓江教授所指出的,“我们社会的一种普遍现实是人人必死,每天都有人死亡,但却不能谈死,哪怕谈得正确,谈得很有艺术,那也不行”。因疾病、意外等导致的无后男性的死亡固然让人悲戚,对于死者妻子、父母的丧偶无后、丧子无后之痛也能非常理解,子代被赋予死者生命的另一种延续色彩,但死亡也属于生命的一部分,死亡意味着诀别,固有遗憾、可惧之处,面对既成的事实,虽然我们无法做到淡定从容,但应理性高于感性,正面亲友的死亡、正面生命有遗憾这种一定意义上的人生常态。从成人视角出发,若男性死后人工生殖可以开展,那么生命伦理中正义原则下的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权利对等的女性死后人工生殖是否也应开展?因为丧夫、丧妻后对生育子代的诉求本质上相同,届时丧妻男子通过代孕获得子代,甚至单身主义者以婚姻关系因夫妻任一方死亡而结束后恢复独身都能享有生育权而提出生育诉求等情况,届时的社会挑战更加巨大。医学有禁区、医疗技术有红线,死后人工生殖区别于医学的疾病诊疗目的,若某项医疗技术存在脱离自然因素、社会因素、人文因素、伦理因素等情况,则应约束使用,限制其非医疗目的使用。
2.2 通过死后人工生殖出生的子代层面伦理问题
生殖是一个独立新生命的孕育和出生,弱小出生婴孩的利益如何维护,出生子代成长的福祉如何保障,亦是权衡死后人工生殖是否可施行的极重要考量因素。成年人有权决定将子女带来世界,但也应考虑可能会给子代带来的影响,子代的健康成长是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环节,所以生育自由与生育责任密不可分,甚至生育责任应大于生育自由,所以死后人工生殖施行与否应该遵循子女利益主位,遵循子女最佳利益主位。
2.2.1 亲子关系混乱
人类社会现行的亲子关系确认多以自然生育为基础,以父母婚姻、在世为前提,在传统伦理中亲子关系的认定不是问题。相比之下,死后人工生殖中男方已死亡,子代出生后与其血缘父亲的关系没有了时间上的明显联系,致使子代与死者间的父母关系得不到现行法律的认可,前述的临床案例即反映出此点,因为不符合许多国家现行的有关亲子关系认定的法律规定,出生子代的身份认定就出现问题,这对子代而言是一个极大的伤害。既往简单、清晰的亲子关系认定变得模糊,亲子关系作为子代出生后建立的首个基础关系而意义重大,在此关系的保障下子代才能更好地成长,亲子关系的认定出现问题,则子代后续人生中所伴随的遗产继承、社会关系等也会出现各种问题。
2.2.2 子代权利损害
死后人工生殖无法保障子代的最大福祉,单亲家庭的环境下单亲需要独立面对工作、生活上的多重压力,单亲出现监护不足的概率会增加,若子代随母亲重组新的家庭,他(她)们的成长将面临更多的挑战。子代也属于死后人工生殖的利害关系人,有权利享有完整家庭,成人人为地剥夺了子代拥有完整家庭的权利,子代毫无选择地丧失了具有双亲的权利,而双亲家庭是子代教育及社会化的重要环境,双亲角色的不同会满足子代成长过程中心理、社会的不同需求,子代自形成胚胎时就意味着会面临亲属缺失的缺陷、面临今后多于同龄双亲家庭孩子的成长不利影响,这种伤害从子代角度又是否符合伦理,是否公平。此外,虽然死者妻子及父母本着为死者生育后代的良好初心,情感的真挚表达容易获得他人感性认可,但若进行死后人工生殖的主要原因是为死者留后等目的主导,亦有悖于生命伦理中的行善原则、正义原则,且主因若以本代当事人的情感需求甚至养老需求为出发点,轻视甚至忽视可能引发的代际不公平,对社会可持续发展也会造成巨大阻碍。
对于死后人工生殖,必须考虑出生子代的利益,而拥有双亲是保护子代利益的重要内容,借鉴已对ART进行立法规范的国家的举措,如1990年英国立法规范ART时,明文要求开展此项医疗技术前须要考量子代利益,此利益包括子代的心理利益,尽量规避子代可能受到的不利风险,如20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的亲子法立法价值取向也由既往的“亲本位”转向“子女本位”[17],所以从保护子代权利层面出发,施行死后人工生殖亦不妥当。
3 展望
死后生殖涉及朴素情感、伦理道德及法学等诸多方面,其“生殖”的医学特征使其具备的影响力巨大。就像“基因编辑婴儿”事件中包括基因编辑婴儿父母在内的相关人员共同对基因编辑婴儿的自主决定权、健康权等造成权利损害[18],死后生殖不仅仅是成年人可于自身进行的一种ART,更关系到出生子代的健康成长,波及当前社会的现行制度,而目前社会的公序良俗、法律法规还没有充分的准备去应对这些问题。生殖医学专家冯云教授在论及ART所包含的植入前遗传学诊断及筛查技术时曾指出,当一些医学技术发展尚有缺陷、个体价值尚无统一评判的情况下,少做比多做好,谨慎比鼓励好[19]。
本质而言,ART作为一种非常态生育方式,其目的为治疗不孕不育患者,适用对象应是不孕不育且无法治愈者,让不孕不育患者达成建立健全家庭生活的心愿,死后人工生殖有悖疾病治疗目的,且不能建立一个健全的家庭,而是以情感寄托或其他非疾病原因为诉求的创造生命,更多地体现了死者在世亲友的情感需求等。此外,“人造子宫”技术发展虽然困难重重,但却未止步,2021年3月17日以色列魏茨曼科学研究所Jacob H.Hanna教授等于Nature发表研究论文公开介绍其团队首次使用人造子宫培养了小鼠胚胎6天且期间胚胎发育正常,6天时间已达到小鼠整个妊娠期的近1/3(小鼠胚胎完整妊娠期为19天~21天)[20],我国也于2020年底由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成功实施国内首次人造子宫胎羊体外培育实验[21]。试猜想,如果“人造子宫”技术发展成熟,届时再配以死后人工生殖合法化施行,两者的结合开创新型治疗方式的同时,也会带来更多、更复杂的问题,如“前人”冷冻的胚胎被“后人”复苏移植并孕育成人,不但有悖于自然秩序,更会乱于社会秩序。
在国内,对于死后人工生殖,虽然目前公开报道的有关临床案例不多,但可以预见其诉求会在将来不断出现,当医疗技术高速发展时,伦理、法律层面可能会出现相对的滞后,但无论现在抑或将来,面临各种因医疗技术飞速发展而产生的情、理、法之间不匹配的问题,我们总会找到某个平衡点去最大化地解决它,但在此之前,笔者认为对于死后人工生殖禁做比准予为妥,死后人工生殖被认为“存在就是合理”是不够负责、不够严谨的,应让辅助生殖技术回归疾病诊疗本质,进一步出台ART相关法律制度,对死后人工生殖产生的价值冲突进行有效的引导。禁止死后生殖:无论死者生前是否明示同意死后人工生殖及相关医疗操作,对死者均不能提取生殖细胞用于生殖目的;在ART治疗过程中若男方死亡,则治疗周期立刻结束并销毁夫妻双方所有生殖细胞及胚胎,仅允许治疗期间女方已移植胚胎并受孕的情况继续进行(若女方已移植胚胎但未受孕,则不能再次移植胚胎进行受孕),且出生的子女的身份定位应为婚生子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