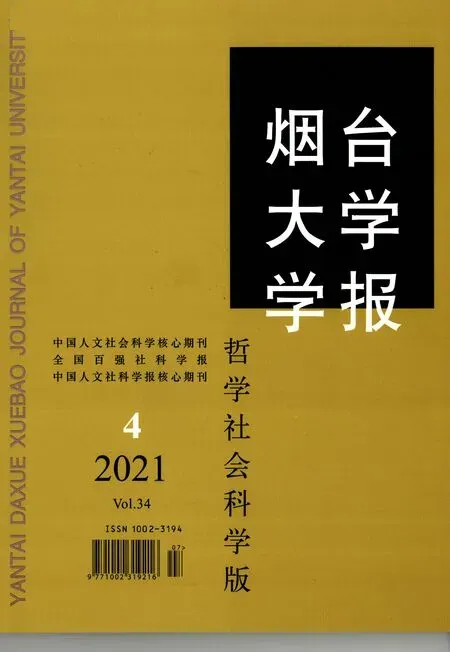中西文学审美自由理想的文化发生问题
2021-11-30马小朝
马小朝
(烟台大学 人文学院,山东 烟台264005)
人类从蒙昧往野蛮、从野蛮往文明的历史进步,就是人类通过社会生产劳动实践活动改造外在和内在自然、创造物质和精神文明的社会文化进步,也是人的自由理想、文学的审美自由理想逐步实现的进步。中西方人的社会文化,同中西方文学的审美自由理想自然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中西方人的社会文化比较,自当是比较中西方文学审美自由理想问题的出发点。
人们通常理解的中西方文化,往往表现为中西方社会生产劳动实践活动的历史过程和发展阶段中的社会生产方式变迁、阶级斗争变化和意识形态变换等等,常常忽略了中西方文化的内在生命机理的发生。我们关于中西方文化的比较,更主要强调研究中西方人最初的社会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如何创造了中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差异性,或者说,更主要强调中西方文化的发生学问题,进而研究中西方人的自由理想、文学的审美自由理想独特性、差异性的发生学问题。德国启蒙理论家赫尔德,最早借助生物学与神话学的结合来说明文学艺术的文化发生学问题。他说:“树从根处生长,艺术的产生和繁荣也不例外,一开始有艺术,艺术的产生也就有了全部的存在,犹如一种植物的整体或所有组成部分都蕴藏于这植物的一颗种子中了。”(1)伍蠡甫:《欧洲文论简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178页。德国古典哲学家黑格尔则在阐释人类社会“法的思想”产生时指出:“萌芽虽然还不是树本身,但在自身中已有着树,并且包含着树的全部力量。树完全符合于萌芽的简单形象。”(2)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导论”,见《法哲学原理》,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年,第1页。“如像一粒萌芽中已经含有树木的全部性质和果实的滋味色相,所以‘精神’在最初迹象中已经含有‘历史’的全体。”(3)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第16页。赫尔德和黑格尔虽然似乎把事物的千变万化简单化为“一次完成”,但其中包含了具有借鉴意义的人类文化发生学原理的端倪。后来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心理学研究所带动的发生认识论原理研究,更进一步奠立了人类文化和哲学认识论的发生学研究的理论基础。皮亚杰有针对性地指出:“传统的认识论只顾到高级水平认识,换言之,即只顾到认识的某些最后结果。因此,发生认识论的目的就在于研究各种认识的起源,从最低级形式的认识开始,并追踪这种认识向以后各个水平的发展情况,一直追踪到科学思维并包括科学思维。”(4)皮亚杰:《发生认识论原理》,王宪钿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17页。
西方的古希腊文明无疑应该是西方古代文化无可争议的发生时期。恩格斯在谈到古希腊哲学时说:“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看法的胚胎、萌芽。因此,理论自然科学要想追溯它今天的各种一般原理的形成史和发展史,也不得不回到希腊人那里去。”(5)恩格斯:《自然辨证法》,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77页。现代物理学家海森伯在《物理学家的自然观》中说:“一个人没有希腊自然哲学的知识,就很难在现代物理学中作出进展。”(6)海森伯:《物理学家的自然观》,吴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第21页。中国秦汉前文明无疑应该是中国古代文化无可争议的发生时期。那么,什么样的社会生产劳动实践活动孕育了古希腊文明、中国秦汉前文明呢?
古希腊文明诞生于爱琴海域的诸多海湾、岛屿上。这些地区的陆地大多山石嶙峋、荒瘠不毛,主要种植橄榄、葡萄。少量的肥沃山谷往往受群山阻隔,但具有比较方便的海上交通。由此,古希腊人的物质生产劳动一开始便与无边无垠、变幻无常的大海纠缠在一起。古希腊《荷马史诗》的《伊利亚特》中就有这样描述海神和海洋女神的诗句:“众神的始祖奥克阿诺斯和始母特梯斯”,“滋生一切的奥克阿诺斯的涌流”。(7)荷马:《荷马史诗·伊利亚特》,罗念生、王焕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第322、323页。亚里士多德在追问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家泰勒斯宣称“水为万物之原”“大地安置在水上”的原因时,也提到远古先哲编撰神话故事时,“他们以海神奥启安与德修斯为创世的父母,而叙述诸神往往指水为誓”。(8)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吴寿彭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7-8页。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在《历史》中指出,有许多人在画全世界的地图时,“他们把世界画得像圆规画的那样圆,而四周则环绕着欧凯阿诺斯的水流,同时他们把亚细亚和欧罗巴画成一样大小”。(9)希罗多德:《历史》上卷,王以铸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279页。希罗多德认为这些缺少理论根据的画有些可笑,但我们却能体会到古希腊人关于生存世界环绕着海洋的现实感受。古希腊人的主要生产劳动实践活动是狩猎业高于农业。兹拉特科夫斯卡雅在其《欧洲文化的起源》的第二章《爱琴文化的出现》中,根据考古发现提供的证据说:“新石器早期地层所发现的工具和武器足以说明狩猎是当时居民的主要职业。我们还没有发现新石器早期从事农业的迹象。”(10)兹拉特科夫斯卡雅:《欧洲文化的起源》,陈筠、沈澄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4年,第53页。这里所说的狩猎业主要指围绕大海的渔猎业。古希腊人先天薄弱的农业与得天独厚的渔猎业显然无以孕育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生产方式。相反,围绕大海的渔猎业因为需要复杂的生产劳动工具,必然会促进手工业的高度发展,进而孕育出贸易交换为主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海洋交通的天然条件又扩展了商品经济生产方式的广度与深度。古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在《工作与时日》中告诫自己的兄弟说:“等到航海季节到来时,再把船拉到海边,装上货物出海,这样你可以用它获利。”“要像你我的父亲一样常常扬帆出海以寻找充足的生活来源。”“你不但要注意所有农活的时令,尤其要记住适宜航海的季节。小船只供玩赏,装载货物要用大船。在一帆风顺的情况下,装货越多,获利越多。”(11)赫西俄德:《工作与时日》,张竹明、蒋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10-20页。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在其《希腊史》中,通过一个法萨鲁斯人转述色萨利一个城邦僭主的话说:“我们的谷物产量自给有余,甚至出口到其他地方,而雅典生产的粮食难以自给,除非从海外购买。”所以,雅典人不得不保持足够强大的海军力量,才“可以自由地获得谷物供应”。(12)色诺芬:《希腊史》,徐松岩译注,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第236、227页。黑格尔说:“大海给了我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际和渺渺无限的观念;人类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人类追求利润,从事商业。”(13)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第84页。中国哲学家冯友兰先生也说:“希腊人生活在海洋国家,靠商业维持其繁荣。他们根本上是商人。”(1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23页。古希腊人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不得不同变幻无常的大海、波谲云诡的商业贸易纠缠在一起。
古希腊人在生产实践活动中发现,海洋作业需要个人的力量、智慧与集体的分工合作在一瞬间充分实现,商业贸易需要通过交换为彼此创造共享利益的复杂系统知识,因此,人们不能不超越血缘亲族纽带的自然关系而注重各尽其责、各显其能、相互合作、诚信守约的社会关系。大规模的商业贸易还需要确定的聚集时间和地点,跨海的商业贸易更需要固定的仓储、港口、码头等,因此,人们不能不脱离土地和宗族的束缚而共同工作、生活在城镇里。法国历史学家让-皮埃尔·韦尔南说:“城邦就处在有别于氏族关系和血亲关系的另一层面上:部落和选区纯粹按地理位置划分,它们集合的是同一地域的居民,而不是氏族和胞族这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15)让-皮埃尔·韦尔南:《希腊思想的起源》,秦海鹰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年,第86页。黑格尔在谈到希腊世界的历史时说:“要是有人以为这样美丽和这样真个自由的生命,是由一个种族在血统关系和友谊关系范围以内,经过毫不复杂的发展过程而产生——这种观念实在是肤浅的愚昧。”“希腊历史在开始的时候,便显示为一半土著和一半外族移民的交互混合。”(16)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第212页。冯友兰先生也说:“商人也就是城里人。他们的活动需要他们在城里住在一起。所以,他们的社会组织形式,不是以家族共同利益为基础,而是以城市共同利益为基础。”(17)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23页。海洋天然条件下的商品经济生产活动,具有难以想象的生死一线风险和一朝暴富机遇,因此,人们不能不告别熟悉的亲昵,迎战陌生的恐惧,甚至完全背井离乡地迁徙、殖民。许多平民通过创造发财致富的奇迹,不断成为新兴的工商业奴隶主。所有这一切,皆使古希腊人从原始氏族公社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过程中,比较果断地建立了超越原始血缘宗亲关系的分工合作关系,完成了人与人自然关系往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变革。所以,亚里士多德在说明人是理性的动物时,就直接从理性的人所具有的社会性存在而明确指出:“人在本性上是社会性的。”“人是政治动物,天生要过共同的生活。”(18)亚里士多德:《尼各马科伦理学》,苗力田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第11、204页。
古希腊人超越血缘宗族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下的个人能力发挥与集体相互合作的社会关系、共同的城镇社会生活,必然孕育出城邦民主政治制度。具体而言,个人与集体合作的生产劳动,商业贸易的城镇生活,存在许多社会公共问题。解决社会公共问题一方面需要相应的财力、人力,另一方面能够获得相应的参与、管理权力。谁应该投入多少财力、人力,谁应该获得多少参与、管理权力,皆没有任何先前的规定。最不坏的方式只能是共同协商。冯友兰先生说:“希腊人就围绕着城邦而组织其社会。”“在一个城邦里,社会组织不是独裁的,因为在同一个市民阶级之内,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认为某个人应当比别人重要,或高于别人。”(19)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23页。共同协商能够获得的最不坏的结果,只能是提供的财力、人力与获得的参与、管理权力相对应。由此,古希腊城邦也就自然确立了根据人的经济财富决定城邦政治权力的基本原则。所以,古希腊的民主政治作为奴隶制度下的民主政治,顺理成章地主要是工商业奴隶主同土地贵族奴隶主分享城邦管理权的民主政治。
民主政治制度无疑推进了古希腊城邦的社会进步。从理论逻辑上讲,民主政治制度使每一个自由公民都可以通过发财致富、熟悉政治获得分享政治权力的机会,这就调动了人的主体性,释放了人的创造性,从而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解放,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古罗马的文论家郎加纳斯说:“民主是天才的好保姆。”“自由,据说,能培养才士的大志,能引起希望,能保持竞争的火焰和争取高位的决心。”(20)郎加纳斯:《论崇高》,钱学熙译,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史》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130页。从历史经验上讲,决定希腊文明生死存亡,进而决定西方文明延续或泯灭的希波战争的结局就是最典型的例证。人们通常谈到战争胜负的时候,常常会从侵略与被侵略引申出非正义与正义,然后想当然地得出结论:非正义必败,正义必胜。其实,这种形而上信念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并没有绝对可靠的依据。因为,侵略与被侵略的定义是现代社会概念,通常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联合起来)侵犯别国的领土、主权,掠夺并奴役别国的人民。但是,“确切地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21)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86页。更具体说,国家是生活在一定区域里的种族、民族,在阶级产生、阶级矛盾不可调和基础上的历史性产物。从来没有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存在且一直不变。甚至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国家依然会因为某种内在或外在矛盾而重新分解、组合。因此,任何道义上的正义或非正义解释只是一种道德情感的表达而已。那么,到底是什么决定了战争的胜负呢?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之希腊波斯战争史部分通过完整讲述希腊波斯战争,毫不讳言地强调在希波战争中发挥关键作用的是雅典人。他说:“如果说雅典人乃是希腊的救主的话,这便是十分中肯的说法了。雅典人站到哪一方面,看来优势就会转到哪一方面。”(22)希罗多德:《历史》下册,王以铸译,第518页。希罗多德强调雅典人发挥关键作用的深层思想,其实是强调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度战胜了波斯的专制政治制度。
民主政治制度肯定了众多普通自由公民只要能够发财致富,或者具有政治智慧,就可能获得分享政治权力的机会,其实也就肯定了众多普通自由公民的求富、求知意愿,就是符合人类社会存在的人性本质,就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理性逻辑。这种思想无疑深刻影响了古希腊人的文化心理和思想意识、价值观念,其表现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古希腊人的世俗生活态度非常注重物质享受和精神愉快,从克里特的米诺斯王宫、迈锡尼的豪华宫殿到影响广泛的奥林匹克体育竞技、充分展现生命健美的建筑和雕塑等等,皆是其充分说明。第二,古希腊人的宗教信仰则显现出独特的人神“同形同性”特征。所以,柏拉图认为《荷马史诗》和希腊悲剧把神和英雄描写得跟平常人一样满身都是毛病。黑格尔说:“神们好像在做与人无干的事情,但实际上他们所作的事情却是人的内在心情的实体。”(23)黑格尔:《美学》第一卷,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289页。当然,古希腊的民主政治毕竟是奴隶制度下的古典民主政治,其历史创造性终归因为奴隶制的局限,不仅不可能全面实现而且必然会发生严重危机,这种危机最直接的后果就是自由公民变成了历史进步的绊脚石,最终“就把整个雅典国家引向了灭亡”。但是,“使雅典灭亡的并不是民主制,像欧洲那些讨好君主的学究们所断言的那样,而是排斥自由公民劳动的奴隶制”(24)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134页。。 民主政治作为一种深藏潜隐的文化基因,无疑是西方人建设现代民主政治制度,从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宝贵思想资源。
古希腊人的商品经济生产方式,超越原始血缘宗亲的分工合作社会关系,充分解放人的主体创造性的民主政治,无疑促进了古希腊人科学思维、理性精神和艺术想象、审美意识的健全发育,培养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童年的“正常的儿童”。(25)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12页。席勒赞美古希腊人说:“他们既有丰富的形式,同时又有丰富的内容,既善于哲学思考,又长于形象创造,既温柔又刚毅,他们把想象的青春性和理性的成年性结合在一个完美的人性里。”(26)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8页。从文化发生角度言,古希腊文化奠立了西方文化的历史理性主义基本性质。古希腊人巧妙地通过天空、大地、海洋、太阳、月亮等诸神的故事,说明了自然世界的发生、发展皆有因果规律的宇宙自然观;通过子辈神不断起而反抗父辈神、围绕金苹果的二雄争一美、杀母复父仇、杀父娶母等故事,解释了人类社会进步必然破坏血缘宗亲纽带、陷入历史与人伦二律背反的社会历史观;更通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对自然、社会、人的哲学思考完成了历史理性主义的理论阐释。古希腊人还通过宙斯与普罗米修斯冲突、和解等故事,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历史理性主义的“至善”目的论思想,预示了热衷探讨宇宙自然本原、人类历史奥秘,具有科学热情和求知倾向的古希腊文化为基础的西方文化,终归可能在历史流变中敞开胸怀拥抱、融合热衷探讨宇宙世界目的、人类生存意义,因而具有伦理热情和信仰倾向的东方希伯来文化。古希腊文化和希伯来文化交汇而衍生的基督教文化,在古罗马时期终于成为西方文化的重要部分。基督教文化,虽以自己已经成熟的价值理性思想,延伸了古希腊文化里处于萌芽状态的伦理学思考,但更以其思想的逻辑前提,吻合了古希腊文化中已经成熟的历史理性思想。比如《圣经》讲述的亚当与夏娃偷吃禁果而痛失乐园的故事,该隐嫉妒杀弟、上帝发大洪水和挪亚方舟的故事,以及耶稣代人受难而横死在十字架上的故事等等,皆进一步诉说了历史与人伦在人类社会里的二律背反。所以,梁漱溟先生说:“西洋人自希腊以来,似乎就不见有人性善的观念;而从基督教后,更像是人生来带着罪恶。”(2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3页。基督教《新约·马太福音》更描写耶稣说:“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承受永生。”《新约·马可福音》《新约·路加福音》里也有同样的描写。从中我们不难领悟其肯定人类必须挣脱血缘亲族伦理羁绊的历史观念。张荫麟先生说:“在基督教势力下,个人所负宗教的义务,是远超过家族的要求。教会的凝结力,是以家族的凝结力为牺牲的。”“基督教一千数百年的训练,使得牺牲家族小群而尽忠超越家族的大群之要求,成了西方一般人日常呼吸的道德空气。后来(近代)基督教势力虽为别的超越家族的大群(指民族国家)所取而代,但那种尽忠于超越家族的大群之道德空气,则固前后如一。”(28)张荫麟:《论中西文化的差异》,引自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89页。西方文化因为融合了基督教文化,也就有了洞悉历史奥秘、满足肉体生存、丰富物质需要和寄托人伦痛苦、表达灵魂愧疚、实现精神解放的两把钥匙,或者说,有了历史理性与价值理性互为依托、各司其职的历史理性主义文化实践模式。(29)马小朝:《宙斯的霹雳与基督的十字架——希腊神话和〈圣经〉对西方文学的发生学意义》,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年,第121页。
中国秦汉前文明诞生于黄河流域地区。这些地区有诸多河流纵横交叉,其冲击土地的肥沃、水利灌溉的方便非常适合农业耕作,从而孕育了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中国古人最初的生产劳动实践,主要是在相对固定的土地上,根据四季循环的天气规律,运用丰沛的水力资源,使用简易的生产劳动工具,从事重复往返的农业耕作,逐步形成了以血缘家族为聚居群体,以农耕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中国古代不管是统治者的政治策略,还是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念,至少在十六世纪前一直是重农抑商占据主流地位。所以,梁漱溟先生说:“然说到经济,首在工商业,中国始终墨守其古朴的农业社会不变,素不擅发财。”(30)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5页。冯友兰先生说:“古代中国和希腊哲学家不仅生活于不同的地理条件,也生活于不同的经济条件。由于中国是大陆国家,中华民族只有以农业为生。”“在农业国,土地是财富的根本基础。所以贯串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思想和政策的中心总是围绕着土地的利用和分配。”“中国哲学家的社会经济思想中,有他们所谓的‘本’‘末’之别。‘本’指农业,‘末’指商业。区别本末的理由是,农业关系到生产,而商业只关系到交换。在能有交换之前,必须先有生产。在农业国家里,农业是生产的主要形式,所以贯穿在中国历史中,社会、经济的理论、政策都是企图‘重本轻末’。”(31)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15页。
中国秦汉前农耕文化发源在北温带偏北地区(北纬35度左右),气候、雨量、物产皆不如处于热带地区(北纬30度左右)的埃及、巴比伦、印度。中国古人需要终日胼手胝足地勤奋耕耘,方能维持以农耕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基本生存和繁衍。宋代诗人范成大的组诗《四时田园杂兴》按节候分为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冬日五组,每组十二首,从各个侧面生动表现了中国古代农民劳动和生活,其中的一首写道:“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也傍桑阴学种瓜。”(32)范成大:《四时田园杂兴》,袁世硕主编:《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年,第114页。其诗句非常生动地说明了中国古代农民的勤奋和辛劳。这种勤奋和辛劳其实是从古至今中国自给自足的农耕文化传统。马克思曾经引用1852年英国驻广州的一位官员米切尔致乔治·文翰爵士的报告书中的话,说明19世纪中叶中国农村农业耕作与家庭手工业密切结合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条件下,“世界上最先进的工厂制度生产出的产品,售价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出的布更低廉”的谜底,就是“在收获完毕以后,农家所有的人手,不分老少,都一齐去梳棉、纺纱和织布”,“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或者毋宁说只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自家生产的糖的价值”。勤劳、节俭的农民“在他的庄稼正在生长时,在收获完毕以后,以及在无法进行户外活动的雨天,他就让他家里的人们纺纱织布。总之,一年到头一有可利用的空余时间,这个家庭工业的典型代表就去干他的事,生产一些有用的东西。”(33)马克思:《对华贸易》,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846页。
中国秦汉前农耕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中国古人的生活方式是紧密依赖固定土地的男耕女织和血缘宗族的群体聚居。固定土地上的男耕女织,需要的不是瞬间的个体快速决断而是经久不息的勤奋劳作和经验积累。血缘宗族的群体聚居,需要的不是迫在眉睫的集体分工合作,而是绵延不断的血缘宗族成员的互帮互助。所以,中国古人强调纵横辐射的“孝悌”为中心的宗族伦理关系,进而倡导血缘宗亲为基础的上下、尊卑等级原则,而不积极推崇创造财富为基础的社会历史原则。这一切使中国古人从原始氏族公社向奴隶制社会的过渡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里,都无须冲破血缘宗亲基础上的家族伦理关系。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禹死以后,其儿子启废除“禅让制”而实行“世袭制”,建立了奴隶制国家。商汤灭夏后,新的血缘宗族成为奴隶制王国的统治者。《盘庚篇》里有这么两句话:“人惟求旧,器非求旧。”“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这两句话的意思是说,殷人要建立国家,就要修筑城市,所以器要新的。同时,殷人又要维系血缘宗亲关系,所以人还是要用旧的,特别是统治者的统治机构必须使用殷人。殷人较早推出的“天帝”思想就包含了两方面的意义:一是维护国家的至上神意义,二是维系殷血族的宗祖神意义。周灭商后,建立了新的封建领主制,继承了殷商血亲种族统治的传统,只是统治权发生了转移。从此,中国古代宗法制社会几千年绵延不绝。后来的统治者虽然对宗族势力的强大有所忌惮,秦和西汉甚至采用过移徙大宗族的措施,但在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独尊儒术”后,宗族势力更进一步演化为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叱咤风云的士族势力。这或许就是帕森斯等所谓的“哲学的突破”,或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的文明历程中,中国文化变易表现得比较温和的共识。(34)Talcott Parsons, “The Intellectual: A Social Role Category”. in Philip Rieff, ed. On Intellectuals. New York: Doubleday, 1970,pp.6-7.
中国秦汉前农耕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劳动方式,因为强调血缘宗亲为基础的上下、尊卑伦理关系,必然孕育出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冯友兰先生说:“中国社会制度可以叫作家邦,因为在这种制度之下,邦是用家来理解的。”“在一个家邦里,社会组织就是独裁的,分等级的,因为在一家之内,父的权威天然地高于子的权威。”(3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23页。中国古代君主专制的政治制度无疑决定了中国古代王朝更替、循环往复的历史宿命。从理论逻辑上讲,君主专制政治制度规定了自上而下的权利分配原则。任何人只有在等级金字塔上获得较高的位置,才可能有幸分得更大的一杯羹。任何人要想在等级金字塔上得到一个较高位置,不得不俯首帖耳地聆听来自等级金字塔上更高位置的呵唤,甚至不得不察言观色、阿谀奉承、瞒上欺下、钻营投机、尔虞我诈、阴谋算计等等。所以,郎加纳斯说:“专制政治,无论怎样正派,可以确定为灵魂的笼子,公众的监牢。”(36)郎加纳斯:《论崇高》,钱学熙译,伍蠡甫主编:《西方文论史》上卷,第130页。这一切无疑会扭曲人的主体性,腐化人的创造性,从而不仅妨碍社会生产力解放,阻扰社会经济发展,甚至严重破坏社会生活秩序。从历史经验上讲,中国古代几千年的君主专制社会一直在治与乱、分裂与统一的怪圈中蹒跚,始终未能实现真正的社会历史进步。尽管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为社会下层人才提供了跻身社会上层、参与社会管理的机会,但因为晋升阶梯无非是记诵符合等级金字塔意识形态的经文,天下英才俊杰在功名利禄诱惑下,戴着“代圣人立言”的思想枷锁,尽精竭思、皓首穷经,其幸运者大多只是驯化成了君主专制等级金字塔的维护人而已。梁漱溟先生说:“一经修养生息,便是太平盛世。但承平日久,又要乱,乱久又治。此即中国历史上所特有的一治一乱之循环。”(37)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254页。“百年前的中国社会,如一般所公认是沿着秦汉以来,二千年未曾大变过的。我常说它是入于盘旋不进状态,已不可能有本质上之变革。”(38)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70页。中国古代文明幸好有马背上的少数民族大军屡屡入主中原,才使其遭受野蛮蹂躏的同时,也接受新鲜生命活力而得以涅槃重生。当然,中国古代君主专制政治制度在农耕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基层宗法制社会里,因为社会生产、生活常常混杂有浓郁的家族自治因素,其消极作用和影响没有充分显现。但是,君主专制作为一种深藏潜隐的文化基因,无疑是后来阻碍中国近代以后现代化建设的沉重思想枷锁。
中国秦汉前农耕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劳动方式,因为强调血缘宗族为基础的上下、尊卑伦理关系,所以还特别注重围绕血缘宗亲祖先的宗教祭祀活动。他们通过悼念、膜拜逝去祖先和亲人的礼仪,以加强血缘家族的情感凝聚和心理认同,规定血缘亲疏的伦理等级秩序,进而想象逝去的祖先和亲人具有护佑生者的神秘力量,强化伦理等级秩序的神圣性。英籍德国学者麦克斯·缪勒说:“中国的宗教还有祖先崇拜和死者崇拜,认为死者对人间的事比较了解,而且有权力给以善恶报应。”(39)麦克斯·缪勒:《宗教学导论》,陈观胜、李培茱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65页。马克斯·韦伯说:“中国人民的最基本的信仰一直是相信祖宗神灵的力量。”(40)马克斯·韦伯:《儒教与道教》,王容芬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141页。钱穆先生特别指出祖先崇拜与政治统治秩序的密切关系。他说:“根据殷墟甲骨文,当时人已有‘上帝’观念,上帝能兴雨,能作旱,禾黍成败皆由于上帝。上帝是此世间一个最高无上的主宰。但甲骨文里并没有直接祭享上帝的证据。他们对上帝所有吁请,多仰赖祖先之神灵为媒介。他们的观念,似乎信为他们一族的祖先,乃由上帝而降生,死后依然回到上帝左右。周代人‘祖先配天’的观念,在商代甲文里早已有了。他们既自把他们的祖先来配上帝,他们自应有下面的理论,即他们自认为他们一族乃代表着上帝意旨而统治此世。下界的王朝,即为上帝之代表。一切私人,并不能直接向上帝有所吁请,有所祈求。上帝尊严,不管人世间的私事。因此祭天大礼,只有王室可以奉行。商代是一个宗教性极浓厚的时代,故说:‘殷人尚鬼。’但似乎那时他们,已把宗教范围在政治圈里了。上帝并不直接与下界小民相接触,而要经过王室为下界之总代表,才能将下界小民的吁请与祈求,经过王室祖先的神灵以传达于上帝之前。”“待到周代崛起,依然采用商代人信念而略略变换之。他们认为上帝并不始终眷顾一部族,使其常为下界的统治人。若此一部族统治不佳,失却上帝欢心,上帝将临时撤消他们的代表资格,而另行挑选别一部族来担任。这便是周王室所以代替殷王室而为天子的理论。”“周代的祭天大礼,规定只有天子奉行,诸侯卿大夫以下,均不许私自祭天。这一种制度,亦应该是沿着商代人的理论与观念而来的。”(41)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45页。原始宗教祭祀活动的“礼仪”,经过夏、商、周三代传承,尤其经过周公的整理、改造后,逐渐升华为人们的行为规范。春秋末年,继往开来的孔子一方面强调自己“述而不作”“吾从周”,以及“梦见周公”,其意皆在维护血缘宗亲伦理关系为基础的周礼;另一方面又把血缘宗亲伦理关系概括为“仁”。因此,“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论语·颜渊》)。余英时先生说:“‘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他终于在这里找到了礼乐的内在根据。礼乐是孔子思想中的传统部分,‘仁’则是其创新部分。”(42)余英时:《道统与政统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原始型态》,见《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85页。换句话说,孔子“仁”的核心内容源自“礼”,“礼”的核心内容源自血缘宗法基础上的“尊祖”“敬宗”和“亲亲”“尊尊”原则。这样,仁爱的逻辑依据也就是建立在宗法伦理基础上的心理情感。这种心理情感可以保证“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欤”(《论语·学而》)。推而广之,则“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学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学而》)。 孔子把社会政治制度建设问题变换成了血缘宗亲伦理秩序问题,进而再升华为社会普遍伦理道德问题。由此,一切社会历史矛盾都可以解释为血缘宗亲伦理秩序的破坏:一方面是统治者昏聩失道,不能将伦理亲情感受推己及人;另一方面是普通百姓僭礼越位,不能谨守名分约定。所以,“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颜渊》)。 孔子的所谓正名,既劝勉、告诫统治者,又安慰、教诲被统治者,最终实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的“仁”。所以,梁漱溟先生说:“而此则把家庭父子兄弟的感情关系推到大社会上去,可说由内而外,就使得大社会亦从而富于平等气息和亲切意味,为任何其他古老社会所未有。”(43)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38页。钱穆先生说:“‘礼’本是指宗教上一种祭神的仪文,但我们在上文述说过,中国古代的宗教,很早便为政治意识所融化,成为政治性的宗教了。因此宗教上的礼,亦渐变而为政治上的礼。但我们在上文也已述说过,中国古代的政治,也很早便为伦理意义所融化,成为伦理性的政治。因此政治上的礼,又渐变而为伦理上的,即普及于一般社会与人生而附带有道德性的礼了。”(44)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72页。后来的孟子和荀子分别从人性善和人性恶的不同角度继承、发扬了孔子的思想。冯友兰先生说:“孟子代表儒家的理想主义的一翼,稍晚的荀子代表儒家的现实主义的一翼。”(45)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60页。春秋时期伴随儒家活跃在文化舞台上的最重要的思想潮流还有道家。道家出自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因而能够体悟到一切事物,包括人类历史皆包含互相对立、转化的复杂矛盾。《老子》里所谓 “有无相生,难易相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46)王弼注:《老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4、1、18页。就是其经典表述。《老子》里的政治理想是宁可退回到“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47)王弼注:《老子》,第18、19页。的原初状态,或者说是宁可让历史(人道)停滞而追回心灵宁静(天道)。庄子继承了《老子》的历史观,但不同于《老子》、也不同于儒家积极问世的政治哲学。庄子不讲所谓治国平天下的方略,而讲“齐万物,一死生”的人生态度,(48)郭象注:《庄子·齐物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2页。主张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绝圣弃智的心灵境界,关心的不是伦理政治问题,而是个体存在的身心问题。从理论上讲,儒家思想是人生的进取,仁爱、复礼是进取的方向。儒家借助自然“血缘亲情”推论出了社会伦理道德,却终归是既没有社会历史理性实践基础,又缺乏超验终极设定的伦理理想。道家思想是人生的退守,道法自然是退守的方向。道家借助“道法自然”建构起了超验终极设定,却终归是既反对社会历史理性实践活动,又摒弃社会道德内容的空幻想象。儒家伦理理想缺乏的超验终极设定,道家超验终极设定摒弃的社会道德内容,无疑为外来的佛教预留了寻机而渗入的文化心理罅隙。
中国秦汉前原始祭祀基础上的神话故事,因为具有维护社会伦理秩序和政治统治的神圣性,所以都是追溯民族祖先筚路蓝缕的英雄和伦理道德的模范。或者也可以说,民族的远古祖先正因为其英雄业绩和模范实践,才得以被尊奉为神灵而受到膜拜与祭祀,从而使中国原始神话同远古历史浑然不分、崇拜的神灵与赞誉的英雄模范浑然不分。这种神话历史化与历史神话化、神灵与英雄模范浑然不分的观念,衍生了天地自然变易与社会伦理理想互为感应、宇宙秩序与政治制度互为影响的信念。这种信念既符合统治者借助意识形态说明其统治权正当合法的目的,又满足被统治者借助超验力量限制统治权随意滥用的意愿,因而很容易得到人们的理解和认同。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神话中的天神都是人间英雄或道德模范,反过来,中国历史中的英雄或道德模范则可以直接转化为神话中的天神,比如民间崇奉的关公、包公、岳王等等。
中国秦汉前农耕为基础的自给自足的生产劳动方式,强调血缘宗族为基础的人与人社会关系,严重歪曲人的主体创造性的君主专制,规定血缘亲疏伦理等级秩序的礼仪,无疑决定了中国古人伦理道德意识的超常发育,培养了马克思所说的人类童年的“早熟的儿童”。(49)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712页。从文化发生角度言,中国秦汉前文化奠立了中国文化的伦理理性主义基本性质。孔子通过继承三代礼乐传统创建的儒家学说应该是其主要理论阐释。所以,钱穆先生说:“在西方文化系统上,宗教与科学为两大壁垒,而哲学则依违两可于其间。在中国根本无哲学,在西方人眼光下,中国仅有一种‘伦理学’而已。中国亦无严格的宗教,中国宗教亦已伦理化了。故中国即以伦理学,或称‘人生哲学’,便可包括了西方的宗教与哲学。而西方哲学中之宇宙论、形上学、知识论等,中国亦只在伦理学中。”(50)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226页。梁漱溟先生说:“中国有许多书,西洋亦有许多书;书中莫不讲到许多理。但翻开书一看,却似不同。中国书所讲总偏乎人世间许多情理,如父慈、子孝、知耻、爱人、公平、信实之类。若西洋书,则其所谈的不是自然科学之理,便是社会科学之理,或纯抽象的数理与论理。”(51)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第149页。中国古代文化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敞开胸怀接纳了佛教文化。佛教的复杂教义本身对中国人来说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第一,佛教非历史的社会历史观前提与儒家、道家都相互吻合;第二,佛教关于生死轮回、因果相续的人生解说里既有吻合儒家、弥补道家的社会伦理关怀,又有吻合道家、弥补儒家的超验心灵允诺。所以,中国人很容易地接受了佛教的思想。但是,中华民族毕竟不同于古希腊民族。中华民族秉承的是超验性宗教观念淡薄、经验性伦理意识浓厚的传统文化。佛教传入中国后历经变迁,发生了两个方面的重要结果:一是提供了一个经验与超验合二而一的心灵允诺和修身妙方,从而孕育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佛学——禅宗。二是提供了一种人生真理和伦理政治的哲学解说。所以,钱穆先生谈到那些不畏险阻,前往印度求法的高僧时说:“虽则他们同样有一股宗教热忱,但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他们对于探求人生真理的一种如饥似渴的精神所激发。”(52)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第149页。这种哲学解说,最终促动传统道家改变了以往避世隐遁、修炼成仙的诞幻方术,而更崇尚人间的道德事业;促动传统儒家衍生了宋明理学“心性论”为重要标志的理学思想。但是,不管是中国化的佛教——禅宗,还是受禅宗精神影响后的道家、新儒家的思想,都依然是在伦理道德领域里求翻新,或者说在人生态度范畴里寻出路,终归难以为社会历史进步或者物质生产发展提供解决问题的思想资源。比如理学尽管沿袭传统儒家的“经世”理想,标举“以天下为己任”精神,且一度在北宋时期具体化为政治改革,但终归因为社会制度建设资源的匮乏而不得不接受政治改革失败的宿命,不得不担承起“觉后觉”的教化使命,甚至无可奈何地皈依“心安理得”或“心体无累”的人生态度。总而言之,佛教传入中国后的儒(包括理学)、道(包括变化后的道家)、释(包括禅宗)的所谓“三教合一”,终归也只是为传统儒家伦理道德增添了一抹形而上超验色彩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