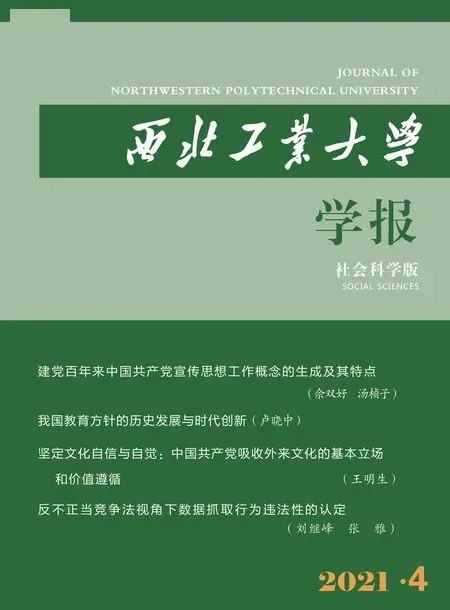作为“英国性”践行者的普通劳动者
——19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对“英国性”的建构
2021-11-30白雪莲
白雪莲
“英国性”是指英国或英国人的独特品质或特性,其表征具有多样性、主观性、建构性和时代性,其本质是英国人在历史长河中为了实现其国家抱负和民族理想建构的一套关于自己民族独特性的话语,诸如崇尚自由、尊重传统、绅士风度、自主自立、勤劳、真诚、讲道德以及理性和爱国等价值观经过不同时代的反复建构而成为其主导性话语、核心内涵和重要表征。这些积极的“英国性”表征在助推英国成为工业革命的策源地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然而,进入19世纪后,随着工业革命的全面推进,英国走上了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的道路,英国社会出现巨大而深刻的改变,传统的“英国性”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作为这个时期的主导性文学形式,记录并展现了当时社会变化引发的社会问题和危机以及其对“英国性”的威胁与挑战。
一、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与“英国性”
现实主义小说的艺术性自19世纪末以来就颇受评论界的诟病,其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建构功能更是一直被学界严重忽视。英国文学评论家博蒙特说,“在文学和文化史这块三明治中,现实主义像夹在新鲜的浪漫主义和新奇的现代主义中间那块无滋无味的午餐肉”。[1]博蒙特的这个比喻形象地说明了现实主义文学在批评界的处境。作为19世纪最重要的艺术文化运动,现实主义企图矫正浪漫主义对生活和事物过分理想化的描绘或塑造,倡导以客观、冷静的态度观察和记录生活和事物,还原其本来面目,因此,“忠实于现实生活”被现实主义小说奉为圭臬。然而,现实生活中,伟大人物何其稀少而芸芸众生何其众多,所以现实主义小说塑造的主人公多是普通人,甚至还有大量罪犯、窃贼、妓女、伪善者、私通者等负面评价人物形象,这成为19世纪后期兴起的文学流派(如唯美主义文学)对其抨击的主因。而且,为生活、生存奔波劳碌的普通大众身上的特性是否可以被看作英国人的民族特性也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在等级观念根深蒂固、精英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英国,尤其是19世纪以前,出身高贵、拥有财产的贵族、乡绅和文化精英才被认为是民族的代言人,普通劳动者的卑微与高大的民族特性相去甚远。因此,致力于表现普通人的“生活体验”的现实主义小说在英国民族性研究领域很难引起重视。
进入20世纪,现实主义小说的叙事艺术受到现代主义的挑战,后者认为前者“粗糙的线性故事、幼稚的全能叙述者以及关于语言透明度的肤浅假设”[2]使它不具有艺术价值。20世纪重要的现代主义代表作家伍尔夫在日记中批评:“现实主义的叙事简直令人恐怖:从午饭到晚饭一直在进行。”[3]形式主义批评家弗莱在其《批评的解剖》中对现实主义的批判更为严厉,声称现实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反文学的”,因为“文学最重要也是最熟悉的一大特征就是不把描述精确当作支配性的目的”[4],而且“现实主义小说家不久就会发现文学形式自身的要求和貌似可信的内容之间是相互对抗的”[5],所以现实主义小说的形式和内容之间的张力使它不可能真实。后现代理论家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抨击现实主义是一个关于模仿的肤浅概念,“永远介于墨守成规与庸俗之间”,要是给它下个定义,那“唯一的定义”只能是“企图逃避艺术真实涉及的真实问题。”[6]
然而,正如瓦特在《小说的兴起》中指出,这种对现实主义的曲解明显混淆了究竟什么是小说形式的最原始特征这一问题,因而存在着严重失当之处。在瓦特看来,如果以小说是否表现生活的阴暗面,作为评判其是不是现实主义的标准,是把现实主义小说看作一种倒置的传奇故事了;然而事实是,现实主义小说“力图描绘人类经历的每一个方面,而不仅限于那些适合某种特殊文学观的生活。”[7]也许,现实主义小说不如浪漫主义小说那样激情澎湃、充满奇思异想,叙事技巧不如现代主义小说那样复杂、新奇,但就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和民族文化的构建而言,其“历史意义被严重低估了。”[8]
库玛说:“19世纪是英国性的时刻”[9],但也是“英国小说的黄金时期。”[10]在那个英国主导世界的世纪,英国社会各阶层通过他们的言行、生活方式和态度演绎着多个版本的英国性。那么,哪个阶层可以作为英国性的代言人呢?他们又是凭借何种德行或品行展现、传承或发扬让英国成为世界的引领者的英国性呢?作为19世纪最主要的文学形式和传播媒介,现实主义小说无疑是了解英国社会文化、民族传统的重要途径,也是英国性想象和建构的重要载体。在现实主义小说家笔下,掌管着国家权力和司法的统治阶级败坏了英国宪政制度宣扬的公平正义,假仁假义的中产阶级、伪慈善家们也不能体现英国性的文明特征,而沉溺于享乐的上层阶级助长了英国社会弥漫着的堕落、不思进取和物质至上等“时代病”。现实主义小说家们对这些负面的英国性表征的揭露与批判表明他们已认识到,在社会大变革时期,那些曾经英国人引以为豪的优良特性(这些特性曾让英国走上了发达之路)正在消失。如果作为社会基石的普通劳动者也变得好逸恶劳,贪图享乐,那么这个民族和国家就会万劫不复。与此同时,19世纪作为工业革命主力军的产业工人开始诉求基本生存需求以外的政治权力,成为社会变革不可忽视的力量。这样的社会“情感结构”和文化语境,与现实主义小说家们尊奉的艺术追求和社会责任一拍即合,使他们开启了不同于同时代的政治家、历史学家、文化批评家等社会文化精英对英国性的建构之路。比如,19世纪英国著名思想家卡莱尔虽然也对英国性的沉沦、英国人普遍表现出的信仰失落、金钱至上、耽于享乐、不思进取的现象予以批判,但他给出的解决之道是英雄崇拜和精英统治,他的《文明的忧思》和《英雄及英雄崇拜》两部著作虽然也对工人阶级的劳动予以一定的赞扬,但却试图证明人类历史就是一部英雄的传记。19世纪最有影响的史学家麦考莱不惜对历史进行文学想象,以证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伟大、优越、进步,但其却认为这些成就为辉格党人创造,与普通劳动者了然无涉。显然,对于英国性的负面表征及其对英国社会和民族文化的危害,他们感同身受,但他们提出的解决之道仍然局限于精英阶层,而看不到普通劳动者已成为社会变革的中坚力量。
相反,现实主义小说家们信仰真实对民众的感化之力而致力于忠实地记录普通大众的真实生活,所以他们能够更精准地感知时代脉搏并提出解决“时代病”的切实可行之策,即普通劳动者才应是英国文化的体现者,英国性的践行者。只有当一个个普通大众以优良的英国性为安身立命准则并身体力行时,英国的优越性才不是盲目自大的自我想象,英国的繁荣富强才会长久,英国作为其殖民地和其他民族仿效学习的榜样才更有激励性。因此,几乎在每一部现实主义小说中,都有一位或几位不平凡的普通劳动者形象,他们可能言行粗鲁,举止不那么文雅,穿着也不够体面,但他们热爱自己的工作,崇尚勤劳致富;他们敦厚善良,对他人富有同情心;他们勇敢正直,临危不惧,面对诱惑能坚守自己做人的底线;他们自强不息,自助自立,通过自己的奋斗过上体面的生活;他们真诚奉献,乐于助人,为他人的幸福不惜牺牲自己的利益甚至生命。这些普通劳动者身上散发出的感人至深的人性光辉,让那些比他们富有、社会地位高但德行低劣、贪图享乐的上等人物相形见绌,自惭形秽。现实主义小说通过塑造这样一批不普通的普通劳动者群像,为19世纪英国社会注入一股正能量,表现了现实主义小说家们关于英国民族应该具有的优良特性的理想。
二、勤劳、善良、正直: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中的普通劳动者群像
威廉斯认为,可以通过五个英语词汇的变迁样式看清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前半叶英国社会生活思想的变迁,它们分别是工业(industry)、民主(democracy)、阶级(class)、艺术(art)和文化(culture)。[11]其中,“industry”一词最为重要,因为它带来的深刻社会变革引发了其他四个词词义的变化。“industry”原指一种特殊的个体人类特征——“刻苦、坚毅、勤劳”,15世纪开始作为“勤奋”(diligence)的同义词,“懒惰”(sloth)和“迟钝”(dullness)的反义词,其形容词形式“industrious”(勤奋的)在16世纪开始普遍使用。[12]直到18世纪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首次用这个词指英国的制造与生产机构,它才成为一个集体词,“工业”之意确定并沿袭下来。威廉斯对“industry”词义变迁的追根溯源表明,“工业”与“勤劳”同源具有深远的意蕴。没有一个个个体的勤劳,就不可能形成集体特征的工业。虽然说世界各民族都喜欢为自己的民族贴上“勤劳”这一标签,但是这一标签于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人尤为名副其实。英国人的勤劳、敬业、乐观给18世纪至19世纪前半叶到访英国的许多外国游客留下深刻印象,蒙田、伏尔泰、塔列朗、爱默生等外国名人都视勤劳为英国人的民族特性并对此赞誉有加。[13]狄更斯也在《艰难时世》第10章中声称:“自己(我)有一种不健全的想法,认为英国人民是普天下最勤劳的人民。”[14]可以说,勤劳这一美德被普遍视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最重要的英国性表征不足为怪,它甚至被视作英国人区别于其他民族的重要身份认同。英国小说家安妮·拉德克利夫(Anne Radcliffe)在荷兰、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大陆国家广泛游历后,在游记中写道“按照英国人的标准,没有一位荷兰人的工作可算得上勤奋。……你绝不会见到像伦敦的搬运工那样既能辛勤劳动又会休息的荷兰人。”[15]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推进,英国的社会物质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开始盛行,英国人变的好逸恶劳、贪图享乐。所以,现实主义小说家们企图通过对普通劳动者的讴歌和赞美,让勤劳这一民族优良特性能够继续得到全社会的认同和坚守,并能够在国家发展和民族认同方面继续发挥其重要的作用。在爱略特的《亚当·贝德》、盖斯凯尔的《玛丽·巴顿》、狄更斯的《远大前程》等作品中,均可窥见现实主义小说家们对普通劳动者体现的勤劳这一理想民族特性的重塑与建构。
《亚当·贝德》中的同名主人公亚当“够得上称作是个撒克逊人”,同时,“身上还有凯尔特人的血统”。[16]两种血统完美融合的亚当“姿态昂然”,热爱劳动。他特别不能理解那些“对工作一点兴趣也没有,生怕多做了一丁点儿似的”[17]人,他听到钉锤敲打的声音,“就像是乐队的定音声,对一个要参加前奏曲演出的小提琴手一样:强健的筋肉开始习惯地紧张起来。”[18]不做额外木工的空闲,他总是抓紧时间读书,读过圣经,还读过《天路历程》《神圣战争》、斯迈尔斯的《自助》《贝利字典》《巴比伦史》等书籍,但大部分的空闲时间他还是忙着做算术,因为算术对提高他设计图有益。[19]亚当相信勤劳可以致富,他相信“上帝帮助自助的人”[20],只要勤劳,自己将来“会站稳脚跟”[21],走出一条宽路子来。亚当还是一个责任心、有担当的人。为了家人,他把成家的计划一再推后,拿出自己的储蓄为弟弟交壮丁费;父亲染上酗酒后,他承担起养家的重任,他认为“健壮的人应该挑起体弱的人的担子,而不应该只图自己快活……如果你追求这,追求那,只是为了使自己过得舒畅顺当,那么你在人生途中就走上岔道了。”[22]对于自己,亚当非常有原则,凡是他认定是错误的事和会让自己良心不安的事,都会毫不动摇地戒除之。而如果他认定是正确的事,即使是当地最大的地主反对,他也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而对别人,他总是以仁慈宽厚的心对待。他特别后悔自己不该对父亲那么严厉,自责灵魂中骄傲过多,爱心不足,宽厚不够。当海蒂隐瞒怀了乡绅亚瑟的孩子和他订婚,结婚前夕又弃他而去,最后因杀婴罪被抓入狱时,亚当虽然十分痛苦,但想到海蒂可能比他还痛苦,就原谅了海蒂对他的隐瞒、背叛和伤害。当看到造成海蒂不幸和他痛苦的罪魁祸首亚瑟真心悔过时,亚当也原谅了他,答应留在他的农庄,尽力把他的工作干好,“使得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更好一点的地方,让能享受这世界的人过得好一点。”[23]
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评判,亚当都是一个崇尚勤劳、有道德、有能力、有爱心的完美英国人。如果说亚当要有一点缺点的话,那就是他对于等级影响很敏感,对于比他更具优势的人都格外尊敬,他不具有民主思想,对于“一切既得权益,没有十足根据,他对它们是不怀疑的”,但当他发现亚瑟行为不道德时也敢于挑战他甚至揍他。他虽然没有“整顿天下的理论”,但也敢于“毫不畏缩地谈出他的不同看法”[24]并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意见。在白芝浩等政治家的眼里,这一可爱的缺点反而让亚当成为英国的模范公民,堪为英国人的榜样。这也是爱略特用近乎浪漫主义的笔法塑造亚当这个形象的初衷。
虽然现实主义小说中像亚当这样长相、能力、品德都堪称完美的普通劳动者不多,但拥有和亚当一样的美德的劳动者却比比皆是。《玛丽·巴顿》中的杰姆·威尔逊也是这样一位勤劳、诚实、勇敢、有担当、有责任心的好青年。他是一家庞大的机械工程公司的机械工。他为人忠厚、老实,工作勤奋,利用业余时间发明了一种不用弯轴的器件,获得了专利,被厂主晋升成领班,后来还成为加拿大一所农学院的机械教授。他对母亲温顺恭敬,用专利挣得的钱,为母亲和孤苦无依的姑母每人买了一份养老年金。父亲失业后,他主动承担起养家的重任。在玛丽父亲巴顿的眼里,杰姆·威尔逊“为人稳重,职业也不错,还是一个极其孝顺的孩子,男子气十足。”[25]父亲被困在着火的厂房,杰姆勇敢地攀过架设在高空的梯子,把父亲救出来。之后,又去救另一名工人,梯子随时可能被大火烧断,他们随时有可能从高空跌落下来,但“保全自己生命的那种本能竟然没有战胜救助他人的好心,他并没有把身上背着的人抛下去。”[26]
很明显,杰姆·威尔逊和亚当·贝德除了职业不同(一个工人,一个农民)、生活环境不同(一个城市,一个农村),他们的相貌、经历、信念、身上展现出优良品德甚至爱情都十分相似。这里固然不排除爱略特借鉴了盖斯凯尔的人物塑造和故事情节,但也充分说明对于理想的英国人应该是什么样子,她们的观点是相同的。
在这个不普通的普通劳动者群像中,还有无数的平凡人物值得大书特书,比如《艰难时世》中的布莱克普尔,《远大前程》中的铁匠约瑟夫·葛吉瑞(简称乔),《大卫·考坡菲》中的渔夫坡勾提、车夫巴斯奇、造船工人汉·坡勾提,《爱玛》中的农民罗勃·马丁、《玛丽·巴顿》中的乔布·利、《职工马南》中的赛拉斯·马南、《米德尔马契》中的土地勘测员、农庄管理者凯莱布·高思、《我们现今的生活方式》中的农民约翰·克拉姆等等,这些普通劳动者身上无不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和美德,他们勤劳、善良,讲原则,有爱心,知恩图报,热爱劳动。亚当·斯密说:“下层民众的那些美德,包括……不辞辛劳的勤勉以及严格遵守各种规矩。”[27]在英国工业化时期维系着整个社会最基本的职业道德,在英国推进工业化的进程中功用卓著。富有的人们的夸夸其谈、自我炫耀,不能让一个民族真正变得伟大,只有那些埋头苦干的人才能让一个民族真正伟大。
三、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对英国性建构之原因探析
现实主义小说家们不遗余力地塑造和描绘英国的普通劳动者,主要有四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现实主义小说家们的艺术追求。他们坚持认为伟大源自平凡,平凡才是真实。狄更斯说:“我相信,衣衫褴褛的穷人身上显示出来的德行并不亚于那些衣着华丽的达官显宦,……德行不仅与乘坐马车的人为伍,而且还和赤着脚步行的人同行,德行与其说居住在宫廷大厦,不如说居住在穷街陋巷。”[28]
爱略特则在《亚当·贝德》中对这样的观点进行了进一步的阐述:
不要强加给我们任何美学的条条框框,从艺术领域中,排斥掉那些用粗活磨损了的手擦洗着红萝卜的老妇人,那些在黑暗的小酒店里休息的粗笨的乡下人,那些俯在铁锹上,干人间粗活的圆宽的背和因风吹雨打而迟钝的脸。……世界上没有几个先知、英雄和绝色美人,我不能把我全部的爱戴与崇敬都献给这些罕见的人物,我要把大量的这种感情交付给平平常常的人类同胞,尤其是站在这一大群人前面的几个。[29]
在爱略特看来,洗着红萝卜的老妇人、粗笨的乡下人和饱经风吹雨打的农夫这些普通劳动者是真实生活中的主体。他们通过诚实的劳动挣得自己的面包,虽然粗俗但却值得艺术家去描绘、歌颂。狄更斯、爱略特的艺术主张说明,普通人是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关注的中心和表现的对象。
其次,现实主义小说把以前认为不具有审美意义而未予以重视的、被忽视或被排除的平凡世界的体验引入了文学领域,可以说是19世纪民主运动精神的体现。[30]经过1832年、1867年两次议会改革,“所有道德完好和政治可靠的英国人在道义上被赋予选举权。”[31]随着政治代表选举阵营的扩大,艺术表现的领域也随之扩大。农村劳动力、工厂工人、办公室职员、仆人或马戏团演员等这样的普通人或下层劳动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成为现实主义小说描绘的对象,如《亚当·贝德》中的木匠亚当·贝德,《玛丽·巴顿》中的同名主人公和杰姆·威尔逊,《远大前程》中的铁匠乔,匹克威克先生的仆人山姆·维勒,《艰难时世》中的马戏团长斯利锐。在小说世界里,这些普通的劳动者具有高尚的品质,不仅勤劳、善良、正直,而且敢于与权贵阶层作斗争。在他们的映衬下,上层阶级的人物(如亚瑟·唐恩桑顿、卡森、庞得贝)更显庸俗、虚伪。与真实的世界不同,这些普通人物在小说世界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决定小说情节的发展,有能力掌控自己的命运,也影响着小说中其他人物的命运。尽管在现实政治生活中,居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土地贵族和工商业权贵,但通过现实主义小说展现的世界,我们已看到了不断上升的、自足的底层中产阶级或者熟练的技术工人成为社会的重要力量,捕捉到了一个与主流文化倡导的以亚瑟王、阿尔弗雷德大帝为表征的精英英国性完全不同的版本——平民化的英国性。
再次,改造好逸恶劳和道德缺失的社会现实之需要。19世纪的英国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风行,使这个曾经以勤奋劳动创造财富为荣耀、以工业精神著称的民族以不劳动、悠闲享乐为追求。而1834英国议会通过《新济贫法》规定,凡是接受救济者必须是被收容在习艺所里从事劳动的贫民。把劳动和惩罚联系在一起的这一法律,表明国家意识形态对劳动的贬低和否定。而戴着镣铐劳动的苦役犯每天在监狱和劳动场地往返的场面,则进一步让人们将休闲与自由关联起来,劳动和奴役联系在一起。逃避劳动在社会各阶层中普遍存在,英国议会把周六开会看作是国家进入紧急状态;伦敦的企业主们一到周六便会离开伦敦去度假。[32]19世纪,英国国内的工厂主们普遍认为要是没有纪律约束,英国工人很少有愿意卖力工作的。农学家亚瑟·扬(Arthur Young)曾说:“除了白痴,任何人都知道低等阶层只有贫穷时才会努力工作。”[33]英国工人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名声也不好。19世纪30年代有一项调研记录了大量来自奥地利、法兰克福、萨克森尼、苏黎世等地雇主们对英国员工所发的牢骚,苏黎世的一位制造商雇佣的员工除英国人外,还有法国人、波兰人、匈牙利人、普鲁士人、荷兰人。相比之下,英国人“最不守秩序、堕落、难管理、低俗和不可信懒。”[34]现实主义作家们清醒地认识到好逸恶劳对国家和民族的危害,也深知他们的同时代人不乏对普通民众持有偏见。正因此,他们塑造了一批热爱劳动的普通民众,通过赞颂其勤劳、正直、善良等美德来建构劳动的重要性。
最后,英国国民性激辩的影响。19世纪的英国社会认识到国民性对于一个国家的成功至关重要,因此许多社会精英重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有关国民性的国民教育。然而,英国是个社会阶层分明的社会。在英国国民性的形成过程中,上层阶级、中产阶级和普通劳动者都做出过各自特征明显的贡献,如上层阶级引领的绅士文化,中产阶级代表的开拓进取精神,普通劳动者的勤劳、忠诚、正直、善良美德等。因此,在国民教育中,以何种文化为主导存在着很大的分歧。19世纪英国著名的文化批评家阿诺德认为英国上层阶级已蜕化成了“野蛮人”,而在思想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是只重实用的“非利士人”,下层劳动阶层则是缺乏“最鲜明的同情心、最迅速的行动力”的“群氓”[35],他说:“如果只有野蛮人和非利士人能随心所欲地行事,这个制度倒也方便实用,但现在群氓也来随心所欲了,那就有点麻烦了,会导致失序状态。”[36]阿诺德对下层阶级持有这样的认识与工人阶级运动兴起有关,也代表了当时精英阶层的普遍认识,即下层阶级懒惰、无知、没有追求、缺乏理性。然而,为广大人民群众写作的现实主义作家们不认同主流社会对下层劳动阶层的歧视,他们认为英国的成功与进步应该更多地归功于民众而非统治者。普通劳动者并不是精英们认为的那样无知,他们有追求,有高尚的爱好。在《玛丽·巴顿》中,盖斯凯尔用充满赞叹的口吻写道,在曼彻斯特、兰开夏等工业区,存在这样一些不为世人所知的工人,他们虽然在不断地穿着梭子,却在永无休止的穿梭声中把牛顿的《数学原理》放在织布机上,利用工间休息、吃饭的时候偷偷抽时间看上几眼,夜深人静的时候如醉如痴地研读;也有对自然科学领域几个比较有兴趣的学科有浓厚兴趣的工人,如林奈代分类法、自然系统、植物学和昆虫学。有些工人虽然语言粗鲁,长相平平,但却能说出方圆百里所有植物的名称和习性。盖斯凯尔还援引了一位史密斯爵士向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请教有关一种植物的知识,这位植物学家不能解决史密斯爵士的问题,便向他推荐了曼彻斯特的一位纺织工人,以此说明有些工人的科学知识虽然是业余的,但达到了专家水平。[37]毫无疑问,在现实主义小说家看来,勤劳、善良、正直的普通劳动者是有能力担当“成就英国伟业的使命”[38]的。
四、现实主义小说对英国性建构之意义
可以说,现实主义小说家们通过塑造一批勤劳、善良、正直的普通劳动者群像来建构英国性具有非凡的意义。首先,对普通劳动者的讴歌和颂扬,体现了现实主义作家们具有的民主思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对消除不同阶级、特别是下层阶级和中上层阶级“两个民族”(迪斯雷利语)之间的矛盾有一定的作用。其次,考虑到小说读者群体的庞大和小说的社会地位,现实主义小说赞美勤劳、善良、正直这样的美德,有助于匡扶社会正义,消除拜金主义、享乐主义造成的不良之风,增进人们的道德感。再次,赞扬劳动、肯定劳动的重要性,有助于消除当时社会上普遍对劳动的歧视。劳动甚至具有救赎功能,在《米德尔马契》中,劳动使游手好闲的公子哥弗莱德·文西转变成一位勤劳有为的农业家,获得了幸福的爱情和社会的认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现实主义小说家们肯定了普通劳动者在英国民族性塑造中的重要作用。爱略特在《亚当·贝德》中用第一人称复数叙事者的身份,用充满共情的语调对亚当这一形象的象征意义做了充分的阐述:
我们每一代农民手艺工人中,到处都培养了像他这样的人,他们有遗传的丰富感情,这种感情是建立在共同需要与共同勤劳基础上的,朴实的家庭生活所哺育出来的,他们有遗传的才能,这种才能是在熟练勇敢的劳动中锻炼出来的。他们步步向上,很少是作为天才,而多半是作为有技术、有良心、足以做好他们的工作的诚实刻苦的人而上进的。他们一生的影响所及,不过是他们周围的邻近地区,但你几乎必能发现他们后来的一两代人还把某条好路、某些建筑、某种矿产的应用、耕作的某些改进、教区某些陋习的改革和他们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他们的雇主因为他们的劳动而更为富足,他们的手工制品经久耐用,他们的脑力劳动的成果指导了其他工人的双手。[39]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作为个体的亚当,其成长离不开英国历史的土壤。但正是拥有像亚当这样无数勤劳、实干、有上进心的普通劳动者,英国才成为了工业革命的发源地。也正是这些具有高尚品德的普通劳动者,使得英国优良的文化传统得以传承。他们身上体现出的英国性,用19世纪英国作家帕蒂森(Mark Pattison)的话说,就是让英国成为一个“典范性的国家”。[40]
总之,现实主义小说家们基于他们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情感结构,对当时社会精英发起的重建英国性运动,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并积极投身其中。他们立足现实,从英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并借助道德策略和对美好人性的塑造,提出了他们对英国性的主张。对勤劳、善良、正直的普通劳动者以及自助自立者和真诚奉献者的褒扬构成了他们作品的主基调,体现了他们对理想英国性的想象。他们对英国性的建构具有平民化、民主化和道德性的特征,较之于主流意识形态宣扬的宏大但荒谬的英国优越性更接近普通大众,更契合时代需求,因而更具影响力。在他们心目中,勤劳、善良、正直、自助自立和真诚奉献这些美德,是“应然的”英国性的重要内涵和具体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