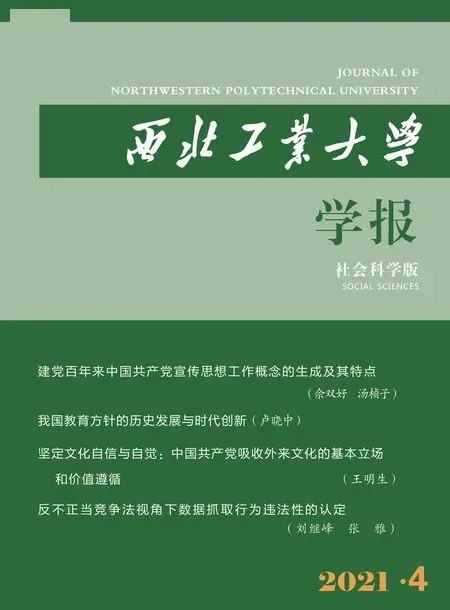《牧师老宅》:语境、文类与诗歌作品的解读
2021-11-30张耀平
张耀平
放在文学史的背景下,单纯以作品质量来衡量,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1887—1915)可能算不得第一流的诗人,我们要讨论的这首《格兰切斯特的牧师老宅》(以下简称《牧师老宅》)也算不得英国文学中非读不可的诗作;但从文化史、文学传统以及由此引出的现代性与历史断裂等问题的角度来看,布鲁克和这首《牧师老宅》则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的题目。
一、诗人布鲁克与布鲁克身份神话
布鲁克同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道森(Ernest Dawson)、劳伦斯(D.H.Lawrence)、萨松(Siegfried Sassoon)、艾略特(T.S.Eliot)、欧文(Wilfred Owen)和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等诗人大致是同时代人。他自然是没有艾略特、叶芝、劳伦斯那样的思想深度,也没有他们那样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和思考。作为同样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士,同萨松、欧文、格雷夫斯描写战争中人的诗作相比,他的战争诗,尽管当时红极一时,但今天读来,让人不免觉得流于天真而肤浅。甚至同颓废叛逆的道森相比,他也没有能够留下诸如“美酒与玫瑰装点的日子”“随风而逝”之类的名句。终其短暂的一生,布鲁克似乎都没有从精神上走出学校,没有走出他读的书,尽管他曾去欧洲大陆、加拿大、美国、南太平洋一些岛屿游历,一战爆发后参了军,最后死在行驶于希腊和土耳其之间达达尼尔海峡的船上。然而,布鲁克又的的确确是一个以诗歌产生了重要影响,以诗歌建立起一个布鲁克身份神话的诗人。下面一段话摘自1922年——此时距他去世已有7年之久——刊载于著名的《诗歌》期刊上一篇对他的事迹成就予以回顾总结的文章:
自弗朗西斯·汤姆逊之后,不曾有任何一位诗人,像鲁伯特·布鲁克这样,在创作的当下即获得承认。他来过了,他歌唱了,他征服了。他的诗是一种突然而至的声音;旋即,这声音消失在远方,消失在一个距离他热爱并歌唱过的祖国十分遥远的地方。而他的死为他的诗赋予了新的生命。[1]
通过评论家对他热情洋溢的褒奖,不难看出他在当时人心目中的地位。
事实上,时至今日,学界仍对他饶有兴趣,除了他的作品——包括书信——不时有新的版本推出而外,各种研究著述也是层出不穷。早在1954年,大量堆积的研究著述就让学者觉得有必要编写一本《鲁伯特·布鲁克研究资料目录》。[2]近年来,专论布鲁克的著作,择其要者,就有莱曼《鲁伯特·布鲁克的生平与传奇》[3]、德拉尼《新异教徒:鲁伯特·布鲁克朋友圈的友谊与爱情》[4]、琼斯《鲁伯特·布鲁克的人生、死亡与神话》[5]、里德《永远的英格兰:鲁伯特·布鲁克传》[6]、博伊尔《鲁伯特·布鲁克:英格兰的最后一位爱国者》[7]、马斯《鲁伯特·布鲁克:诗歌、爱情与战争》[8]、德拉尼《死得绚烂:鲁伯特·布鲁克传》[9]和米勒《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鲁伯特·布鲁克》[10]等近10部。国内也于2017年出版了江鑫鑫翻译的《鲁伯特·布鲁克诗全集》。[11]
而且,布鲁克的诗名,还走出书本,走出学术圈,演变成为一种布鲁克身份神话。这位相貌俊朗,在战争背景下于人生的春天即不幸离去的战士诗人,受到广泛追捧,幻化为一个文化符号——一个象征着纯真青春,象征着诗意的传统英格兰,象征着所谓“高尚的闲逸”(Otium cum dignitate)这一自古罗马以来相当一部分西方文人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和生活方式的文化符号。
通过以上梳理,我们不难看出,围绕布鲁克,存在一种反差:他的诗歌创作似乎支撑不起他担负的盛名和所产生的巨大文化影响。如何解释这种(似乎存在的)反差?本文认为,布鲁克其人其诗的精神底色,是早已淹没在主流的基督教文化之下的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的哲学思想;人们之所以追捧他,围绕他之所以能够建构起来一个布鲁克身份神话,是因为他的诗歌撩动了潜伏在部分西方文人心底的精神梦想;当然,反过来说,他的诗歌也应该放在这样的精神传统中来读,而不是用叶芝、艾略特、萨松、欧文等的路子来要求于他。
可以说,布鲁克是把人生当哲学过了;而从他所表现出来的人生态度和人生追求来看,对他影响最大的当属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
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都形成于古希腊晚期,都是在希腊化时期以及古罗马时期才渐成气候,但对于后来西方文人的精神境界形成了深远影响。伊壁鸠鲁派的鼻祖伊壁鸠鲁(Epicurus of Samos)和斯多葛派的宗师芝诺(Zeno of Citium)都没有著作流传下来;他们的思想后人只能通过拉尔修(Diogenes Laertius)《名哲言行录》以及古罗马哲人如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塞内加(Seneca the Younger)等引述的片段来加以了解。总结起来说,伊壁鸠鲁派把追求快乐视为人生的目的;这里的快乐主要指精神的快乐,而不是物质和荣誉等带来的感官快乐,因为物质和荣誉在带来快乐的同时也往往带来痛苦;要获得精神的快乐,就要追求一种“藏”的生活(拉丁文lathe biōsas,英语即live hidden),尽可能回避社会政治和公共生活,尽可能回避不必要的痛苦(比如对于神灵和死亡的恐惧等);而友谊是实现快乐人生的重要途径。质言之,伊壁鸠鲁派所倡导的精神的快乐,实际主要就是内心的恬静。[12]
斯多葛派的思想核心是宇宙决定论和独立的个人,认为世界万物无不服从于自然律,偶然是不存在的;个人德行就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意志,就是“顺应自然”“顺应理性”;个人不可能控制外部事件,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想法,可以选择自己的行为,因而重要的不是外部发生了什么,而是我们对于外部事件做出何种反应;焦虑、恐惧、嫉妒等痛苦都源于对事物的错误认识,智者可以不受任何不幸的侵扰,美德(智慧、公正、勇气和节制等)足以让个人实现幸福人生。[13]
在历史上,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二者之间相互竞争,彼此攻伐,但后来的文人多并不执于一端,而是从中汲取思想元素,融入自己的世界观和行为方式。对于诗人、学者布鲁克来说,更是将来自两个哲学派别的思想元素同文学传统相结合,去寻找自己的处世方式和表达方式。具体到《牧师老宅》一诗,则主要是伊壁鸠鲁派的哲学思想同牧歌传统的结合。
下面我们通过布鲁克的成长经历、青年时期的交游与游历、后来的从军及不幸离世,来对表现于他身上的伊壁鸠鲁派和斯多葛派的思想态度做一番粗略的考查。
布鲁克成长于远离普通民众,专注于探究知识,传播知识的象牙塔中。他的父亲一生任教于著名的拉格比公学,长期担任舍监。拉格比公学——这也是半个多世纪前著名诗人阿诺德(Matthew Arnold)成长的地方——便是他的家,便是他的人生起点。
布鲁克在剑桥时期的生活状况,我们透过因他而成为名胜的两处地方来看,可能最为直观。一处是“果园”,一处是《牧师老宅》这一诗题所指的一幢老房子。也许是巧合,也许在最初时用此雅称相呼相传,确实是青年学子用以表明心志的姿态,当年伊壁鸠鲁在雅典开设的学校就叫“果园”,17世纪诗人马维尔(Andrew Marvell)一首著名的牧歌诗题目也称《果园》。
“果园”因布鲁克而成为剑桥一景。“果园”位于离剑桥不远的格兰切斯特村。1897年,一群经常坐卧在附近草地上聚谈的剑桥学生,请求女主人允许他们在她家果园里用茶。自此,对于一拨又一拨住宿附近的剑桥学子来说,“果园”茶叙成为大学生活的固定节目。“果园”主人似看到潜在的商机,于是开始接纳学生租住。1909年,就读于国王学院的布鲁克毕业后搬了进来。而布鲁克在剑桥颇有诗名,交游极广,很快为果园茶叙吸引来众多日后名震天下的嘉宾,这其中有小说家伍尔夫(Virginia Woolf)、福斯特(E.M.Forster),有诗人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有经济学家凯恩斯(Maynard Keynes),有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有传记作家斯特拉齐(Lytton Strachey),有画家约翰(Augustus John)——这样一伙人聚集在一起,基本就是后来伦敦布鲁姆斯伯里街那个文人圈子的早期剑桥版。时至今日,“果园”仍在。虽然如今的“果园”,对于当地人来说,成了一个买一份茶点,坐在苹果树下,伴着头顶上飞来飞去的蜜蜂,享受缓慢时光的好去处;对于游客而言,不过是又一个有名人留下过足迹的旅游点。但透过眼前纷扰,仍可想象布鲁克那些诗人、思想家、艺术家、科学家朋友们,在一派乡野背景下,在这里上演的灵魂交流。
布鲁克后来搬出“果园”,迁往同在格兰切斯特村的“牧师老宅”。现存的这座房子建于17世纪晚期,原本是教会财产,后转变为私人住宅,所以称“牧师老宅”。布鲁克在这里租住时,房主是尼福夫妇(Henry and Florence Neeve)。1915年,布鲁克以27岁之年不幸离世,他的母亲买下这座房子,赠予布鲁克的好朋友、经济学家沃德(Dudley Ward)。
20世纪初年是一个同时代诗人艾略特看出西方文化空前精神危机的时代。在剑桥时期,以“果园”和“牧师老宅”为主要背景,布鲁克和他的那一圈朋友呈现出的生活态度和生活方式有很多自由奔放,蔑视礼俗,甚至惊世骇俗之处;但这种远离公共生活的尘嚣,沉浸在诗、思想观点和学术探究之中,沉浸在友谊的温情中,从中获取人生快乐的取向,则明显是伊壁鸠鲁派的路数。不错,他们确有“左倾”的表现,但对于他们来说,现实问题更多的只是观点和知识。伍尔夫将布鲁克这个朋友圈称之为“新异教徒”(Neo-pagans),所强调的无疑是他们与基督教之前的古典时期异教徒之间在精神上的契合。
1913年秋,诗人经美国来到南太平洋的法属塔希提岛,在这个激发画家高更画出其最杰出作品的地方,鲁布克——用评论家德拉尼的话说——“经历了他生命中持续最久的一段快乐时光”,也“写下了他最好的一些诗作”。[14]结合诗人的生活背景和其他诗作,不难想见,这些作品所写无非是异域环境下无忧无虑的纯净感情。这样的诗歌,率真,自然,对于布鲁克来说,可能的确写出了他内心的体认和诉求。但是,自20世纪初以来,奠定英语诗歌主流趣味的是艾略特、叶芝等诗人的作品。用他们的创作来衡量,《塔希提栀子花》之类的诗歌明显是简单肤浅了一些。
布鲁克另外一组被人传诵一时的作品,是总题为“1914”的五首十四行组诗。一战爆发的前夕,诗人赶回英国毅然报名参军。五首十四行诗便是军营中的创作。这些诗作,在战时读来,和参战初期全英上下民族精神高涨,意气昂扬、不畏牺牲的乐观精神相合拍,发表后立刻引起轰动。布鲁克虽未亲历战场硝烟,但战士诗人的形象已然深入人心。1915年复活节,伦敦圣保罗大教堂教长英吉(William Ralph Inge)在布道时朗诵了“1914”中的《战士》一诗。[15]在战时的英国,这样的诗行被传诵一时:
假如我死去,记着这一点便已足够:
我静卧在这里,让异国他乡的一角
永远变为英格兰。……
战时首相丘吉尔也对布鲁克予以热情赞扬,还拿他青春英俊的外貌说事,说他代表了精神与外在的和谐。
复活节之后不到一个月,布鲁克在海上执行任务时,因虫叮而罹患败血症。4月23日,当船航行在连接爱琴海和土耳其马尔马拉海的达达尼尔海峡时,不幸离世。这位后来有“金发碧眼的英格兰阿都尼斯”之称的年轻诗人,在一个文学史上刻下永恒印记的日子(莎士比亚忌日),死在一片长期以来和另外一位英年早逝的英国诗人拜伦联系在一起的异域海洋,更强化了人们的惋惜之情。于是,在当时很多人看来,《战士》一诗成为诗人自己的光荣写照,成为他永恒的墓志铭。于是,一个关于布鲁克——一个清纯美好,为国捐躯的诗人战士——的身份神话从此形成,一直流传至今。
后来的学者评论这一组诗歌作品,往往同萨松、欧文等和他一起走上战场的战士诗人最终留下的满纸沉重的幻灭感的作品相比较,多强调其天真而过分乐观的一面,或认为布鲁克身份神话只是政治操弄的结果。如德拉尼就说:“这一组十四行诗给国内的人们完美地呈现出了他们愿意想象的战争的样子;而不是欧文所知道的战争的样子——‘说什么为国捐躯幸福而光荣,不过是一则古老的谎言。’”甚至认为“布鲁克死后,《战士》一诗在流传中沦为滥情,沦为关于这场大战的文化俗套。”[16]另一位评论家科尔也评论说,在英国不仅需要一个战士偶像,而且需要一种激发民族意识的语言的时候,布鲁克恰巧出现了,恰巧完美地满足了这样的需要。[17]
但这样的解读太过简单了,没有触及文化和思想深处的东西。应该看到,在他选择奔赴战场,坦然接受牺牲的态度中,有他所接受的教育灌输给他的斯多葛派人生哲学的影响。指出这一点不是为了简单的褒扬,而是为了找到放在上面来解读他的诗的坐标。
二、牧歌与“高尚的闲逸”
说到读诗的坐标,除了写作背景,当然要考虑诗歌所属于的文类。一首诗有很多方面要借助文类的习惯和规矩而获得意义。《牧师老宅》属于“牧歌”,那么,这首诗就要放在牧歌的文类语境中来读。
什么是牧歌?评论家阿斯珀搜罗西方学者的研究,罗列出这样一些描述:
牧歌“是对天真和快乐的双重向往”;牧歌的普遍精神取向是黄金时代;牧歌建立于艺术与自然的对立之上;牧歌的根本动因是对城市生活的憎恶;牧歌的“中心原则”是“情感误置”;牧歌表达的是闲逸理想;牧歌是对文艺复兴时期“审美柏拉图主义崇拜的最恰当的诗意表达”,或者说是对希腊化世界的伊壁鸠鲁派思想的最恰当的诗意表达;牧歌是透过乡野世界的媒介来看待普遍经验的方式”。[18]
“牧歌”这个概念实在太大,可以是诗,可以是小说,可以是戏剧,甚至让人觉得,把“牧歌”视为一个文类有些勉强;但从另一方面来看,似乎只有从文类的角度来看,才能够给出一种宏观的描述。以上阿斯珀所列举的,是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结合不同作品,所得出的对牧歌的认识。综合来看,作为一个文类,所有“牧歌”文学都表现出这样两种倾向:其一,视牧人的乡野生活为城市社会的反面,那里没有城市的复杂和堕落,那里是一片人心纯澈的净土;其二,作品中的牧人生活不过是理想的投射,是假人假景,而不是对现实的真实生活的刻画。所以,所谓“牧歌”,实际透着浓浓的文人气。所以,也有学者干脆说:“牧歌是城市的诗歌,由城市诗人发明,目的在于考查检视城市的困境。”[19]
人类文明的进程是一个不断地、越来越快地向城市集中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们也不断地、越来越强烈地感受到自我的异化、彼此的倾轧和各种各样的压力。而农作和乡村作为人类最古老的生活模式,它简单、稳定、宁静,为人类提供了日后可以不断回望、寻求慰藉的故乡。这种回望的需要,早在以城市为社会重点所在的古希腊罗马时期,似乎就已存在。古希腊诗人忒俄克里托斯(Theocritus)的田园短诗告诉人们,城外幽静祥和的乡野才让人向往。古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的《牧歌》被后世视为“牧歌”文学的先河和范本,虽然其中不无打通与现实联系的篇章,但后人竞相追慕,因而成为范式套路的,则是这样一些因素:石上清泉、溪边松柳、阳光与绿荫交错的田野背景,在这样的背景下,牧人在无忧无虑地歌唱,歌唱生活中简单易得的快乐,也表达由人生固有的不可避免的不幸——如爱情的挫折或亲友的早逝等——而引发的沉思。西方文学史上留下很多模仿维吉尔《牧歌》的作品,其中的各种母题(motifs)、意象甚至人物都被广泛地借用。
维吉尔的《牧歌》在文艺复兴的翻译热潮中被翻译成了英文。但英国文学中,“牧歌”更多表现为一种融入作品中的元素。斯宾塞(Edmund Spenser)的《牧人月历》(The Shepheardes Calender)固然包含有对于英格兰乡村每个月份物候变化的准确刻画,对牧人爱情的生动描写,和对各种民间习俗礼仪的记录,但全诗充满着对于当代现实生活(包括现实政治)的关注和评论。锡德尼(Philip Sidney)的小说《阿刻底亚》(Arcadia)有着“牧歌”的形式——乡间是逃避可怕命运的理想庇护所——但是在神谕、牧人的歌唱、男扮女装假冒他人、神奇的巧合、复杂的恋爱关系等因素背后,贯穿始终的是宫廷政治的内容。莎士比亚的《皆大欢喜》在营造阿登森林里的“牧歌”生活的同时,又在嘲讽着、颠覆着这种人造梦幻。像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的诗作《激情的牧人致心爱的姑娘》(The Passionate Shepherd to His Love)那样纯而又纯的“牧歌”,在英国文学中反倒好像是例外。17世纪赫里克(Robert Herrick)、马维尔等人的作品在布鲁克的诗中留下明显的影响印迹,但这些作品在深厚学养的基础上追求精致隽永的歌咏表达,其中的“牧歌”元素往往只是诗人拿来为我所用的程式化意象,甚至可以说是一种文人气装点。18世纪崇尚古典,蒲伯(Alexander Pope)的个人禀赋似乎也适合写这样的高度程式化的作品,然而他的“春”“夏”“秋”“冬”四首《牧歌》(Pastorals)以及《温莎森林》(Windsor Forrest)等早期作品中的一些“牧歌”段落,里面虽有牧人和牧人的歌唱,但由于缺少透过想象,远眺生活之外的理想乡野的距离感,实际成了自然诗。从18世纪末开始,经过汤姆逊(James Thomson)《四季》(The Seasons)、扬格(Edward Young)《哀怨,或关于生、死、永生的夜思》(The Complaint:or,Night-Thoughts on Life,Death,&Immortality)、哥尔斯密(Oliver Goldsmith)《荒村》(The Deserted Village)等所谓感伤主义诗歌的短暂准备之后,当彭斯(Robert Burns)、克雷布(George Crabbe)、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等浪漫主义诗人真正把目光投向现实的乡村,为我们描绘现实的——而非想象的——乡村中牧人、农人的日常的时候,“牧歌”作为一个文类便失去了基本的思想基础。
在英国文学史上,“牧歌”元素最清晰、流传最持久的,可能要数如弥尔顿的《利西达斯》、格雷(Thomas Gray)的《墓园哀歌》(Elegy Written in the Country Churchyard)、雪莱的《阿都尼斯》(Adonais)和阿诺德的《瑟西斯》(Thyrsis)等一类牧歌式挽歌。同样,这类挽歌在古典世界就已定型。后人写牧歌式挽歌,不仅整体结构、措辞语气沿用古人,就连诸如上面用作作品标题的“利西达斯”“阿都尼斯”“瑟西斯”等都是忒俄克里托斯或另外一位古希腊诗人彼翁(Bion)或维吉尔“牧歌”作品中的人物。在传统“牧歌”中,牧人往往也是歌者、诗人,而这些挽歌,除格雷的《墓园挽歌》悼念的是一位无名的乡野“缪斯”而外,其他都是献给诗人的同道友人的。在挽歌中,这些同道友人是牧人,也是诗人,作者在痛悼人生的无常、英才早逝之余,表示要用最美的花朵来装点死者的坟墓,然后邀请潘神、牧神、林仙、水仙以及自然界的一切都来共同哀悼生前在这里放牧、唱歌的牧人—诗人,最后意识到死者没死,只是去到另一个世界,在那里摆脱了人世间的喧嚣、污浊和烦恼,找到了永生、和谐和安宁。理想化的乡村纯净和谐,处处鸟语花香,便是那个美好世界的象征。
最后,为讨论布鲁克《牧师老宅》做准备,再来谈谈牧歌的一个重要主题:“闲逸”。“闲逸”一词这么用在汉语中,不免生硬,因为这里的意思本就是外来的,它和汉语中常说的一些“闲逸”的近义词——如“闲适”“逍遥”“散淡”“悠然自得”等——都不是一回事。这里说的“闲逸”,其意思在根源上来自古希腊语“skhole”和拉丁文“otium”,这两个词所对应的英语词是“leisure”,但内涵远远超出“leisure”。英语中“学校”(school)、“学者”(scholar)和“经院哲学”(scholasticism)这些词,其最终源头都是古希腊语“skhole”。古希腊语“skhole”,本义是“闲暇”“清闲”“安逸”“慵懒”。在古希腊时期,由于奴隶承包了全社会的体力劳动,自由民衣食无忧,且有大把的闲暇时光。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部分社会精英推崇在冥思、辩论、研讨哲学、推演数学的过程中度过漫长时日的生活方式。于是,“闲逸”便产生了另外一个意思,指古希腊人随处可以上演的无实用目的指向、非功利的问题讨论。然后,自然而然,这个词又有了讨论场所的意思——这样的讨论场所便成为后来的“学校”。实际的历史当然要复杂得多,但词汇在语义流变的过程所留下的痕迹告诉我们,“学者”“学校”——自然还有“学术”——的根都在“闲逸”。事实上,在其他主要的现代西方语言中,表“学校”的词——如法语的“école”、西班牙语的“escuela”、意大利语的“scuola”、德语的“Schule”、俄语的“школа”(即拉丁字母的shkola)等——其词源的最终源头也都是这个古希腊语“skhole”,即“闲逸”。
概括地说,“闲逸”实际指的,是一种无功利、也不关心其外部指涉的精神追求和知识追求。很明显,这样的“闲逸”同伊壁鸠鲁派所追求的恬静的精神快乐,同斯多葛派所强调的顺应自然律,接受世界,接受生活的态度,都是相通的。
现代人存在工作中人和生活中人的分裂。对于古典时期的精英们来说,这种精神追求、知识追求是“志”,是“业”,也是生活本身。那么,这样一种我们称之为“闲逸”的精神追求、知识追求,其价值和用途是什么?希腊人似乎不屑于提出这样的问题。据说曾有一个学生跟着欧几里得研习《几何原本》,问学这个能干什么,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得鄙夷地对身边人说,给这家伙三个小钱儿,他学东西竟然还有所图!
也可以说,古希腊人是准备了答案的:这样的精神追求、知识追求,其动因和目的就在于:“认识你自己”(to know thyself)。不过,这样一个高标超俗的理由,到作风务实的古罗马时代,就不大容易说服人了,所以西塞罗、小塞内加等人做了大量的论证,来证明社会精英的“闲逸”追求之于社会和大众的价值,于是便有了“高尚的闲逸”的说法。
不用说,这样一种古代遗风,和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发展而建立起来的社会生活方式是格格不入的,因而不可避免地被越来越挤向边缘,但它在某些社会群体中仍有其根深蒂固的影响。布鲁克便是一个对这样的古代遗风恋恋不舍的现代人,写于1912年的长诗《牧师老宅》,其主题便是“高尚”的闲逸。
剑桥大学一直流传着一个传说,据说踏着三一学院的田产,可以一路从剑桥走到牛津。自然,坐拥如此资产,尽可以让自己的教授们“闲逸”。维特根斯坦原本在曼彻斯特大学学机械工程,因机械工程而喜欢上数学,由数学进而痴迷于数理逻辑,进而走进哲学的天地。他在厌倦剑桥的学院生活后,选择回到奥地利,去一个山区小学教农家子弟;在厌倦教师生活后,又重新回到英国,继续先前的哲学研究。他可以慷慨资助身边的朋友,可以对自己的老师罗素撰写大众读物去赚取稿酬大不以为然。这一切都是因为父亲给他留下一大笔遗产,他才可以任性“闲逸”。就社会环境来说,古希腊那种优越的氛围在后世很难再现。所以,很早人们就意识到积极进取、热闹繁忙的城市公共空间中的“无闲”生活(negotium)和宁静自在、独处内省的乡下一己空间中的“闲逸”生活之间的差异和对立。于是,便有了人造乡野:在古罗马时期出现了居住于乡间别墅的时尚,而更早之前就产生了艺术想象的“牧歌”。
三、在阅读坐标下来读《牧师老宅》
全诗共141行,分为5个长短不一的部分。诗的写作场景是柏林的一家咖啡馆。置身都市,置身城市文明的典型场所——咖啡馆,置身德语世界的众声喧哗中,异乡人顿时生发出强烈的格格不入的感觉。哪里是归处?自小受的古典教育和长年读的书,让他下意识地想到的解决方案就是:牧歌。即便是刚才出门时匆匆一瞥的小屋门前的丁香花,和可以想知的花坛里、小径旁,正在开放的康乃馨、石竹花、三色堇,也是安慰啊!一想到植物的景象,思绪便不肯停下,便不由自主联想到让他魂牵梦萦的浓荫婆娑的格兰切斯特。那里才是真正可以走进去的,可以亲近,可以得到精神慰藉的心灵家园。第一部分结尾处旁边顾客的一声德语“Du lieber Gott!”(噢,我的天!)才把他从梦幻中拉回现实。
第18~33行构成诗歌的第二部分。现实中身在此处的自己“病病歪歪,热汗淋漓”①,多么渴望能回到彼处。在这里,德国被视为到处是管制,到处是规训的现代文明的代表;而英国则被想象为自由散漫,甚至没有时间意识的过往时代的缩影:“此处,郁金香开放,像听到吩咐”,连草地都禁止行人入内;篱笆旁一朵“自作主张,不修边幅地绽放”的英国玫瑰,让我想到那里——“那里,随着白昼将尽,/ 太阳,自由散漫地,渐渐西沉,/ 去休息,去唤醒一颗迷迷蒙蒙,/ 大大咧咧,不甚守时的长庚星”。想象中那样一方自由的天地怎能不让人想要归去。
引出第三部分(第34~71行)的,不再是身边不时听到的只言片语的德语,而竟然是一句希腊语:“eithe genoimen”——诗人已完全进入想象。原文来自据称是哲学家柏拉图所作的一首短诗,表达对于一个名叫“星”(Aster)的美少年的爱慕:“我的星,你在凝望着群星;我多想化作天宇,那样我就可以用无数只眼睛看着你了!”而对于布鲁克,此时让他神往的“星”则是格兰切斯特:于是,他不仅动情地呼喊:“归去!归去!……我多想,此刻,/ 就在格兰切斯特,就在格兰切斯特!”因为那里是一片神奇的所在,“或许是呢,有的人,在那里,/真能和自然、大地什么的建立联系”;在那里,无须非得看到“有牧神在草丛间张望,有水仙/头顶芦苇,在远处浮现,或者是/ 听见,浅浅低吟,羊足潘神的芦笛”,就能感知到“古典从来未曾湮灭”;因为那里是诗的国度,乔叟、拜伦、丁尼生都曾在那里吟唱(当然,追述剑桥的诗歌传统,也是在按照牧歌写作的习惯和规矩,把自己作为这一传统的延续,在建立牧人—诗人的形象);因为那里至今或仍可打通现实与传说,超自然物或仍还存在——而不像眼下这个无趣的现代世界。
第四部分(第72~115行)看似谐谑荒诞,却最是神来之笔,不过也只有放在牧歌写作的习惯和规矩下来看,才能读懂。首先点出,之所以有着如此想要归去的强烈愿望,是因为“英格兰这个国度/ 是真性灵应当选择的去处”,而在全英格兰,剑桥郡“对于明白人,最是美妙绝伦”,而在剑桥郡呢,“我最心仪,/ 则是格兰切斯特那个可爱的村子”。那么,为什么是格兰切斯特?诗人给出的理由让人忍俊不禁:一方面,剑桥城代表城市,自然不行,那的人“精于世故,身材矮胖,/ 满肚子心眼,难得有笑容出现在脸上”;另一方面,历数周围十多个村庄的种种不是——
往南很远有个罗伊斯顿村,那里的男人
面黑,性凶,一口土话带着古怪口音;
在奥弗村,人们张嘴就是脏话,
诅咒谩骂,比特鲁姆平顿人还差,
迪顿的姑娘邋里邋遢,还心地不善,
哈斯顿人全都老迈,三十以下一个不见,
在舍尔福德以及周边一带,
人不仅口斜唇歪,而且心术也歪,
巴顿人附庸风雅,写一些没腔没调的诗行,
在柯顿,到处是闻所未闻的恶行罪状,
麦丁莱发生的事,而且是在圣诞平安夜,
让你无法置信,十足的罪在不赦。
倘若有切里-亨顿人突然冲你一笑,
纵然强悍男儿,都要夺路奔逃;
纵然强悍男儿,宁愿射杀自己的女人,
也断不敢送她们去圣艾维斯村;
纵然强悍男儿,听闻发生在巴伯拉罕姆的事,
都会像守在妈妈身旁的婴儿,不住地哭啼。
而只有在格兰切斯特,在一片“安宁与祥和”中,“男人、女人透着率直的目光,/ 儿童和婉可爱,让人感觉恍若梦里”,而且,“那里的女人懂得本分,该干什么干什么;/ 那里的男人头脑清楚,遵守思维法则。/ 他们崇尚善;他们信仰真”。正如学者科尔所指出的,牧歌所造出的是“一处遗世独立的风景,一处宜人的所在,里面既有城市的文明便利,又有乡野的田园风光,但既不存在前者的堕落奸诈,也没有后者的野蛮鄙陋。”[20]一句话,诗中所描绘的格兰切斯特,只是诗人内心向往的投射,而不是现实的刻画。
布鲁克当然不是牧人,他写花草树木、麦田野兔、阳光清露等,写的是一种想象中理想化的生活状态,一种精神上的依托。归去,也不只是为了可以“自由散漫”,可以“大大咧咧”,不只是为了那里的云朵、晚霞、岸柳、草地和流淌的河水,而是因为在“那里”,可以找到血脉的所在和灵魂的归属。所以在最后的第五部分(116~141行),发出了这样的询问:
告诉我,在那里,“美”依旧长在?
还有“确然”?还有“安宁”的青睐?
还能寻得那片片茂密的草地,
好忘记痛苦、各种谎言和诸多真理?
就如同阿诺德在《多佛海滩》(Dover Beach)中说,现代社会看似“多姿多彩,美艳,崭新,/ 但实际没有快乐,没有爱,没有光明,/ 没有确然,没有安宁,没有缓和痛苦的慰藉。”[21]而在布鲁克的回望和想象中,格兰切斯特似乎蕴藏着这一切。但诗毕竟不是无稽的春梦,诗不是巫术。诗人把格兰切斯特描画成摒绝尘俗,如在云端的所在,还得有下来回到现实的台阶!所以,他只能把内心的向往以问句来展现。不仅能否在那里找到“美”“确然”“安宁”自己吃不准,就连风景——诗人当然知道,牧歌的风景是想象——是否真如以上诗中所说也吃不准的:
告诉我,守护着那片神圣土地,
那些榆树丛是否依旧傲然挺立?
那些核桃树,浓荫如梦,是否依旧,
会遮蔽那条沾染不上学院气的河流?
清晨依旧羞涩,冷峻,像一个秘密,
像圣洁的海中维纳斯,光彩熠熠?
日落依旧是一片金色大海,
从哈斯林菲尔德绵延至麦丁莱?
……
最后那一句“哦,是否依旧,教堂的钟停在两点五十”,让不少实心眼的读者四处打探,想要考证清楚,究竟是哪一座教堂的钟停在了两点五十。实际诗人在为我们呈现出一副心中梦想的可以找到伊壁鸠鲁派所说的“内心的恬静”,可以实现西塞罗所说的“高尚的闲逸”的格兰切斯特村之后,再回头告诉我们,牧歌不仅是“情感误置”,也是时间错乱。
批评家多博雷(Bonamy Dobrée)分析蒲伯(Alexander Pope)的牧歌作品的一段话经常为人们所引用。他说:
若问是否做作?做作,没错。不是做作,还能是其他?这同德莱顿笔下的牧人、牧女完全是同类东西。但按这类东西的写法来读,我们就会喜欢……若问是否严肃?是否充满激情?必须说,不是;就诗中似乎要表现的生活来讲,不能说严肃,也不能说充满激情,但就诗论诗,则必须说这是上乘佳作。[22]
不同类型的诗歌有着不同的写法,不同的趣味追求,不同的评判标准。只有把作品放在支撑它的坐标体系下来读,才能走进作品,才能真正读懂作品。布鲁克这首《牧师老宅》也正是这样,忽视它的写作背景,忽视它的主题的思想渊源,忽视牧歌这一文类在写作上的规矩和习惯,是无法真正欣赏,也无法给出有价值的分析判断的。
注释
①国内已有江鑫鑫的译本出版,但为行文方便,以下所引用的诗歌片段均为笔者自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