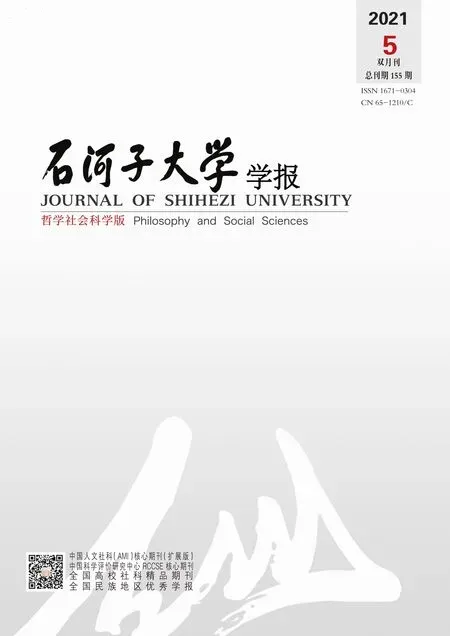唐宋行状创作目的变迁及其影响
2021-11-30杨向奎杨雯钤
杨向奎,杨雯钤
(石河子大学 文学艺术学院,新疆 石河子 832003)
明代徐师曾《文体明辨》释行状云:“盖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或牒考功太常使之议谥,或牒史馆请编录,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类皆用之。”[1]147其中“牒考功太常使之议谥”“牒史馆请编录”“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云云,即为行状的创作目的。徐师曾对行状创作目的的静态总结可谓全面,但动态描述没有涉及。行状的创作目的也具有时代性,受当时礼仪制度、文化心理、社会风气等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时代、同一时代不同的人群之间,三种创作目的会各有侧重。为更加深入分析创作目的对行状文体的影响,本文拟对唐宋行状创作目的的演变及其影响进行探讨。
一、唐宋行状创作目的变迁
传世行状文中,以南朝为最早。南朝行状最著名的是任昉撰《齐竟陵文宣王行状》,该文文尾曰:“易名之典,请遵前烈。”注云:“《礼记曰》:公叔文子卒,其子戍请谥于君,曰:日月有时,将葬矣,请所以易其名者。”[2]2585易名,即由生名易谥号。可见此文请谥之目的。江淹撰于南朝宋明帝泰豫元年(472)的《建平王太妃周氏行状》,是传世行状中较早的一篇,文尾云:“今祖行有期,泉穸无远。素旂望路,彩旌思归。所以垂宣徽容,仿佛金石者,谨详牒行状,具以申言。”[3]370牒状予谁,申言何事,文未明言。但从“祖行有期”“谨详牒行状,具以申言”等所反映的时间点及恭敬态度来判断,其主要目的也应该是请谥。另,据《宋书·文九王传》,建平王刘景素元徽四年(476)举兵奔京邑,兵败被斩。齐受禅,建元(479—482)初,故景素秀才刘琎上书讼景素之冤,有“臣闻王之事献太妃也,朝夕不违养,甘苦不见色”句,据此可知太妃谥号“献”[4]1864。而谥号的获得只能在元徽四年之前。请谥需行状,这正好印证了江淹撰文的目的。
唐代行状承接南朝遗绪,仍以请谥为主要创作目的。目前见于著录的首尾完整的唐代行状共33篇[5]17,其中僧人行状7篇,创作目的与一般世人行状不同,暂不列入研究范围。剩下的26篇作品中,未书写作目的者2篇,仅以请谥为目的者14篇,请谥兼牒史馆为目的者3篇,仅呈史馆者3篇,仅以请托碑志为目的者4篇。总体来看,以请谥为创作目的者17篇次,以牒史馆为目的者6篇次,请托碑志者4篇。从以上数字可见请谥目的在唐代行状中的主导地位。
唐代行状虽然主要以请谥为创作目的,但从仅以请托碑志为创作目的的行状产生时间来看,其中却孕育着新变。以请谥为目的的行状,也会为碑志撰写提供素材。如杨炯撰《中书令汾阴公薛振行状》,与之对应的《大唐故中书令兼检校太子左庶子户部尚书汾阴男赠光禄大夫使持节都督秦成武渭四州诸军事秦州刺史薛公墓志铭并序》已出土,两相对比,有多处人物行事细节及用语都高度一致,可以断定,行状的写作目的是请谥,但在实际操作中,它也承担了为墓志撰写提供素材的功能[6]130。请谥为目的,顺带为墓志撰写提供素材,毕竟不同于直接以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为目的。请谥要牒考功太常,属于私人呈递给官方的文书,而乞墓志碑表,是私人对私人,两种情形下的行状文,其体制格式、语气选材等均有所不同。现存首尾完整的唐代行状文中,有4篇以乞墓志碑表为唯一创作目的,分别是韩愈撰《唐故赠绛州刺史马府君行状》,柳宗元撰《唐故秘书少监陈公行状》、白居易撰《故巩县令白府君事状》《襄州别驾府君事状》。韩愈文文尾曰:“今葬有期日,从少府请,掇其大者为行状,托立言之君子而图其不朽焉。”[7]660能否牒考功太常议谥、牒史馆请编录,由状主身份地位决定,一般不是“托”而可得的,既然“托”立言君子而图不朽,上作者乞墓志碑表无疑。柳文直言:“宗元,故集贤吏也,得公之遗事于其家,书而授公之友,以志公之墓。”[8]549白文篇前有一总题“太原白氏家状二道”,题下注云:“元和六年,兵部郎中、知制诰李建按此二状修撰铭志。”[9]2832均表明上作者以乞墓志之唯一目的。这种文学现象出现在中唐著名作家文集中,未必是历史的偶然。纵观历代行状创作目的,为乞墓志碑表而撰写行状的现象北宋以降大量出现,将之纳入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下考虑,则这4篇行状具有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为乞墓志碑表而撰写行状的现象在宋代较为流行。检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可得行状文411篇,其中110余篇未书创作目的,62篇虽书但不甚明确,故存疑。剩下的篇目中,请谥兼供修史、乞碑志3篇,请谥兼供修史10篇,请谥兼乞碑志2篇,仅以请谥为目的16篇,几种相加,请谥为创作目的者共31篇。供修史兼请谥、乞碑志者3篇,供修史兼请谥10篇,供修史兼乞碑志12篇,仅供修史45篇,几种相加,供修史为创作目的者70篇。仅乞碑志为目的者有146篇,再加上请谥、修史兼乞碑志者17篇,则乞碑志为目的者163篇。除此之外,宋代出现了一些不以请谥、牒史馆、乞碑志为目的的行状,它们更像传记,欲通过行状本身将人物事迹流传后世,可明确判定为此种情况的宋代行状大约有七八篇。
通过以上统计可以发现,与唐代相比,宋代行状在创作目的方面有如下特点。首先,以请谥为创作目的的行状数量增长不明显。这个特点容易理解。唐代“诸职事官三品已上、散官二品已上身亡者,其佐史录行状申考功,考功责历任校勘,下太常寺拟谥讫,覆申考功,于都堂集省内官议定,然后奏闻。赠官同职事”[10]44。宋代一仍其旧,规定“王公及职事官三品以上薨,本家录行状上尚书省考功,移太常礼院议定,博士撰议,考功审覆,判都省集合省官参议,具上中书门下,宰臣判准,始录奏闻,敕付所司,即考功录牒,以未葬前赐其家”[11]2013。职事官三品以上的格限不变,有资格获得官谥的人数就不会大规模增加,那么以请谥为创作目的的行状数量就会相对稳定。其次,供修史和乞碑志的行状数量增加明显,其比例分别占可明确创作目的行状的26.5%和61.7%,尤其是乞碑志的行状,占据了主流。其中原因较为复杂,容下文再论。再次,不以请谥、修史、乞碑志为目的的行状开始出现。请谥、修史、乞碑志为创作目的的行状,或为获得谥号,或为修史、撰碑志提供素材,此种状况下,谥号、传记、碑志处于主体地位,行状处于从属地位,是为它们服务的,而逝者的人物形象也更多是通过谥号好恶、传记以及碑志所载事迹传播,行状不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但不以请谥、修史、乞碑志为创作目的的行状与此不同,其目的本身就是记载人物事迹以劝诫当世、传之后世,实质与传记基本相同,具有独立的文体地位。为更加具体地说明问题,兹举两例。苏轼撰《苏廷评行状》,状主苏序,乃苏轼祖父。文尾曰:“公之无传,非独其僻远自放终身,亦其子孙不以告人之过也。故条录其始终行事大略,以告当世之君子。”[12]495据状文,苏序累赠职方员外郎,明显未达请谥号、牒史馆资格。另据状文,苏序于北宋仁宗庆历七年(1047)五月终于家,八年(1048)二月葬于眉山先茔(时苏轼11岁),由此可知,状为追记,而文中并未涉及任何补刻碑志的信息,撰文不为乞碑志可知。综合观之,文中“不以告人之过也”“以告当世之君子”等,当为实语。黄干撰《朝奉大夫华文阁待制赠宝谟阁直学士通议大夫谥文朱先生行状》,状主朱熹,南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撰文,文曰:“先生没有年矣……行状之作,非得已也,惧先生之道不明,而后世传者之讹也。”[13]第228册,452撰状为彰明先生之道,与上太常、牒史馆、乞碑志的创作目的明显不同。由此两例可见此类行状的性质与功用。
二、创作目的变迁原因分析
供修史和乞碑志行状的增多,以及具有独立地位行状的出现,是行状文体发展史上的新现象,任何现象的出现,背后都有复杂多元的原因。
首先,与宋代社会的平民化紧密相关。钱穆曾言:“论中国古今社会之变,最要在宋代。宋以前,大体可称为古代中国。宋以后,乃为后代中国。秦前,乃封建贵族社会。东汉以下,士族门第兴起。魏晋南北朝迄于隋唐,皆属门第社会,可称为是古代变相的贵族社会。宋以下,始是纯粹的平民社会。……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此后门第传统之遗存。”[14]第6册,232“纯粹的平民社会”似显绝对,但从整个古代社会变迁趋势来看,此论颇有意义。后来的学者,在接受钱穆基本判断的基础上,表述上有所修订。如邓小南在谈唐宋变迁时云:“从唐代到宋代,一方面社会形态、文化学术方面有非常清晰的延续性,另一方面当然也有走势上的明显不同……这两者间的区别,如果用一种较为简单的方式来概括,就是出现了‘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趋势。所谓的‘化’,不是一种‘完成时’,而是一种‘进行时’,是指一种趋势,这在很大程度上塑就了宋代社会、宋代文化的特点。”[15]“平民化”这个表述更为准确,平民化是一种趋势的判断也更加科学。在平民化的过程中,普通文人的身份地位得以提高,价值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如何实现死而不朽,是历代文人思考的人生问题之一。早在春秋时期,叔孙豹就有“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的说法[16]1088。之后,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强调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年寿有时而尽,荣乐止乎其身。二者必至之常期,未若文章之无穷。是以古之作者,寄身于翰墨,见意于篇籍,不假良史之辞,不托飞驰之势,而声名自传于后”[2]2271。叔孙豹所谓“立言”之“言”与曹丕之“文章”,内涵与外延均不尽相同,但所强调凭此得以不朽的对象性质上却是一致的,皆为立言、作文之主体,而非言中、文中之人物。此可视为实现不朽之一途。而另一途,则是将一生事迹写入文章,成为文中之人物,从而随文流传后世。通过这种方式实现不朽,至迟到东汉就已经比较流行了。如蔡邕撰《胡广碑》云:“论集行迹,铭诸琬琰。其词曰:……泽被华夏,遗爱不沦。日与月与,齐光并运。存荣亡显,没而不泯。”[17]161《彭城姜伯淮碑》云:“于是从游弟子陈留申屠蟠等悲悼伤怀,惧微言之欲绝,感绝伦之盛事,乃建碑于墓,甄述景行,曰:嗟乎殒没,搢绅永悼,依依我徒,靡则靡效。勒铭金石,弥远益曜。”[17]178借碑文流传不朽之意甚明。后代的墓志兼具志陵谷迁变与传之不朽的双重功用,欲传之不朽这一方面与汉碑一脉相承,传播的对象也是文中所写之人,而非撰者。
平民化背景下,在如何借助他人之文实现人生不朽方面,宋代普通文人有着比前代更为具体深刻的认识。如南北宋之交的李吕在《上晦庵干墓志书》中批评苏轼“某于天下未尝志墓,铭者五人,皆盛德故”时云:“窃隘其言,以为此五君子者勋在王室,太常纪之,史册书之,使无苏公之笔,愚知其不朽也,非若抱道怀义,无所设施,倘非盛德之士或志或铭,则草木俱腐矣。审如苏公之云,则得铭者无非达官伟人,彼清介自守,礼法是蹈,厄穷而无位者,皆在所弃矣,不几于失人乎?”[13]第220册,267南宋郑良嗣父为权臣所嫉,谪死岭表,后被昭雪,郑良嗣在《求何秘监作墓志铭书》中云:“后虽久已昭雪,而未得大贤名笔作为文章,以传远而信后,则公论徒溢于千万人之口,无益也。”[13]第254册,343南宋陈耆卿在《代吴守上水心先生求先铭书》中云:“人者,物之灵也,物枯能荣,而人死则终于死也。人固不及物邪?虽然,人固有可以不死之道也……惟有功伐德美,得附丽于良史之笔,则不爵命而尊,不车服而华,不可喜可玩而足乐,死犹生也……虽然,史法至近世略矣,非大官大职,及天子之所旌别而显异者,不得预……故天下之人,进而不得附于圣世之史,则退而求托于宗工巨伯之文。盖附于史则为传,而托于文则为铭,使人虽死而犹生,是或一道也。”[13]第319册,30“倘非盛德之士或志或铭,则草木俱腐矣”“而未得大贤名笔作为文章,以传远而信后,则公论徒溢于千万人之口,无益也”“盖附于史则为传,而托于文则为铭,使人虽死而犹生,是或一道也”,这些表述充满着热切与悲伤、思考与探索,是普通文人生命意识觉醒后的理性诉求,具有明显的平民化社会痕迹。与前代相比,宋代普通文人借助他人之文以传不朽的意识更自觉,在此文化心态与意识下,人们就会重视碑志文的请托,从而引起以乞碑志为目的行状的增多。
其次,宋人对行状与碑志之间的依存关系有着更明确的认识。唐代碑志的素材来源方式有撰者回忆、书信、口头、行状等多种形式[18]188-193,相较而言,撰者回忆较多,而北宋以后,表明请铭时提供了行状的碑志文明显增多,翻阅《全宋文》与《全唐文》即可得出这一结论。这种变化与宋人对行状与碑志之间的依存关系的认识有关。“必先有行状,然后求当世名士叙而书之,埋之墓中,谓之墓志,为陵谷变迁设也”[13]第224册,80“盖今传后之文有状有铭,而又或有表”[13]第313册,209,无不在强调行状与碑志文之间的紧密联系。而在现实操作层面,首先行状的使用,有效地解决了墓志撰写时怕托于他人多所遗略、而亲属自撰又有宠亲自贤嫌疑的矛盾;其次通过行状请托撰文可以打破时空的限制而显得更为便利;第三提供行状显得恭敬有礼,更容易实现请托的愿望[6]133。这种认识和现实需要促进了以乞碑志为目的的行状撰写。
再次,以修史为创作目的行状的增多与修史制度以及人们进入史书的愿望相关。史馆修史,史料采集有规章制度或常规做法。《唐会要·诸司应送史馆事例》即云:“诸色封建,京诸司长官及刺史、都督都护、行军大总管、副总管除授,刺史、县令善政异迹,硕学异能、高人逸士、义夫节妇,京诸司长官薨卒,刺史、都督、都护及行军副大总管已下薨,公主百官定谥,诸王来朝。已上事,并依本条,所由有即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如史官访知事由,堪入史者,虽不与前件色同,亦任直牒索。承牒之处,即依状勘,并限一月内报。”[19]1286规定范围内的,勘报史馆,修入国史,在规定范围之外,但史官访知堪入史者,“亦任直牒索”。可见,有司呈报是唐代国史史料来源的主要方式,史官访求是重要的辅助手段。宋代修撰实录、国史时一仍唐旧,只是在史官访求史料方面更为具体深入,行状成了重要的访求对象。《仁宗实录》历五年又八月修成,较之太宗、真宗实录,为时最久,编修官韩琦在《修仁宗实录毕乞不推恩》奏表中解释了延宕的原因:“臣窃以仁宗临御天下四十二年,其间事迹至多,兼自前有中书、枢密院时政记并日历,各积压十余年文字,未曾编修,昨来逐旋伺候了当,方行撰次;及散下诸路取索臣僚墓志行状,多以年纪之远,难于寻究,以至经历年岁。”[13]第39册,137“取索臣僚墓志行状”成为重要环节,因此而“经历年岁”也在所不辞。曾巩修《五朝国史》,元丰四年(1081)十月辛巳言于神宗曰:“臣修定《五朝国史》,要见宋兴以来名臣良士,或尝有名位,或素在邱园,嘉言善行,历官行事,军国勋劳,或贡献封章,著撰文字,本家碑志、行状著述,或他人为作传记之类,今所修国史须当收采载述。”不仅如此,恐访寻有所未尽,还要委各级官吏“博加求访”[20]7696。《五朝国史》最终并未修成,但从进言可知,国史修撰对行状的重视。实录、国史修撰对行状的访求,刺激了行状的创作,《全宋文》中有一部分行状,其目的即为“待史官之访”“备史氏采录”“备太史氏采择”等。曾肇撰《曾舍人巩行状》,文尾曰:“以告铭公葬若碑者,且以待史官之访。”[13]第110册,91杨时撰《曾文昭公行述》,曰:“故掇其大节而详著之,以备异日史氏采录焉。”[13]第125册,21胡寅撰《先公行状》,曰:“反覆订正,凡十有五年,粗能成章,以备太史氏采择,且求志于有道立言之君子,传诸永世。”[13]第190册,147可以推想,如果没有史官对行状的采择制度,一般文人即使有将其父祖事迹写入实录、国史的愿望,也不会在行状中有这样的期待。
最后,不以请谥、牒史馆、乞碑志为目的的行状出现与行状地位的上升有关。如前文所言,请谥、修史、乞碑志为创作目的的行状,或为获得谥号,或为修史、撰碑志提供素材,谥号、传记、碑志处于主体地位,行状处于从属地位,是为它们服务的,不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但是,北宋以降,人们对行状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其主体地位有所提升。王柏在《答刘复之求行状书》中,批评曰:“若以行状而求铭,犹有说也。今先夫人已有墓铭,乃撝堂之门人述其师之语,理已当矣。若又为行状,不亦赘乎?”[13]第338册,95虽然王柏对有墓铭后仍求行状的社会现象进行了批评,但反而说明此种现象的存在。在刘复之的观念中,行状已然不是请托墓铭的工具,而是另有价值的主体文体了。韩琦在《与文正范公论师鲁行状书》中,首先批评了《师鲁行状》所载“有与闻见殊不相合者”,而后提出质疑:“今所误书,若不先由之翰刊正,遂寄永叔,彼果能斥其说,皆以实书之,则《行状》与《墓铭》二文相戾,不独惑于今世,且惑于后世,是岂公许死者之意果可不朽耶?”最后韩琦提出,愿范仲淹将行状附还,使悉刊其误[13]第39册,300。从此可以看出,在韩琦眼中,行状与墓铭之间相互独立,二者可以相互印证,才能更好地实现传之不朽的目的。从以上两例,我们可以窥见部分宋人的行状文体观念,这种观念施诸创作,不以请谥、牒史馆、乞碑志为目的的行状就会出现和增多。
三、创作目的变迁所产生的影响
创作目的迁变,其影响是多方面的,显而易见者有三。
其一,以“行述”名篇者增多。明代陈懋仁《续文章缘起》在解释“状”时,引北宋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云:“状者,言之于公上也。”[21]第3册,2555清代唐彪《读书作文谱》云:“行状(行述同),伯鲁曰,行状者,取死者生平、言语、行事、世系、名字、爵里、寿年、后裔之详,著为行状,亦名行述。或牒考功太常,使之议谥,或牒史馆,请为编录,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类,以其有所请求,故谓之状。”[21]第4册,3564“言之于公上也”“以其有所请求”的意思大致是一致的,强调的都是“状”上呈的功能和特点。因此,宋前行状的篇题多为“行状”,少见“行述”,其原因正在其创作目的为上考功、牒史馆、上作者等。但是,北宋以后,以“行述”为篇题者成为常见现象。笔者以为,其中主要原因是单纯以乞碑志为目的行状的增多,以及不以请谥、牒史馆、乞碑志为目的的行状的出现。不以请谥、牒史馆、乞碑志为目的的行状,不用上呈,既非“言之于公上也”,亦非“以其有所请求”,故篇题不用“行状”而用“行述”,较为容易理解。而乞碑志为目的的行状,“以其有所请求”,有时却不用“行状”名题,究其原因,实与碑志的创作生态有关。南宋李吕(1122—1198)在《与何少卿干墓志书》中曾感叹:“呜呼!文之难,铭人之墓之难。盖分不深则知有弗究,知之矣文不工则辞有弗达,辞达矣非天下重名则文有弗传。”[13]第220册,265这其中道出了古人请托墓志铭时对撰者选择的期待,首先是丧家的亲故,其次是亲故中善文辞者,最后是有大名于天下的人。实际操作过程中,请托有大名的撰者并不容易,请托亲故中善文辞者,就成了现实中最合适的选择[22]127。将行状上呈给考功或史馆,与提供给亲故,其情形与心态大有不同。提供给亲故就会少些格套与客套,用“述”不用“状”更显亲切与自然。高步瀛在其《文章源流》中云:“后世行状,多出为子者所撰,将以求名人铭志,而非为请谥而作,故或曰事状,或曰行述,以避行状之名。”[23]1481从后文来看,此段重点在强调人子所撰行状增多引起的篇名变化,但笔者以为,此段同时也在强调另外一个方面,即以求铭志而非为请谥而作,也是篇名用“述”不用“状”的重要影响因素。
其二,世系书写的位置。徐师曾说行状云:“盖具死者世系、名字、爵里、行治、寿年之详,或牒考功太常使议谥,或牒史馆请编录,或上作者乞墓志碑表之类皆用之。”[1]147世系是行状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之一,据徐师曾的论说即可见一斑。世系的书写位置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列于正文之前,一种是书于状文之内。至于什么情况下列于前,什么情况下书于文内,大致有规律可循。乾隆年间著名学者沈彤在其《与沈六如论东湖行述书》一文中云:“凡所状之曾祖、祖、父与其乡贯,有列于状之前者,将以上太常史馆议谥编录,任彦升之状萧子良,韩退之之状董晋,柳子厚之状柳浑、陈京是也;有疏于状之内者,将以托文章家撰著碑志,韩退之之状马彙、苏子瞻之状其祖序是也。”[24]第264册,376据此段文字,上太常议谥、上史馆编录的情况下,世系列于状之前,请托碑志时,世系书于文之内。纵观六朝隋唐行状,沈彤的判断虽然不能称作定例,但称作常例是没有问题的。北宋以后,以请托碑志为主要创作目的的行状增多,世系书于文内的行状篇数自然也随之增加,这就打破了六朝隋唐时期世系主要列于文前的状况。而且,二者之间互相影响,宋元至明清,请谥而不列于文前、请托碑志反而列于文前的行状时有出现,这种现象出现,应与乞墓志碑表行状成为主流后对请谥行状的影响有关,也应与乞碑志行状对请谥行状的模仿有关。
其三,婚娶子女的书写。黄宗羲在其《金石要例》“行状例”条云:“行状为议谥而作与求志而作者,其体稍异。为谥者须将谥法配之,可不书婚娶子姓,柳州状段太尉、状柳浑是也;为求文者,昌黎之状马韩、柳州之状陈京、白香山之状祖父是也。”[25]上册,424以请谥为目的的行状,文中可不书婚娶子女,而乞碑志的行状常常书之。黄宗羲的判断依然不是定例,但是常例无疑。除《金石要例》中所举例证外,《昭明文选》所收任昉撰《齐竟陵文宣王行状》,也是不书“婚娶子姓”的。宋代以降,为求文的行状增多,书婚娶子女的现象自然普遍,受此影响,请谥的行状也都书写“婚娶子姓”了,并且几乎成了定例。
纵观元明清行状,其模式或与宋代相同,或由宋代萌发,可以说六朝隋唐奠定了行状文体的基本格式,宋代成就了它的形态多样,元明清完成了对宋代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