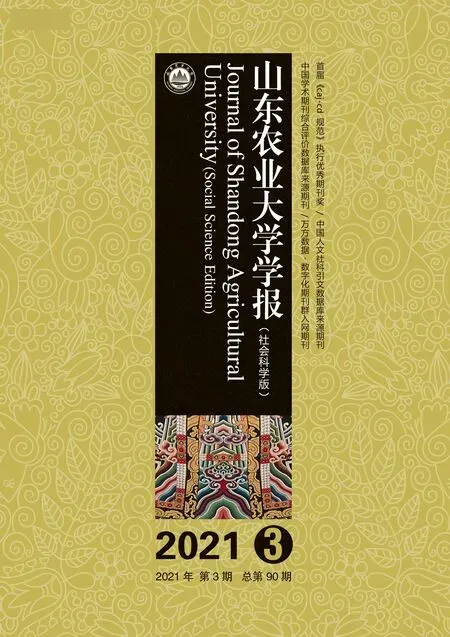融合与互动:宋明时期心性变化与三教关系的演变发展
2021-11-30潘叶青
□潘叶青
[内容提要]三教异同是宋明理学的一个重要议题。朱熹因严守三教界限而主张“天下无二道”,认为儒家与佛老的差异在于认心为性。王阳明则主张三教融通,认为三教差异在于见道有偏全。焦竑进一步发展王阳明的三教观,主张三教殊途同归,三教差异在于教。三教关系的变化实际是心性论的变化。朱子因此认为“圣人本天,释氏本心”,王阳明则认为圣人既本天亦本心,焦竑认为三教心、性、理皆同,本心之学皆为圣学。朱熹、王阳明、焦竑对三教的不同认识也加深了儒释道在心性论上的互动与融合。
回顾程朱陆王之间关于“性即理”还是“心即理”的争鸣,核心皆在于心、理、性等概念的辨析与诠释。在儒佛道互相批判融摄的背景下,三教关系的演变与发展实际可说是心、性、理、道等思想的变化。那么反其道而思之,若要了解程朱理学如何转向陆王心学,则可从他们对三教关系的看法入手。他们对三教的看法通常基于自身思想体系建构的立场,思想的差异又反映在他们对三教关系的不同看法上。如以朱熹为代表的宋儒往往严守三教界限,而到明中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儒者则表现出融通三教的倾向,再到晚明时期,焦竑更是表现出三教合一的趋势。
本文主要以朱熹、王阳明、焦竑的相关论说为代表和根据,来考察王阳明融通三教这一事件在整个宋明理学的发展变化中所具有的转折意义。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也是理学一系辟佛道的代表人物,而王阳明系融通三教的代表人物。焦竑是阳明后学的代表人物,他的活动则主要在万历中后期。三者的活动时间恰好覆盖了三教关系在整个宋明理学中的变化过程。他们对三教关系的论说反过来也体现了整个宋明理学心、性、理的变化发展。而不以王龙溪为阳明后学在三教论说中的代表,一是因为彭国翔所著《王龙溪与佛道二教的因缘》以及《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已对王龙溪和三教关系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二是因为王龙溪主要活动于嘉靖、隆庆年间以及万历初年,从时间维度上,焦竑更为合适。因此,以朱熹、王阳明、焦竑的相关论说为代表来考察王阳明融通三教的整体意义,决非任意的选择,而显然在学理上具有充分的理据。
一、朱熹:天下无二道
(一)三教各道其道
朱子曾说过:
吾之所谓道者,固非彼之所谓道矣……吾之所谓道者,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当然之实理也。彼之所谓道,则以此为幻为妄而绝灭之,以求其所谓清净寂灭者也。[1]684
显然,朱熹将儒家之道看成是儒家三纲五常等伦理内容,而佛老之道则为幻灭清寂之道。“传道之谓教”,道不同,教亦不同,各道其道,自然也就各教其教,所谓道不同而不相为谋。在朱熹看来,儒佛道是三种不同的道,自然也有各自的教,即各教其教。三教之间的道与教有着清晰的界限,而朱熹严守着三教界限。为此,以他为代表的理学家以“理”作为道与教关系的标准。程颐提出:“吾学虽有授,‘天理’二字却是自家体贴出来”[2]424,在内涵上,程朱又视君臣、父子、夫妇之伦理秩序为“天理”“人伦者,天理也”[2]394,并一再强调释老将此当然之实理亦看作空虚寂灭。当普遍之天理落实到具体的社会伦理生活时,它便对社会伦理生活确立起了秩序与意义。这与佛道否定所有实在的“空”、体验真理时心灵所体验到的“寂”是大为不同的。虽然朱熹认为“气有动静,理无动静”[3]2374“理不可以动静言”[3]2374,但是这并不等同于“空虚寂灭”。因此,朱熹十分注意分辨“寂然”“无欲”等与佛道的“空虚寂灭”的区别。他认为“寂然”“无欲”是人心与天理相合的本原状态,而不是佛道所追求的“空寂澄明”之境。
然而,焦循反对以“理”作为划分三教的标准,认为儒释道只是一个理,其曰:
伯淳,宋儒之巨擘也,然其学去孔孟则远矣。孔孟之学,尽性至命之学也。独其言约旨微,未尽阐晰,世之学者又束缚于注疏,玩狎于口耳,不能骤通其意。释氏诸经所发明,皆其理也。苟能发明此理,为吾性命之指南,则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也,而又何病焉![4]82
焦竑认为宋儒之所以严守三教界限皆是因为不能通佛经之义,也不能真正通孔孟之本义,认为佛经所说最得孔孟“尽性至命”精义,佛教经典只是孔孟之学的注疏。释氏诸经所明之理,与孔孟所明之理是相同的,都是我们性命的指南。只要能发明吾人尽性至命之学,无论是佛是道,就是真正的道,就是孔孟的道。如此,三教之理并无不同,理也就不能成为划分三教异同的标准。其实,朱熹早已反对过以儒释道为同一个道或理的不同表现,认为儒释道只是同一个道的说法极其荒谬。他虽然赞同“天下无二道”,但也恰恰说明儒家之道为唯一之道,佛老便不是道。他说:“惟其天下无二道,圣人无两心,所以有我底着他底不得,有他底着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圣人有两心,则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3]3933正因为儒学之道之心与佛学之道之心不相同,故而二者没有相同处,更不可结合。即使天下存在“二道”,圣人有“二心”,那么二者也并行不悖,毫不相干。
(二)圣人本天,释氏本心
此外,朱熹亦从“圣人无二心”的角度批判佛教之心。佛教讲究明心见性,然而以知觉为心,以空为性,最后也只见得个“空虚寂灭”。朱熹说:“释、老称其有见,只是见得个空虚寂灭。真是虚,真是寂无处,不知他所谓见者见个甚底?”[3]3014朱熹从“见地”角度批评佛教的“空”确实看到了问题的要害。程朱正是以人伦之“理”否定佛道的超越之“心”,可以说,儒家人伦天理是程朱辟佛老的根本缘由。朱熹以禅最为害道,因为禅以“自心即佛性”的本原、简易直截的顿悟途径和“空”的无差别超越境界为自己学说的主脉,而这一主脉的支点则为人性与佛性之争,从根本上有瓦解人伦天理终极意义的危害。
针对佛教尤其禅宗这种“唯心”思想,程颐一开始便提出“圣人本天,释氏本心”的观点,其谓:“天有是理,圣人循而行之,所谓道也。圣人本天,释氏本心”[3]274,按照上述程颐对天理的相关阐述,我们可知,“圣人本天”中的“天”即是天理,“本天”即以天理为本,又因为在程颐那里,性与理同一,即“性即理也”,故而“本天”则是以性为本。此后,朱熹又进一步以心性之分解释“本天”与“本心”,其曰:
“儒者之学,大要以穷理为先。盖凡一物有一理,须先明此,然后心之所发,轻重长短,各有准则....但见其所以为心者如此,识其所以为心者如此,泛然而无所准则,则其所存所发,亦何自而中于理乎?且如释氏擎拳竖拂、运水搬柴之说,岂不见此心?岂不识此心?而卒不可与入尧舜之道者,正为不见天理,而专认此心以为主宰,故不免流于自私耳。前辈有言:‘圣人本天,释氏本心。’盖谓此也”。[3]274
从朱熹的解释可知,他强调要“穷理为先”,如果如佛教一般“专认此心为主”而忽略穷理的重要性,那么就会落入“泛然而无所准则”的窠臼中。于朱熹而言,“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也。性则心之所具之理,而天理之所从以出者也”[3]88,“心之全体湛然虚明,万理具足”[3]94,心只是个虚灵知觉,虽具众理但却不是理,仍然需要格物穷理将心中之理践行出来。
二、王阳明:道一而已
(一)道一而已
伴随宋明初期三教融合互动与理学理论的提升,佛道已不能撼动儒学的统治地位,尤其是程朱之学被定为官方之学以后,“自今教人取士,一依程朱之言,不许妄为叛道不经之书,私自传刻以误正学”[5]265。程朱理学官学化后出现一定的流弊,沦为获取功名的工具,也因此成为王阳明主要批判的俗学。故而,王阳明此时对佛老等的批判已转向儒学内部的批判。这些问题集中体现在他对朱熹“天下无二道”的批判上,王阳明提出自己的“道一”说:
道一而已,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释氏之所以为释,老氏之所以为老,百姓日用而不知,皆是道也,宁有二乎?……世之儒者,各就其一偏之见,而又饰之以比拟仿像之功,文之以章句假借之训,其为习熟既足以自信,而条目又足以自安,此其所以诳己诳人,终身没溺而不悟焉耳![6]205
在王阳明这里,“道一而已”是儒佛道具有共通性的根基。王阳明认为,天下只有一个道,并不是儒佛教各存在一个道,只不过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儒家与佛老的差异只是由于见道有偏全。显然,与程朱理学刚开始的辟佛卫道相比,王阳明对佛老的态度显得更为包容,他说:“夫杨、墨、老、释,学仁义,求性命,不得其道而偏焉,固非若今之学者以仁义为不可学,性命之为无益也。居今之时而有学仁义,求性命,外记诵词章而不为者,虽其陷于杨、墨、老、释之偏,吾犹且以为贤,彼其心犹求以自得也。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6]231王阳明认为其他思想学说与吾儒有相似之处,皆学仁义求性命,并且“犹有自得”,反而是溺于辞章训诂不知求诸本心的世之儒者无“自得”,其弊端比之佛老反而有过之而无不及,盖因世儒只知“外务讲求考索,而不知本诸其心”[6]179,无法穷理达道。而“学之不明,皆由世之儒者认理为外,认物为外”[6]77。
当然,在儒释道竞争的语境下,王阳明并未放弃批判二氏,如果说在王阳明心学的语境内,以朱熹为代表的儒者有“务外遗内”之弊,那么佛老则是“务内遗外”之弊,“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7]227佛教倡导出世,寻求解脱的最重要的理论根源即为缘起性空,诸行无常,寂静涅槃,从根本上认定现实世界是虚幻的,不能积极入世,更不可能治理天下国家。于王阳明而言,无论是朱熹的“务外遗内”还是佛道的“务内遗外”,皆非明道之举。如果说朱熹的“三道三教”着眼于儒佛道的各不相同,那么王阳明意欲“合三为一”即是寻求儒佛道之间的相同点。因而,“道一”说为儒释道的“共通性”奠定了根基,并在其诠释中发挥着化解分歧、疏通儒释道关系的枢纽作用,是涵摄儒释道的共同依据。需要注意的是,王阳明虽然以“道一”融通三教,然而并非无立场的包容,他以“三间一厅”的比喻说明儒佛道的关系,其曰:
二氏之用,皆我之用:即吾尽性至命中完养此身谓之仙;即吾尽性至命中不染世累谓之佛。但后世儒者不见圣学之全,故与二氏成二见耳。譬之厅堂三间共为一厅,儒者不知皆为吾用,见佛氏,则割左边一间与之;见老氏,则割右边一间与之;而己则自处中间,皆举一而废百也。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儒、佛、老、庄皆吾之用,是之谓大道。[6]1289
王阳明基于“道一”的视域融通三教时,始终坚持“儒、佛、老庄皆吾之用”的儒家立场。这里,“吾”才是主体,成全实现这个“我”才是终极目的。“吾之用”作为诠释者的基本立场,其中的“吾”强调的是作为诠释者有其诠释意图,“用”则是对儒、佛、老、庄多种异质思想的会通。王阳明进一步阐述“三教之分”:
道大无名,若曰各道其道,是小其道矣。心学纯明之时,天下同风,各求自尽。就如此厅事,元是统成一间。其后子孙分居,便有中有傍。又传,渐设藩篱,犹能往来相助。再久来,渐有相较相争,甚而至于相敌。其初只是一家,去其藩篱,仍旧是一家。三教之分,亦只如此。[6]1289
王阳明基于“道一”视域,认为三教便是基于各自立场所见“大道”之一隅,而互相隔绝,渐成“执态”,陷入“一偏”。王阳明的“道一而已”说被其门徒进一步发挥。如王龙溪说王阳明屋舍三间之喻是将儒释道三教看作“本有家当”,儒者本应守此“家产”,然而“吾儒不悟本来自有家当,反甘心让之”[8]718“仅守其中一间,将左右两间,甘心让与二氏”[8]718。焦竑亦曰:“道一也,达者契之,众人宗之。在中国者曰孔、孟、老、庄,其至自西域者曰释氏。由此推之,八荒之表,万古之上,莫不有先达者为之师,非止此数人而已。昧者见迹而不见道,往往瓜分之而又株守之。道是吾自有之物,只烦宣尼与瞿昙道破耳,非圣人一道,佛又一道也。大抵为儒佛辨者,如童子与邻人之子,各诧其家之月曰:‘尔之月不如我之月也。’不知家有尔我,天无二月。”[4]745焦竑以“天无二月”比喻天下无二道,区分儒佛释之道犹如童子争辩自家自有一个月亮一样。道本是“自有之物”,自家家产,然而儒者不悟,往往“瓜分之而又株守之”,使得自有家当日益减少。如此说来,王阳明用以融通三教的“道一无二”只不过是重聚家产。
与朱熹“天下无二道”相比,王阳明以“道一”说将佛老化为“同道”,主张融通三教,但仍然认为三教是有分的。也即是说,王阳明只是对三教持融通与调和的立场,既比朱熹的“天下无二道”更包容,也比以焦竑为代表的阳明后学所主张的三教“殊途同归”显得有立场。而在王阳明心学体系中,道即心即良知:
先生曰:“‘天命之谓性’,命即是性;‘率性之谓道’,性即是道;‘修道之谓教’,道即是教。”问:“如何道即是教?”曰:“道即是良知。良知原是完完全全,是的还他是,非的还他非,是非只依着他,更无有不是处,这良知还是你的明师。”[7]224
王阳明从本原处解释性、命、道、教,并且以“道即是良知”,将性、命、道、教全归于良知中,而王龙溪认为王阳明正是提出以良知作为“范围三教之宗”[8]764。在此,王阳明又巧妙地重新诠释了道之义。朱熹以性为道,王阳明以心为道,由三道三教之分到三教一道的三教融通,三教关系变化背后实际是心性论的变化。
(二)圣人本心又本天
对程朱一系提出的“圣人本天,释氏本心”的观点,王阳明亦不赞同,他提出:“君子之学,心学也。心,性也;性,天也。”[6]263依王阳明,心即性,性即天,心即天。儒家与佛道都以心性为学,“皆求尽其心也”,“本天”与“本心”并不是儒佛之间的根本不同之处。在王阳明看来,圣人既本天又本心,本心即是本天。王龙溪十分认可其对儒学的这一重新定位,他坚决反对将心性之学的发明权归于释氏,他说:
先师有言:“老氏说到虚,圣人岂能于虚上加得一毫实?佛氏说到无,圣人岂能于无上加得一毫有?老氏从养生上来,佛氏从出离生死上来,却在本体上加了些子意思,便不是他虚无的本色。”吾人今日,未用屑屑在二氏身分上辨别同异,先须理会吾儒本宗明白二氏毫厘,始可得而辨耳。圣人微言,见于大易,学者多从阴阳造化上抹过,未之深究。夫乾,其静也专,其动也直,是以大生焉;夫坤,其静也翕,其动也辟,是以广生焉,便是吾儒说虚的精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便是吾儒说无的精髓。[8]292-293
王龙溪反对将空无虚寂作为佛老专利而将其充分融摄到儒家思想内部,并把心性单独提取出来,为后来的阳明学者超出三教,只求心求性拓开了路径。如周汝登(海门,1547—1629年) 强调不能将“天”与“心”一分为二,他说:“故天与心不可判,判天与心而二之者,非惟一之旨矣。”[9]7-8明末的刘宗周(1578—1645)也说:“释氏之学本心,吾儒之学亦本心。”[10]370
作为“朱学后劲”的罗钦顺继承朱子学心性之分,与阳明心学形成对峙,形成理论张力。罗钦顺作《困知记》以辨心性之异,以闢王、湛为目的,并且在《困知记》勾勒了一个庞大的异端谱系,主要包括陆九渊、陈白沙、湛甘泉、王阳明、阳明弟子及佛教,尤其禅宗。他说:“释氏之学,大抵有见于心,无见于性,故其为教,始则欲人尽离诸象,而求其所谓空,空即虚也。”[11]2他认为儒释之别在于能否对心、性等概念正确理解,“圣人本天,释氏本心”是“万世不易之论,儒佛异同,实判于此”[11]105。罗钦顺在心性关系上一贯反对陆王心学“心即理”“心即性”的说法,他指出心与性不相离但也实难合一,并且如此论述心、性、理之间的关系:
孔子教人,莫非存心养性之事,然未尝明言之也,孟子则明言之矣。夫心者,人之神明,性者,人之生理。理之所在谓之心,心之所有渭之性,不可混而为一也……二者初不相离,而实不容相混。精之又精,乃见其真。其或认心以为性,真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者也。[11]卷上.1
罗钦顺所坚持的心性之辨,主要集中在心性之别以及不可以心为性上,因为以心为性恰恰陷入佛氏作用见性的窠臼了,所以他又说:“其或认心以为性,真所谓‘差毫厘而谬千里’者也。”而他正是从这一标准出发,他对理学中的心学一系,全然以佛禅视之。在罗钦顺看来,心学一系落入禅学窠臼的原因,在于“心即理”说消泯了“理”“性”的主导地位,一味突出心之灵明发用,混淆儒、佛边界,甚至篡改孟子之说曲意逢迎佛禅,误导士人。丁为祥指出,罗钦顺认为所谓本心、良知,则只是灵明知觉,是人主观的神明发用。他所主张的道心人心的主客观之别,使他根本不顾本心、良知对天理的贯彻与落实,不顾其表现天理的思想内涵,一定要将其推到只主灵明知觉的佛禅一边。[12]就理学与心学的关系而言,“心即理”与“性即理”的分歧说到底不过是理学内部的分歧,并不具有根本对立的意义。[12]而在罗钦顺以心性划分异端的方法,视阳明心学为禅学,成为后来阳明心学被定调为“阳儒阴释”的一大主因。
三、焦竑:三教殊途同归
(一)儒释道殊途同归
焦竑自诸生时即受学耿定向,耿定向以佛解儒的方法对他影响很大。他与李贽交情甚笃,李贽的“三教融合”对焦竑也有相当大的影响。焦竑受师友熏染,精研佛典,思想中有极强的佛学因素。这与明代后期思想界三教融合的思潮是一致的。明代后期,随着阳明学的确立与推广,王阳明对佛道二家的吸收与融合为学者效法而逐渐形成趋势。学者大都到佛理中寻找理论养分,而泰州后学首当其冲,焦弘便是其典型代表,其曰:
晚而读《华严》,乃知古圣人殊途同归,而向者之疑可涣然冰释已。何者?《华严》圆教,性无自性,无性而非;法无异法,无法而非性。非吐弃世故,栖心无寄之谓也。故于有为界,见示无为;示无为法,不坏有为。此与夫洗心退藏而与民同患者,岂有异乎哉!……余以谓能读此经,然后知“六经语孟无非禅,尧舜周孔即为佛”,可以破沉空之妄见,纠执相之谬心。”[4]183
在焦竑这里,三教是殊途同归的,王阳明的“三教归儒”亦变成了三教义理相通。焦竑甚至认为佛老也可为孔孟之义疏。于焦竑而言,三教虽然教不同,但仍可通过修持各自的教而得到同一个“道”,此为“殊途同归”。焦竑又将佛教经典视为儒家经典义理注脚,所谓“释氏诸经,即孔孟之义疏也”。焦竑以佛教为儒学义疏,认为“学佛然后知儒”,他是把佛学作为儒学的辅翼来看的。因此,他反对先儒出于卫道之心对佛教所作的批评,极力辩白佛教与儒家的相同处。如此,焦竑便将儒释道之心性义理贯通了起来,就不存在王阳明所说的“见道有偏全”。王龙溪也认为心性之学正是借佛氏之超脱而悟入。[13]65周汝登则认为三教心性之理并无分别,他说:“教虽有三,心则惟一。心一是实,名三皆虚。不究其实而泥其虚,则此是彼非,力肆其攻击,或彼歆此厌,不胜其驰求,纷纷多事,而真教湮矣。”[9]414此外,管志道(东溟,1536—1608年)也认为,儒佛道三教“其见性之宗同,其尽性之学亦同也,所不同者应机之教耳”。[14]689管志道强调,三教学者通过各自的教法都可以达到“道”的境界。
焦竑认为三教殊途同归,实际主张的是三教合一,可以说,三教之间的距离几乎被抹除,比王阳明主张的三教融通更进一步,这当然也会招致严守三教界限的朱子学者的抨击,如冯从吾就曾批评三教殊途同归之论根本就是在混同三教,其曰:
倘有人焉,出而洞佛氏之一偏,见吾道之大全,举顿悟渐修、心性事物而一以贯之,可谓千古一快矣。而又或过于张惶,以为吾儒曰心,彼亦曰心,吾儒曰性,彼亦曰性,道理本同,但华言梵语异耳。且偏处二氏不能兼吾儒,而全处吾儒可以兼二氏;吾道至大,二氏之学虽甚高远,总不出吾道之范围也。不知吾儒既曰可以兼二氏,二氏亦曰可以兼吾儒,彼此相兼,是混三教而一之也。欲以崇儒辟佛,而反混佛于儒,蹈三教归一之弊,岂不左哉?[15]44
冯从吾的批评是尖锐的也是切中要害的,他强调欲想合三教为一的言论会导致学者对儒佛教思想不再做任何区分,如说心性,儒家说心,佛道也说心,儒家说性,佛道也说性。如果都是同道,而只有语言不通,那么区别在哪呢?顾宪成亦指出,阳明后学三教殊途同归的倾向是“深有味乎仙释,见其与吾圣人同,而又为名教所持,不敢不谓与吾圣人异,故阳离阴合,为此含糊影响之语”[16]415,是“以吾之性命与二氏混也”[16]415。张履祥(杨园,1611-1674)亦批评说:“三教合一之说,莫盛于阳明之门。察其立言之意,盖欲使墨尽归儒,浸淫至于今日,此道日晦,彼说日昌,未有逃禅以入儒,只见逃儒以入释,波流风煽,何所底极!”[17]764明末的方学渐(1540-1615)说:“世混三教而一之者,曰三教之体原同,但作用不同耳。夫体用一也,知用之不同,则知体之不同矣,知体之不同,则知三教之非一矣。”[18]206然而,这并非是阳明及其部分后学有意为之,而是当时三教合流已成趋势。事实上,至晚明时期,林兆恩已创立以儒为主体的三教合一的宗教“三一教”,他说:“岂不以三教之道合之一人之身,随时而为儒,随时而为道,随时而为释?余则以为三教之道混于一身之内,无适而非儒,无适而非道,无适而非释。盖能寂灭,便能虚无;能虚无,便能事事也。”[19]673三一教实行了三教在信仰崇拜体系上的合一。
(二)“本心之学,圣学也”
焦竑的三教义理旨趣同归一致与王阳明明讲的“圣人之学,心学也”有极深的联系。理学批判佛道的一个重要依据是“圣人本天,释氏本心”,在此依据下,以“本心”为依据的心学一系难免沦为异端。焦竑认为不能因佛老极言心性,就因噎废食而不讲心性,把心性之学归于佛老,这无异于将自家家产拱手让人。其曰:
尝谓此性命,我之家宝也,我有无尽藏之宝,埋没已久,贫不自聊矣。得一贾胡焉,指而示之,岂以其非中国人也,拒其言哉?彼人虽贾胡,而宝则我故物。人有裔夏,宝无裔夏也。况裔夏无定名,由人自相指射。”[4]284
可见,儒学即是心性之学,根本不存在儒家与佛道二教之分。儒佛道三教不仅都以心性为学,而且所说性命之理也相同,所谓“释氏之典一通,孔子之言立悟,无二理也”。对焦竑来说,儒佛道三教心性之理是相互贯通的。其曰:
佛虽晚出,其旨与尧、舜、周、孔无以异者,其大都儒书具之矣。所言“本来无物”者,即《中庸》“未发之中”之意也。“未发”云者,非拨去喜怒哀乐而后为未发也,当喜怒无喜怒,当哀乐无哀乐之谓也。故孔子论“憧憧往来,朋从尔思”,而曰:“天下何思何虑。”于憧憧往来之中,而直指何思何虑之体,此非佛法何以当之?顾学者不察,而猥以微言奥理,独归之梵学,是可叹也![4]284
焦竑以“未发之中”解佛教之“本来无物”,认为二者之意相同。他这么解的原因与他对心性的看法紧密相连。焦竑尊信孟子、阳明之学说,心即性,性即心,在他这里,心与性是同一的。他认为儒与佛都是以“空无”来理解心性,只是以不同方式命名而已,儒家称之为“未发之中”,而佛家称之为“本来无物”。在王阳明那里,心即理和心与理为二就是儒佛同为“本心”之学的差异之所在,而到了焦竑这里,他认为三教所说心性之理并无不同,“而猥以微言奥理,独归之梵学,是可叹也”。总之,在焦竑看来,心性之学非佛老专有,“苟得其性,谓之梵学可也,谓之孔孟之学可也,即谓非梵学非孔孟学而自谓一家之学亦可也”[4]82-83,三教之不同,不在于心性,而在于教之不同,“佛言心性,与孔、孟何异?其不同者教也”。
晚明时期这种儒佛道互释的潮流虽打破了当时束缚人们思想的僵化的程朱理学教条,为思想界和文学界提供了新的因素和推动力,也为佛学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资源,但是王门后学对儒释道不加以分别、区分界限,一切以心性(或良知)作为考量的标准,符合心性(良知)的则是,不符合心性的则非,他们对三教的认识超越了王阳明的三教融通论,也超越了王阳明所坚守的儒家本位。由王门后学掀起的狂禅风潮亦是阳明心学被定调为阳明禅的另一重要原因,刘宗周认为:“明以来讲姚江之学者,如王畿、周汝登、陶望龄、陶奭龄诸人,大抵髙明之过纯入禅机,奭龄讲学白马山,至全以佛氏因果为说,去守仁本旨益远。”[20]在此背景下,佛老二氏也不再被视为异端,对这种变化,杨起元(字贞复,号复所,1547-1599)曾经有过明确的说明,所谓“二氏在往代则为异端,在我朝则为正道”[21]281-282。熊赐履亦认为:“昔之儒只要辟佛老,今之儒只要佞佛老。昔之儒只要明二氏之异,今之儒只要明三教之同。”[22]63
四、结语
总之,宋明理学时期三教关系的流变背后伴随着心性的发展与深化。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以儒家人伦天理作为判教的根本标准,此外,王学本就以朱子学为问题意识,而焦竑又是阳明后学中的一个代表人物,他们之间亦有批判继承的关系,因而他们之间的价值取向可说是大同,都以儒家的人伦天理为根本核心价值。但随着心性之理的不断深化以及自身思想体系构建的需要,他们的思想诠释与对佛道的摄取重心则各有差异,这一差异在宋明理学发展的语境下只是内部的小异。
宋明理学本就在儒释道互动融合的背景下产生,彼此都面临着批判融摄对方以建立新的思想体系的任务,也因此而共用许多一样的核心概念,通过对这些概念范畴与内容的重构将对方的理论资源化为己用。恰是在毫厘之差的概念论述中蕴含了巨大的重新诠释空间,故而相似表述后面实则蕴含千里之别的思想旨归。需要注意的是,朱熹的各道其道到王阳明的道一而已,再到焦竑儒释道殊途同归,体现了三教关系的不断融合同化。而在不同思想的融合互动中如不注意持守自身立场,也会导致思想的混乱以及理论越来越缺乏创新性的弊病,进而使各自的理论建构都陷入困境,如焦竑认为佛经所说最得孔孟“尽性至命”精义,汉宋诸儒所注反成糟粕,这就进一步抹除了三教之间的差距。这种我是你你是我的混同最后导致三教完全殊途同归,大同小异的价值判定里的“小异”不复存在,也就导致在小异之处蕴含的巨大阐释空间不复存在,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理学自身理论规模的缩减与创造性资源的枯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