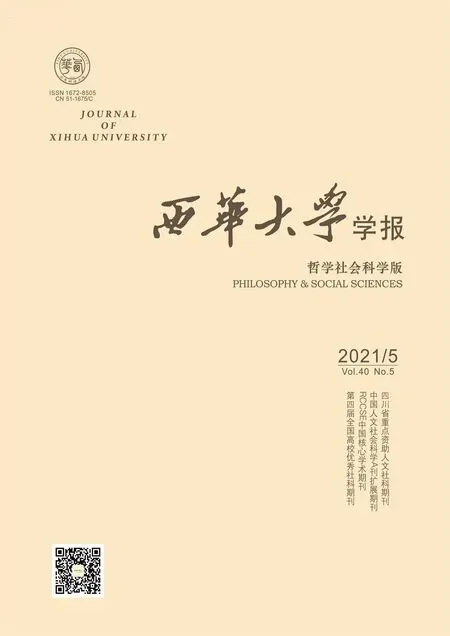晚宋边事视域下蜀士家国情怀的多重面相
2021-11-30程海伦
程海伦
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 北京 100083
晚宋蜀地屡经兵火,逐渐从一方乐土变为百战之地。萧元之诗“千年文物郡,百战虎狼群”[1]37985,即鲜明地点出了蜀地发生的这一巨大变化。大量蜀人或死于战火,或流寓他乡,生活状态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宋廷对于蜀地的治理具有一定的特殊性①。蜀士的地方观念非常浓厚,晚宋的战乱,更使蜀士面临着与其他地区士人不同的政治和家庭问题。在此背景下,蜀士的诗文创作呈现出某些特殊的主题与情感取向,这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家国情怀。
目前,文学界对于晚宋蜀士群体生存境遇与文学创作情况的研究较为薄弱,这可能与南宋文学的研究集中于东部地区而忽略西部有关[2]。在晚宋的蜀籍士大夫中,魏了翁、李鸣复、吴泳、程公许、吴昌裔、阳枋、牟子才及高斯得等人有较多诗文留存,为我们探究其生平经历、心理状态以及思想观念提供了可能。本文拟以上述诸人的创作为中心,从蜀士对于家庭、蜀地与朝廷这三个层面的情感入手,具体论述晚宋边事背景下蜀士家国情怀的多重面相及其内在的紧张关系,以期更为全面、深入地认识宋代的蜀士群体及其文学创作。
一、家事:存殁之悲与西还之念
蜀人本就有极强的乡土意识[3]56,动荡的外部环境与艰困的生存境遇,更增强了蜀人的家族观念。在蜀士避难迁徙的过程中,就存在着不少亲族之间相互照拂、相互依存的事例。如牟子才曾帮助其妹一家逃离四川:“女弟在眉山,拔其家于兵火,致之安吉。”[4]12355阳枋在兵难后周济亲故免于饥寒:“敌退,张恭人偕子妇俱保全,公悉所有以周亲故之饥寒。”[5]434姚希得照顾投靠自己的蜀地亲族数十家:“蜀之亲族姻旧相依者数十家,希得廪之终身,昏丧悉损己力,晚年计口授田,各有差。”[4]12590由上述诸例可以看出,乱离之世,亲族关系的重要性格外凸显。因此,在蜀士的诗文中,多处可见对家庭情况的细致书写,存殁之悲与还家之念即是其中两种主要的情感取向。
(一)聚散存殁:家国巨变下的亲情
蜀地的战乱使蜀士不得不直面亲族的分散乃至死亡,这种异常的聚散存殁情状,往往会引发蜀士的深重悲慨。
在晚宋蜀士之中,程公许即是一位笃于亲情之人。据《宋史》本传记载,“蜀有兵难,族姻奔东南者多依公许以居”[4]12459,可见,程公许曾给予流寓东南的族姻以极大的帮助。除此之外,程公许与留在蜀中的亲族也一直保持着联系。其诗云:“故园未有西归日,且愿平安信数通。”[1]35590与故乡亲人通信正是程公许维系亲情的重要方式。这些家庭生活的侧面,都被程公许一一写入诗中。其淳祐二年(1242)所作《去岁重阳日得彦威信附六月间二小倒及从弟倒》诗,长近百句,详细记载了与蜀中弟侄的一次书信往还。此诗首句至“死不去榆枌”一段,回忆了去岁重阳节接到弟侄家信的经过。“是时陈理卿”至“重我忧心熏”为第二段,是对信中内容的引述,概写了兵火之后弟侄携家仓皇逃难,复遭寇盗掠夺与官府暴敛的凄凉情状。面对亲人的哀告,诗人在答信中云:
尔苦我得知,尔创我得扪。岂不忆松槚,岁时荐炮燔。
永惟宗祀计,忍自遏其源。威也托我久,尚以穷愁言。
宁不思尔曹,命危豺虎群。安得田二顷,有屋休寒暄。
顺风招之来,相与共饔餐。皇后职生化,蛰蛰庶且蕃。
胡忍趣其毙,狝割如羔豚。夙传老上殒,国乱犹丝棼。
若为秋风高,已复群吠狺。呼童具黑渖,襞纸当前轩。
万一邮传通,庶几信息闻。严装理航棹,及春下荆门。②
这一段中,诗人连用“尔”“我”之称,絮絮如与弟侄对语,在自诉自叹中将委曲心迹尽数剖白。诗人首先表明对于亲人所遭苦难的理解,指出自己并非不念故乡之人。“安得田二顷”以下四句,描绘了想象中与亲人相聚的温馨场景,而这幻境的美好,正反衬出现实的令人绝望。“皇后职生化”以下八句,诗人连用反问之句,在对蜀地局势未曾好转的不解中,发出了对天意的强烈质疑。结尾一段,诗人寄希望于余玠这位新任蜀帅对弟侄的援助,并再次强调了离蜀避难的紧要。最后“愤极思一吐,声出辄复吞。长谣欲上诉,九穹隔重阍。劫运极必复,玉石可不分”六句,诗人虽相信物极必反之理,但更担忧“玉石可不分”的悲剧无法避免,全诗在对时局的控诉和隐忧中作结。程公许以诗代书,将弟侄的来信及自己的回信作为主体内容展开叙述,诗人的情绪亦随之周回曲折,悲痛、无奈、焦虑、不安等种种复杂感情展露无遗。
在无可避免的时代悲剧之下,程公许“玉石可不分”的不详预感,终于变成了玉石俱焚的残酷现实。在《屏居北郊自秋涉冬绝省人事触绪有感托之讽吟书云前一日缉成八章寓兴抒情非以言诗也》(其七)中,程公许记述了亲人遭遇的噩运:
坤维以文瑞,民俗本柔淑。何代无战争,冤哉今尔酷。
戎马塞里墟,劫钞遍林谷。平生金石交,屈指半鬼录。
从子尤可哀,别归奉水菽。伯侄并戕殒,荼毒复荼毒。
探囊数幅书,吞声不忍读。昆岗焮烈焰,宁辨石与玉。
叩首一炉香,请为遗黎赎(自注:侄子能伯请假归奉亲,同其伯父先后皆为敌所害)。[1]35518
此诗开篇八句叙写蜀地兵难造成的种种破坏。“何代无战争,冤哉今尔酷”一句,可视作全诗主旨,后文即就“酷”之表现具体展开论述。“从子尤可哀”以下四句,概写亲人遇难之事。结合诗人的自注可知,其侄因侍亲返蜀而与伯父先后被敌人杀害。“荼毒复荼毒”五字,极言伯侄双双遇难之惨痛,诗人的伤悼之情至此亦到达高潮。“昆岗焮烈焰,宁辨石与玉”引用《尚书》“火炎昆冈,玉石俱焚”之语,对乱世中玉石俱焚这一现象进行总结,可见诗人内心极度的痛悼与悲愤。
程公许诗作中对于聚散存殁的强烈感受并非个例,而是晚宋蜀士所共有。高斯得的《蜀酒》一诗,即将这种群体情感明白道出:
我辞相国归,遗我酒十器。拜受起潸然,为上有蜀字。
狐狸之所嘷,种秫宁有地。得非父兄血,或是乡人泪。
我饮不下咽,思广相国赐。愿得投岷江,咸使西南醉。[1]38550
开篇四句先点出“蜀”字,引发下文对于父母之邦的感慨。高斯得为沔州知州高稼之子,据《宋史》本传记载:“端平二年九月,稼死事于沔,时大元兵屯沔,斯得日夜西向号泣。会其僮至自沔,知稼战没处,与斯得潜行至其地,遂得稼遗体,奉以归,见者感泣。”[4]12322联系高斯得的生平与家世,或可体味出“父兄血”三字所包含的深切悲痛。对此血泪汇聚之酒,诗人自然不能下咽。由一己之哀推而及人,诗人希望能将蜀酒投入岷江,使西南之人尽皆长醉不醒,以忘却惨酷的现实。此诗比兴与联想的运用,以深婉含蓄的笔调,道出了亲人丧亡带给存者的绵绵不尽的苦痛,正是为所有蜀人发一长叹。
由上举诸作观之,蜀士对于亲人生活境遇的关切、未来命运的担忧以及不幸遭遇的痛悼都历历可见,从中也显示出家国巨变的时代背景下亲情之于个体士人的重要意义。这些描写亲族聚散存殁状况的文字,出于作者之至情,往往饱含血泪,因此感人至深。
(二)吾归何处:蜀士的故园之思
蜀士的故园之思,也表现出特定时代背景下的复杂情愫。如魏了翁诗句“蜀人谁不望西还”[1]34976,“西还”正是贯穿于蜀士诗文中的重要主题。与身处其他时、地的士人相比,蜀士之所以无法归乡,主要不是由于衰病穷困或官职羁绊,而是晚宋特殊的战争形势。因此,蜀士西还之愿的表达与其对蜀地安危的关切紧密相连,并在蜀地局势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发生着微妙的改变。
如魏了翁终其一生均对故乡怀着极深的情感。开禧二年(1207),入仕不久的魏了翁即“以侍养不便力蕲外补”[6]260。翌年行至蜀口,因吴曦叛变而只得返回荆州,至六月方才辗转返里。魏了翁后有《跋二苏送宋彭州迎视二亲诗》一文回忆这段经历,提及赴荆州途中曾获观苏轼《送宋构朝散知彭州迎侍二亲》与苏辙《次韵宋构朝请归守彭城》二诗的真迹,魏了翁此行与宋构同样出于得郡养亲之愿,却因蜀地“尘沙瞇目,岷峨凄怆”的战乱局面而“尽违始愿”[7]84,故当其览及二苏诗中对宋构归迎二亲之乐的描摹,不能不慨然叹息。绍定四年(1231),魏了翁从靖州贬所返乡时,再度遭遇兵难。此行途中,魏了翁作有数诗言及还乡之艰难。其《和虞退夫见贻生日诗韵》诗云:“虎豹当关路险艰,家人占鹊望予还。四方蹙蹙还何许,家在西南山外山。”[1]34974诗中并未正面直抒乡思之情,只从家人盼归与还家不易两处落笔,在诗意的跌宕起伏中,尽显诗人对于家人与故乡的牵挂。由还家之艰难所引起的,则是魏了翁对于家乡战事的关切:
十一月九日新滩李囗示余开禧三年四月九日所跋外舅杨宪使滩字韵诗为次韵
忆从筮仕岁涒滩,三十余年阅暑寒。
抚事无成人潦倒,怀人有梦涕汍澜。
家山扰扰胶胶里(自注:时鞑犯蜀未退),庙社嘻嘻出出间(自注:临安火焚宗庙、朝廷)。
欲上青天愁险绝,谁能为我斩楼兰。[1]34975
此诗颈联上下两句分写蜀地与朝廷形势,“扰扰胶胶”“嘻嘻出出”八字,将南宋内外局势之纷杂扰攘一笔画出。尾联收归到此次还乡之行,因路途之艰险而发出“谁能为我斩楼兰”的呼喊。
直至人生的最后一年,魏了翁仍以还乡为念。嘉熙元年(1237)正月,魏了翁在《辞免知福州福建路安抚使奏状》中自言心志:“日伺上流粗定,即反室于岷山之阳。会寒暑所侵,腹心受病,况又边虞洊至,蜀祸方殷,臣之进退,如蹈坎谷······伏望皇帝陛下检会累牍,曲垂哀矜,仍畀丛祠,俾得翱翔江干,以须平复。俟蜀道渐通,即归田里。”[6]196此时魏了翁已决意致仕,其所期望的是在“上流粗定”“蜀道渐通”的情况下,早日返回故乡。然而“蜀祸方殷”的现实,令魏了翁进退两难。此年三月,魏了翁因病辞世,在临终前依然牵挂着蜀地形势,“复语蜀兵乱事,蹙额久之,口授遗奏,少焉拱手而逝”[4]12970。
可以看出,魏了翁始终将故乡视作归宿之所在,而其还家之愿能否实现又必须以蜀地局势的安危为转移。巧合的是,魏了翁端平三年与绍定四年的两次返乡之行均笼罩在兵火的阴影之中,这种特殊的经历无疑使其更为深切地感受到了战争对于个人生活的影响。由此,对蜀地形势的担忧以及肃清蜀乱的愿望,也成为了魏了翁思归诗文最为重要的情感底色。
在蜀地局势日趋危急的情况下,能如魏了翁一般“寇焰兵氛返故乡”[1]34978已渐成奢望。端平之后,更多蜀士终身流寓异乡,故乡成为孤悬于西南、可望而不可即的怀想之地。如程公许端平元年(1234)被召入朝后,即一直居官东南,再未回蜀。当获知亲人来信或与亲人重逢之时,程公许对于故乡的感情常常会喷薄而出、无法遏止:
屏居北郊自秋涉冬绝省人事触绪有感托之讽吟书云前一日
缉成八章寓兴抒情非以言诗也·其五
鸟飞暮知还,蚁微亦有藏。
游子怅无托,故乡那得忘。
轒辒岁横骛,生涯日凄凉。
骨肉各窜匿,冢祠缺烝尝。
万里一缄书,临风泪千行。
垂白念汝兄,忧乐苦相望。
安得附羽翮,奋飞同一觞。[1]35519
送别彦威侄西归侍母·其三
宇宙暗矛戟,吾当何处归。
故山几幸免,暮景傥同依。
若见亲知问,愁无羽翮飞。
一箪元自足,底用带金围。[1]35644
此二诗都使用了近乎对话的语气,营造出一种亲密的家庭氛围,诗人由此得以尽情倾吐自己对亲人与故乡的眷恋之情。第一首开篇以鸟、蚁起兴,引出自己身为游子、漂泊无依的处境。当家信从万里之外寄来时,诗人自然难以抑制激动的情绪,由此不禁产生了生出双翅,飞至亲人身边这样无望的幻想。第二首起笔宏阔,在整个国家均陷入战争的情况下,“吾”—这一渺小脆弱的个体又何处可归呢?对此疑问,诗人自答:若故乡能侥幸摆脱兵火,在垂老之年你我或许还可以重聚吧!颈联与前诗“安得附羽翮,奋飞同一觞”二句用语相似,一为愁叹、一为希冀,共同道出现实中的相聚已难以实现。程公许明知还乡的可能性已甚为微茫,但又始终存有一丝幻想。欲归而难归,既难归而仍欲归,成为程公许诗作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在情绪的纠葛中,映照出诗人心中的无尽怅恨。
要之,蜀士的还家之愿能否实现,必须视蜀地乃至整个南宋局势的安危而定。在整个国家均被烟尘笼罩的情况下,蜀士返回故乡的希望也愈趋渺茫。然而,流寓异乡的生活并不能带给蜀士真正的安定之感,如其“四方蹙蹙还何许”“吾当何处归”的反问所示,答案永远指向故乡—蜀地。
二、乡事:积极迫切的救蜀之议
南宋时期,朝廷对蜀士虽时有排抑,但出仕于朝的蜀士数量仍不可小觑。以本文重点讨论的几位蜀士来看,魏了翁、李鸣复、吴泳、程公许、吴昌裔、牟子才、高斯得诸人均曾进入中央任职,魏了翁、李鸣复、高斯得三人更位居宰辅。以一定的政治地位为前提,蜀士留下了大量涉及朝政的奏议文字,这其中有不少与蜀事相关。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蜀籍士大夫并不属于同一个政治派别,甚至曾尖锐对立③。但若搁置党派之间的差异,而观察其与蜀事相关的政治言说,则会发现他们由“蜀人”身份出发在表达方式上的高度一致性。
以“蜀人”自居,是蜀籍士大夫谈说蜀事时的立论基础。具体而言,这包括几层含义。首先,“蜀人”身份意味着熟知蜀事的地域优势。蜀人生长于蜀中,对蜀地情况本就熟悉。即使任官于外,亦可凭借与蜀地亲友的通信而全面、快速地获知蜀事。如吴昌裔云:“臣近收乡人书,言戎帅曹友闻得谍者报,草地欲以八月入寇,则是臣防秋之说,于蜀尤不可缓也。”[8]110这种直接来自战地的信息,无疑可以帮助蜀士全面且快速地了解蜀边战事的发展情况。此外,南宋时期蜀士出仕于蜀的现象极为普遍,魏了翁、李鸣复、程公许、吴泳、吴昌裔、阳枋、牟子才、高斯得数人,均有在蜀地任职的经历。由上述身履目击的经验,蜀人对蜀地政治军事情况的了解程度自然远高于其他地区的士人。以李鸣复为例,其在不同的奏议中曾多次申说:“臣蜀人也,三仕剑外,十数年安危成败,身履而目击之。”④可见成长与仕宦于蜀地的经历对于李鸣复来说十分重要,因而成为其讨论蜀事的出发点。又如吴泳在绍定二年(1229)所作《西陲八议》:
口占屯戍之数,不如习见其事,而后知兵数之精;指示舆地之图,不如亲履其间,而后识地形之要。泳蜀人也,其于江淮、襄汉间事,则不敢望空而言,如蜀之险阨,边防之要害,则粗能知之,而亦粗能言之。[9]356
吴泳认为自己对于江淮、荆襄二边之事,只是望空而言。但作为蜀人,对于蜀地的边防情况则不仅“粗能知之”,而且“亦粗能言之”。宝庆三年(1227),吴泳被蜀阃郑损辟入幕中⑤,这篇《西陲八议》即是基于军前的实地考察而写成。事实上,宋廷亦以此“习见其事”与“亲履其间”之优势期望于蜀士。《宋史全文》记载了宝祐三年(1255)的一段君臣对话:“上谕辅臣:‘朝士有蜀人晓边事者,可令条具备御之策,参考而用。’”[10]2816可见,“晓边事”正是蜀人区别于其他地区士人的一个重要特征。
其次,蜀地是蜀人的“父母之邦”,因而蜀籍士大夫对于救蜀一事怀有强烈的责任意识与时不我待之感。如吴昌裔端平年间为监察御史时曾言,“臣以蜀人,待罪言路,若乡有急证而不言,则为有负于乡”[8]99,体现出其为乡事发声的责任感与紧迫感。吴昌裔于端平二年(1235)所作的《论蜀变四事状》[8]56与端平三年所作之《论本朝仁政及边事奏》[8]113,就是这种心态的集中展现。这两篇上奏的论述思路极为相似,吴昌裔均首先点明“臣蜀人也”的身份,并指出蜀地已经极为危急的局势。因此,吴昌裔在怀抱着“不敢欺君上而负父母之邦也”的担当意识上陈己见之后,呼吁朝中蜀士能够“各尽至公血诚,以救乡国”,并希望理宗谕令臣僚“亟图以救蜀之策”。若不如此,则蜀难保全,且因蜀居上游的战略地位,晚宋的整体防御布局亦将随之崩溃。这种强烈的危机感并非吴昌裔所独有,牟子才在《论全蜀六策疏》中亦以棋局比喻蜀地形势,指出蜀“亡形已具”,需“急着以救之”。当此之时,若坐视不救,则不但蜀将亡,江南地区亦难以独存。从“臣去蜀十又七年,日夜忧愤”[11]335之句,可见牟子才虽离蜀日久,但未尝一刻忘怀故乡。而其欲全力挽救蜀地于危亡之境的忧愤之情,亦流溢于字里行间。
由救蜀的急切心态出发,蜀人纷纷以“言蜀事”自任。这种“言蜀事”的积极性在吴泳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其在端平三年所作的《论坏蜀四证及救蜀五策劄子》中云:
臣窃见边事日急,国事日蹙,民生日困,士大夫日危,宗庙社稷之日凛凛矣。江淮事体,臣近者旅从橐之条陈,陪都堂之末议,计必转而上闻。独惟蜀中乃臣父母之邦,而弄坏至此,臣窃痛之······臣自离乡里,及造天朝,今九年矣。己丑,上西陲八议;辛卯,乞遣葵范救蜀;壬辰,疏四失三忧;癸巳,论武仙窥我安康,乞严作堤备;乙未,言元兵先通川路,后会江南,不可不固上流。又言西边连年调度,财殚力薄,乞速赐科降,蚤趣援兵。今岁之夏,乞蚤储蜀帅,以备不虞。又以彦呐末疾告老,会议都堂,尝言李埴有威望,杨恢有精力,皆可以为彦呐之代。无一岁不言蜀事,无一日不忧蜀亡。而诚意不积,不能感动,事势至此,噬脐何及![9]102
吴泳指出,蜀是其父母之邦,因此蜀地的破坏更令其感到切身之痛。从绍定二年(1229)到端平二年(1235)的数年内,吴泳连续上言蜀事,前文叙及的《西陲八议》即是其一。据吴泳所言,竟达到“无一岁不言蜀事,无一日不忧蜀亡”的程度,可见其上奏之频繁与忧虑之深重。在此劄结尾,吴泳又着重强调了蜀地对于南宋边防的重要性,希望朝廷能重视蜀事,“合群策而救之,资群力而复之”。对于吴泳这一系列议论蜀事的奏疏,四库馆臣有极高的评价:“至当时边防废弛,泳于山川阸塞,筹划瞭如,慷慨敷陈,悉中窾要······大抵于四川形势言之最晰,良由南宋以蜀为后户,于形势最为冲要。泳又蜀人,深知地利。故所言切中窾会,非揣摩臆断者比,实可以补史所未备。”[12]1393蜀人言蜀事的积极姿态与地域优势,都于此可见。
在上层官僚之外,未曾入仕于朝的蜀地士人又是如何谈论蜀事的呢?可以阳枋为例略窥一斑。与前述李鸣复、吴泳、吴昌裔等士大夫不同,阳枋一生浮沉州县,仕宦不显。其《送云山文先生吏部赴召》一诗,即是借着送文先生入朝的机会,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此诗首先点明蜀地护持东南的重要战略地位,“蜀为头目吴腹心,头目清明腹心佚”;接着回顾了近年来蜀中战事的成败,指出在蒙军实施斡腹之谋的形势下,尤其应该重视蜀地的防御作用;最后,诗人分述了“海道”“淮堧”“荆南”这三个战区的战况,以其情势尚宽作为对比,归结到对保蜀一事的强调之上:
当今重势在蜀川,蜀事艰难今转急。井络丘墟烟火空,荆棘漫弥虎窟室。
频年旱暵民流亡,褚无完裳瓶无粒。兵将愿战民效死,彼此交病财不给。
就中活着犹可为,民心戴宋元一日。益兵降财劳蜀民,旒冕周咨宜委悉。
射干狼毒漫战吻,芝朮参苓难愈疾。恳切深惟保蜀方,蜀苟措安国宁谧。[1]36102
阳枋认为,如今三边中以防守蜀地最为关键。而蜀地在经过战火之后虽民贫财竭,但民心未变,因此“活着犹可为”。可以看出,阳枋对于蜀事的密切关注与上层官僚并无二致,而其“恳切深惟保蜀方,蜀苟措安国宁谧”二句所传递的全力保蜀的政治立场,也正为晚宋蜀士群体所共同持有。
综上所述,由乡国之念出发,联系晚宋的国家形势,蜀士明确指出了“救蜀”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与此同时,蜀士也意识到熟知蜀事正是“蜀人”身份的优势所在,并在表达政治观点时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以增添言论的说服力。可以说,“言蜀事”已经成为了晚宋蜀士自觉的政治参与方式,而其议论也普遍呈现出忧急、痛愤的情感基调。
三、国事:愤郁绝望的误蜀之恸
蜀地危急的局势,时刻牵动着蜀士的心弦。与旁观者的立场不同,蜀地之残破对于蜀士来说是切肤之痛,这促使他们深刻反思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在蜀士看来,朝廷处理蜀事的方式与对待蜀地的态度,存在着诸多的问题,故此每有朝廷误蜀、弃蜀之恸。
晚宋蜀地屡经大变⑥,几次较大的战事中南宋军队之所以频遭惨败,主帅任命的失当是问题的关键所在。试看以下蜀士所论,“议者皆曰蜀经三变,一败而失四堡者,董居谊之罪也;二败而弃五州者,郑损之罪也;三败而委三关者,桂如渊之罪也”[8]56,“迩者丁卯之变,程松实当之,则自米仓遁;己卯之变,董居谊、聂子述实当之,则自剑门遁;辛卯之变,桂如渊实当之”[13]439,均指出对于战事的失利,董居谊、郑损、桂如渊、赵彦呐等阃帅不得不担其责。即使是理宗本人,也不得不承认“蜀从前亦委寄非人”[10]2739的事实。
在蜀士的诗作中,可见对朝廷委任非人不满、痛惜而又无奈的复杂感受。如魏了翁的《书所见闻示诸友》,作于前述绍定四年返乡途中,用组诗的形式对时事进行了记录与评论:
其一
行到青天最上头,蜀人争看锦衣游。谁知一夜北风恶,吹起家山万斛愁。
其二
闻说奔军闯阆州,余州民溃去如流。亲曾见虎诚堪怖,只为狐惊亦可羞。
其三
一从轻弃五边州,所恃藩篱仅武休。又谓武休无足恃,并捐洋汉守金牛。
其四
金缯啖虏已无谋,况恃空言废内修。师卦在中惟九二,曾闻帷幄授成筹。
其五
死城陷阵已长休,捍虏鸠民亦漫忧。局外闲人倚江立,全躯保室信良谋。[1]34976
第一首用“一夜北风恶”代指日益紧迫的边境形势,并由此展开对于故乡战事的评论。第二首描绘百姓一路溃逃、风声鹤唳的情状,暗含对于南宋军队的讽刺。第三、四首指出宋军失利的原因:蜀帅桂如渊一意与蒙古讲和通好,做出弃五州、退守三关的决定,在军队的指挥上更是失误连连。在这组诗中,魏了翁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辛卯之变,主帅应负主要责任。高斯得则更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朝廷,其宝祐元年(1253)所作的《次韵李通甫赋中秋》一诗,开篇描写中秋之时与友朋聚饮的场景,“赏心与景会,喜极悲还作”以下,意脉陡转,由西南之望,引发了对于故园的感怀:
渺然望西南,慨想旧猿鹤。岂无首丘情,归去事耕凿。
奈何朝廷上,聚铁方铸错(自注:时余晦将入蜀)。弃置勿复道,洗盏更深酌。
我老倦吟诗,无悰纪行乐。故人诗筒来,晨檐有鸣鹊。[1]38553
诗人明言欲归故乡,然而庙谟之误,却使蜀地局面更为不堪。对于以余晦为蜀帅的任命,晚宋士人多持批评态度⑦,高斯得也不例外。但其作为乡人而发声,更包含着对蜀事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的沉重叹息。与结尾“弃置勿道”之语可资参照的是,上举魏了翁之诗在末二句亦以“局外闲人”自居,这种故作反语的姿态所反映的,正是蜀士明知朝廷举错之非却不能有所作为的无力之感。
此外,蜀士亦常常提及朝廷处理蜀事的淡漠、迟滞,以及朝议近乎“弃蜀”的态度。“而今之待蜀也,如破釡坏甑,任其残缺而莫之省忧也······旷岁弥年,无一语相及,告者益急,应者愈缓,恐远方之人便谓朝廷无保之之意。”[9]73“自丁卯曦乱兴沔,而权臣已有弃蜀之说;自己卯寇入汉中,而廷臣又有无蜀亦可立国之论;自辛卯敌兵破利入阆,而襄阳帅臣复有扼均房、守归峡之策。积习至于去冬,庙堂条具边事,夔帅申明事宜,则又欲置襄州一屯于金,移田家一军于戎矣,何待蜀之薄如此耶?”[9]102“众议欲除一宜谕从夔门经理,今已旬月而未见施行,又闻有台臣有言欲斥逐小吏之壅蔽蜀事者,公论咸以为快,而亦未见检会行遣,岂朝廷之议殆类于弃蜀耶?”[8]113从这些奏议中不难看出,朝廷对待蜀地的重视程度,远远无法满足蜀士的期待。事实上,即使是非蜀籍的士大夫,对于朝廷轻忽蜀事的态度亦感到有欠妥当。如吕午认为:“勿谓蜀为去天之远,而此可苟安;勿谓蜀为已坏之证,而遂不加意。”[14]41程元凤亦云:“蜀之存亡,关系若此,而朝廷之上若罔闻知,毋乃谓蜀为去天之远,而此可久安欤。抑不知其地虽远,而实有唇亡齿寒之忧。其证虽坏,而岂无回生起死之剂?”[15]55二人以“去天之远”与“已坏之证”的相似表述,指出蜀地存亡关乎南宋安危,不可坐视其败。
朝廷的弃蜀倾向,使蜀士深感身处于被忽视、抛弃的境地。如魏了翁诗,“蜀力如蜗涎,仅足以濡身。云胡走荆楚,坐视空川秦。天下本一家,奚必尔我分。独怜去天远,缓急呼不闻”[1]34887,“蜀山在何许,斜阳点鸦背。家住扶桑东复东,却望斜阳铁山外。金头奴子扼熙秦,银州兵马冲兰会。使我六年望烽火,征人穿空枕戈祋。使我千里致钟石,居人轑釜泣粗粝。县官无蓄租,百姓无藏盖。上有苍苍之高天,卒然叫呼不可待”[1]34894,均表达了蜀人呼天不闻的痛苦。由上文可知,这种“天远”的感受,并非仅由于蜀地与朝廷距离的遥远,更是根源于朝廷对待蜀事的冷漠态度。
面对故乡的残破,蜀士虽察其因却无力拯救,而朝廷处理蜀事的态度更令其怀有一种被弃置之感,这造成蜀士言及蜀地命运之作中往往掩抑着极深的愤郁与绝望。程公许之诗就深切地反映了蜀士的这种幽微心绪:
屏居北郊自秋涉冬绝省人事触绪有感托之讽吟书云前一日 缉成八章寓兴抒情非以言诗也·其六
西陲失支吾,如老屋积腐。墙闼纵蹂躏,堂屋何依怙。
伊谁阶此厉,乃为元老误。疾痛切吾身,利钝难逆睹。
瘴暑困新恩,陨星泣忠武。梁坏将安仰,天高杳难诉。
向来十二楼,卷帘误一顾。洒泪嫁时衣,谁与论心素。[1]35519
诗中对“元老”误蜀的指责和“天高难诉”的叹息,已见前述。“疾痛切吾身”二句,诗人更提及对于蜀地未来的不详预感,所谓“难逆睹”,正出于诗人之不愿言与不忍言。结尾“向来十二楼”四句,化用陈师道《放歌行》语意以寄托己志⑧,诗人之“心素”,当指拯救乡国之愿,而回顾入朝至今的经历,其愿望无疑是落空了。此诗多用比兴寄托,将国家形势比拟为老屋之将腐,颇具汉魏五古风味,其中婉转哀怨的思致,正典型地体现出蜀士对于朝廷不易明言的复杂情感。
结语
蜀地之残破与蜀士之流寓,成为了晚宋新出现的社会问题。蜀士诗文中的家国情怀,既为时局所激发,亦因时局而复杂化。首先,在兵戈扰攘之时,蜀士家人的平安与其归家之愿的实现必须以蜀地乃至整个南宋局势的安定为前提。魏了翁词中“家国两平安”[16]2366的祝愿,或可视作晚宋蜀士的共同心声。这使得蜀士对于上述私人领域情感的书写,始终与时代的大背景紧密相连。其次,蜀士在救蜀一事上有着坚决的政治表达,这既是从南宋的整体防御局势着眼所进行的考量,亦根源于其深切的乡国之念。因此,蜀地士大夫呼吁救蜀的急切与紧迫姿态,在晚宋朝士中显得极为突出。其三,晚宋朝廷处理蜀事的方式与态度令蜀士深感失望,这就造成了蜀士对于朝廷既望其救蜀亦怨其误蜀的复杂心态,而其诗作也由此常常被压抑、悲观的情绪所笼罩。
余蔚、任海平在《北宋川峡四路的政治特殊性分析》[17]一文中指出,北宋时期川峡地区对于中央有比较大的离心力,而向心力相对较弱。南宋时期则由于外患这一外力因素凸显,使得川峡地区与朝廷之间的联系趋于紧密。这一阐释模式颇具启发性,但若以此来审视南宋后期,则应看到向心力有所增强的情况下,离心力的余波仍然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一方面,朝廷在重视蜀地防御的同时,措置蜀事多有失误,弃蜀之说更甚嚣尘上;另一方面,蜀士固然希求朝廷之力以救乡国,但其对朝廷举措亦颇为不满,对于蜀士来说,保蜀、救蜀的急切性甚至更在保国、救国之上。综上所述,巨大的外患压力与地理、政治隔阂持续存在,造就了晚宋蜀地与中央之间向心力与离心力共存的微妙关系。因此,如果将蜀士的家国情怀具体分为家事、乡事与国事三个维度,则能看到蜀士对于这三者的情感固然密不可分,但前两者与后者之间又并非全无冲突。而正是这些不易察觉的冲突,造成了蜀士家国情怀的书写之中忧愤与怨抑并呈的情感底色。
注释:
① 相关研究可参看林天蔚:《南宋时强干弱枝政策是否动摇?—四川特殊化之分析》(收入氏著《宋代史事质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林文勋:《北宋四川特殊化政策考析》(收入云南大学历史系编《纪念李埏教授从事学术活动五十周年史学论文集》,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2年)、粟品孝:《宋朝在四川实施特殊化统治的原因》(《西华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何玉红:《南宋川陕边防行政运行体制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等论著。
② 程公许:《去岁重阳日得彦威信,附六月间二小侄及从弟侄所寄书,自蜀阃递中附至。历言去冬今春所遭兵祸,及有司督迫科调之苦,喜其存全,哀其窘蹙,洒涕如霰。寄讯邀其下峡,而边事又告急,未知其达与否也。会杪冬见邸报,宣谕使者余公侍郎改命授钺,尽护蜀师,意欲以此事归控骨肉会聚,兹事其谐矣。喜极涕零,遂成长篇》,《全宋诗》第57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35524页。由诗题“宣谕使者余公侍郎改命授钺,尽护蜀师”,知其作于淳祐二年(1242)。参看(宋末元初)佚名,《宋史全文》卷三三,(淳祐二年十二月)“四川宣谕使余玠权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北京:中华书局,2016年,第2752页)。
③ 如李鸣复曾多次弹劾魏了翁,(元)脱脱等《宋史》卷四二《理宗纪》记载:“台臣李鸣复论曾从龙、魏了翁督府事,不允。”(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809页)吴昌裔亦与李鸣复处于对立阵营,参看《宋史》卷一六七《杜范传》:“会杜范再入台,击参政李鸣复,谓昌裔与范善,必相为谋者,数谗之,以权工部侍郎出参赞四川宣抚司军事。”
④ 李鸣复:《拟轮对劄子》二,《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年,第308册,第439页。此句亦出现在其《论复家计寨增忠勇军额疏》及《论蜀中守御疏》中。
⑤ 参看吴泳《缴奏赵汝谈指摘告词状》(《全宋文》第316册,第128页):“照得损帅蜀四年,臣于宝庆三年十月十八日以成都路机被制司辟差入幕,至次年二月二十一日祗受都堂审察之命。”
⑥ 主要有丁卯之变(开禧三年,1207)、己卯之变(嘉定十二年,1219)、丁亥之变(宝庆三年,1227)、辛卯之变(绍定四年,1231)、丙申之变(端平三年,1236)及辛丑之变(淳祐元年,1241)等。
⑦ 如《宋史全文》卷三四宝祐元年(第2821页)载:“是日,国子司业叶梦鼎进对,奏至三蜀遣使,上曰:‘此人有才。’叶梦鼎奏:‘其人虽少有才,蜀当垂亡危急之秋,恐不胜任。愿入圣虑,毋嫌反汗。’”又如(元)佚名撰,王瑞来笺证,北京:中华书局,2010年,第204页,《宋季三朝政要笺证》卷二:“宝祐二年(笔者注:宝祐二年误,当为元年),以余晦宣抚西蜀······徐清叟奏云:‘······今乃以素无行检轻儇浮薄不堪任重如晦者当之,臣恐五十四州军民不特望而轻鄙之,夷狄闻之,亦且窃笑中国之无人矣。所有除晦内批,乞赐收回。’”
⑧ 陈师道:《放歌行二首》(其一):“春风永巷闲娉婷,长使青楼误得名。不惜卷帘通一顾,怕君著眼未分明。”(宋)陈师道撰,(宋)任渊注,冒广生、冒怀辛整理:《后山诗注补笺·后山逸诗笺》卷下,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5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