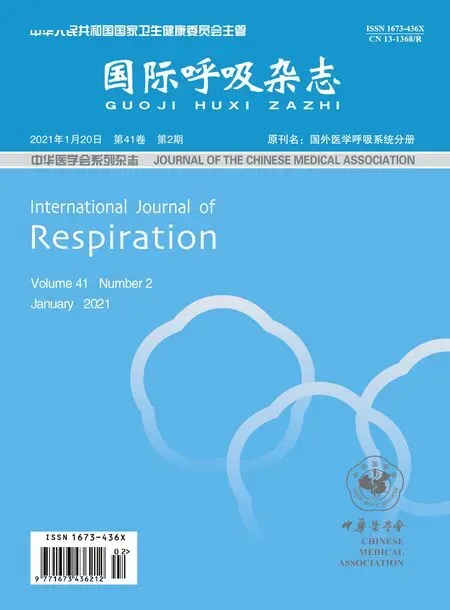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断研究进展
2021-11-30吴昊郑锐
吴昊 郑锐
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盛京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沈阳110004
随着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的出现[1],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SARS-Co V-2)感染人数迅速增加,WHO宣布将COVID-19作为国际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事件[2]。与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相比,SARS-Co V-2具有高传染性,人群对这种病毒普遍易感,尽管病死率低,但它仍对人们的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3]。
截至2020年12月4日12时,中国共86 601例确诊患COVID-19,其中累计死亡病例4 634例[4]。截至2020年12月4日18时9分,全世界已有235个国家或地区出现过感染病例,其中疫情最严重的美国已有13 759 500例确诊病例,其中死亡271 233例[5]。控制疾病传播,及早诊断和治疗可有效控制感染率和病死率。疾病的诊断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文综述了COVID-19的临床症状、化验指标、影像学特征、分子学及血清学检测方法,和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的诊疗方案多个修订版本诊断标准的变化,为疾病的诊断提供最新的认识,也可为之后的研究提供参考。
1 COVID-19的临床表现
COVID-19的临床症状缺乏特异性,在不同人群中的表现也不尽相同。最常见的有发热、咳嗽、咽痛、流涕、头痛、乏力、肌痛、结膜炎[6-8]。Luo等[9]发现,16%的患者仅表现为胃肠道症状,如食欲差、恶心呕吐、腹泻和腹痛等。疾病也可导致厌倦、孤独和愤怒等情绪变化[10]。重症患者可表现出多种并发症,包括ARDS、心脏损伤、肝脏损伤以及继发感染,严重时可出现败血症甚至休克[3,11-12]。
年龄与疾病的病死率相关,84%的死亡患者年龄在60岁以上[13]。这可能是因为老年人血清抗体浓度降低,免疫力下降,导致老年COVID-19患者感染后病死率增加[14]。有研究发现儿童感染者潜伏期更长[15],新生儿、婴儿及儿童的症状比成人轻或无症状[6,15],有的儿童仅有干咳[16]。也有儿童出现发热、干咳和乏力,并伴有一些胃肠道症状。大多数患儿预后良好,可在发病后1~2周内恢复[17-18]。重症儿童最常见的症状是呼吸困难,其次才是发热和咳嗽[19]。也可出现多器官损伤,如肝脏及心脏损伤,甚至发生败血性休克、代谢性酸中毒以及出血和凝血功能障碍,且疾病进展迅速[16,20]。COVID-19感染对孕妇的影响较轻[21]。目前还没有数据表明怀孕会增加COVID-19的易感性[22]。武汉以外地区大多数孕妇症状为轻到中度,主要为发热和乏力,咽痛和气短并不常见[23]。部分患者也可出现妊娠并发症,如死胎和胎膜早破[21]。
总体来说,COVID-19主要表现为发热、咳嗽、乏力,也可出现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和精神症状。老年人症状相对较重,儿童及孕妇较轻。但COVID-19症状和常见的呼吸道感染相似,缺乏特异性,只能对疾病的诊断起到一定的提示作用,需注意和其他疾病的鉴别[24]。
2 COVID-19实验室指标
COVID-19患者实验室检查主要表现在血常规、炎症指标、凝血指标及肝肾功能的异常,虽然无特异性,但可以对疾病的诊断和预后的判断起到一定的提示作用。
2.1 血常规 血常规中白细胞计数通常正常或较低[3,6];可能出现淋巴细胞计数减少,这和疾病严重程度有关[3,6,25]。有研究发现,死亡组较恢复组患者入院时有更低的淋巴细胞计数和淋巴细胞与白细胞的比值,且比值在住院期间会持续性降低[26]。血小板计数通常正常或稍下降[6,27]。难治型较一般型患者有更低的血小板计数[8]。血小板计数降低可使重症患者风险增加5倍[28]。
2.2 炎症指标 关于常见的炎症指标,大多数患者表现出C-反应蛋白、ESR升高,降钙素原(procalcitonin,PCT)水平通常正常[3,6]。重症患者PCT水平高于轻症患者[25]。和成人患者相比,PCT升高更常见于儿童,其更易出现混合感染,因此儿童的抗微生物治疗很重要[29]。但也有研究发现,儿童患者PCT在大多数情况下是正常的。PCT>0.5μg/L时表明与细菌共感染[20]。
多数研究发现,COVID-19患者炎症细胞因子中的IL-6、IL-8和IL-10高于其他疾病,且重症患者更为明显[3,19,30-31]。同严重程度相同的其他疾病相比,COVID-19患者更易观察到高水平的IL-6和IL-10[3]。COVID-19重症患者的IL-8和IL-10高于非重症患者[30]。一项对19岁以下患者的研究表明,IL-6可作为重症COVID-19感染的潜在预后指标[31],对重症儿童的研究也得出类似的结论[19]。但也有研究发现,COVID-19和其他类型肺炎患者的IL-6水平均升高,且两者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2]。这需要进一步研究加以证实。
2.3 凝血指标 凝血指标和COVID-19的发生及预后密切相关。研究发现,COVID-19患者的D-二聚体、纤维蛋白/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fibrinogen degradation products,FDP)和纤维蛋白原均明显高于健康对照组。严重SARSCo V-2感染者的D-二聚体和FDP水平更高[25],这有助于早期发现危重病例[33]。同样,重症儿童也出现D-二聚体水平升高[20]。一项对预后的研究发现,入院时死亡组D-二聚体和FDP水平明显高于存活组,71.4%的非幸存者和0.6%的幸存者在住院期间符合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标准。重症COVID-19患者易发展为脓毒症及多脏器衰竭,脓毒症是弥散性血管内凝血一个重要原因[34]。
2.4 肝功能及肾功能 少数患者可出现肝功能、肾功能的异常。与非COVID-19相比,COVID-19表现出更为异常的肝功能指标,如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谷丙转氨酶、γ-谷氨酰转移酶等[32]。相比于恢复组,死亡组谷丙转氨酶、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和肌酐的水平更高[26]。
虽然COVID-19患者化验指标没有明显的特异性,但可以作为诊断及判断预后的辅助手段。成人和儿童的实验室指标未见明显差异,但有研究表明儿童更易出现降钙素原水平升高,这需要进一步的研究证实[29]。
3 COVID-19影像学特征
COVID-19的影像学检查对疾病的诊断有很大价值,且胸部CT较X线更为敏感[6]。COVID-19患者的影像表现具有多变性。在特殊人群以及不同年龄、不同地域人群具有不同的特点。
3.1 COVID-19影像的典型和非典型表现 COVID-19典型CT表现包括:双肺多发、斑片状、节段性磨玻璃影或实变,可伴有“铺路石”征[1-2],甚至出现“白肺”[35]。非典型CT表现可见胸膜下小叶间隔的网格状或蜂窝状增厚,支气管壁增厚,实变结节伴周围磨玻璃影[1]。
一些少见的表现还有胸腔积液、心包积液、气胸、淋巴结肿大等[36]。随访CT中可出现类似“供血管征”表现,这可以预测最初的肺部恶化。少量胸腔积液提示临床预后不佳[37]。
因此,教师应积极引导学生对自己经营失败的思想认识,尽量将经营失败归因于自身努力不足等相对不稳定的内因,以及将偶尔的失败归因于不好的运气等,使其保持学习的持续性或付出更大的努力。
3.2 影像学病灶分布 病灶在胸部CT上分布也有一定规律。常见分布于双肺支气管束或胸膜下[38-39]。半数以上患者病灶表现为双侧多灶性周围分布[3,40],个别患者可出现局灶性非外周分布[41]。COVID-19患者全部肺叶受累占44.4%,单个肺叶受累占30.2%[42]。病变多位于下叶[40],右下肺叶病变最常见[43]。但有研究表明,病灶在儿童以左肺下叶为著[44]。个别患者病变会出现在右肺中叶及左上肺磨玻璃影[36,41],进展期病灶主要分布于肺中部和外部[42]。重症及危重症患者病变常累及4~5个肺叶,多分布在双侧更偏上或偏下的肺叶[7]。总之,COVID-19肺部病灶主要分布在支气管束或胸膜下,多位于双肺下叶,重症患者会出现更多肺叶受累。儿童的病变分布是否与成人一致需要进一步研究证实。
3.3 特殊人群影像表现 针对孕妇的研究发现,磨玻璃影及磨玻璃影合并网格影更常见于非妊娠组,但实变更常见于妊娠组,这意味着疾病严重程度的增加[45]。
有研究表明,所有感染的婴儿都有家庭聚集现象[46],但家族聚集性发病的影像学表现也不同[47]。COVID-19儿童的胸部CT表现与成人相似,但多为轻症。实变影周围出现晕征是儿童的典型表现[29,45]。对重症儿童的研究发现,胸部影像学最常见的是多发斑片状阴影,其次是磨玻璃影[19-20]。
疾病的CT表现也与年龄分布有关。年轻患者(<50岁)往往有更多磨玻璃影,而年长患者(>50岁)有更多的实变合并机化肺炎影[48-49]。
3.4 不同地域人群影像表现 不同地域人群影像表现各有不同。在中国湖北省以外省份患者的影像表现更为温和[50-51],而其他国家患者影像表现轻于中国[52]。在中国湖北以外地区,如浙江和北京,患者的临床症状及影像表现都轻于湖北武汉[50]。这部分患者的胸部CT更多表现为磨玻璃影,部分可有“铺路石”征[51]。无实变的磨玻璃影在韩国病例中占45%,在中国占45%~67%。中国COVID-19患者中实变为主病变的比例约为30%~60%,但韩国患者没有实变为主病变[52],影像表现更轻[52]。
研究发现,最严重的CT表现常出现在症状发生后9~10d[53-54],与临床症状改善相对应的影像表现通常发生在发病第2周以后[36],但CT的表现和临床症状并不完全相符。部分患者胸部CT无阳性表现[2,55],尤其是儿童、青少年及年轻患者[7]。CT表现可先于症状发生[54],也可出现临床症状缓解时CT表现加重[47],因此定期复查CT有助于判断疾病进展及预后。
总的来说,胸部CT主要表现为双肺胸膜下磨玻璃影,可合并斑片影、实变影、小叶间隔增厚等。胸腔积液、淋巴结肿大、气胸等表现不常见。中国湖北以外的地区以及其他国家患者的影像表现更温和。另外,CT表现和临床症状不一定相符,定期复查CT有助于判断疾病进展。
4 COVID-19分子学及血清学检测
WHO推荐将分子学检测作为确诊COVID-19的首选方法,血清学检测主要在疾病监测和流行病学研究中发挥重要作用[56]。
虽然核酸检测可以作为诊断的直接证据,但该方法存在一定的假阴性率[59,62]。这可能和标本的收集方法、干扰物质存在、接受检测患者治疗等因素有关[63]。流行病学史、化验和影像学检查的联合应用,可以帮助筛选出阳性患者。
4.2 COVID-19血清学检测 目前人们对SARS-Co V-2特异性Ig M和IgG抗体的产生时间有较多争议。研究表明,SARS-Co V-2感染人体后,其Ig M抗体在5~7d产生,IgG抗体可在10~15d产生[64]。也有研究发现,发病5d后可检测到Ig M和IgG抗体[65]。罗效梅等[66]证实最早在发病4d时可检测出Ig M抗体阳性,8d时其阳性率达到100%;28d后Ig M抗体开始消失,IgG抗体阳性率开始提高;Ig M和IgG抗体阳性率与发病天数有关,与疾病的分型无关。但也有研究得出不同结论,血清IgG抗体产生同时或早于Ig M抗体[67]。研究结果的不同可能与血清学抗体检测方法不同有关[58],另外个体免疫应答产生抗体的差异性、抗体检测时间、不同研究中人群的年龄分布也会影响检测结果[14,68]。
Ig M抗体阳性往往表明最近接触了SARS-Co V-2,而IgG抗体阳性则表明一段时间前接触了病毒[69]。Ig M浓度下降或消失,IgG浓度升高,预示着患者逐渐痊愈,并产生了对SARS-Co V-2的免疫力[65]。也有研究证实,SARSCo V-2棘突抗原刺激产生的抗体对机体可能有保护作用[69-70]。与单一Ig M或IgG抗体检测相比,Ig M-IgG抗体联合检测具有更好的特异度和敏感度[68]。血清学方法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检测的阳性率[64],但抗体产生时间和假阳性率仍是需要关注的问题。
5 中国COVID-19诊断标准的变化
疾病爆发后,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并且随着疾病的进展和对疾病认识的逐渐深入,从2020年1月15日至2020年8月18日先后进行了8个版本的修订。其中诊断标准分为疑似病例和确诊病例的诊断[71-77]。疑似病例主要通过流行病学及临床表现诊断。确诊病例通过核酸检测、病毒基因测序和SARS-Co V-2特异性Ig M和IgG抗体判定。不同版本之间的比较体现了对疾病认识的逐步完善。和第一版相比,第二版给出了病毒人传人的传播途径。确诊方法增加了实时荧光RT-PCR检测手段。第三版中重症病例的诊断标准更加严格[71]。第四版强调部分患者影像学检查可能为阴性,确诊标准中增加了血液标本。同时增加了临床分型,其中重型患者的纳入条件更少,降低了重症患者的比例[72]。临床分型可以及早发现重症及危重症患者,使其尽早接受更多的医疗支持,提高生存率,同时有利于资源合理分配。第五版增加了临床诊断病例,这部分患者虽然核酸检测可能为阴性,但同样需要引起重视[73]。第六版重型病例增加了影像学的诊断标准,强调影像学复查的重要性[75]。第七版增加了血清学方法作为确诊标准,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和敏感性[76]。第八版强调了重型/危重型高危人群的范围,同时增加了重型/危重型的早期预警指标,更有助于判别重症患者,使资源得到更合理的应用[77]。
综上所述,COVID-19作为高传染性疾病,其主要表现包括发热、咳嗽、乏力等,也可出现胃肠道、神经系统及精神症状。实验室检查主要表现为血常规、炎症指标、凝血指标及肝肾功能的异常。影像学表现在特殊人群以及不同年龄、不同地域的人群也会有所不同。核酸及血清学抗体的检测作为确诊的主要手段,具有一定的假阳性和假阴性率,规范操作、减少污染等可以提高其准确性和敏感性。临床医师应结合流行病学史、化验及影像学检查、核酸及血清学检查等方法加以诊断。我们希望可以有更多的诊断相关研究帮助人们提高对COVID-19诊断的认识,及早的诊断并有效地控制疾病传播,使感染者得到更加有效的治疗,提高患者的生存率。
利益冲突 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