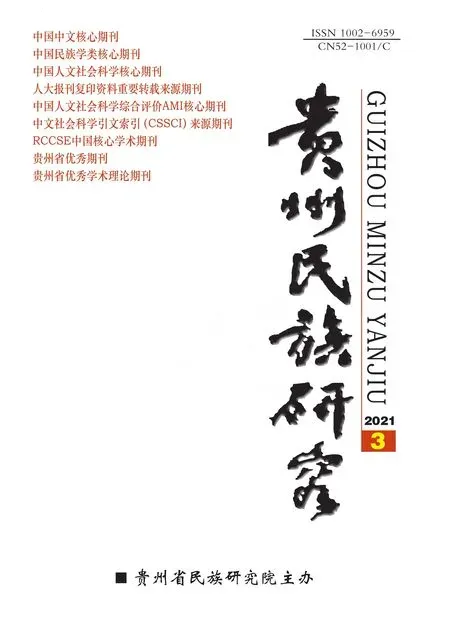文化选言中的爱情体验:以吴娜电影为例
2021-11-30普天行
普天行
(贵州民族大学 传媒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吴娜导演成长于贵州黔东南,毕业于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英语教育专业,生活背景、文化体悟奠定了其电影的双面底色——一面是对民族文化的眷恋,一面是对外部世界的好奇。《行歌坐月》(2011)和《最美的时候遇见你》(2014)均从女性视角讲述了初恋体验的青涩、美好和遗憾。前者克制、细腻地再现了贵州黔东南侗族村寨的生活情趣及自然风貌,用轻缓的视听呈现了侗族大歌、吃新等民俗,少女情愫埋藏并氤氲在这片浓绿的大山之中,又充满了对外界的向往;后者则将爱情放置于现代化城际间距的背景之中。
一、故乡
《行歌坐月》作为一部“献给家乡的情书”,少女心思显得含蓄而令人着迷。这封情书属于未来和过去,但不存在于现下,她深藏于一个少女的暗恋潜流中,随着姑姑的归来,恋情的挫折已然若揭——故乡也回不去了。这位中学毕业便留守侗乡的女孩,因少年时的返乡情愫而涌动。醋意伴随着对外界的好奇,暧昧交织。风雨桥中裸露的女性大腿,野泳的红色泳衣,渐次去往城市的伙伴,木质吊脚楼与砖房,文琴与吉他,镜头始终深深埋在绿色的大山中,直至火焰将之心绪波动。外部世界的样貌囿于离乡少年们的玩笑、姑姑的故事和父辈的“不准去”里。城市在电影中不作为一个具体的形象被呈现,它被廓除了,观众始终停留在一个孤独的少数民族村寨中。尽管杏还是追随飞(是追随爱情的对象还是追随着想象的时髦都市?)离开侗寨,她遇着什么,亦无明示。归来的杏怀孕了,又做了一场梦:她背着一个戴了民族帽的婴儿。拉镜头离开她,失焦。这个她属于过去。因为爷爷去世了,时间的流动性意味着逝去,影片最终言明了创作者对故乡的眷恋。这与该片开头第一个梦呼应,那个源自醋意(一面关于飞,一面关于其他出走的伙伴)的梦暗示了杏对于外部世界的好奇和对未来的期许。
显然,城市或乡土作为一种非此即彼的选言命题,在时间的流动中,在一个少女不甚明朗、谨小慎微的暗恋姿态下缓缓推进。结尾隐喻出一个往复洄游的文化认同,不甚明了。孕育代表了爱之永恒的延续性,它是恋人间的,也是文化间的——融合始终伴随着彼此间或多或少的拉锯式淘汰与失落。于是,民族身份尤为显眼地成为这部影片的视觉识别系统,间或出现的他者以及“叛离”,使其文化的徘徊变得迟钝又脆生生地撕扯阵痛起来。
有些时候,文化身份会在叙事中作为一个不相容选言——譬如这样的句式:“文明客不是同‘蛮荒’之人相杀,就是同‘蛮荒’之人相爱”。在库珀和舍德萨克的《金刚》(1933)、吉勒明的《金刚:传奇重生》(1975)以及杰克逊的《金刚》(2005)中,不同语境产生出“相同故事”的不同选言。1933年的金刚还是一个徒有其表的异域奇观,来自现代文明的金发丽人则作为一个诱人的符号;四十多年后,金刚和金发丽人之间的关系就显得暧昧多了;到2005年,他们似乎坠入爱河,尽管文化身份依然作为一道鸿沟[1]。不相容选言中的爱情故事,往往“顾此失彼”,建立在“主客体”视域中的本体论规则之上。又如复杂社会格局和国家想象中孕育的《瑶山艳史》(1933)讲述了汉族青年黄云焕深入瑶疆,与瑶族少女孟丽、李慕仙之间产生的三角恋情故事,“是30年代初期中国社会的产物,在联合境内各民族打造‘中华民族’的年代,蛮荒被视为摩登,走入边疆是流行的壮举。”[2]这部现实中“有迹可循”的电影在宣传上描摹了边民的异族情调,用一种不着边际的招摇将瑶族形象为文明客倾心的情色待开化者。“瑶女裸浴曲线毕露,瑶民就谈教育普及”[3],这部影片的宣传语从某种程度上再现了西方世界“想象的东方”。闯入者的“他者之眼”是文化想象中影响力最强的表达范式,《云上太阳》(2012)诚挚地表达了丑丑作为一名少数民族导演对异乡人的热情好客,对法国女画家的奇妙治愈则显现出这部电影某种虚无缥缈的诗意。相比《瑶山艳史》呈现出的对于异质文化的情色欲望,《云上太阳》的友好姿态是善良而积极的——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后者健康地传递出落落大方的包容和人情味。通过不相容选题,我们最终选择一个正确答案,为之感动或兴叹。但是,究竟如何才能在深度上显示出文化交流的裨益?文化想象将他者文化降格为淫靡的狂女,或者我们仅仅停留在“一厢情愿”的美好期许下,那么文化与文化之间的沟壑与摩擦在疏忽大意的小心呵护中消隐了。不得不说,润滑剂并不能使得那个最为本真的存在彼此靠近,我们依然需要正视并珍惜那些在文化的长谈中不经意流露的真心话。文化的交往,与两个他者的相遇一样,不可能是没有体积碰撞的。
另一方面,“还要经历多久时间,个体身份才能不再与民族同情的律令死死地绑定在一起?”[4]从《瑶山艳史》到十七年电影创作,爱情首先作为一种服从于主流话语的意识形态表达——如《秦娘美》(1960)及《刘三姐》(1960)。政治教化作为这些电影最重要的任务,“党的文艺方针是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文艺为大众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一切文学创作都要围绕着这个方向,作为社会主义文化组成部分的电影也不例外。在这样的语境下,电影为‘政治服务’成为首要的‘政治任务’,特别是作为与国家政权稳固息息相关的文化宣传工具,少数民族题材影片的拍摄,从某种程度上说,也必须为‘巩固边疆,加强民族团结’的政治形势服务。”[5]随着现代化进程加快脚步,国家战略不断发生调整,个人生活体验急剧改变。少数民族或地方创作主体对于民族、地域及自我的思考亦在发生改变。当两个不得不同处一室的陌生人在短暂地相互客套和试探性地彬彬有礼之后,很可能进入到一个认识论的紧张阶段。这与“寻找到同者、志同道合者,从而导致我们的经验视野日渐狭窄”[6]不同,我们可能对他者产生敌意,也可能产生敬畏,我们意识到一个特异于我们的另一个主体,有助于了解自己。
在吴娜的电影中,少数民族身份并未沦为媚态的刻奇,作为一位暗恋状态无法迈出的少女,作为一个封闭的孤独个体,其恋情无法与人诉说,只能克制而隐忍。初恋的青涩,家庭的善良以及自我的省思,对于那个未来的世界,已到的现代化,亦非采取强烈的批判姿态,这种意识流的直接感受正诚实而可贵地尝试着将概念世界廓除。
杏的爷爷在“看电视”时,电视内容总是本民族的(影片最开始,爷爷面前的电视正在播放一个侗族少女弹唱民歌的内容;杏离家出走后,爷爷生病卧床,电视上播放的是侗族大歌的场景);而年轻人面前的电视则播放流行音乐和偶像剧。前者的观看如同顾影自怜,是等待或守望的,甚而是那喀索斯式的;后者是向外拓展的,表明了一种想象和渴望。爷爷的离世告知了这种等待的无望和茫然,杏重复了姑姑的命运又告知了渴望的无期和困惑。电视作为现代媒介兀然放置于这个孤独的村落中,投射出两种文化身份的可能性,却无法给出那个选言的确切答案。这个现下处于等待中的少女并未被动地遭到一种民族关系或文化表征的裹挟,而是先在最一般人类情感的肇始下触碰到了异质的他者和文化。民族、文化、政治、性别或者简单的媒介关系,反过来使得爱情作为受到抑制的情感冲动显现——在“保守”的村寨里,杏渴望着出寻;而后,时间又使这个村寨变成了回不去的故乡。正如加缪在《局外人》里说,“故乡安置不了肉身,从此有了漂泊,有了远方。异乡安置不了灵魂,从此有了归乡,有了故乡。”在故乡与异乡的回环中,总有一个是不在场的,在加缪的句式中,文化身份是飘忽的,它同样是一个优柔寡断的选言命题。如同乡愁的发生一样,爱情的发生亦伴随失去或空缺。《行歌坐月》敞开了一个更为复杂和本真的文化状态和爱情存在——一个相容的选言。
二、他乡
与第一部影片相比,即便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是这个爱情故事的重要“发生地”,《最美的时候遇见你》似乎除了镇远的徽派古城及凯里的现代民族体育馆,已无更多可供辨识的地域特征(甚至方言的使用也并不“地道”)——这个故事仅保留了一段促成爱情生发的简化的时空距离。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爱情叙事,最终导向的是那种巧妙对仗(置换)在时空关系中的话语、伦理及概念。爱情由一个动词转换为名词,即一个结果。促成这个结果或相反,取决于横亘在一对恋人间的阻碍(矛盾)是否得以解决。当这个矛盾作为一种宗教、政治、伦理或种种其他因素出现时,所有使之不能结果的,均会引起人们的同情或厌恶之感。
无论是斯万的嫉妒、欧律狄刻的消失还是波德莱尔的惊魂一瞥,无论是莎翁的毒药、法海的雷峰塔还是珠郎娘美的款约,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爱情叙事都作为一个不永恒的存在显现,它们(爱情)存在于信息不对等的时空流动中,伴随着某种猜测、诱惑和妒意。在这部电影中,杨芳芳和郭阳的每一次“遇见”都伴随着疾风骤雨的快乐和随之而来的痛苦。不同地域不再表征城市与乡村的紧张,也并未出现一个其他的矛盾阻碍他们的爱情关系,这个相对立体的行为,只存在于时间和空间的拉扯中。在吴娜的电影中,电视、电脑、书信、火车、手机的介入完成了一层媒介的隐喻——人们的经验世界及关系受到媒介的左右,另一方面,这些影响了人们如何使用感知的媒介反过来道出了“观者之意”。
从书信、火车再到手机,技术似乎使得分隔两地之人愈发便捷地取得联系,但这些依赖于位置和时间衡量的技术“创造了闻所未闻的机遇,但又立即以相同的方式破坏这些机遇。”[7]杨芳芳在浮光掠影的城市中踽踽而行时,过去恋人的电话让她回忆往昔——与爱情一样,回忆是抓不住的。她最终没有走入那个咖啡馆,如同穆罕默德二世所做的,一旦感受到自己的强烈情感,他就用匕首刺死那个妃子。
杨芳芳不愿意重蹈哥哥缺乏勇气的覆辙,希望避免自己像他那样在站台上错过邂逅,面对“无聊”的“大海”。命运的火车注定她将失去“美好”,因为她同样没有在站台(凯里)“停下”,而是去了海边(广东)。最后,吴娜将结果置换成如果。回到过去,郭阳拥抱了离别时回头的杨芳芳。时空距离的不可克服在这部影片中被媒介赋形,媒介一方面解决了人际交往的间距,一方面又将这种间距显现出来。手机不是直接联通的,它必须有双方的授权,对于拨出者和接话者而言都是需要等待的。在这段时空的间距中,与手机的被动性一样,火车的终点亦被决定。火车的运行不可逆转,此种意义上,它与时间保持一致(这部电影的副导演毕赣在其作品中完成了另一种诗化的表达)。解决空间问题的火车意味着离开,解决时间问题的手机意味着等待。
电影中的现在时是杨芳芳置身于城市中,接到了郭阳的电话,约她在咖啡馆见面。火车驶向“大海”,将永远无法回到时间原点;手机接通思念,将伴随着空间距离而持续膨胀,在持续的未达成中,爱情于此得以显现。“一个人既然爱,就是还没有那样东西;他盼望它。就是盼望他现在拥有它,或者将来拥有它。即钟爱者还没有得到所爱的对象。”[8](P46,58)在语境中,乡土成为了城市的“后花园”和附属品。一方面,它在一些由于城市“从来不用心……鬼头鬼脑……神经极度衰弱……心肠太硬而骨头太软……(城市中的)一幢幢高楼在黑暗中跪了下来,一个个美人儿在谎言中毁容,一座座展览馆,只展出不三不四的东西”(《把城市拉回乡下喂狗》俞心樵)而回望的文化逻辑下被定义。在这种因果关系中,乡土丧失了首先作为生活场所的本然。另一方面,乡土又作为一个与城市“分庭抗礼”的被复制的文化消费品导致了一些传统村落的破坏性“保护”和开发。主体性丧失使乡土不再作为一个文化的他者,选言变成了“城市或‘非城市’”(或者反过来,“乡土或‘非乡土’”),而非“城市或乡土”。本文并非要用批判的方法研究这些现象,而是时间决定了“相对于”的逻辑是很难解决的,简单来说,我们总会先局限于一个城市或乡村——如同那位塞浦路斯国王一样,不爱所有现下的美人,却爱一个“没有生命”的雕塑(完美的相)。与叙事中的雕塑终于获得生命不同,现下的我们不具备完整性。
另一则神话中的俄尔浦斯因为回头,永远失去了妻子(于是拥有爱),他的悲痛(爱)被酒神(麻痹记忆)的狂女(匮乏爱的)撕碎并吃进腹中。于是,《最美的时候遇见你》是以回忆的方式展开的,爱并不以具体的存在者化身,它始终作为匮乏之物的某种假定性存在——一个“如果”。当然,这不是一部在形式上颇值得玩味的电影,其独特在于,如何能展现一个绝大多数私有的爱情故事——在某种意义上,它廓除的不是叙事,而是观众。通过“抛却族群诉求的羁绊,当代中国大陆少数民族女性导演在处理非本民族题材影片时,个体化的女性视角却表现得更为自由和深入。”[9]某种意义上,那些腻歪的对白,只有忘我的情侣才能亲昵出来。
三、爱情
两部影片对于爱情状态的描写截然不同。前者中的爱情是神秘的,其爱的滋味源于一种不甚明了的暗恋;后者抽象出一个空荡的舞台,猜忌和热烈的重逢轮番上演。前者房门半掩的村落中有人离去,有人归来,原有的少数民族生存样态,潜移默化地让人嗅到异质文明的气息——含蓄而低调。对于他者的好奇和外界的期待,暗合了少女暗恋的心意,涌动却没有声张,“达成”作为一种渴望而非现实。这种人与人、人与物或文化与文化的暧昧关系生成了一种诱惑。后者转变为一种更为直接而浅层的情感体验,相应地,一旦其失去了同类“青春片”的“漂亮脸蛋”或错综复杂的叙事策略就更显乏力了。伴随着现代化进程的脚步,原本封闭的社群在诸多因素下与外界发生联系,这种愈发密切的联系带来更为暧昧含混的文化交融。其予之个人的直接体验、身份不再作为一个首要克服的矛盾,爱情体验简化为时空关系;时间的前后脚中,亦不再有一个如此不同的乡土等我回去。
卢曼在谈论爱情时指出,当“爱情作为媒介本身(时)不是情感,而是一种交流符码,人们根据这一符码的规则表达构成、模仿情感,假定他人拥有或否认他人拥有某种情感,如果相应交流得以实现,还能让自身去承担所有的后果。”[10]当我们试图找到那个爱情本身时,语义层面的爱情并不作为爱情本身存在,非但因为有了爱情的“相”爱情才存在,“相”或语义还作为可替换之物,是被爱情的叙事传唤的。爱情本身作为那个不被拥有的“东西”,在最难以捉摸的距离中显现。爱情本身“不可见”。但在艺术创作中,我们始终“鄙夷”那些最直接给予我们情感的冲动之物,反以修辞赋予其形而上的“美感”和“韵律”——爱情作为名词被歌颂。爱情的感知并不首先是语义,即我们予之的任何定义或先验的概念,而是距离的偶然与不可控性,是时空不对等造成的人与人之间的错位。换言之,爱情并不简单显现为语义,而是语义因之传唤的距离。其神秘与诱惑正源于语义的可替换和不确定性,距离之感是第一性的。
前面我们说吴娜第二部作品中的两位青年男女在初恋时的腻歪对白是忽略了观众的。当爱情作为一种语义操纵的媒介时,其矫情伴随着以往爱情叙事的模式,人们揣测其拥有的小小幸福是否与符合着最一般规则的爱情期待视野相匹配。当其作为一个“他的”而非“本我”的方式和嵌套了的存在者出现时,投其所好的叙事学用符合观众期待的方式供其“扮演”,于是作为我的观众看见我想看见的。换言之,只有当这个作品再现的是一个知觉现象时,我们才看见另一个作为主体的他者。由此,钟爱者才无法得到所爱的对象——爱情得以存在。此种意义上,文化亦是如此。迄今为止,吴娜只拍摄了两部影片。这位细腻直接的电影导演,在其爱情故事中潜移默化地投影出别样文化体验。从城乡关系的对立到地域与地域之间对文化符号的消隐,他者的存在从文化的冲突摇摆转变为面对直接时空的错过,其爱情图式又最终化身为都市男女的一般情感。
“爱并不是以美的东西为目的的……其目的在于在美的东西里面生育繁衍。”[8]假如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所说的“爱的生育”是“爱的不朽”,这种不朽之永恒不是某种“确定性”,而是“美的东西”的持续变化之生灭。杏在离开后,她的爷爷问了村里的先生,他们能不能找到杏;先生答,不能,只有当杏遇到了问题,想念家人才会回家。杏怀孕后回家,显然在北方的城市中遇到了麻烦,此刻爷爷已经离世,她可能重新陷入对于过去(文化身份)的追索里去,这意味着除此以外的世界重新处于未达成的状态之中。也就是说,那个还未诞生的新生命孕育着不确定性,当它来到这个永远在未来存在着可能性的世界时,它的身后留下一条线性的足迹,它的下一步则可能踏在不确定(未达成)的任何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