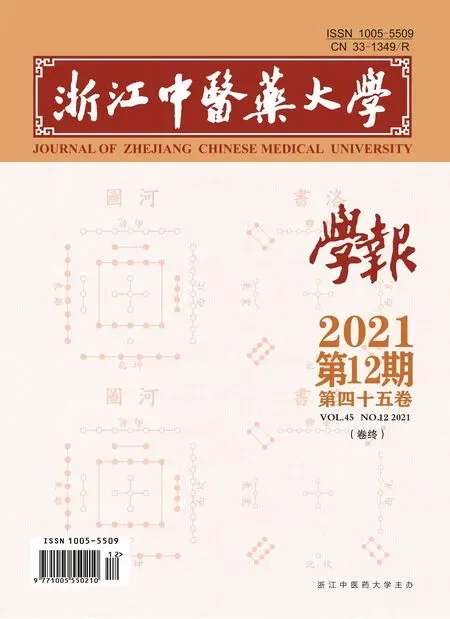黄元御治疗妇科病学术特色探析
2021-11-30何易章勤
何易 章勤
浙江中医药大学附属杭州市中医院 杭州 310007
清代名医黄元御,名玉路,一字坤载,号研农,别号玉揪子。黄氏理必《内经》,法必仲景,药必本经,本着厚古崇经的思想,被后世称为“医门大宗”。《四圣心源》是黄氏晚年的著作,被后世医家誉为“诸书之会极”,是黄氏将自己一生对四圣(黄帝、岐伯、扁鹊、张仲景)及其著作的认识,并结合自己的临床理解,进行高度系统化的一部精华之作。《四圣心源》中对妇人经带胎产诸病的阐发,其“调经养血,扶阳为先;妇科杂病,调之肝脾;胎妊产后,首在补土”的思想及对遣方用药的见解独到,十分值得探究。本文通过分析黄氏遣方用药的特点,总结其治疗妇科病的学术特色,以期为妇科病的中医治疗提供借鉴。
1 辨证遣方特点
1.1 月经病 黄氏认为经水之原,化于己土,脾阳左旋,温升而生营血,所谓中焦受气取汁,变化而赤,是谓血也。有云:“血者,木中之津液也,木性喜达,木气条达,故经脉流行,不至结涩,木气郁陷,发生不遂,则经血凝滞,闭结生焉。”[1]163闭经的病机缘于肝木之郁,而其肝木之陷,咎在于脾,脾土湿陷,抑遏肝木发达之气,因此以桂枝丹皮桃仁汤,即桂枝茯苓丸加丹参、甘草治疗。方中茯苓配伍甘草培土泻湿为主药,茯苓泻水燥土、冲和淡荡,甘草培植中州、养育四旁;桂枝配伍芍药疏木清风,桂枝达肝气之郁,芍药清风木之燥也;佐以丹皮、桃仁、丹参行血破瘀。
崩漏则责之于肝木之陷,肝木主生,木气条达,则经血温升,不至下泄。木气不达,经血陷流,则病崩漏。而导致木陷的原因,亦是由于土湿,水旺土湿,脾阳陷败,不能升发木气,升举经血,于是肝气下郁,而病崩漏。由于黄氏[1]162认为“调经养血之法,首以崇阳为主也”,故其十分推崇仲景温经之法,如以桂枝姜苓汤(甘草、茯苓、桂枝、芍药、干姜、丹皮、首乌)治经漏,以桂枝姜苓牡蛎汤(甘草、茯苓、桂枝、芍药、干姜、丹皮、首乌、牡蛎)治血崩。首乌养血荣筋、息风润燥,敛肝气之疏泄,用之崩漏淋漓俱止。
月经先期与后期,其机制与闭经和崩漏类似。先期者,木气之疏泄,崩漏之机也;后期者,木气之遏郁,闭结之机也,其缘由也总归于脾湿而肝陷,木气郁陷,不得发扬,则经血凝瘀,不能通畅。黄氏[1]165曰:“其通多而塞少者,木气泄之,故先期而至。其塞多而通少者,木不能泄,则后期而至。”故常以桂枝姜苓汤治经水先期,姜苓阿胶汤(桂枝丹皮桃仁汤去桃仁,加首乌、阿胶)治经水后期。
对于痛经的病机,黄氏归于肝气郁塞而刑脾,水土湿寒,乙木抑遏,血脉凝涩不畅,经水不利,木气壅迫,疏泄不畅,克伤脾脏,则成经前腹痛;经后血虚,肝木失荣,枯燥生风,贼伤土气,则成经后腹痛。以苓桂丹参汤(丹皮、甘草、干姜、茯苓、桂枝、丹参)温燥水土治经前腹痛,归地芍药汤(当归、地黄、甘草、桂枝、茯苓、首乌、芍药)温经养血治经后腹痛。
1.2 带下病 带下病在《四圣心源·妇人解》中属于杂病篇,“土湿木郁,生气不达,奇邪淫泆,百病丛生”[1]168。相火下衰,肾水澌寒,经血凝瘀,结于少腹,阻碍阴精上济之路,肾水失藏,故精液淫泆,流而为带,故云“带下者,阴精之不藏也”[1]168。而造成下寒上热的原因,则过不在于心肾,而在于脾胃之湿,有云:“土湿则脾胃不运,阴阳莫交,阳上郁而热生于气,阴下郁而寒生于血。血寒,故凝涩而瘀结也。”[1]169
黄氏治疗带下病的主方为温经汤,即仲景温经汤(人参、甘草、干姜、桂枝、丹皮、当归、阿胶、麦冬、芍药、川芎、茱萸、半夏)加茯苓,温中去湿、清金荣木、活血行瘀。当然,除了治妇人带下外,少腹寒冷,久不受胎,或崩漏下血,或经来过多,或至期不来也可应用。
1.3 妊娠病 对于妊娠病,古往今来医家多从肾论治,但黄氏[1]171认为“胎妊者,土气所长养也。气统于肺,血藏于肝,而气血之根,总原于土。土者,所以滋生气血,培养胎妊之本也”。木升火化、金降水生,则胎气坚完。生长之气衰,则胎堕于初结,收成之力弱,则胎殒于将完,其实皆土气之虚也,所以养胎之要,首在培土,其重视中气的学术思想一以贯之。
妊娠恶阻之证,“胎气一结,虚实易位,大小反常,缘于中气之壅阻也”[1]172,所以胃气上逆,恶心呕吐,食不能下,治宜培土泻湿、行郁理气,方拟豆蔻苓砂汤(白蔻、杏仁、甘草、砂仁、芍药、丹皮、茯苓、橘皮)。
“命门阳败,肾水澌寒,侮土灭火,不生肝木,木气郁陷,而贼脾土,此胎孕堕伤之原也。”[1]174黄氏对腹痛之胎动不安者,责之木陷而克土,拟姜桂苓参汤加砂仁、芍药治疗。方中茯苓、甘草培土泻湿,人参补中培土,干姜燥湿温中,桂枝、芍药清风疏木,丹皮行瘀泄热,砂仁行气安胎。
黄氏认为,胎漏或由于肝脾阳弱,不能行血,瘀血积聚而阻碍经络,此为离经之血,于是下漏,方用桂枝茯苓汤,即仲景桂枝茯苓丸加甘草培植中州;或由于肝脾下陷,肝气贼脾,而致下血伴腹痛,治宜疏木达郁而润风燥,其漏血腹痛自止,方用桂枝地黄阿胶汤(甘草、地黄、阿胶、当归、桂枝、芍药、茯苓、丹皮)。
1.4 产后病 黄氏[1]175有云:“产后血虚气惫,诸病丛生。”《金匮要略·妇人产后病脉证治第二十一》言:“新产妇人有三病,一者病痉,二者病郁冒,三者大便难。”对于产后三病,黄氏[1]176认为“胎气生长,盗泄肝脾,土虚木贼,为诸病之本”。血弱经虚,表疏汗泄,又感风寒,则病痉;气损阳亏,凝郁内陷,群阴闭束,则病冒;津枯肠燥,阴凝气结,关窍闭涩,则便难。拟桂枝栝蒌首乌汤(桂枝、芍药、栝蒌根、首乌、生姜、大枣、甘草)治柔痉,发热汗出者;葛根首乌汤(桂枝、芍药、甘草、葛根、麻黄、首乌、生姜、大枣)治刚痉,发热无汗者;桂枝茯苓人参汤(人参、甘草、茯苓、桂枝、生姜、大枣)治阳虚郁冒;苁蓉杏仁汤(甘草、杏仁、白蜜、肉苁蓉)治津亏木燥,大便艰难。总以培土疏木为本,或加以养血润燥,或加以解表疏风,或加以润肠通便。
2 临证用药特色
2.1 注重培土疏木 黄氏[1]52言:“胃主降浊,脾主升清,湿则中气不运,升降反作,清阳下陷,浊阴上逆则人之衰老病死,莫不由此,以故医家之药,首在中气。”因此,治疗上黄氏时刻强调执中培土,升脾陷而降胃逆。脾胃之升降,亦即调达阴阳之升降,推运肝心肺肾、气血精神之轮转。
《四圣心源·妇人解》共20方,而20方均用甘草,可见黄氏对甘草的重视,称其为“交媾精神之妙药,调济气血之灵丹”[2]9。甘草性甘、平,入脾胃心肺经,补益脾气,调和诸药,“体具五德,辅以血药,则左行己土而入肝木,佐以气药,则右行戊土而入肺金……脾胃者,精神气血之中皇,凡调剂气血,交媾精神,非脾胃不能,非甘草不可也”[2]11。本篇14方用到茯苓,茯苓性甘、淡、平,入脾心肾经,泻水燥土,冲和淡荡,黄氏[2]92称其为“除汗下之烦躁,止水饮之燥渴,淋癃泄痢之神品,崩漏遗带之妙药”。
妇人病除了归因于脾土湿困外,还责之肝木郁陷,黄氏喜用桂枝达肝气之郁,加芍药清风木之燥。《四圣心源·妇人解》中桂枝配伍芍药共12方,单用桂枝17方,单用芍药14方。桂枝入肝家而行血分,走经络而达营郁,善解风邪,最调木气,得之脏气条达,经血流畅。“大抵杂证百出,非缘肺胃之逆,则因肝脾之陷,桂枝既宜于逆,又宜于陷,左之右之,无不宜之,良功莫悉,殊效难详。凡润肝养血之药,一得桂枝,化阴滞而为阳和,滋培生气,畅遂荣华,非群药所能及也。”[2]62芍药入肝家而清风,走胆腑而泻热,厥阴以风木之气,生意不遂,积郁怒发,而生风燥,芍药酸寒入肝,专清风燥而敛疏泄,故善治厥阴木郁风动之病。
2.2 兼以行血化瘀 《长沙药解》云:“血者,木之精液,而魂之体魄也。风静血调,枝干荣滋,则木达而魂安。温气亏乏,根本失养,郁怒而生风燥,精液损耗,本既摇落,体魄伤毁,魂亦飘扬,此肝病所由来也。于是肢寒脉细,腹痛里急,便艰尿涩,经闭血脱……”[2]44木性善达,水土寒湿,生气不达,是以血瘀。
《四圣心源·妇人解》中14方用丹皮,丹皮辛凉疏利,善化凝血而破宿癥,泻郁热而清风燥,善治血滞经闭、痛经等。此外,丹参行血破瘀、通经止痛,“癥瘕崩漏兼医,调经安胎,磨坚破滞”[2]127。当归养血滋肝、清风润木,“调产后而保胎前,温经最效”[2]43,《四圣心源·妇人解》中4方用到当归、丹参。桃仁通经而行瘀涩,破血而化癥瘕;阿胶养阴荣木,补血滋肝,止胞胎之阻疼,收经脉之陷漏,最清厥阴之风燥,善调乙木之疏泄,亦各有3方用到。
2.3 善用温阳之品 黄氏独创了中气轮转思想,而使中气轮转的方法,则是“泄水补火,扶阳抑阴”[1]52。其“补火”之“火”和“扶阳”之“阳”皆指脾阳,故“补火扶阳”之法,指的是温中燥土。“扶阳抑阴”为黄氏的另一主要学术观点,太阴以湿土主令,阳明从燥金化气,从气焉能敌过主令之气,是以太阴常旺,阳明常衰,故“扶阳抑阴”,为一定之法[3]。
温补脾阳以干姜配甘草为主,其配伍源于仲景经方,理中汤、肾着汤、半夏泻心汤、柴胡桂枝干姜汤诸方皆以干姜配甘草为扶脾阳的主要药对。干姜温中以回脾胃之阳,燥湿温中,行郁降浊,补益火土,暖脾胃而温手足;甘草培植中州,养育四旁。去寒湿则以桂枝配茯苓为主,《四圣心源·妇人解》篇中有13方以苓桂配伍,其配伍亦源于仲景,仲景治疗痰饮的苓桂术甘汤用桂枝配茯苓通阳化痰饮,桂枝茯苓丸也以苓桂配伍,通阳活血为先导。黄氏认为脾不升清源于脾阳不升,脾阳虚衰则寒湿中阻,故以茯苓泻湿,桂枝清风而疏木为主。
3 临床拓展应用
笔者将黄氏理论应用于临床诊疗中,发现从“中气”论治,使用桂枝姜苓汤治疗崩漏及月经先期疗效显著,不论二七少女或是七七妇人经水淋漓不尽、月事提前而至往往可取得不错的疗效。笔者曾以豆蔻苓砂汤治疗妊娠恶阻一例,投以豆蔻苓砂汤少量频服,胃纳及精神明显改善。其余方剂,尚待进一步于临床实践中验证。
3.1 病案一 蔡某, 女,26岁,2020年4月20日初诊。主诉:月经先期半年。生育史:0-0-0-0。月经史:初潮13岁,周期23~25 d,近半年来经讯一月两行,末次月经2020年4月10日,量中,6 d净;前次月经2020年3月20日,量少,8 d净。刻下:烦躁易怒,夜寐欠安,二便尚调,舌淡红,苔薄,脉弦细。观前医曾从血热论治,效鲜,思及黄氏[1]165“其通多而塞少者,木气泄之,故先期而至”的理论,辨证为脾虚肝郁,改投以桂枝姜苓汤治之。 处方:丹皮10 g,甘草6 g,茯苓10 g,制首乌10 g,干姜6 g,桂枝10 g,炒白芍10 g,柏子仁10 g,绿梅花5 g。共7剂,一日一剂,水煎服。
4月29日二诊。月经未至,烦躁好转,舌脉同前。处方:丹皮10 g,甘草6 g,茯苓10 g,制首乌10 g,干姜6 g,桂枝10 g,炒白芍10 g,路路通10 g。共7剂,一日一剂,水煎服。
5月7日三诊。末次月经2020年5月6日,量中,色鲜,夜寐改善。 处方:丹皮10 g,甘草6 g,茯苓10 g,制首乌10 g,干姜10 g,桂枝10 g,炒白芍10 g,旱莲草10 g。共7剂,一日一剂,水煎服。
如此加减治疗2个月,月经周期基本规则。
按语:患者木气郁陷,肝失疏泄,而致经血陷流,先期而至,烦躁易怒。究其木陷之由,则因于土湿,土湿之由,原于水寒。水土温和,则肝木发荣,木静而风恬;水土寒湿,不能生长木气,则木郁而风生。故以桂枝姜苓汤培土疏木,其中甘草、茯苓培土泻水,干姜燥湿补火。所谓“肝木左郁而血病”,故以桂枝达木扶阳,芍药清燥除烦,丹皮泻热化瘀,首乌敛肝养血,绿梅花疏肝解郁,柏子仁养心安神。全方共奏补中暖脾、疏肝调经之效。二诊时患者烦躁好转,去柏子仁、绿梅花,加路路通祛湿通络;三诊时月经已至,去路路通,投旱莲草加强滋补肝肾、凉血止血之功。经两月调治,经渐如期。
3.2 病案二 陈某,女,31岁,2020年7月8日初诊。 主诉:停经52 d,恶心呕吐1周。患者近1周恶心呕吐明显,食入即吐,呕吐清涎或胃内容物,伴胃脘不适,倦怠乏力,小便短少,舌红苔薄腻,脉滑略弦。辨证为脾虚湿盛、胃失和降,治以豆蔻苓砂汤加减。处方:白豆蔻3 g,杏仁6 g,甘草3 g,砂仁3 g,炒白芍10 g,茯苓10 g,陈皮5 g,姜半夏6 g。 共7剂,少量频服。
患者服上药3剂后恶心呕吐明显缓解,胃纳改善,精神转振,嘱其少食多餐,进食易消化食物。
按语:患者胎孕初结,升降不利,中气郁阻,脾土湿困,胃土不降,则胃气上逆而恶心呕吐、胃脘不适;脾虚气血化生不足,则倦怠乏力。故以豆蔻苓砂汤升清降浊,其中甘草、茯苓培土渗湿,豆蔻、砂仁化湿行气,芍药敛阴柔肝,杏仁降气开痹,陈皮、半夏降逆和胃。诸药合用,以达开郁降浊、和胃止呕之效。
4 结语
黄元御《四圣心源》一书中自拟方颇多,审其源流,皆宗四圣之旨,用药简洁,配伍精当。黄氏盛壮之年亲遭苦寒之祸,故对滥用寒凉之痹深恶痛绝,临床多以阳衰土湿、水寒木郁立论,而其基点,无不系于中气之不调。
“调经养血,扶阳为先”[1]162,黄氏认为调血养血当以崇阳为要,强调阳气在治疗月经病中的重要地位,崇土扶阳一直是黄元御核心学术思想之一[4]。“妇人之病,多在肝脾两经”[1]168,黄氏之学,最重脾胃升降,而妇人之病与肝木关系最近,故又重升达脾阳,认为脾阳健运则木达血畅[5]。“养胎之要,首在培土”[1]171,黄氏独创中气升降理论,四象之推迁,皆中气之转运也,土中阳旺、升降有序则胎气畅茂。综上所述,黄氏独特的学术思想,具有较高的临床指导价值,值得进一步学习,并于临床中深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