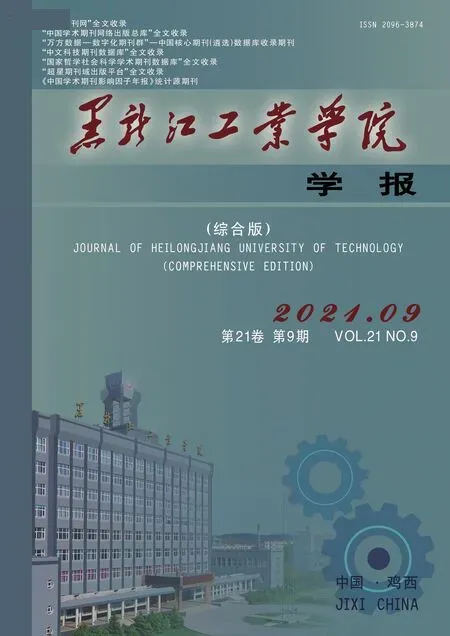论胡塞尼小说的叙事结构与风格
——以《群山回唱》为例
2021-11-29王巧
王 巧
(黄山学院,安徽 黄山 245041)
卡勒德·胡塞尼,著名美籍阿富汗裔作家,1999年,该作家开始从事创作行业,2003年,发布第一部小说《追风筝的人》;2007年,发布第二部作品《灿烂千阳》,这部作品是他走向成熟作家的标志;2009年,胡塞尼开始创作第三部作品《群山回唱》,2013年5月21日,《群山回唱》在美国首发,《群山回唱》荣获美国亚马逊书店2013年上半年最佳图书、美国独立书店排行第一、美国国家公共电台(NPR)夏季最佳图书等多项荣誉,被《纽约时报》评为“胡塞尼在感情上最扣人心弦的小说”。胡塞尼的这三部作品主题都以阿富汗时代背景为主线展开,鲜明地突出了战争与人性,国内外学者多聚焦于小说的人物情感、文化认同及身份意识,鲜有研究者从叙事艺术角度出发研究这三部作品。《群山回唱》作为胡塞尼的晚期代表小说,其叙事艺术风格较为成熟,以《群山回唱》为例,探究胡塞尼小说的叙事艺术具有可行性。
《群山回唱》主要讲述了因为战争和贫穷,阿卜杜拉和妹妹帕丽经历了六十年的骨肉分离,在六十年漫长岁月内发生的一系列事件[1]。胡塞尼通过巧妙的叙事手法,将这一系列故事串联起来进行讲述,他的创作特色之一在于他的叙事艺术表现,人们对他的作品留下深刻印象。鉴于此,从叙事视角、叙事结构和叙事独特风格三方面进行叙事艺术探究,深入了解胡塞尼小说的叙事艺术。
一、《群山回唱》叙事视角概述
叙事视角指叙述者或人物与叙述文中的事件相对应的位置或状态,即叙述者或人物从什么角度观察故事[2]。在《群山回唱》中,作者通过内外两种聚焦视角进行叙述,叙事视角相互穿插进行。
1.内聚焦视角
内聚焦视角,即事件都严格按照一个或几个人物的感受和意识来呈现。在《群山回唱》中,内聚焦视角体现在第一人称和第三人称的使用上。第一人称的使用,虽然第一、四、八、九章都是以第一人称来讲述,但是,讲述方式不同,所交代内容角度不同:其一,第一章是故事中的故事,作品开篇写到“那好吧。你们想听故事,我就给你们讲个故事”,通过“我”给阿卜杜拉和帕丽讲故事,但“我”不是故事的主人公,这里的“我”没有明显的形象特征,降低了讲述者的存在感,突出所讲故事内容;其二,第四章,胡塞尼同样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叙述,但这里的“我”是讲述的主人公纳比自己,通过第一人称讲述自己的一生经历,让读者不自觉地跟随他的脚步进入故事当中;其三,只有第八九章,是整篇中的真正第一人称叙述,讲述自己,主人公是“我”。在不同情况下,第一人称的内聚焦的叙事方式,可以容易并且充分展现焦点人物的内心世界,这样的叙述更能增强作品的真实性。
第三人称方面,《群山回唱》中的第三人称并非以往大众认知的“他/她”,而是定型某一个特定人物,以此特定人物为中心,但又不是以他们自己的口吻陈述的叙事视角。以《群山回唱》的第二章为例,第二章以阿卜杜拉为叙述者中心,“阿卜杜拉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一路追赶,直到那片羽毛落入巨石的背阴……”,但第三章转换到帕尔瓦娜,讲述帕尔瓦娜的生活经历,直接进行了叙事者转换。作品中的叙事没有过于生硬,而是自然地过渡到另外一个事件中,全篇的故事发展掌握在叙述者的转换,更具有灵活性。
综上所述,在内聚焦视角下,一方面,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让读者随着故事的发展内心产生变化,读者会跟随不同的聚焦人物的视角,深入故事;另一方面,这种不局限于“他/她”的第三人称讲述,使视野更加自由,可以从多角度观察每个人物,也可以灵活巧妙的移动叙述者,这种叙事视角细分来说,也叫不定式内聚焦型。
2.外聚焦视角
韦恩·布斯指出“小说家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况变换视点”[3]。胡塞尼作为文学的创新者,不拘泥于内聚焦的叙事方式,他在《群山回唱》中每章不规律的注入外聚焦视角模式,使内外叙事视角相互穿插。外聚焦视角下,叙述者严格客观地从外部呈现每一件事,只提供人物的行动、外表及客观环境,而不告诉人物的动机、目的、思维和情感。例如,《群山回唱》的第二章开篇,“父亲以前从没打过阿卜杜拉……父亲接着又打他……”只是表现出了外在环境,只能知道父亲第一次打了阿卜杜拉,但读者并不知道父亲打人行为的原因,这些疑惑只有萨布尔(父亲)知道,叙述者无法得知,听众更无法知晓。胡塞尼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关闭,叙述者只能站在外围进行观察、解读自己所见,但又不能进行大胆揣摩和猜测,这样的开端让读者产生好奇,会去追寻真正的原因,而父亲第一次打了阿卜杜拉的原因,本章末进行解释说明。由此可见,在父亲打阿卜杜拉的片段中,虽然是以阿卜杜拉为中心进行讲述,但没有将阿卜杜拉的委屈和不解表现出来,也没有发出质问,只是简单地表面化讲到“震惊的泪水”,没有进行阿卜杜拉震惊的内心活动描写。此处外聚焦视角的运用,一方面,形成对事实的朦胧神秘感,读者带着好奇不解进行追寻事实真相,另一方面,外聚焦视角的运用,将叙事者和故事保持距离,使叙事者站在一个旁观的角度展现故事的场景,不会将个人情感带入事件的发展,进一步增强了作品的真实性。
二、《群山回唱》叙事结构探析
胡塞尼在叙事结构上,使用倒叙、预叙和插叙以及闪回的叙述结构,其中,倒叙使故事更加完整,预叙预示了故事的结局,插叙使故事情节发展更加清晰,闪回则补充了文中需要解释说明的情节。不同的叙事结构形成一部完整的故事,体现出胡塞尼的叙事艺术魅力。
1.倒叙预叙变换文本空间
叙事时间是个伪时间,因为从读者的经验来说,它是唯独靠阅读才能重新变换为时间的一个文本空间。通过阅读,读者重新理清故事时间,而通过倒叙,作者则帮助读者梳理了事件所发生的时间[4]。作者在第二章埋下伏笔,设置悬念,通过倒叙手法使用,使故事细节得到证实。《群山回唱》整部作品讲述的是从1952年到2010年期间的故事发展,虽然,中间时序倒换,但是,整体讲述了近六十年间的故事,只有第三、六章采用倒叙。《群山回唱》的第二章讲述1952年所发生的事件,第三章倒叙回到1949年,通过第三章的倒叙,让读者知道了帕尔瓦娜会成为阿卜杜拉继母的原因。这部分通过倒叙的运用,解开了第二章故事的谜团,也使作品的事件发展前后串联起来。《群山回唱》第五章讲述2003年伊德里斯和铁木尔回到喀布尔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到了第六章回到1974年讲述帕丽与妮拉之间的事,以及帕丽到了巴黎之后的生活状态,通过倒叙将一条时间轴的事件得到补充。
除此之外,预叙也是胡塞尼小说中的常用叙事结构,例如,《追风筝的人》运用的梦境预叙,《灿烂千阳》中运用的语言预叙,而《群山回唱》中则创新性的运用了寓言预叙的方式,这里的寓言是萨布尔精心编造的寓言,暗示萨布尔卖女儿的决定,也预示了以后的故事发展。
2.插叙补叙紧凑文本结构
根据插叙内容在文中所起的作用分裂,插叙分为映衬插叙、对比插叙以及解释插叙。映衬插叙在叙述的过程中,插入涉及到另外人和事,对表现主要人物起铺垫映衬作用;对比插叙是追忆过去有关的人物事件;解释插叙是对事件发展,人物行动的某些原因做出解释。胡塞尼通过不同插叙手法的应用,将故事叙述更加完整,紧凑了整体文本结构。
《群山回唱》中在许多情节使用了插叙,第二章开端,讲述帕尔瓦娜照顾马苏玛的情节时,插入帕尔瓦娜、马苏玛和萨布尔儿时生活的回忆,此时的插叙是对比插叙以及映衬插叙,通过对比萨布尔年少与成年后的他,以及年少貌美的马苏玛与后来瘫痪的她的强烈对比,给读者强烈的落差感[5]。而通过追忆过去,与现在的生活进行强烈对比,也进一步映衬和表现了人物性格。第八章,通过插叙马科斯回忆离开岛上之前的一系列过程,为马科斯逃离家乡最后成为一名医生作出解释,这里的插叙为解释插叙,是对故事发展的解释说明,使故事情节发展更加清晰、紧凑。
3.外部闪回补充故事脉络
闪回即回头叙述先前发生的事情,其与插叙倒叙具有相似性,但又不同于插叙和倒叙,闪回是逆时序的一种叙事方式,出现的更为突然,具有较强的震撼效果。叙事学根据闪回与开端时间的关系,将闪回分为外部闪回、内部闪回和混合闪回。外部闪回在叙述时,讲述故事开端时间之前的事件,内部闪回是讲述故事开端时间之后,混合闪回是对内部和外部闪回的结合。《群山回唱》多用外部闪回补充故事脉络。例如,《群山回唱》第五章提到的相框,相框内是一张黑白照,左下角似有烧过的痕迹,第八章通过马科斯回忆的外部闪回,文中对相框进行了解释,相框是被一个意大利女孩点燃过,因此留下痕迹,这个细微的事件,胡塞尼没有将其忽略或者一带而过,而是将其描写入微,通过外部闪回让作品的故事情节更加完整,让读者随着外部闪回方式探寻到真相,真相的残酷又让读者体验了一种特殊的震撼[6]。另外,这种外部闪回使作品的故事发展更加紧凑,能够衔接前文的故事,使作品中的故事情节发展更具有真实性;外部闪回的使用让作品增加了开始的神秘,结尾的震撼。
三、胡塞尼小说的叙事风格
1.寓言故事开篇,预示情节发展
“在文学的寓言叙事中,寓言自身带有的隐喻和象征的功能,使它能够自由地穿梭在写实与虚构之间”[7]。通过寓言叙事可以丰富文本所隐喻的真实,胡塞尼在《群山回唱》中,通过预叙的文本结构,注入寓言叙事手法,以寓言故事为开端,这种创作风格具有创新性,也让寓言叙事发挥到作用,寓言故事的每段发生,暗含着下文所述之事的发展。
《群山回唱》在第一章中,是关于萨布尔在出发前一晚给阿卜杜拉和帕丽讲的寓言故事,萨布尔讲述了魔王与巴巴·阿尤布的故事,寓言中,阿尤布为了全村人的生命献出小儿子的举措,暗示着萨布尔即将做出的决定,他也喜爱帕丽,可是贫穷的压迫,让他没有选择,只有放弃一个孩子,才能保住一家人温饱,寓言中,萨布尔提到“不得不砍下一根指头,这样才能把手保住”,表达萨布尔内心的煎熬、犹豫和痛苦之情。而寓言故事后半部分阿尤布看望小儿子的情节,再次暗示萨布尔决定放弃帕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妮拉能够给予帕丽更好的生活。后文中写到,妮拉的住所金碧辉煌,妮拉有更好的条件提供给帕丽,给帕丽选择更好的生活是萨布尔的一丝安慰。由此可见,在第一章的寓言故事里的几次暗示,都为下文故事发展提供了线索,也为下文故事做好了开端,悲剧性的寓言故事在开端营造出悲剧氛围,为下文故事做好悲剧的铺垫,而寓言性的叙事风格,也为小说创作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8]。
2.人物关联性强,搭建叙事桥梁
在胡塞尼的小说创作中,人物的关联性是其叙事风格的一大亮点,也体现了其“看似随意、实则相关”的创作风格[9]。胡塞尼将每个看似不重要的人物安排在故事当中,等读者追随到故事结局,才会发现,出现的每个人物都是不可缺少的部分。小说中,人物关系错综复杂,涉及多个方面,因此产生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线索,这些不同的空间也反映了多样的社会关系。
《群山回唱》中,人物之间的关系主要体现了社会空间的第一种关系:生物性生产关系,即夫妻、性别和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群山回唱》中出现的每个人物都是故事发展的关键,看似无意的提及,实则是故事发展的一个部分,故事中出现二十多个人物,其中有十六个人物是贯穿整部作品的重要因素,通过每一章的发展,呈现了不一样的角色,而每出现一个人物便有一段故事,出现的人物之间又相互关联,最终都围绕着阿卜杜拉和帕丽这两个中心人物。例如,由第一章父子三人登场,到第二章引出帕尔瓦娜是阿卜杜拉的继母,在此章出现的新人物是马苏玛、瓦赫达提夫妇及纳比;第四章以纳比口吻讲述了帕丽被卖到瓦赫达提家里的过程及后来生活,在此章出现的新人物是马科斯、铁木尔和伊德里斯。十六个人物之间关系密切,但都是为阿卜杜拉和妹妹帕丽做铺陈,众多人物参与到他们失散的六十多年的时光里。
在构建人物的关联性上时,胡塞尼通过简单的某个地点或者事件将故事的人物相互关联,搭建人物相互关联的桥梁。例如,《群山回唱》中瓦赫达提夫妇是帕丽的养父母;马科斯是阿卜杜拉与帕丽六十多年后重聚的关键人物;伊德里斯和铁木尔认识阿卜杜拉,是根据他们是阿卜杜拉饭馆的熟客,这里的饭馆为他们关联的桥梁;吴拉姆和阿德尔因足球而相识,一场足球是他们之间相识的桥梁;吴拉姆的父亲与阿卜杜拉是同父异母兄弟,胡塞尼将每个人串联起来,在串联的过程中也将形成每段故事。
3.创伤叙事风格,凸显人文精神
学者刘喜波曾指出,胡塞尼小说具有社会创伤叙事的特点[10]。通过探析《群山回唱》的叙事视角及叙事结构,也能够透析出其创伤叙事的叙事风格。一方面,作品中的部分倒叙和插叙是叙述主体“对创伤记忆的回访”,通过逆时空叙事里对记忆的追溯和解释说明,营造悲伤氛围,将读者代入故事中,不仅体现了胡塞尼小说创作的创伤叙事风格,更突出了小说的人文主题,达到胡塞尼“立志拂去蒙在阿富汗普通民众面孔的尘灰,将背后灵魂的悸动展示给世人”的创作目标。另一方面,在美国文学作品中,“族裔文学”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胡塞尼自身的双重文化身份使其小说的叙事风格同样具有“追求身份认同”的族裔文化,通过阿富汗战争背景下对身份的追寻以及个人的成长,将成长、战争、家庭伦理等人性主题通过创伤叙事娓娓道来,是族裔文学的代表,更为美国文学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结语
胡塞尼的叙事艺术中,无论在内外视角的转换上,还是倒叙、插叙的相结合,都让作品增加了不一样的色彩,尤其在《群山回唱》中,再次加入新颖的寓言叙事手法,体现其创新性的叙事风格。胡塞尼勇于揭露“家国创伤”的叙事风格,更是凸显了强烈的人文精神,具有一定程度的“人性叙事”特点。综上所述,文中通过探析胡塞尼小说的叙事艺术,能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作品的主题和意义,其创作手法也对其他小说创作者提供了不同程度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