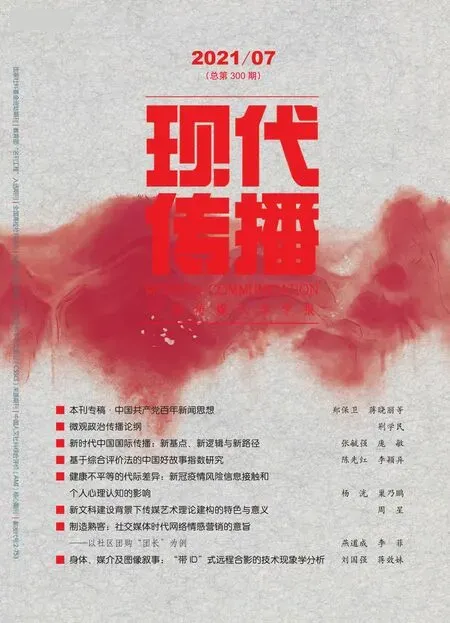华中地区新闻教育之发端:艾玮生与华中大学新闻组
2021-11-29张继木
■ 张继木
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的新闻教育机构已逾30余所。然而,就地域而言,这些机构的分布极不均衡,“大都集中在上海、北平两个地方。南京、济南、广州、厦门,只有一点点缀而已;至于香港、桂林、重庆,那还是抗战以后东南人文移向西南的局势所造成。”①抗战胜利后,这个面貌并未改观。不仅如此,而且就总量而言,已不可与二三十年代同日而语。②不过,这一时期,某些原本没有新闻教育的地区开始寻求突破。武昌的华中大学便随着艾玮生的到来而成立新闻组,结束了华中地区长期无新闻教育的历史。③
一、华中大学的学科拓展逻辑
华中大学是一所教会大学,1924年由武昌文华大学、博雅书院大学部及汉口博学书院大学部组建而成,其后又将长沙的雅礼大学、岳阳的湖滨大学纳入其内。事实上,早在商议筹建华中大学的“汉口会议”(1922)上,与会代表就表达了创办新闻教育的愿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该增加一个研究生院、一个农学院、一个工学院和一个新闻学院。”④循着这个思路,抗战期间,华中大学制定了一个战后学科提升与拓展的十年计划。这份计划书雄心勃勃:“文学院之经济商业系,应于最短期间,扩充为商学院”“教育学院之音乐组,宜速扩充成系”“教育学之研究宜成一系,师资培养,另为一系”“理学院之数学组,宜扩充成系”⑤。但同时亦反对冒进,如改历史社会系为历史系,即为了稳妥起见:
现时文学院之历史社会系,偏重历史,其社会学各学程,多未遑及。因吾国社会学有系统之研究,尚在初期,而社会学为富有地方性之学科,借镜于欧美各国社会研究之材料,本无不可,然取他人之课本,以教中国之学生,未尝见其得计。故本校社会学之研究,宜先设社会学研究讲座,从事于社会学各部门之探讨,汇集资料,为将来教学之张本。盖学问之道,未可躐等也。⑥
上述计划未有回应“汉口会议”上创办新闻教育的愿景,这与调整“历史社会系”是一个道理,背后均是稳健的学科拓展逻辑在起作用。那个时候,新闻学在中国的处境并不比社会学强多少:首先,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新闻教育机构大多因经费问题而停办⑦,就连燕京大学新闻系也一度停办。其次,师资严重不足,对此,蒋荫恩不无感慨地写道:“大学新闻学系师资的缺乏、情形相当严重。普通科目如《新闻学概论》《新闻采访与编辑》《报业史》等,要聘请适合的教授人才,已经不易;若《新闻法令》《广告与发行》《印刷研究》等一类比较专门科目的教员,简直更难。”⑧最后,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对新设专业、学科的管理甚严。如1946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否决了金陵大学将“电化教育专修科”改为“电影播音系”的申请。⑨
然而,亦应看到华中大学在发展应用学科方面的初心并未改变,这自其急切地想将“经济商业系”扩充为“商学院”的举动可见一斑。也就是说,一旦条件成熟,发展新闻学等应用学科便具有某种必然性。事实上,彼时学界呼吁发展新闻教育的理由与华中大学升格“经济商业系”的动机相当一致,均指向国家与社会之急需,如1948年武道(M.Votaw)在陈述中国急需新闻教育时写道:
现在不仅是报纸及其他出版物需要受过大学教育与训练的新闻从业人员,而且,设有新闻系的大学校里也需要受过良好训练,有资格的教师。如果中国要使本国的情形及本国的问题与发展,让国内外大多数人士有所认识,那么还得要大批的男女学生到大学里去受新闻训练。⑩
而华中大学升格“经济商业系”正是考虑到社会的急切需求:“一以供应武汉区工商业各部门急需之专门人才。”由此可以想见,当发展新闻教育的呼声传导到华中大学时,若能适时出现一位新闻专业教师,华中地区的新闻教育史将由此改写。
二、艾玮生与华中大学新闻组的成立
华中大学的新闻教育愿景因艾玮生的到来而变成现实。艾玮生其人,1909年生于河南禹州,1934年毕业于华中大学历史社会学系,1946年受信义会资助,赴美国密苏里大学攻读新闻学硕士学位,1948年学成归国,居于武昌胭脂坪,从事信义会的新闻出版工作,1949年上半年开始在华中大学任兼职教师,讲授“新闻学”。对艾玮生的兼职情况,《华中通讯》的报道称:“据悉,新闻学为华中大学新设课程,由艾玮生先生讲授。艾先生专习新闻学,经验甚富,同学选修是种课程者,皆甚感兴趣云。”实际上,艾玮生不只任课,还指导新闻班的同学创建了“华中大学新闻学会”(任学会顾问),邀请业界人士给学生做学术讲座,指导学生出版实习刊物《新报》,等等。在此期间,艾玮生的一系列推动新闻教育的举措在校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华中通讯》对此报道甚详,而且赞誉有加:
兹悉该班(新闻学班)同学复组织新闻学会,于(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二日下午七时在C教室举行成立大会,推选颜瑾瑜同学为该会主席。并请汉口《大刚报》刘人熙社长,作首次学术讲演,题为:《民营报纸》。嗣后该会干事会努力推行工作,并于三月二十六日往汉口参观《武汉日报》,实地学习。又于四月十一日请《新湖北日报》廖行健社长讲:《新闻学漫谈》。四月十八日请武汉老报人蔡寄鸥先生讲:《武汉报纸沿革》。先后三次学术演讲时,除该会同学听讲外,尚有爱好“新闻(学)”各师长及同学参加,每次均告满座,盛况空前,可见母校师生爱好“新闻学”之风气甚盛。
《大刚报》不仅报道了其社长刘人熙在华中大学新闻学会的演讲梗概:“刘氏就民营报纸之定义,报纸态度与立场及新闻写作方法,阐述甚详。讲后并提出有关问题,由刘氏一一解答,直至九时始散会云。”而且还报道了华中大学“新闻学”的开课盛况:“学校(华中大学)本期开了一门‘新闻学’课程,除了许多同学选修外,旁听生之多,为其他任何课程所不及。”相对《大刚报》在报道其社长演讲时的简略与含蓄,《新湖北日报》则不仅详尽地报道了其社长演讲的具体内容(有数百字之多),而且颇富感情地描摹了现场的热烈气氛:“参加聆听同学达百余人,除教室内满座外,室外窗口、走廊亦为‘不得门而入’之同学拥挤得水泄不通。”“廖氏以现实新闻材料作活的比喻,讲来活泼生动,使得聆听同学捧腹不止。”
从这些反响中,可以看出艾玮生在华中大学推动新闻教育的努力已初见成效。根据华中大学的学科拓展逻辑——先设讲座以汇集资料,等积累到一定时候再设立学科组织,基本可以预见,华中大学成立新闻组(系)的时间已为时不远。在迈向新闻(系)组的进程中,艾玮生由兼职教师转为专职教师是关键的一环。在艾玮生的推动下,1950年5月9日韦卓民给远在香港的贝约翰(John L.Benson,信义会负责人)写信,介绍艾玮生在华中大学的工作状况,并请求信义会支持其转任专职教师:
艾玮生先生,我们华中大学的一员(兼职教师),已经和我谈过话了。正是在他的建议下,我写信向你并通过你向信义会报告他在我们这里的工作情况。
艾先生是我们(华中大学)的毕业生、一名虔诚的基督徒(a very faithful christian)。自他从美国学成归国并担任我校的兼职老师以来,在许多方面给予我们很大的帮助。(自其任兼职教师以来)一直担任“新闻学”和“社会学”这两门选修课的教学工作,其中“新闻学”班有30名学生,“社会学”有16名学生。他除了教学,还负责照料校内信义会(Lutheran)的学生,他们有28名(这真是个吉利的数字)。他自担任华中大学校友会主席(Chairman)以来,也参与编辑《华中通讯》(中文版)。这些工作,再加上他在校内的信义会团契活动,着实令他十分忙碌。
我们一直希望同情我们教育方针与事业的信义会能够给予华中大学更大的支持。首先,希望你能继续支持艾玮生先生留在华中大学,并给他专职教师的身份。不论你将为他在华中大学(的工作)提供何种资助,但均应向华中大学会计处交付(should be paid to the Treasurer of Huachung University),我们再征得你的同意(concurrence)付给他相应的薪水。如果他须得你们差会(信义会)派遣,他的派遣期限至少一次一年。我们的财政年度(fiscal year)为8月1日到7月31日。有任何消息,请尽早告知,这样我好向6月下旬即将召开的校董会(Board of directors)报告。
6月1日贝约翰即函复韦卓民,不仅同意了将艾玮生转为专职教师的请求,而且还表示继续给予艾玮生每年1000美元的资助,并承诺将这笔款项汇入华中大学会计处。韦卓民对此甚为满意,艾玮生闻讯后也极为高兴。于是,1950年下半年,艾玮生由兼职教师转为专职教师,所定职级为副教授,随即华中大学“新闻组”成立。这些情况可见之于华中大学的教学档案:在“1950—1951学年度华中大学各院系课程调查表”中,“新闻组”便同文学院的中文、历史、外文各系一样,并列为文学院下属的教学组织。而据“1950—1951学年度私立武昌华中大学新闻学组教学计划”之记载,艾玮生的“职位”一栏填为“副教授”。此外,在《华中大学》一书的“附录”中,新闻组(原书写作“新闻学”)及其教师艾玮生亦被列入“1950—1951(学)年度华中大学机构人员一览表”。
不难看出,华中大学新闻组的成立,背后除了华中大学自身的学科拓展逻辑和艾玮生的个人努力,信义会的作用也不容小觑。尽管信义会起初并未参与创办华中大学,即便是信义大学停办,也只是将学生送来,未有趁势加入的打算。但是,信义会协办华中大学的呼声却在战后日益高涨起来,如,就是否开办信义大学的问题,牧师文道辉(David Vikner)建议:“目前如能同武昌华中大学合作,比较(而言)很为合适:就地域而论,武昌正为我中华信义会之中心。就教职员,或是学生,以至校风等,华中大学在各教会大学中,确是一个最基督化的学校。就作者所知,在各教会大学中,只有华中大学尊重各宗派的信仰,也只有华中大学有不同宗派的团契存在。我们现在虽然尚未与之合作,我们的信义团契就是在该校当局的协助之下成立的。”于事实层面,信义会不仅同意艾玮生转任华中大学专职教师,而且还积极予以资助。
三、华中大学新闻组之情状
在介绍华中大学新闻组的情状前,有必要弄清:在过去的大学中“组”究竟是一个什么机构?和“系”“院”又是什么关系?据笔者考察,过去的大学,设“组”的现象比较普遍,大致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在“系”内设组,如“民国十五年(1926年),上海复旦大学在中国文学科中,将原设‘新闻学’讲座扩大,设立新闻学组”;1946年山西大学向教育部申请在法律系内增设“司法组”。另一种是于各系之外设“组”,如震旦大学法学院原有法律学系、政治经济学系等系别,1947年又向教育部申请在这些系别之外,增设“司法组”和“国际法学组”。在新闻教育领域也存在类似情形,东方语文专科学校就在各语言科之外设有新闻组,《报学杂志》还曾报道1948年底原景信主持召开的该校新闻组二年级的座谈会。
华中大学新闻组属于第二种类型,即它与文学院下属的中文系、外文系、历史系、经济商业系以及地理学组、哲学心理组、宗教组等系、组并列,互不隶属。既然如此,又何必多此一举,作“系”与“组”的区分呢?为此,笔者专门访问过经历其事的张泽湘,据他讲,“系”与“组”的区分主要在师生规模,规模较小者就称“组”。的确如此,就师资而言,当时新闻组的专职教师就艾玮生一人,地理组也只有陶吉亚(T.R.Tregear)一人,哲学心理组则由校长韦卓民、文学院院长骆传芳兼理;宗教组人稍多,亦仅有戴惠琼等三人。就学生而言,各组基本没有单独招生,韦卓民在致麦默伦(Robert J.McMullen,纽约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执行秘书)的信中交代:“上学期(1948—1949学年度的第一个学期),文学院有324名学生,其中中文系43名,英文(外文)系78名,经济(商业)系160名,历史系43名”,信中未见各组的招生情况;另据《华中通讯》刊登的1947年华中大学招生简章,亦未将“组”列入招生目录。
尽管华中大学新闻组同该校其他各组一样,没有招生,但是,其作为教学单位的基本功能却得到了充分发挥,承担了中文、外文等系的新闻学教学任务。根据“华中大学各院系课程调查表”反映的情况来看,艾玮生开设了“新闻学”“时论编译”等两门课程,每门课均讲授两学期。其中,“新闻学”自“1950—1951学年度”的第一个学期就成为了中文系的系级必修课;“时论编译”则在该学年的第二学期成为了中文系和外文系共同的系级必修课,此判断来自外文系主任安务德(W.P.Allen)1950年9月4日致教务长的征求意见信。在信中安务德提到:“艾玮生先生准备开设一门叫‘时论编译’(Editing and Translating Current Articles)的课程,这门课程的学分将计入中文、外文两系学生的必修学分(major credits)。因此,为方便起见,艾玮生先生和我本人提议该课程定为两个学分。当然你若有不同看法,以你的意见为准。”从中可知,在1950年9月文学院已经确定,将由艾玮生开设“时论编译”,拟作为中文和外文系的必修课,但究竟给多少学分尚无定论。这意味着,在第一学期该课程没有开设的可能,因为一门课程只有在给定学分的情况下才能开设,更何况是一门必修课,而在学期初尚在讨论学分事宜,则意味着该课程不可能在当期开设。因此,作为中文和外文系的必修课,“时论编译”应在第二学期开设。
在整个“1950—1951学年度”,华中大学依然是私立身份。同政治和意识形态紧密关联的新闻学课程,是否还是或者说还能讲授资产阶级的那一套?答案是否定的。必须看到,华中大学作为一所教会大学,外国教会对其课程设置与讲授是有要求的。1949年12月纽约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托事部(华中大学系其成员)来函称:“教会学校中如果要讲共产主义的课程,或其他未经托事部批准的课程,则各校要设法筹备这些经费。”言外之意,作为一所教会大学不准开设共产主义的课程。而新成立的人民政府与此针锋相对,要求收回掌握在外国教会手中的办学权。1950年6月在京召开的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讨论通过的《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关于高等学校领导关系的决定》等决议草案明确指出:“私立高等学校的行政权、财政权及财产所有权均应由中国人掌握”;“全国高等学校以由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统一领导为原则”。华中大学顺应潮流,没有听从外国教会的指令,而是按照人民政府的要求做出了调整,譬如,应人民政府的要求开设“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Dialectical Materialism and Historical Materialism)和“新民主主义”(The New Democracy)两门三学分的课程。艾玮生也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他在“新闻学”课程的“教材内容简纲”中写道:“根据新民主主义的文教政策,分析新闻学范畴内各种理论与实际业务情况,如新民主主义报纸的特点、任务和方向,报纸的组织和管理,消息的采访、写作和编辑以及新闻工作之参观与实习等。”而且,他在“新闻学”的参考教材中列入了扎斯拉夫斯基的《新闻学研究提纲》、《长江日报》编写的《新闻工作文选》等著作。这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在华中地区首次有系统、成建制地实施。因为这门课不仅是中文系的必修课,而且还要系统地讲上两学期。
艾玮生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遵从与贯彻,有其主动的一面,这自他早年的经历及解放战争时期的举动可略见一二。据艾玮生二哥艾瑞生回忆:“北伐战争时期,(艾玮生)投笔从戎,由三弟(艾)毅根介绍参加郑州豫陕甘农村训练处(系冯玉祥所办)工作,因‘赤化分子’罪名被捕入狱,后由三弟友人余心清(开封训政学院负责人)营救。”另据其胞妹艾辉(原名艾琴生,民革成员,曾当选国民党“国大”代表)回忆:“我五哥艾璋(玮)生常和同乡艾伯良(解放后河南禹县第一任县长,老共产党员)接触。思想进步,1927年曾在河南被捕入狱。”这两段回忆一致表明艾玮生早年就有革命倾向。因此,1932年他在寄赠其三哥艾毅根的照片上,写下了这样几行饱含深情的诗句:“我们好像荷叶上的露珠,在清风吹动时,滚来滚去,但是,我们,终于会碰在一起,落在一起!”后来的情形果真如此,他的这位三哥是中共地下党员,他本人也于1946年由左派人士李公朴介绍加入了民盟。在艾辉的回忆文章中,还记述了这兄弟二人对她的思想触动:
(1948年9月)在上海见到我久别的五兄(艾玮生)后,他的第一句就说:“什么时候了,你还当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呢?”我当时听了震动很大。
在我和我三兄(艾毅根)、五兄见面以前,我还是个“迷途羔羊”,和他们见面后,我才有了初步的觉醒,对形势有所认识。在我的思想转变中,得他们的教益是不少的。
而且,在武汉解放时期,艾玮生向党靠拢的愿望相当强烈、行动十分积极。据张泽湘回忆,艾玮生曾同武汉地下党联系,邀请解放军首长到华中大学给教师们介绍形势,当时他本人就在现场。《湖北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书也写道:“(民盟)盟员艾伟(玮)生在地下党的支持下,团结进步师生和各方面的进步力量,阻止了华中大学的搬迁。”
遗憾的是,成立未久的新闻组还来不及发展,便已成为历史。“1951年11月,公立华中大学组织全体师生参加了武汉市和湖北省的土地改革运动。除年岁较高和体弱多病者留校外,学校共有753人(教工209人,学生544人)投入到武昌青山、新洲、黄冈等地参加‘土改’工作,至1952年6月止,历时8个月。”艾玮生自然也在这批参加“土改”的师生之列,据当时还是华中大学物理系学生的刘佑星回忆:“记得我们参加了青山区的土改。那时打破了师生、院系的界限,统一编队。和我一块参加土改的有我们系(物理系)的韦宝锷、历史系的张舜徽、新闻系(组)的艾玮生、音乐系的张才义等老师。”当时已无“系”“组”的区分了,不仅大家统一编队,而且所有的教学活动都已停掉。在这个意义上讲,新闻组已名存实亡。而在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中,华中大学新闻组便彻底消失了。
四、结语
华中大学新闻教育从无到有的转变,经历了授课、建学会、开讲座等一整套的流程,合乎华中大学学科拓展的稳健逻辑。华中大学新闻教育的实际开办得益于艾玮生的直接推动。自艾玮生主动请缨,来华中大学兼职讲授“新闻学”开始,华中大学的新闻教育迅速向前推进。仅年余,随着艾玮生转为专职教师,华中大学新闻组正式成立。依华中大学各组不予招生、仅负责开课的惯例,新闻组开设了“新闻学”和“时论编译”两门课程,其中“新闻学”课程为中文系必修课,“时论编译”则为中文系和外文系共同的必修课。在课程的设计与讲授中,艾玮生主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在华中地区首次有系统、成建制地开展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教育。
注释:
① 卜少夫:《谈新闻教育》,《新中华》,1944年复刊第2卷第4期,第66页。
② 据武道(M.Votaw)称:“目前(1948年)中国全国大学中,设有新闻学训练及课程的,有四个大学和一个专科学校。上海方面,另外还有一两家私立学校。”见武道:《中国新闻教育的现状与急需》,月卿译,《报学杂志》,1948年第1卷第3期,第10页。
③ 这里所说的新闻教育是指正式的新闻院校教育,不含各类新闻教育培训。笔者注意到,1948年秋,诞生于战争烽火中的中原大学创办了“新闻系”,但其实际只是新闻短训班。该短训班一共办了两期:第一期招收学员60人(这批学员一部分选自“南下干部中原支队新闻大队第一、二中队”,另一部分选自“河北平山县中共中央组织部干部训练班”),第一期学员经过五个月的培训,于1948年底结业;随即开办第二期,招收学员70余人(这批学员选自中原大学第一、二大队),第二期学员也大约经过五个月的培训,于1949年5月结业。(参考陶军主编:《中原大学校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21页。)这种短训班的性质由中原大学的办学性质与任务决定,“中原大学从一开始就是中原解放区第一所新型的‘抗大’式的革命大学。作为‘抗大’式的新型革命学校,它开始只具有短期训练性质,而训练目的在于培养当时形势发展所亟需的各方面的干部。”(见熊复:《中原大学校史·序》,载陶军主编:《中原大学校史》,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序”章第4页。)
④ 周挥辉编著:《百年华大与百年记忆——掌故·逸事·风物》,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39页。
⑦ 参考梁士纯:《中国新闻教育之现在与将来》,《大公报》,1936年5月9日,第12版。
⑧ 蒋荫恩:《新闻教育感想》,《中国新闻学会年刊》,1944年第2期,第113页。
⑨ “教育部代电(高字第22879号)”(卅五年十月一日),《教育部公报》,1946年第10期,第11页。
⑩ 武道:《中国新闻教育的现状与急需》,月卿译,《报学杂志》,1948年第1卷第3期,第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