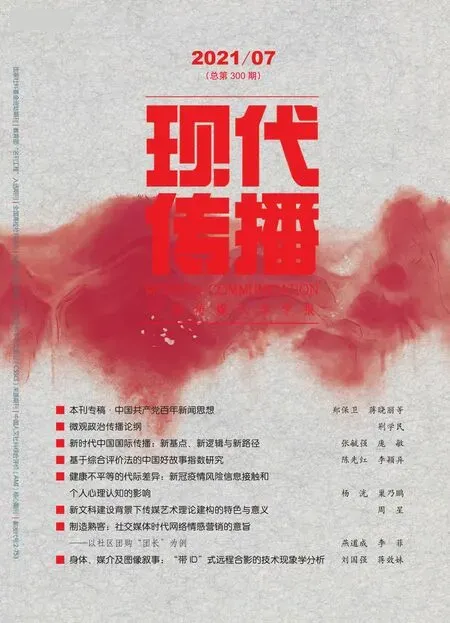论社交媒体中的整容围观及其审美陷阱
2021-11-29陈思睿
■ 詹 琰 陈思睿
一、引言:整容风险的广泛传播与公众愈发漠视的医疗风险
中国近年来整容人数激增,多种报告、白皮书的统计虽无法将极精确的数值呈现出来,但惊人数字的频频出现,以及整形文化的普及、整形常识的家喻户晓已说明了医美的流行。与此相伴的是,主流媒体中高频出现的伤害与负面新闻:因整形引发的毁容、失明、面部神经永久性损伤甚至脑死亡……在客观事实面前,“美丽动人”的真相被逐渐揭示,“美与风险并存”成为整形的代名词。
然而社交媒体舆论场却往往呈现另一景象,公众肆无忌惮地以三种方式——猜测对方整容、认定对方整容、想象整容背后的故事蜕变和围观并议论明星、网红们整容后的成果。只有少数人关注医疗风险,多数却只关注已有结果而漠视过程中的风险和伤害。历来,社交媒体的相对匿名性被认为能激发公众的真实表达欲,但显而易见的矛盾是,公众在明确知晓风险的前提下仍“知其然而不言其然”,甚至沉溺于无关痛痒的八卦绯闻。此现象即广义的“异化”,“异化”一般指主体在发展过程中,由于其自身活动而生成自己的对立面(客体),这个客体又成为一种外在的“异己力量”去反对自身。①
二、冲突与体认并存:社交媒体中带有异化色彩的整容审美奇观
道格拉斯·凯尔纳认为,媒介奇观指能体现当代社会价值观、引导个人适应现代化生活方式,并将现实中的矛盾冲突和解决途径加以戏剧化呈现的媒体文化现象。②当下,社交媒体充斥着整容审美奇观,表现为:明星整容后自信登台,容颜巨变引发观众惊诧;网红们顶着整容脸,角色千变但千人一面地与粉丝互动;真正引起关注的是某选秀选手那句“有什么不敢承认的,哪个艺人不微调”。一时间整容成为“常态”,与此伴随的是被遮蔽的医疗风险与公众受此潮流影响而渴望的化身、颠覆。这种无视风险并将“无视”转化为“流行趋势”的行径,正是凯尔纳口中冲突与体认(“解决途径”)并存、带有异化色彩的“审美奇观”。
公众人物以无所顾忌的“改造人”甚至“义体人”形象展示魅力,尽管他们羞于承认,却依托身体力行的展演引诱着观众的附和;改造过程被巧妙置换为荣耀加身的直接结果,改变成为常态、不变成为了反常,同时,“常态”与“反常”之间的原则性区隔已不复存在。虽然医美机械、用具未必直接嵌入人体,但我们认为,医美技术通过流行、大范围应用而炮制的与中国公众的亲密关系,同样形塑了哈拉维视角下“赛博格隐喻”的现实转向。
随着科技进化、发展,医用基因技术模糊了人、兽界限;起搏器和假肢从肉体上、人工智能技术从心智上模糊了人与机器的界限;③整容、医美则模糊了“原本我”与“改造的我”之间的界限。对比其他方面,“整容赛博格”不啻为肤浅易碎的幻梦,缺少深刻、革命性的科学依据,也缺少裹挟科技发展的宏大的工具意识形态,仅仅被消费文化、“颜值主义”盲目性驱使,最终构成了“画面”本身而与其后的“景深”无关。这种显而易见的肤浅性正是异化意味的另一种表现。
支撑异化奇观的动因有三。首先,“美丽”并非是使公众人物赢取注意力资源的制胜法宝,却是社交媒体所开启的“秒读时代”“滑动手势时代”的入场券。其次,“绝世容颜”是联结虚拟与现实的经济资本。由此,网络空间中新的社会结构事实几乎被完全忽略,公共舆论生成的空间转型、网红经济的溢出效应被视作无聊议题④,美丽身体引发的崇拜变成了有形可感的全部事实。最后,改变容貌是明星、网红们“无需以实际劳动来抵偿”的“自我压榨”,是将其自己的身体作为“劳动场域”而换取成名、成功的资本。马克思指出,随着协作性发展,劳动者未必亲自动手,只需成为总体工人的一个器官就可以完成所属职能。⑤尽管“器官”只是隐喻,却生动描绘了社交媒体对身体分工的篡改:在肉身经由医美解构、建构而重新到场后,完整身体成为了非完整的“系统性结构”,并为“观赏把玩、消费变现”这一事实上具有统摄力的“总体性动机”服务。
三、无视风险的演出:社交媒体中的“整容围观”现象
奇观往往引起围观,社交媒体中出现了观众们围观整容的现象,主要表现为如下三种情形。
(一)猜测对方整容:社交媒体的身体分离术
观众在注视公众人物时发出疑问:他们究竟是否整了容?观众只看到公众人物的光鲜外表,却无从在社交媒体亦真亦幻的内容陈设之下发掘对方的真实整容动机。但公众人物对此极为坚定:希望美丽成为光鲜形象的维持力,以此塑造职业面貌的“现代感”,从而召唤服膺者,使其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炮制情感认同。两种心态的对比凸显出观众潜在的趋向心理:整容是难解、迷人的“斯芬克斯”,需投入思维心智以发掘、探索。
虽然,观众往往能意识到媒体内容的虚假性而并未注入全部个人期待,也似乎未完全失去对整容一事的鉴别能力,但整容过程中的医疗风险依旧未能“到场”并引发重视。它被排斥在围观圈层外,理所应当地成为了“臆测”的组成。公众有所克制的好奇心针对的是风险的随机性、不确定性所塑造的“微弱可能”,而非风险自身的负面意指。炮制这种“视角错位”的原因是,明星、网红的光环魅力超脱了理性思维构型而上演着无时无处不在的价值观输送:“以景观取缔真相、无需关注真相本身的正负属性。”
仰海峰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任何物的存在都依赖与其他物构成的系列关系,消费就是在这种关系中寻求主体身份、地位的过程,后两者又是由符号体系建构起来的。⑥在观众欣赏明星、网红的软消费环节,前者一方面试图捕捉可感的视觉享受和审美移情,从而建构“清晰的自我意识”并证明自身享有对其的主导权,但同时,这种“自我意识”正被媒体环境中汹涌的、关于“美丽、魅惑”的无序符号浪潮一轮轮解构,最终只剩“观看、欣赏”的表层动作而疏远了“真相”。换言之,观众们欣赏到的“美”是由零散符号碎片拼凑、整合而成的“人造美”,“人造成分”既存在于整容的技术操作中,更表现为整容面孔的展演给审美体验乃至观念带来的“深层符号式冲击”。
综上推测,公众的风险意识并非全然淡漠,而是转化为符号,融入了社交媒体世界的主导符号体系并被算法推荐、后台内容筛选、媒介运营机制所控制,无法发挥真实效力而闭塞、终结于该层面。由此,“社会身体”与原本身体之间的鸿沟似乎本属正当,身体的“分离态”被篡改为了它在媒介社会中的“原本态”。
(二)判定对方整容:自欺之下的快乐掩饰
认定对方整容并因之议论的行为事实上是自欺。因为无论赞美或抨击都无法找到适切证据——除去极夸张的容貌颠覆外,“微整”技术的普及在很大概率上使美只存在于修饰、微调层面。心理学研究认为,自欺阻挡了威胁性信息从而维持正面自我形象,使个体保持积极心境。⑦由此,不妨推测观众的动机:凭借不假思索的、“对方一定整过容”的判断来释放非理性情绪,从而彰显强势并成为舆论领袖。
此动机并非有意壮大声势的揭竿而起,而是自我压制后的“应激反应”:以“坚定”的口吻讲出未必可信的事实以引领舆论,枉顾自身探求欲而草率结论。显然,社交媒体通过展示美丽容颜而炮制的无需思索、“必然真实”的“快乐”塑造了此行径,使得参与者贪图刺激享乐而漠视行为公正和价值准则。社交媒体先是抛出具有猎奇性的整容脸孔,其次诱导观众将“审美”的内在涵养过程转化为“评头论足、一针见血”的快感宣泄,进而赐予其浅表的满足感。无数研究表明这种“满足”只是快餐式的满足,当积累到一定阈值便会被倦怠与松懈取代。此行为心理虽显消极,却是具有解脱意味的真实生理状态,往往使人感到真正的轻松愉悦。对比之下,公众在当下的“满足”受到了媒体摆布,随浏览开始而开始,随浏览结束而终结,缺少长时间维系能力,更无法转化为具有建设性的幸福感。
此时,被屏蔽的医疗风险成为了可有可无的谈资。究其原因,风险阻碍了与“满足感”形影相伴的“快乐”的到场,形成了情绪创造过程中的障碍,它过于鲜明地使人意识到“逢场作戏”的尴尬,哪怕是辨认力较低的观众也会一眼识破。一旦风险“入场”,则“审美体验”将被击碎,整容审美所刻意营造的迷惑性与事实上的伪审美价值将顷刻曝光,随即,“快乐”被忧思取代,观众的武断与呐喊无法使他们凭借此种姿态而回归自创的“假想栖息地”之中。
乌尔里希·贝克指出,当内在和外在都遭遇自身时,对知识和启蒙的吁求面对得到成功发展的“易错论”开始降低,原来归之于科学的接近现实和真理的途径,被那些随意的决定、规则和惯例替代。⑧如其所言,社交媒体通过展示明星网红的容颜而为受众炮制的“无脑审美愉悦”,极荒谬地屏蔽了整容蕴含的医疗风险。我们认为,针对现实风险确应反省、警惕,而当反思被无视取代,并被视作建构出的“极乐净土”中的不合时宜者时,“理性”亦被取缔了。无疑,承认、解析风险是进行“对方一定整过容”的判定的前提,而当公众删除此前提并向社交媒体俯首帖耳时,他们对自我的、关于容貌与内在的价值判定亦将动摇。在即时审美的刺激性愉悦之下,对关于美丽的“真相”的主动遗忘被扭曲为了“快乐源泉”。
(三)想象整容背后的故事:声色社会中的枯竭灵感
议论整容却不限于此是部分观众的选择,他们看到的不是“局限于此”的表象,而是在社交媒体发酵下生机盎然的想象容器,其后更多轶事、八卦、“内幕”尚待揭开。整容本是私人事宜,但如今其公共属性更受关注:红人整形后亮相是关注点之一,他们的大胆自白是其二,失败后丑态尽显则是其三,无论哪一点,都是“应当”受到驻足评价的公共话题,是视觉怡情所布施的精神食粮。
在观赏上述景象后,观众却仍不满足,他们希望依靠想象力的发酵带来“高质量娱乐体验”,于是在可见的整容景观之外伸展开幽深的欲望围栏,进一步催生“想象式奇观”。在以议论事实上“蕴含医疗风险的行径”为荣的“半脱轨空间”中,观众们的快乐源泉屈指可数且气质单调,游离于越轨边缘却不敢完全脱缰,不敢完全地面对、道破风险。这种自娱伎俩使审美的“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一般逻辑顺序转化为“表象—对表象展开无差别想象”,曲解了深度审美认知的正当流程,使“对外在事物的审美与沉醉”变为了“自我想象式的欣赏与沉迷”。
在“公众对蕴含医疗风险的整容行为展开想象”背后,可能蕴含的某种“动机”是什么?事实上,在明星网红千篇一律的社交媒体展演背后,往往隐含着显而易见的媒体运营规律与商业资本诱导。二者并不在意整容行为会将大众审美引至何境地,仅将之视作视听率诱饵和维持运营的“视觉动力”。当这种十分粗糙的“工具性意图”即将暴露时,带有争议却不至哗然、不完全背离常理的话题便是搅动氛围、使“濒死”的视听声势被复苏的不二之选。
Hogle指出,面对新形式的“代理性”和“社会性”(二者可以指代本文所述的社交媒体中的整容奇观充斥荧幕,使受众遗忘医疗风险并对这种遗忘习以为常,最终创造出“虚假社会事实”的情形),除了考虑成本效益、权利框架或潜在形式带来的剥削,还应考虑形成身体增强技术的社会条件和过程。⑨在观众对整容行为的想象中,关注点被本末倒置:只有主观臆测、极为表象的“社会条件、过程”,例如明星、网红的身价、绯闻和私生活,却缺少对整容者试图在整容时获得/规避的自我心理满足感、生活满意度等方面的效益、权利/医疗风险所带来的肉体剥削等实际、深入问题的关注。上述现象的成因是:前者使观众降低了审美成本,在无需借助天然、真实的审美对象的前提下停滞于社交媒体所创造的声色享乐,并获得与原生体验“相差无几”的“审美体验”;后者却需要设身处地地代入同理心并为之思考,无法继续享受“审美的快乐”,因而被封杀。在此过程中,包括医疗风险在内,所有可能的“干扰项”均无足轻重,尽管鲜血淋漓、后果严重。
四、“整容围观”现象的多重成因
上述三种围观姿态的共性是,专注于明星、网红展演而炮制的异化审美体验,忽视了对整容过程中的风险、伤害的分析或关注,其成因共有三点。
(一)“颜值经济”促成了屏蔽审美伦理问题的“铁幕”
当下“颜值经济”大行其道,观众乐于观看美好肉体,商品生产者也乐于以此盘活经济,使媒体发展的活力可供性(affordance)生生不息。但以“软性商品营销”为核心而构建的审美浪潮充斥着十足的闭塞性,并非真实社会需求的外显,仅仅用以迎合公众浅显的生理性欲望和介入虚拟世界、操纵“快感政治”以收获虚假繁荣的诉求。随着大众审美符号与具体社会进程间的有机性断裂,文化表达与社会进步路径日益疏离,数字媒体成为了隔绝物质的、具体社会实践与人类文化体验之间的“铁幕”——人类在赛博空间中日趋丧失主体性和历史使命感、缺乏对技术红利背后的文化偏向的反思。⑩
缺乏反思的表现是:关于风险的内容几乎被屏蔽,公众执意认为美丽世界“不染纤尘”,决然与风险无关。但美与医美尚有不同,前者追求内外统合的身心兼修,是自然舒适的稳定态;后者却追求模拟、仿效,比如医师开展手术前会与“病患”沟通,了解其希冀成为的刻板模式,这正是韩国曾经“遍地韩佳人、宋慧乔”的根源。
此时,医疗风险既源自医学科技自带的不确定性,亦源自受术者对原本身体不忠而招致的“惩罚”,甚至是想要篡改真容的“原罪”——这使医美所象征的审美伦理无法绝对向善。反观观众——他们对医美之恶与“恶”所炮制出的“美丽”的习以为常,正塑造了一种“规训、群嘲”决然合理的“全景监狱”:因为自我的“审美享受”而无视他者安危。将整容美视作众星捧月的“必然美”,正是媒体资本、“颜值经济”的无序扩张,或曰资本力量在“自由竞争”过程中渲染的“表象美好”(例如颜值和外貌层面)所诱发的道德颠覆。事实上,披着“自由”外衣的诱惑极可能使观众动摇并加入排斥善良、本心的队伍,这在黑格尔的伦理观中得到佐证。在他看来,抽象的善是完全无力的东西,同样,作为精神的主观性的良心因欠缺客观现实性而缺乏确定内容,此两者导致了实质的主体的空虚性、否定性痛苦。
在媒体经济翻手为云的同时,医美机构的联合亦是支撑“颜值经济”的动因。明星、网红的“颜值推广”得以抵消对整容的功效、危害的详细交流,生动逼真的案例使美丽的到场成为了“无需追问缘由”的“本源”。尽管这一“本源”遭到社交媒体的无限悬置——明星、网红对普通公众而言只是不可触碰的幻影,但在欲望浪潮中,单纯的刺激图示已是无穷诱惑之来源,导致了观众对审美的渴望,但其本身却并非真实审美体验,含有误导成分。最终正如Marwick所言,媒体呈现改变了我们对整容的道德理解。
(二)媒介资本的“唯我”力量诱发“集体造梦”式的审美体验
荧屏角色的魅力使美的到场成为天然、无需追问缘由的结果,这虽然与明星魅力对观众的误导不无关联,但同样重要的是后者的“自我崇拜”。以源自韩国的“饭文化”为例,粉丝缔结的并非对偶像的绝对认可,而是对自我图示的根源依赖——在他者处见证了有朝一日可能与现实联结的自己。“粉丝”可分为“姐姐粉”“妈妈粉”“路人粉”等多种类型,但任一模式都是观众代入个人角色、结构性体认后发出的外向心理干预,其目的是在公开舆论环境中传播主体价值观、锚定同好以融入社群。
由此,“整容围观”也是试图建立同伴社群的“自我考量”,然而其会将观众导向何境地,真的是日益强健的个人形象或自我心理暗示吗?在社交媒体时代答案或是否定的,任何沉溺线上容颜的观众未必会毫无顾忌地在线下整容并接纳其风险——他们能做的,仅是假装淡漠地屏蔽风险并置身于“套子”中,炮制含有自欺意味的“审美观感”。
此举的背后是媒体资本对医疗风险的“操控”:拒绝为无法控制的伤害性事实负责,只在看似合理、可控的范围内协助参与“围观”的观众集体造梦。换言之,为了使资本力量和促使观众为各色脸孔买单的消费氛围在媒体中日益强化,原本严重的风险后果被资本力量视作在视听娱乐中召之即来、挥之即去的非原则问题。其“来”“去”的循环过程的动力,正是齐泽克所谓“资本主义唯我论的自我受精”。由此,扭曲的审美心态被日益正当化。这种遮蔽了医疗风险的痛苦、伤害乃至原则性的行径并非弱化或杜绝风险,而是用“建构”的方式赋予其如下特征:“非医学化、非科学技术化”、无关痛痒且“无效”。在某种程度上这正是对哈贝马斯观点的诠释,医疗科技风险同所有的“科技”一样不具有“真理性价值”,只是虚浮的“构型”。但谬误在于,风险因何而沦为被漠视的“非真理”?如果是在凝视整容脸时屈从于媒体资本布局的盲从,那么风险便沦为了附属于“凝视”这一单纯行为动作的“次要构型”,而与“凝视”本应该关联的“审美、内化、沉思”绝无联系。
(三)回声室效应导致了肤浅的“审美价值观内爆”
胡泳指出,“回声室效应”指网络空间里,主体在接受大量意见的相类回响后,认为自己的看法代表主流、扭曲一般共识的现象;个人总是倾向于接受协调自我认知的信息并避免异己。“整容围观”即是“回声室”的生动呈现,虽然对比一般回声来看,不涉及深度信息传递与审美体认,被传播的只是肤浅庸俗的看客姿态,但带来了更深层面的价值削弱、崇尚故作姿态与表象崇拜,将无需遵循本心、诉诸内生审美思考便可宣扬自我价值观的行径发扬到极致。类似行为有着貌似合理的雅称:“审美亚文化”,看似包含深层次“对抗”意味,实则通过不同主体观看姿态的交互而抵消了内部充能,最终呈现出吸收、消化了无穷内爆的死水一滩。
在“围观姿态至上”的宏观环境中,公众“追随大潮流”“不得已地漠视着医疗风险”,但正如诸多研究提示的那样,“回声室”并非层层加密、无法突破的死循环,而是取决于受困者意愿的“开放题”。虽然媒体算法、社交同僚塑造的过滤气泡、信息茧房在事实上加重了突破封锁的困难,但只要了解、甚至单纯畏惧风险便可能脱身。反之公众的表现是:放任风险的真实意义在交错、纷乱的评论声中由强转弱而不愿出手干预。与其说在回音之中难辨真假,不如说他们迷失于回音世界的价值引导,仅仅在意不断重叠的逼真的“美”并将整容面孔的逼真性误认作移情对象。
师曾志认为媒介叙事是一种能力,它需要讲故事的人将自己与他人的经验交织在一起叙事,会随着受众的情绪、态度等随时调整内容,也有移情而唤醒听者自我经验的技巧,因而是名为分享的技艺。与此相反,在“明星整容”的故事陈述中,被分享的并非是同理心和人文关怀,而是跟风的“社交媒体审美潮流”,就像自互联网进入中国几十年来轮番上演的那样。近20年前我们议论芙蓉姐姐,十余年前关注凤姐,如今关注随处可见的整容网红,追逐噱头、猎奇的脚步并未改变,医疗风险不过是暂时的医美印记,无法阻止恒长往复的对新奇容貌的观赏欲,哪怕后果可能伤痕累累、坠入深渊。
五、“整容围观”现象与其炮制的“审美的特殊性”
在分析“整容围观”的表现和成因后,有两方面问题亟需深入思考,我们合称为“审美特殊性”方面的思考:首先就根源而言,观众们或主动、或由于上述原因影响而表现出的,不同于一般审美“沉静、内敛”特质的“热情”甚至“狂热”源于何?其次,相较其余围观行为或相关媒介现象,因为“审美”和种种原因得以成立的“整容围观”有何特殊性?
针对前一问题我们发现,中国公众对整容的热情与西方人大相径庭。例如,西方多数填充物手术只用于老年白人的面部减龄,而非普遍的整容(在年轻人中广为流行)。存在此差异的渊源是中国社会正经历的“美丽的工业化浪潮”:因为医美科技、工业的发展对“美丽等于年轻、‘完美’”的绝对化观念的建构和社交媒体对此的传播,医美这一“巧夺天工”的技术手段被推崇备至,以至于在围观整容明星、网红的过程中,观众视其为符合美丽标准的示范者而非风险携带者。进一步讲,正如科技发展希望展示利好而掩藏缺陷的惯性过程,医美技术在“反思科技”的人文观念未被广泛普及的当下,也引诱着中国公众的“审美”——其本质是对科技利好的单方面依附,与真实审美所推崇的“天然、原生态、感性”不符。
针对后一问题我们认为,“整容围观”的“审美诉求”有着比较清晰的意图,这使其区别于单纯的“无脑式围观”和其他媒介现象。但当此诉求折射的“审美偏好”源于某种误区:更多针对容貌本身而非其内化后的风蕴、气质,昭示着中国文化传统中“君子涵养”的失落,那么“整容围观”也势必具有更深层的非正义性——既具有实存的成立动因和内生逻辑(均为“诱导消费”),又以鲜明、大胆的“歪曲审美”行径引导公众趋从,二者合并、凸显出试图瓦解审美正当性的刻意倾向。
从大量观众加入“围观”且屏蔽医疗风险的举动来看,引导行为已收获成效,但为何它能使观众响应、甚至在社交媒体中蔚然成风?我们认为缘由或在于媒体对“审美情结”的压缩、矮化甚至“符码化”处理:因为供用户深度交流亦即“走心”的功能尚不完善,在急需盈利的前提下,媒体便相对轻松地通过像素、音频和图像帧的组合来搭建吸引受众的“视觉享受”,由此,“美丽”的内生涵养被置换为了画面陈设。对用户而言,欣赏画面是轻松、便捷且毫无负罪感的休闲体验,尽管与“审美”相关,但既无需深度代入同理心、开展严肃审美,更无需关注“画中人”的身体健康,最终,无数以审美为借口、实则无视医疗风险的自我姿态便被默许。这对应Gimlin的观点——“默会的具身性”是一种理想化、甚至处于优先地位的状态:如果观众自己的“审美乐趣”已得到满足,那么屏幕那端相隔千里的明星、网红所承担的医疗风险何足挂齿?
注释:
① 郭冲辰、陈凡:《技术异化的价值观审视》,《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2年第1期,第1页。
② [美]道格拉斯·凯尔纳:《媒体奇观:当代美国社会文化透视》,史安斌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③ 李建会、苏湛:《哈拉维及其“赛博格”神话》,《自然辩证法研究》,2005年第3期,第20页。
④ 杨江华:《从网络走红到网红经济:生成逻辑与演变过程》,《社会学评论》,2018年第5期,第25页。
⑤ [德]卡尔·马克思:《资本论》,李睿编译,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95页。
⑥ 仰海峰:《商品社会、景观社会、符号社会——西方社会批判理论的一种变迁》,《哲学研究》,2003年第10期,第25页。
⑦ 陆慧菁:《自我欺骗:通过欺骗自己更好地欺骗他人》,《心理学报》,2012年第9期,第1269页。
⑧ [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何博闻译,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92页。
⑨ Linda F.Hogle.EnhancementTechnologiesandtheBody.Ann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vol.34,2005.pp.712-713.
⑩ 战迪:《如何塑造我们的面孔——“脸性社会”的媒介文化批判》,《文艺研究》,2019年第12期,第1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