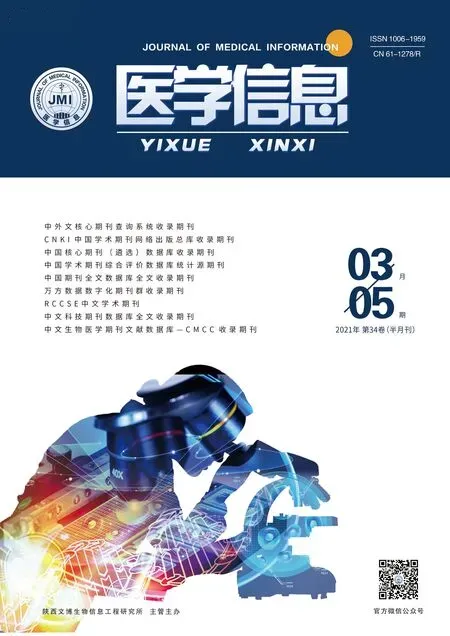康氏学术流派在原发性肝癌治疗中的经验拾萃
2021-11-29郑春榕阮清发
郑春榕,阮清发
(1.福建中医药大学,福建 福州 350122;2.福建省厦门市中医院肝二科,福建 厦门 361006)
原发性肝癌(primary liver cancer,PLC)系指发生于肝内胆管上皮细胞或肝细胞的恶性肿瘤,该病的病因及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其发病是多种因素相互胶着发展而来的复杂过程,目前认为主要与病毒性肝炎感染、黄曲霉素暴露、肝硬化、环境污染等密切相关。近年来研究显示[1],我国肝癌的死亡率居高不下,是我国主要恶性肿瘤之一,该病起病隐匿、发展迅猛、预后差,肝癌患者5 年生存率极低,严重威胁我国人民的健康,目前尚缺乏特效治疗手段,因此肝癌的预防及控制尤为重要。现代医学主要通过介入、射频、放疗、化疗、肝移植等手段治疗原发性肝癌,但存在肝癌术后出现诸多并发症、毒副作用明显等问题。中医药在治疗原发性肝癌术后发生的并发症具有独特的优势,能够减轻手术后的毒副作用,缓解患者的临床症状,从而提高生活质量,延缓病情的进展,实现带瘤生存的目标。康氏学术流派是福建省重要的中医肝病学术流派,阮清发主任是康氏肝病疫郁理论的学术继承人之一,师从流派创始人康良石及第二代传承人康俊杰教授,精于中医肝病的诊治,笔者幸列门墙,得阮老师言传身教,获益良多,现将康氏学术流派运用中医药辨治原发性肝癌术后的临床经验总结如下。
1 审证求因,病证结合
康氏流派观点认为,肝癌是以正气虚损为本,痰凝瘀毒为标,日久博结于肝脏而成,病情常为虚滞相兼、标本夹杂。机体正气亏虚,阴阳失和,脾肾虚损,津液代谢失司,无以运化水湿,凝聚为痰浊,邪无出路日久而成毒,痰浊癌毒积于肝脏,肝脉受阻,可进一步形成血瘀。痰凝血瘀又可作为致病因素,加重脏腑气机的郁滞,使得正气更虚,损伤肝脾肾三脏,致使气血阴阳衰败,正气无力抗衡邪气,故由积变化为癥[2]。
导师在继承康良石教授辨治肝癌的基础上,结合临床,认为原发性肝癌手术属于祛邪的范畴,肝癌术后复发的关键在于正气亏虚,常伴随一系列并发症的出现,甚至癌转移。手术虽去除瘤体,但机体尚留存致病因素,即发病病因、诱因等,因此肝癌术后患者仍应重视致病因素的清除,如由肝炎病毒感染所致的肝癌患者,术后仍要积极抗病毒治疗。此外还有酒精、肝硬化、黄曲霉素等致病因素,均需进行治疗。另外,术后虽瘤体去除,然而患者体内的某些病理改变仍然存在甚至更加明显,如痰浊血瘀等,若术后不加以施治,各种病理产物相互胶着重沓,又可作为致病因素,久之癌毒生成,故而肝癌再次复发,因此肝癌术后患者也应重视体内病理产物的清除。康氏肝病疫郁理论中的“疫”为病因,即肝炎病毒,疫毒侵袭肝脏,而肝具有“肝气易郁”之特点,故属于“因疫而致郁”的疫郁,由郁而生病,肝癌的发生发展符合这一演变规律[2]。
2 审察病机,论其治法
康良石教授认为肝癌属全身虚、局部实证,机体正气不足,脏腑功能失调,常责之于肝脾肾,临床上根据肝癌的发病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瘤体体积较小,无明显的临床症状和体征;中期肝脏尚能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但偶尔会出现肝区疼痛感;晚期肝功损害严重,肿瘤细胞严重侵犯肝脏,此时需手术切除癌变组织。对于以上三期的肝癌患者,采取的治疗原则不尽相同,应根据各期的四诊资料进行辨证论治,或邪盛正未衰者(早期),则重祛邪解毒化瘀;或正虚邪恋者(中期),则祛邪与扶正相兼;或正气衰败者(晚期),则以扶正为主。但解毒化瘀法贯穿于各期,应仔细辨证,注意药物剂量及比重的调整。
导师结合既往治疗原发性肝癌术后的临证经验,指出在辨证论治阶段需分清正虚与邪实的占比。对于肝癌患者术后近期阶段而言,其机体虽有正气亏虚,但体内的瘀毒等尚存,甚至部分肝癌术后患者常伴有炎症的发生,多表现为湿热证症状,此时邪实较重,故在扶正的同时应注重祛邪。对于肝癌患者术后远期的治疗,则常以扶正为主,但也应配合化痰散瘀解毒之法。无论是近期还是远期阶段,扶正与祛邪二者贯穿始终。
3 遣方用药,运筹帷幄
康良石教授辨治肝癌,认为瘀毒伤损正气者,应治以扶正固本、健脾益气,增强自身机体的免疫力,提高抗癌能力,配合活血化瘀、清热解毒之法,经多年临床经验探讨总结出经典方剂参芪三甲汤,主要药物组成如下:人参、黄芪、茯苓、炙龟板、薏苡仁、醋鳖甲、生牡蛎、九节茶、半边莲、龙葵、菝葜根、仙鹤草、半枝莲、白花蛇舌。此方充分突显了辨病与辨证相结合的思想,标本兼顾,具有益气健脾,解毒散瘀之功效,对于气血亏虚,毒瘀蕴结的肝癌患者,颇具良效,临床上往往能屡试不爽[2]。
通过对康良石教授辨治肝癌思想的学习继承,导师结合临床实践,对于原发性肝癌术后毒瘀肝脾,脾虚湿热者,提倡扶正固本、解毒散瘀、清热利湿,拟参芪三甲汤化裁:半边莲、九节茶、川芎、姜半夏、白豆蔻、薏苡仁、半枝莲、黄芪、芡实、醋鳖甲、牡蛎、炙龟板、泽泻、茯苓、续断、炙甘草。方中半边莲、九节茶、半枝莲解毒散瘀、抑菌抗癌;川芎、姜半夏活血化瘀散结;白豆蔻、薏苡仁、黄芪、芡实、茯苓、泽泻健脾益肾除湿;醋鳖甲、牡蛎、炙龟板软坚散结抑瘤;续断滋补肝肾;炙甘草调和诸药。全方共奏健脾益肾、清热利湿、活血散瘀、解毒抗癌之功。
临床上随症加减,对于术后正虚的患者,常重用黄芪、人参、仙鹤草、龟板等扶正固本的药物。现代药理实验证明黄芪可以抑制体液免疫反应,也能提高细胞免疫功能,具有防止肝糖原减少和保肝的作用[3]。另外,仙鹤草的药理试验证明其具有抗癌细胞、使血管收缩、升血小板的特殊疗效[4]。对于胁肋不适者,加延胡索、川楝子,疏肝行气止痛;胃胀肠鸣者,加焦山楂、鸡内金、炒麦芽,健脾消食除胀;鼻衄、皮下瘀斑者,加仙鹤草、紫珠草,收敛止血抗癌;夜寐不安者,加合欢皮、夜交藤,宁心安神;呕恶痰多者,加旋复花、姜竹茹,止呕消痰;腰膝冷痛、夜尿频多者,加补骨脂、巴戟天、桑寄生等,补肾壮阳。导师在遣方用药上注重扶正与解毒药物比例的平衡,多用性味平和之品,避免大剂量使用大寒大热之物,使机体阴阳调和,同时强调肝癌术后患者易情志失调,可酌情加用疏肝行气之品,积极引导患者消除不良情绪。
4 病案举隅
患者,洪某,男,81 岁,退休人员,2017 年1 月体检查腹部MRI 提示:①肝尾状叶占位性病变:考虑巨块型肝CA 可能性大(5.4 cm×4.3 cm);②肝内多发小囊肿;③肝硬化,脾大,腹水;④胆囊多发结石。2017 年2 月14 日于厦门市中医院肝外科行局麻下肝动脉栓塞术,术后出现嗜睡,乏力、纳差,查血氨75.1 μmol/L,肝功能:TB 44.3 μmol/L,DB 11 μmol/L,IB 33.3 μmol/L,ALT 72 IU/L,AST 96 IU/L,遂急请会诊,导师结合四诊合参,中医治以清热利湿、解毒散瘀、健脾化痰。拟栀子根汤化裁。中药处方:栀子根、郁金、蛇舌草、石菖蒲、盐泽泻、赤芍、丹皮、大黄、姜半夏、黄芪、醋鳖甲、玄参、薄荷、甘草片、山药。服药3 剂后,患者诉食欲改善,精神状态明显好转,住院期间继续守方加减治疗,经治后上述症状明显改善,病情稳定后出院,出院后间断门诊随访中药治疗。2017 年10 月14 日复查腹部彩超:肝尾状叶内可见高回声占位(6.0 cm×5.3 cm)。2018 年2 月因“上消化道出血”第2 次住院治疗,查腹部彩超(2018年2 月9 日):肝尾状叶内可见高回声占位(6.3 cm×5.6 cm),经止血、补液、保肝等综合治疗后,病情好转出院。出院1 月余,患者再次就诊我科门诊,要求中药治疗,症见:乏力,右上腹胀闷不适,腰酸,口略干,口苦,纳一般,夜寐安,二便自调,舌淡红胖大,舌中有裂纹,苔薄腻,舌下络脉迂曲,脉弦细。诊断:积聚病(毒瘀肝脾,脾虚湿热),拟参芪三甲汤加减,中药处方:半边莲30 g、九节茶15 g、川芎10 g、绵茵陈30 g、白豆蔻5 g、薏苡仁20 g、半枝莲15 g、黄芪40 g、山药30 g、仙鹤草30 g、枸杞15 g、桂枝6 g、大黄炭3 g、醋鳖甲10 g、牡蛎30 g、神曲10 g、酒萸肉15 g、酒续断10 g、红枣6 g。7 剂,水煎服,日1 剂,早晚饭后温服。药后患者精神体力佳,食欲食量可,口干、口苦好转,腰酸、右上腹胀闷明显改善,夜寐尚安,二便自调。以上方为基础继续门诊随访取药治疗,2019 年11 月21 日复查肝功能:TB 19.4 μmol/L,DB 9.1 μmol/L,IB 10.3 μmol/L,ALT 22 IU/L,AST 32 IU/L,AFP 正常。患者腰酸改善,纳寐可,二便调,舌淡胖中有裂纹,苔薄白,舌下络脉迂曲,脉沉细。守上方减绵茵陈、神曲、萸肉,加姜半夏、石斛、生麦芽、茯苓、芡实、泽泻,14 剂。继续门诊随访,患者口服中药至今,未诉明显不适,正气渐复,肝功能、肾功能基本稳定,复查彩超提示肿块(6.6 cm×5.5 cm)并无明显增大,未再复发及发生癌转移,病情稳定。
按语:患者老年男性,为原发性肝癌术后患者,中医辨证为毒瘀肝脾,脾虚湿热证。中医治以健脾益气、清热利湿、解毒散瘀。拟栀子根汤化裁。患者术后并发乏力、嗜睡,此时属湿热证且湿重于热,治疗上注重祛邪药物的占比,疗效良好。后患者肝癌术后再发,正气不足,治疗当以扶正为主,兼以解毒,药后腹部胀闷、纳差等临床症状好转,守方同前,酌情稍减清热解毒之品,以免过于寒凉伤正,加石斛、茯苓、芡实滋补肝肾,姜半夏、生麦芽理气除胀,余药可随症加减。同时导师在诊治之际还重视患者的心理疏导,给患者树立积极抗癌的信心,常叮嘱患者要适寒温,节饮食,畅情志,关注患者生活质量的提高。该患者2017 年手术至今已有3 年余,精神状态尚可,病灶长期稳定,肝功能、肾功能明显改善,其他血清学指标也逐渐恢复正常,目前未发现术后肝癌转移灶,生存质量较高,临床疗效较为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