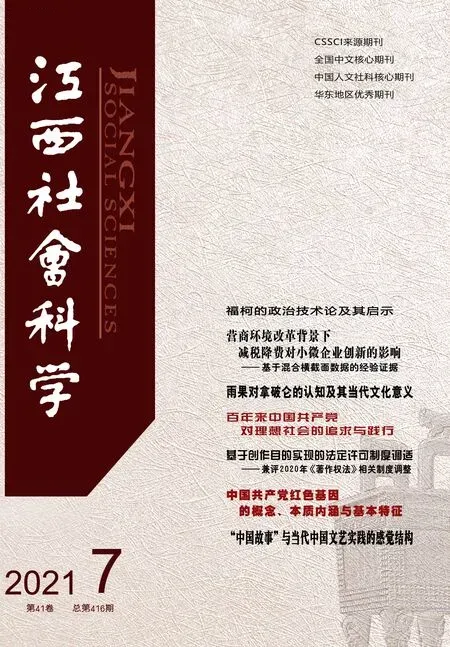基于创作目的实现的法定许可制度调适
——兼评2020年《著作权法》相关制度调整
2021-11-29刘铁光向静洁
■刘铁光 向静洁
不同作者具有不同的创作目的,但实现创作目的却是基本相同的路径,即作品的利用与传播。法定许可创造了一种无须授权只需付费的作品利用与传播方式,其降低交易成本与预防垄断的制度价值,实质上增加了作品利用与传播的机会。互联网与数字技术催生了作品传播的去中心化模式,但中心化传播模式并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法定许可制度作为实现创作目的的一种制度,依然具有存续的价值,但应允许权利人拒绝。202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非但未在作品广播法定许可中增加权利人有权拒绝的“声明保留”,反而在教材汇编的法定许可中删除了“声明保留”的规定,这应在未来修订中予以调整。
一、问题的提出
2012年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草案中有关音乐作品法定许可的规定一经公布①,便遭遇直接抵制:高晓松、刘欢、小柯等知名音乐人签署联名书信,呼吁修改“新草案”,认为该条款没有尊重作者的权利②。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甚至认为,有关法定许可的规定将导致著作权人的私权利被公权化,其创作的作品被轻易地、合法地转化为了公共财产③;中国音像协会唱片工作委员会认为,修订草案中的法定许可制度,“剥夺了著作权人的许可权和直接获酬权,摧毁了音乐产业基本的商业模式,也会使一直在困境中挣扎的音乐行业雪上加霜”④。著作权立法主管部门基于该抵制,在公布草案第二稿时直接删除了该规定。⑤
与现实中《著作权法》修订草案法定许可制度中只有音乐作品录制法定许可遭遇抵制相比,我国著作权法理论界则走得更远,认为至少部分法定许可制度应该退出《著作权法》。持这种观点的主要论据有二:其一,法定许可这种非自愿许可的方式剥夺了权利人自主协商的机会。“经过二十多年实践的经验教训,我国《著作权法》的法定许可制度已完成其阶段性任务,应当逐步退场,由使用人按照商业惯例与权利人协商订立作品使用合同的自愿授权制度取代。”[1](P29)亦有学者主张:“摒弃试图一蹴而就构建著作权许可机制的传统,以恢复和建立著作权市场中产业主体自由协商机制为优先……应在已经具备著作权市场协商机制的领域废除法定许可的适用。”[2](P80)其二,法定许可制度原本就不具有或者不再具有存在的价值。“我国《著作权法》确立非自愿许可的法定许可制度主要是一种务实之举,理论上并无充足的依据,也谈不上具有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公共利益因素的考量。”[1](P21)亦有学者主张:“我国著作权立法应重新定位法定许可的立法价值,将其视为调和传播技术发展初期产业利益分配分歧的临时性工具。”[2](P80)除此之外,还有针对某种特定法定许可应该退出的论据⑥,但这些论据,若无法定许可“剥夺了权利人自由协商机会”或者缺乏稳定的立法价值的论据,则基本也可以忽略。然而,确实如此吗?有体财产的相关理论套用到著作权领域一定能实现其预想的效果吗?2020年修订的《著作权法》对法定许可制度的调整,其合理性需要更深层次的评判。为此,本文将从创作目的的实现路径出发,分析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存续的正当性基础,并为其在当前新技术时代提供制度调适的方案,据此对2020年《著作权法》调整之后的法定许可制度进行评析,并提出下一步调整建议。
二、不同创作目的实现的相同路径
著作权法定许可的理论基础是经济学中的科斯定理,即交易费用为零,不管产权初始如何安排,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财富最大化的安排,即市场机制会自动达到帕累托最优,在经济学中通常被表述为“法定权利的最初分配从效率角度上看是无关紧要的,只要这些权利能自由交换”[3](P498)。科斯定理的前提是当事人愿意选择通过谈判的方式进行交易,这对于有体财产权而言确是如此,至少没有人喜欢其交易财产的自由受到任何的限制。然而,对于以作品为基础的著作权而言,此观点并不当然证立。作品源自人的创作,创作与劳动具有本质的区别:劳动是人类生存不得已而为之的必需选择,故劳动的目的必然是以劳动成果兑换成金钱或者其意欲的替代物;而创作已经超出人类生存的需要,并非人类的必需选择。哲学领域的研究成果认为创作是一种“精神本能”[4](P160),因为“生命本性可以说就是莫知其所以然的无止境的向上奋进,不断翻新”[5](P32)。既然创作并非人类生存的需要,创作目的自然就不是,或至少不全是将创作的成果兑换成金钱。尽管每一个时代,确实有部分主体的创作是追求经济利益,但不能以此否定不以经济利益为目的的创作主体存在。根据创作目的的差异进行适当的类型化,至少可将其分为经济利益需求型创作主体与非经济利益需求型创作主体。
(一)非经济利益需求型主体创作目的的实现路径
非经济利益需求型创作主体创作作品是基于多种需求,或是为了娱乐,或是为了爱好,或是为了学术,或仅仅是为了表达,等等。但其共性是该类主体创作作品不是基于经济利益的需求,或者至少不直接是经济利益的需求。正如美国学者研究新媒体环境下的软件共创平台后认为,当前网络用户创作动机是多元的,大量网络用户参与创作的目的并非基于价格体系,而是基于社会关系与共享的伦理。[6](P276)以学术类的创作主体为例,其并不依赖作品的交易来获取利益以维持生计,其创作作品是为了提升其学术影响力,进而提升作品被利用与传播率,学术界以“作品的被引频次来评价作者的影响力”[7](P59)就是很好的例证。实际情况亦是如此,如某个学者发表在学术期刊上的论文,不但希望被他人引用,而且希望其论文能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人大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或摘编,这种现象在学术界是无人否认的。因此,学术需求型创作主体创作目的的实现是作品更多的被利用与传播。实际上,与学术型创作主体一致,娱乐需求型、爱好需求型与表达需求型创作主体,其作品更多的被利用与传播,能更大程度地实现其娱乐、爱好与表达的目的,至少可以提升娱乐、爱好与表达的价值。正因如此,对于非经济利益需求型创作主体而言,欢迎任何保留其署名的方式对其作品进行被利用与传播。也就是说,任何人对其作品的被利用与传播根本上不需要与该类主体进行任何交易。这正是因为作品被利用与传播是实现该类主体创作作品目的的相同路径。
(二)经济利益型主体创作目的实现路径
不可否认,传媒产业的发展确实催生了经济利益需求型的创作主体,最为典型的是专业小说、电影、广播电视节目等创作主体。这类创作主体自然希望其作品能以权利交易的方式实现被利用与传播——尤其是作品创作的投资人——由此获取可观的经济利益。然而,其作品不一定能以交易的方式实现被利用与传播,因为作品能否被交易,与创作主体的影响力密切相关。对于已经具有一定市场影响力的强势权利人而言,其作品具有明显的市场优势地位,诸如文学领域的畅销书作家、音乐领域的知名词曲作者以及电影界的知名导演等,其自然可以实现作品以自主交易的方式进行被利用与传播的愿望,以获取其所认可的经济利益。即便如此,由于创作主体的影响力,又与其先前作品的被利用与传播程度密切相关,作品被利用与传播程度越广泛,创作主体的影响力就越大。如一个在文学领域具有很强影响力的作家,并不必然反对其作品在九年制义务教育教材汇编中被使用;一个在诗歌领域具有很强影响力的作者,亦不必然反对其作品被电视台广播,尤其不会反对在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电视台进行广播,比如我国的中央电视台。至于在某个领域未形成影响力的创作主体,其作品不具备市场交易优势,故难以得到交易机会。由于作品可以因为更多的被利用与传播机会而增加知名度,从而提升该创作主体的影响力,以使之将来可以进入具有影响力的创作主体行列并提升未来作品的市场地位。可以想象,一个没有任何知名度的词曲作者,是何等的希望知名歌星表演其作品并被具有强影响力的电视台播放;一个在文学领域没有任何影响力的作者,是多么渴望其作品被法定许可汇编进入九年制义务教育规划教材。因此,对于经济利益需求型创作主体而言,无论其在相关领域是否具有影响力,其创作目的的实现都依赖于其作品的被利用与传播。正因如此,即便是已经具有很强影响力的创作主体,对于可以扩大其影响力的作品被利用与传播,并不会必然反对。而对于在特定领域没有任何影响力的创作者,任何保留其署名方式的作品被利用与传播或许都在受欢迎之列。
前述经验分析表明,无论是非经济利益需求型还是经济利益需求型的创作主体,尽管其创作的目的或者直接为经济利益,或者为了娱乐、为了学术或者纯粹是为了表达,但其目的的实现却依赖一个相同路径——即作品的被利用与传播。换言之,作品被利用与传播的机会越多,作者创作目的实现的可能性就越大。
三、法定许可增加作品被利用与传播的机会
如前所述,无论何种需求类型的创作主体,尽管其创作目的各异,但其实现创作目的的路径却并无二致,均为作品的被利用与传播。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实际上创造了作品的被利用与传播方式,即在授权使用之外,增加一种无须获得授权却需支付合理报酬的被利用与传播方式。此外,法定许可还具有防止作品被利用与传播机会减少的功能,本质上亦是增加作品被利用与传播的机会。
(一)法定许可创造作品被利用与传播的机会
对于非经济利益需求型的创作主体而言,由于其本身目的不在于以交易的方式实现作品的被利用与传播,自然无须“充分协商”的权利,甚至难以承受“充分协商之重”。试想,如果一位学术著述颇丰的学者,对其作品转载、摘编、编入教材、广播等都需要与该作者进行单个交易,协商的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作品被利用与传播的报酬及其支付方式、被利用与传播范围、被利用与传播目的、违约责任、诉讼管辖等,估计该学者还必须专门配备一个秘书帮其处理此类工作,否则,其创作时间将消失殆尽。当然,问题的关键在于,该类作者并不愿意通过协商以换取作品的被利用与传播,“自由协商”自然就成为该类作者的“不可承受之重”。因此,非经济利益需求型的创作主体对其作品利用意愿的经验分析至少可以说明,法定许可制度实质上增加了作者作品的被利用与传播机会。
国家版权局在《著作权法》(修改草案)说明中认为:“从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二十年的实践来看,基本没有使用者履行付酬义务,也很少发生使用者因为未履行付酬义务而承担法律责任,权利人的权利未得到切实保障,法律规定形同虚设。”⑦著作权法定许可废除论者据此来作为支持其观点的论据之一。然而,“也很少发生使用者因为未履行付酬义务而承担法律责任”的结论,极可能是因为鲜有权利人主张权利。如果权利人都不主张权利,使用者如何承担法律责任?如果权利人主张权利,在法律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又怎么可能“很少发生使用者因为未履行付酬义务而承担法律责任”呢?由此可知,在权利人有权依据法律规定主张报酬的情况下,仍很少有主体主张报酬。这至少可以表明,权利人非但不反对,甚至是愿意免费提供他人基于法定许可制度的利用。正如郑成思教授在论证作品转载的法定许可时认为,在一般情况下,作者的作品能够被更广泛地传播(即被多家报刊转载),自己也能够获得更多的报酬,他们是不会反对的。[8](P356)
法定许可为创作主体创造作品被利用与传播的机会,权利人并不反对这种限制其充分协商权利的被利用与传播方式。这一结论与法律经济学的研究结论一致,法律经济学有关因为人们的偏好差异而影响私有权赋予效果的结论认为:“如果人们的偏好是有冲突的,私有权或任何其他形式的所有权对任何人都不意味着更多的机会。”[9](P3)对于著作权而言,作品的被利用与传播便是权利人的机会。尽管著作权法选择将一种私权赋予权利人,由于权利人创作作品的偏好完全不同,私权的赋予并不意味着作品被利用与传播机会的增多。然而,法定许可却实在地创造了作品被利用与传播的机会,即作品增添了一种无须授权但需要支付费用的利用渠道,实际上增加创作主体创作目的实现的机会。若无法定许可,使用人会因为怵于侵权责任承担的风险而不再被利用与传播作品,作品被利用的机会必然减少。甚至会出现因作品的利用需求无法得到合理的实现和供给,而形成权利人作品被利用与传播的“错过的市场(missing market)”⑧,实际上,法定许可制度完全符合著作权法的变革应该“向创作者承诺其作品有机会向其意欲的读者传播”⑨的基本原则。
(二)法定许可预防减少作品被利用与传播的机会
除却前述防止因为“错过的市场”而导致的被利用与传播机会减少之外,法定许可制度因其降低交易成本与预防垄断的功能,可进一步防止作品被利用与传播机会的减少。必须明确的是著作权法定许可制度设计的初始价值就是降低交易成本与维护竞争秩序,并非前述学者所认为的“无理论上充足的依据”。著作权制度本身是顺应出版产业发展的需求而诞生:英国在1695年之前,书商是依赖《特许法》所授予的出版特权进行出版审查,并赋予其对印刷业的搜查、没收和罚款的权力,以维护书商在出版产业的垄断利益。随着1695年《特许法》的废除,书商失去了出版特权的庇护,开始遭受盗版之苦,在诉求恢复出版权特权失败之后,转而借助作者利益与图书财产权的名义寻找突破口,并在1710年的《安妮女王法》中得以作者权利保护的方式实现。[10](P21)
相关产业发展亦顺应著作权制度的变革逻辑。首先,针对新传播技术分离出的新产业,以著作权为基础设立的产业便寻求在著作权法上增加新的权利。当音乐产业从出版产业分离出来之后,著作权法的回应是设立表演权;广播电视产业出现之后,著作权法的回应是设立广播权;互联网产业出现之后,著作权法的回应是设立信息网络传播权。其次,新的传播技术所催生的新产业必须与著作权的权利人进行权利交易方可实现其可持续发展。如果完全采取单个授权的交易方式,新产业的发展必然存在两种可能的障碍:(1)单个授权交易导致交易成本高昂,尤其是需要海量使用海量作品的新产业,如广播电视产业。如果不在制度上对单个授权的交易方式进行调整,将导致新产业因为交易成本高昂而难以为继。因为“一个作品接一个作品”以及“一个权利人接一个权利人”的交易方式必然使交易成本过高[11](P38),从而导致“版权市场或者不能形成,或者功能失常”[12](P149)。难以想象,若广播电视产业无广播权法定许可的护佑,现今会处于一个什么状态。(2)不受任何限制的单个交易,可能导致特定的主体因为获得大面积权利人的独占授权而在新产业里产生行业垄断。美国国会就担心一个生产钢琴卷纸名为“Aeolian”公司的音乐独占许可授权计划将导致“巨大的音乐垄断”⑩,其不希望一个持有大量知识产权的公司统治一个国家的艺术方向。[13](P97)为消减或降低交易成本,防止可能出现的行业垄断,以期不阻碍新产业的可持续发展,著作权制度便在不同的领域创立了法定许可或强制许可制度,比如音乐领域、广播领域等都有特定的法定许可或强制许可制度。当然,不同的国家根据本国产业发展的状况,在法定许可的领域选择会有所不同,比如我国因为传媒产业中报刊数量庞大,应对报刊市场的细分需求,为报刊转摘设立了专门的法定许可。因此,降低交易成本与预防垄断,是法定许可制度真切的理论依据与初始价值。
除此之外,法定许可还产生一个不可忽视的间接价值,即其降低交易成本与预防垄断的副作用——预防作品被利用与传播机会的减少。其一,若无法定许可制度,单个协商获取授权的高昂交易成本,必然会阻碍作品利用交易的达成,导致作品丧失许多被利用与传播的机会。而法定许可制度其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价值,防止了因为交易成本过高而减少作品的利用机会。其二,若无法定许可制度,特定领域单个主体获取大面积权利人的授权,从而产生相关行业的垄断。随后,该垄断主体作为作品利用交易的强势主体,将形成大面积作品利用的垄断权利。在利益驱动下,其必然会选择通过较少作品交易以获取更高的利益,从而减少了作品被利用与传播的机会。而法定许可制度因为预防了垄断,从而预防了因为垄断导致作品被利用与传播机会的下降。
综上,法定许可不但为作者创造了一种无须授权却需付费的作品被利用与传播途径,从正面增加了作品被利用与传播的机会;而且因其降低交易成本与预防垄断的功能,防止了作品被利用与传播机会的减少,反向增加作品的被利用与传播机会。因此,法定许可本质上增加了作品的被利用与传播机会,增加了作者实现创作目的的可能。
四、作品传播中心化与去中心化混合模式时期法定许可的制度调适
互联网时代,作品的传播实现了从权利人直接到用户或在用户之间传播,无须依赖传播中介,呈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然而,依赖传播中介进行作品传播的中心化模式,非但未退出历史舞台,反而依然占据着非常重要的地位,故法定许可制度应该予以存续。但去中心化的传播模式已经形成,即作品的权利人可以无须传播中介而自己将作品传播到用户,确实无须法定许可所增加的作品被利用与传播机会实现其创作目的。从而,一方面,在作品中心化传播模式中,著作权人依然需要法定许可制度所增加的作品被利用与传播机会以实现其创作目的;另一方面,在作品去中心化传播模式中,著作权人则无须法定许可制度便可实现作品被利用与传播,从而实现其创作目的。在这种状况下,法定许可制度需要调适以适应当前作品传播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混合模式。
(一)当今处于作品传播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混合模式时期
传统媒体时期,由于作品传播技术、设备、制作等方面的高成本,包括权利人在内的个人一般难以成为传播中介,作品的被利用与传播必须通过诸如出版机构、广播电台、电视台以及电影制作机构等传播中介的桥梁作用,方可从权利人传播到用户,此即作品传播的中心化模式。传播中介与权利主体之间关于作品被利用与传播的交易,如果以单个授权交易的方式必然导致高交易成本以及单个传播中介因获得大量作品授权而产生行业垄断。正是基于降低交易成本与预防行业垄断,法定许可制度才得以应运而生。但互联网时代,作品却可以通过去中心化的方式进行被利用与传播,即作品可以绕过传播中介直接向用户传播,亦可以在用户之间传播,此即外国学者所谓的“去中心化”和“去阶层化”的网络用户之间共享[6](P278)。理论上,作者与用户可以通过互联网实现单个磋商的方式完成权利交易,并且通过拆封合同(shrink-wrap license)与点击合同(clickwrap licenses)等互联网线上的格式合同,大幅度降低权利的交易成本。即便是需要大规模使用海量作品的专业媒体,亦可通过互联网实现低成本交易。单从此方面看,以降低或消除高交易成本为存在基础的法定许可制度,似乎不再具有继续存在的价值。正因如此,有学者提出“应在已经具备著作权市场协商机制的领域废除法定许可的适用”[2](P80)。
然而,无可否认的是,以传统媒体技术为基础的产业并未退出这个时代,即中心化传播仍是这个时代作品的主要被利用与传播模式。无论纸媒、非交互方式的广播电视、电影院线以及传统的出版产业都依然在社会占据重要一席,就是很好的例证。加之传播中介的国家管制与人类生活的惯性,亦必然有部分公众选择这种中心化作品传播模式下的媒介获取信息,这种传播模式依然具有广阔的市场。比如,欧盟对于数字单一市场版权规则现代化的影响评价报告认为,尽管因为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给电视的方式带来了改变,但传统电视依然既是经济上的、亦是观众娱乐与信息的主要来源。在2014年,欧盟28个电视台的市值高达860亿欧元,同年,电视内容(包括直播与时间转换的观看)在六个国家(法国、西班牙、德国、意大利、英国和美国)中占到96%的视频消费。⑪这足以说明,作品中心化的传播模式及以此为基础的传媒产业依然在当今时代占据重要一席。故互联网所带来的这种去中心化传播只是当今时代作品的一种被利用与传播模式,而非全部,作品的被利用与传播至少还是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混合模式。
(二)法定许可制度应允许权利人“声明保留”
去中心化是当今这个时代一种作品被利用与传播的模式,即无须传播中介,直接将作品传播到利用主体,也就无须法定许可制度降低交易成本与预防垄断。对于经济利益需求型并具有优势市场地位、希望作品可以通过充分协商的方式实现作品的被利用与传播的主体而言,可以更加直接地实现作品的被利用与传播。在这种情形下,应该给予权利主体更多的选择。在制度的调整上,应该允许权利人以声明的方式退出该种限制。实际上,我国2010年《著作权法》所规定的法定许可中,除作品(含录音制品)广播的法定许可不允许权利人事先声明保留之外,其他三种法定许可都允许权利人声明保留。我国有学者将这种“声明保留”类比美国谷歌数字图书馆案中所提出的“选择-退出”机制,认为我国《著作权法》法定许可的“选择-退出”制度具有优越性。[14](P93)虽然在谷歌数字图书馆案中谷歌公司所提出的“选择-退出”只是一种私人主体的倡议,而我国《著作权法》所规定的“声明保留”属于立法上的制度,但两者之间产生的效果并无不同。但我国《著作权法》法定许可制度中允许权利人“声明保留”的规定却在学术界遭受诟病,认为“大量的作者或出版商已频繁使用其声明保留权,使得该三种‘法定’许可使用制度完全形同虚设”[15](P280)。此种无实际调研支撑的结论不可能正确。如前所述,不同创作目的的主体具有实现目的的相同路径即作品的被利用与传播。与有体财产不同,作品著作权的价值取决于作者的影响力,而作者的影响力又取决于作者先前作品的被被利用与传播状况,故作品的被利用、传播的频次与该作者的影响力成正相关关系。我国2010年《著作权法》颁布后,一直未出现因“声明保留”而致教材汇编、报刊转载以及音乐录制领域无作品可供法定许可之用的状况。如果当时修订的《著作权法》规定广播法定许可亦允许权利人“声明保留”,更不会出现因为权利人大面积“声明保留”而致广播法定许可制度中无作品可供广播的状况。因为基于作品被利用与传播作为不同创作目的实现的相同路径,权利人愿意接受甚至是欢迎法定许可实际上所增加的作品利用渠道;况且,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广播电视依然是具有主导地位的作品传播平台,该平台对权利人作品及其权利人本身影响力的扩大,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大部分权利人对于作品被广播电视的被利用与传播求之不得,不可能出现权利人大面积地选择“声明保留”。
具体而言,我国2010年《著作权法》法定许可制度可按照如下方案予以调整:(1)继续保留第23条所规定的教材汇编的法定许可、第33条第2款所规定的报刊转载的法定许可以及第43条第3款所规定音乐录制的法定许可,无须进行调整。因为该三种类型的法定许可,可增加作品被利用与传播的机会,而且其所规定的“声明保留”,为权利人在去中心化传播模式中自行利用作品提供了机会,完全契合当前中心化与去中心化混合传播模式中著作权人实现创作目的对法定许可的不同需求;(2)第43条第2款所规定的已出版作品广播的法定许可,应该增加“声明保留”的规定,应调整为:“广播电台、电视台播放他人已发表的作品,可以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但应当支付报酬。著作权人声明不许使用的不得使用。”从而使其既契合当今作品传播中心化模式中实现其创作目的对法定许可制度的需求,又契合作品传播去中心化混合模式中著作权人无须法定许可便可实现其创作目的的客观实际;(3)删除第44条播放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规定,因为我国《著作权法》只赋予词曲作者广播权,表演者与录音制作者并不享有广播权,对于一个录音制品,法定许可实质上也只是对音乐作品词曲作者广播权的限制,第44条也只能对音乐作品词曲作者表演权与广播权的限制。其与第43条第2款对已发表作品广播的法定许可,区别在于:如果是通过播放录音制品对音乐作品广播权的法定许可,必须是已经出版的录音制品;如果不是通过播放录音制品对音乐作品广播权的法定许可,比如找乐队现场演奏,则只要求该音乐作品已经发表。对于表演者与录音制品制作者而言,由于均无表演权与广播权,这种限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对于音乐作品的词曲作者而言,都是对其广播权的法定许可,这种区别亦不具有实际意义。至于该条所规定的“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由于著作权是权利主体的私权,当事人自然可以另行约定,即便是立法未作该种规定,也不影响当事人的另外约定。因此,“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的规定并不具有实际意义。而该条所规定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主要指法定许可制度中报酬确定问题由国务院另行规定。然而,并不仅仅是广播权法定许可制度,《著作权法》中所有类型法定许可制度中的报酬确定都需要科学合理的配套机制。删除“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表述,并不影响为所有类型的法定许可确定科学合理的机制。当然,删除之后,应该在《著作权法》中单独规定一条,明确由国务院为所有类型法定许可的报酬确定制定办法,以为报酬的确定提供科学合理的机制。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2020年修订《著作权法》时,对法定许可制度的调整未能按照上述方案进行,除删除第44条播放录音制品法定许可的规定以及继续保留作品转载法定许可的规定具有合理性之外,在第25条教材汇编的法定许可中删除权利人可以拒绝的“除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的表述,以及未能在规定作品广播法定许可的第46条第2款增加权利人可以拒绝的“除作者事先声明不许使用的外”的规定,都是法定许可制度本次调整的遗憾。这些遗憾,剥夺了权利人选择作品利用方式的权利,应在《著作权法》未来的修订中予以调适。此外,值得肯定的是,2020年修订《著作权法》第45条,为录音制作者在其录音制品用于有线或者无线公开传播,或者通过传送声音的技术设备向公众公开播送具有获得报酬的权利,尽管该条并不采取法定许可制度的固定表达模式——“无须许可,但需支付报酬”,但本质上与法定许可对录音制作者报酬权的保护并无二致。
五、结语
尽管互联网与数字技术改变了作品的传播方式,但由于传播中介的国家管制与人类生活的惯性,必然有部分公众依然选择通过传统媒体时代中心化作品传播方式下的媒介获取信息,且这种状态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继续存在。法定许可创造一种无须授权只需要支付报酬的作品被利用与传播方式,增加了作品被利用与传播的机会,其降低作品传播中心化模式下,权利交易成本与预防垄断所附带产生了预防作品被利用与传播机会被减少的作用,实质上增加了作品被利用与传播的机会。故在当今作品传播中心化与去中心化混合的时代,法定许可具有继续存在的价值。但去中心化已经成为当今作品传播的一种模式,权利主体应该有权选择绕过传播中介的模式实现作品的被利用与传播,使经济利益需求型创作主体中具有市场优势地位的权利主体,可以拒绝法定许可,从而选择充分协商的方式实现其作品的被利用与传播。为此,法定许可在具体制度上的调适,应该允许权利人通过“声明保留”的方式退出法定许可。2020年最终修订通过的《著作权法》在法定许可制度的调整方面,既有合理的地方,亦有遗憾之处。这些遗憾,剥夺了权利人选择作品被利用与传播方式的机会,需要《著作权法》在未来的修订中予以调适。被利用与传播
注释:
①该草案第46条规定:“录音制品首次出版三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
②参见《版权局回应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两大争议》,http://finance.people.com.cn/GB/17618862.html。
③参见《音著协建议删除著作权法草案部分争议条款》,http://www.chinanews.com/fz/2012/04-23/3839351.shtml。
④参见《唱工委:版权局代表无视音乐人呼声 发表呼吁书表不满》,http://industry.caijing.com.cn/2012-04-26/111829501.html。
⑤草案第二稿还删除了录音制品播放的法定许可(第44条)以及教材汇编法定许可与报刊转摘法定许可中权利人“声明保留”的规定。
⑥比如报刊转载法定许可导致了“超国民待遇”应该予以取消,该种观点主要基于根据《实施国际著作权条约的规定》第13条的规定,报刊转载外国作品不适用有关法定许可的规定。
⑦参见国家版权局《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简要说明》(2012年3月)。
⑧国外学者用来描述孤儿作品的利用现象,由于孤儿作品无法查询到权利主体,使孤儿作品的利用需求无法得到合法的供给,从而产生孤儿作品利用的“错过的市场”。See Dennis W.K.Khong,Orphan Works,Orphan Works,Abandonware and the Missing Market for Copyrighted Goods,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aw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Volume 15,Issue 1,1 March 2007,p.54.
⑨美国“版权原则规划:版权变革的方向”的项目研究认为,应将“向创作者承诺其作品有机会向其意欲的读者传播”作为现代版权法变革的一项基本原则。
⑩See Recording Industry Assoc.v.Copyright Royalty Tribunal,662 F.2d 1,17 (D.C.Cir.1981),at 4.
⑪See IHS Technology,Current market and Technology Trends in the Broadcasting Sector,May 2015,p.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