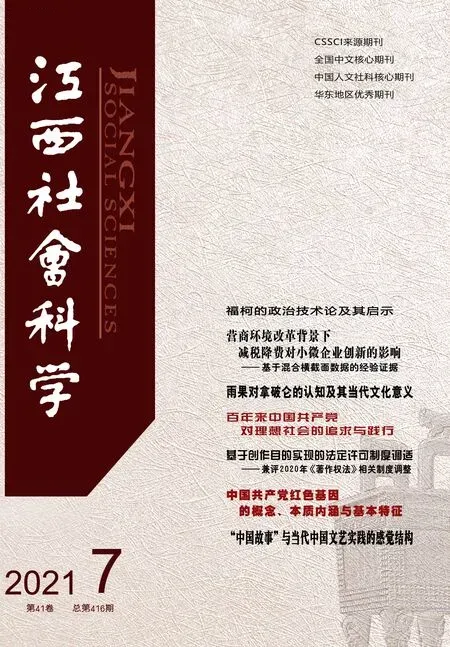不断挖掘:谢默斯·希尼诗歌中的沼泽与文化记忆
2021-11-29袁广涛
■袁广涛
沼泽是贯穿谢默斯·希尼创作生涯的一个重要主题,并被赋予个人、家族、民族和历史等不同层面的象征含义。作为家族世居之地的沼泽代表了个人和家族的记忆,是诗人的代际之地;作为考古场域的沼泽代表了对往昔知识的好奇与探究,是思古的回忆之地;上演杀戮仪式的沼泽象征了诗人的民族记忆,成为诗人的纪念之地;而当诗人反思自己赋予杀戮以民族政治价值,转而揭示暴力造成的伤口时,沼泽则变成了创伤之地。这种多层次、多角度的描写赋予沼泽平实的生活感、森然的仪式感、厚重的历史感、精确的抒情性,使诗人能够借助这片风景探索自我和群体、诗歌和社会、记忆和现实的关系。
对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Seamus Heaney,以下简称希尼)而言,记忆是一个持久的主题和写作动机。而在触发记忆的事物之中,沼泽的意义最为丰富。就个人层面而言,希尼家乡的托纳沼泽可谓是诗人的成长之地;在国家和民族意义上讲,沼泽是爱尔兰的典型地理特征,其中蕴藏的泥炭曾是爱尔兰人的主要燃料,象征着爱尔兰民族历史;在文化方面,因为能隔绝空气避免氧化,沼泽保存了丰富的历史遗物,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记忆库。对希尼来说,书写沼泽就是挖掘记忆。在《感觉进入文字》一文中,诗人把沼泽和记忆、民族意识联系起来[1](P54-55),而诗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创作的一系列以沼泽为主要题材的诗歌,尤其是诗集《北方》中的《沼泽女王》《格劳巴勒男子》《惩罚》《奇异的果实》《亲属关系》等,被统称为“沼泽诗”。然而,希尼的另外一些早期作品,如《挖掘》《沼泽橡》《图伦男子》以及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图伦》和《春天的图伦男子》等,同样构建了诗人与沼泽之间的精神关联,使沼泽成为几乎贯穿希尼的创作生涯并被不断赋予新的意义。
对希尼诗歌中沼泽意象的评论大多认为通过对沼泽及其发掘物的沉思,希尼把历史、神话和现实交织在一起。一方面,“沼泽诗”因为其对历史的挖掘和对现实的反思而广受赞誉;但另一方面,它们也因为书写了古代献祭仪式中的牺牲者而被批评为“把暴力美学化”。例如,齐亚兰·卡尔森(Ciaran Carson)将希尼称作:“暴力的桂冠诗人——神话制造者,书写仪式性屠杀行为的人类学家。”[2](P84)埃德娜·朗利(Edna Longley)认为希尼在诗歌中美化了暴力和历史。[3](P83-84)针对这些政治性的批评,海伦·文德勒(Helen Vendler)反驳说:“把抒情诗读成论说文是一个根本性的哲学错误。”[4](P9)并辩称希尼的这些诗讨论的不是教派、阶级和政治立场的问题,而是呈现了“一种可以追溯到多个世纪以前的在文化上对暴力的普遍认同”[4](P5),海伦·文德勒试图将讨论的焦点从政治转移到文化上。但是,文德勒的辩护没有改变这些诗的现实指涉,也不能避免读者阅读时的现实联想。在散文《地方与移位:北爱尔兰近期诗歌》中,希尼承认虽然诗歌可以是独立王国,但诗人却不能免除政治责任,而读者对诗歌的政治性解读“也是艺术家努力的一种延伸或投射”[5](P12),因而具有自然的合法性。由此看来,对沼泽意象的政治性解读似乎是合理的途径。但是,笔者认为,要全面理解希尼所说的作为记忆象征的沼泽,我们需要一个更为开放的视角,即把沼泽看成在诗人创作生涯中一个持续的、意义不断增值的题材。
笔者将借用德国学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的文化记忆理论来探讨沼泽在希尼诗学和诗歌创作中的多层次含义。阿斯曼在《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以下简称《回忆空间》)中讨论了文字、图像、地点等作为记忆媒介的性质和功能,其中,她把地点概括为代际之地、纪念之地、回忆之地和创伤之地。不同的力量把这些地点和记忆联系起来:“在代际之地上,这种力量来自于活的人与死者的亲属链条;在纪念之地上,这种力量来自于重新建立和重新传承的讲述;在回忆之地上,这种力量来自于一种纯粹好古的历史兴趣;在创伤性地点上,这种力量来自于一个不愿意结疤的伤口。”[6](P392)在希尼的诗中,作为记忆对象和记忆载体的沼泽,在这四个不同的层面上被赋予个人、家族、民族和历史等不同含义。
一、代际之地
阿斯曼在《回忆空间》中曾以希尼为例来阐发文化记忆的理论:“爱尔兰诗人谢默斯·希尼把文学创作看作是个人记忆和文化记忆的一种工作……他也用挖掘的图像描述了这种记忆工作。”[6](P182)阿斯曼拈出的“挖掘”正是希尼写作行为的象征:在《北方》这首诗中,希尼把创作形容为“躺在/文字的宝藏之中,深挖/被犁过的大脑的/沟回和微光”,仿佛写作就是用文字来探索和表达意识中的层层记忆。希尼的第一部诗集《一个自然主义者之死》的开卷之诗就以《挖掘》为题。如果对希尼来说,“诗歌是一种挖掘,为发现地下埋藏之物而进行的挖掘”[1](P1),那么,《挖掘》就是诗人掘入地下的第一铲。在这首也许是希尼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中,诗人目睹父亲在窗下花圃中铲土,追忆起多年前父亲在田地里挖土豆以及更早些时候祖父在托纳沼泽里挖掘泥炭:“我的祖父一天里在托纳沼泽/挖的泥炭比任何人都多……(他)利落的又切又割,把草泥/抛到肩后,不断向深处/为了好泥炭。挖掘。”这些对祖辈们的挖掘的回忆让作者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也是挖掘,是以笔为铲,对家族的记忆挖掘:“在我的食指和拇指之间/夹着粗短的笔。/我将用它挖掘。”在《挖掘》中,如同生产食物的田地,提供燃料的沼泽也是支撑家庭生活的地方,与家族历史保持着固定而长期的联系,构成了阿斯曼所说的代际之地:“代际之地的重要性在于产生于家庭或群体与某个地方长期的联系。由此产生了人与地点之间的紧密关系:地点决定了人的生活以及经验的形式,同样人也用他们的传统和历史让这个地点浸渍了防腐剂。”[6](P356)
在希尼其他涉及沼泽的诗篇中,也有不少对家族历史的追溯。例如,在《沼泽橡》中,希尼描写了一段被从沼泽中挖出并用作房屋拱肋的沼泽橡:“一个马车夫的战利品/劈成了屋椽子/一个挂满蜘蛛网、黑色的、/风干已久的供肋”。橡木长期浸没、保存在沼泽地中,无氧潮湿的环境赋予它坚硬的质地,是爱尔兰人常用的建筑材料。诗中茅草屋顶下的这段橡木早已成为房屋的一部分,而古老的房屋唤醒了诗人记忆中祖先的形象:“那些蓄着胡子的死者,那些/背箩筐的人。”所以,沼泽橡见证的是家族的历史,唤起的是作者对已故先辈的回忆。《亲属关系》的标题即指明了诗人和沼泽的密切联系。在此诗开篇,诗人将沼泽称为自己的“本源”(origins),并以狗对荒野的记忆来比喻他对沼泽的眷恋是家族遗传的原始本能,“我穿过本源之地/如厨房草垫上的/一只狗/回味着荒野的记忆”。随后,诗人又以柳树的形象来说明沼泽是其根之所系,“我生长于沼泽之上/像一棵垂柳/弯向/引力的欲望”。弯腰的柳树呈现的是一种投向沼泽怀抱的姿态。这首诗还回忆了诗人幼时随舅公休伊运送泥炭的经历。希尼曾经自述在其心中,休伊代表了希尼家系的始祖。[7](P31)此处,诗人把休伊想象成“马车之神”,与其同行让年少的诗人感受到“男子汉的骄傲”。这种在家族祖辈荫护之下从少年到男子汉的成长,把作为代际之地的沼泽以及寄居在沼泽地上的一代代人紧紧联系在一起。
二、回忆之地
如果说《挖掘》《沼泽橡》和《亲属关系》中的托纳沼泽象征诗人的代际之地,更多的沼泽诗却聚焦于北欧的沼泽。其中,多数以北欧沼泽出土的铁器时代遗留下来的尸体为题材。这些异国沼泽不再象征个人成长、家族兴衰的连续性。阿斯曼认为被中断的历史在废墟和残留物中获得了它的物质形式,那么,在希尼诗中那些从北欧沼泽中发掘出的尸体也可以被看作代表了被中断的历史。但这种残留物和《挖掘》中的土豆和泥炭以及《沼泽橡》中的橡木明显不同:土豆和泥炭是食物和燃料,沼泽橡木被用来建筑房屋,两者都参与并延续了生活。而被发掘出的原始遗体却代表了早已逝去的、无关眼下生活的时代。《图伦男子》描写了在日德兰沼泽发现的一具男尸。此人在铁器时代作为献给土地女神的祭品被勒死,在数千年后被挖泥炭者发现,被考古学家发掘,被博物馆收存。它提供了关于远古文明的历史知识,但与当地的生活却似乎漠不相关,至多吸引了一些参观者:“不懂当地语言,/只能望着/乡下人指点的手。”因为空间的距离,日德兰沼泽无法充当希尼的代际之地,而是一个真真实实的考古场所。而希尼创作沼泽诗,尤其诗集《北方》中的沼泽诗的灵感来自于《沼泽人》这本考古学著作。希尼曾经自述阅读这本书就好像为自己打开一扇门。[7](P194)研究者也注意到了希尼与考古学的关系,以至于海伦·文德勒干脆将其专著《Seamus Heaney》中讨论《北方》的一章命名为“考古学”。在这一章中,文德勒把《北方》之前的作品所涉及的沼泽出土物和《北方》中的相区别,认为前者或是友善的家常之物,或是有教益的生物演变奇迹,而后者则是献祭等人类暴力的牺牲品。[4](P38-39)在这些以出土物为题材的沼泽诗中,沼泽首先是考古场所。
事实上,爱尔兰的很多文物都是从沼泽中发掘出来的。沼泽甚至被戏称为爱尔兰的国家博物馆。而希尼本人受到在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后来成为考古学家的汤姆·德拉尼(Tom Delaney)的影响,一度对考古学颇感兴趣。1972年,希尼从北爱尔兰移居爱尔兰共和国时,都柏林正经历维京遗址发掘的考古热潮。诗人受此影响,在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中采用了很多考古学的术语和主题,而《北方》诸诗中的沼泽化身为考古的场域,代表了一种对历史知识的理性探究,沼泽于是就成了阿斯曼所称的“回忆之地”。在《回忆空间》中,阿斯曼如此界定“回忆之地”的特征:“如果一个鲜活的传统的回忆和传承链条断裂的话,记忆之地也会随之变得不可读。但是全新的阅读方式由此也会都变得活跃起来。好奇会代替虔敬出场……历史研究的精神发展起来,这是以传统的断裂以及遗忘具有规范意义的过去为代价的。”[6](P366-377)作为回忆之地的沼泽,不是连接了延绵的个人生命和家族生活,而是通向了博物馆,因为考古出土物被移存到了博物馆中。阿斯曼提出过关于博物馆的悖论:“出于保留原真性的目的对这些地点进行的保存工作不可避免的意味着丧失原真性。”[6](P386)博物馆所储存的记忆是抽象的,失去了在泥土之下的原真性。所以,在考古学意义上讲,沼泽脱离了鲜活的生活和生命,呈现与现代生活天悬地隔的远古文明,代表了历史连续性的断裂。
三、纪念之地
尽管作为考古场域的沼泽是希尼沼泽书写的重要维度,但从本质上讲,考古学家以真实性为旨归,而所谓“诗可凿空”,诗人可以虚构场景和使用修辞。所以,虽然希尼在《图伦男子》中写道:“有一天我要去奥胡斯/去看他那深棕色的头”,但他仅是在想象中流连于那些“用来杀戮的古老教区”,即古代进行献祭仪式的日德兰沼泽,而不是位于奥胡斯的博物馆,这说明,他在意的是沼泽的诗学意义。阿斯曼认为回忆之地通过想象和叙事,可以变成纪念之地[6](P357)。纪念之地虽然也代表历史的中断,但可以通过虔敬的情感、想象的重构以及故事性的叙述重新连接古今,使人们重建记忆并获得身份认同。例如,在《图伦男子》的开始,说话人以虔诚的口吻做出朝圣的誓言,将沼泽神圣化。如果图伦男子的献祭能延续大地的繁殖力,那么,诗人祈求他催发被英国武装力量“黑棕队”所杀害的一家人的“散落的血肉”和被警察残杀的天主教四兄弟的“不言自明的皮肤和牙齿”。希尼所用的“催发”(germinate)一词与第二节中所描写的图伦男子腹中残留的“种子”(seeds)相呼应,在语法上也承接爱尔兰暴力冲突受害者的血肉、皮肤和牙齿,后者如同种子可以生出新的生命。种子的意象呼应了希尼为纪念1798年“爱尔兰人联合会起义”而作的《献给短发党人的安魂曲》一诗。在这首诗中,起义牺牲者衣兜里的麦粒发芽、生长:“到八月,大麦自坟墓里长出”。所以,与《献给短发党人的安魂曲》一样,《图伦男子》肯定了暴力和牺牲在复活民族意识方面的政治功能。希尼在记忆的维度中将古代与现代、神话与现实连接、组合和重叠。
查尔斯·泰勒(Charles Taylor)在《世俗时代》一书中认为,在人类文化的开端,暴力和宗教是紧密联系的:战争或献祭中的仪式使暴力神圣化;虽然之后的高级宗教不提倡暴力,但神圣化暴力会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而且宗教仍会借助暴力维持自身的纯洁性,会和好战的世俗意识形态杂糅在一起,形成由教派界定的民族主义。[8](P788-789)20世纪六七十年代被政治、民族和宗教纷争割裂的北爱尔兰完美说明了“由教派界定的民族主义”。而在希尼诗中,本是博物馆展品的图伦男子成了部族杀戮的隐喻,赋予现代暴力以仪式感和神圣感。仪式化死亡是西方文学尤其宗教文学中常见的主题。徐贲认为:“在西方文化传统中,死亡常常被想象和叙述为通往解救的一个阶段。死亡因此成为一种仪式。经由这种仪式,人生的无目的转化为有目的,混乱转化为秩序,不公正转化为公正……死亡还因此成为一种奉献和牺牲。忠于某种理想的人为了替他人守护这种理想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9](P268)所以,希尼在诗中借助古代献祭来解释、定义当代的社会暴力,而沼泽被用来守护民族理想,建构集体意义,变成了阿斯曼所说的纪念之地。
事实上,希尼的沼泽诗歌从一开始即牵连了民族观念和集体记忆,如《挖掘》中,先辈们在土豆田和沼泽地中的挖掘可以代表爱尔兰民族的生存史;在《挖土豆》中,诗人描写了农田上人们收获土豆的场景,同时回忆起1845—1849年爱尔兰的土豆瘟疫造成的大饥荒,那些濒死的爱尔兰人被刻画成“活得、目盲的头骨,安放在/乱七八糟的骨架上”,他们“在45年的时候翻遍大地/吞咽枯萎的土豆然后死去”,由此希尼对爱尔兰民族历史进行了想象,并且使之进入当下的记忆:“发臭的土豆弄脏了大地/……/在现在土豆挖掘机工作的地方/你还能闻到持久的创痛”。所以,当沼泽变成纪念之地时,它代表的是爱尔兰民族意识。在《沼泽地》中,诗人试图强调爱尔兰的独特性:“我们没有大草原/在傍晚分切一轮落日”,此处的“prairie”指的是北美大草原,是美国西部神话的地理象征。而诗人认为,作为相对狭小的岛国,爱尔兰需要构建一种不同的神话。不同于美国的开拓者在广度上的拓展,爱尔兰神话需要在纵深的方向上挖掘:“不断朝内/和朝下面敲击”。所以,希尼的“挖掘”意象不仅指涉个人身份、家族历史,而且是对爱尔兰民族意识的探索。希尼通过将沼泽这一自然空间塑造为纪念之地来表达民族认同和彰显民族意识。
四、创伤之地
如果说纪念之地对于回忆者有建构民族身份认同的意义,同样与献祭、杀戮、迫害、侮辱等苦难事件相关的创伤之地则因为良知、道德或社会禁忌,成了难以面对、无法言说的东西。[6](P380)《惩罚》一诗即表达了面对苦难而无能为力的挫折感和创伤感。诗中描写了一位因通奸而被沉入沼泽处死的少女。希尼使用了一个取自《约翰福音》的典故,众法利赛人要投掷石头处死一个通奸妇人,而耶稣却怜悯并宽恕了她。而诗人却不得不承认自己缺乏耶稣的道德勇气:“我几乎爱上你/但知道自己会投下/沉默的石头。”同样,当目睹一些当代北爱尔兰女孩因为与英国士兵交好而被爱尔兰共和军公开惩罚时,“我”理解这是“严格的/部族内部的复仇”,所以“默许文明的义愤”(connive in civilized outrage)。此处的“connive”意思是“纵容、放任、同流合污”之意,诗人的自责不言而喻。由此看来,这首诗如同弗洛伊德·柯林斯(Floyd Collins)所说的,“是一首令人不安的自白诗”。[10](P95)在这首诗中,沼泽女孩的创伤使诗人回忆起那些北爱尔兰女孩的创伤,再次经历自我道德上的窘迫,于是被观看者的身体创伤转化成观看者的精神创伤,沼泽也从纪念之地转变为创伤之地。
《格劳巴勒男子》全诗如同一幅工笔画细致地描写了一具从日德兰沼泽出土的男尸。埃德娜·朗利认为这首诗试图通过隐喻来遮蔽暴行。[3](P76-77)但事实上,诗中的修辞并没有掩盖残酷的事实,格劳巴勒男子是一个承受着巨大痛苦的形象。丹尼尔·托宾(Daniel Tobin)认为,在“愈合的伤口/向内张开,通向一个黑暗的/接骨木色的部位”中,“愈合的”(cured)具有反讽意味,因为格劳巴勒男子的伤口并没有愈合,而是“向内张开”(opens inwards),因为这是在部落内部的杀戮。[11](P119)但笔者认为“向内张开”也意味着观看者内在的精神创伤。在《回忆有多真实?》一文中,阿斯曼讨论了精神创伤记忆:“这类回忆太令人痛苦或太令人羞愧了,所以若没有外因的帮助,它们不能重新回到表层仪式上来。”[12](P58)对诗人来说,在“无语旁观”那些北爱女孩所受的伤害之时,即在内心埋下了因道德缺陷而感到羞愧的精神创伤,并最终为这些沼泽尸体上的创伤所唤醒。
在《奇异的果实》中,诗人描写了在丹麦沼泽出土的一个遭到斩首的少女的头颅。这首诗的题目原是一首美国歌曲的标题,指的是在美国南方,被私刑处死的黑人的尸体如果实般挂在树上。[13](P74)诗中的西库鲁斯是古希腊史学家,记录过不同地区的杀戮事件,包括凯尔特人对砍头仪式的嗜好。[14](P182)所以,这首诗暗示了多重杀戮:日德兰沼泽的、美国南方的、古埃及的以及爱尔兰(凯尔特)的。诗人说西库鲁斯“对这类事情已经处之泰然”,显然是在谴责人类面对暴力时的无动于衷。如有学者曾说,要把创伤从文学主题转变为哲学和道德主题,把身体、精神和社会创伤深化为文化创伤,把创伤变成人类的社会责任和文明反思的问题,就需要给创伤一个世界性的语境,而创伤记忆的真正意义不是创伤经历本身,而是这一事件对于整个社会和文化结构性的震撼,以及人类如何克服震惊与恐惧并拯救自己。[15](P105-106)值得注意的是,希尼既借助语言的能力表现牺牲者的身体创伤,表达震惊与恐惧,也通过面对创伤时语言的无力来反衬这种震惊。在《奇异的果实》 的最后诗人一连用了5个形容词来修饰女孩:“murdered,forgotten,nameless,terrible,beheaded”,用词繁芜,所以,这首诗不入侧重审美的文德勒的法眼。[4](P48)而理查德·罗素则认为诗人堆砌词汇乃是因为他自己陷入语言无力之窘境,这是希尼在表达自己在面对被害女孩时的无力之感。[16](P77)所以,《奇异的果实》颠覆了《惩罚》所确认的诗歌的记忆功能和救赎能力:创伤不再局限于特定民族,而是人类文明的问题,对此语言已失去表现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希尼并非在否定诗歌,因为记忆和反思皆是在诗歌内部发生。诗人之意在于以否定的方式呼唤人性的道德责任,让世人共同理解、分担和反省人类自身的过错、失败和由此造成的伤害。
当作者反思自己赋予杀戮仪式以诗学意义和民族价值,并转而揭示暴力造成的伤口时,沼泽变成了创伤之地:首先沼泽是杀戮的场所,出土的尸体展示着它们不言自明的伤口;其次它也是民族和宗教冲突中的北爱尔兰的缩影,揭示着暴力给北爱民众造成的苦难和伤痛;再次它也代表了作者在面对人性的残暴时精神上所受的屈辱与创伤,这创伤促使诗人审视自己赋予沼泽的政治意义,反思自己曾经神化的民族主义意识,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把握人性和历史的复杂性。
五、重返代际之地
值得一提的是,希尼对沼泽的书写并未止步于《北方》这部诗集。1994年,希尼游历了图伦沼泽,并创作了《图伦》一诗。这首诗开头写道:“那个星期日上午我们走了很远。/我们长时间站在图伦沼泽里:/那低地,那黑水,那密草/既虚幻又熟悉。”作者对图伦沼泽的描写,恰似作为代际之地的托纳沼泽,收入眼底的柳树从、灯芯草、粗硬树、青储饲料皆是传统乡村生活的元素,所以,作者说“它完全有可能是马尔霍兰镇或斯克里布”,即希尼家乡附近的城镇。图伦沼泽不再是《图伦男子》中拥有的神秘气氛的圣地,也无须以悲凉的语气想象囚车中的图伦男子。日德兰不再是“古老的杀人教区”,反而呈现出生命的连续性,传统农业社会正在向现代科技文明过渡:“稻草人双臂/张开,面对着小围场里的/碟形卫星天线”。碟形卫星天线所代表现代化与铁器时代的原始文明愈加疏离。在下面几行“有各种游客告示牌,北欧古文字如尼文,/丹麦文,英文。事物已经变迁”中,古代文字和现代语言的分置既如上文所言,代表了原始文明和现代生活之间的鸿沟,同时说话人所说的“事物已变迁”也暗示了北爱尔兰时局的新曙光:在希尼抵达日德兰的前几天,爱尔兰共和军宣布停火,北爱尔兰境内的暴力和杀戮有了终结的希望,使诗人感受到他在《踏脚石》中描述的“轻松的状态与敞开的可能”[7](P445)。
在这个语境下,诗人感到不是《图伦男子》中的“失落,/不快乐而又如在家乡”,而是“无拘无束,如在家中而又远离部族”。希尼不再将沼泽视为民族斗争、部族暴力和创伤之地,而是温暖宁静的田园生活之所。但同时,诗人之前的沼泽书写都成了《图伦》的潜文本。这首诗既批判了部族冲突的野蛮历史,又呈现出传统乡村生活的连续性,同时怀着希望向未来敞开。所以,虽然沼泽意象回溯到代际之地,但与之前作为代际之地的沼泽相比更为开放和包容。米山·理佐在《记忆的未来化》一文中引述了哈贝马斯关于“面向未来的记忆”的论述,认为其含义是“赋予记忆以‘面向未来性’,以此来了解过去,这不是肯定现状,而是培养以批判性的眼光认识历史的想象力,以此来积极地变革现在”[17](P205)。在《图伦》中,对于沼泽的记忆同时也暗示了希尼的“面向未来的记忆”。
如果说现代性被写入《图伦》的沼泽之中,那么,写于21世纪的《春天的图伦男子》则讲述了复活的图伦男子面向未来,融入21世纪都市生活的经历。诗中的图伦男子宣称“信念加之与我,而我毫无信念”,意味着对附加于沼泽和沼泽人的民族政治观念的否定。在诗的最后图伦男子说道:“像铲泥炭的男子汉那样/我直起身,朝手上吐口水,鼓起劲/抖擞精神,走上大街。”这是一个义无反顾投身现代生活的挖掘者的形象。这一形象使这首诗在某种意义上呼应了希尼最早的作品《挖掘》。在一次访谈中,希尼使用这一形象来赞美当代爱尔兰人:“他朝手上吐口水,就像一个劳动者一样,如此他就代表了国人坚毅的一面——年轻人投身于海外救助工作……而在国内,每年有大量教师、护士和公务员准备出境为人类共同福祉尽心尽力。”[18](P205)这既是一个扎根于爱尔兰乡村传统,但却超越狭隘的民族意识,向现代性敞开的形象。苏珊娜·里德斯托姆曾经评价说晚期的希尼有意使自己的作品去地域化[19](P128)。但在《春天的图伦男子》中,希尼重拾地域色彩鲜明的沼泽,毕竟他曾说过,我们天性中的基本法则一直在驱使我们从稳定的土地中寻找延续性。[1](P149)通过重写《挖掘》中的劳动者的形象,希尼返回作为代际之地的沼泽。劳动者形象的延续,从希尼的祖辈到其本人再到当代爱尔兰人,代表了生活在此地之上的家族和群体的连续性,这符合阿斯曼对代际之地的定义。在《春天的图伦男子》中,这个劳动者要奔赴的是以数字科技、消费场所和飞越大西洋的航班所代表的现代化、商业化和全球化的生活空间,所以,这首诗中的图伦男子既代表家族和群体的连续性,又象征对现代化的面对和接受。诗人带着开放的心态以及全球化的意识来看待传统和现代化的关系,而这一既立足传统与本土,又面向未来和世界的新的地域观,赋予了作为代际之地的沼泽以更具包容性的意义。
六、结语
对希尼来说,真正的记忆不是简单机械的重现,而是“永恒更新与自信出发之地”。在他的笔下,沼泽就是永恒更新和自信出发之地:它能让诗人瞥见过去的轮廓,感受隐匿在风景中的传统与情感,赋予它民族意识并进而审视、反思此民族意识,从而向未来敞开。沼泽如同不断增生的年鉴,呈现人类持续在场的印记。托马斯·德昆西曾经把承载记忆的大脑比作复写羊皮纸:“人类的大脑难道不像一张自然的,伟大的复用羊皮纸吗?不可磨灭的思想、图像、感觉一层层柔和得就像光线一样叠放在你的大脑中。每一层新的看起来都会把前边的所有层次掩埋。但实际上没有一层会被消除掉。”[6](P170)作为记忆象征的沼泽正像德昆西眼中保存记忆的大脑,不同时间点上的回忆都能赋予沼泽新的意义。希尼在《沼泽地》一诗中所写的:“我们的开拓者们不断朝里面/和朝下面敲击,/他们剥掉的每一层/似乎都有人扎过营”,也是其诗歌写作的自我指涉,因为挖掘是希尼作为一个诗人的基本姿态:诗人正是这样的开拓者,在对沼泽这个诗歌题材进行一层层的挖掘。如有不同时期的字迹覆盖其上的复写羊皮纸,在沼泽这片记忆风景上,代际之地、回忆之地、纪念之地和创伤之地叠加在一起。这种多层次、多角度的描写赋予沼泽平实的生活感、厚重的历史感、森然的仪式感、精确的抒情性,也使诗人能够探索自我和群体、诗歌和社会、记忆和现实之间的复杂纠结,由此沼泽形象变得多重、复杂而深邃,就如《沼泽地》的最后两行所说:“沼泽孔眼也许是大西洋的渗漏。/潮湿的中心是无底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