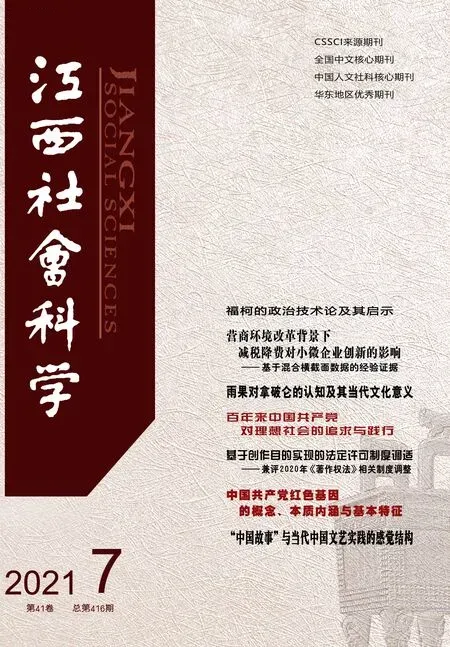被直观呈现的世界
——罗伯-格里耶反传统创作探析
2021-11-29桂青云张新木
■桂青云 张新木
在传统视角的解读下,罗伯-格里耶的前期作品呈现出描写平面化和叙事碎片化的特征,但平面化和碎片化的表象下却隐藏着深度和连续性,背离传统的形式背后是作者借由人物视角对个体存在经验的直观式呈现。对文学中既存的诗意表达和阐释系统的拒斥构成了作者创新的驱动,而展现个体原初的感知世界和精神生活则是其创作的重要目的之一。人物所意向的画面直接面向读者,它们替代任何解释性的语言,为主体的真实存在进行言说,读者也从而在直观中与作品发生更为深刻的牵连和互动。
作为法国新小说派的领袖,阿兰·罗伯-格里耶(Alain Robbe-Grillet)的创作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之初便引起了法国评论界的批评浪潮。新形式的小说违背传统的阅读习惯,不论是中性的笔调、烦琐的描绘,还是破碎的叙述、虚无的表达,种种阅读印象将读者拉离舒适圈,并激起他们对文本的一再重读和解读。20世纪50年代,以罗兰·巴特为代表的学者侧重评析罗伯-格里耶小说中的形式创作特色,强调他在文本中止于外物和人物行为表层的客观书写方式。而20世纪60年代以后,布鲁斯·莫里塞特、吕西安·戈德曼等批评家则开始从心理学或社会学的角度对作品进行阐释,他们挖掘与人物相关联的心理或社会内涵,以实现对作品意义的反追寻。评论者从不同的侧面出发,不断在对形式的探究和意义的迎拒中走近这个陌生的文学世界。本文借鉴前批评家的观点以及作者自身发表的理论观点,试图围绕他前期创作的四部小说——《橡皮》(Les Gommes,1953)、《窥视者》(Le Voyeur,1955)、《嫉妒》(La Jalousie,1957)、《在迷宫里》(Dans le labyrinthe,1959),其中所显示出的直观特性,从主观的层面解析他的形式建构特色及其意义。通过先后探讨在描写与叙事方面的反传统创作,笔者将分析作者如何用直接的形象和画面构造出人物的意向维度和生存经验,从而实现与传统阐释模式的分离以及对主体存在状况的求真,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直观的呈现方式对读者阅读体验的重塑。
一、平面化描写下的深度
罗伯-格里耶在小说中描绘了大量的物,物的线条、颜色、形态等视觉特性被突出并细致刻画。作者用几何用语和祛除了夸张成分的朴素语言来塑造物的外观:“那油漆的木门高踞在五级石阶上的一个凹进处,那些没有挂帘的窗户——左边两扇,右边一扇——还有上面四层楼全是一式一样的长方形的窗门。”[1](P131)“坡岸是一个倾斜的梯形物,由两个垂直的平面交切成锐角。”[2](P4)“每阵狂风过后,雪花又重新飘落下来,形成白色的线条,平行的、交叉的、螺旋形的线条。”[3](P9)物在准确、中性的语言描绘中再现,它似乎也因而脱离了与人的精神相通,在文本中获得了独立的存在。巴特曾在《客观文学》中表示:“罗伯-格里耶的文字没有托词,既无厚度,也无深度:它停留在物的表面,对它进行平等地描述,并不去突显这个或是那个优点:因而,这甚至与诗意化的文字是相反的。”[4](P33)在传统的现实主义文学中,物的呈现总与人的主观发生着联系:它的某些特性被放大、甚至被加工,并通过各种连接被指向它存在之外的情感或是意义。而在巴特看来,罗伯-格里耶的文字客观地记录了物的事实,这样的物不具备那些超越自身的情感牵连,它仅被呈现为一种单纯的、被铲除了深度的存在。
但物在罗伯-格里耶小说中的统一客观呈现却值得商榷。小说中的描写大都从人物视角切入,它显示出“一个人在看,在感觉,在想象”[5](P209),人物所感知的画面被呈现出来。当外物牵引人的注意力,被其视线所聚焦,此时的物便不再独立存在,它与主体产生联系。罗伯-格里耶在1981年发表的文章《罗兰·巴特的利益》中曾表示巴特有意将其小说缩减成一个“只显示出客观的和字面的坚固性的物质世界”,并选择忽视那些“隐藏在极现实画面阴影下的怪物”。[6]小说中一些看似客观的画面实际连通了人物视角,而背后的感知主体则经由物质形象显现出来。索莱尔斯(Philippe Sollers)如此评价罗伯-格里耶的文字:“隐喻的缺失……加强了文字的透明性,因为隐喻是将图像反射到另一图像的镜子,而在这儿镜子是事物本身,语言是这些事物被感知的界限。”[7]拟人或者隐喻构建的是各种联想网络,情感通过相似性被投射在变形的或是转接的图像上。但罗伯-格里耶摒弃了这样的修辞方式,他用文字所描绘的物质图像能够让读者直接识读出主体经验。
传统的类似拟人和隐喻的修辞语言某种程度上能依赖具象更为生动地传达人物情感,但如果这之中存有对某些固化符号的直接套用,那情感本身则遭到了忽略。罗伯-格里耶在《自然本性、人本主义、悲剧》一文中表露出自己对拟人化语言的担忧:“在我们几乎全部的当代文学中,这种拟人化的类比反复出现得实在太频繁,实在太严密了,不能不显示出整整一个形而上学的体系。”[5](P120)人在物上所刻下的精神印记如果反复地出现,则容易成为人类的“自然本性”[5](P122),当人为的特征被当作是天然和永恒的存在时,人们便容易因此而忘却自身情感的源头。在文化的传递中,某些认识已经内化成先验的概念,构成物质形象固定的所指,人们在认知圈内不断重复某些逻辑,依赖语言符号惯性地言说。在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中,传统修辞的缺失使得人物情感不再借由间接的图像被传达,在文本中滥用诗意符号的情况也被规避。同时,朴素的语言刨除了诗意描述中可能存在的夸张与想象成分,仅作为人物“目光的支撑”物或者“激情的支撑”物被直观地呈现出来。[5](P119)对于罗伯-格里耶而言,物不应该成为人借以刻意抒情、聊以自慰、用来实现自我崇高感的工具。①他在小说中尝试消除人对物的加工,以呈现出人与物碰触的直接经验。但是,热奈特(Gérard Genette)也曾经为巴特的客观解读进行辩护,他指出罗伯-格里耶所描绘的那些“可被测量并且可被几何性复原的表面”[8](VertigeFixé,P75)都指向了对物的客观塑造。诚然,主体视觉印象中的物难以显现出科学的精准性,小说中的一些画面也因此显示出了一种主观与客观相矛盾的杂糅。②这种矛盾的现象可被视为作者在文学探索过程中的产物,而他的探索皆基于其“求真”的初衷,无论是寻求对客观真实,还是对主观真实的展现。除此之外,不可否认的是,在罗伯-格里耶的创作中,与人物视线相接的物能够直接映射出主体经验,它们由此成为其意识和情感的佐证。
在小说《嫉妒》中,种植园里的香蕉树、房子里的摆设、妻子A和弗朗克的举动被描绘出来,平实的语言不带有情感的涟漪,被勾勒的画面清晰可见,如同被摄像机记录下来一般。但“朝河谷深处”看去的香蕉树,从“百叶窗”的“木质叶片”间瞥见的A,“朝厨房门方向”仔细察看的蜈蚣斑迹却暗示出了凝望的角度和被投射的视线。[9](P13,P48-49,P56)从同样的角度折返,顺着视线追寻,画面背后的注视者,即文中被隐藏的叙述者显现出来,所有视线都指向可能存在的A的丈夫——房子的主人。在房子内外,男主人的视线勾勒出了他意识的方向。他数次描绘A为招待朋友弗朗克在露台上摆放的桌椅:A和弗朗克的椅子并排放着,另外两张椅子则被斜放在桌子另一边,而坐在这两张椅子上的人需要费力转身才能看见A。桌椅的摆放位置被投射了A的念想,成为她欲望的影射,而男主人公对此画面的数次描述和关注则显示出了他的情感,他对A的执念在其解不开的猜疑与嫉妒中和物相缠绕。人物视线与他“看的能力、看的认知、看的欲望”相关联,而观看欲望则被其“心理特征或是性格特征”所解释。[10](P172-173)小说中的男主人公在其视线所能触及的房子内外,在了解到妻子的惯常行为后,情感支配了他观看的方向,而被观看的画面则替代解释性的语言为其自身发声。
情感驱动人物视线,但人对物的关注并不总是由内因所主导,物同样发挥其能动性,吸引人的注意力。《橡皮》中的侦探瓦拉斯在他侦查案件的小城中穿梭,街道、形色各异的店铺、窗帘上的图像、软硬程度不一的橡皮——或大或小的图景被依次描绘出来,它们以其各色形态捕获男主人公的注意力;《在迷宫里》的士兵在下雪的街道上寻找约会地点,白雪、灰色的大楼、紧闭的门窗、灯柱底座雕刻的图案——单一的背景和背景中凸显的细节反复出现,它们抓取人物视线,霸占其意识。不断更新的视觉图像显示出人物注意力的更迭,叙述者依照人对物的关注程度施以笔墨进行刻画,而纤毫毕现的描绘和重复出现的图像则源于物的引诱,表征出处于物中之人的执念与迷失。《橡皮》和《在迷宫里》的主人公在小说中都充当了寻找者的角色,但与找寻客体无恰当关联的物却时常分散他们的注意力,零散的感知画面削弱了找寻的目的性,寻找者更多地被呈现为注意力易受干扰或精神状况遭遇危机的主体形象。莫里塞特如此谈论罗伯-格里耶所描绘的物:“对于罗伯-格里耶来说,如果物能够承载一种激情,一种顽念,或是任何其他的情感负荷,这只是简单地因为人只能通过感知事物而存在。”[11](P68)主体目光下的物难以显示出物自身的存在,因为物无法自我察觉,相反,主体依赖物进行感知,物于是成为其精神存在的证明。在对物的直观呈现中,人物的感知经验朝向读者直接显形,被沾染了人物意识与情感的外部世界由此而成为映射主体存在的明镜。
二、碎片化叙事中的连续
罗伯-格里耶对物的描绘挤压了他文本创作的叙事空间,叙述轴上并置着来自不同时空的图像,它们扰乱叙事节奏,打破叙事的连续性。在传统小说中,故事的情节发展多数由一条叙述主线串联而起,事件跟随叙述节奏逐渐显露出它前后的样貌,读者依据前后变化构建因果联系。以展现现实事件为主的叙述主线可能伴随倒叙或者插叙,但它们不过是旁生的枝干,用以丰富主要事件的发展。在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中,传统的叙述结构和等级秩序遭到了破坏。现实事件的发展时常被突如其来的回忆和想象画面所干扰,当读者期待这些“离题”的片段适可而止时,期望却被细腻冗长和反复更迭的描写消磨干净。大量精神画面涌现在叙述主轴上,穿插于其中的时空被赋予了同等的描述,获得了平等的地位。但它们之间不由因果关系所联结,读者无法轻易地在转换的时空之间获取事件的连贯性,每次转换都意味着新的适应。正因如此,事件叙述是破碎的,而读者的阅读体验是断续的。巴特曾经这样描述《窥视者》这部小说:“在这儿,故事材料不是心理的,甚至也不是病理的……它们被缩减为在空间和时间中逐渐涌现的物,它们之间没有显露出任何的因果毗邻性。”[4](Littérature Littérale,P68)小说中的主要场景都被定格在一些重复出现的形象上:女孩、绳索、海鸥、8字标记等,它们出自一些记忆碎片、假想画面或是真实感知。这些形象每一次出现都被仔细刻画,但它们彼此之间却没有能够组织起外部事件发展的明显牵连。
破碎感来自于读者对小说中所呈现事件的连续性的期待,但如若放下固有的期待,放弃对事件脉络的追寻,阅读体验则会有所不同。法语中的现在时和过去时被用来区分当下和过去所发生的事,而虚拟式或者条件式则和直陈式一起用来标识行为的虚与实。传统小说谨遵这样的语法规则以让读者更好地厘清先后次序和逻辑关系。但罗伯-格里耶在《嫉妒》与《在迷宫里》两部小说中大量使用直陈式现在时来描写回忆、想象和外部环境,过去与现在、虚与实的对立被取消,所有的时空被纳入了唯一的“现在”。这样同质、均等的时空构建了一个与寻常阅读不一样的环境,它是一个内部的,顺着人物的精神体验不断向前延展的空间。无论是人物所感知的外部事物,还是各类精神画面,它们都是人物所意向的内容,均出现在意识的当下,这样的“时间属于现在,因为意识是与所有时间同时的”[12](P519)。不仅时态的标识取消了时空的异质性,意象的彼此触发也消解了时空的断续。《窥视者》中马弟雅思在现实中注意到的小麻绳、8字标记、海鸥浑圆的眼睛等连通了他儿时收集小麻绳的记忆,唤起了他在房间内画海鸥的景象;船上倚靠铁柱的小女孩、照片上的雅克莲等女孩形象久久地萦绕在他脑海,他由此对这些女孩产生了邪恶的想象。现实形象触发精神画面,后者又继而牵引男主人公的意识,使其对现实中的类似形象进行反复关注。现实之物与精神之物互相关联,人物的意识在外部世界与内部世界的互动中不断延续。罗伯-格里耶曾经这样解释精神的容纳物:“我们精神的完整胶片同时地、依次地并且同等地接纳那些由视觉和听觉在瞬间引起的真实碎片,和那些过去的、或遥远的、或将来的、或者完全虚幻的碎片。”[13](P15)在主体的精神时间内,各类图像依靠彼此的相似性相互触发,它们依次、连续地出现在意识的当下,构成意识流中的真实存在。罗伯-格里耶因而不遵循客观现实的因果变化,而是以主体的精神时间为参照来推动小说中叙述的进行。
依照联想的机制或者感知的次序,作者将人物所意向的连续性图像直观地展现出来。热奈特这样描述他作品中想象物与感知物的同等透明度:“正如罗伯-格里耶赋予了想象物和感知物同样的准确性,同样清晰的轮廓,幻想的行为、假想的事件、最幽暗的想象在他这儿获得了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所说的‘同等的光亮’,冷淡的光线,没有阴影,但它刺穿所有的迷雾,消解所有的虚幻,或是阻止它们显现。”[8](Vertige Fixé,P76)虚实之物接受了同等细致的刻画,并都被朴素直白的语言所展现。这种不带晦涩且不具备差别的描写在热奈特看来印证了罗伯-格里耶的客观书写方式,对实际行为和想象行为的统一平铺直叙并不能显示出人物对待现实与虚幻的不同心理感受。但是,从主观的角度来看,叙述者经由人物视角对其想象画面的反复雕琢,却反倒能够从心理层面解释人物当下意识活动和感受的清晰与强烈。不论画面虚实与否,人物所意向的内容被直接裸露在外,而在对图像的直观中,人物的情感则无处藏匿。《嫉妒》中作为男主人公的叙述者在妻子A搭乘弗朗克的汽车进城购物后,一遍又一遍地描述他们在路途中出现的汽车故障以及他们当天因无法及时返回家中而在小旅馆逗留的画面。在现在时态的统一呈现中,读者无法确定这些略带不同进展的画面是出自现实还是想象,但它们都因每一处被雕琢的细节而显得鲜活,因细节中被浸透的焦虑和嫉妒而强烈地存在。这些场景不论是否真实,它们至少都曾占据男主人公的意识,霸占他的情感。
人物情感随其意识而流窜,它既受到外部意向物的滋养,也能够对意识活动进行主导。它可以串联起四散的精神碎片,构建起内部精神的连续性。《在迷宫里》的士兵拖着疲倦的病体在临时兵营夜宿时,意识的游丝在黑暗中游荡,它勾画出士兵近日纷乱的遭遇——酒吧、女人的家、随小孩前往兵营,又继而在梦境中勾勒出被人当作是间谍的图景,回忆与现实、梦魇与未来相互映衬,一个迷失、焦虑的灵魂在交错的画面中被烘托而出;《窥视者》中,马弟雅思的性虐癖好引导他对绳索、8字标记、海鸥眼睛、女孩等形象的特定关注,各种时空图像在其欲望的主导下汇聚,在过去、想象与现实间彼此牵连。男主人公的欲望也因而在相似形象的滋养下和逐渐变形的想象中膨胀,最终驱使他在现实中用罪恶的行径来解除欲望的饥渴。回忆、想象与对现实的感知共同构筑了人物的精神生活,而情感则作为内在的驱动力,使得虚实之物相互关联,彼此触发,从而进一步影响着主体的意愿与行为。罗伯-格里耶仔细雕琢出意识图像的存在与分量,让读者在直观的同时能够直抵人物内心的情感囹圄。
三、主体经验的直观呈现
罗伯-格里耶勾勒出了一个视觉与物相碰撞的感知界面,一个浮现着各种精神图像的意识空间,主体的存在经验经由意向性的画面被展示出来。在展示背后,他不寻求更多干涉,文中的叙述者只负责记录人物的意识活动,却从不介入去解释心理或是评价行为。叙述者的痕迹被抹去,任何能够显示其主体性的思想、观念都隐匿不见。罗伯-格里耶在《未来小说的一条道路》中表示传统文学都在用各种框架内的解释性理论——“不论是情感上的、社会学上的、弗洛伊德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还是任何别的体系”[5](P85)——在分析人物,借以挖掘作品深度,但在习惯性的言辞和重复的论调背后,解释性的话语有可能遮蔽世界本来的面目。因此,他提出在小说中“构筑一个更坚实、更直观的世界,来代替充满‘意义’(心理学的、社会的、功能上的)的这一宇宙”[5](P85)。构筑直观世界的条件在于剖除任何经过阐释的描述,而作者借由人物视角所构建的画面则能够让读者直面人物的感性经验。罗伯-格里耶对解释性语言的摒弃防止了叙述者在既定的认知框架内进行惯性的观念传输,叙述者不再全知全能,他只是一位忠实的描述者。
贝纳尔曾指出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与他所属时代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被带回到现象学态度”,它是“反抗传统观念和价值的新式反应”,亦是“当代哲学的主导态度”。[14](P13)贝纳尔所说的现象学态度即为通过“悬搁”那些根植于集体意识中的惯性认知与偏见,使得主体关注到自身未经加工的意识经验的“先验还原”态度。[15](P43-45)罗伯-格里耶舍弃传统的解释系统与诗意符号的策略与先验还原的态度相契合,直观的呈现方式使得读者能够感知人物所感,借由对其经验的直观产生共情和反思。与此同时,小说中的人物大都受困于自身杂乱的意识和情感桎梏中,认知和理性鲜少介入其思维以主导他们的行为,如此被塑造的形象使得读者得以感受人物原初的生存状态。布托尔形容现象学是“研究真实以何种方式向我们显现或是能够向我们显现的场所,这就是为什么小说是叙述的试验场”[16](P9)。从人物的视角出发,通过减少叙述者的主观干预,罗伯-格里耶用直观的方式复刻出人物的意向画面,这样的画面源自于作者对主体经验的再现,正如他本人所言,他的“作品不带来任何别的东西,只有他(人物)的经验”[5](P209)。
与先验还原态度略有不同的是,罗伯-格里耶对小说中解释性话语的舍弃并不是一种悬搁,它不涉及暂时性的策略。作者有意展示人物存在,却不企图在这之后去分析、阐释和重构意义。如此,直观的方式将人物经验向无数个他者开放,它激发主动性,邀请读者进入人物世界。面对陌生的小说架构,惯性地寻求逻辑解释是读者在遭遇不适应、不确定后的自然反应,读者试图将小说中错乱的时空重组,以勾勒出一条能显示出先后次序,且虚实可辨的脉络。热奈特批判这种重组活动,他认为这是一种“自然的寻求解释的倾向,但在审美上是糟糕的,也就是说,它常常使得所有事物都变得平庸”[8](Vertige Fixé,P78)。小说内容被其形式所承载,而文本的意义则建立在形式与内容的结合之上,在文本之外去寻找解释是在“寻求赋予它唯一的意义中拿掉它全部的意义”[8](Vertige Fixé,P78-79)。在自身预设的阅读模式和解释框架中理解作品,事实上是对文本实质和意义的忽略。
罗伯-格里耶的小说之于读者可以被看作是“文学事件”,作品中的创新“对现存规范进行重塑”,而读者在经历这种重塑的同时自身也在被塑造——“它能够对意义和感觉开启新的可能性”。[17]罗伯-格里耶的创作形式引导读者跟随叙述文本,跟随它展开的方式,让自己融入人物意识的洪流中。陌生的文字描绘与叙述结构能够凝聚读者的注意力,使其以一种更鲜活、更直接的视角去凝视他人生活的世界,从而感受人物的存在状态与情感流动。这样的直观也同样以强烈的方式呼唤读者对自我经验的反视,他者经验的刺激和自身的共情感受在阅读体验中交替。读者的感觉系统与想象能力在阅读中更多地被调动,但理性和认知也同样可能参与其中,并间隔性地发挥作用。与传统阅读不同的是,读者不是只“需要凝神观看以期读懂预设的概念意义的东西”[17],而是以一种主动的姿态,以他者和自我经验作为参考进行思索和领悟。先验还原中的悬搁对于胡塞尔而言,“是一种方式,它揭示关于相关性的判断,揭示将所有意义的整体都还原到我自己,以及具有其所有能力的、意义拥有的和意义给予的主体性”[15](P44)。悬搁“不是对这个世界以及关于它的任何判断的放弃”[15](P44),被还原的经验可以是主体造就理论的源泉,而主体拥有能力去赋予意义。罗伯-格里耶在小说中将虚构世界的既定意义瓦解了,但读者则可能继而成为赋予意义的主体。
四、结语
人物视角破除了统一的平面化描写,意识连续消解了传统印象下的碎片化叙事,反传统的创作背后存在着用直观的感知形象与意识画面所建构的人物的意向世界。对形式的解构源自于罗伯-格里耶对传统文学中形而上学的诗意表达与阐释体系的担忧,而外物形象作为主体感知经验的承载,意识画面作为其精神生活的写照,它们的直接在场脱离既有的表达符号和阐释体系的操控,显示出人物更为深层和真切的生存及情感体验。与此同时,可视性的画面将人物经验向读者开放,使其进入文本与人物共存。对人物经验的直观加强读者的情感代入,使其用更沉浸的状态和主动的姿态进行阅读。无论是进行小说创作的作者,或是处于阅读体验中的读者,他们都在自身的文学经历中摆脱某些既定认知,通过改变创作的形式或阅读的惯习,以实现对主体经验的溯源和情感真实的还原。
注释:
①在《自然本性、人本主义、悲剧》一文中,罗伯-格里耶把人拒绝赋予物精神标签的态度提升到了自我救赎的高度。他认为,人们经常将类似于痛苦、孤独、负罪感的负面情绪加诸在物上,从而使自身的精神特质成为物的深度和意义。人们企图借此升华自身的情感,使之变得高尚,以自我安慰,实现救赎。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摆脱或是接受了自身的情感,相反,人以自我为代价哺育着它们,从而深陷情感漩涡之中,而这只能是一种无休止的悲剧。
②几何性的描写所显示出的人物的度量目光实际和主体的自然目光相悖。胡塞尔认为,在个体的感知中被给予的物具备一定的模糊性,“如果我们试图将在几何学里才能找到的精确性和精密度强加给生活世界里的现象,我们就破坏了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