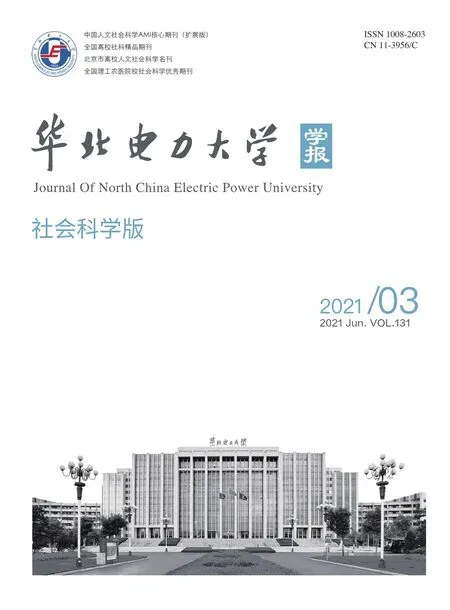弗吉尼亚·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念的批评研究
2021-11-29王喆,马新
王 喆,马 新
(1.安徽建筑大学 外国语学院,安徽 合肥 230601;2.东北大学 外国语学院,辽宁 沈阳 110819)
“双性同体”(androgyny)是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术语,流变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地理家族,例如传统的英美女性主义理论与哲思色彩浓烈的法国女性主义理论中,体现了不同时空中女性主义理论家对于女性写作理想状态的极致追求。20世纪20年代末,在其女性主义宣言《一间自己的屋子》中,英国女性主义先驱伍尔夫(Virginia Woolf)援引了18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有关于双性同体观念的表述,赋予了该观念文化、文学的维度。伍尔夫号召女性作家在写作过程中尽量做到非个人化,其中最理想的状态即是拥有一颗男女两性气质统一和谐的大脑。
自伍尔夫以降,双性同体观念即是女性主义理论中的一个热点话题,且“更有批评家与评论家从特别的思想位置上对此进行处理”[1]290。例如,从伍尔夫的家庭成长环境审视,双性同体观念是一种“对于平衡的找寻”[2]。双性同体学者海尔布伦判定20世纪早期伍尔夫身处的布鲁姆斯伯里团体(The Bloomsbury Group)是该观念在日常生活中的“第一种实际例证”[3]。反之,双性同体观念的实际功用及效力受到严厉质疑,它仅是伍尔夫编造的一则“寓言故事”[4]、或一个“黄粱美梦”[5],旨在消解伍尔夫与女性主义两者间的冲突。而这些对于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念的迥异发声足以“证明了对于为该议题选定一个连贯一直表述方式的困难性”[6]。
一、女性写作中的“双性同体诗学”
以《她们自己的文学:从勃朗特到莱辛的英国女性小说家》为核心理论文本,美国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家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建构了有关于女性写作的“女作家批评”学说(gynocriticism)。女性作家的性别问题,或性别的意识形态是肖瓦尔特在其“女作家批评”学说中关注的核心之一。此前,肖瓦尔特就已觉察出双性同体观念的某种易变性,延续了20世纪70年代初相关女性主义学者对于该观念的思辨潮流。在传统的精神分析学说中,双性同体观念指代人格层面的一种乌托邦完满状态。而作为一个文学批评中的理论术语,该观念多被用于对于女性作家文学作品“娱乐性的”[7]解读中。
随后,在界定、描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不同发展阶段和模式中,肖瓦尔特再度触碰到了“双性同体”这个话题。她认为,在70年代左右的女性解放运动之前,有关于女性作家的批评形式即是某种“双性同体诗学”(an androgynist poetics)风格的,其中所意欲宣扬的是女性作家在进行文学创作时所要面对的单个、统一的批评标准。与此紧密呼应,女性主义文学的预设目标即在于进入一种“中性与‘通用’的美学领域”[8]361。而后,以女性解放运动的第二次浪潮为历史背景,“女性主义美学”(the Female Aesthetic)、“女作家批评”学说得以兴起,女性作家文学经验中的女性气质得到凸显,这也标志着新时期中女性文学批评审美标准与先前“双性同体诗学”的首度决裂。
对于“双性同体诗学”,肖瓦尔特一贯持有较为复杂的态度。尽管“双性同体诗学”的写作方式很可能是“女性自我憎恨的一种形式”[8]360,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却又接近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本质。“双性同体诗学”招致了众多女性主义理论家的不同发声。例如奥茨(Joyce Carol Oates)曾描述严肃作家在具体写作过程中应做到无性别的区分,而吉尔伯特(Sandra M.Gilbert)却指出女性作家的性别应与其文学创作互为整体。结合当时日渐盛行的精神分析学说,肖瓦尔特强调了女性作家凸显性别差异与解构性别等级的重要意义:“否定自身女性身份的女性作家限制、甚至削弱了其艺术”[8]361。
二、女性作家的乌托邦
在《她们自己的文学》的第十章,肖瓦尔特以“弗吉尼亚·伍尔夫:遁入双性同体论”(“Virginia Woolf and the Flight into Androgyny”)为标题,对“女作家批评”中的“女人”阶段的代表人物伍尔夫及其双性同体观念提出质疑。《她们自己的文学》标志着女性主义理论学说和双性同体观念研究的一个崭新阶段,肖瓦尔特本人则隶属于“强调自身作为女性主义者重要性的女性学者”[9]149。然而,这位女性学者却在母辈伍尔夫身上觉察到了一种遁入虚无的迹象。首先,肖瓦尔特判定,《一间自己的屋子》书名本身就隐含着其作者主动脱离社会、性属的意味。私密空间演变为女性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圣殿”[10]264。在其遮蔽下,女性作家得以与男性保持距离,其怒火与性欲得以安全表达。随后,从伍尔夫的生活背景为切入点,肖瓦尔特宣判伍尔夫无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双性同体气质。双性同体观念不幸沦为致使布鲁姆斯伯里团体成员,例如当时英国艺术家马克·格特勒(Mark Gertler)、朵拉·卡琳顿(Dora Carrington)及伍尔夫本人死亡的“连环杀手”[11]117。同时,肖瓦尔特研读了伍尔夫的生平经历及传记,指出伍尔夫性别两极化生活观形成的具体依据,例如其父母所代表的男女两性气质。在肖瓦尔特的犀利论述中,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念绝非致力于男女两性气质的融合,而是一种有关于其中某个微妙的力量平衡点的找寻。伍尔夫早年的家庭生活经历、她与丈夫伦纳德(Leonard Woolf)的婚姻关系、生活中母亲身份的缺失及多次的疗养经历等均被肖瓦尔特置于严密的审视下。
从伍尔夫的文学创作经历入手,肖瓦尔特继续推进,解构伍尔夫构建的双性同体观念。她细查了伍尔夫的文学创作手法,指出在20年代社会夹缝中,伍尔夫竭力寻找着有关于女性写作的某种特殊方式。此时,她所创作的小说等文学体裁偏离了正常轨道,如肖瓦尔特本人异常偏重的现实主义。《一间自己的屋子》正是顺应这种背景诞生。对于这本女性主义的圣经级读物,肖瓦尔特给予了一种分裂性质的解读。首先,她剖析了伍尔夫的写作风格,指出文中的第一人称叙事者“我”不仅是一位无性别的角色,更是伍尔夫对几位名叫“玛丽”的女性人物的随意拼贴。其次,肖瓦尔特论述道,在一、二两章漫不经心的论述之后,伍尔夫才得以开始论述全书核心的论点,女性与小说。此外,肖瓦尔特坦言,伍尔夫对于双性同体气质的男性作家代表,例如莎士比亚等人的选取过于散漫。对于双性同体气质女性作家的代表,伍尔夫却并无深入探讨。经由肖瓦尔特的层层严密论证,双性同体观念已倒退为某种“战略性的撤退”[10]285的倡导。
在《一间自己的屋子》的第六章,伍尔夫完整建构了“双性同体”这一视像。与先前的“一间自己的屋子”类似,双性同体气质的思维模式是女性作家解决其写作困境的出路之一。然而,在肖瓦尔特的批评视阈中,“一间自己的屋子”被定义为某种幽闭空间。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女性作家的发声被弱化、甚至被消音,她们由此沦为无明显性别特征的“流放者和阉人”[10]285。伍尔夫坚信,在女性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过程中,双性同体气质会以某种专属于女性性属的词汇或句式呈现。然而,肖瓦尔特认为,这种抽离愤怒的女性气质仍将附着于女性作家所创作的文学形式表层,例如在小说中就存有愤怒情感的宣泄表现。伍尔夫详细阐明,在任何情况下,一颗富有创造力思维、或双性同体气质的大脑会迈过性别意识的障碍,即便是缺少私密的空间或坚实的物质保障。在文学创作中,伍尔夫渴望拥有平和的心境和澄明的写作思维,但受制于自身的性别身份,她无法逃离20世纪早期伦敦的父权制社会环境。此时,伍尔夫精心雕琢的双性同体视像已被肖瓦尔特形象比作一台冰冷的“心理层面的前脑叶白质切除术”[10]287。
在肖瓦尔特的批评中,伍尔夫对于双性同体观念的描述手法“近似于性爱式的遐想”[10]287。对于读者较为熟知的“黑暗中的联姻”(nuptial in the darkness)这一场景,或其中暗含强烈性别色彩的“圆房”(consummate)、“躺下”(lie down)等字眼,肖瓦尔特给予了颠覆性重读。同样,希斯(Stephen Heath)指出,这一场景中存在的依旧是“插入的、主动的男性;接受的、被动的女性”[12]114。此外,在该场景的最后一幕,伍尔夫描述道,作家“必须采摘下玫瑰的花瓣或是看着天鹅平静地在河上漂流”[1]177。对此,希斯认为伍尔夫把原属于女性的玫瑰花形象借给了男性,而这种摘花行为本身作为一种文学意象,暗示着“男性欲望的高潮”[12]114。此外,“天鹅”这一形象在文学批评中常与女性气质、女性身体相联系,充盈着某种性别色彩。盖洛普(Jane Gallop)判定,伍尔夫意欲赞扬的并非是异性、或双性恋的繁殖能力及由此积攒生成的文学创作力,而是它的性高潮潜力[13]。肖瓦尔特甚至敏锐注意到,在伍尔夫的行文中,女性作家的人称代词不动声色地被偷换为“他”,男性作家沦为“窥淫狂者”[10]288。由此,作家作为“第三者”窥视男、女双方的性爱现场,这种三角结构“使得对于双性同体观念的呈现复杂化”[14]。
肖瓦尔特再次将伍尔夫置于其生活环境中考量。“布鲁姆斯伯里团体”一度曾是20世纪早期伦敦文化思想界的非主流中心。在日常生活中,布鲁姆斯伯里成员,例如当时的文艺评论家弗莱(Roger Fry)、传记作家斯特拉齐(Lytton Strachey)、小说家福斯特(E.M.Foster)等皆奉行理智与情感并存的双性同体气质的生活方式,勇于抵抗各类权威与传统习俗。同样,伍尔夫深度践行着该精英文化团体内的价值观或性取向,例如她一贯热衷尝试的双性、同性恋的情感方式。肖瓦尔特裁定,这样无任何鲜明性征的双性同体视像令大部分女性作家无从捉摸。她号召在写作过程中,女性作家应平均地使用大脑中的双性气质,而这也终将会是有关“女性写作”的一种崭新姿态。
对于之后伍尔夫有关于双性同体观念的态度转变,肖瓦尔特亦给予了相关说明。例如,她认为伍尔夫在《奥兰多》中所践行的双性同体理念仅是一种解决心理冲突的矛盾方案。30年代中,受限于其写作技巧,伍尔夫的文学创作风格仅被狭窄划分为男性、女性气质的,例如报刊文章或传记写作、小说创作,两种类型始终无法融合。在杂文《女性的职业》中,伍尔夫再次刻意逃避描写女性身体。同时代末,她遭遇了较多的个人情感悲剧,因此继续沉迷于双性同体的幻象中。在《三个畿尼》中,伍尔夫又以反战为借口,欲使她的女性读者从带有侵略性的男性世界中主动撤离。作为一种带有缺陷性质的伦理道德观念,双性同体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演变为某种女性美学问题,更是伍尔夫本人“女性社会角色观念的延伸”[10]296。结合伍尔夫的文学创作实践,肖瓦尔特进一步揭示出双性同体观念的乌托邦性质。例如,她分析道,在《灯塔行》中,伍尔夫对“身体”、“性欲”等女性气质代表物的描写始终过于稀疏。
在肖瓦尔特的“女作家批评”学说中,女性文学传统得以延续的重要因素之一即在于超越伍尔夫及其双性同体观念。“一间自己的屋子”转化为一口阴森墓穴,伍尔夫也由此沦为一位“阁楼上的疯女人”。通过批判双性同体观念,肖瓦尔特“杀死了一个文学意义上的尸体;她更是通过这躯尸体本来武器的子弹反弹进行杀戮”[15]38。在某种意义上,通过诋毁伍尔夫笔下著名的“屋子里的天使”(the Angle in the House)形象,肖瓦尔特甚为荒诞地“扮演了伍尔夫的天使”[15]38。然而,肖瓦尔特对于伍尔夫的抨击过于主观夸张,导致双性同体观念沦为一个千疮百孔的“靶子”[16]。在细读肖瓦尔特的批评中,更有少数评论家敏锐觉察到了当代批评理论的某种发展朝向,例如70年代中“双性同体”作为一个基本理论术语的渗透性所在。其中,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念通常被诋毁为“压抑的,而非是激进的”[11]117。
同样,肖瓦尔特对于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念的顽强抵制更受制于当代女性主义思潮的影响,绝非是停滞在20世纪早期《一间自己的屋子》的创作年代、或受限于当时占主流地位的现代主义文化、文学背景。因此,在某种程度上,肖瓦尔特对于双性同体观念的批评仅是“有选择性的”[11]118,并集中指向着该观念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的第二个流变阶段,“逃离双性同体”(“The Flight from Androgyny”)[9]149。1974年,《女性研究》期刊(Women’s Studies)刊发了专门性论文集《有关于双性同体的论文》(The Androgyny Papers),其中收录了数十篇与“双性同体”相关的研究论文。海尔布伦、托平·贝津(Nancy Topping Bazin)等知名双性同体学者均表述了她们对于该观念的兴趣与分歧。鉴于70年代中女性主义理论学界对于该观念的激辩,这一阶段的目标仅是“分裂主义的”[9]145,而肖瓦尔特的批评正是对于这种分裂潮流的一种完美呼应。
80年代,斯塔布斯(Patricia Stubbs)延续了肖瓦尔特对于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念的批评基调。她指出,在19、20世纪的小说中,对于女性“性力”、“身体”等议题的描写是女性作家难以抵达的一片荒野之地。在相关文学创作中,伍尔夫逃避刻画女性身体和激情,更无力论述女性社会生活、女性经验及物质现实。例如,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女性经验通常被过度神秘化。因此,伍尔夫被判定为是一位极不称职的女性作家,其相关的美学、文艺理论,例如读者熟知的双性同体观念仅是“令人惊奇地中性、不完整的”[17]232。在实践层面上,这种带有明显瑕疵的双性同体观念最终致使伍尔夫的文学创作“失去生气”[17]232。
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家巴雷特(Michèle Barrett)同样觉察出了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念中透射出的悖论。在她看来,伍尔夫把神秘主题、或完整性视为艺术作品中的最高价值,而这种艺术作品通常拥有超越社会、政治问题的能力。通过使用带有神秘色彩的双性同体观念,伍尔夫“持续抵制着她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所提出的物质主义姿态的暗示”[18]。伍尔夫曾把艺术作品划分为两类:非个人、超脱现实的与政治、说教性的。而她本人偏重的则是前一种类型,正如独立于物质世界之外存在的双性同体气质的作家形象。新世纪伊始,伍尔夫对于双性同体观念中“物质性”的冷漠态度再度遭到质疑。例如,哈格里夫斯就曾谈及该观念使“作家忽视了由性别差异文化规范生成的物质现实”[11]96。
三、女性写作的第三种方式
在《性/文本的政治:女性主义文学理论》中,当代挪威裔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莫伊(Toril Moi)致力为其女性主义偶像伍尔夫及其双性同体观念正名。在导论“有谁害怕弗吉尼亚·伍尔夫?伍尔夫的女性主义解读”中,莫伊批评肖瓦尔特忽略、或误读了《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原本积极的政治、美学及文学性,肖瓦尔特的解读方式和女性主义的实践方式互为矛盾。在后记中,莫伊又再次阐明她对于肖瓦尔特批判的目的,欲使后者意识到其中所涉及到的隐蔽的理论政治性。在莫伊后结构主义的批评视阈中,肖瓦尔特所追求的是某种资产阶级现实主义色彩的女性写作方式,女性经验应以无限真实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肖瓦尔特被莫伊冠以“现实主义者”等诸多称谓。在莫伊的评述中,肖瓦尔特对于“主体性”、“自我”等字眼的论述类似于马克思主义文论家卢卡契(Georg Lukács)对于现代主义文学的批评阐述。在卢卡契的论述中,现代主义文学是“对现实的稀释和对人格的分解”[19],现实主义文学才是艺术表达中的最高形式。在20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的社会背景下,现代主义是人类消极存在状态的导火索之一。对于卢卡契的观念,肖瓦尔特表示赞同,并指出伍尔夫对于自我意识的描写是其对于女性社会角色思考观点的延伸,等同于对自我毁灭命运的被动接受。
尽管卢卡契并无明确指射,伍尔夫极可能是其潜在的批评对象之一。例如,在《当代现实主义的意义》中,他曾谈及身为现代主义作家的伍尔夫对于日常现实的曲解。在一定程度上,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框架内,有关于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念的批评可被界定为“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这两股主流文学思潮间的互相角力。肖瓦尔特始终无法理解伍尔夫所批判的“西方男性人文主义的中心概念”[20]4,即一元论自我(the unitary self)。在法国后结构女性主义者眼中,这种一元论自我通常是“男性的自我”[20]4,而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念正是对这种男性、一元论自我的强力解构。对于肖瓦尔特有关于《一间自己的屋子》的批评,莫伊给予了后结构主义特色的逐条回击。例如,她总结道,伍尔夫所使用的语言及其意义被无限延搁。且有别于传统小说,伍尔夫小说中的人物通常并非是权威的叙述者。通过践行这种多角度的叙述方式,一元化的身份被巧妙否定。此外,伍尔夫在文本和理论中韵律般的写作、或革新的叙事策略皆是她本人对于父权制象征秩序中一元论、固定性的消解。
在莫伊看来,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念是解构性质的,它辨识出了常态下男女两性的虚假对立,更摈弃了“父权制意识形态中潜在的形而上学本质主义”[20]9。为了在女性主义理论框架中较为客观地看待伍尔夫及其文学创作,莫伊与时俱进地提出了某些可供选择的解读方式,她重点阐述了法国女性主义哲学家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的后结构女性主义政治观念。在《女性的时间》中,克里斯蒂娃曾把女性主义的斗争划分为三个阶段:自由女性主义、激进女性主义与解构男、女两性二元对立的第三种方式或态度[21]471。这种有关于“身份”、“性别身份”的第三种立场与伍尔夫的双同体观念互有交集。在《一间自己的屋子》中,女性作家玛丽·卡迈克尔(Mary Carmichael)的写作方式即验证了后现代主义视阈下的“第三种态度”。玛丽·卡迈克尔严格执行着女性风格的写作方式,勇于书写新式的情感体验,同时她又成功忘却了自身的性别身份。随后,另一位“玛丽”,玛丽·波顿(Mary Borton)对于二元性别对立的质疑更坚固了这种有关于女性写作议题的“第三种方式”。
除莫伊外,相关评论家亦质疑肖瓦尔特对于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念批评的公允性。例如,在威尔看来,肖瓦尔特对于双性同体观念的评述足以构成一种“严重的谴责”[9]150。比尔(Gillian Beer)同样注意到了肖瓦尔特对于伍尔夫叙述政治的忽视,并敏感地觉察出肖瓦尔特在批判过程中始终流露出的某种焦躁情绪。当谈及伍尔夫对于日常女性经验或生活危机的逃避态度,比尔分析其原因“正是在于伍尔夫否认所有的排序主张是无所不包的”[22]。然而值得指出的是,尽管莫伊否定了相关女性主义者对于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念的批评,她同样承认海尔布伦等双性同体学者在评述该观念时的积极态度。由此,她号召学界对于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念的研究应致力超越传统的英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及其美学范畴。20年代后期,以解构、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法国哲学理论框架正是一个极佳的理论视角,伍尔夫本人也被贴上“颠覆性的、甚至是解构性的女性主义者”[23]的标签。总体上来看,肖瓦尔特、莫伊等女性主义理论家对于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念的激辩可被理解为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中不同阵营传统、不同地理家族间思想交锋的佐证之一。
四、结语
在《西方正典》中,美国当代文学批评家布鲁姆(Harold Bloom)曾坦言,“当今,描述伍尔夫时能保持一种平衡心态或分寸感实为不易。”[24]。作为伍尔夫研究的热点之一,双性同体观念为女性写作提供了某种理论保障。然而,诸多女性主义理论家对于该观念褒贬不一。其中,在肖瓦尔特“女作家批评”学说的研究视角中,伍尔夫双性同体观念沦为女性作家个人情感世界及其文学创作的乌托邦投影。莫伊则尝试以当时学界中流行的理论风尚为标尺,重估了双性同体观念的功效。在这些争议声中,同样也掺杂着某些中立的发声。例如,米诺·平克尼(Makiko Minow-Pinkney)给出了辩证性总结,她判定伍尔夫的双性同体观念把女性主义与现代主义美学较为完美地融合,因此应被有机定义为“一个单个计划的两个侧面”[25]。随着伍尔夫研究视野的多元化、跨学科态势,双性同体观念被提升至了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哲学的思辨高度;又或与现代心理分析学、优生学有所关联。作为一个西方文学、文论关键词,“双性同体”是一个“在理论意义上灵活的术语”[26],其内涵绝不局限于唯一性质的定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