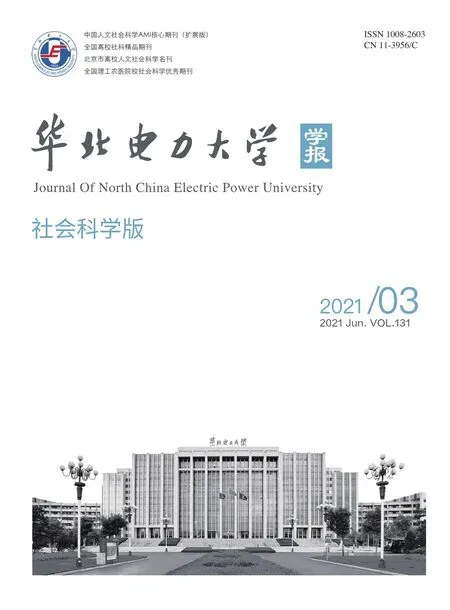从周、克己与为仁
——孔子礼学思想探析
2021-11-29盖立涛
盖立涛
(华北电力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2206)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无序,孔子直面社会无序这个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仁义思想和礼治思想。一方面,孔子提出了自己的仁义学说,以至仁大义立千年之人极①船山谓:“自非圣人崛起,以至仁大义立千年之人极,何足以制其狂流哉?”(参见王夫之.读通鉴论[M].北京:中华书局,2013:547.),开启了中国人内在的道德世界;另一方面,孔子崇尚周代的礼乐文明,希望重建礼乐文明秩序。孔子继承了三代之礼,通过审视三代礼制的变革,提出自己的礼治思想。礼是治国的根据和基础,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礼的合法性和神圣性来源于天,圣人通过取法天道以“制礼作乐”,用礼来统合天道与人情,礼因效法天道而获得神圣性。孔子不仅继承了三代的礼乐文明,孔子对礼的根据和合理性也做出了深入的考察,提出了“礼之本”的问题。春秋之时“礼崩乐坏”,礼的形式出现问题,礼的内在精神也失落了,孔子提出了自己的仁学思想,为礼寻找到新的根基。孔子强调“克己复礼”,把礼的外在约束转变为内在的道德自觉。孔子结合时代的变化,积极对周礼进行革新,突破了周礼的宗法性与封闭性,突出了礼的简易化、世俗化和内在化,凸显了礼的平等性与人文性。
可以说,“从周”是孔子礼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起点,孔子又强调了克己修身的功夫,把礼的外在约束转变为内在的道德自觉。孔子还对礼的根据和合理性做出了深入的考察,提出了“礼之本”的问题,认为仁为礼之本,孔子“以仁释礼”,建立了仁礼合一的思想体系,也奠定了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三代礼制
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礼”字最早出现于殷商的卜辞中。刘熙在《释名·释言语》中谓:“礼,体也。得事体也。”[1]110许慎在《说文解字》中云:“礼,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从示从豊。”(《说文解字·示部》)许慎对“履”也做出了解释,“履,足所依也。”“屦,履也。”(《说文解字·履部》)段玉裁注云:“今时所谓履者,自汉以前皆名屦。”[2]407屦是用麻、葛等制成的单底鞋,后泛指鞋。履也与行有关,有可行、可实行之意。礼“从示从豊”,豊是行礼之器。“事神、致福”也说明了礼起源于宗教活动。郭沫若认为“礼之起,起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这都是时代进展的成果。愈往后走,礼制便愈见浩繁。”[3]96礼可能起源于原始部落祭祀上帝和各种神灵活动,后来由宗教活动逐步扩展到政治生活和日常生活方面。
《礼记·表记》中记载道:“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郑玄谓:“远鬼神、近人,谓外宗庙,内朝廷。”[4]1732夏代虽然敬奉鬼神,但却敬而远之,按照郑玄的解释,夏代重视朝廷事务,而外宗庙事务。“先鬼后礼,谓内宗庙,外朝廷也。”[4]1733殷人则相反,殷人先鬼后礼,重视宗庙事务,而外朝廷事务。“‘尊礼尚施’者,谓尊重礼之往来之法,贵尚施惠之事也。”[4]1734周人最重视礼,重视礼之往来之法。“夏道尊命”、“殷人尊神”、“周人尊礼”,说明三代所尊是不同的,也可看出三代文明存在着差异性。殷人的宗教信仰最为浓厚,从甲骨文卜辞中可以看出,殷人遇到战争、立国、风雨、生育等活动都要问卜,而且殷人祭祀种类多,祭祀活动频繁,是宗教色彩最为浓厚的时代。周人则重礼,由重视宗教事务转向重视人事活动。
在《论语》一书中,孔子也提到了三代之礼。子张向孔子询问道:“十世可知也?”孔子回答道:“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孔子说:“殷代沿袭夏代的礼仪制度,有些损益的,是可以知道的;周代沿袭殷代的礼仪制度,有些损益的,也是可以知道的;将来有继周而起的,就是以后一百代之久,也是可以预先知道的。”马融云:“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统。”[5]26朱子谓:“文质,谓:夏尚忠,商尚质,周尚文。三统,谓:夏正建寅为人统,商正建丑为地统,周正建子为天统。”[6]59此章孔子历陈夏、商、周三代礼之变革,“礼,时为大”(《礼记·礼器》),一时必有一时之礼,此历史之常。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①在《礼记·礼运》篇也出现了与此章相同的语句。“言偃复问曰:‘夫子之极言礼也,可得而闻与?’孔子曰:‘我欲观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征也。吾得《夏时》焉。我欲观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征也。吾得《坤乾》焉。《坤乾》之义,《夏时》之等,吾以是观之。’”(《礼记·礼运》)(《论语·八佾》)包咸云:“征,成也。”[5]36郑玄云:“献,犹贤也。我不以礼成之者,以此二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故也。”[5]36朱子谓:“征,证也。文,典籍也。献,贤也。言二代之礼,我能言之,而二国不足取以为证,以其文献不足故也。文献若足,则我能取之,以证君言矣。”[6]63“征”有两意,包咸认为是成的意思,朱子认为是证的意思。按照包咸与郑玄的解释,这一章的意思是,夏礼与殷礼我可言之,我不以礼成之是因为杞宋两国之君文章贤才不足的缘故。按照朱子的解释,此一章的意思是夏礼与殷礼我可言之,杞宋两国不足取以为证,是由于两国文献不足。刘宝楠云:“夫子学二代礼乐,欲斟酌损益,以为世制,而文献不足,虽能言之,究无征验。故不得以其说箸之于篇,而只就周礼之用于今者,为之考定而存之。”[7]93从夏礼到殷礼、再从殷礼到周礼是一个不断演变的过程,礼的特点是“时为大”,随着时代变化有所“损益”,有所变革。孔子“从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夏礼、殷礼“不足征”,于是,孔子从周,取法周代礼制。
礼是如何产生的呢?《礼运》篇云:“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以贤勇、知,以功为己。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礼记·礼运》)小康社会中“大道既隐”,郑玄谓:“隐,犹去也。”[8]771“天下为家”,最高权力由家族世袭,进入到了“家天下”时代。“各亲其亲,各子其子”,小康社会中的人只亲近自己的亲人,只慈爱自己的孩子。“货力为己”,此时出现了“为己”的自私观念。“大人世及以为礼”,此时出现了礼,用礼来规范社会秩序。在小康社会中,出现了等级差别,出现了争夺,因此需要用礼来规约人们的行为。为抑止日益增多的纷争,执政者制定了一整套礼乐制度,通过礼乐制度来维护社会秩序。但礼制作为一套制度,会出现行久而弊的问题,因此,礼应当随着时代发展而变革。
孔子继承了三代之礼。陈来认为“夏以前是巫觋文化,商殷已是典型的祭祀时代,周代是礼乐时代。”[9]12陈来教授的看法突出了夏商周三代文化之变革,但这种看法,也可能过度强调了三代文化的差异性。三代礼制既有变革,也存在延续性。孔子正是通过审视三代礼制的变革,提出了自己的礼学思想。
二、周代礼制
“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礼记·明堂位》)。周公在文王武王的基础上“制礼作乐”,奠定了周代的礼乐文明。同时,周代礼乐文明也是在继承夏商之礼的基础之上,逐渐形成的一套复杂的礼乐文明。在宋代以前,都是周孔并称,周公在儒家思想中有着很高的地位。“周公是一个真正的克里斯玛人物,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思想家,不仅经他之手而奠定了西周的制度,而且构造了西周的政治文化。”[9]214周公开创的事业和他的思想,也影响到孔子,孔子在周代礼乐文明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思想。
孔子也多次表达了对周代礼乐文明的向往。“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孔安国曰:“监,视也。言周文章备於二代,当从之。”[5]39-40朱子谓:“郁郁,文盛貌。”[6]65周代礼制吸取夏商之礼,礼乐日备,文物日富,孔子美其文而从之。“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孔子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以复兴周礼的方式来重建社会秩序。“‘吾从周’不再是一个政治宣言,而是成了一个文化取向。此后,周代的文化和价值观念,经过孔子的放大和普遍化,成了中国人生命之主流的河床。”[10]36“吾从周”也表达了孔子的价值诉求。面对“礼崩乐坏”的局面,孔子不仅提出了自己的礼学思想,对周礼做出新的解释。同时,孔子还提出了自己的仁学思想,通过为周礼注入新的内在精神的方式来重建社会秩序。
孔子有着对传承周代礼乐文明的责任感和自信心。“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朱子谓:“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6]110孔子深通周代文武周公相传之礼乐制度,相信道在己身。正是对传承周文的责任感和担当精神,让孔子面对困境,也能泰然自若。
王国维先生指出:“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而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之结体也。”[11]135在王国维先生看来,周代制度典礼只是表层,周礼的内在精神是尊尊、亲亲、贤贤、男女有别四者。王国维先生又云:“以上诸制度皆由尊尊、亲亲二义出,然尊尊、亲亲、贤贤此三者治天下之通义也。周人以尊尊、亲亲二义,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而以贤贤之义治官。”[11]133王国维先生认为,周代制度皆由尊尊、亲亲二义出,周人通过尊尊、亲亲二义,来统合亲族,“上治祖祢,下治子孙,旁治昆弟”;又以贤贤之义来治官。王国维先生的看法很有见地,周代礼制建立在分封制和宗法制的基础上。《荀子·儒效》篇云:“(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武王与周公分封了天下诸侯,分封的诸侯国作为藩篱拱卫周朝。周代宗法制的基本原则是“立嫡以长不以贤,立子以贵不以长。”[12]18宗法制以宗族血缘关系为纽带,利用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来确定政治关系的上下尊卑贵贱,来调整统治阶级内部权力和财产的继承与分配。
“亲亲”优先于“尊尊”和“贤贤”。“某一官职虽不世袭,但其继任者必定是世代从某一固定的氏族中选拔出来的,血缘在这里仍然是不可逾越的界限。”[13]在《周礼·天官冢宰·大宰》中记载道:“以八统诏王驭万民:一曰亲亲,二曰敬故,三曰进贤,四曰使能,五曰保庸,六曰尊贵,七曰达吏,八曰礼宾。”在《礼记·丧服小记》中记载道:“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在《天官冢宰》和《丧服小记》中都把“亲亲”放到了首位,可以说,“亲亲”是周代社会的第一组织原则。
周礼实现了对殷礼的变革,由殷礼强调礼的宗教性,转向突出礼的政治性、人文性和道德性。“周初对宗教之祭祀,已由宗教之意义,转化为道德之意义,为尔后儒家以祭祀为道德实践之重要方式所本。”[14]26“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祭祀是周人最重视的活动,也是周礼最核心的部分,不过周人寓道德于祭祀之中,使祭祀更具有道德内涵和人文内涵,实现了从尚质到尚文的转变。
周礼涉及的范围极广,国家制度,社会的道德规范,国与国之间的朝觐、聘问、交接、来往等礼节,社会生活中的冠、婚、朝、聘、丧、祭、宾主、乡饮酒等礼仪活动,都需要通过“礼”来规范调节。“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国家非礼不治,社稷得礼乃安,故礼所以经理国家,安定社稷。”[15]127国家社稷也由礼来安定,礼具有经理国家,安定社稷的重要功能,礼还可以教民和睦,可以“次序民人,利益后嗣。”[15]127“故礼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于未形,使人日徙善远罪而不自知也。”(《礼记·经解》)人之为人的根据在于礼,“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礼记·礼运》)。礼也调节着人伦关系,整合着社会伦理,让国家、社会、人伦秩序更加和谐有序。
“夫礼,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礼记·礼运》)礼是建立社会秩序的保障和根据,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礼的合法性和神圣性来源于天,圣人通过取法天道以“制礼作乐”,用礼来统合天道与人情,礼因效法天道而获得神圣性。
三、孔子对周礼的继承和发展
在《论语》中“礼”出现了75次,礼在孔子的学说中占有重要的地位①有的学者认为孔子的思想体系是仁礼结构,“孔子思想是仁与礼二位一体结构”。(参见张岂之.中国思想学说史(先秦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246-247.)还有学者认为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立于礼’是孔子的中心思想”。(参见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128.)劳思光则认为“‘仁、义、礼’三观念,为孔子理论之主脉”,劳思光提出了“仁义礼三位一体”说。(参见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第一卷)[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81.)。孔子既重视三代之礼,同时又对礼做出了新的解释,并在礼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仁学思想。
礼不仅仅是制度礼仪,礼也承载着文明,承载着价值。礼承载着文明,这是孔子重视礼的根本所在。孔子所处的时代“礼崩乐坏”,出现了僭越礼制的行为。鲁大夫季孙氏以“八佾舞于庭”,僭用了天子之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面对诸侯大夫僭越礼制的行为,孔子非常不满。“孔子的批评,一面是历史的观念,根据文王、周公,从礼之本源处看。一面是人道的观念,根据天命、性、仁、孝、忠恕等等的观念,从礼的意义上看。”[16]98孔子对僭越礼制行为的批判,一方面是依据周代礼制来判定是否合乎礼;另一方面是按照孔子自己的道德标准来判定是否合乎礼。“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论语·季氏》)当天下有道之时,制礼作乐以及征伐都由天子来决定;天下无道之时,制礼作乐以及征伐便由诸侯来决定。现在诸侯大夫纷纷僭越礼制,导致天下无序,这是孔子重建礼制的原因所在。
孔子继承了周礼,同时又有所革新。“以德、礼为主的周公之道,世世相传,春秋末期遂有孔子以仁、礼为内容的儒家思想。”[17]279周代是礼乐的时代,而春秋时代是德性的时代,孔子重视礼,又在礼的基础上提出了仁学思想,为礼寻找到新的内在精神,将礼安立在内在之仁的基础上。
孔子还主张“为政以德”、“为国以礼”,强调以德礼为主,以政刑为辅助。孔子强调“为政以德”、“为国以礼”,就是使民众知“仁”懂“礼”,通过教化构筑起“德治”与“礼治”为本的理想社会,也实现了寓道德教化于政治之中,政治也通过教化得以提升。
“礼以时为大”,礼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变革。随着社会发展,礼出现了简易化的趋势。孔子的礼学突破了周礼的宗法性和封闭性,强调了礼的普遍性和平等性。一方面,孔子在整理、传授周代典章制度过程中娴熟地掌握了周礼;另一方面,孔子结合时代变化,积极对周礼进行革新。
(一) 简易化
周礼复杂繁琐。《礼记·礼器》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礼记·中庸》云:“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周礼的特点是文胜质,于是孔子损文益质。孔子的弟子林放曾经向孔子询问礼之本的问题,林放追问“礼之本”也就是探求礼的内在精神。孔子称赞了林放,孔子不仅仅关注礼的形式,更重视礼的内在精神,孔子损文益质,丰富了礼的内在精神,也实现了礼的简易化。“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论语·子罕》)礼的简易化使礼由贵族性向平民性转变,礼可以深入民间,孔子也为重建礼乐秩序寻找到新的社会基础。
(二) 平等性
周礼强调君、父、夫的权威性,《仪礼·丧服》说:“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夫至尊也”。孔子则强调了礼的平等性。“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孔子又提出“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在一定程度上,孔子强调了君臣之间关系的相互性和平等性。《礼记·曲礼上》云:“礼不下庶人”,周礼最早施行于贵族阶层。孔子强调以礼教民,礼可以施行于社会的各个阶层,礼的平民化也突出了礼的平等性和普遍性。
(三) 人文性与世俗性
孔子也重视祭祀,重视宗教性的祭天、祭祖,重视对逝去父母的祭祀。《礼记·祭统》云:“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祭礼和丧礼是孔子最为重视的,孔子重视祭礼和丧礼,以礼乐化民,引导民众向善。“礼,国之干也。”(《左传·僖公十一年》)礼也是治国的工具。“孔子把周礼的神秘性转换成世俗性,天人关系转向人伦关系,在礼的活动内容上使礼世俗化,贴近于现实生活。”[18]孔子把周礼的神秘性转化为世俗性,突出了礼的人文性和世俗性。
(四) 礼乐的内在化
孔子在齐听到《韶》乐,三月不知肉味。子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韶》是舜乐名,陈舜后,陈敬仲奔齐,齐亦遂有《韶》乐。“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孔子多次表达了对《韶》乐体现出的音乐之美的欣赏,乐以载道,“三月不知肉味”也体现了乐之感人之深。孔子对音乐的教化作用深信不疑,“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19]2345乐应该体现“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论语·八佾》)的中和原则,孔子倡雅乐,反对郑音,“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论语·卫灵公》)音乐有着引导人心向善的作用。圣人观音知政,以礼乐化民。“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礼与乐不能仅仅体现为外在的形式,礼乐应该体现其内在的仁义精神,表现出内在之仁。
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表现了对传统的迷恋,“只要宇宙还存在着神秘性,只要人类还在其中寻找秩序,只要他们还好奇地希望认识它,那么他们就会创造、完善和迷恋于传统。”[20]345孔子不仅仅继承了传统礼学思想,同时又在仁义价值基础上对礼乐制度进行了革新,提出了新的礼学思想。
四、孔子对周礼的突破
孔子不仅仅继承了周代的思想资源和制度资源,同时提出了更为根本的问题,就是“礼之本”的问题。春秋之时“礼崩乐坏”,礼的形式出现问题,礼的内在精神也失落了,礼需要寻找到新的基础。“礼崩乐坏不仅仅表现为外在礼制规范的破坏和各种僭礼、越礼行为的大量发生,更严重的问题是周礼精神的失落。”[13]孔子提出了自己的仁学思想,为礼寻找到新的根基。正是在仁义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周礼的突破和变革。我们知道周礼的精神实质是“亲亲”,孔子则强调“爱人”,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周礼的宗法性和封闭性,扩展了礼的普遍性。孔子的仁学思想也突破了周礼“亲亲”原则所规定的血缘界限,仁成为普遍性的道德原则。
孔子在仁的基础上丰富了“礼”的内在精神。孔子也把周代礼制提升为超越时代限制的儒家之“礼”。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包咸曰:“言人而不仁,必不能行礼乐。”[5]32在孔子看来,仁为礼本,失去了仁,礼乐也就失去了其内在的精神,如果空有礼乐的外在形式,也不足观。“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林放向孔子请教礼之本的问题,孔子称赞了林放。“礼之末节,人尚不知,林放能问其本,其意非小,故曰‘大哉问’也。”[5]33朱子谓:“礼贵得中,奢易则过于文,俭戚则不及而质,二者皆未合礼。然凡物之理,必先有质而后有文,则质乃礼之本也。”[6]59在这里,孔子跟弟子林放讨论了礼之本的问题,礼之本的问题在先秦之时有一个转变。《左传·昭公二十五年》记载道:“晋侯谓女叔齐曰:‘鲁侯不亦善于礼乎?’对曰:‘鲁侯焉知礼?’公曰:‘何为?自郊劳至于赠贿。礼无违者,何故不知?’对曰:‘是仪也,不可谓礼。礼,所以守其国,行其政令,无失其民者也。’”叔齐做出了礼与仪的区别,仪是外在的形式,而礼则关系到守国、行政令、得人民等根本问题。礼与仪的区别说明春秋之时已经在思考礼之本的问题。《左传·桓公二年》晋师服说:“夫名以制义,义以出礼”,“义以出礼”说明义更为根本,礼建立在“义”的基础上。在孔子之前,人们把义作为礼之本。
孔子在思考礼之本,追问礼的本源时,突出了仁的重要性。在论证三年之丧的合理性时,认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论语·阳货》)在这里,孔子把人对父母的感恩怀念之情作为了礼的本源,把仁作为礼的本源。仁成为礼的基础,礼来源于内在之仁。同时,孔子也把礼纳入人心,把行礼变为自觉的行为。“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自觉、自主的“复礼”行为才能够接近仁。礼由外在约束转变为内在的道德自觉,礼由仁而获得了提升。孔子强调“爱人”(《论语·颜渊》),强调“泛爱众”(《论语·学而》),仁就突破了周礼“亲亲”原则的限制,仁与礼的普遍性得到了提升,仁成为儒家最根本的价值原则。
孔子“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礼记·中庸》)一方面,孔子向往周代礼乐文明;另一方面,孔子又向往尧舜之道,向往大同社会。尧、舜、文、武、周公都是孔子取法的对象,都是孔子心目中的圣人,但在孔子看来,尧舜之道与文武周公之道还是有所不同的。周代实行礼治,而尧舜之时是无为而治。可以看出,孔子对周礼做出了根本性的反思,并进一步提出了道治、德治的思想。①“孔子既重视五帝时期的无为之道、道治、德治,崇尚天下为公,又重视夏商周三代的礼治。”(可参见盖立涛.道治与礼治之间——《礼记·礼运》篇大同小康关系新论[J].哲学动态,2017(3).)
五、结语
春秋时期“礼崩乐坏”,社会无序,孔子直面社会无序这个问题,通过审视三代礼制的变革,提出了自己的礼学思想。礼是治国的根据和基础,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规范。礼的合法性和神圣性来源于天,圣人通过取法天道以“制礼作乐”,用礼来统合天道与人情,礼因效法天道而获得神圣性。“礼以时为大”,礼随着时代变迁而逐渐变革,随着社会发展,礼出现了简易化的趋势。孔子的礼学也突破了周礼的宗法性和封闭性,强调了礼的普遍性和平等性。一方面,孔子在整理、传授周代典章制度过程中娴熟地掌握了周礼;另一方面,孔子结合时代变化,积极对周礼进行革新。孔子突出了礼的简易化、世俗化和内在化,凸显了礼的平等性与人文性。可以说,“从周”是孔子礼学思想形成的历史起点,孔子又强调“克己复礼”,把礼的外在约束转变为内在的道德自觉。孔子还对礼的根据和合理性做出了深入的考察,提出了“礼之本”的问题,认为仁为礼之本,孔子“以仁释礼”,建立了仁礼合一的思想体系,也奠定了儒家思想的理论基础。孔子正是站在仁义价值基础上对礼乐制度做出了根本性的反思,通过继承三代之礼,提出了自己的礼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