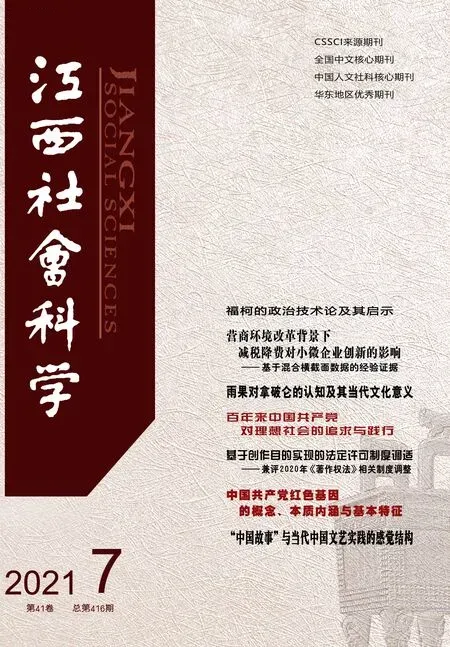以“哲学的科学”思考摄影
——拉吕埃勒非摄影思想初探
2021-11-29黄其洪马文灏
■黄其洪 马文灏
拉吕埃勒认为,标准的哲学和摄影理论都是思想试图决定实在的媒介,他反对这种企图,提出了非摄影思想。非摄影摒弃通过哲学思考摄影的方式,重新思考摄影的本质。非摄影用“克隆”的思维方式审视摄影,接近了彻底内在性的实在本质。拉吕埃勒对科学的看法是在与阿尔都塞的观点交锋中形成的,非摄影拥抱科学以保持自己的开放性,避免自己陷入“哲学决定”的结构,而照片的内容构成自身内在的现实和真理,成为独特的“在照片中的存在”,而不是标准哲学认为的那样,是对实在的复制和反映。拉吕埃勒的非摄影思想与量子学说的互补性原理非常相似:摄影中同一性和差异性的对立可以通过“量子叠加”的状态来解决。通过克隆分形算法的无限性特征,拉吕埃勒发展出一套可以使摄影的内涵无限延伸的“广义的分形”。
拉吕埃勒目前有两本著作论述自己的“非摄影”思想,一本是2011年出版的《非摄影的概念》,一本是2012年出版的《虚构摄影——一种非标准的美学》,在前者中,拉吕埃勒由自己的非哲学思想出发对摄影艺术进行了剖析,进而为他在后者中提出非美学思想开辟了道路。以这两本著作为基础,国外学界已经对拉吕埃勒的非美学思想展开研究,如乔纳森·法迪的《拉吕埃勒与非摄影》、约翰·罗伯茨的《观念与摄影:对弗朗索瓦·拉吕埃勒的抽象概念的批判》和汉娜·拉敏的《能从照片中看到的:作为积极的野蛮主义的非摄影》,等等,这些著作和文章或详尽或简略地介绍和剖析了拉吕埃勒的非摄影与非哲学的关系、非摄影思想与以往哲学家的思想交汇等重要问题,本文希望在这些基础上,通过对非摄影的理论位置、重要特征、操作流程等内容的深入分析,开启国内对拉吕埃勒非美学思想的研究,激发国内学界对这位已经蜚声海外,却在国内少有人知的哲学家的研究兴趣。
一、非哲学观下的非摄影
首先简单地概括一下非哲学与非摄影的关系:非摄影是拉吕埃勒非哲学思想的子项——非美学的典型事例,也是拉吕埃勒阐释自己非美学思想的起点(与非美学思想并列为非哲学思想的子项的,还有非马克思主义、非基督教思想等内容)。需要注意的是,拉吕埃勒所谓的“非……(Non-)”并不表示反对和否定,而是“非标准……(Non-standard)”的简写,更多地代表一种异于传统的新思路和新见解:“‘非摄影’首先并不意味着对摄影的某种荒谬的否定,就像非欧几何并不意味着我们否定了欧氏结构。”[1](P2)
拉吕埃勒把以往的哲学都称作标准哲学,在他看来,这些标准哲学都“自以为是”,具体表现为:标准哲学不论流派,总是试图用外在于实在的范畴去规定实在,从而充满主观性和偶然性,也失去来自实在本身的规定。[2]拉吕埃勒列举柏拉图、海德格尔、德里达等人的例子,对柏拉图来说,实在是超越空间和时间的、永恒的、完美的关于形式的世界;对海德格尔来说,实在是关于“存在”的世界;对德里达来说,实在是关于“差异”的世界。[3](P2)但在拉吕埃勒看来,以往这些哲学家们对实在的所谓解释,无非是哲学家们从某个角度去象征或者展示实在,远远谈不上揭示实在本身,充其量“只能说明哲学自身的存在罢了”[4](P119)。对于拉吕埃勒来说,实在是内在于自身的元一,是彻底的内在性,是不可被思想规定的,相反,一切思想都是由实在决定的,以往的哲学家们把自己对实在的所谓解释当作对实在的正确揭示和呈现,这就是拉吕埃勒所说的以往哲学的“自以为是”,他将这种“自以为是”命名为“充分哲学原则”,并将从中发展出的结构称为“哲学决定”。[2]
那么,拉吕埃勒的非哲学又是怎样看待实在与哲学的关系问题呢?由于实在在拉吕埃勒眼中是彻底的内在性,故非哲学和哲学一样无法从这种彻底内在的实在开始,但拉吕埃勒认为,尽管任何思想都不足以孤立地、完整地把握实在,但是,以往的标准哲学的内容至少是“真实存在的”,因而可以把不同的哲学看作对实在的不同面向或者环节的不同表达,这样一来,哲学就脱离了它的“自以为是”,降低为认识实在的材料了,由此非哲学就可以使用各种哲学,把它们当作认识实在的材料,以做出对实在的非哲学话语。[2]在哲学之外,拉吕埃勒也尝试从广泛的文化、科学、宗教和艺术等文化门类中寻找材料,以期建立起对实在的局部乃至整体的认识。正因为如此,拉吕埃勒毫不避讳在哲学研究中对科学的使用,甚至骄傲地将自己的非哲学称为“第一科学”“哲学的科学”,意图站在哲学之外使用和反思哲学(有关非哲学对科学的使用以及“哲学的科学”这个术语的含义,在后文中还会有进一步的阐释)。
摄影正是拉吕埃勒选择的材料之一。摄影技术出现于19世纪中叶,这项技术一经问世,就具有双重属性:有的人把它看作客观地观察世界的科学工具,有的人把它看作创造性的、主观的表达媒介。这种双重属性导致摄影理论家们长期呼吁关注摄影实践中存在的对现实的操纵和扭曲,拉吕埃勒认为,这与标准哲学在结构上有相似之处。他提出,无论是把摄影看作对现实的客观反映,还是把它看作一种对现实的中介和操控方式,都未跳出关于实在的标准哲学式的主题,标准哲学和摄影都以不为人注意的方式向实在施加了自己的结构和框架,换言之,拉吕埃勒把摄影和标准哲学视为摄影师和哲学家对实在施加不合理的结构、框架和解释的两种不同形式的媒介。
而主张非哲学和非摄影的人对这种施加提出异议,拉吕埃勒这样写道:“摄影绝不是通过对‘世界’(这里的‘世界’可理解为实在)的分割或决定而获得的关于世界的复制或镜面形象,也不是对原本世界的劣化的复制品……摄影不是对世界的降解(degradation),而是一个与世界‘平行’的过程。”[4](P24-25)也就是说,摄影和哲学的框架和结构是局部的,仅仅内在于它们自身,它们不足以决定实在。拉吕埃勒用非哲学使思想摆脱哲学决定的努力,与他用非摄影使摄影摆脱对实在的依附是高度一致的。非摄影要摒弃那种认为摄影使实在可见的观点,对拉吕埃勒来说,摄影使我们能见到的仅仅是照片中的图像而已,只是对象的一个面向或者环节,而不是对象本身,就像哲学家以为照片是对实在的阐释,但实际上只是揭示了实在的一个面向或环节。
那么,非摄影究竟是什么呢?拉吕埃勒自己写道:“非摄影不是一种新的技术,而是一种对摄影及其产生的实践的本质的新的概念和描述,是一种不再通过哲学思考摄影的必要性,是对摄影是什么和摄影能做什么的重新思考。”[1](P4)这种新的思考是如何进行的,具有怎样的特征呢?
二、非哲学为非摄影提供“克隆”的思维方法
“克隆”是拉吕埃勒进行非哲学研究时采用的最重要的思维方法,其重要性堪比标准哲学研究中的“概念”。众所周知,“克隆”这个词来源于生物学,克隆出的后代个体会高度相似于被克隆体,而在非哲学中,克隆体则高度相似于实在本身。非哲学的克隆体是彻底的、只在非哲学的语境下才有意义的“新”词汇,它们选自标准哲学,但已经不再像它们在标准哲学中那样拥有决定实在的能力。我们或许可以参考安东尼·保罗·史密斯对拉吕埃勒的“克隆”的解释:
我们可以从意识到克隆既不是原本物体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原本物体之外的什么东西的反映这一点开始,理解是什么吸引了他使用这种“概念的”伪装。克隆体有着自己的身份,因此不是简单的反映或复制,而是带有与它所克隆的材料相同的基因结构的独立个体。通过这种方式,克隆体就在克隆的过程中带出了实在的本质,但又不能从任何意义上对实在有所宣称。[5](P83)
通过克隆的方式,拉吕埃勒的非哲学中的概念(或说克隆体,拉吕埃勒避免使用“概念”这个词)带着实在的某种本质,这种本质是它与那个内在于一切、因而与一切都不可建立联系的实在的“非(标准)关系”。可以说,非哲学的克隆体就是被一种与实在的单边关系所建构的,而克隆的过程就是以一种内在性的模式重新审视哲学的材料。这里可能还有人会质疑这样一个问题:既然拉吕埃勒避免使用“概念”这个词,为什么还要将他关于非摄影的著作命名为《非摄影的概念》呢?这里给出这样一个可能的解释:“非摄影的概念”是一个外在于非摄影的内在程序的“哲学的”术语,拉吕埃勒这样使用它,是为了吸引那些还停留在标准哲学中的读者,引导他们进入文本,并最终放弃标准哲学中的概念的思维方法,转而采用“克隆”这一富有创造性的非哲学的方法。
可以说,非摄影思想也是拉吕埃勒的非哲学在摄影领域的克隆,拉吕埃勒试图将摄影从充分摄影原则中解脱出来,正如他试图将哲学从充分哲学原则中解脱出来一样。拉吕埃勒反对充分摄影原则,源于他反对现实主义者和结构主义者所持的摄影观,前者认为摄影能经验地复制世界,后者认为摄影足以重构现实。拉吕埃勒认为,这样的观点会导致摄影的哲学对实在的或隐或显的决定,因为依照这两种观点,实在要么在照片中反映出来,要么在照片中重构出来,由此,摄影的性质便决定在这种与实在的预设关系中,非摄影的目标就在于一次性地打破这种哲学和摄影思想的双重决定——拉吕埃勒认为摄影不仅是技术的行为,还是哲学自发的自我解释。[1](P8)这里可以引出一位摄影学家——威兰·弗鲁塞尔,他的观点与拉吕埃勒相似,他在《走向摄影哲学》一书中提出,无论黑白的还是彩色的图像,都是一种“理论的图像”,因为实在或者肉眼可见的世界不是黑白的,也不是胶片或数字化编码的色彩模拟的,所以照片代表的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抽象”,是“概念被编码到相机用来描绘世界的化学或数码结构中(的体现)”。在弗鲁塞尔看来,照片是一个“技术的集合体”,通过这个集合体,实在与世界都被概念地编码化了,这使得照片不是世界的“反映”,而是世界的转化、变异[6](P44),用拉吕埃勒的话来说就是“克隆”。
拉吕埃勒与弗鲁塞尔对“摄影不是对世界的‘反映’”这一观点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们都认识到摄影与实在之间的差异,但拉吕埃勒有意与弗鲁塞尔保持距离,因为在他看来,弗鲁塞尔的方法还是太过哲学化。弗鲁塞尔是从一个囊括本体论、概念和摄影的技术本质的程序来思考摄影的,相反地,拉吕埃勒的非摄影拒绝决定摄影的本质,也拒绝决定其与实在的关系,在拉吕埃勒看来,摄影不需要本体论的依据,给摄影寻求本体论依据是哲学为了展示自己存在的“自以为是”的行为。拉吕埃勒的目的就是要见证在没有标准哲学的情况下,摄影可能会变成什么样子。拉吕埃勒将在反还原主义中,根据多种非稳定化的和去等级化的本质重新设置摄影理论:“摄影既不能归结为它的技术条件,也不能归结为与媒介、知觉或审美规范相联系的经验的集合体,它是一个内在的过程。”[1](P39)在非摄影的视域中,摄影不再是一个固定的本体论范畴,而是一个思想和图像共同使一种激进的、非决定性的思维模式成为可能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科学的介入和参与。
三、非摄影对科学的使用
科学究竟怎样介入非摄影的构造过程呢?前文已经提到,拉吕埃勒从广泛的文化、科学和哲学中寻找材料,而在他开创自己的非摄影思想的过程中,发掘和延续了罗兰·巴尔特对摄影中的科学的思考,并加入自己克隆的两个科学概念,一是量子理论,二是几何分形,这后来成为他的非摄影思想的重要特征。但在介绍这些之前,可以先介绍一下拉吕埃勒有关“科学”的看法是怎样形成的。
拉吕埃勒对科学的看法是在与他的老师阿尔都塞的观点交锋中形成的。阿尔都塞认为科学高于哲学,因为哲学只是批判错误,科学却要内在地再现实在。但前文已经提过,在拉吕埃勒看来,实在是彻底的内在性,一切思想和知识都是由实在决定的,这个决定过程是不可逆转的、单边的,而正是由于这个过程是不可逆转的,每一种知识和思想都同样不可能完整地再现实在,科学与哲学之间也就不存在谁高于谁的问题,因而拉吕埃勒认为,科学与哲学具有同一性,且科学和哲学的地位是真正平等的。[7]由此,参考阿尔都塞的“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解释——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社会历史发展的内在深层结构,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区别于“非科学”的意识形态,成为社会历史的“科学”——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拉吕埃勒要把自己的非哲学称为“哲学的科学”。相似的,拉吕埃勒认为非哲学能够揭示各种哲学受制于其中的超历史的不变结构,使我们能够把握到各种哲学的普遍本质,因而非哲学就是关于哲学的“科学”。[2]
现在回到正题,我们可以从拉吕埃勒对罗兰·巴尔特的讨论和反思中,一窥非摄影中“科学”的内涵:
罗兰·巴尔特的著作《明室——摄影札记》在当代摄影理论中是无法忽视的存在。在这本书中,巴尔特以自己对摄影作品的欣赏为范例,试图将摄影的欣赏者的主观的情感经验理论化。在撰写该书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常常受到“科学与主体性之争”的困扰,他困惑于是否存在一种能够将个体性与普遍性连接起来的科学——他最初认为这种摄影的科学就是摄影的本质,但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他逐渐转向了建立一种“关于独特的存在的科学”,而一张关于他母亲的“冬日花园里的照片”帮助他实现了这个目标,他写道:“这张照片是至关重要的,它乌托邦式地为我实现了(本来)不可能的关于独特的存在的科学。”[8](P71)
拉吕埃勒克隆和发展了巴尔特的“关于独特的存在的科学”概念,并反思巴尔特对“冬日花园里的照片”的评价。他认为:“摄影的科学是独特的,也的确是一种关于特性的科学;但只有当把它的独特性从它的哲学和形而上学的解释中祛除时,这种科学才是彻底地可能的。”[1](P43)对拉吕埃勒来说,巴尔特母亲五岁时的这张照片对巴尔特母亲的“独特的存在”来说确实是“不可能的科学”,因为巴尔特母亲在照片上的形象仅仅是一种在照片上的形象而已,因此不能构成对其独特存在的“科学”,真正使巴尔特母亲变得独特的,是她“没有复制品”[1](P43-44)。在拉吕埃勒看来,巴尔特受限于标准哲学的思考方法之中,他对照片的观看和思考成了“半真实半理念的混合”[1](P34),关于独特的存在的摄影科学是不可能的,但关于独特的“在照片中的存在”的科学还是可能的。
拉吕埃勒的摄影的科学紧紧把握住了“在照片中的存在”的特性,“照片中的存在”赋予了巴尔特对母亲的一种新的“理念”,也就是拉吕埃勒在《非摄影的概念》中提及的“照片是一种理念——一种影像中的理念”[1](P37),巴尔特观看“冬日花园里的照片”时体验到的,是他的母亲在照片的图像中的独特性,是他的母亲“在照片中存在”的独特性。经由摄影成为可能的,正是这种“关于特性的科学”。[3](P35)
“在照片中的存在”,显然,拉吕埃勒这个词还受到了胡塞尔现象学的影响,当然他自己也承认这一点:“为了重现和激进化胡塞尔那里所开始的一种区分,我将把照片拍到的东西,即照片‘中’出现的东西、一种完全从世界的超越性中抽取出来的东西,与照片相区分。”[1](P28)胡塞尔认为,现象学家应该关注所有出现的东西,而不必关注这些出现的东西是否是真实的,就如同我们说一个噩梦是可怕的,但不必计较噩梦中的事件是否是真实的。拉吕埃勒认为,照片的内容构成“照片中的存在”,它包含它自己作为图像的内在现实和真理,它摆脱标准哲学下摄影是把可见的世界复制成实在的观念,构筑起一种非哲学思想的范式。
这种思维范式究竟为何被拉吕埃勒称为科学呢?可以把拉吕埃勒笔下的科学理解为一种对科学思想的“通用性(generic)”,所谓“通用性”,指的是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皆有的对新思想的开放性和对实验的开放性[3](P35),国内有一些学者也直接称之为“科学性”[7],将其与“科学”区别开来。拉吕埃勒使用“科学”这个词,是要借用科学的那种在实验之前不会决定任何事物的立场,意在以实验的方式处理作为原材料的哲学,从而抵制哲学决定的结构,使事物停留于未决定的状态之中。可以说,拉吕埃勒的“科学”就是自己的非哲学的一种“克隆”。这里不得不引用亚历山大·加洛韦的评价,他认为(以往的标准哲学的)哲学家们“永远在黑暗和光明之间通行”,哲学通过对其所谓的从黑暗到光明之路的回顾性叙事来自我确证;而“(对拉吕埃勒来说)问题不在于哲学处于黑暗之中,而在于哲学尚未完全处于黑暗之中”[9](P134)。换言之,问题在于哲学拒绝接受事物的未决定状态,具体到摄影领域而言,哲学不能忍受摄影的模糊性,不能忍受对摄影表达或决定实在的能力的确证处于悬而未决的状态;而对于拉吕埃勒的非哲学来说,就是要使事物停留于黑暗和未决定之中。拉吕埃勒通过对科学的如此这般的使用,就无须去确证思想从晦暗走向光明的哲学叙事。
可以说,非哲学的科学类似于“实验艺术”——在实验艺术中,艺术家通过实验发现或创造新的艺术形式,同样,非哲学也用哲学的原材料进行实验,发现或创造新的思想形式,“科学在这里为我们服务的不是它的结果或它所产生的知识,而是它的立场”[1](P33)。科学的立场就是科学的“通用性”,它使人们摆脱了经典和教条的桎梏,赋予人们进行实验和探索的能力,改变了人与哲学的关系。在非摄影领域,这种“通用性”将使以往我们熟悉的摄影行为及其理论陌生化,为那些实验性的有关摄影的思想开辟道路。
四、“非摄影”思想对量子学说的克隆
拉吕埃勒从物理学中克隆量子理论,这是一个关于不确定性的理论,其核心原则之一就是物理学家海森堡在1927年提出的“不确定性原理”(又称“测不准原理”),即不可能在某个时刻精确地同时确认一个粒子的位置和速度,对其中一个知道得越多,对另一个知道得就越少。不确定性原理使完全知晓量子系统中的一切成为不可能的妄想,制造一个先天的、认识论上的宿命缺陷。在这个原理提出后,海森堡的导师玻尔认为,研究量子现象需要一个全新的哲学框架,经典的物理学概念框架对于研究行星这种符合我们日常生活直觉的宏观物体的运动是有用的,我们依然可以从因果、位置、动量等角度入手,但用来理解量子的行为却不行。在量子领域,一个粒子可能在某个时间不只出现在一个地方,经典力学对物体运动的解释完全失效了,甚至量子领域中物体的现象学特征都变得相当奇怪,例如电子就表现出波粒二象性的特征,玻尔则提出“互补性原理”来解释这种反直觉的现象。
互补性原理是非摄影从量子学说中克隆的第一个特征。互补性原理认为,量子现象无法像经典力学那样从一个角度一次性地完备描述出来,而需要一系列互补的原理,通过对量子的不同面貌的描述来解释量子现象。关于量子的内在性质的知识都需要从实验中推导,然而不同实验的条件可能是不相容的(比如研究量子在某个方向上的位置的实验与研究量子在这个方向上的速度的实验,二者的实验条件是完全相反的),每个实验都只能揭示量子的某个独立的面相,这些不同的面相的知识是互补的。[10]这与拉吕埃勒的非哲学观非常相似:非哲学观认为,不同的标准哲学可视为对实在的不同表达,每一种哲学,在去除了其中的哲学决定的结构之后,都可以看作对实在的某种面相的平等描述;而非哲学可以使用各种哲学,把它们当作认识实在的互补性材料,以形成对实在的非哲学话语。[11]
在以往经典的物理学中,确证一个物体的速度和位置是可能的,波和粒子也是截然不同的东西。但在量子的世界里却全然不同,量子在没有观测者的情况下总是处于一种叠加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粒子的出现位置完全是概率性的,甚至同一个粒子可以同时出现在两个不同的地方。①换言之,叠加状态中的粒子是无法被决定的。量子世界并不按照通常观念中的前与后、因与果的概念运行,研究(或观察)量子世界的行为本身就会对量子世界造成影响,观察者和被观察者都是量子系统的一部分,因此它们是共同干涉、共同决定的系统。这与后结构主义对古典认识论的批判非常相似。量子学说对社会科学的影响不仅仅是拉吕埃勒克隆了它,在人类学领域,如今的人类学家在研究某个文化的过程中向这个文化施加的影响,就是一种受到了量子物理学思维的影响的现代认识论的实践。
言归正传,拉吕埃勒怎样在非摄影之中克隆了量子理论呢?首先,他克隆了“量子叠加”这个术语来解释他眼中的摄影。他认为,摄影是一种关于同一性与差异性的激进的二元对立——同一性指的是摄影是一种客观地观察世界的科学工具,差异性指的是摄影是一种不依附于世界的主观表达媒介——在这种二元对立中,同一性和差异性都保留下来,都无法超越。拉吕埃勒把这种情况称为摄影的“叠加”状态,叠加状态中的双方都不能排除或超越对方,任何一方都不具有优先地位。这种叠加的状态并不是简单的混合,而是一种“既同一又差异”的结构,一种同时处于两种状态的状态。[10]此外,量子叠加的状态是一种充满偶然性和不确定性的状态,非摄影中对量子理论的克隆是一种保持自己对偶然性开放的思维方式,在非摄影的视角下,摄影活动中可以有无限的偶然性因素和主观性因素参与其间,无论是摄影的主体还是摄影的客体,都是不确定的,都是向无限可能性开放的。甚至对摄影作品的欣赏和评价本身也参与摄影作品的建构,摄影作品不是作为静止的现成作品摆在我们的意识之外,被动地接受我们的欣赏,而是在主体欣赏的过程中重新产生差异性的新意义,因此,非摄影使传统摄影的确定性和决定性归于无效。
五、“非摄影”思想对几何分形的克隆
“分形”一词是由数学家本华·曼德博在1977年创造的。分形是一种在尺度上由大到小的每一个部分都在形状上近似整体的图案,例如,画一个正方形,然后把它分成九个相等的小正方形,无视中间的小正方形,把剩下的每一个小正方形再分成九个更小的正方形,然后再无视每一个小正方形中心的更小的正方形,把这个步骤无限地重复下去,就得到一个分形图案。理论上讲,这一行为可以无限重复,并且图案中所有正方形的线段总长度接近无穷大,而总表面积接近零[3](P45),这就是分形图案的无限性特征。
分形图案的无限性特征带来了极度复杂的运算和绘制过程,不过,曼德博在自然界的雪花、动脉、树木、海岸线、云朵等等常见事物中都发现了分形的存在,这些自发产生的锯齿状线条与欧几里得的理想化的直线世界完全不同,曼德博就这种复杂性评价道:“有的分形集是曲线,有的分形集是曲面,有的分形集是由不相连的点组成的云,有的分形集形状奇特,无论是在科学还是艺术中都没有什么合适的术语来形容它们。”[12](P1-2)在曼德博有关分形的研究成果首次发表时,他在文章中附上了大量的图片,从计算机生成的形状到日本画家北斋的画作《巨浪》,再到海岸线、陨石和月球陨石坑的照片,这使得他的著作既像一本数学著作,又像一本艺术画册。就像拉吕埃勒阐释非哲学一样,曼德博利用了艺术、哲学和科学等多种手段,构造出了一种超越种种标准学科限制的思想。
那么,拉吕埃勒非摄影的分形又是什么呢?在拉吕埃勒看来,对照片表示的物体状态和模式不能从照片的物理、化学、风格等意义上去理解,只能从其“在照片中的存在”的意义上去理解。“在照片中的存在”已经引起了现象学、符号学、精神分析学等学派的关注,但其中的分形内涵却很少有人注意到。拉吕埃勒认为,这或许是由于照片这种表征形式不如几何的或者现实的分形直观、新颖,然而,摄影却是一个能使平面、角度、阴影、深浅和色彩等现实的特性集合在一个平面上表征出来的奇迹,这是摄影中的分形的一个初步迹象。
拉吕埃勒提醒我们,不要把分形看作对摄影的一种新的解释框架,那是哲学的做法,拉吕埃勒把这种将艺术封闭起来,为了非艺术的目的而在哲学中使用的做法称为“单一的”,而将那种把艺术从哲学的封闭中解放出来的理论称为“统一的”。[1](P71)拉吕埃勒追问一个问题:如果从摄影理论中祛除标准哲学的决定性要素,摄影理论会变成什么样子?他的答案是:“(会成为一个)关于分形的摄影的统一理论。”[1](P72)拉吕埃勒在这里显然是克隆了“分形”这个词汇,那么该怎么去理解呢?实际上他就是要强调一种摄影理论的无限性特征——就像分形图案具有无限性特征一样。通过曼德博的阐述,我们已经知道分形算法的无限性,指的是分形图案可以依照算法无限地分形下去,那么,摄影理论结构内部的无限性又指的是什么呢?拉吕埃勒的“广义的分形”把摄影理论的内涵拓展到无限——标准摄影理论的内涵往往指的是对平面、角度、阴影、深浅和色彩等现实特性的表征方式,但非摄影还要把符号学、艺术史学、视觉资料研究等目前与摄影理论相并列的学科的内容囊括进摄影理论之中。拉吕埃勒把前述这些学科作为一个无限的(或用他自己的话说,“分形的”)摄影理论的统一的诸方面。
可是,拓展摄影理论的内涵和分形有什么关联呢?用拉吕埃勒自己的话来回答:“曼德博的分形是几何的,但照片作为一种同一性——一种事物本身与其表征的同一性,施加了一种更‘彻底的’和‘现象的’关于分形的概念。一张照片在‘看’,也必须被人‘看’,这种看与被看的内在的冲突之中蕴含着一个新的分形概念,这种分形的概念以既先验又具体、既物质又理念的方式存在于照片之中,我们可以称它为‘非曼德博式的’或‘广义的分形’。”[1](P46)也就是说,在拉吕埃勒看来,照片在“照片展示‘照片中的存在’”和“照片被观察者观看”之间重复,这种重复的模式形成一种分形结构,这种分形结构是纯意识的而非图像的,是在“看”与“被看”的循环中迭代而生的关于凝视的分形结构。通过这种分形结构,照片的观看者能赋予照片以新的解读,进而可以不断地拓展摄影的内涵。也就是说,尽管分形是一个几何学的概念,但拉吕埃勒关于摄影的分形科学却不是关于几何图像的理论,不单纯是如何审视照片的理论,也不单纯是关于摄影媒介和摄影实践的理论,它是一个借由摄影者的表达和观看者对这种表达的解读的循环来拓展摄影的内涵的理论。
六、结语
在结束本文之前,可以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非摄影对科学的使用(或者叫克隆)是否真的是必要的?毕竟,当巴迪欧提出“数学=本体论”,以数学科学思考存在问题的时候,拉吕埃勒自己都还对其进行长篇大论的批评。[13]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先从一个与拉吕埃勒同时代的例子谈起:让·鲍德里亚就曾经习惯于在阐释自己的技术决定论时使用物理学词汇(许多后现代主义哲学家也是如此),当然这招致了大量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批评,比如物理学家阿兰·索克尔就指责过这种对科学词汇的使用是不负责任的:“在拉康、鲍德里亚和德勒兹的文本中都能见到对科学的严谨性漫不经心的态度,而且这种态度在法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并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添加到科学论述的内容中去的,为什么有人会把科学看作是一种对世界的客观描述呢?”[14](P207)这些文字出自索克尔的文章《流行的胡言乱语:后现代知识分子们对科学的侮辱》,从标题中就不难看出它的攻击性。但是,最后一句话提出的问题值得回应:
科学的客观性问题始终并且恐怕往后也依旧会是科学界与哲学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在这个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有人把科学视作一种对世界的客观描述无可厚非。当然还有一些学者指出,在澄清科学理论与世界的关系之前就先抛出“对世界的客观描述”这样的说法,本身也是不负责任的。[3](P13)
就像前文中所提到的量子力学对人类学的影响的例子,自然科学的思维方式的确是可以对社会科学产生积极影响的。而拉吕埃勒对巴迪欧数学本体论的批判,并不是反对用数学(或其他别的什么科学)思考实在,而是反对巴迪欧那种把数学视为“元本体论”和思考实在的唯一路径的观点。[15]
拉吕埃勒从两个方面对自己使用科学的方式给出了解释:一方面,在他那里,科学更多地意味着一种科学的思维方式,这是一种与哲学决定相反的、开放的、非决定性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拉吕埃勒只是在自己熟悉的原材料中寻找能够阐明自己思想的素材和话语,而科学不过恰好是这种原材料罢了——这更像是拉吕埃勒在用比喻的修辞阐释自己非摄影思想的过程中恰巧选择了“量子”“分形”等概念作为喻体。或许有科学家认为这种对科学话语的使用是不科学的、错误的,但“指责一个思想家没有按照科学定义使用一个科学术语,就如同指责一个诗人没有遵循气象学的定义使用‘下雨’这个词一样”[3](P13)。以往的哲学总是试图以独断的范畴来决定实在,但拉吕埃勒认为实在是彻底内在的、对思维起决定作用的东西,因而哲学决定实在的尝试只能是一场空谈。于是,拉吕埃勒力图摒弃“哲学决定”与“充分哲学原则”,转向一种非哲学的尝试,而非摄影是非哲学思想在摄影领域的一次理论实践。在这场实践中,拉吕埃勒批判了标准摄影哲学通过决定摄影与实在的关系来决定摄影的做法,拒绝将实在作为思考摄影的出发点,试图将摄影从“充分摄影原则”中解放出来,这与拉吕埃勒构建非哲学是为了使思想从“充分哲学原则”中解放出来的目标是高度一致的。
哲学试图用概念把握实在,而非哲学试图用克隆创造出与实在相似的结构。克隆体既不是对原本物体的简单复制,也不是外在于原本物体、与其完全无关的东西。在非摄影中,照片被视作对实在或世界的克隆。此外,拉吕埃勒通过复制其他学科的素材、思想和方法来推动自己的研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对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克隆。拉吕埃勒对科学的使用事实上指的是一种科学的科学性,拉吕埃勒借由这种科学的科学性保持自己思想的开放性和实验性,以避免陷入充分哲学原则和“哲学决定”的结构。
对拉吕埃勒来说,科学意味着事物会保留一丝未被决定的神秘色彩,会使事物停留在“晦暗”之中,这样更加能激发人们越过现成的标准和框架对事物进行思考。从这种立场出发,拉吕埃勒借用了诸多来自科学的资源,其中最典型的便是量子理论和几何分形。拉吕埃勒从量子力学中克隆了“量子叠加”的概念,使非摄影摆脱了以往摄影哲学中同一性和差异性二元对立的状态,并且,量子理论中的偶然性成为拉吕埃勒批判哲学决定的结构的最好武器。同时,非摄影也从几何学中克隆了“分形”这一20世纪70年代的新兴概念,非摄影中的分形是照片中的(摄影者的主观表达与客观世界结合而生的)存在与照片观看者的解读之间的循环对话,在这种循环中,摄影的内涵拥有了无限拓展的可能。至于这种非摄影将对摄影艺术产生怎样的冲击,这种冲击又将如何反作用于人们的现实生活,这将是另一篇文章专门讨论的问题。
注释:
①著名的“薛定谔的猫”假设就是用来表述这种无法确定的量子叠加的情况:当一只猫被关在纸箱中,而纸箱中还有随时会挥发的毒药,那么,在我们打开箱子之前,我们无从得知箱子里的猫究竟已经死了还是依然活着,这只猫对我们来说就处于死亡状态和存活状态的叠加之中,再简单一点说,叠加状态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既……又……”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