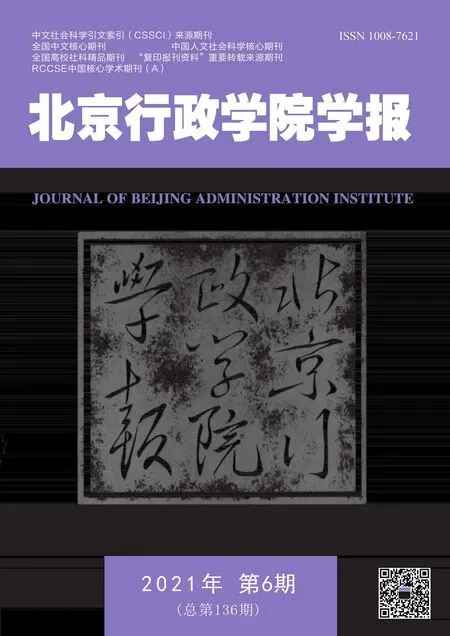马克思早期的批判路线:历史主体的交织与嬗替
2021-11-29孙夕龙
□孙夕龙
(北京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100044)
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马克思的异化论批判,仅用“异化”这个词,是不能完整表达它的全部内涵的,因为它还包括另外一半,即“本质”的“复归”(“回归”“回复”),单单“异化”只是揭露了问题,没有提出如何解决问题。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作为先驱,他们的异化(“外化”)论都包括了“本质”的回归,所以,“异化—复归”是对异化论路线的更准确表述。加入“复归”后,作为“异化”和“复归”的主体的“本质”的非现实性就凸显出来了。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以下简称《穆勒评注》)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之前,马克思只是少量使用异化和回归概念及其论证方法,到了这两部手稿,异化和回归的论述突然变多,但是在紧接着的《神圣家族》及其之后,却又突然断崖式减少。原因在于,《手稿》的“异化—复归”批判集成了之前精神批判思路的全部虚假果实,在全面运用过程中,它的根本缺陷暴露了出来,而一直与之并行的唯物主义路线却孕育成形并突破了它的束缚,于是,马克思就果断地抛弃了它。
正如阿尔都塞的“认识论断裂”所论,马克思的哲学革命确实是通过否定自己先前的“隐性的理论问题式”——“人本主义的逻辑构架”[1]41实现的,但此革命并非他所指认的“历史是无主体的过程”[2]128的结构主义问题式——历史“真正的主体”不是“具体的个体”和“现实的人”,即使有“主体”,也是“决定生产当事人所占有的地位和所担负的职能”的“生产关系(以及政治的和意识形态的社会关系)”[3]209。恰恰相反,马克思是在探寻历史的物质基础和物质主体过程中逐步抛弃黑格尔式精神主体,从而发现历史唯物主义的。
一、“哲学”批判思路的建立和实践
“异化—复归”批判路线的起点是马克思的博士论文,最初表现为“哲学”批判思路。马克思借助伊壁鸠鲁原子偏斜运动的观点,论证了世界和人的本质——“绝对自由”,以及人的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并在自由的基础上构建了他自己的哲学。马克思认为,世界的自由本质体现在“哲学”中,“哲学”有一颗“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4]12,可见哲学的本质内容就是高于一切的、“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征服世界”表明了哲学与尘世的关系,即通过哲学作用尘世的方式来实现自由,“在自身中变得自由的理论精神成为实践力量,作为意志走出阿门塞斯冥国,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尘世的现实”[4]75。针对哲学如何作用世界,马克思明确提出,“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4]75,它是对物质世界开展理论批判的一种自我意识活动。而“人的自我意识是最高神性的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4]12,哲学高于神学,而且是最高的神。实践的结果则是“世界的哲学化”以及“哲学的世界化”[4]76。就批判的具体方式来说,哲学的“直接的实现”就是“批判根据本质来衡量个别的存在,根据观念来衡量特殊的现实”,它在尘世的现象中获得自己的具体形式,并给尘世的现象“打上自己的烙印”[4]75。简言之,哲学实践方式就是“理论精神”(“批判”)根据“本质”和“观念”来“衡量”“个别的存在”和“特殊的现实”。就衡量对象是“个别的存在”和“特殊的现实”来看,作为衡量者的“哲学”或“理论精神”自然具有普遍性的特质,所以,这个批判思路其实就是用普遍性来批判特殊性,要求特殊的现实符合普遍的“本质”和“观念”。剩下一个问题就是“哲学”“自我意识”和“理论精神”在衡量特殊现实时的标尺,而这就是理性,自由甚至“是理性的普遍阳光所赐予的自然礼物”[4]163。总之,在批判现实世界之前,马克思就依据自由和理性为自己构建了一个以“哲学”命名的批判思路。虽是雏形,但这个批判的武器中已植入了一个一直延续到他放弃这种批判思路为止的硬核。正如恩格斯总结道:在黑格尔哲学以及其他本质相同的哲学中,“绝对观念是从来就存在的,是不依赖于世界并且先于世界而在某处存在的”[5]278-279,马克思此时的“绝对自由”“理论精神”“本质”和“观念”无疑就属于这种“绝对观念”。
进入《莱茵报》后,马克思第一次运用预制的哲学来批判尘世事物。他首先描述了现实事物实现了绝对的自由和理性之后应有的样子,也即事物实现了自身“本质”后的状态。绝对的自由和理性具体化在新闻报刊中就是“自由报刊”[4]171,它应该表达作为“人的本质”的自由,并评判公共利益。具体化在法和法律中,一方面是“人类的法”,它是“自由的体现”[4]248,应有“人类内容”[4]249;另一方面,法律应该是“事物的法理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4]244,所以,法律应“按照对象世界所固有的规律来对待对象世界”[4]317。具体化在国家中,国家应该“符合自己的概念”[4]261,应具有“一般国家原则”,是“合乎伦理和理性的共同体”[4]426,所以应根据“国家的本性”“人类社会的本质”以及“自由理性”来“构想国家”[4]226。再者,“真正的国家”“只有精神力量”,不与任何“地产、工业和物质领域”等“粗陋的要素”达成什么“协议”,国家“用一些精神的神经贯穿”各种物质要素,“占主导地位的”是国家的“形式”,而不是“物质”。[4]344-345
马克思进一步提出:“精神的实质始终就是真理本身”[4]111,就是“按照事物的本质特征去对待各种事物的那种普遍的思想自由”[4]112,简言之就是“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4]163。但是,当“哲学”以“真正的国家”及其要素的本质去考察现实的国家及其要素后,所有自由和理性的期望都被击碎了,没有一个现实事物符合和实现了它自身应有的状态。现实的国家并没有体现普遍利益和共同利益,实际上成了私人利益的手段,特殊等级的利益主导着国家,国家要素充斥着特殊等级的精神。代表机构则违背人民利益,成为特殊利益阶层故意摆弄的幌子,有特权的特殊等级把同人民和政府对立的个人特权和个人自由妄称为普遍权利,把“普遍理性和普遍自由”看成是有害的,甚至为了自己的特权和自由而“斥责人类本性的普遍自由”[4]163。新闻出版、法律、制度和宗教等意识形态形式所表达的国家利益或共同利益都是虚假的。总之,哲学在短短数年的尘世斗争中失败了,马克思得出一个结论:特殊利益在政治上的独立化是一种国家的必然性,是“国家内部疾病的表现”。[4]344
二、“异化—复归”路线的形成
为了解决《莱茵报》时期让他苦恼的物质利益的疑问,马克思在1843年3月中旬开始剖析黑格尔的法哲学,试图在国家理论中寻找答案。5月,他在《致阿尔诺德·卢格》中总结了德国制度的专制本质,指出德国社会就是“庸人世界”“政治动物世界”和“非人化的世界”[6]57,提出了与封建主义的“庸人”相对立的“自由的、真正的人”[6]60,从而确立了哲学批判思路中的衡量依据,即“本质”和“观念”的核心载体——“真正的人”。到此为止,“异化—复归”路线完成了一半,即确立了批判的主体是“绝对自由”“普遍理性”及其各种具体实现——“真正的国家”“自由报刊”(“真正的报刊”[4]352)、“真正的表达者”,尤其是“真正的人”,显然,它们本质上是没有现实性的纯粹精神主体。
在9月底完成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中,首先,马克思揭露了黑格尔国家观的思辨本质,指出黑格尔按照绝对观念外化出现实世界的思路,抽象地构造了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形成及其与国家的关系,“观念变成了主体,而家庭和市民社会对国家的现实的关系被理解为观念的内在想象活动”,国家从家庭和市民社会中产生并以之为前提的事实成了“观念”外化的结果,整个过程颠倒了,论述方式显露出“逻辑的、泛神论的神秘主义”。[7]10这个批判表明马克思已经建立唯物主义思维。其次,这一时期,马克思通过剖析黑格尔的论证进一步说明《莱茵报》时期所揭露的事实的根源,即为何封建国家及其要素是特殊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手段,“真正的国家”没有实现。《法哲学原理》的最大难题是如何将家庭和市民社会“消融”在国家中,使其成为国家“机体”的组成部分,也即在国家的各种制度和权力中实现国家自身,如果实现了,那么国家就是“具体自由的现实”。[8]260黑格尔的思路是:“具体的自由在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特殊利益体系和(国家的)普遍利益体系的同一性(应有的、双重的同一性)。”[7]7王权作为“最后决断的主观性权力”[8]287,通过行政权把法即国家的普遍性贯彻到国家内部的各个特殊领域和个别事物中去,从而实现国家和国家精神,王权就是普遍与特殊结合起来的整体,就是“具体的自由”的实现。但是马克思否定了君主制和王权是普遍与特殊有机结合的整体的观点,认为君主制国家中的等级、官僚制、行政权、立法权等要素与国家的现实关系始终是分裂的,国家要素没有实现真正的普遍性,因此所谓君主制国家的普遍性是抽象的和虚假的普遍性,普遍事务的形式是“一种虚假形式”和“假象”[7]81。在君主立宪制度中,君王既是“国家的观念”和“神圣的国家尊严”,同时“又是单纯的想象”,没有“实际的权力”和“实际的活动”,因此“从最高矛盾的角度表现出政治的人和现实的人、形式的人和物质的人、一般的人和个体的人、人和社会的人之间的分离”。[7]136
马克思进一步把现实的君主制论述为国家制度的“异化的完备表现”[7]42,同时设想了一种等着现实的国家去回归的、完全实现了国家本质的国家,从而给哲学批判思路添加了另一半,完成了“本质”的“异化—复归”。首先,现代世界的政治制度是“抽象的二元论”[7]43,因为现代世界从中世纪的异化中抽象出私人生活,从国家中抽象出“国家本身”和“政治国家”等“类的内容”和“真正的普遍东西”。政治国家同作为人民生活的“物质国家”就不再真正同一了,而是成了“外在的同一”了。政治国家以一种“普遍理性”和“彼岸之物”的形式发展起来了[7]42,人民从属于政治制度,人民是“国家制度的人民”[7]39。作为“统治的东西”的国家、法律和国家制度“并没有真正在统治”,“并没有物质地贯穿于其他非政治领域的内容”[7]41。因此,政治国家其实是肯定了人民生活的各个特殊领域自身的“异化”,甚至可以说,它是同人民现实生活相对立的“天国”。政治生活成了“人民生活的经院哲学”,异化成了宗教,这种异化的完备表现就是君主制。[7]42其次,马克思提出,“历史任务就是国家制度的回归”[7]42,回归民主制。民主制消除特殊领域的私人本质,克服现代世界的“抽象的二元论”,从而,国家制度表现出了“它的本来面目”,“即人的自由产物”,所以民主制实现了内容和形式的同一,是“普遍和特殊的真正统一”[7]40,解决了普遍的国家制度和特殊的人民生活之间的外在同一。因此,民主是“国家制度的类”,“是一切形式的国家制度的已经解开的谜”,“是一切国家制度的本质”。[7]39-40
在9月给阿尔诺德·卢格的信中,马克思对基于绝对自由和普遍理性的“理论精神”和“哲学”的批判思路进行了简要总结:“理性向来就存在,只是不总具有理性的形式。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特有的形式中引申出作为它的应有和它的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6]65一是“向来就存在”的“理性”;二是现实并“不总具有理性的形式”,也即没有完满地体现“理性”的“现存的现实”;三是批评家可以“引申出”作为“现存的现实”的“应有”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作为“应有”和“最终目的”的“理性”如果能在有缺陷的“现存的现实”中得到实现,“现存的现实”就成了“真正现实”。
至此,马克思提出了两个序列的概念。第一是“绝对自由”“普遍理性”及其实现的“真正现实”序列:“真正的人”(“人”)“真正的国家”“真正的民主制”“真正的”国家要素如“真正的报刊”(“自由报刊”)、“真正的表达者”“真正的婚姻”以及“真正的普遍东西”[7]42“真正的普遍事务”[7]78等等。第二是“现存的现实”序列:现实的国家(封建国家、君主制、共和制)及现实的国家前提和要素(作为特殊利益和私人利益的手段的新闻报刊、法和法律、社会团体、区乡组织、家庭、宗教、官僚制、行政权、立法权、等级和等级代表制)等。这两个序列的关系是:“现存的现实”是对“真正现实”的“异化”,因此要从异化的“现存的现实”“回归”“真正现实”。这里立即产生了一个问题:如何实现回归?马克思明显受到黑格尔理论论述方法的影响。整个黑格尔哲学从理念自在自为的逻辑学到理念外化的自然哲学再到理念回复到自身的精神哲学,整个精神哲学从自在自为的主观精神到外化的客观精神再到回归的绝对精神,体系演绎的动力是理念和精神自身。马克思否定了黑格尔把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生活解释为理念和精神外化的结果,但同时又承认有先于现实世界的“绝对自由”和“普遍理性”及其实现的“真正现实”序列。显然,马克思不能用自由和理性自身的回归作为方法来实现“真正现实”,所以就必须在现实中寻找实现者。
马克思在论述“真正现实”序列时立即引入了一个关键主体及其概念“人民”。首先,作为绝对自由和理性载体的哲学就汇集了“人民的最美好、最珍贵、最隐蔽的精髓”,哲学家则“是自己的时代、自己的人民的产物”。[4]219-220就具体现实来说,把“人民”与报刊相结合,即“真正的报刊即人民报刊”,“报刊只是而且只应该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的‘表达者’”[4]352,“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4]155,“自由报刊的人民性”体现了“独特的人民精神”[4]153。把“人民”和法律联系起来,“法律是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4]349习惯法“按其本质来说”只能是“最底层的、一无所有的基本群众的法”[4]248,而“国家形式”应该“同更深刻、更完善和更自由的人民意识”“相适应”。[4]306到了《批判》中,作为国家制度回归的民主制则是“人民的自我规定”和“人民的国家制度”,每一个环节“都只是整体人民的环节”,它有“自己的现实的基础、现实的人、现实的人民”,“被设定为人民自己的作品”。[7]39-40同时,国家制度“本身具有与意识同步发展、与现实的人同步发展的规定和原则”,“而这只有在‘人’成为国家制度的原则时才有可能”。[7]27引入“人民”后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一方面,“现实的人”“人民”和“群众”是基础,另一方面,国家制度的原则是“人”,而以“人”为原则的真正的国家制度——民主制又是“人民的国家制度”,“人”和“人民”在这里是如何实现同一的?除了主要论述真正的国家的人民性内容之外,《批判》也进一步提出历史创造者的问题,似乎回答了这个问题:“不是国家制度创造人民,而是人民创造国家制度。”[7]40“人民”如何创造出实现了“人”的国家制度?尤其“人民”是谁?诸侯、骑士和城市市民的意识充满了反对绝对自由和普遍理性的特殊等级精神,君王则是虚假普遍利益和共同体的代表,他们显然不是“人民”。在辩论新闻报刊自由时,倒是农民等级的一位议员提出:“人类精神应当根据它固有的规律自由地发展,应当有权将自己取得的成就告诉别人”,德国人民不需要书报检查制度的“精神紧束衣”,相反需要的是新闻自由。[4]200但是马克思没有明确把农民等级等同于“人民”。显然,“人民”这个概念不是最后的,除了已经使用的与之几乎等同的“群众”外,还应有另外的概念及其主体与之同属一个序列。当然,人民及其创造性为马克思进一步思考历史动力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两条路线的并行与冲突
1843年10月中旬至12月中旬,马克思同时完成了《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一方面,如同列宁所说,这两部著作的完成标志着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的彻底完成;另一方面,第一次引入了人的解放主题和新的历史主体来解决国家问题。但是,新的历史主体在论证思路上还是为了完成“异化—复归”逻辑。
《论犹太人问题》延续了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主题,主要问题之一仍然是国家与各种国家要素的关系,但是已经从《批判》的封建国家推进到政治解放和政治国家,即资产阶级解放和资产阶级国家。马克思指出,政治解放是把国家从宗教的控制中解放出来,使国家成为所谓纯国家的国家,但是,政治国家却并没有消除宗教作为人民的信仰。这个缺陷的根源不在宗教,而在国家自身,在于“政治国家的世俗结构”[9]27,是世俗结构的局限性使得宗教依然存在于政治国家中。这是对《莱茵报》的“国家内部疾病”的说明。因此,政治解放没有实现人的解放,“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9]32。马克思指出,国家对特殊要素的超越是必须的,否则没有普遍性国家,但是,这是有缺陷的普遍性超越,造成了多重分裂。“完成了的政治国家”在本质上应该是“人的同自己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类生活”,但人的利己的物质生活的前提却不在国家中,而在市民社会中,所以,在政治国家中,存在着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类生活与现实生活的分裂,同时这又引起了人们在思想意识和现实生活中都过着天国和尘世的双重分裂生活,国家对市民社会的关系成了“唯灵论的”。[9]30这些分裂又进一步引发了国家的普遍性假象。在政治国家中,人“被剥夺了自己现实的个人生活,却充满了非现实的普遍性”[9]31。现实的政治国家无法成为天国意义上的作为普遍性和类生活的国家。因为政治解放创造了抽象的公民,所以,“只有当现实的个人把抽象的公民复归于自身,并且作为个人,在自己的经验生活、自己的个体劳动、自己的个体关系中间,成为类存在物的时候,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9]46。
《导言》虽然是《批判》的导言,在理论逻辑上却是接着《论犹太人问题》的主题,它以德国这个特殊国家为对象,力图解决“普遍的人的解放”如何实现的问题。马克思在专门揭露了宗教的现实根源和唯心主义本质之后,立即转向批判尘世、法和政治。一方面,基于德国的特殊阶级关系,马克思提出,“在德国,普遍解放是任何部分解放的必要条件”[9]16,“在德国,不摧毁一切奴役制,任何一种奴役制都不可能被摧毁。……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9]18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在前述基础上,批判现实就不能再像以前一样专注于理论批判自身,而是必须通过实践也即革命来解决问题。此时仅有“批判的武器”是不够的,需要“武器的批判”来摧毁“物质力量”[9]11,这个武器就是经过理论武装的无产阶级。不同于其他特殊的市民社会成员,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特殊等级具有彻底的普遍性——“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以及“由于自己遭受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他们同国家制度的前提处于“全面的对立”状态,因此,无产阶级要想解放自己,就必须进行一场普遍解放的革命,也就是把自己“从其他一切社会领域解放出来从而解放其他一切社会领域”的革命[9]17。
至此,第三个序列引入了最重要的概念:“无产阶级”。在这之前,不仅“人民”的具体所指是模糊的,而且即使提出了“人民”是国家制度的创造者,总体上也是没有革命性的,不是改变现实的动力。然而,作为主体的无产阶级的引入则决定性地削弱了以绝对自由为心脏的哲学对于实现世界的主导作用,决定性地否定了“异化—复归”路线的立足点和依据。首先,“绝对自由”“普遍理性”和“人”等等是纯粹虚幻的精神主体,“人民”和“无产阶级”是物质主体。其次,因为其特有的普遍性特征,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是社会的普遍解放,所以,只要无产阶级具有解放自己的主动性,作为普遍解放的人的解放就是必然的,完全不需要黑格尔式的精神主体来引领。这是人的解放的唯物主义路线的第一步。至此,马克思构建了两条批判路线和人的解放路线:一是以“绝对自由”“哲学”和“人”等为动力和主体的精神运动路线,这条路线本质上是唯心主义的;二是以人民和无产阶级为动力和主体的物质运动路线,这条路线是唯物主义的。
当然,《导言》此时不但没有把这两条根本冲突的路线分开,相反却把它们交织起来。一方面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和“理论只要说服人”[9]11“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以及“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哲学”当主语,主导解放;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等[9]17-18,无产阶级也充当主语,开辟了新的解放道路。进一步考察可见,马克思此时依然是在“异化—复归”框架中确立无产阶级自身解放路线的理论根据。马克思指出,作为“物质武器”还不够,无产阶级还把“哲学”作为“精神武器”[9]17,“哲学”是解放的“头脑”,无产阶级是解放的“心脏”,也就是在“哲学”的引导下来“消灭”无产阶级自身[9]18。而哲学要成为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就需要彻底的理论来说服和掌握无产阶级,而理论的彻底性就是抓住“人”这个根本,“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革命的立足点就是“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9]11。无产阶级革命的理由不只是它的“普遍苦难”的“普遍性质”,还因为“普遍苦难”引起了“人的完全丧失”,而“只有通过人的完全回复才能回复自己本身”[9]17,无产阶级革命就是要回复这个曾经存在的“本身”。“人是人的最高本质”是人的解放的立足点,这也明确了“异化—复归”思路的根据和起点。可以说,在《手稿》及其之前的批判过程中,“异化—复归”路线一直高于唯物主义路线。
四、两条路线的嵌套与唯物主义的突围
《穆勒评注》和《手稿》的批判框架是完整的“异化—复归”。通过引入异化劳动来解释无产阶级的苦难,马克思把《导言》中相互否定的“精神武器”和“物质武器”“批判的武器”和“武器的批判”更加复杂地整合在一个总逻辑中了。第一,人的活动是“类活动和类精神”,它的真实的和真正的存在是在生产和交换中实现“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因此“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10]24。人这个种有其“类本质”,是“类存在物”,在理论和实践中都把类作为对象,从而表现出有意识的、普遍的和自由的生命活动的特质,“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恰恰就是人的类特性”[7]272-274。“人”的内涵此时完成了。第二,劳动从野蛮状态下的直接劳动发展到为了交换而进行的劳动即谋生劳动之后,劳动本身不再是目的,“成为完全偶然的和非本质的”活动[10]28。工人成为“高度抽象的存在物”以及精神和肉体上的“畸形的人”,产品、私有财产和货币成为“异化的物”,实现了“对人的全面统治”,人越来越失去社会性,“同自己固有的本质相异化”[10]29。(工人的)劳动成为异化劳动,人在异化劳动中丧失了的类本质,“是人作为单纯的劳动人的抽象存在”,人随时可能沦为“绝对的无”和“现实的非存在”[7]283。第三,只要回归“作为人”所进行的生产,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命表现中直接创造了他人的生命表现,从而“直接证实和实现了”自己的“真正的本质”,即自己的“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10]37,那么“作为人”的生产就消灭了异化。消灭路径就是通过共产主义,也就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实现“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7]297。
在此三步推演中,作为现实的特殊群体的工人阶级的异化劳动如何引起了作为普遍本质的人的本质的异化?人世间所有苦难都集中在无产阶级身上,可以说无产阶级解放了自己就能消灭人世间所有苦难,但说无产阶级消灭了人世间所有苦难,就能顺理成章地实现了“人”和“类本质”的复归,则缺少一个逻辑扣子,因为无产阶级及其背负的世间苦难与“人”和“类本质”及其异化不是同等级和同类型的东西。“人”是谁?是工人,是资本家,还是包括两者在内的所有人?当然,从理论上说,本质异化的不只是工人,也有资本家,但是马克思进一步用特定的劳动异化来说明一般的本质异化,而劳动就是工人阶级的劳动,因此,劳动异化不能等同“人”的本质异化,无产阶级解放自身也不能等同于“人”和本质的“复归”。马克思把这两个方面联结在一起并不表明理论自洽。
在汇集了之前所有思路的基础上,可以看出,“异化—复归”逻辑实际上包含了四层嵌套关系:第一层从“绝对自由”“普遍理性”作为世界的本质到以“绝对自由”为心脏的“哲学”批判现实;第二层从“人”及其“类本质”(同层次的“真正现实”序列)到“类本质”的异化,再到复归人的“类本质”,其中“人”和“类本质”是第一层的世界的本质的具体化;第三层从劳动层面说明第二层的“类本质”如何异化,即从作为“类生活”“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和“真正的生产”的劳动[7]273到异化劳动,再到作为“类生活”的劳动的复归;第四层是从工人的层面说明第三层的异化劳动及其克服,即从工人的沦为“绝对的无”的外化劳动到劳动异化为私有财产和资本家,再到通过作为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扬弃的共产主义运动,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同时完成“人”和“类本质”的复归。很明显,前三层理论架构都是唯心主义的构想,只有第四层架构,即工人的包含“普遍苦难”的现实劳动和扬弃私有财产的运动是真实存在的物质运动,但却被包裹在前三层精神运动的套子中了。
到了《手稿》时期,马克思还没有放弃精神主体单独承担历史运动的自由主义精神,但残酷的现实又迫使他不得不进一步把“人民”明确为无产阶级和工人,从而在理论上把最具体的工人同最抽象的“人”和“类本质”勾连起来。在此勾连中,“工人”和“人”随时混同在一起并相互替换,或同时作论述的主语。例如马克思说:“人(工人)只有在运用自己的动物机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7]271“人(工人)”合用普遍的“人”和特殊的“工人”,这表明马克思此时一方面还没有自觉意识到“人”和“工人”区分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尊重事实,劳动就是工人的劳动,如果有异化劳动,也是工人的异化劳动,没有所谓“人”的劳动和异化劳动。
物质解放主体的逐步具体化,不可避免地促进了唯物史观的成长。事实是,到了《手稿》中,“异化—复归”路线作为一个总逻辑收纳了大量它容纳不了的唯物主义批判内容,或者反过来说,唯物主义内容已经扩充到必须突破唯心主义路线束缚的程度了,因为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的批判逻辑,即将分娩。从思维方式来看,从博士论文直到《手稿》,马克思的探索思路一步一步从绝对和普遍走向了个体和特殊:从作为整个世界本质的“绝对自由”“普遍理性”到其载体“本质”“观念”和“哲学”,到“人类”“人”和“真正现实”序列,到“现实的人”“人民”和“群众”,再到“无产阶级”和“工人”;从“类本质”到作为“类生活”和“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的劳动,再到“工人”的“普遍苦难”的劳动,再到“私有财产”,最后到达阶级斗争。关于历史运动的阐述逐步去绝对化、抽象化和普遍化,逐渐增加物质性、现实性和具体性,从而历史的真实面貌和真正的主体逐步显现了出来,完全不需要精神和观念来解释历史运动了。“异化—复归”路线则因其动力的虚假性的彻底暴露,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被物质主体和动力所替代。我们找到了一个马克思在语言上彻底解决历史主体问题的标志——1847年的《“莱茵观察家”的共产主义》:“人民,或者(如果用个更确切的概念来代替这个过于一般的含混的概念)无产阶级考虑问题的方法却是和宗教事务部的人士所想象的完全不同。”[11]只有在理论方法上持续追问历史的真正动力,直至完全抛弃虚幻的抽象的普遍性概念,才能获得彻底的唯物主义,对虚幻的普遍性有一点迷恋就会走向反面。而在《手稿》之后,循着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和斗争,马克思发现并在《神圣家族》中初步论述了物质生产在历史进程中的决定作用,从而真正发现了历史的秘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