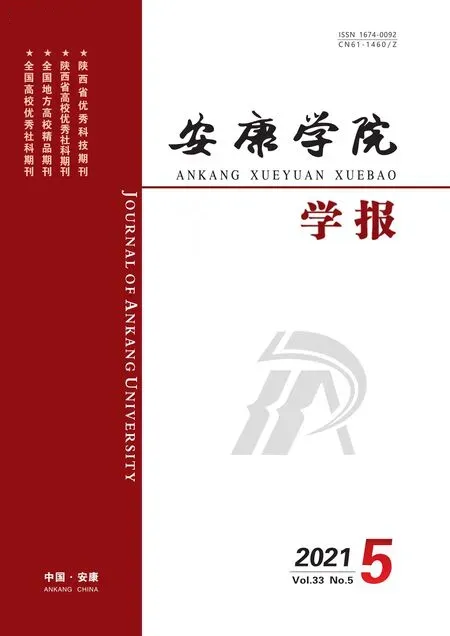极高明而道中庸
——从“孔颜乐处”看冯友兰天地境界
2021-11-29张红云
张红云
(安徽大学 哲学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极高明而道中庸”出自《礼记·中庸》,它不仅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精神,也是冯友兰新理学体系的重要概念。冯先生以“境界”论中国传统哲学,将“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审视各学派价值的标准。他认为,传统哲学中完全符合“极高明而道中庸”标准的基本没有,或偏于“道中庸”,或重于“极高明”。在《新原人》一书中,冯友兰又将“天地境界”与“极高明而道中庸”画上等号,认为“圣人有最高底觉解,而其所行之事,则即是日常底事。此所谓‘极高明而道中庸’”[1]75。学界目前认为,“天地境界”是接着“孔颜乐处”而提出的[2]。本文拟以此为基础,从“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角度,探讨冯友兰境界哲学与“孔颜乐处”的关联。
一、“道中庸”:孔子、颜回的生活之乐
“孔颜乐处”是先秦儒家追求完美品格的概括,这一内容的原义没有后世宋明道学家的阐释那么复杂。回归文本,我们能够发现它更多指一种乐处生活的朴素观念。“孔颜乐处”的典故源自《论语》:“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3]99“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3]82这两段话,前者是孔子自述,后者是其对颜回的赞扬。在孔子看来,钱财富贵乃身外之物,即便粗茶淡饭、穷困潦倒,其中亦有可乐之处。孔子对弟子颜回充满欣赏,也是因为他虽居陋巷而“不改其乐”。“乐”是儒家的人生哲学,先秦有曾子的“气象之乐”,有孟子的“君子三乐”,也有孔子与颜回的生活之乐。通过分析可知,“孔颜乐处”大体包括了学习之乐、仁者之乐、朋友之乐三方面。
其一,学习之乐。汉代扬雄《法言·学行》有“孔子铸颜渊”语,既表明了孔子对颜回的塑造,也佐证了二人的高度相似。颜回之乐实际上就是孔子之乐,虽然其中有细微区别,但考察二人共通处,就能比较接近“孔颜乐处”的本来面目。颜回好学,面对哀公与季康子询问“弟子孰为好学”时,孔子都对答曰:“有颜回者好学”[3]77。孔子亦自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3]74方圆十家,必定有如孔子一般讲忠信之人,但好学的品质却不如他。由此可知,在好学这一点上孔子与颜回别无二样。颜回的好学体现在“不迁怒,不贰过”,“凡人任情,喜怒违理,颜渊任道,怒不过分”[4]。颜回与凡人的区别在于一者“任道”,一者“任情”。颜回不以情欲纵容自己,而任道以行,故不迁怒于别人,也不犯同样的过失,这就是好学最大的快乐。学习的重点不在于学了多少知识,而在于能够经常温习与练习,故孔子又云:“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3]2《论语》开篇首句正是对颜回“不迁怒,不贰过”的最好诠释。孔颜之乐首在学习,至道难闻,学之至则可以为圣人,故乐在其中矣。
其二,仁者之乐。“孔颜乐处”所描写的是一种安贫乐道的快乐。富贵于我如浮云,即便穷困潦倒,也不改精神上的快乐。贫穷本身不能给予快乐,富贵更不是快乐,那么为何孔子与颜回能够获得如此之乐呢?在《论语》中亦有答案。首先,所谓“孔颜乐处”只是一种现象,它背后的本质是“仁者之乐”。孔子曾有言:“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处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3]48拥有仁德之心的人才能长久居于穷困之中,居于快乐之中。“仁”是儒家思想的哲学体现,它有多重涵义。在这里,孔子所说的“仁”不是“爱人”之“仁”,而是一种“心境之仁”。钱穆先生说:“一切人事可久可大者,皆从此心生长,故此心亦称仁。若失去此心,将如失去生命之根核……苟其心不仁,终不可以久安。安仁者,此心自安于仁。”[5]换句话说,“孔颜乐处”的关键在于其心之“仁”。这种仁心之境,能够使得他们无论处己处群,各种情况都能够安适自在。其次,《论语》还有言:“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3]87。后人对“山水之乐”的解释多从美学角度出发,以山水客观实体与知仁审美主体相联系。其实,这句话也同样体现了孔子对快乐的独特理解,即无论乐山乐水都是由己出发,展示了儒学自觉追求的仁者之乐。
其三,朋友之乐。正如孟子主张将“善”扩充发扬,“乐”的本质也不是个体的独乐。《论语·学而》开篇就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3]2主张交友也是一种快乐。古人以同门为朋,以同心为友。颜回虽然是孔子的弟子,但又仿若是其知己。孔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于吾言无所不说。”[3]156“非助我”,表面是在责怪颜回,其实为盛赞。恰因二人志趣趋同,而非颜回不愿反驳老师。从颜回与孔子的距离看,二人虽为师徒,却乃知己。前人对“孔颜乐处”的理解往往分开说,忽略了二人的相互影响。孔子“乐在其中”,颜回“不改其乐”,如若粗浅看仿佛二人二事,但他们何尝不是惺惺相惜,互相感受到知己的同趣而快乐呢?孔子“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颜回作为最接近孔子的人,“也不改其乐”。孔子正是看到了知己朋友的志同道合而感到快乐,颜回也是看到了老师的心意相通而散发快乐。“益者三友,损者三友。”[3]245互为朋友所以道不孤而乐矣。
总之,从先秦儒家对“孔颜乐处”的讨论来看,孔子与颜回的快乐更多是日用人伦方面。
二、“极高明”:宋明理学的形上之乐
寻“孔颜乐处”是宋儒热议与思考的话题之一。道学家们认为不仅要知道孔颜之乐,还要真正明白乐在何处。因此,在宋儒以及后代看来,“孔颜乐处”已然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孔子与颜回的快乐”问题,而是一个从形上角度思考的本体、工夫与境界问题。
理学宗师周敦颐最开始在《通书》中探讨“孔颜乐处”,他说:“夫富贵,人所爱者也。颜子不爱不求,而乐乎贫者,独何心哉?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贵富贫贱处之一也。处之一则能化而齐,故颜子亚圣”[6]76-77。周敦颐在这里将之前的“孔颜乐处”上升到天地间的可爱可求,拉大了“乐”的哲学视域。他认为颜回所乐不仅在“贫”,而且在于“至贵至爱可求”者。通过对“大小”的对比,周敦颐进一步阐释了颜回成为“亚圣”的原因。颜回所乐者不是物质性的大富大贵,此类为“小”,然而天地间至贵至爱者为“大”,颜回“见其大”。何为“见其大”?“君子以道充为贵,身安为富,故常泰无不足。而铢视轩冕,尘视金玉,其重无加焉尔!”[6]81周敦颐把“乐”与“道”结合起来,认为“道”是宇宙天地运动、发展的根本法则,人若能真心体会“道”,自然会超越对功名富贵的庸俗追求与计较,而获得一种高度持久的精神快乐。由此,“孔颜乐处”上升到一种境界层面。周敦颐诠释了颜回内心所追求的东西乃超越世俗意义上的富贵,不是非此即彼的超越,而是在跃升到天地间的角度来超越世俗。
周敦颐也令二程“寻颜子、仲尼乐处,所乐何事”[7]16,后来他们回忆说自此才慨然有求道之志。关于“孔颜乐处”两兄弟体会不同。程颢说:“若颜子箪瓢,在他人则忧,而颜子独乐者,仁而已。”[7]352他认为颜回之所以能够生活在简陋的环境下,依然保持心中的快乐,其根源在于“仁”。也就是说,程颢理解的“孔颜乐处”本质是“仁”。“仁”在程颢的哲学体系中无疑具有独特地位,他的“仁学”,既涉及本体论的问题,又涉及境界论的问题。先秦“仁学”强调博施济众的道德仁义,程颢这里的“仁”则是“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的最高境界。他认为,“仁”在根本上不是个体的小我,而是天地的大我。故此之“乐仁”,是颜回体会到宇宙的浑然不可分割、天人合一后,心中自然彰显的“大乐”。程颐另有看法。“鲜于侁问伊川曰:‘颜子何以能不改其乐?’正叔曰:‘颜子所乐者何事?’侁对曰:‘乐道而已。’伊川曰:‘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7]395他认为“使颜子而乐道,不为颜子矣”,颜回所乐不在“道”,即不存在一个具体的乐的对象,“乐”是达到与道为一的境界。学颜回之所“乐”是要追求圣人的境界,这是一个内圣的问题,不仅仅是仁义礼智信,而是君子德性之学的全部面向,是儒家内圣之学的真切通达。
朱熹承接二程并继续深化“孔颜乐处”,他认为:“‘人于天地间并无窒碍,大小大快活’,此便是颜子乐处。这道理在天地间,须是直穷到底,至纤至悉,十分透彻,无有不尽,则于万物为一无所窒碍,胸中泰然,岂有不乐”[8]。朱熹界定了“孔颜乐处”的概念,显然这还是将“乐”与“天地参”结合在一起,注重人与宇宙的合一。他认为个体只要体会到天地的本有德性,就可自然得乐。朱熹还完善和推进了周敦颐与二程对于“孔颜乐处”的讨论。在他这里,“乐”的重点是“直穷到底”。“乐”来源于圣贤证悟到充斥天地间的本体与无限后,进入境界而全身散发的一种自上而下之畅快感,但朱熹强调这种快乐是得来不易的,“须是直穷到底,至纤至悉,十分透彻,无有不尽”,故朱熹更多的是偏向于实践的工夫。对照王阳明可以发现,在心学中则是“乐”的本体作用突出了。“乐是心之本体。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合和畅,厚无间隔。”[9]165王阳明还强调乐也是正常表达情绪的一部分,人有七情六欲,在正常的情绪表达之后,人才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心体之乐,这个乐在心的状态需要境遇和时限作为承载。阳明先生曰:“须是大哭一番方乐,不哭便不乐矣。虽哭,此心安处是乐也。本体未尝有动。”[9]98
总之可以看出,通过对“孔颜乐处”的诠释,宋明理学的本体论、工夫论、境界论全部联系在一起,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形上学体系。
三、世间与出世间:冯友兰的境界之乐
无论先秦儒学或宋明理学,都是讲世间与出世间,以“极高明而道中庸”作为自家标准的。它们对“孔颜乐处”的看法也都体现了高明与中庸的合一。冯友兰说:“对于本来如此底有充分了解,是‘极高明’;不求离开本来如此底而‘索隐行怪’,即是‘道中庸’。”[1]79孔子、颜回学道求道,于箪食瓢饮等日常事务中尽性至命;宋明道学体与物冥,在孝忠仁义等伦理生活中居敬穷理,这就是中国哲学玄远与俗务的统一。然而,二派又有很多不同。具体言之,先秦重于“道中庸”,宋明偏于“极高明”。
一般认为,先秦儒家为伦理实践之学,宋明儒家偏本体心性之学。在宋代以后,理学家为了迎接佛老挑战,建构了宇宙本体论和心性修养论,并从形上学的角度重新诠释经典。通过前面的分析也可以看出,宋明儒学对“孔颜乐处”的讨论早就不是单纯的“快乐”问题了,而是要追求这背后存在的终极原因,将本体、工夫、境界等全部囊括进来。先秦儒学则恰好与之相反,孔孟倡导积极有为的人生,并多注重在日常生活中提高自己的境界。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3]65孔子注重的是培养学生的现实精神,是日用人伦间的学问,性与天道却罕言。这是两派倾向的不同。
冯友兰正是站在先秦儒学与宋明理学未达的基础上提出了“天地境界”。在《新原人》一书中,说到人生到底有没有意义以及何为意义时,冯先生认为,事情的意义在于人对此事的了解,这个了解与一个人的觉解相关。有觉解是人生最显著的特征,它使人在宇宙中享有特殊的地位。从宇宙人生对于人的不同意义的角度出发,冯友兰将人生境界分为四个层面,由低到高分别是: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处在自然境界中的人,觉解最少,境界是混沌的,行事是根据其生物学上的习性和习惯。处在功利境界中的人,有清楚的觉解,行事总是为他自己的利,以“占有”为目的。处在道德境界中的人,人性已经有了觉解,行事是求社会的利,以“奉献”为目的。处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已完全知性,有了最高的觉解,不仅了解全部的社会,还洞察到宇宙的万物,达到“与天地参”的大无我境界。
在冯友兰看来,达到“天地境界”的人自然而然地会由心散发出一种快乐,这个“乐”,就是儒家所追寻的“孔颜乐处”。“于事物中见此等意义者,有一种乐。有此种乐,谓之乐天……此等‘吟风弄月’之乐,正是所谓孔颜乐处。”[1]175概言之,冯友兰赞同宋儒的分析,认为孔子和颜回之所以快乐不仅是安贫乐道,而且是因为他们参透了人生之意义,明白自己的身份不但是社会的分子,而又是宇宙的分子。这种意义的觉解使得颜回能够深切感受到宇宙间事物所依据的永恒规律。这个规律,既是天道的运行,也是人道的法则。虽然颜回穷困潦倒,但他已然能够从大全、理及道体的观点看待事物,于是未尝觉得有一分之忧苦,反而充满了无限的快乐。然而,冯友兰也反对将“天地境界”拔得太高,仿佛超脱了日用人伦。他说:“出世间底哲学,所讲到底境界极高,但其境界是与社会中的一般人所公共有底、所普通有底生活,不相容底……是无实用底,是消极底,是所谓‘沦于空寂’底。”[10]从先秦孔、颜开始,儒家一开始强调的哲学是要贯彻于生活日常中,而到宋明理学的时候,为了以儒学为主干,他们创造出一种新形态的哲学,重构了宇宙本体论、心性修养论和工夫境界论。这样,“孔颜乐处”的“乐”也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周敦颐说乐道,程颢说乐仁,王阳明说乐心等等。这种情况在学说发展时弊端并不明显,但到了“道学家的末流,似乎以为如要居敬存诚,即不能做这些事。他们又蹈佛家之弊”[1]78-79。
冯友兰认为,世间与出世间可以统一,他的“天地境界”即强调首先要做到“极高明”,然后也要实现“道中庸”。他认为,一方面,天地境界的人是“无我而有我”的,自己的个体消解于宇宙之中,进而与宇宙融为一体。他又自觉承担起自己的主宰责任,如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等;另一方面,天地境界的人还要“有为而无为”,虽然在日常生活中只是做到了尽职尽责的本分之事,但“天民行之,这种事对于他又有超道德底意义”[1]171。这种“极高明”,自然是就圣人的境界而言,超越流俗,觉解万物;而所谓“道中庸”,也就是就圣人的行为而言,日积月累,将自己的理想贯彻到日常生活中。要之,冯友兰的“天地境界”正是把“极高明”与“道中庸”二者结合起来,从而不仅让人的精神能够在现实世界获得一种形上的升华,还又使得境界不离人伦日用,境界的超越体现在形下世界中。
冯友兰先生正是看到了宋明道学自身的弊端,故其新理学得以成立的核心,就在于将先秦与宋明的观点统一了起来,使之突破传统哲学而成为一种有特色的体系,这即是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精神的新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