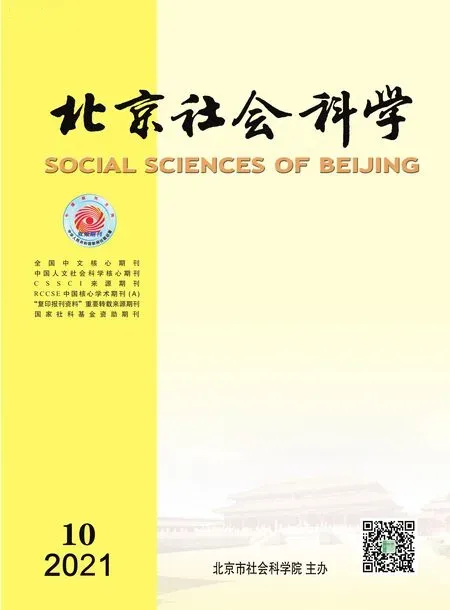地方传说的生活实践性探究
——以晋南赵氏孤儿传说为例
2021-11-29孙英芳
孙英芳 萧 放
一、引言
从关注民间文学文本的文学性到民俗文化,再到民间文学生活,体现出现代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伴随着近年民俗学日常生活研究的转向,民间文学已不再是单纯的文学讲述,而是作为民众生活实践的一部分受到研究者的重视,因此“必须重视对民众实践的分析,考察他们出于何种需要,以及如何利用民间资源,同时也要看到文本中蕴含的民众生活、情感及历史文化信息”。①近年民俗学、民间文学的实践性问题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关于民俗学“实践”的讨论从偶见到频繁,向“实践研究范式”的转向成为当下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新趋势。②
民间传说是民间文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被看作是“人民创作的与一定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地方古迹、自然风物、社会习惯有关的故事”。[1]“民间传说,是社会民众‘口传的历史’。”[2]学界对传说特征的论述,一般都强调它的地方性、历史性特征,“传说的创作是以特定的历史事件、特定的历史人物或特定的地方事物为依据的。有些传说往往离开了一般历史事物的凭借便不能称之为什么传说了”。[3]历史性、地方性作为传说的主要特征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但在传说的实践性研究方面,一直以来探讨得并不充分。在学术界对民俗学、民间文学实践问题进行理论探讨的同时,以民间传说的具体案例对民间文学的实践性进行反思和探讨,有益于深入理解民间文学的本质特性。在此方面,陈泳超结合具体的田野调查对传说动力、传说讲述人等的分析提供了较好的例子,③其著作《背过身去的大娘娘——地方民间传说生息的动力学研究》虽非专门探讨传说的实践性问题,但通过对传说演变的动力机制的分析,揭示出地方传说生存、变动的内在因素,正是基于传说实践性的前提。[4]从实践的角度深入挖掘民间传说蕴含的多方面信息,有着独特的意义和价值。本文基于对山西晋南襄汾县赵康镇一带流传的赵氏孤儿传说的田野调查,④着力分析传说在地方民众社会生活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并通过对传说实践性问题的探讨,挖掘传说实践背后的本质及深层意义。
二、赵氏孤儿传说的生活实践表现
具有明显地方性的赵氏孤儿传说在生活实践中有多方面的表现,这些表现或显著或隐微,从民俗研究者最关注的传说讲述和民俗活动的角度看,其实践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讲述作为一种生活实践:无需讲述的传说
讲述一般被认为是传说的一个主要表现形式,也是传说传承、传播的一个主要手段,但是调查中发现,赵氏孤儿传说在赵康镇一带的流传情况并非如此。这一传说虽然在这一带流传久远、妇孺皆知,但并不是一个经常被讲述的故事,当地也没有出现比较知名的民间故事讲述人,传说的讲述情况在当地民众中显得参差不齐。在当地能够比较完整地讲述这一传说的只是个别村民,他们被认为是村落里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也即村落的民俗精英。而对于绝大多数的普通村民来说,即使他们确定自己知道赵氏孤儿的故事,但请他们讲述的时候,却往往讲不出来或者三言两语就讲完了。他们的讲述更像是解释,当研究者作为“陌生人”进入到这个传说语境中并对该传说的情节进行追问时,才能得到当地人解答释疑般的讲述。而对于当地人群来说,传说是无需专门讲述的,它是人尽皆知的地方性知识,是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背景常识。如果需要讲述,那么这种讲述一般不是独立的,常伴随着特殊的行为实践。赵氏孤儿传说的这种讲述情况,陈泳超教授在论述他对山西洪洞羊獬村一带娥皇女英传说的调查研究时也曾提到过。娥皇女英传说和赵氏孤儿传说同属晋南文化圈,可见讲述中的这种情况并非个别案例。
因此,赵氏孤儿传说在赵康镇一带的流传,表现出来的是无需讲述的状态。它不是被讲述的传说,而是在日常生活中被实践的传说。当然,传说讲述本身不仅是一种口承叙事,也是一种行为方式。如果把讲述也看作一种生活实践的话,那么讲述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显性的实践,而其他表现形式是隐性的实践。这样的话,赵氏孤儿传说的表现是以隐性形式为主的。
(二)讲述之外的生活实践
传说具有地方性、实践性特征,与一定群体的日常生活、民俗活动密切相关,如前文所述,传说是被实践的,讲述之外的生活实践是其主要的表现形式。因此,与生活剥离开来对传说文本进行讨论分析,并由此探索传说意义的做法无疑是片面的,毕竟以文字或口头形式表现的文本只是传说文本的表象,它内在的价值在于传说在生活实践中的具体表现以及传达的意义。晋南的赵氏孤儿传说在生活实践中的表现突出地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1.地方信仰中的祖先祭祀与村落庙会
赵氏孤儿传说作为赵康镇一带民众集体的文化记忆,之所以能够在今天的生活中依然发挥深刻的影响,根本原因在于它与民众的宗教信仰紧密结合。当传说精神内化为地方民众的精神信仰,传说便具有了长久的稳定的生命力。传统社会由于生产生活方式相对稳定,与这种信仰伴随的民俗活动也会长期延续下来,直到今天仍能够看到。田野调查发现,目前能够看到的与赵氏孤儿传说相关的信仰活动主要有两大方面:一是赵氏家族的祖先祭祀活动,二是依托赵大夫庙会的赵大夫信仰活动。
(1)祖先祭祀
中国古代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家族社会素有慎终追远的文化传统。在灵魂不灭观念盛行的时代,人们祭祀祖先尚且有得到祖先庇佑的希冀,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祭祀祖先的目的也在发生变化。祭祀祖先不仅是为了感念先人和获得祖先的庇佑,更是为了团结当下的家族成员,达到“亲亲”的目的。家族成员共同参与祭祀祖先活动,不仅可以增强自身的归属感,而且能够团结、和睦族人,巩固和增强家族力量。
据当地民众说,民国以前赵康镇一带赵姓村民很多,当地有许多以“赵”姓命名的村落,如赵康、北赵、南赵、大赵、小赵、赵雄、赵豹等。随着人口变迁,如今这些村落的赵姓村民逐渐减少,很多已发展为杂姓村。目前赵姓村民较集中的是东汾阳村和赵雄村,共有赵姓村民1000多人,他们中大多数认为自己是晋国赵氏的后代,对先秦晋国赵氏家族祖先有着比较一致的认同。新中国成立之前,赵康镇一带数量巨大的赵姓村民在各自村落有自身的宗族组织,随着时代变迁,目前赵氏宗族的管理已经非常松散,宗族组织功能近乎消失。即便如此,距离赵大夫墓地较近的赵雄村和东汾阳村,一直保持着清明节上坟祭祀赵盾的习俗,祖先祭祀活动延续至今。
(2)赵大夫庙会
庙会是地方社会民俗文化的集中展现之处,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文化历史,是地方民俗文化传统的标志性民俗事项。赵康镇的赵大夫庙会是为了祭祀、纪念春秋时期晋国的大夫赵盾而举行的庙会。“庙会,一般而言,是指围绕着庙宇所发生的群体性信仰活动。”[5]赵大夫庙会正是因赵大夫(赵盾)庙而起。在西汾阳村南不到1公里的田地里有赵盾墓,墓西北处大约五六百米的地方,曾经有一个很大的赵大夫庙。在民国以前,赵大夫庙占地40亩,其中10亩是庙宇建筑用地,30亩是庙田,有内墙把庙宇和庙田隔开,又有外墙把庙田和外面隔开。庙宇建筑是四合院建筑,进入庙门会看到一个戏台,正对着庙宇正殿。正殿房屋高大,里面供奉着赵大夫和其他神灵。赵大夫庙在抗日战争时期被日本人炸毁,现在仅有庙基址尚存。
据村民讲,民国之前的赵大夫庙会是太平县开春后的第一个大庙会,远近皆知,逢会期间,商贩云集,热闹非凡。当时赵大夫庙会由西汾阳、赵雄、赵豹、北王4个村子联合举办,庙会就在赵大夫庙旁内墙和外墙之间的庙田里进行。庙会期间有剧团来唱戏,持续将近一个月。庙会上有隆重的祭祀仪式和热闹的社火表演,北王村的“台”(即台阁,一种表演),赵豹村的竹马,西汾阳村的社火(扮演成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物骑马表演)和拐子(即高跷),赵雄村的花腔鼓,都是每年庙会的例行表演。村民们在庙会当天敲锣打鼓,带着香火和祭品,先到赵大夫庙里举行献祭仪式,然后才开始唱戏。赵大夫庙被毁后,庙会的具体地址屡有变更,但是庙会活动一直保留了下来。⑤
现在赵大夫庙会的时间在每年阴历的二月十四、十五、十六三天,在赵大夫庙会中依然要举行传统的祭祀仪式。祭祀的过程大致如下:在庙会的前一天(阴历二月十三)西汾阳村召集本村的锣鼓队(组织一部分村干部或村民,敲锣打鼓),到赵大夫庙基址处烧香、放鞭炮、进行献祭。在这个过程中,听从神婆的指挥,把象征赵大夫神的香火带到村里戏台处。在戏台对面临时搭建布棚供奉赵大夫神位。棚里面摆放宽大的桌案,中间供奉赵大夫神位,神位前面摆满祭品,供桌前方是上香用的香炉。阴历二月十五上午,在司仪的组织下,一部分村民(现在一般是36岁村民)跪拜、烧纸、上香、燃放鞭炮,完成祭祀仪式后,戏台上开始表演活动。庙会结束后还有送神仪式。
赵大夫(赵盾)是赵康镇一带赵氏孤儿传说中的重要人物,这是赵氏孤儿传说地方性的一个突出表现。赵盾的忠诚敬业和赵氏家族的功业在赵康镇一带的传说讲述中是一个重要情节,因而赵大夫庙会的举办和延续,是传说在民众生活中的鲜活体现,也是以实践形式进行的传说讲述。
“传说就是为了信奉而存在,并由历代的信徒保存传诵到了今天。”[6]赵大夫庙会长期以来能够传承不衰,甚至在特殊政治环境的年代里也能让民众自发地坚持下来,其背后强大的精神动力在于地方信仰的支撑。“庙的实质同样在于偶像的供奉,显示出一定时代一定人群共同的文化理念。”[5]赵大夫在赵康镇一带的村落里不仅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也是民众信仰的地方神灵。当地民众信仰赵盾不仅是敬重他的才能和忠诚,还相信其精神力量具备强大的超自然神力,可以保佑自己平安健康。有的村民在纸上写上“赵大夫牌位”字样贴于家中墙上,在岁时节日中进行献祭。由此可见,赵氏孤儿传说作为当地民众的集体记忆,通过神灵信仰的形式表现出来,并借助庙会活动进行着传承实践。从历史记忆到精神信仰再到社会秩序,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内在关系链条。
2.传说在民间戏曲中的艺术化演绎
民间传说借助民间戏曲的形式表现,既是一种艺术的讲述,也是保存集体记忆或表达群体情感的重要形式。赵氏孤儿传说在赵康镇一带不仅以口头讲述的形式流传,在民间艺术尤其是戏曲中也有鲜明的体现,其中最为突出的是蒲剧《赵氏孤儿》。
山西戏曲渊源流长,素有“中国戏曲的摇篮”之美誉。早在金元时期,山西的戏曲演出活动已经兴盛,剧作家辈出。到明清时期,戏剧演出达到鼎盛,今天在山西晋南一带还能看到大量明清时期的戏曲文物,可见当时民间戏曲演出盛况。在赵康镇一带,蒲剧是最受民众欢迎的剧种,岁时节日的庙会中常有蒲剧演出,村民在重要的人生仪礼场合也会请蒲剧班子来唱戏。《赵氏孤儿》是晋南蒲剧的重要剧目之一,也是赵康镇一带民众最为熟悉的剧目之一。在庙会和当地人婚丧嫁娶的人生仪礼活动中,凡是有戏曲演出的,《赵氏孤儿》都是经典剧目,出现频率很高。且不说东汾阳村、赵雄村每年的庙会和“过三十六”活动都会把《赵氏孤儿》作为必选的剧目来演出,在赵康镇、汾城镇的其他村落,《赵氏孤儿》的演出也非常频繁。以2017年和2018年的调查为例,仅在赵康镇、汾城镇“过三十六”活动中,演出《赵氏孤儿》的就有东汾阳村、赵雄村、北赵村、南赵村、义西毛村、汾阳岭村、西中黄村、南高腴村、北高腴村、三公村、尉村等不下十几个村落,实际演出此剧的村落远不止于此。
由于赵康镇一带的民众把赵氏孤儿传说当作当地的历史来看,这样《赵氏孤儿》戏剧的演出就具有了非同一般的意义。戏剧表演是另一种形式的讲述,但却更加生动形象,更具有感染力。戏剧中丰富的人物语言、动作、表情,曲折的情节、淋漓尽致的感情表达都给观众带来不同于口头讲述的新体验,把民众带入历史的语境中,使古今在瞬间联系在一起。对于东汾阳村、赵雄村的赵氏村民来说,几乎年年必演的《赵氏孤儿》有着更为特殊的意义。由于有着宗族灭亡、360余口赵氏族人被杀的惨痛情节,赵氏孤儿传说被看作是一个悲剧,所以在西汾阳村传统的赵大夫庙会上,从古到今流传下来的一个禁忌就是不能演出《赵氏孤儿》。如果演,也只能演小段戏《朝房》,表现忠臣赵盾对奸臣屠岸贾的斥骂痛打,酣畅淋漓,大快人心。但在后起的东汾阳村庙会和赵雄村庙会上,却刻意反其道而行之,其所要表达的是对当代村民的教育意义。在他们看来,赵氏孤儿传说是赵氏祖先的历史,也是村落的历史,是进行道德教育的好素材。看戏的过程,是回溯历史,是对自我的重新认知,也是对民众的教育。传说在戏曲演出这样艺术化的生活实践中被突出地展现出来。
3.传说影响下的婚姻禁忌与村际关系
赵氏孤儿传说在赵康镇一带并不是一个茶余饭后闲谈的民间故事,它对当地的婚姻禁忌和村际关系有着长期的影响,是传说在民众生活实践中的又一个鲜明体现。
首先是婚姻禁忌。在当代赵康镇一带流传的赵氏孤儿传说中,永固乡的永固村是春秋时期晋国屠岸贾家族的居住地。屠岸贾灭了赵氏家族,和赵氏结下了深仇大恨。后来赵氏孤儿复仇,也消灭了屠岸贾家族。屠岸家为了求生,一部分改作“原”姓,今天永固村的“原”姓村民中有一部分被认为是屠岸贾的后代。由于有着这样的历史关系,赵康镇一带的赵氏家族与永固村便很少来往,并形成了一个民俗禁忌,即赵姓村民和永固的原姓村民不能通婚。这个禁忌是否如村民所言从赵氏孤儿事件之后就已形成,已经不得而知,但东汾阳村附近的几个村落乃至整个赵康镇以及永固村都熟知这个禁忌,赵姓村民普遍认为这是很久以前老祖先留下来的规矩,不能违背,并表示从未听过民国以前赵姓和原姓通婚的例子。在主要依靠媒人撮合缔结婚姻的农村里,当地媒婆对这个禁忌都了然于心,不会轻易说合有违此禁忌的婚姻。更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禁忌在村落中的扩张。原本是赵姓村民与原姓村民不通婚,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扩大为东汾阳村、赵雄村等多个村落与永固村不通婚。由于没有姻亲关系,村落之间的交往很少。从中可以看到,一个遥远的历史事件(无论学界如何质疑它的真实性),却鲜明地映射在当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并在长期的恪守规则中实践和传承。
其次是村际关系。由于赵氏孤儿传说,传说流传核心区域的东汾阳村、赵雄村、西汾阳村,与当地村民认为曾为赵氏宗族性村落的赵豹、赵康、大赵、小赵、南赵、北赵等联系密切,这些有着地缘或血缘关系的村落彼此之间交往很多。即使现在看来这些村落大都变成杂姓村而不再是宗族性村落,过去的宗族性组织也已荡然无存,但是这些同处一个地域文化圈又曾有着宗族关系或姻亲关系的村落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已经形成了相同的人生仪礼、岁时节日活动和日常生活习俗,共同的文化习俗使这些村落的村际关系比较和谐,村际之间通婚现象长盛不衰,经济、文化方面的交往也很频繁。除此,东汾阳等村与隶属汾城镇的程公村、三公村、太常村、尉村、西中黄村、北中黄村等的交往也比较多,村际关系较为和谐,而这些村落都是赵氏孤儿传说流传的中心区域。
身体实践、纪念仪式、婚姻禁忌、村际关系是村落文化传承中重要的传授行为,在传说的传承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因为非正式口述史的生产,既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描述人类行为的基本活动,也是全部社会记忆的一个特征。”并且,“有关过去的意象和有关过去的记忆知识,是通过(或多或少是仪式性的)操演来传达和维持的”。[7〗所以,无论是赵大夫庙会、赵氏祭祖还是民间戏曲表演,多种表现形式都是地方民众对其文化记忆的演述,这种实践,与传说讲述有着一致的精神内涵。地方民众正是通过日常生活中多样化的民俗实践,让传说成为维持集体记忆、强化文化认同的重要手段。
三、再论传说的实践性及其意义
(一)基于历史性的实践性
在晋南赵康镇一带的许多村民看来,赵氏孤儿传说不是一个虚构的故事,而是历史上曾经发生的真实事件。因为有着这样的思想认识和情感真实,传说才会在民众日常生活的诸多行为中体现出来,在民众日常生活中被年复一年、长期不懈地践行。因此在赵康镇一带的村落里,即使对赵氏孤儿传说了解较多的讲述人,他们在讲述传说时也不像一般民间故事传承人那样有意识地安排叙事结构,注意故事讲述的语言和技巧,努力使故事情节曲折引人等。他们的讲述没有技巧性,故事内容显得凌乱而散漫,讲述只是一种陈述,因为对于他们来说,这种讲述是当作历史来讲的。所以这一带的赵氏孤儿传说并不是用来讲述的文艺作品,也不是茶余饭后用来消遣的口头故事,而是一种生活背景,是当地村民日常生活场域的构成要素,也可以说是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从赵氏孤儿传说的这种情况可以看到,当地村民对于传说的生活实践是基于历史性的前提,无论这种历史是真实的历史还是集体的建构,只要他们从情感上认为是真实的,就达成了认同,在认同的支配下,实践成为自然而然的行为。这样,历史性成为实践性的基本前提,地方民众对历史的认同是他们进行民俗实践的先决条件。传说的实践性和历史性相互交融,形成默契,共同建构并延续着这种精神认同和生活形态。
(二)实践语境下“传说”概念的反思
调查中发现,在地方民众的看法中,“传说”是虚构的故事,而“故事”是“过去的事”,包含有“可能是真实的历史”之意,因此,他们更习惯于用“故事”这个词来指代赵氏孤儿的历史,而很少用“传说”。学术上习惯使用的“传说”概念在实际田野调查中遭受了认识偏差带来的尴尬。如果抱有“传说是虚构的故事”这种先入为主的学术观念来认识“赵氏孤儿传说”在这一带村落里的实际情况,就让它变成了一个伪命题。显然,赵氏孤儿传说是学者认知中的传说,而不是村民的认知,他们更愿意接受“故事”这个概念。不过这里的“故事”也不是民俗学上的“故事”概念。当然,从学术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且不说传说的真实性如何,神话、传说、故事等作为现代学术话语体系中划分出来的概念,和古代已经有很大不同。“在我国历代民间社会,人们对神话、传说、故事这些体裁并无细分,人们从来都是笼统地称为‘讲故事’,或者根据各地的习惯叫法,称之为‘讲瞎话’‘讲经’‘摆龙门阵’等等。”[8]即使在当代的民间社会,情形依然如此。在调查中,笔者真切地感受到,“故事”是民间村落社会普遍接受的说法,它是对民间村落社会里神话、历史、传说、故事等多种民间叙事的统称,而“传说”是很少使用的概念。放在地方民众生活实践的语境中,传说已经不是我们所认为的“传说”,对于传说性质和特征的界定,应该放在传说传承主体——地方民众的生活实践中重新考量。因此,超越学术话语权所带来的片面认识,“把被精英主义操控的民间体裁解放出来,给予其生活化的定义,赋予史料全新的学术意义”,[9]无疑是极具意义的。在具体的实践语境下反思“传说”概念,对于重新理解传说的范畴和内涵有着重要的意义。
(三)传说的实践性及其意义
口头讲述一般被认为是传说传承最基本的方式,也是传说的一个重要特征。但如上文所述,赵康镇一带流传的赵氏孤儿传说在口头讲述之外,还具有强烈的实践性特征。它在长期的流传中伴随着多样化的生活实践融入当地民众的精神信仰和社会关系,成为地方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反作用于地方民众的文化发展和社会生活。因此,基于田野调查的实际情况和对赵氏孤儿传说性质的分析,笔者认为传说并不仅仅依赖口头讲述进行传承,在口头讲述之外,生活实践是其最重要的传承方式,应当给予关注和重视。因为在民众现实的日常生活里,作为口头传统的民间传说,讲述只是其最直观最简单的传承方式,当它融入日常生活的具体实践中,成为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才真正开始对生活世界的意义进行建构,从而发挥其认同、规训的社会功能,进而影响着地方人群的思想观念乃至行为方式。
实践性特征对于深入了解传说的精神内涵和深层价值具有重要意义。“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10]文化是人自己编织的意义之网,文化构成群体的信仰观念和意识体系,并形成一套规范行为方式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种基于文化认同的群体意识形态和行为方式最基本的意义在于主体对自我的认知。因为人们对自我真正的领会,主要是依靠与客体世界及其他人的实践性参与活动而实现的,通过这些具有反思性特征的实践活动,人们形成了对自我的认识和塑造。换句话说,人对自我的认知是通过日常生活的实践来把握的,集体的认知亦是如此。赵氏孤儿传说所表达的精神内涵、群体认知和文化认同,是地方民众通过长期的日常生活展现出来的,它们是被不断实践的民俗生活的一部分。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中,地方民众构建起对自我的认知和对集体的文化认同,传说也因此在地方民众用各种各样彼此联系的文化事象构建的有机社会生活整体中成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四、结语
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认为,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民族文化是自我认知的边界。同一共同体的成员,可以在主观上想象、确认与他族的边界,这种边界并不一定是一个有形的空间界域,而是更多地表现为主观上的文化特质。[11]传说是地方民众建构其精神世界的要素之一,多样化的外在实践和内在精神的结合,才是传说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事象的全部表现。它是地方民众现实生活整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代表了他们的一种生活秩序。若从历史渊源上考察,作为文化记忆的赵氏孤儿传说,是地方民众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进行文化选择和文化建构的结果。这种建构不是一时一地一次完成的,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也是文化不断再生产的过程。它在长期的传承过程中,既是地方民众文化认同的鲜明表象,也塑造着地方的文化传统。同时,地方文化传统又反作用于地方民众的现实生活,依托村落人群、地方风物,以行为实践的方式来延续或强化地方文化认同。这样,以传说为表征,地方社会的文化传统与文化认同之间互相形塑的内在关系,以及地方文化发展中动态循环的传承机制得以揭示,显示出传说实践性特征研究更深层次的意义。因此,传说在日常生活中的民俗实践表现,是我们把握传说本质的关键,从这一角度出发,才能看清传说在构成生活整体秩序中的意义和隐藏在生活表象之下的精神内涵。
注释:
① 可参阅:万建中.新编民间文学概论[M].上海文艺出版社,2011;万建中.从文学文本到文学生活:现代民间文学学术转向[J].西北民族研究,2018(4):134-141;万建中.现代民间文学体裁学术史建构的可能高度与方略[J].西北民族研究,2018(1):155-161、130.
② 主要研究成果有:周星.民俗主义、学科反思与民俗学的实践性[J].民俗研究,2016(3)5-14、158;尹虎彬.从“科学的民俗研究”到“实践的民俗学”[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17(3):11-17;王杰文.“实践民俗学”的“实践论”批评[J].民俗研究,2018(3):15-25、157;(日)福田亚细男等著,彭伟文译.民俗学的实践问题[J].民间文化论坛,2018(3):57-64;吕微.两种自由意志的实践民俗学——民俗学的知识谱系与概念间逻辑[J].民俗研究,2018(6):5-13、154;萧放,鞠熙.实践民俗学:从理论到乡村研究[J].民俗研究,2019(1):28-42、156;李向振.重回叙事传统:当代民俗研究的生活实践转向[J].民俗研究,2019(1):43-57、156-157;尹虎彬.回归实践主体的今日民俗学[J].民族文学研究,2019(5):66-72;王杰文.“实践”与“实践民俗学”[J].民俗研究,2019(6):5-15、157;等。
③ 可参阅:陈泳超.地方传说的生命树——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身世传说为例[J].民族艺术,2014(6):101-110;陈泳超.规范传说——民俗精英的文艺理论与实践[J].文化遗产,2014(6):87-96、158;陈泳超.民间传说演变的动力学机制——以洪洞县“接姑姑迎娘娘”文化圈内传说为中心[J].文史哲,2010(2):60-73;陈泳超.作为地方话语的民间传说[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94-103;等。
④ 此调研内容为北京师范大学“百村社会治理项目”子课题“地方传说与村落社会治理”的一部分,调查组由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民俗学专业师生组成,于2017-2019年在山西襄汾县、新绛县进行了多次田野调查。
⑤ 关于赵大夫庙及庙会历史,主要来自笔者2017、2018年在山西赵康镇西汾阳村的访谈资料。